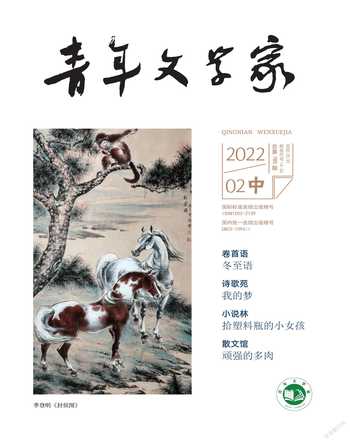论张岱《陶庵梦忆》中的超越意识
张嘉欣
张岱经历了明、清朝代更迭,披发入山,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亡国丧家的故国感怀与抑制不住的湖山兴亡之思推动着他在创作上突破了“独抒性灵”的苑囿。他的作品有着可触摸的生活实感,但他同时也给笔下的明代社会生活风俗画卷建立起了一个超越性的背景,试图在变化中寻找不变,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和永恒,摆脱现实的羁绊,寻求精神上的自由愉悦。本文拟从《陶庵梦忆》中超越意识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展开,分析张岱如何践履庄学的超越精神,以艺术化方式安顿苦难人生。
一、遥思往事:超越意识的时间维度
《陶庵梦忆》成书于明亡之后,刊行于乾隆四十年,序文中张岱自述:“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饥饿之余,好弄笔墨……遥思往事,忆即书之。”由此可知,《陶庵梦忆》是张岱晚年回忆往昔亲身经历过的繁华旧事所作,具有回忆录的性质。这赋予《陶庵梦忆》中所述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图景一种深邃的历史感。他以历史的维度去打量笔下的茶楼、酒肆、说书、演戏、山水风景,这些变动不居的昔日生活场景就悬浮起來,与现实生活有了距离。遥远的历史感是张岱《陶庵梦忆》中超越意识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借此契机他可以摆脱深陷于“现在”的各种繁杂细节之中得到的瞬间感受、片段思想,获得相对整体性的感受和认知。
与过去隔着距离的张岱对昔日王公贵族沉溺享乐的淫靡生活进行了反思。《陶庵梦忆·序》中,张岱写道:“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在《陶庵梦忆》中,张岱的情感往往十分克制,只有在这篇自序中,才完全袒露出反思过往的创作意图以及情感基调,这句话亦可成为《陶庵梦忆》诸篇小品的阅读导引。在《二十四桥风月》中,张岱写族弟向其炫耀狎妓之乐“弟今日之乐,不减王公”,他以“余亦大噱”回应,看似不带价值判断的直接描述,实则暗含了冷峻的反思的情绪。张岱在《斗鸡社》中回忆自己年轻时曾爱好斗鸡,“有言唐玄宗以酉年酉月生,好斗鸡而亡其国,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他将自我生活方式与国家命运相联系,以小见大,将明亡的根本原因归结到王公贵族贪图享乐的生活方式上,由此可以感知张岱笔端的深哀剧痛。
对贵族的失望,对过去生活的忏悔,以及晚年跌落社会底层衣食不继的生活经历,使得张岱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底层群体,张岱看待底层的态度也由此发生了转变。从张岱在《秦淮河房》以及《二十四桥风月》中对烟花之地的详细描摹来看,张岱年轻时好享乐,经常出入风月场所,此时的他对底层女性的态度如其族弟一般“颐指气使,任意拣择”。而晚年的张岱看待底层妓女的眼光带着悲悯和担忧的色彩,写她们“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以及待客一天结束后无人问津者“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的悲惨遭遇。张岱在自我立场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对于社会底层的悲悯之心,打破了时代与自我认识的局限,这种认识上的提升和超越是“梦忆”的历史维度赋予的。历史意识也使得张岱能够超越认识上的偏狭,对各色各样的人都抱有同情和理解,尊重人的独特性。张岱散文中多人物小品,出现在他的小品中的人物可以没有身份地位,但不能没有真性情。在《陶庵梦忆》中,张岱表现出对率性而为却有真情至性的人的宽容,《祁止祥癖》里他提出了自己的交友标准:“人无癖不可与交也,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宋代林逋爱好游历西湖,与当时大部分文人不同,他隐居西湖孤山,终身不仕不娶,与梅、鹤作伴,正是张岱喜爱的有癖之人。还有《金乳生花草》中癖于花草的金乳生,《朱楚生》中癖于戏,为情而死的朱楚生等人,张岱对他们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正是由于张岱具有历史维度的超越眼光,他才能对人的不同性情抱有充分理解,所以现代读者才有了解明末清初时期人生百态的契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由此而更加丰富。
二、虚化的梦境:超越意识的空间维度
《陶庵梦忆·序》中,张岱把过往五十余年的人生经历视为繁华靡丽的梦境:“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但这不是为觉悟之后对往日的忘却,而是为珍视和保留做铺垫。他说:“今当黍熟黄粱,车旋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可知张岱所言“今当黍熟黄粱,车旋蚁穴”,是梦醒之时不可挽留的遗憾,促使他以生花妙笔保留过往的点点滴滴,“翻用自喜”,作为留存在精神中的“故人故土”,以慰平生。虚化的梦境是张岱化解现实国破家亡之怆痛的一种方式,将美好的过往封装于梦境,承载于文字,便可随时流连忘返,这是张岱的超越意识在空间维度的徐徐延展。
常常出现在张岱回忆中的一处名胜是西湖,他说:“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然而,张岱痴爱的是梦中的西湖,而非现实中的西湖,他阔别西湖多年后故地重游,却发现现实中的西湖与记忆中的有所不同,张岱不愿接受,致力于“保我梦中之西湖”,记忆中的梦境,成为张岱安顿心灵的一种方式。在《湖心亭看雪》中,张岱写他孤身一人去往湖心亭观雪,触目所及皆是白茫茫一片,广阔孤寂的天与水之间,好像只有“我”的存在,“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张岱似乎是把西湖扩展为无穷无尽的空间,亭与人在其中渺小如微尘,与其说这是对游历西湖情景的回忆,不如说是超越意识在想象空间中的外化。这样的超越方式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张岱对此有明确的认知。因而“忆梦”只是张岱的超越意识在空间延展的一个层次。在“忆梦”的基础上,张岱试图优化这种初步化解苦难的方式,让自己的精神再度升腾飞越起来,以摆脱沉重现实的负累。从这个角度读解《陶庵梦忆》,就会发觉现实中的场景也被虚化成了梦境,有着“梦中说梦”的意味。张岱已悟“五十年来,总成一梦”,则将梦醒,梦醒之际“犹事雕虫”,又开始沉入新的梦境。他痛斥自己对梦境的沉溺:“痴人前不得说梦矣。”张岱不仅自嘲为“梦呓”的痴人,而且反省自身痴性的由来:“因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由此看来,他将美好的过往虚化为梦境以淡化失落的痛苦,再通过文字转化为精神性的存在,这是对现实苦痛的一次文学性的超越。更进一步,他不断地自嘲自省,对已成梦境的美好过往和自身坚固的名心慧业加以荡涤扫除,以使过往和现实无累于心,这是对现实苦痛的一次哲学性的超越。
张岱把现实世界当作梦境,在梦中回忆过去,不再眷恋外界的功名利禄,而是求诸内心的自由。在《湖心亭看雪》中张岱表现的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比《日月湖》中表现得更为直接。《日月湖》除了写景,还写了贺知章归隐之事。贺知章想飞升成仙,却又不能忘记俗世名利,而张岱对外物的态度更为通达,“平泉木石,多暮楚朝秦”,外物不傍身,转瞬即逝,甚至于危害自身。这缘于他吸收了庄子的思想精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庄子认为即使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也常常被名利所累,所以要去除追求名利的心,使内心达到空明的状态。张岱对现实的疏离也体现在他对现实冷静观照的态度上,他虽好物,却可以不为外物拘束,通脱于物色之外,他好市井生活、俗人俗物,但也不沉溺其中。可以说,张岱试图超越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他的内心渴求借助庄学的智慧,寻求不变的恒久的存在。
三、清梦甚惬:超越意识的实现方式
张岱的人生态度展示在《朱文懿家桂》中,他赞叹道:“樗栎以不材终其天年,其得力全在弃也。”既然过往如梦,现实如梦,索性自然无为,方能终其天年。从张岱晚年致力于文章著述来看,他的“无为”,只是追求心境的无欲无求,这样洒脱自由的心境是张岱理想的状态,现实中的他却“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张岱晚年的心态是矛盾和复杂的,在破碎的现实中,他寄情于记忆中的山水人文,从而达到对现实苦痛的文学性超越。他接受了庄学“人生如梦”的思想,企图给自己的超越意识奠定扎实的哲学根基,让自己的心摆脱现实的羁绊。他一方面想超越短暂、易变、有限的现实人生,彻悟生命真谛,追求无限与永恒,他笔下广阔浩渺的西湖就象征着这种追求;另一方面,他详尽描绘记忆中繁华热闹的西湖胜景,沉湎于世间风俗与人生百态。
在對待现实的态度上,张岱受到庄子的启发。他自号“蝶庵”,自称“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纡徐,帷吾旧梦是保”,此处是对庄周梦蝶典故和《庄子·大宗师》中“成然寐,蘧然觉”一句的化用,庄周以物化泯灭物与我的界限,由此委运乘化,趋向内心无所系缚的逍遥之境。张岱的超越意识虽然受到庄子哲学的启发,但是落实到人生实践,他偏离了庄周泯然与物同体的超越理想,转而以艺术的方式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胡益民在《张岱评传》中认为,张岱散文“将审美主体的情感意绪升华到通常的山水游记所难企及的全新境界”,这种全新境界就是张岱生发出的关于宇宙人生的哲思。他试图以超越个体狭隘视野的历史意识及整体性思维,吸收庄学的智慧,排遣亡国丧家之痛,让精神从现实的困境中升腾起来,达至自由的境界。在《西湖七月半》中,张岱写道:“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这与苏轼《赤壁赋》中“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的飘逸洒脱有异曲同工之妙。苏轼面对困境的心态给了张岱很大的启发,在张岱看来,与广阔无垠的宇宙相比,世间英雄豪杰、乱世纷争只是沧海一粟,只有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与惬意清梦才是寄托心灵的处所。明王朝昔日鼎盛已成过往,人世间繁华就如赏月时的热闹一样短暂易散,人生纷扰与诸多痛彻心扉的痛苦只是天地一瞬,与其困于现实纷扰,不如在宇宙自然中安顿身心,纵情山水,达到内心和谐、圆融的状态。
张岱所惬意的“清梦”,并不只是文学之梦,还包括散发着五彩斑斓的艺术人生之梦。在人生践履上,张岱用艺术人生的方式来落实庄子的“道”。张岱喜爱自然山水之美,对于西湖诸景如数家珍,王雨谦说他:“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这些景物风光成为张岱的审美对象及心灵栖居处所。他把人生融入艺术与美中去,把庄子哲学转化为现实人生体验到的艺术精神。张岱非常欣赏专注于艺术创造的人,在多篇小品中描写他们从事艺术活动时浑然忘我的状态,如“虽冰龟其手,日焦其额,不顾也”的金乳生,还有被张岱称赞为“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的濮仲谦,他们的作品都以艺术性的方式呈现出美的存在,他们沉浸在技艺的创造中,心与物的对立消解了。更进一步,当他们达到心手合一的状态,也就是张岱在《吴中绝技》中说的“盖技也而进乎道矣”,技术对心的制约也取消了,他们的精神由此感到自由与愉悦。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认为:“艺术性的效用和享受,正是庖丁‘所好者道也’的具体内容。”张岱对他们在技艺活动中达到精神无所系缚的自由境界心驰神往,自身也由此常常沉浸在艺术世界。在《绍兴琴派》中,张岱不乏得意地讲述自己精妙的琴技:“余曾与本吾……取琴四张弹之,如出一手,听者駴服。”张岱爱好艺术,早年的他借助艺术活动获得精神上的享受,晚年的他通过书写回味艺术生活中的精神享受以超越现实人生,缓解精神痛苦。
张岱通过“惬意清梦”,在文学世界中回到过去,留存昔日美好,回味艺术生活;又在“梦中说梦”的反省中,虚化现实,在思想上与现实拉开距离,实现了自我心灵的超越。晚年的他通过写作与艺术的方式寄托自我,顺任自然与时代的变迁,破解人世间各种执着,企慕“南华秋水意”的境界。在《湖心亭看雪》中,张岱独自前往湖心亭,却见两人“铺毡对坐”,张岱借舟子的口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文中的痴人,既是张岱个性的体现,也是他沉醉于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以及艺术美的世界之真实写照。张岱不断在苦痛的现实生活中寻求心灵的超越,文学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越性,才能从琐碎庸常的世俗生活趣味中脱离出来,使人的心灵变得丰赡而自由。
——领悟张岱的“痴”
——以《陶庵梦忆》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