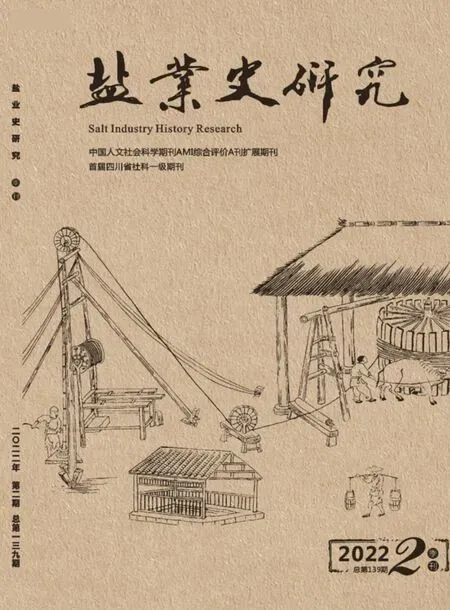元代制盐典籍《熬波图》作者及成书背景新证
王 青
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库馆臣将《熬波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收入《四库全书》之中①陈椿.熬波图[M].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为我们保留下这部珍贵的元代制盐典籍,其学术意义值得充分肯定。与此同时,四库馆臣为熬书撰写“提要”,提出熬书为陈椿一人所撰的观点,致使200多年来学术界一直信从这种错误说法。事实上,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四库提要在熬书作者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疏误,对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吉田寅、郭正忠等先生曾著文分析②吉田寅.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の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1983;郭正忠.略论宋代海盐生产的技术进步:兼考《熬波图》的作者、时代与前身[J].浙江学刊,1985(4);赵慧芝.《熬波图》提要[G]//任继愈.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化学卷(一).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笔者近年也有所讨论③王青.元初制盐典籍《熬波图》之作者问题新考[G]//王青.环境考古与盐业考古探索.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但仍未彻底纠正学界的传统观点。关于熬书的成书背景,四库提要仅言及“亦楼璹《耕织图》、曾之谨《农器谱》之流亚也”,吉田寅、郭正忠两位则从盐业史角度做了更多分析。现在,随着相关史料的增加和认识的不断深入,对这两个问题实有必要再做进一步辨析,以下分别予以专门讨论。
一、《熬波图》作者问题
关于熬书作者这一基本问题,最基础的史料主要有两条,均出自目前所知的熬书最早版本四库本,分别是卷首陈椿撰写的“熬波图序”,以及四库馆臣撰写的熬书“提要”,现将两篇全文抄录如下:
浙之西、华亭东百里,实为下砂。滨大海,枕黄浦,距大塘,襟带吴松、扬子二江,直走东南,皆斥卤之地。煮海作盐,其来尚矣,宋建炎中始立盐监。地有瞿氏、唐氏之祖,为监场、为提干者,至元丙子,又为土著相副、管勾官(皆无其任者也)。提干讳守仁(号乐山),弟守义(号鹤山),《诗》《礼》传家,襟怀慷慨,二公行义,表表可仪。而鹤山尤为温克,端有古人风度。辅圣朝开海道,策上勋膺宣命,授忠显校尉、海道运粮千户。深知煮海渊源、风土异同、法度终始,命工绘为长卷,名曰《熬波图》,将使后人知煎盐之法、工役之劳,而垂于无穷也。惜乎辞世之急。仆曩吏下砂场盐司,暇日访其子讳天禧(号敬斋)于众绿园堂,出示其父所图草卷,披览之余了然在目,如示诸掌。呜呼!信知仁民之心如是,其大乎!抑尝观淮甸陈晔《通州䰞海录》,恨其未详,仅载西亭、丰利、金沙、余庆、石堰五场,安置处所、捎灰、刺溜、澳卤、试莲、煎盐、采薪之大略耳。今观斯图,真可谓得其情、备而详矣。然而浙东竹盘之殊、改法立仓之异,犹未及焉。敬斋慨然属椿而言曰:“成先君之功者子也,子其为我全其帙,而成其美云。”椿辞不获已,敬为略者详之,阙者补之。图几成而敬斋下世。至顺庚午始得大备,行锓诸梓,垂于不朽。上以美鹤山存心之仁、用功之勤,下以表敬斋继志之勇、托付之得人也。有意于爱民者,将有感于斯图,必能出长策以苏民力。于国家之治政,未必无小补云。时元统甲戌三月上巳,天台后学陈椿志。①陈椿.熬波图:熬波图序[M].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3-4.
臣等谨案:《熬波图》,元陈椿撰。椿,天台人,始末未详。此书乃元统中椿为下砂场盐司,因前提干旧图而补成者也。自“各团灶座”,至“起运散盐”,为图四十有七,图各有说,后系以诗。凡晒灰、打卤之方,运薪、试莲之细,纤悉毕具,亦楼璹《耕织图》、曾之谨《农器谱》之流亚也。《序》言地有瞿氏、唐氏,为盐场、提干。又称提干讳守仁,而佚其姓。考《云间(旧)志》,瞿氏实下砂望族,如瞿霆发、瞿电发、瞿震发、瞿时学、瞿时懋、瞿时佐、瞿先知辈,或为提举,或为盐税,几于世任盐官。其地有瞿家港、瞿家路、瞿家园诸名,皆其旧迹。然作是图者不知为谁。至唐氏,则旧志不载,无可考见矣。诸图绘画颇工,《永乐大典》所载已经传摹,尚存矩度。惟原缺五图,世无别本,不可复补。姚广孝等编辑之时,虽校勘粗疏,不应漏落至此,盖原本已佚脱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总篡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②提要[M]//陈椿.熬波图.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1-2.
熬书陈序详细交代了此书的成书过程,四库提要则对熬书作者做了最初的考证,认为是陈椿一人撰成,尽管也指出是“因前提干(守仁)旧图而补成者”。在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的现代研究中,吉田寅首先发现了清嘉庆二十二年《松江府志·田赋志》中所引陈椿此序前部有“地有瞿氏、唐氏。瞿氏之祖……”字样,即在四库本陈序“唐氏”之后另有“瞿氏”二字。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但吉田氏并未以此为重点探究该书作者问题,而是依据清代史料大致推测此书原作者可能是瞿霆发等人。郭正忠则指出,四库提要考证熬书作者为陈椿是错误的,也不是“前提干”“守仁”,郭先生以陈序全文之意得出作者应是“守义”的结论,并推测他可能姓瞿。另外,赵慧芝先生也指出,熬书应是守义和陈椿合著,但对守义此人未做深究③赵慧芝.《熬波图》提要[G]//任继愈.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化学卷(一).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1133.。笔者在研读这些资料和观点基础上,认为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根据陈椿序文,当时浙西华亭县的下砂盐场(场署在今上海浦东新区新场镇)有瞿姓和唐姓两大豪户,其中守义在至元丙子(1276)前后出任忠显校尉和海道运粮千户,因他“深知煮海渊源、风土异同、法度终始”①陈椿.熬波图:熬波图序[M].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3-4.,故出于“使后人知煎盐之法、工役之劳,而垂于无穷”②陈椿.熬波图:熬波图序[M].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3-4.的目的,命画工绘制了《熬波图》长卷,使煮盐过程“得其情、备其详”③陈椿.熬波图:熬波图序[M].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3-4.。守义辞世后,作为下砂场盐司官吏的陈椿(天台人)在拜访守义之子天禧时得观此图,赞叹之余发现图卷也有不足之处,诸如“浙东竹盘之殊、改法立仓之异,犹未及焉”④陈椿.熬波图:熬波图序[M].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3-4.,天禧遂委托陈椿对此加以补充出版。至顺元年(1330)前后,此书由陈椿定稿成书并开始刻版(天禧此时已离世),到元统二年(1334),此书正式出版面世,陈椿遂作序志之。
从陈序全文可知,熬书的最早撰写者、也是出力最多的应是守义此人,陈椿则是受其子天禧之托做了补充并出力付梓,此书才得以在天禧亡后出版传世。因此,在守义所命画工已无可考的情况下,我们理应将此书作者系于守义和陈椿二人,而非四库全书提要所言只陈椿一人撰成。四库馆臣之所以如此认为,只能如郭正忠先生所言,是未及细读陈序才有此“疏误”。但郭先生认为此书作者只有(瞿)守义一人也有失公允,因为陈椿对本书有“略者详之,阙者补之”之功,并筹划出版之事,所劳不可谓不多,则陈椿理当也是作者之一,以我们今天的著作权意识来看,自应是本书的第二作者。而吉田寅在注意到守义与瞿霆发(字声父)可能并非一人的前提下,仍以雍正版《两浙盐法志》所载瞿霆发之事绩为据,推测熬书作者可能是瞿霆发等人。但仔细对比史料即能发现,《两浙盐法志》等明清地方志所载瞿霆发之为官事绩应在元武宗和仁宗年间,即1308—1313年间,而陈椿序文已载明,守义为官是在元世祖至元年间,比瞿霆发早二三十年,且二人名、字各异,显非一人。因此,吉田寅先生的推测是没有道理的。
吉田氏所以有此推测,主要原因在于守义此人除了陈椿序文外,其它史籍均无记载,其生平始末大都无可考证。但这并不能作为否认守义此人存在的理由,正如我们不能以陈椿“始末未详”为由,否定陈氏本人存在一样。现在看来,史籍之所以不载守义和陈椿,很可能与二人只在地方担任品秩不高的官职有关。由陈序可知,守义担任过忠显校尉和海道运粮千户,陈椿则是在盐司任职的官吏。查《元史》“百官志”“食货志”等史料可知,其中忠显校尉为从六品的武散官之一,海道运粮千户是海道运粮万户府的下辖职官(正五品),下砂场的盐司官吏包括司令、司丞、管勾、典史等,其中前三职分别是从七品、从八品和从九品。明修《元史》向以粗糙闻名,只用一年修成,所收史料较少,推测这可能是正史不载只担任过品秩不高的地方官吏的守义和陈椿之原因。
尽管如此,值得庆幸的是,明清时期两浙一带的地方志仍保存了少量有关陈椿的史料片语。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他(署名“佩弦”)在1927年发表的熬书书评中即指出,在嘉庆版《两浙盐法志·艺文志》收录的元代陈旅撰《运司同知睢阳赵公德政碑记》中,有“属寓士陈椿来征予文纪之”的记载,推断在熬书出版数年后(1335—1340),陈椿仍住在下砂盐场所在的华亭县⑤佩弦.熬波图[J].小说月报,1927(2).。
笔者循此进一步检核相关史料,发现这篇碑记还收于嘉庆版《松江府志·田赋志》①莫晋,纂,宋如林,修.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志辑2:嘉庆松江府志1[M].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645.嘉庆版的《松江府志·田赋志》及下文陈旅撰写的另一篇碑记《李侯德政碑记》,已收入李修生主编文集,参见:李修生.全元文1:卷38[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584-599.中,而更早的记录则见于明万历《重修两浙鹾志》卷二十三,署为“前人”所撰②王圻.重修两浙鹾志:卷23[Z].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49-50.。嘉庆版《松江府志·田赋志》还收录了陈旅撰写的另一篇碑记《李侯德政碑记》,其开头的30多字与熬书陈序开头文字基本相同,为“浙西华亭东百里,为下砂。滨大海,枕黄浦,距大塘,襟带吴松、扬子二江。直走东南,皆斥卤。”③莫晋,纂,宋如林,修.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志辑2:嘉庆松江府志1[M].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644.仅比陈序开头诸字省略4字,重复率极高。此篇提到李侯行善政之举是在至顺二年(1331),而此时熬书已处于完稿刻版之中,至于陈旅撰写碑记的时间就更晚了。陈旅是元朝有名的诗人,在《元史》“儒学传”中有其传,其于元统二年(1334)即熬书正式出版之年出任江浙儒学副提举,4年后回京,1343年去世。可知陈旅撰写这篇碑记很可能是在任副提举期间,因此碑记这30余字应引自熬书陈序。我们从同为陈姓的陈椿、陈旅都有文采并很可能是同龄人,又同为江浙行省的老乡,可推知二人平时应交往甚密,陈旅应看过陈椿最终出版的熬书,遂引用卷首陈序的文字。总之,从这几条史料可知,陈椿本人无疑是实际存在的人物,并且生前与诗人陈旅还有较为密切的交往,甚至还把刚出版的熬书赠予了陈旅等人,至于陈旅回京后熬书是否在京师也有流传,则有待其它史料的发现来验证。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守义的姓氏问题。四库馆臣所见熬书之版本应来自永乐大典本,其陈椿序中只有“地有瞿氏、唐氏之祖……”之语,而于守义等父子三人名前并未署其姓氏,遂认为守义等人已“佚其姓”。但我们从此序全文可知,陈椿本人知晓天禧及其父、伯之姓氏已毋需多言,其无意于隐瞒此三人姓氏也毋需多言,但若序文中只为“地有瞿氏、唐氏之祖……”字样,则读者自不会从全文确知守义父子姓瞿抑或姓唐。而若按上述嘉庆版《松江府志》所引为“地有瞿氏、唐氏。瞿氏之祖……”,则全文通读下来,守义父子姓瞿已一目了然,陈椿无需再多着笔墨在各人名前署“瞿”字。故嘉庆版《松江府志》所引“地有瞿氏、唐氏。瞿氏之祖……”应为陈序原文,只是在后来传刻中脱漏了后一个“瞿氏”。因此,守义姓瞿已可确定,而不是提要所言“其姓无考”。郭正忠先生则在未引述《松江府志》所录陈序文字的前提下,推测守义“大约姓瞿(也可能姓唐)”,理由是守义之子讳天禧,而瞿氏此前名人如瞿霆发、瞿时佑等人名讳首字,或从雨,或从日,与天禧之名讳首字从天,其取名之意相近,所以他认为熬书原作者守义的姓氏为“瞿氏的可能性,大于为唐氏之可能性”④郭正忠.略论宋代海盐生产的技术进步:兼考《熬波图》的作者、时代与前身[J].浙江学刊,1985(4).。郭先生的谨慎推测给笔者以很大启发,而笔者的分析已能使这一推测得到证实。
除了上述以外,如果能确定熬书中哪些内容是瞿守义原作、哪些又是陈椿的补充内容,也是我们论定此书作者的重要基础,但要具体厘清这一点,目前资料尚不具备条件。以下仅能依据熬书四库本及相关资料,对此做些大致推测。根据陈氏序文,已经明了图版部分是瞿守义命画工所绘,则陈椿所作的补充应是针对图版的文字说明部分。但陈氏在序文中只以“敬为略者详之,阙者补之”一语带过,对自己补充的内容并未详细说明。笔者分析目前所见资料,认为至少有三条线索值得注意。
首先,瞿守义在命画工绘制图版之前,应已撰写必要的文字说明。这些图版多达47幅,且每图所占版面很大,这在现存的古代典籍中极为少见,工程不可谓不大。要想使这一工程顺利完成,若瞿氏只有口头表述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必要有较为详细的文字说明,才能使每幅图的表现内容与瞿氏之筹划设计相符。从瞿氏本人以“《诗》《礼》传家”“端有古人风度”“深知煮海渊源、风土异同、法度终始”看,他在“命工绘为长卷”①上海市通志馆.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M].上海:上海通社,1936:1-47.之前已为每幅图版撰写了某种形式的文字说明,此亦自在情理之中。至于是哪种文字说明,是每节的俗语文字还是俗语之后的题诗,抑或两种文字都出自其手,则不好遽断。
其次,根据陈序所言可知,瞿守义最初的草卷中没有提及“浙东竹盘之殊、改法立仓之异”,则成稿中理应有陈椿将这两点补入的内容。“改法立仓之异”应是说团外筑墙和团内设仓的新措施,目的在于防止成盐走私外流,扰乱食盐的官营专卖市场。通读熬书全文,这一新举措应体现在正文之首“各团灶座”节的最后一句“置关立锁,复拨官军,守把巡警”②陈椿.熬波图.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2.,与“改法立仓之异”相符合。此节之后的题诗“东海有大利,斯民不敢争。并海立官舍,兵卫森军营。私鬻官有禁,私鬻官有刑。团厅严且肃,立法无弊生。”③陈椿.熬波图.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2.也是防止成盐走私外流的新措施,也与“改法立仓之异”相符合。因此,此节的最后一句和节后题诗很可能是陈椿补入的。再如,“铁盘模样”一节的最后有“以篾为者,止可用三二日,焚毁继成弃物,则应酬官事而已,终不如铁铸者,可熬烈火蒸炼也”④陈椿.熬波图.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30.一句,明显是对“浙东竹盘之殊”的说明,则可以确定这一句应是陈椿补充加入的。
再次,仔细研读熬书的文字说明会发现,有些言语在内容上并不协调。如“樵斫柴薪”一节中,用百余字详细介绍了煮盐所用柴草的砍斫地点、时间和方法,字数上已经是各节中最多的,却在最后另有“浙西为有官荡,每引工本比浙东减五两”16字。从内容上看,这一句与“樵斫柴薪”并无多少联系,倒与盐政有关。而陈椿当时任下砂场盐司官吏,对盐政应当较为熟悉,故此句很可能是他补进去的。又如“筑垒围墙”节的题诗最后一句为“团门慎出入,北军守其旁”,出现了“北军”二字,北军即指元军,这在当时应是不敬之语。从瞿守义在元初曾协助元军开通运粮海道,并被授予校尉和千户的经历和身份看,瞿氏本人叛宋入元的态度比较积极,是不太可能用“北军”一词的,则很可能这也是陈椿修改加进去的。至于能否以此说明全书47节的题诗都是陈氏本人所作,则不敢断言。另外,熬书以“熬波”为书名应是瞿守义之意,其正文“上卤煎盐”节的题诗中正有“海波顷刻熬出素”⑤陈椿.熬波图.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42.字句,这显然是化用了成语“熬波出素”,也就是为书名由来做的注解,则此节的题诗很可能出自瞿守义之手,但能否以此说明其它各节的题诗都是瞿氏本人所撰,也不好断言。上海通社1936年出版的《熬波图咏》书后跋语曾提出,熬书之俗语文字和题诗都应是陈椿所作①陈椿.熬波图:熬波图序[M].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3-4.。笔者以为,以目前资料显然尚不宜做此论断。
二、成书背景
关于熬书的成书背景,四库提要首先指出是“楼璹《耕织图》、曾之谨《农器谱》之流亚也”,即与宋代《耕织图》和《农器谱》是同类书籍,亦即受到它们的影响。今天看来,这一论断是有道理的。《耕织图》和《农器谱》都属于宋代兴起的图解式记载生产劳作类典籍,其中南宋成书的《农器谱》至今已佚,其详情无法推断。成于南宋初年,流传至今的《耕织图》,据作者楼璹之侄楼钥所述,《耕织图》最初的格式为耕图21幅、织图24幅,共计45幅图版,“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农桑之务,曲尽情状”②楼钥.攻媿集:卷76:跋扬州伯父《耕织图》[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418.。可见其格式为图和诗两部分,这与熬书由图、文、诗三部分组成的格式是相似的。另外,熬书共有47幅图版,比《耕织图》多出2幅图版,推测这很可能也是刻意为之。所以现在可以推断,熬书的成书格式至少应参考了《耕织图》,受到了《耕织图》的启发和影响,才使它们成为宋元时期图解式记载生产劳作类典籍的重要代表。
在现代研究中,吉田寅和郭正忠等先生则从盐业史角度分析了熬书的成书背景,都主张熬书在制盐工序的编写上受到了《通州䰞海录》的影响或触动。郭正忠甚至推断,“守义大约是嫌《通州䰞海录》记述‘未详’,才开始另行绘著其《熬波图》”③郭正忠.略论宋代海盐生产的技术进步:兼考《熬波图》的作者、时代与前身[J].浙江学刊,1985(4).。淮甸人(今江苏淮安及淮阴一带)陈晔所著《通州䰞海录》,《宋史·艺文志》录其书目并记为一卷,原书今已失传,现在对此书内容的了解只有陈椿序中记录的数语:“仅载西亭、丰利、金沙、余庆、石堰五场,安置处所、捎灰、刺溜、澳卤、试莲、煎盐、采薪之大略耳。”④陈椿.熬波图:熬波图序[M].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3-4.郭正忠从陈序所言通州(今江苏南通地区)有5处盐场的数量推测,《通州䰞海录》应成于南宋初年绍兴年间,早于瞿守义最初撰熬书草卷的宋末元初约有150年。基于这一情况,我们从陈序可推知,瞿守义和陈椿二人肯定是研读过《通州䰞海录》此书的,尤其是对“安置处所、捎灰、刺溜、澳卤、试莲、煎盐、采薪”这7道工序已有掌握。而根据现在各家研究,熬书记载的整个制盐工艺流程也与《通州䰞海录》大致相同,只不过工序更为详细一些,如赵慧芝先生曾将熬书的生产流程总结为建场、引潮、摊场、晒灰、淋灰、试卤、输卤、备薪、造盘、熬盐、收盐和散盐12道工序⑤赵慧芝.《熬波图》提要[G]//任继愈.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化学卷(一).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1133.,吉田寅和郭正忠则将之分为9道与10道工序。由此可见,熬书这10道左右的工序应是受到《通州䰞海录》的触动,即陈序所言“恨其未详”,而有意将制盐工序的编写和记录进一步细化,以区别于《通州䰞海录》。如此才成就了我们所看到的这部现存年代最早、记录最详细的海盐生产典籍。所以,郭正忠先生认为《通州䰞海录》是熬书的“某种前身”也是有道理的。
除了上述四库馆臣和吉田寅、郭正忠等人的推论,笔者认为,有关熬书的成书背景还有一种可能性似乎不能排除,就是瞿守义最初之所以撰写熬书,可能也有藉以升官进爵的目的。这一点陈椿在序言中自然不会言明,但从宋末元初王朝更替的特殊背景和瞿守义本人及其家族的特殊情况考虑,还是有可能的。对此,目前所知主要有两方面的线索可稽。
一是此前已有楼璹因进献《耕织图》而仕途升迁的事例。据《宋史·艺文志》记载:“《耕织图》一卷,楼璹撰,高宗阅后即令嘉奖,并敕翰林画院摹之。”①脱脱,等.宋史: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79.尽管楼璹于《宋史》无传,但据其它史料可知②楼钥.攻媿集:卷76:跋扬州伯父《耕织图》[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101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6;陆心源.宋史翼[M].北京:中华书局,1991:214-215.,楼璹是在绍兴三年(1133)任於潜(今属杭州临安区)县令时创作了《耕织图》,不久即献图于宋高宗并蒙嘉奖,两年后即任邵州通判,后又迁福建市舶、三转运判官、扬州知州等职,到绍兴二十六年已累官至右朝仪大夫。其仕途可谓一路高升,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当初进献《耕织图》,正如其侄楼钥所言:“(楼璹)所至多著声绩,实基于此。”③楼钥.攻媿集:卷76:跋扬州伯父《耕织图》[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1018.楼璹的事迹发生在都城临安附近,一时朝野传诵,其周边地区当尤为流传,下砂盐场所在的华亭县距临安约150公里,推测瞿守义对楼璹的升迁故事已早有耳闻。
二是瞿守义个人可能有家族利益的考虑。从熬书陈序及提要可知,瞿氏家族是当时下砂一带的名门望族,像瞿守仁、瞿守义兄弟和瞿霆发、瞿时学父子等人,曾历任监场、提干、提举、盐税等职(任监场、提干当在南宋末年),堪称盐官世家,在当地还置有诸多田产庄园等。这些人尽管未见正史记载,但瞿霆发在正德版《松江府志》、雍正版《两浙盐法志》等明清地方志中有传记,此人应为瞿氏家族中名望最高者,曾官至正三品的两浙都转运盐使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篡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81[M].济南:齐鲁书社,1996:782-783.,但已比瞿守仁、瞿守义兄弟晚了数十年,在这两兄弟之时瞿氏家族应当还未发达,仅为品阶很低的提干等职。而从瞿守义在宋末元初曾辅助元朝开通运粮海道,并被授予校尉和千户来看,他对新王朝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推测这很可能是出于保护家族利益而为。那么可进一步推测,瞿守义撰写《熬波图》一书的目的可能还有仿效楼璹故事进献熬书以加官进爵,从而提高瞿氏家族地位和势力的考虑,只不过因他过早辞世而未能成事罢了。
另据《元史·食货志》记载,两浙盐使司在元统元年的盐额为48万引(每引400斤),又据正德版《松江府志·田赋志》《华亭县志》等载,至元十三年两浙办盐为4.4万余引⑤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篡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81[M].济南:齐鲁书社,1996:494.。即从至元十三年到元统元年(1276—1333)的近60年间,两浙盐使司的办盐定额激增了10倍以上,为此前所未有,对此有研究曾评价道,这种做法“是很荒唐的”⑥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71.。由此也可见元人施政之野蛮,以及元朝为了灭宋和统治全国而对各大盐场课盐之重,造成了大批盐户不堪重负而外逃流亡,乃至揭竿起义。而下砂场又是两浙盐使司所辖各盐场中产量最高的,则可推知包括瞿守仁、瞿守义兄弟在内的盐场官吏,其仕途在催盐日急和时局动荡的情势下也是飘忽不测的。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我们推测瞿守义有可能想借进献熬书以加官进爵,从而保护和提高瞿氏家族的地位与利益。当然,这只是我们从有关史料中找到的两条间接线索,并非确凿证据,因此只能是间接推论,还有待今后发现更多史料来验证。
另外还有一个附带问题,就是《熬波图》书名由来问题。“煮海为盐”和“熬波出素”是我国古代文人形容煎煮海盐的常用词汇和成语,目前所知,前者最早出自先秦文献《世本》的“宿沙作煮盐”,后者最早见于南朝齐张融《海赋》诗中:“漉沙构白,熬波出素。”①转引自:张荣生.中国历代盐文学作品选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20.唐宋以来与这二词有关的词语已常见于诗词之中,如唐代诗人卢纶的“潮作浇田雨,云成煮海烟”②转引自:张荣生.中国历代盐文学作品选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34.,北宋诗人程大昌的“熬波出素料同机,会心一笑撒盐诗”③转引自:张荣生.中国历代盐文学作品选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91.,南宋诗人楼钥的“熬波亦良苦,乐岁色犹菜”④楼钥.攻媿集:卷76:跋扬州伯父《耕织图》[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018.等等。具有一定文学修养的瞿守义和陈椿二人自然也熟知这些词语,并用于熬书中,如陈序的“深知煮海渊源”、正文题诗的“海波顷刻熬出素”等⑤另据最近的研究成果,熬书中引用或化用《诗经》《尚书》《史记》等典籍中的词句和典故达10余处,详见:李梦生,韩可胜,等.熬波图笺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但鉴于早已成书的《通州䰞海录》使用了“煮海”为书名(“䰞”为“煮”之异体字),则熬书只能用“熬波”作书名了,以示与《通州䰞海录》的区别。再加上可能还参考了《耕织图》的书名,遂取名为《熬波图》。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古来至今一直有人以为“煮海”和“熬波”就是直接煮海水为盐,如《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刘濞)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现在权威的辞书如《辞源》也把“煮海为盐”解释成“煮海水以为盐”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943.,有的新闻报道甚至妄言“熬波”是晒盐。但实际上,现代研究已表明,海水的含盐量并不高,每公斤平均约含盐27克,而食盐的浓度要达到265克时才能结晶,“所以若直接煮海水提取食盐,燃料要消耗很大,效率相当低”⑦赵匡华,周嘉华.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478.。郭正忠先生也指出,南朝张融的《海赋》诗中,“漉沙”应是指淋卤积卤,是“熬波出素”的基础⑧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2.。近年来笔者在鲁北沿海的盐业考古实践也表明,商周时期的海盐生产是开采地下卤水并进行淋卤,再把获得的高浓度卤水上灶煎煮成盐,这一工艺流程与熬书的记载基本类似,应是原始的淋煎法⑨王青.淋煎法海盐生产技术起源的考古学探索[J].盐业史研究,2007(1).。由此证明,先秦文献《管子》中屡次提到的“煮海为盐”并非直接煮海水,因为该书同时还提到了“煮泲水为盐”,“泲水”即指地下卤水⑩王青.《管子》所载海盐生产的考古学新证[J].东岳论丛,2005(6);王青.山东北部商周时期海盐生产的几个问题[J].文物,2006(4).。可见,将“煮海”和“熬波”理解成直接煮海水为盐,应是一种望文生义式的误解。这也是未亲见海盐生产场景的古代文人容易犯的错误,而曾担任过盐场盐监的北宋词人柳永在《煮海歌》长诗中,就把制盐流程描述得更为详细准确,如“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咸味加,始灌潮波塯成卤”⑪描写的就是煮盐之前的刮泥和淋卤工序,与熬书记录的
⑪ 转引自: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49.摊灰和淋卤流程很相似①钱钟书先生曾对此诗做了经典注释,认为“始灌潮波塯成卤”的“塯”通“溜”,作“流动貌”解。此说可能有误,“塯”应是淋卤设施,亦即熬书所言“灰垯”。详见: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49.。这也说明,我们需要深入研读《熬波图》一书,才能避免那种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错误。
三、结论和余论
综上所述,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对熬书的作者和成书背景两个基本问题重新做了研究和辨析。笔者认为,《熬波图》一书的作者应是瞿守义和陈椿二人,而非提要所言为陈椿一人所撰,只因四库提要的考证存在严重疏误,才有此数百年之谬。而致此谬误实非陈椿本意,因其在熬书序言中已详述成书过程,言明其原作者为瞿守义,并无掠人美誉之心。正如郭正忠先生所言:“长期以来将《熬波图》一概列于陈椿名下的做法,不仅不符合事实,湮没了该书的真正作者,而且与陈椿补刊《熬波图》之本意,亦深相悖逆。”②郭正忠.略论宋代海盐生产的技术进步:兼考《熬波图》的作者、时代与前身[J].浙江学刊,1985(4).因此,笔者特著成此文,以再次申明纠正此事。关于熬书的成书背景,笔者认为除了前人指出的受到楼璹著《耕织图》和陈晔著《通州䰞海录》的影响或触动之外,可能还有瞿守义欲仿效楼璹故事进献《熬波图》以加官进爵,从而提高瞿氏家族地位和势力的考虑。但这只是一种间接推论,有待今后发现更多史料来验证。
如今再来看熬书的这两个问题,不禁要钦佩和感怀陈椿此人,正是他在瞿守义父子去世多年之后,始终坚守自己当年的承诺,倾力完成此事并出资刊印,才使这部从初稿到出版辗转半个多世纪的珍贵典籍得以全帙问世。陈椿这种对先辈知识成果的敬畏之心和对诺言的长期坚守,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与情怀的集中体现,值得今人永远传颂和学习。而造成熬书作者长达200多年的错误说法,始作俑者实为四库馆臣,其撰写的“提要”现在还影响甚广,四库馆臣为文之粗疏草率,后果之严重难除,也是值得今人引为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