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集》的怀疑和希望
翁海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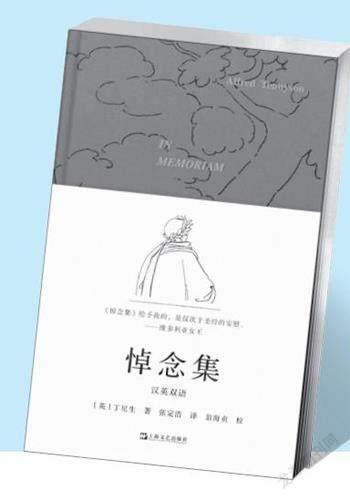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悼念集》原题名是“In Memoriam A. H. H.”,纪念亚瑟·亨利·哈勒姆。一八三三年,二十二岁的哈勒姆因病去世。此后十七年,丁尼生反复以友人的死亡为主题赋诗,在一八五○年才结集出版。丁尼生与亚瑟·哈勒姆的情谊,大抵类似庄周与惠子。惠子死后,庄周指着他的坟墓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在一首诗里,丁尼生描述不息的海水犹如自己的丧友之痛:
拍啊、拍啊、拍啊
拍在你寒冷的灰色岩石,海啊!
而我多么希望,我的舌头能够说出
在我心底浮现的思绪。
挚友死后十七年间,他怀疑死后的世界,怀疑灵魂是否永恒。丁尼生居哀思索、反复怀疑,失去知己的哀痛成为他思索死亡与灵魂的契机。他所承受的痛苦,没有让他的诗歌流于情感的放纵,没有让他以智性的文字作激情与幻想的歌手。在第一首诗里,诗人回顾这段沉默时期悲伤而宝贵的经历:
我同意由他的歌声所传递的真理,
用千种音调面对一架竖琴的明净,
说人类会以他们死去的自身
作为阶石,迈向更高的事物。
《悼念集》充满了生活的坚硬事实与对死亡的疑问。他对友人的爱、对于友人的灵魂在另一世界依然爱着自己的信念,敦促他思索万物的真理,最终以肯定回答人类无数世代疑惑的问题:灵魂是否永生?在《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一部回忆录》里,丁尼生说这部诗集类似《神曲》,“以幸福为终结。……悲伤的各种情绪,如同一出戏剧,是一种戏剧化的前提,我个人觉得,恐惧、怀疑、痛苦,都只能在信仰爱的上帝里找到答案与解脱”。
张定浩先生想要翻译诗集,托我一起看看数句语法复杂的诗行。读了这数句之后,意犹未尽,索性从头读起。这样随意二三天便读完整部集子。只是竟未能摘取二三句,在心里记诵。这样的读书着实让人惊心。诗歌怎能没有即读即摘的佳句?过了些时候,阅读普鲁斯特《在少女的花影之下》,憬悟也正是同样的阅读体验。每个句子读来都很平淡,似乎描述着平常的事理,然而,又因作者长年病态似地胶着于同一个主题,将单独一个对象反复地咀嚼,从而每个句子的诗意与哲理连绵不断,渗入下一个句子。因为全篇都是这样前后相贯、难以截断的句子,从而不会为了某一句而读得特别高兴,要格外摘取。
在某种意义上,《悼念集》颇似一部小说。在故事的开头,主人公独自沉思亡故的友人,然后漫步走过墓地,正如任何多愁善感的年轻人,坐在朋友的墓前,沉浸在自然的感应之中。故事继而叙述更多的沉思,然后他上床睡觉,但悲痛让他难以入眠。他思索诗歌的艺术,思索自己该如何写作,然后收到朋友来信,又勾起无数思绪。清晨,他外出散步,来到亡友的旧居,又怕惊忧房屋里的人。时隔多年,诗人归返校园的公寓,却听见室内传出陌生的笑声。不过,这部“小说”只注重诗人的思想与感受,外界的事件只是为内心的旅程提供可信的背景。
死亡是真实的经验,爱被自然事实阻断是人类共同的悲剧。因而,这部诗集开篇没有预设,没有想要证明的假设,只是死亡的冷漠与迷惘的哀痛。有人或许可以指摘这部诗集为病态,以如此长篇承载如此空洞的主题。然而,曾经悲痛的人,深知哀痛麻木思想,让人短气跼步,更会景慕诗人“迈向更高的事物”的力量。
在《悼念集》里,缺席是永恒的丧失,而诗人对于友人的爱未曾随着时间消逝,并且笃信死去的友人必定也是如此。尽管他称这些诗句为“狂乱的哭泣”,任由读者去寻找诗行之间的深意。T. S.艾略特觉得《悼念集》具备一部日记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可谓是记载自白的日记。很多学者研究丁尼生的手稿,认为这个观点确实有所依据。然而,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关注的是诗和诗人,而不是丁尼生平常如何写作。我们已在开篇就读到,诗人虽狂乱地哭喊,却又不能放弃灵魂永生的希望,在第一百二十八首,诗人说自己终于领悟,自然万物如同艺术作品,都是朝着一个终点的劳作(toil coöperant to an end)。同样地,艺术作品,譬如《悼念集》,也没有写日记之时的放心散漫,如同自然万物,写诗的劳作始终朝向同一个目标:在痛苦的黑暗里不忘记光的存在;在怀疑之时不放弃寻找希望的方向。
怀疑让怀疑者不满足于现有的人生框架,然而,脱离这个框架之后,在没有找到新的结构之前,怀疑者只能更加痛苦。倘若能够不问究竟地接受一些教义,生活在既定的框架里,人生或许可以感觉些许融在集体中的安慰。第六首诗里,丁尼生便拒斥这种约定俗成的安慰:
有人写道,“依旧有别的朋友”,
“失去是人生之常态”—
而常态就是没有什么可奇怪,
是空谷壳脱离谷粒的理由。
失去是一种常态,这说法不会
减轻我失去时的苦涩,反倒加重:
太平常!就像清晨的光从来无法走进
黑夜,但有一些心已破碎。
作为诗人,丁尼生有自己的担当。他是维多利亚时代养育的典范诗人,但也在浪漫主义影响之下成长,智性上依然推崇启蒙时代的古典精神。他一向以此自勉,要让诗歌不但表现自己的痛苦,也能传递人类共同的情感。诗人虽以极其主观的方式寻找生命的价值,但深信自己的求索经验富有普遍意义。丁尼生在《回忆录》里说:“这是一部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诗中的‘我’并非总是作者在自述,而是人类的声音通过他在说话。这部诗更是整个人类的呼喊。在诗里,最私人的悲痛扩展为整个世界的思想与希望……因此,这部诗既十分客观,又极富个人色彩。”
然而,丁尼生又不似启蒙时代的人,譬如亚历山大·蒲柏在《一篇论人类的短文》(An Essay on Man)中,坚决地相信宇宙的终极秩序,认为自有宇宙以来,普遍的秩序便存在于自然之中,存在于人类之中。蒲柏歌颂这个秩序,安定得仿佛自己不属于这个宇宙:“一个英雄死去,或者一只麻雀掉落/一些原子或体系掷入废墟/时而一个水泡破裂,时而一个世界破裂”。
在第一百二十七首,丁尼生终于也接纳这样的宇宙秩序。然而,他接受,是因为看到了希望。他自日常中找到了死亡的意义,理性地相信灵魂在宇宙里占据一席之地:他友人的灵魂在观看这个世界的一切。
堡垒自高处崩塌,
残忍的大地在天空下发亮
伟大的永世在血中沉没,
被地狱烈火环绕;
然而你,亲爱的精灵,幸福之星,
从远处俯瞰这骚动,
微笑,知道一切安好。
这样坚定的信念赋予死亡一股恢宏的乐观精神,迥异于汉语挽歌面对死亡的无奈与凄凉。苏轼追念亡妻,写下“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袁枚祭奠三妹素文,写下“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实为汉语挽歌之最。然而,袁枚之于生死永隔的无奈,身为生者被抛弃的孤单,虽令读者觉得切中心怀,却也因同样地感染了那无奈与孤单而消沉。
人类的思想总是忍不住沉思未来的各种可能,无论我们如何恼怒肉身存在的边界,人只能一次活在一个世界。我们与另一世界的关系也只能是在这个世界的关系。希腊的戏剧作家最擅长触及人类最畏惧的主题,欧里庇得斯的《阿尔刻提斯》(Alcestis)讲述一名男子注定要早死,但因为他曾有恩于阿波罗,这位神祇便灌醉命运女神,骗得女神的承诺,允许这名男子找人替死。然而,他怎么也找不着人代替,连父母也不肯替儿子去死。衰迈的父亲说:确实,我活的日子不多了,可我的眼睛跟你的一样,也喜欢看着阳光,不敢看到黑暗。他的妻子阿尔刻提斯便主动替他死。在她的葬礼上,赫拉克勒斯正巧路过,按习俗,丧葬人家不能待客,这位神祇应该饿着肚子继续赶路。这位丈夫好客之至,隐瞒丧妻的真相,设宴招待大力神。最后赫拉克勒斯获悉真相,感于主人的殷勤款待,下到冥界与死神搏斗,救回阿尔刻提斯。戏剧的结尾:阿尔刻提斯默默地站在台上,其他人继续表演,她默默地站着,一言不发。
死后的世界,让欧里庇得斯不敢想象?无论是阅读剧本,或是观看舞台表演,看过死亡的人返回人间,默默地站着,都是让人惊心的意象,让人顿时丧失所有美好的期待。然而,丁尼生经历一十七年的深思,最终坚定地认为,死亡无损生者对死者的深情,亦无损死者对自己的深情。
也许《悼念集》只是传达一个简单的民间信念:爱是永恒。只是,丁尼生用反复咀嚼的思想,而不是混乱的情绪,去定义爱的边界,从而为这一个简单的信念增添真实的力量。诗人宣称自己会追随这个信念,至少要证明它在此生此世并不虚妄。第二十六首说道:
因为我渴望证实
爱不会被时间的流逝所侵蚀
你若在焦灼或颓丧,意欲阅读一些激情的诗句来回应自己混乱的心绪,《悼念集》可能不是你想要阅读的诗集。丁尼生的爱,是平静,他的失去,是甘心接受,他的诗意,是在怀疑之后,以理性节制情绪的从容,是云外苍天。
在平常的生活里,我觉得最接近这种诗意的体验,莫过于驱车行驶一条设计在理的道路。我尤其喜欢小城与邻城之间一条路,规定的车速在七十公里每小时。按常情,人们从来不会按照规定的车速行驶,而是至少超速十几公里每小时。再者,路上车辆不多,稍不经心就会超速。然而,在这条路上,满怀敬意地对待规定车速的人,并非只有我一人。路虽傍着铁道线,却没有依托铁轨,而是蜿蜒成大弧度。后来听说,设计时征询一位顾问,如何让人自觉地遵循规定的车速。这位老者原本是设计战舰的。他说,多用弧度,眼睛望不到远方,身体就会自动慢下来。这位老者的建议,只是分析人的心理与身体之时的关系。也许,正是因为饱含着理性的节制,开车行驶在这条公路,总有一种近乎诗意的体验。循着这些弧度,在零落的车辆之间保持遥远的距离,心思集中,可以从容、安定地行驶到无限,就像诗歌,剪裁了结构,讲究了押韵与音步之后,自然地呈现理性的诗意。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1809-1892)
这部诗集共收有一百三十三篇诗,首尾两篇标为“序曲”(prologue)与“终曲”(epilogue),中间一百三十一篇以罗马数字标示。阅读之时,或可认为《悼念集》毫无内在的结构,丁尼生只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诗歌。这样的读法也是好的。在序曲里,诗人说,亚瑟去世之后,自己便终日沉没于“狂乱的恍惚的哭泣”。诗集前半部确似语无伦次,犹如哀未忘时不能成声的曲调。友人逝世后的九年间,也是丁尼生的沉默时期,仅出版两首短诗。然而,在一八四二年,他不再沉默,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诗集,收录有 《两个声音》《洛克西雷庄园》《爱与责任》《亚瑟之死》《尤利西斯》。这些诗歌说明了诗人从未在沉默里颓废,他的沉默是深思,是诗艺的练习。这两卷诗出版之后,当时有评论说这些诗作表明诗人“作过很多思索,受过很多痛苦”。在打破沉默之后,丁尼生并未立即结集出版追念友人的挽歌,世人须再等八年,才能见到《悼念集》。我们在诗集后半部看到,十七年时间,让“狂乱的恍惚的”伤逝者,成为一个博大、静穆的心灵。
正如丁尼生所崇尚的理想,诗歌首要的特征是不失于“朝着一个终点而劳作”。《悼念集》也可以读作一部结构缜密的长诗,采用三轮循环的结构,贯穿跨越生与死的深情,从居哀的颓思,到怀疑死后的真实,到笃信灵魂的永世,在季节的更迭与年光的积淀里,诗人找到一种理性的心满意足。诗集的开端纵然哀伤迷惘,也包含着一股期冀,期冀爱始终不变。丁尼生似乎想要说,哀痛也可以成为神圣,如此,便可证明曾经忠诚的心灵,将永远忠诚。
若将《悼念集》视为一个精心安排的整体,或许可以将整部诗集划分为三重循环。譬如,序曲、初步阶段(1-27)、第一循环(28-77)、第二循环(78-103)、第三循环(104-131)、终曲。由于每轮循环传达不同的思想,内部的结构安排也会有所不同,但每轮循环都包括最基本的元素,以圣诞节为始,接着用一系列诗歌(第三轮循环仅录一首)阐述这一时期的思想历程,继而描绘特定的季节、亚瑟的生辰。譬如,第一轮循环写初春,第二轮循环写新年,第三轮循环则写死者的生辰。
第一轮循环诠释过去的爱,想象死去的友人生活在一个不可见的世界。于是,两位好友同时呈现在读者眼前:一个不可见,只能出现在信念里,另一个则以自己的深情诠释友人的境况。第二轮循环试图再现世与永生的友人沟通。诗人相信这样的沟通是可能的,但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珍惜与生者的灵魂交流。诗人相信,倘若他的友人依然活着,他必定也会如此珍惜。因而,诗人结下的新的友谊,也可契合死者不可见的世界。第三轮循环想象未来的福祉,诗人期待在同一个神圣的爱里找到最高的人类归宿。《悼念集》的第一轮循环读来有些凄凉,诗人似乎冰冻在过去的友情与个人的悲伤之中,然而,在第二、第三循环,我们读到他面对现在,望向将来,从孤独的哀思走向新的友谊。
序曲作于一八四九年,类似一种祈祷,诉诸我们不可见的世界。在三轮循环里,诗人在悲痛的世界经历漫长的内心冲突、疑惑,最后也是抵达序曲所信仰的那个世界。可以说,序曲第一节概括了全诗的要旨:
刚强的上帝之子,不朽的爱,
我们这些,无法目睹你容颜的孩子,
因着信,唯余信,皈依,
在我们无力证实之处也相信。
这里的“不朽的爱”(immortal Love),可以简单地读作单纯的深情,人类的友谊。在《悼念集》里,“爱”不只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情感,更是一个超越我们的实体。诗人追随着这个不朽的实体,将它视为信仰与爱的神圣对象去崇拜,将它作为最高贵的人生目标。诗歌以死亡为开端,经过漫长的轮回,诗人战胜了悲痛,在爱中获得凯旋。“终曲”描述一场婚礼,象征着爱在现世的完美。尾声的诗行是婚礼的赞歌(Epithalamium),庆贺丁尼生的妹妹塞西莉亚与埃德蒙·勒欣顿的婚礼,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举行。第一节诗的措辞颇似第一百零八首开头:
我不会茕茕孑立于众人之外
在颓丧里沉默诚然不是难事,不过是纵容情绪罢了。丁尼生既然坚信自己的灵魂将来与友人的灵魂后世相遇,又怎会忘记自己的职责。诗人要自己不再执拗,要接纳新的友谊,要做好这个世界的事。人世的喜悦为诗歌的终结,在一部悼亡的诗歌里,可能确实有些出乎意料。然而,倘若将这首尾声放置在整体的结构之中,或许也不难理解诗人的用意。
擅长欣赏结构的读者,也可以在下面一些佐证里,看到诗人似乎有意打造一种内在的秩序。
再版时添诗 一八五一年,诗集发行第四版之时,丁尼生添加一首新诗,即第五十九首。这首诗的开头写道:“哦悲伤,你若是决意要与我同居”。这声呼唤必定让读者听来耳熟,也许会记起诗人在第三首诗里也曾召唤:“哦悲伤,这残忍的伴侣”。这两处呼唤显然具有迥异的情感。第三首诗里,诗人依然在绝望,而悲伤这个庇护所,当然是很残忍的友伴。在第五十九首诗里,诗人已经萌生新的希望,诗歌开始将眼光穿透自然世界,将悲伤视为神圣的和平的侍者:
大声宣告你的存在,因你是我的,
伴随如此强烈的对于未来的希望,
希望无论如何我都能了解你,
而有些人可能还难于叫出你的名字。
在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三年的版本里,诗人再次增添一首新诗,即第三十九首。诗中第一句也有一声呼唤:
这些地下骸骨的老守卫
这个“老守卫”无疑也是指涉前文所呼唤的“悲伤”。再版之时所增添的两首诗,可谓是见证了诗人意欲将这部诗集打造为一个整体的努力。倘若逐次阅读《悼念集》描述同样情绪的诗(如第2、3、34、49、116首),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心灵因悲伤而麻木绝望,继续被初春万物苏醒的景象感动,生发欣喜。这一内在心灵的转变是一个有序的进程,呈现在诗集的结构里。
合唱队的副歌 在这部诗集里,尤其是在前半部,诗人频频提起他的艺术(如第5、8、21、27、48、49、57、75-77首)。这些诗篇讲述格律语言的实用性,仿佛剪裁以就音律的措辞,才能最自然地传达他的情绪。第五首诗说起,诗歌只能机械地缓解痛苦,第一百二十五首则回顾过去的悲伤,印证诗歌可以如此用来表达情绪,无论悲伤或希望,让诗人积聚力量与希望。
如果那诗篇充满忧虑的关切,
那是爱神在吐露诗的精魂;
如果那言辞甜美而有力,
那是爱神烙上了高贵的印记;
……
本书译者是批评家与诗人张定浩。他翻译《悼念集》的初衷,是因为一位诗人朋友的去世,想以同样的主题来传达自己的悼思。说起丁尼生的诗艺难译,张定浩颇有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虽心中担忧,畏惧自己词不达意,但勉力要以这份劳作来传达一份心意。确实,人类一向以劳作的成果为荐享。纵然不能相信精诚通于神明,人类的思想本身总是最可靠的寄托。
在译后记里,张定浩说起译文不得不牺牲音步、押韵等元素。即便不提诗歌的元素,丁尼生的选词与句法,都平淡而有思致,避免生僻或惊人的造句。然而,正是这样白描式的诗歌,在汉语翻译里十分难以传达。
例如第十一首,这首诗用词浅近,翻译为汉语之时,却会碰到很多难题。首先,这首诗通篇的动词几乎都是不及物动词。譬如“The chestnut pattering to the ground”(栗子拍打地面),“all the silvery gossamers/That twinkle into green and gold”(银蛛丝荧荧闪烁为绿色金色),“These leaves that redden to the fall”(树叶红得掉落),“waves that sway themselves in rest”(波浪在休憩里摇动)。在这些不及物动词的描绘之下,诗里的一切事件都成为宇宙的自行运动,然而,汉語的句法难以突显这样的动词。
再者,诗人在每节重复“calm”,描述清湛的早晨,大自然的静谧,叙述者的“calm despair”(镇定的绝望),依然在海上航行的已故友人的“dead calm”(在死亡之中的安然)。在这首诗里,诗人将“calm”重复十七次。重复的词语最容易营造气氛,让人仿佛以为诗人在岸边等待亡友的遗体,也是宇宙固有的一个事件。
张定浩最后选择使用“平静”来翻译“calm”。就传达各节诗的蕴意而言,平静一词确实颇为庸常,但稳妥地传递了原诗的重复手法。你若暗自斟酌,或似我一般翻阅词典,恐怕最后也会无奈地认同这个寻常的译法,除非你选择舍弃重复。诗歌的翻译,或者无论哪一种体裁的翻译,大概都是译者舍此取彼的选择过程。无论经过多少次选择,我们依然不敢说自己擅长选择。因此,只能说,取舍得当之时,便是一个好的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