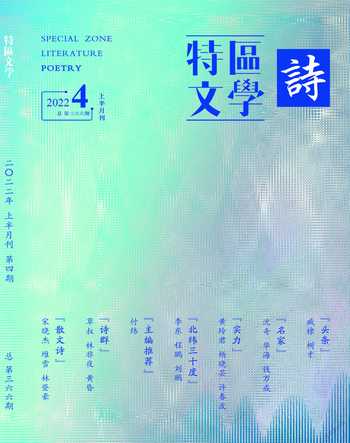“系列诗”的发明
当一度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大幕徐徐拉上,个人化写作的趋势日渐凸显。在此背景之下,臧棣无疑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汉语诗歌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在纷繁芜杂的当代汉语诗歌生态系统中,臧棣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凭借其日臻成熟的诗歌作品,他有效地超越了当代诗歌中普遍存在的那种过于仰仗才气的青春期写作,而投入到一种更为自觉、日趋丰富的诗艺探索之中;另一方面,臧棣以《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新诗的晦涩:合法的,或只能听天由命的》等文为代表的诗论,从诗学观念上对现代汉诗的当下境遇及其话语策略作了一种必要清理和深入思考。
正如诗人曾在一本诗选的前言中所言,“我们必须学会习惯把当代诗歌首先当成是一项自主的艺术工作来看待”(臧棣《2005北大年选·诗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臧棣那里,诗歌写作是一项自觉自为的工作,并得到一种双向度的全面展开。而正是创作和理论二者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使臧棣的诗歌写作显得步履稳健,为现代汉诗不断开启着新的可能性。诗人近年来所致力创作的“协会系列诗”和“丛书系列诗”,正是这种新可能性的一种体现。
“系列诗”的发明
“系列诗”是一个十分新颖的命名,堪称臧棣的发明。何谓“系列诗”?对此,臧棣本人的解释是:“在我的诗歌潜意识里,系列诗是对付长诗写作的一个比较有趣的方法。”具体而言,“它的主题更庞杂,它要研究的是一个时代的生存状况。相对于长诗,它在结构上又有更灵活的适应性,和多样的形式。”(臧棣:《后记》,臧棣:《沸腾协会》,自印诗集2005年,P65)显然,“长诗”在这里被当作描述“系列诗”的一个参照对象。在这种比照中,我们注意到,按照臧棣的构想,一方面,“系列诗”必须具备替代承担长诗某种功能的能力(“研究一个时代的生存状况”,就意味着规模之庞大和主题之复杂,甚至让人联想起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对于长篇小说强大功能的期许),另一方面,“系列诗”在结构、形式等方面又必须具备一些自身鲜明的特点。臧棣的系列诗作品的标题,都被加上“协会”或“丛书”作为醒目的后缀,体现了某种整体性和统一性。这些诗不仅鲜明地区别于当下其他诗人的作品,即使与诗人的前期作品相比,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显示了臧棣诗歌写作的勃勃野心。
事实上,在经过若干年系列诗写作实践之后,臧棣对于系列诗写作的意义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表示:“我的‘丛书诗,有些是对非常具体的事物的命名。在这背后,包含着我的一个想法:‘丛书是很重的东西,大部头的、体系性的、预设性,有很强的规划性。而我们对待细小的事物时,恰恰要放下点身段来;这意味着,诗人可以用体系性的东西,很重的东西,去关注卑微事物所处的境况。不要以为那种很细小的东西,很卑微的东西,就跟‘丛书这种宏大的格局不匹配。一旦放下姿态,我们就会發现,很多东西其实以前都没有细心地去关怀过。所以,要说‘丛书有一个诗歌的含义的话,那就是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的人生境况。”(胡少卿:《建立中国新诗的认证机制—臧棣访谈》)臧棣在这里不仅重申了系列诗足以取代长诗的体系性、预设性、规划性等外部特征,还特别强调了系列诗中主体姿态的调整和转变、诗歌主题的反思和表现对象的重新发现等问题。事实上,臧棣近年推出的系列诗文本也有力地支持、印证了他的上述观念。
不难发现,臧棣有意识地把系列诗提升为一种自足的写作行为。“写作”一词来自罗兰·巴尔特,它与原有的“文学”概念密切相关,并被当作后者的一个突出方面:“正因为写作来自作家的一种有意义的姿态,它才比文学中任何其它方面更显著地汇入历史之中。”显然,他有意以写作这一概念冲击传统文学概念的边界。臧棣对系列诗的苦心经营和由此流露的鲜明的写作姿态,同样向既有的“新诗”概念提出了挑战,当然也为之注入了新的活力。
臧棣的系列诗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不少作品都流露出鲜明的元诗意味,所谓“元诗”,简言之,就是诗人直接在诗里现身说法,以诗歌的方式,谈论诗歌写作艺术诸方面的问题。当然,臧棣在诗里所谈论的是“新诗”的写作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元诗”的写法,不同于古代诗人那种以诗论诗的做法,而是有意模糊文体的界限,以寻找语言的新的活力和可能:“……我坦率地承认我追求的/不仅仅写诗的过程,而是/诞生在诗中的一种新的声音。”(《非常朦胧协会》)因此,诗人充分打开诗歌文本的表达空间,让读者切身参与到诗歌情境的演绎、推进过程中。在臧棣的系列诗里,这样的作品颇为常见:“你仿佛每天都从这公园旁边走过,但你想过/它距离你的生活究竟多远吗?/应你的要求,我们已从你的眼前/将整个宇宙挪开了。剩下的,就是这首诗。/如果有兴趣,请对这首诗做些什么吧。”(《迁徙学丛书》)“我不担心美丽的蝴蝶/能否听懂我特意为它们准备的语言。/我这样端正态度—/一首写到蝴蝶的诗不在乎/蝴蝶是否会加入到它的读者中来。”(《蝴蝶迷者协会》)“你在我手掌上颠动着,跳上去时,/你像一块试金石,跌回到掌心时,/你无辜得像一块冰凉的动物化石。/假如把我把你从威尔士带走,带回北京,/你能告诉我,诗,究竟对你做了什么吗?”(《顽石学丛书》)在这里,作者、诗中的说话者和读者三方之间,不再是传统文本所呈现的相互封闭的层级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互动、相互激发的多元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读者的在场感得到了充分的强调,另一方面,文本的“可写性”特征也凸显出来。
除“协会”和“丛书”两大系列诗外,臧棣近年出版的诗集《未名湖》(臧棣:《未名湖》,海南出版社2010年)收入同名诗100首,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系列诗”。《未名湖》的写作时间跨度为1988-2008,整整20年。臧棣以十年时间为界,把这批作品划分为上下两卷。其中下卷的写作风格与“协会”和“丛书”系列诗更为接近。
开放文本的快乐
早在1940年代,袁可嘉就曾谈到“新诗”的戏剧化问题。不过,他的侧重点在于借鉴现代戏剧的某种“间接性”手法来匡正当时的“新诗”普遍存在的“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见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68页。),是从技巧的层面讨论问题。多年之后,这篇诗论的核心观点在臧棣笔下得到一种呼应。不过,臧棣似乎更愿意把“戏剧化”置换成“喜剧性”,并具体落实到语言、形式、诗歌情境等多个层面,从风格的角度来阐述其诗歌中的喜剧性及相关问题:“……我身上有很多喜剧性,表现在诗歌中可能就是轻盈的美感效应。在重和轻这种关系上,我偏重轻的一面,像丰富、微妙,不够决断,获得一种开通开明的境界等。……我的方式是选择像蝴蝶那样跟心灵关系密切的轻盈状态。”(王光明等:《可能的拓展:诗与世界关系的重建—臧棣与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山花》,2004年第12期。)在这里,轻盈、开放、喜剧性显然是几个关键词,它们的内涵相互勾连、相互渗透,共同标示了臧棣诗歌文本的重要美学特征。
里尔克是臧棣偏爱的一位诗人。他曾在一篇文章如此描述里尔克:“里尔克是位晦涩的诗人,但却不是位复杂的诗人。”其实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臧棣自己。与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相比,臧棣的诗是晦涩的。不过,我们不应把简单武断地把“晦涩”理解为一个贬义词。从某种意义上说,晦涩是现代诗歌的特质之一。具体到臧棣的诗,晦涩主要表現在诗人对语言的精心“把玩”上。或者说,诗人在语言中加入了必要的难度和弹性,使语言摆脱了日常工具性的强大规约,焕发出自身的活力和光芒。诗人的这种做法,用罗兰·巴尔特的话说,就是“用语言来弄虚做假和对语言弄虚做假”。臧棣诗中的一些比喻就具有一种晦涩的别样魅力。比如《陈列柜》里的“一些灰尘像浅浅的殖民地”,《刺猬》里的“我的身体会膨胀如/一部公共财产保护法”,《孔雀园》里的“变化很突然,/如同码头深处一次咖啡色的爱”等等。这些出人意料的比喻,很有玩味的余地,让读者能够领略到一种“文本的快乐”。
这种“文本的快乐”,在臧棣的系列诗里,更多地是通过意象的内涵更新和微妙关联的重建来呈现的。比如,被自古以来无数诗人抒写过的蝴蝶意象,在臧棣笔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它时而扮演“我们的变形记”大戏中翩然起舞的主角:“你假定每个人都会受到/蝴蝶的启发。轻盈而美丽—/用这样的装备,即使陷阱再深,/也无法阻止我们从里面翩翩飞出”(《极限体验协会》);时而成为一个掌控世界命运巨变的开关:“静止在小水洼边的蝴蝶—/它确实像一个天然开关,/而我,克制不住那想要去按动它的愿望。/我必须告诉你:我不知道/十秒钟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新超验主义协会》)不过,在轻盈的背后,其实又隐藏着种种沉重的约束:“如果需要的话,这故事/会有一个结局的。怎么又是蝴蝶?/能动而盲目,一路飞过底层,//浏览自然的奥秘,就好像重要线索/都是可以裁剪出来似的。看不见的锋利/就藏在它随身携带的小剪子里。”(《道德学丛书》)蝴蝶的优美飞翔甚至遭遇到无形的笼子的限制:“你也许会在声音的笼子里捕捉到两只蝴蝶。/从这个角度看去,蝴蝶的笼子/就是你不曾想象过花也会有笼子。”(《假如没有笼子丛书》)在这些诗里,蝴蝶不再是寄托诗人自我的一个简单符号,而是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涵,成为诗人思考一些形而上命题的重要媒介。
球形(圆形)意象也是臧棣所偏爱的一类意象,在《即兴表演协会》一诗里,世界被作者先后描述成“橘子”“皮球”和“绣球”:“ 稳稳地接住它吧,即便你从不知道/什么叫绣球!即使它无法告诉你/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你手上的功夫/不会流失,它将传递到这首诗中。”把纷繁复杂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个好玩的小圆球体,以小写大,具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效果。而在另一首诗里,满月、柚子和金币三个意象相互指涉,具有一种秘响旁通的表达效果:“立秋后第一轮的满月已升起来,/它硕大并且新鲜,如同被宇宙之露/泡大的另一个柚子。它不同于我在夜市上/见过的一枚足以乱真的金币。”(《小道消息协会》)而《沸腾协会》里的“小圆球”“小混球”“元宵”等意象之间呈现的转化、互换和融合的微妙关系,为读者揉捏出了一个灵动、浑圆的诗歌情境。这种浑圆与灵动同样被赋予了绣球花的意象中:“我恳求我们的命运就好像一群蜜蜂突然飞过来/将你的紫阳花团团围住。命运之赐/如何减去命运之刺?声音的裸体/多么及时,多么辩证。偏僻的甜/正好配套本能秀。这些木绣球确实很形象,/很适合回答来自另一个大陆的问候:/它们的火焰既热情又安静,它们的固执/仅次于诗:就像是刚介绍给你的一个节目,/它们的雪球晃动在爱的手套里。”(《脑海学丛书》)
臧棣系列诗文本的喜剧性还体现在诗歌情境的荒诞性和反讽性上。在《喜剧演员协会》一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人与猴之间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换位”过程:“我当然是它的主人,这一点/几乎不用证明。而一旦走出屋门,/我很快就会感到一丝难堪—/很多时候,我更像是它的跟班。”作为主人的“当然”姿态很快就被沦为“跟班”的无奈所取代。给猴子取名更具喜剧意味:“……给它取名字,颇费了我一番工夫。/它看不上以往那些为猴子准备的名字。/它就像一个公诉人盯着我,直到最后/我给它起名叫天鹅,它才回应我。所以,/也不妨说,每天,我是带着我的天鹅在散步。”命名的有意错乱与主体的换位是相互呼应的。无独有偶,在另一首诗里,狗被主人命名为“天使”:“他的狗是纯种的猎狐犬。/他给它取过很多名字,/但最终选定它叫‘天使。”(《非常神秘协会》)“天鹅”也好,“天使”也罢,其实都是一种反讽话语,只不过臧棣的这种反讽并非指向某种批判,而是同样通向文本的快乐效应,正如诗人自己所言:“我的反讽主要在于获得对事物的一种领悟,获得对事物重新认识的可能性,获得某种乐趣,而不是像奥登或九叶诗人那样为了获得一个批判性的主题。”(王光明等:《可能的拓展:诗与世界关系的重建—臧棣与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山花》2004年第12期。)
审智:“让语言冒一点险”
臧棣的系列诗自然不像传统抒情诗那样,把表达重心放在情感的抒发上,而是落在了语言能力(洞察力、感受力等)的呈现上。诸如诗题中“如何让阅读避免麻木”“追问我们是如何着迷的”“如何有条件地把握真实”“反对粗暴对待自言自语”“假如事情真的无法诉诸语言”“诗可以写得像散文一样好”“野花心理学”“诗歌植物学”等颇具挑战性的语词,以及高频出现的“宇宙”“世界”“事物”“真理”“自由”“自我”“时间”等富有形而上色彩的语词,都受到臧棣的偏爱。这种偏爱其实折射了臧棣诗歌的审智色彩。这里所说的“审智”,借用自孙绍振先生论述当代散文的一个独创概念,意指臧棣的诗充满灵动的智性和鲜活的感觉,二者相互激发、相得益彰,生成一种独特的诗意质地。
这一典型特点使得臧棣的诗鲜明地区别于那些造作的、既没有哲理也没有诗的所谓“哲理诗”。譬如,面对异国美丽的海湾,诗人的目光越过海浪、沙滩,投向更为广阔无垠的思想空间:“酸甜的小灯笼,我们无法进入的黑暗,/它们凭融化几个自我/就能轻易地进入。我们无法照亮的地方,//只要经过一阵融化,反复渗透,便可被它们照亮。/它们比禁果的滋味更强烈,/更容易赢得我们对时间的反抗。”(《金角湾丛书》)这里通过一串葡萄,透露了诗人关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个体生命与时间的关系等命题的思考。但这种思考不是纯粹的逻辑推演,而是通过一些生动具体的意象、感觉来呈现的。与之相类似的表达方式在《茴香酒丛书》中也可以看到:“猛烈的记忆,/据推测,诗的友谊也想像它一样/拥有一个神奇的配方。将肉桂,丁香,薄荷/混入蜂蜜,甘菊,柠檬,似乎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所有的配料均取自/当地丰饶的物产。在蒸馏过程中,/酿造者发现,任何事物,想要完美的话,/只能从改变比重入手。他庆幸自己的哲学严谨于/每个人最终都会受到口味的启发。”美酒和诗歌之间的天然亲密关系,引发了诗人关于诗歌艺术的思考。这种思考自然也不是板着哲学家般的严密而刻板的面孔,而是弥漫着活跃的感性分子。
罗兰·巴尔特曾特别强调现代诗歌中“字词的迸发作用”,认为“在现代诗的每个字词下面都潜伏着一种存在的地质学式的层次,在其中聚集着名称的全部内涵”(罗兰·巴尔特:《有没有诗的写作呢?》,《符号学原理》, P88。),对于語言中“地质学式的层次”的挖掘,自然需要以审智的话语方式来展开。在臧棣的诗里,审智式的语言挖掘得到了一种形象的描述:“感谢诗里总会有一点秘密。/感谢诗大多时候就像一口只有半尺/就要被挖到泉眼的井。/感谢诗里有湿:其中,漩涡/可用来测量人生,点点滴滴/可用来润滑记忆和愿望。”(《金不换协会》)这几行诗又让人想起诗人西默斯·希尼在《挖掘》一诗里显示的一个著名姿态:“我的食指和拇指间/夹着一支矮墩墩的笔。/我将用它挖掘。”
而要真正深入挖掘语言内部的潜在活力,必须破除层层障碍,一步步向前艰难地推进。在《新诗的百年孤独》一诗里,臧棣曾对新诗的语言问题做了一番戏谑性的表述:“它解雇了语言,/理由是语言工作得太认真了。/它扇了服务对象一巴掌。它褪下了/格律的避孕套。它暴露了不可能。”在调侃式的表层语义之下,其实隐含着诗人关于新诗语言的一种深层思考。换言之,当“新诗”的语言解除了格律、日常惯性、意识形态等的外在枷锁,它的繁殖力就会被大大激发出来。而在《新诗协会》中,臧棣为诗歌格律安排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位置:“我倒是不讨厌诗是一种舞蹈,/但我不会接受要跳好这样的舞蹈,/我们必须得戴上镣铐。/我想我理解存在着更复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锻造出这镣铐。/但是,制作它,并不一定要戴上它。/假如我有这样的镣铐,我会在我的房间里/给它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我或许会把它放在柜子顶上,/当我跳舞,它就在一旁静静地观摩着。”在这里,格律并没有被完全放逐,而是成为诗歌现场的一个旁观者。臧棣的这种诗歌观念让人不由想起罗兰·巴尔特的另一段话:“文学的第三种力量,它的严格的符号学力量,在于玩弄记号,而不是消除记号,这就是将记号置于一种语言机器里,这种机器的制动器和安全栓都去掉了。简言之,这就是在奴性语言的内部建立起各种各样真正的同形异质体。”(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符号学原理》, P12。)就新诗写作而言,如何最大限度深入到背负着沉重文化传统的现代汉语内部,获得真正的表达的自由,是值得每一位当代诗人深思的一个命题。而臧棣在这方面的努力,同样在系列诗写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与审智的语言挖掘相呼应,臧棣的言说姿态也是独特的,他往往乐意于扮演一位站在“诗”外的观察者。这可能跟诗人关于诗歌的“不及物性”的观念有关。在论述里尔克的那篇文章里,臧棣曾经谈到观察的重要性,认为“观察不仅是对事物运用一种客观的视角,而且意味着事物有其自身的神秘的规律。……观察在类型上还导致了现代咏物诗的出现”(臧棣:《汉语中的里尔克》)。其实,臧棣的不少系列诗似乎都可以归类为“现代咏物诗”。而在不少系列诗作品中,连“诗”本身都成了一个被观察的对象。譬如:“你不是食腐动物,你会放下它。/你会感到诗就在附近”(《先知协会》)、“诗,意味着没有人能声称他不在现场”(《浪漫人格协会》);“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付/一个正用碧蓝的天空照自己的人。/所以,我必须写出这首诗。/而你将判断,诗是否还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最佳托辞协会》),等等。这里的观察,其实就是一种诗歌观念的反思和内省。
在臧棣的笔下,“我”“你”“自我”“你我”等指称主体的名词之间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纠缠关系:“一个谜就可以救你,假如你答应过/放聪明点的话。我想,我会做得比这些刺更好。/我会记住你的选择的。我的位置有天赐的一面,/和他们不同,我活在你我之间。”(《复活学丛书》)“你不只是你。你还有一个责任,你是你我。/感谢汉语的奇妙让你我不只是你和我,/也要感谢每首诗似乎都包含着一个命运的动机。//这首诗关心命运的动机如何体现,就好像/你我不是我的黑暗。假如你还没有忘记运动,/你我就是根的面面观。你最近是不是一个人爬过很多山?”(《抵抗诗学丛书》)主体关系、位置的模糊化处理,也可以说是“让语言冒一点险”的另一种表现:当原本相对比较稳定的主体都被激活了,一首诗的整体情境自然就变得更为活跃、开放起来。
结 语
臧棣的系列诗写作王国仍然在不断地扩张中。如今,臧棣在微博平台上为系列诗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传播、阅读空间。笔者注意到,臧棣在新浪注册的微博账号,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发表他最新的系列诗作品,以及接受一些网友关于这些作品的即时评论。从频繁的更新和活跃的互动可以发现,臧棣显然颇为看重这个高度开放的文本交流平台,除在第一时间发布作品外,他还十分认真、细致地回应来自网友的各种评论,包括对一些批判声音的理性回应。我们期待着日新月异的新媒体能让臧棣未来的诗歌写作如虎添翼。
伍明春,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美学学会副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