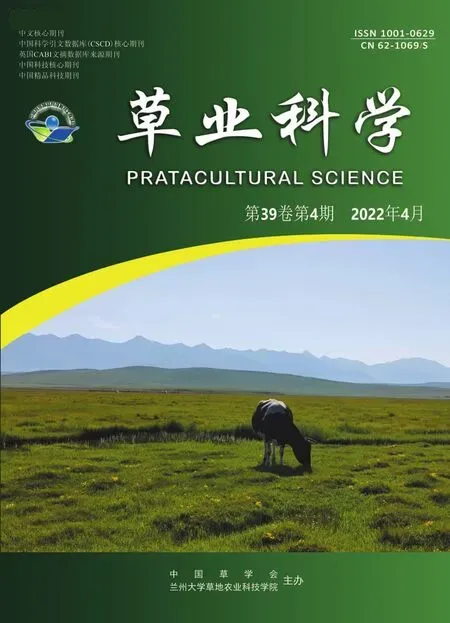青藏高原东北缘不同利用率高寒草甸植被构成及种间关联
宣文婷,赵一军,李艺妆,刘金银,王先之,于应文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是我国面积最大、分布最广高寒生态系统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牧区,高寒草甸占青藏高原草地面积的47.0%。随气候变化、人口和家畜饲养量增长,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超载严重,原有草畜平衡被破坏,高寒草甸面临严重退化问题[1-3]。因此,制定合理草地利用管理策略,是避免高寒草甸退化的关键。植物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和种间关系是草地稳定性管理及群落演替的主要评价指标,研究不同利用率高寒草甸植被构成及种间关系,有助于了解不同利用率下高寒草甸的变化,对于该类草地的管理[4-5]和稳定性维持机制揭示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诸多学者已对青藏高原不同退化程度、放牧制度、放牧强度及植被斑块和群落(排泄物或鼠丘)下高寒草甸的植物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种间关系和草地稳定性特征等[2,6-11]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高寒草甸退化过程中,莎草 (Cyperus rotundus) 和禾草比例降低,豆科和杂类草比例增加;冷季放牧、一定时期封育和植被微斑块形成利于高寒草甸稳定性维持或增强[6-8],养分(畜粪)添加提高高寒草甸中禾草比例,促进高寒草甸向禾草群落或禾草 + 莎草群落转化;重牧降低高寒草甸中禾草和莎草比例及草地群落稳定性[11]。这些结果为青藏高原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特征和草地稳定性深入分析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不同草地利用率下青藏高原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结构和种间关系的整合研究相对缺乏。植物种间关联是由于群落生境差异不同引起的,是群落特征之一[11]。植物种间正关联,是群落中两个物种互相依赖(如寄生、共生等)或者有相似的生物学特性,对环境表现出相同的生态适应性的结果,而两个相互竞争或生态位分离的物种之间则表现为负关联[8]。青藏高原草地经营管理多以牧户为经营单元,不同牧户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水平等存在差异,因此草地家畜承载力和草地利用率差异很大,植物群落结构和种间关系也不同。基于此,本研究以青藏高原东北缘高寒草甸为对象,通过不同利用率下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结构、种间关系及群落稳定性分析,探究较适宜草地利用率和利用制度,为高寒草甸的管理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肃省天祝县抓喜秀龙乡的甘肃农业大学天祝高山草地试验站附近,地理坐标102°40′~102°47′ E,37°11′~37°14′ N,海拔2 771~3 211 m。年均气温-0.1 ℃,1月最低气温-18.3 ℃,7月最高气温12.7 ℃,≥0 ℃年积温1 380℃·d。年降水量 416 mm,集中于7月 - 9月,年蒸发量1 592 mm;无绝对无霜期,仅分冷热两季,生长期120~140 d。土壤为亚高山草甸土,表层有机质含量达10%~15%,pH为5.0~7.0。草地植物种主要有线叶嵩草(Kobresia capillifolia)、矮嵩草(K.humilis)、洽草(Koeleria cristata)、扁穗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紫花针茅(Stipa purpurea)、西北针茅(S.sareptana)、珠芽蓼(Polygonum viviparum)、冷地早熟禾(Poa crymophila)、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等。
1.2 样地设置
研究区草畜生产主要以家庭为单元。前期调查发现,研究区放牧家畜为藏羊和牦牛,草地主要有冷季放牧、连续放牧、轮牧利用3种利用模式。由于不同牧户草地利用率差异较大,通过返青期前期(4月中下旬)草地牧草现存量和牧草年生产力调查,并基于不同利用模式草地利用率变幅,确定研究区3种利用模式的草地利用率,分别为中度利用60%~70% (5月 - 11月 轮 牧 牧 场)、重 度 利 用80%~90% (11月 - 翌年5月初,冷季连续放牧牧场)和极度利用 > 90% (全年连续放牧公共牧场)。
2017年7月,在研究区不同利用模式或利用率高寒草甸上,各选取3块全年草地利用率中度(MG)、重度(HG)和极度(EG),且放牧制度多年持续一样的牧户和公共牧场高寒草甸为试验样地,每个利用率草地总面积为1~2 hm2,该时期各草甸的草层高度和盖度分别约为5.9 cm和89.3%、14.5 cm和80.3%、4.3 cm和76%。
1.3 测定指标及方法
1.3.1 群落特征
2017年8月中旬,在已设置的3种利用率的每块草地上,分别随机均匀设置0.5 m × 0.5 m的正方形样方5个,先调查每个样方内各植物种的高度、盖度;然后齐地刈割按样方收获地上生物量,将收获的各样方地上生物量,按死物质和活物质分开,再将活物质按不同植物种分开,分别装入信封袋,带回实验室。在测定完地上生物量的各样方中,用直径9 cm土钻,分别采集 0 - 10 cm、10 - 20 cm和20 - 30 cm深度土壤,分别装袋带回实验室,转入自制纱布,用流水冲洗出各根系样品。所有植物样品于75 ℃下烘干称重。
植物种重要值(important value, IV):基于样方植物种高度和盖度数据,由公式IV= (RH+RC)/2计算得出。式中:RH和RC分别为植物种的相对高度和相对盖度,分别由样方内某种植物的高度或盖度除以该样方内所有植物种的高度或盖度之和计算。
植物物种数(R) =S。
物种β多样性指数(βw):

式中:S为群落中物种数,mCa为各样方或样本的平均物种数,Pi表示群落中i种的相对重要值。
经济类群生物量构成分析:基于样方地上分种生物量数据,统计禾草、莎草、豆科及其他分别占其总和构成百分比。
1.3.2 植物种间关系分析
采用植物种间关联度Jaccard指数和Spearman秩相关,对不同利用率草地物群落主要植物种种间关系进行分析。
Jaccard指数(Jaccard index, JI):基于样方植物种出现与否数据,由公式JI=a/(a+b+c)计算得出。式中:a为所有样方中种A和种B共同出现的样方数,b、c分别为所有样方中种A或种B单独出现的样方数。本研究借鉴张金屯的[12]划分方法,将其划分 为3个等级:0.67 <JI≤ 1为强联结,0.33 <JI≤0.67为弱联结,0 ≤JI≤ 0.33为无联结。
植物种间Spearman秩相关:基于样方各植物种地上现存生物量构成数据,采用SPSS 16.0中Correlate中的Bivariate模块,计算主要植物种间Spearman秩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1.4 数据分析
采用Excel处理数据及制图。采用SPSS 16.0软件的One-Way ANOVA对不同利用率草地植物群落数据和不同土层深度根系生物量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和检验,数据表示为均值 ± 标准误。由于功能群地上生物量比例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先对其平方根标准化后,再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主要植物种重要值
如表1所列,MG草地以禾草(西北针茅、垂穗披碱草、冷地早熟禾)为优势种;HG草地以垂穗披碱草、矮嵩草、西北针茅为优势种;EG草地以矮嵩草为绝对优势种。3类草地主要伴生种为扁蓿豆(Melissitus ruthenicus)、甘肃棘豆(Oxytropis kansuensis)、翻白叶委陵菜(Maoutia puya)和平车前(Plantago depressa)。

表1 不同利用率高寒草甸主要植物种重要值Table 1 Important values of main plant species of alpine meadows under different unitization rates
2.2 植物物种多样性
草地群落植物样方物种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βw指数均为MG草地和HG草地 >EG草地(P< 0.05);Simpson指数3种利用率的草地间无差异(P> 0.05) (表2)。上述结果表明,一定草地利用率,利于草地群落物种多样性维持。

表2 不同利用率高寒草甸植物物种多样性Table 2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of alpine meadows under different unitization rates
2.3 地上经济类群和根系生物量构成
草地利用率对禾草、莎草和豆科地上现存生物量构成有显著影响(P< 0.05) (图1)。莎草地上现存生物量比例为EG草地(61.58%) > HG草地(44.02%) >MG草地(26.01%) (P< 0.05);禾草地上现存生物量比 例 为MG草 地(65.33%) > HG草 地(50.17%) >EG草地(29.21%) (P< 0.05);豆科和杂类草地上现存生物量比例均相对较低,分别为3.16%~6.84%和2.06%~3.26%。

图1 不同利用率高寒草甸地上经济类群生物量构成Figure 1 Aboveground biomass composition of economic groups of alpine meadows under different unitization rates
随草地利用率增大,0 - 10 cm土层根系生物量显著下降(P< 0.05),MG和HG草地根系生物量为EG草地的1.78倍和1.48倍;其他两个土层3种利用率间无显著差异(P> 0.05)。0 - 30 cm土层总根系 生 物 量 为MG草 地(3 675.60 g·m-2) > HG草 地(3 177.24 g·m-2) > EG草地(2 401.51 g·m-2);随土层深度增加,其根系生物量呈明显下降趋势,0 - 10 cm土层根系生物量占比最大(图2)。?

图2 不同利用率高寒草甸根系生物量Figure 2 Root biomass of alpine meadows under different unitization rates
2.4 植物种种间关联度JI指数
草地群落主要植物种Jaccard种间关联指数(表3)显示,MG草地与HG草地比EG草地的强联结与弱联结的植物种对多,而无联结种对则是EG草地最多,比例达69%。MG、HG和EG草地之间弱联结的种对比例相近,分别为27%、25%和22%。说明,EG草地群落中,较多种对联结性弱,群落结构简单,种间关系不稳定。

表3 不同利用率高寒草甸主要植物种种间Jaccard指数Table 3 Jaccard index of interspecific main plant alpine meadows under different unitization rates
2.5 主要植物种种间Spearman秩相关
Spearman秩相关分析(图3)显示,在MG、HG和EG草地中,正相关种对数分别占各自总对数的51%、40%和48%,显著或极显著正关联种对分别占7%、3%和4%;负相关种对数分别占各自总对数的49%、60%和52%,显著或极显著负关联种对分别占8%、5%和5%;正负关联比分别为1.06、0.67和0.93。说明,HG和EG草地中多数植物种对的种间联结松散,群落相较MG草地群落来说,处于变化竞争之中;MG草地群落中多数植物种对的种间关联性较强,群落内部各物种相互依赖,群落稳定性相对较强。

图3 不同利用率高寒草甸主要植物种对Spearman秩相关分析Figure 3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ain plant species of alpine meadows under different utilization rates
MG草地中,显著正相关种对为矮嵩草-翻白叶委陵菜、高山嵩草-蒲公英、高山嵩草-甘肃棘豆、高山嵩草-唐松草,垂穗披碱草-球花蒿、甘肃棘豆-蒲公英、紫菀-翻白叶委陵菜,显著负相关种对为矮嵩草-垂穗披碱草、矮嵩草-西北针茅、矮嵩草-球花蒿、垂穗披碱草-高山嵩草、西北针茅-甘肃棘豆、西北针茅-翻白叶委陵菜、西北针茅-紫菀、扁蓿豆-球花蒿、翻白叶委陵菜-球花蒿。HG草地中,显著正相关种对为洽草-赖草、西北针茅-翻白叶委陵菜、甘肃棘豆-兰花韭,显著负相关种对为矮嵩草-冷地早熟禾、垂穗披碱草-翻白叶委陵菜、垂穗披碱草-平车前、洽草-平车前、赖草-平车前。EG草地中,显著正相关种对有垂穗披碱草-冷地早熟禾、垂穗披碱草-赖草、赖草-冷地早熟禾、赖草-醉马草,显著负相关种对有矮嵩草-西北针茅、矮嵩草-赖草,矮嵩草-翻白叶委陵菜,矮嵩草-醉马草、西北针茅-二裂委陵菜。综上,3种草地中,显著关联种对多数发生在优势种与伴生种或伴生种与伴生种之间。
3 讨论与结论
植被群落构成反映群落外貌与功能,植物群落退化表现为优势种和群落构成变化[6]。本研究从中度、重度到极度利用过程中,高寒草甸从禾草/嵩草群落向嵩草群落转变,禾草优势地位逐渐被莎草等取代,中度利用草地优势种或亚优势种(垂穗披碱草和冷地早熟禾等)重要值逐渐减小,优质牧草和可食牧草比例降低,低质和不可食植物重要值上升,洽草(Koeleria cristata)、紫菀(Corydalis edulis)、兰花韭(Miersia chilensis)和唐松草(Thalictrum aquilegiifolium)等消失,草地物种多样性和生产力降低。相关研究也表明,过度利用草甸中,家畜采食和践踏强度较高[2],特别在牧草返青期-种子成熟期(5月 - 8月)因家畜反复啃食和践踏牧草,抑制牧草生长和损伤种子,降低营养价值和适口性高的禾草等比例,使禾草等在草甸中逐渐消失[13-14],群落结构单一化[15],进而降低群落物种多样性和草地稳定性[16-18];还因重度放牧通过破坏土壤表层物理结构,影响草地植物根系生长和土壤水分和养分下渗,形成干旱贫瘠环境[14],进而降低地上植被养分吸收效率,使植被生长受阻,土壤裸露,致使高寒草甸退化。本研究极度利用草甸中,矮嵩草是绝对优势种,禾草和适口性较高的其他牧草重要值均很低,甚至出现一定量醉马草;原因是莎草以根茎繁殖为主,受放牧时期与放牧强度影响小,过度放牧可使禾草或嵩草群落退化成矮嵩草群落[14]。说明,莎草比禾草更适合在过度利用草地生存,研究区极度利用草地呈现一定程度退化。此外,本研究中度和重度利用率高寒物物种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较高,植物物种数越来越少,植被群落结构逐渐简单;这与诸 多 学 者 研 究 结 果 类 似[1,3,17,19-20];其 原 因 是 高 寒 草甸具很高恢复力和对人类活动耐受性[13,16],一定程度放牧不仅刺激牧草补偿性生长,提高草地生产力,还利于植物多样性维持[2-3]。本研究中度利用率利于草甸群落物种多样性维持。
植物种间关系决定群落结构特征和动态,反映植物种群和群落分布格局及其互作关系,研究群落植物种关联性是了解群落稳定性的重要途径[8,21]。本研究植物种间Jaccard指数和Spearman秩相关结果均表明,极度利用草地中,较多植物种对联结松散,群落结构简单,群落稳定性相对较弱;中度利用草地中,多数植物种对种间关联性较强,稳定性相对较强。这是因为极度利用草地,群落物种数少,多个植物种在所有样方中均出现,每个物种均占据对其有利位置,进而使其种间独立性强,群落趋向松散,抗干扰能力弱,群落稳定性降低[9,11];而中度利用草地群落因其植物物种多样性和样方内植物种类较多,且矮嵩草和西北针茅为明显优势种,其他物种优势度相似,进而使其绝对关联种对数比例降低,强关联种对较多,由此利于群落稳定[8]。本研究3种利用率高寒草甸植物Spearman秩相关总体结果为,莎草与禾草呈负相关关系,莎草与豆科呈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禾草植株高大,利于光竞争且对养分敏感,返青后禾草生长迅速,进而抑制草丛内矮小莎草的生长所致[9];而莎草科嵩草根浅且为须根,豆科甘肃棘豆根较深和莎草嵩草属根系生态位形成互补,豆科扁蓿豆枝条贴地面伸长生长,利于占有更多空间资源,且其固氮为莎草利用[8,11],进而与莎草形成正关联。
本研究中,某些种对的联结也随草甸利用率增加而变化,如矮嵩草和扁蓿豆,二裂委陵菜、火绒草、平车前都由正相关逐步转变为负相关。这是由于同一种群在不同群落中因环境差异,具不同资源位和生态位[5,10],当两个或多个有机体必须获取同一资源,而资源又达不到有机体极限生长需要时,就出现竞争[5,22];且这些有机体获取同一资源难易程度决定竞争强度,在利用强度逐渐增加时,群落内可利用资源越来越少,种间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某些种对由正相关变为负相关,在资源充足时,他们是潜在竞争者,资源不足时,变为竞争者[7,11,22]。有研究也表明,草地植物种对联结性质或关联程度受外界条件和群落演替阶段影响[4-5,9]。此外,本研究3种草地群落的Spearman秩相关均显示,显著关联种对多数发生在优势种与伴生种或伴生种与伴生种之间,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8-9,11];主要原因是优势种和亚优势植物在群落中迅速占据适合生长生态位,相互制衡,竞争非生物资源的能力势均力敌,而伴生种生长缓慢,在不利条件下与其他伴生种和优势种激烈竞争剩余资源,所以出现此类情形。
综上,研究区高寒草甸在中度利用下,群落结构较稳定;在重度和极度利用率下,植被构成发生改变,群落结构趋于退化;轮牧模式下60%~70%的全年平均草地利用率,利于研究区高寒草甸群落稳定性维持。研究区高寒草甸利用时,需综合考虑草地牧草生产力、草地利用率和放牧制度;建议适当降低冷季重度利用牧场的家畜承载力,采取围栏封育恢复全年极度利用公共牧场,以利于研究区高寒草甸的保护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