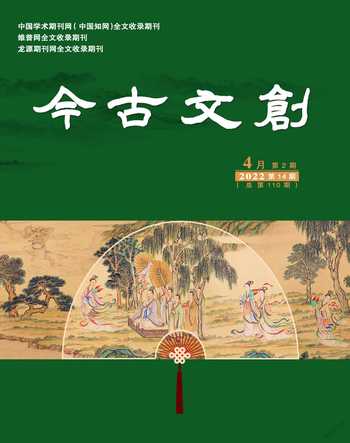未能复合的圆形结构 “ O ”
【摘要】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的写作始终游离于对革命前俄国生活的追忆和无从逃避的流亡现实之间。身为俄裔流亡作家,他渴求通过在作品中创造“另一世界”来实现过去与现实间的平衡。1924年首次出版的短篇小说《机缘》可被认为是纳博科夫实践其这一文学要义的初步尝试。从小说中暗含的多个圆形结构“O”这一隐喻出发,通过探究无法和解的悲剧精神、卢兴中途破灭的自杀计划、埃琳娜丢失的婚戒以及卢兴记忆中的盲点这四个未能复合的圆形结构,研究揭示了《机缘》中记忆与现实之间难以企及的平衡以及纳博科夫“另一世界”的幻灭。
【关键词】 纳博科夫;《机缘》;圆形结构“O”;“另一世界”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4-003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4.010
一、引言
《机缘》(“A Matter of Chance”)主要讲述了1919年俄国革命后三个俄国贵族的流亡之旅。纳博科夫以卢兴(Luzhin)和其妻子埃琳娜(Elena)的分离和无法实现的重逢为主线,试图再现一幕尼采式悲剧。《机缘》整篇小说中充斥着一种强烈的落差感,这源自流亡者记忆中耀眼的俄国生活和苍白、污浊的流亡现实之间的对比,面对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纳博科夫(Nabokov)企图通过创造悲剧艺术以实现记忆和现实之间的平衡,最终抵达想象中的“另一世界”(The Otherworld)[1]。纳博科夫对流亡者困境的这一艺术解决与尼采(Nietzsche)的悲剧艺术观遥相呼应,尼采发现“悲剧艺术是应对人类悲剧式存在的有效途径”[2],而作为所有艺术形式的顶峰,“悲剧体现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这两种对立倾向的统一”[3]16。相应地,“悲剧艺术的最终生成以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和解为前提”[4]445。
在《机缘》中,卢兴这一典型纳博科夫式人物起伏不定的生存状态以及在记忆与现实碰撞之下的痛苦挣扎就体现了这一文学创作理念。本文从小说中暗含的多个圆形结构“O”这一隐喻出发,揭示了卢兴的整个情绪系统代表着尼采悲剧艺术中的酒神精神,而埃琳娜以及老乌克托姆斯基公爵夫人(old Princess Maria Ukhtomski)则是日神精神的外化,这主要体现在她们作为日神形式的象征意义以及对于回忆的理智态度上。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二元冲动的平衡象征着流亡者现实困境的艺术解决,而卢兴和埃琳娜机缘巧合下五次的错失相逢预示着这场难以生成的悲剧艺术。故事中卢兴最终的的自杀计划实际上是酒神精神诉诸日神形式的精妙统一,但故事结尾卢兴的意外死亡却打破了悲剧艺术中两种对立倾向——酒神精神和日神的结合,这反映出纳博科夫对于俄国记忆和流亡现实的清醒意识,即不可调和的过去和现在。此外,《机缘》中未能复合的圆形结构“O”这一意象的重复出现也揭示了在过去和现实之间不可实现的平衡以及《机缘》中纳博科夫“另一世界”的幻灭。
二、酒神精神的代表和日神精神的外化
纳博科夫在《机缘》中对流亡者卢兴生命悲剧的书写证明了以“艺术的方式生存是解决流亡者生存困境的形而上的慰藉,这使他们暂时逃脱事态变迁的纷扰”[3]17。而艺术的生存依赖于酒神冲动和日神冲动的和解,否则流亡者的生命只能被命运和机缘的洪流所决定。纳博科夫有一种类似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作家意识,他们都关注社会变革后的边缘群体,纳博科夫在《机缘》中聚焦作为流亡者的俄国没落贵族的生活。《机缘》中主要描绘了三位曾经的俄国贵族,而根据尼采的悲剧艺术观,他们分别代表着悲剧艺术中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是卢兴所象征的酒神精神;埃琳娜和老乌克托姆斯基公爵夫人则共同象征着日神精神。卢兴在俄国革命后被迫流亡,几经辗转后来就职于一列德国列车的国际餐车上,白天的侍者夜晚在肮脏、潮湿的角落里无法抑制地陷入对革命前俄国贵族生活的回忆之中,为了应对如同“钢铁翘板”[5]300一般的两极生活,卢兴诉诸于“迷醉”(intoxication)和“麻痹”(paralysis)的状态,但却采取了吸食可卡因的方式。卢兴对于回忆无节制的热情以及对于迷醉状态不可遏制的沉湎在本质上代表了无法抑制的酒神精神。
尼采认为,“日神艺术的本质能力在于创造形式”[6]12,“造型艺术可以被归类为日神艺术”[4]103。纳博科夫笔下蝴蝶的对称结构将形式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在《机缘》中,卢兴的妻子埃琳娜是蝴蝶形象的化身,她在寻找婚戒时的身姿就宛如一只飞舞的蝴蝶。“她匆匆走出车厢;双臂张开,左右摇摆”[7] 。在这一层面上,埃琳娜的蝴蝶形象是日神形式的表象。此外,根据尼采的观点“……日神精神的属性是理性、克制……”[8]。因此,老乌克托姆斯基公爵夫人和埃琳娜对记忆的克制也象征着日神精神的本质。和卢兴一样,老公爵夫人也流露出对革命前俄国生活的怀旧之情,但面对不可逆转的现实,她先是移居德国,后搬到了法国,继续她的生活。不同于卢兴,她没有沉迷在对过去的永恒回忆中,而是对记忆建立了理性的感知。“她并不伤感,因为她知道,快活的事情只能快快活活地来说,不必因为这些事情已经消逝而感到悲伤”[5]308。同样,在与卢兴分离后,埃琳娜也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选择不断寻找丈夫。与卢兴相反,埃琳娜和老乌克托姆斯基公爵夫人在面对过往的俄国贵族生活记忆与流亡生活的鲜明落差时所表现出的克制与理性,也象征着卢兴所不具備的日神精神的秩序。
三、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间难以实现的和解
悲剧艺术诞生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和解。然而,卢兴与埃琳娜不可企及的重逢,以及卢兴无法回想起的由老公爵夫人所象征的巨大的过去皆暗示着卢兴悲剧艺术的难以形成,也预示着最终卢兴艺术生存的破灭。尼采探究了酒神的神秘仪式,发现希腊人的自我放纵和丧失自制的自暴自弃实际上植根于希腊人对人类悲剧存在的深刻理解。而“尼采关注的是希腊人通过艺术的生活来驱散生存之苦”[9]42。尼采的艺术观从这一方面而言也渗透着他的生命哲学。“悲剧艺术的最终生成有赖于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和解”[4]445。
《机缘》中流亡者悲剧存在的亟需解决也要通过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这两种倾向的和解来实现。面对生命的无意义本质,卢兴试图以克制、理性的日神形式来表达对于记忆不可抑制的酒神冲动,以达到理想中艺术的生存。由此,卢兴才能继续他的生命。卢兴的酒神精神体现在他像希腊人那样选择了迷醉状态,但希腊人的迷醉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欺骗,是以艺术的方式化解现实中的苦难。然而,卢兴的迷醉是无意识的,它源于可卡因的致幻作用。而也正是由于吸食毒品的副作用,卢兴才无法迅速采取行动,因而失去了与妻子重逢的第一次机会。
同样地,当卢兴遇见老公爵夫人时,乌克托姆斯基的脸在卢兴的记忆中变成了一个“盲点”(blind spot)[5]312。日神精神体现了形式之美。寻找妻子的周密步骤、细致的自杀计划以及用图画来表达内心恐惧的种种做法都是卢兴追求日神形式的表现,他试图通过构建种种计划的策略来重新把握生命,从他无序的生活中获得秩序。小说中对卢兴制定计划有这样的描述,“他估计了每一个细枝末节,就好像他在安排一个国际象棋问题那样”[5]309。国际象棋是秩序的游戏,像構思国际象棋问题一样制定计划象征着日神艺术之美。在尼采看来,“日神精神对酒神精神具有约束作用”[6]10。死亡本身对于卢兴而言并不重要,使他感兴趣的是建构细密计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卢兴混乱的生活和强烈的情感被赋予了秩序。然而究其本质,卢兴虚假的酒神精神是在毒品致幻作用下产生的不同于希腊人的无意识迷醉。相应地,在此种酒神精神的作用下所产生的看似秩序井然的日神精神,即为追寻妻子打算采取的理性步骤、用以表示恐惧感起伏的图表以及那些奇特的自我毁灭的图景设定,在可卡因的致幻作用褪去后均沦为了毫无意义的胡写乱画。卢兴想要在自己身上实现酒神精神和日神形式之间的和解,以有序的日神形式约束其整个情绪系统里对于回忆无可抑制的热烈冲动,以此作为重新获得秩序的手段。但由毒品催生的虚假的酒神精神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日神形式,决定了卢兴终究难以触及记忆和现实之间的平衡。
四、不可调和的过去与现在
《机缘》中卢兴既定的自杀计划实际上是酒神精神借助日神形式的回归本质。然而,故事结尾卢兴的意外死亡却破坏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结合,对自杀计划的背离也反映出纳博科夫对不可调和的过去与现在的清醒认识。尼采所强调的是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这两种二元冲动在悲剧身上的和解与结合,而酒神冲动是贯穿于悲剧的根本动机,日神形象仅是表达酒神冲动的手段。周国平认为,“悲剧快感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即通过个体的毁灭而给人的一种与宇宙本体结合为一体的神秘陶醉”[3]17。”
卢兴的自杀计划如下所述:“……绕过这节停着不动的车厢,另外一节车厢一会儿就要来和这节车厢连接上。等那节车厢驶近等候着的这一节时,他就把脑袋搁在减震器那盾一般的头上。两只减震器将会相互碰撞。他低下的脑袋就夹在减震器接合起的两端之间。那么他的脑袋便会像肥皂泡那样爆开,变成彩虹般的气体”[5]309。卢兴自杀计划实现的时刻即是悲剧艺术诞生的时刻,在那一刻,卢兴所代表的酒神精神在以圆形结构为代表的日神精神中回归其本质。然而,卢兴的自我毁灭未能如愿实现,一列行驶的火车饥不择食般地吞噬了他,这一意外死亡打断了他预计的自杀计划,从而阻碍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结合。
在《机缘》中,“O”这一重复出现的圆形结构最终均以未复合的状态结束也体现了纳博科夫对于俄国记忆和流亡者现实遭遇的清醒认知。这篇小说中存在着三个明显的圆形结构“O”:在卢兴的自杀计划中,两列火车连接时盾牌式减震器形成一个圆形结构“O”,埃琳娜的婚戒是故事中出现的第二个圆形结构“O”,而卢兴在看到老公爵夫人时联想到的盲点是第三个“O”。第一个圆形结构“O”的未能复合归因于卢兴自我毁灭的中途告破,卢兴在故事结尾被飞驰而来的火车撞死,而本应在两列火车接轨之时形成的圆形结构最终未能生成,取而代之的是撞死卢兴的列车所形成的线性结构,它那灯火通明的窗户以一条连续的条纹飞驰而过,象征着不可阻挡的前进着的现实。婚戒是婚姻的象征,在这个故事中,埃琳娜的婚戒象征着她和卢兴的重逢,而婚戒的丢失则预示着二人注定的分离。
小说中卢兴和埃琳娜共有五次重聚的机会,但他们在机缘巧合之下五次错过对方。最后一次当埃琳娜终于要踏入餐车寻找她的戒指时,餐车从列车上分开了。丢失的婚戒所隐喻着的卢兴和埃琳娜的错失相逢随即成为小说中第二个未复合的“O”。卢津记忆中的盲点是第三个未复合的圆形结构“O”。老公爵夫人的脸是卢兴记忆中的盲点,而这个卢兴无法回想起的盲点实际上隐藏着至关重要的俄国记忆,它关乎卢兴和妻子的重聚乃至决定了卢兴的生死,而这一盲点终究成为卢兴死前的缺憾。盲点所象征的难以企及的俄国记忆、由戒指所暗喻的夫妻的未能重逢以及自杀计划的失败所代表的三个圆形结构均以未复合的状态结束,体现着记忆和现实的冲突与疏离,也象征着《机缘》中不可调和的过去和现在。
五、结束语
纳博科夫的写作始终在记忆和现实之间游离。《机缘》中卢兴这一人物形象是个人对俄罗斯的怀旧之情与作为流亡者的现实这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的阵地。流亡者所面临的困境,即俄国记忆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艺术的方式共存,而艺术的生存有赖于酒神精神和日神形式的和解。然而,以卢兴为代表的酒神精神和以埃琳娜为代表的日神精神之间不可实现的重逢与结合、卢兴计划之外的意外死亡和那些“未复合”的圆形结构,都表明了卢兴无法在消逝的过去与残存的流亡现实中实现二者间的平衡,以重新把握生命的秩序。纳博科夫用卢兴最终的生命悲剧诠释了流亡者悲剧艺术的难以生成、俄国记忆的不可挽回、过去与现实的难以平衡以及身为流亡者无法企及的悲剧艺术式生存,这也标志着《机缘》中纳博科夫“另一世界”的幻灭。
参考文献:
[1]Alexandrov,Vladimir E. “The Otherworld[A].”Vladimir Alexandrov.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C]. New York:Garland,1995.
[2]Richter, David H.The Critical Tradition:Classical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M].Bedford:Bedford Books,1997.
[3]周国平.悲剧的酒神本质:尼采的悲剧观[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11-19.
[4]Nietzsche,Friedrich.The Birth of Tragedy[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1994.
[5]纳博科夫.纳博科夫小说全集[M].黄乐山等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6]周国平.日神和酒神:尼采的二元艺术冲动学说[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7]Nabokov,Vladimir.The Stories of Vladimir Nabokov[M].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97.
[8]Baldick,Chris.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9]周国平.悲剧的诞生:尼采哲学的诞生[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作者简介:
周小雯,女,陕西西安人,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硕士,研究方向: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