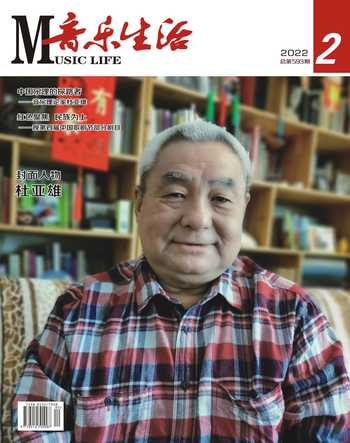音乐修养的君子品性构成研究
史文露 宁汐
“君子”一词由来已久,先秦时期便广泛运用于诸多典籍之中。最初“君子”之意是指出身高贵的统治者。《说文解字》曰:“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1]这里的“君”,便是指能够发号施令的最高统治者。春秋时期,受到孔孟儒学思想的影响,“君子”一词,成为儒教推崇的理想人格,多用于品行高尚、高风亮节之人。《荀子》曰:“君子寬而不侵,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2]这里的“君”,则是更注重自身的品行修养。由此可以看出“君子”之义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阶级的变化而转变的,后来所见的对人格品性的内在追求的那类“君子”,与春秋时期礼乐文化有关,但不再囿于权力地位的象征,已经转化为思想价值与精神内涵的德行典范,成为历代世人所追崇的理想人格。
而“君子”在“乐”上的作用也有其价值显现。“乐”除了外在音乐形式的审美意识,更是被赋予了音乐本体以外的特殊含义,“乐”成为评判君子的重要准绳之一。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君子的修身大致分为了诗、礼、乐三个阶段:人的修养要从学《诗经》开始,“礼仪”是以制度而立身的确立之本,音乐则是作为人修养的最后融合汇成阶段。这足以见得“乐”对于人思想、人格所起到的积极影响。孔子不仅对君子的自身品行有着严格要求,同时也充分地认识到“乐”能够修身、治学,对于个人素养全面、广泛地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儒家“以德为基”的人文精神,通过“君子”为载体,用“制礼作乐”“以乐抒情”等方式,以展现出君子良好的伦理品性与崇高的理想信念。
君子的修成与音乐之间密不可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士对“君子”重新进行了诠释。孔子将德性修养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旨在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君子,通过建立崇高的伦理道德体系,从而实现“以德治国”的礼制政治目标。其中“以乐树人”便是儒学的重要举措。
孔子的“君子观”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包括了个人品德的内涵,也包括政治上致用的目的。孔子认为“君子”并不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修养,而是要达到“成己”和“成人”两个目标。“成己”就是个人道德品质上的修养,是自身的管理与约束,其实质是“安仁”;“成人”则是在“成己”的基础上,先将自身做到尽善尽美,以自身为典范,再通过政治上的引导,将“成己”推己及人,进而达到民众教化的目的,其实质是“行仁”的内涵所在。
孔子认为实现君子的人格,首先要有丰富的学识以及完善的人格修养。这些在其音乐上也有具体的表现。他认为君子要做到“博学于文”,所谓的“文”,主要就是指“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 其中“乐”便是实现“君子儒”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六艺”中居于次位。孔子自身也是以乐修身的典范。他十分喜好音乐,并且在琴的演奏上有着很高的造诣《。史记· 孔子世家》中就有详细的记载: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4]。
孔子学琴的典故充分地体现了他的务实学风。孔子所谓的“成己”,并不只是看重君子自身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这个途径,养成学而不厌、恪守自律的品性修养。孔子以自己学琴的经历,身体力行地展现了“君子儒”,实现了“成己”的自我修养。他认为,君子的修成首先就是要抛弃一切外在功利的欲求,以探求知识的本原为出发点,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思索,不断地精益求精,从而达到博学于文的目标。孔子强调,君子自身的修养应落实到日常的生活、交际、学习之中,依德而行,行中见德,才是君子之所为。
尽管“君子”自身的品性修养至关重要,但孔子所提倡的“君子”并非止步于此。他认为“学以致用”,君子应为统治阶级所服务。因此,“成己”只是君子修身的基础,其后在“成己”的基础上,行“君子之道”,进而实现“行君子之教以救世”的政治抱负,才是他的最终目的。孔子极力推崇君子之政,他指出想要达到和谐社会的目标,其首要任务是对于从政者的道德品性就要有严格的要求。孔子认为音乐能够培养君子的仁爱之心,使人明志,同时还能“与政相通”。
儒家主张“乐以治心”,即通过陶冶心性的方式,将个人内心的情感与乐所表达的情感相合,使听者内心产生一种情感的共鸣,从而对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以此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精神体系。“从感化人心来说,乐正是一种使人们乐于行‘仁’的最为有效的手段。”[5]通过“乐”来治教天下,对民众施行伦理的道德教化,已经成为阶级统治者治国理政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
德治是君子为政的原则,而乐是德治的媒介。《乐记》曰:“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6]通过音乐能够知晓一国政治的兴衰,国家和谐稳定、长治久安,在音乐上也会体现出平和、雅正的特点。因此,“以乐促德”是孔子建立和谐理想社会的重要组成。孔子认为,君子必须具备“德”的基本素养,在音乐上才能体现出“和”的特征。“通过潜移默化的陶冶、熏染,使不同人得以和,这乃是乐的重要功能。”[7]乐教成为君子治国理政的重要途径,君子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对民众进行文化和价值的熏陶,以此达到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的政治目的。
孔子认为君子应以天下之乐为己任,并以“乐教”这一形式而实现“君子儒”的修炼养成。孔子通过“乐”来培养君子良好的品性修养,以达成“成己”的初级目标。而君子学以致用,以乐为载体,通过“以乐养德”的方式来反映社会与人文的和谐,从而最终实现“成人”的理想人格。
礼乐是中国传统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以“礼乐”来培养君子的人格。“礼”代表着天地的秩序,是礼仪、制度的规范。“乐”则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涵盖。古代礼乐所指的范围十分广泛,上到国家政权的稳固,下到君子的行为规范,礼乐都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配合“礼”的实施,古人常常將“礼”和“乐”并用。《礼记· 乐记》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8]他们认为,礼乐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乐为内,礼为外,乐修内,可以感化人心,促使君子道德上的自省;礼修外,可以约束君子外在的言行、举止,使得君子的行为得到规范和约束。由此观之,礼乐教化的实质是道德教化,礼乐教化是德治的具体实现方式。
中国古代社会既需要礼的规范,又离不开乐的配合。礼和乐皆为治理天下的必要因素《。乐记》曰:“礼乐皆得,谓之有德。”[9]礼乐内外兼修,互通互融,以此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礼记· 乐记》曰:“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10“]礼”能够约束天地之间的秩序“,乐”能够使天地和谐。“礼”和“乐”相须为用,已成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
阶级统治者通过礼乐“别异”,以此划分上下等级的亲疏。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季氏八佾舞于庭”。这里的“八佾”是指奏乐舞蹈的规模。按照用礼的要求,季氏是大夫,只能使用四佾之舞,而他却用了“八佾”的规模,这显然是公然逾礼僭越,是对封建周礼的藐视。孔子对这种违礼的现象予以了强烈的批判。有鉴于此,礼乐是区分君臣、上下、尊卑关系的重要依据。“礼”是行为的规范,但倘若没有“乐”这种形式的外显,那么礼就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孔子所期望的礼乐制度是以符合客观存在为前提,通过君子内心对于礼乐的崇敬,进而自觉地区分上下等级,以此来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
礼乐具有“使民敬上”功用,中国古代社会以“礼”维护着封建宗法的等级制度。“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11]通过“礼”能够知道国家的政事,通过音乐能够知道一个人的德行。“礼”将音乐从一种感性的认知,提升到对君子道德伦理的追求。“礼乐”是衡量“君子”的重要标准之一。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是行为规范的外化,必须要通过“乐”才能得以彰显。而“乐”必须合于“礼”制约,通过“礼”才能合乎规范。尽管两者的形式不同,但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礼乐”的内在道德修养要求,从而达到内外统一、以德自治的政治社会功用。
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核心,礼乐制度就是内外兼修,自内而外地对君子实行思想上的教化。儒家以“德”来规范君子,通过礼乐教化,从而达到乐、教一体的目的,以此来实现儒家“以德治国”的政治理想。
儒家推崇“以乐致和”,其最终目的是达到道德的教化。是所谓“乐合同,礼别异”[12],礼的作用是使人有亲疏的等级差别,“和”的作用则是在这些差别中找到万物和谐共处的原则。
关于“和”的概念,最初在《国语· 郑语》中就有明确的解释:“以他平他谓之和”[13]。这里的“和”就是指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虽有不同,但都能根据自身的内在发展需要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这即是“和”的本质“。和”为乐的本义也是遵循这一原则,音乐的节奏和音调虽有不同,但从音乐的整体结构和框架中却呈现出中正、和谐的原则。和谐的音乐能够使人性情平和,通过乐的感化,进而实现“人和”“政和”,最终达到“天和”的目的。
但并非所有的音乐都能起到修养身心的作用,只有“和”为乐才能够体现人身心的和谐以及社会政治的和谐,反之,“淫声”则会扰乱人的心志。孔子对民风开化的“郑卫之音”一直是持有否定的态度,并明确地提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14]尽管孔子并不认同“郑卫之音”,但是他并没有因自己的喜恶而改变客观存在的事物。相反,在《诗经》中孔子还将“郑卫之音”客观地保留了下来。笔者认为,孔子之所以将“郑卫之音”留存下来,并不是让“淫乐”放任自流,而是考虑到现实的客观因素。所谓的“郑卫之音”只是一种外在音乐的表现形式,仅靠君子“耳不听淫声”,并不能真正意义上起到“和”的作用,孔子所说的“和”是指君子在面对“奢欲”之时,内心是否能够依然能够保持清净平和的本性,也就是达到人身心内外的统一,其实质就是通过“和乐”以达到“和心”的目的。
通过对音乐的艺术审美,能够窥知君子的品性和道德修养,因此音乐与内心所想要表达的感情也是互通互融的。荀子强调:“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15]这里“淫乐”主要是指奢靡享乐、扰乱心智的音乐。靡靡之音是满足声色享乐的欲望,带来的只是感官上短暂的愉悦。“淫乐”不利于君子道德品质的养成,久而久之,只会让人产生放荡和邪恶之心,相反,“和”的音乐能够使听者保持平和恬淡的心境。儒家认为,只有中正雅和的音乐才能使君子保持内心平和,以中正平和的心情去品味平和雅正的音乐,才能够对君子自身起到修身养性的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由此见得,“和乐”与“和心”两者是互为因果,相互制约的。
在孔子“中和”的乐论思想中,君子的身心和谐只是前提和基础,最终目的是顺应世间万物的和谐共生。《吕氏春秋》提出:“乐之务在于和心”[16],也就是说,人的快乐来源于人的内心,内心快乐听到的音乐才会和谐。“一个人根据其心理感应能力,可以产生道德行为,但是只有对方做出积极回应,这种道德行为才能真正发挥调节人际关系的功能,产生应有的社会和谐效果。”[17]所谓“和”为乐,即是指中正平和的音乐,也就是雅乐,其实质就是“德音”。这里所指的“和”除了音声中正、和谐的本质属性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和的情感。“和”需要讲究一定的原则,便是既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又要在此范围内恰到好处,以此达到事物的平衡与和谐的状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8]讲的就是快乐不能放纵,悲哀也不能过度,体现的即是中和之美的适度要求。“声出于和,和出于适”[19]这里的“和”即是适度、恰当之意。体现在“乐和”上便是君子作为欣赏的主体,应控制自己享乐的“奢欲”,做到适度;乐作为实践活动的客体,应合乎规范,做到合适。合适且适度地用乐,才能实现“和”为乐的最终目标。
儒家所提倡的“和”,带有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指向。只有“和”为乐才能身正,身正才能达到“和心”“和志”的和谐人格。因此,制礼作乐的最终目的就是达到“和”的统一,其本质也就是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
君子良好品性的养成离不开“乐”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因而它成为“六艺”中仅次于“礼”的地位。孔子所指的“君子”不只是独善其身的自我修养,而是肩负着胸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君子通过“礼乐教化”“以乐致和”等具体的方式来感化民众,并以自身品性修养为道德的典范,陶冶民众的性情,促使他们发自内心地“尊礼”“崇礼”,以此形成政通人和的社会风貌。音乐是传承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促进身心和谐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君子的品性修养通过“乐”这一途径得以彰显,他们从小我融入大我之中,以天下之乐为己任,以自身的品性修养推动社会美好生活的构建,从而进一步达到社会和谐统一的理想目标。
注释:
[1]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2]于民主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3]蔡先金等著:《孔子诗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290页。
[4]薛金学编著:《〈论语〉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7页。
[5]鄯爱红:《儒家乐教思想与和谐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41页。
[6]孙景琛总主编:《中国乐舞史料大典· 杂录编》,上海音乐出版社版,2015年,第77页。
[7]张锡勤:《试论儒家的“教化”思想》《,齐鲁学刊》,1998年第2期。
[8]叶朗主编:《中国美学通史(二)汉代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页。
[9]张岱年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
[10]蔡仲德注释:《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第2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677页。
[11]蔡仲德注译:《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上》(增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12]朱立元:《美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7页。
[13]朱立元主编:《艺术美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35页。
[14]季旭升编:《论语》,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页。
[15]〔战国〕荀况:《荀子》,〔唐〕楊倞注,耿芸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
[16]朱立元主编:《艺术美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0页。
[17]邓思平:《“克己复礼”是为和谐》,见: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编《儒学与世界和平及社会和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页。
[18]张宪军、赵毅:《简明中外文论辞典》,四川巴蜀书社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31页。
[19]朱立元主编:《艺术美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0页。
史文露 哈尔滨音乐学院学生
宁 汐 博士,哈尔滨音乐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