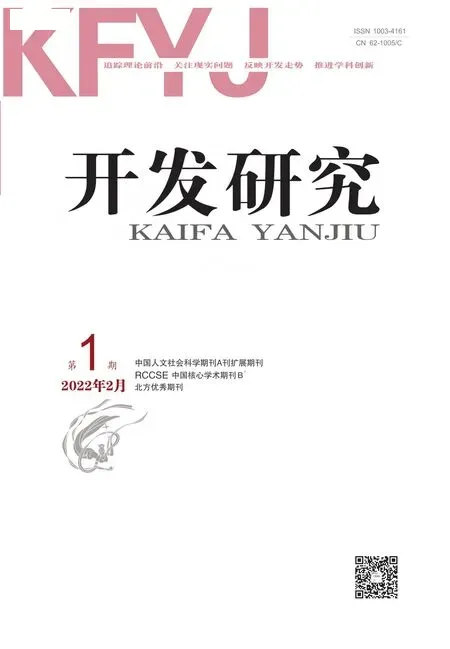国有资本份额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竞争框架的确立
马秀贞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 科研部,山东 青岛 266071]
一、引言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启动的初期就明确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和动力的综合性指标。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靠增加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发展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边际递减效应凸显,副作用上升,显然不能支撑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亟须加快形成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的增长模式。我国国有企业作为具有特殊性质和功能定位的经济主体,一直处于改革的前沿,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1]。2016年7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的批示中强调,“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这是由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重要地位、功能作用以及在改革中的关键性和基础性作用等因素决定的[2]。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对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断纠偏,平衡质与量的关系,这其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关键[3],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重中之重。
从2015年年底到现在,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历了从启动到深化,从“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八字方针”(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任务和内容的深化拓展,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规律,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追求的永恒目标。国有企业通过“去产能、去僵尸、降成本、降杠杆”以及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措施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其题中之意。国有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影响机制和逻辑怎样,提高国有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安排、政策框架应如何设计,值得深入研究。
在提高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陈茹的研究发现,审计改革提高了试点地区地方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包括规范政府干预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4];郭金花认为国家审计能提高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5],国有企业并购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在并购当年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高于其他年度,并购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高于并购前;Boardman等从公共政策角度研究发现,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明显提高了生产效率[6];熊爱华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金融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影响机制,认为引入非国有资本提高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却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挤出效应,在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弱或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挤出效应更明显[7];刘晔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国有企业改革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且在竞争性行业中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更优[8];庞雨蒙以中国发电行业为例,发现产权改革正向影响行业全要素生产率[9];任仙玲、刘天生分析了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及行业资本结构、国有企业民营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发现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混合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0]。二是市场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Hsieh等研究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时认为,中国产业组织如果能借鉴美国的经验将资源配置到高效率企业,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提高30%到50%[11];简泽认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引入市场竞争能够激励企业提高生产率[12];毛其淋从市场竞争的表象——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动态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尽管产业中新进入企业一开始生产率水平较低,但凭借自身显著的学习效应能够实现赶超存续企业的生产率目标[13];李平以产业内国有资本占总资本比例衡量产业市场化程度,认为市场竞争通过推高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宏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促进企业内部创新投入增长进而提高微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3]。可见,学术界基本认为市场竞争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也有研究认为针对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市场竞争反而会抑制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14]。
上述研究为提高国有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思考的视角和方法,但也有不足,没有区分国有企业所处的市场类型。事实上,根据市场竞争状态,中国经济存在两个系统或者说二元经济[15]5:一是受政府严格监管的子经济体。该经济体具有较强的市场准入壁垒,主要依赖行政手段进行资源配置,且国有企业集中度较高,大都是垄断性或垄断竞争性市场。二是开放竞争的子经济体。该经济体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市场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15]296-298。鉴于行业市场竞争状态存在异质性,非国有资本份额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有区别以及行业竞争异质性在非国有资本份额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是否起到调节作用?如有,其大小和方向如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拟依据产业性质及其规制状态[15]296-298,将中国全部工业2位数代码产业划分为自然垄断、完全垄断、政府偏爱的国有行业和市场开放[15]296-2984类,然后分子样本考察国有、非国有资本份额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最后引进行业竞争异质性与国有资本份额交互项考察行业异质性的调节效应。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资本份额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促进作用受行业竞争异质性的影响,同时,行业竞争异质性的调节效应具有显著差异。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1)在研究视角上,本文站在中国市场经济的二元结构角度,分析了市场竞争异质性在国有资本份额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目前,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比较不同股权结构下企业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得出了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行业效率低下等较为一致的结论,且普遍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缺乏对市场竞争异质性调节效应的探讨。刘晔[8]在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虽然考虑行业竞争异质性因素会得出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结论,但仅将中国行业简单分为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其研究结果的“中国特色”仍未得到完美诠释。(2)在研究结论上,本文佐证了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混合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也发现相对其他行业,开放竞争性行业中非国有资本份额的上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且行业竞争能正向调节两者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两个假设:(1)行业的非国有资本份额越高,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且这种抑制作用受行业竞争异质性影响;(2)行业的竞争异质性对非国有资本份额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市场竞争越强越有利于非国有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为验证研究假设,本文拟根据市场竞争异质性划分的子样本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非国有资本份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引入市场竞争状态与非国有资本份额的交互项,探讨市场竞争性质差异的调节作用。
(二)样本描述
本文选取的初始样本为2000—2017年的我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①。在后续测算行业资本投入时,以2000年为基期,获取初始资本存量,获得2001—2017年各行业资本投入数据;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以2001年为起始年份进行计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鉴于我国工业行业统计标准在2003年和2012年有所调整,本文在时间维度上为保持行业一致性,同时考虑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剔除2002年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剔除2003—2011年的“其他矿采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合并2002—2011年的“橡胶制造业”与“塑料制品业”,记为“橡胶与塑料制品业”;剔除2012—2017年的“开采辅助活动”“其他矿采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和“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合并“汽车制造业”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运输设备修理”,记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经过上述行业调整,本文最终研究样本为36个工业行业,样本期为2002—2017年,共计576个样本。
(三)模型的构建
在对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后,本文决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基于两个理由:(1)样本是面板数据,具有个体和时间两个维度,如果仅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结果会出现偏差;(2)本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通过控制样本个体的差异,减少其对模型回归结果的影响。在此设定全样本回归模型如下:
TFPi,t=α0+α1Inogrowthi,t+α2Controli,t+λi+εi,t。
(1)
其中,下标i代表行业,t代表时期。TFP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行业i在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Inogrowth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行业i在t时期的非国有资本份额增长率,Controli,t为控制变量。α1为本文所关心的核心系数,表示非国有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及大小。若α1显著为正,说明非国有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积极影响。此外,α0为常数项,α2为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λi为行业固定效应,εi,t为估计残差项。
为研究行业性质与政府规制状态在非国有资本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文拟采用两条路径进行研究。
第一,将全样本依据产业性质及其规制状态划分成4个子样本,记为Statei,若Statei=1,则表示该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若Statei=2,则表示该行业属于完全垄断行业;若Statei=3,则表示该行业属于政府偏爱的国有行业;若Statei=4,则表示该行业属于市场开放行业。同样地,使用全样本回归模型研究子样本,为方便标识,本文将全样本、4个子样本回归结果分别记为全样本、子样本1、子样本2、子样本3和子样本4。
第二,量化产业性质及其规制状态,记为Marktetstaet②,使其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纳入全样本回归模型中,单独考察不同产业性质及其规制状态对非国有资本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TFPi,t=β0+β1Inogrowthi,t+β2Inogrowthi,t×Marketstatei,t+β3Controli,t+λt+εi,t。
(2)
其中,Inogrowthi,t×Marketstatei,t为非国有资本份额增长率与市场性质及其规制状态的交互项,用以衡量市场性质的调节作用。其他变量含义与模型(1)中相同。模型(2)中,β3为重点关注系数,若β3显著为正,则说明模型研究的市场性质正向调节非国有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四)变量的定义及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TFP)本文运用Stata软件中的malmq2③命令测算2002—2017年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所需行业产出和投入指标如下:(1)行业产出指标。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原价)衡量行业的产出情况,其中在假定2017年行业销售产值增速与2016年相同的条件下,推算出2017年各行业的工业销售产值。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2)行业投入指标。①劳动投入指标。以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衡量,其中,因相关统计年鉴未直接公布2014—2016年的工业企业分行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故此处采用“主营业务收入/人均主营业务收入”公式估算出的行业从业人数替代。②资本投入指标。借鉴赵玉林[16]的经验做法,将2000年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视为初始资本存量,利用当年与上一年的累计折旧差额和上一年的固定资产原价测算出当年折旧率,以当年与上一年的固定资产原价之差作为当年行业投资额,最后运用永续盘存法原理计算出2001—2017年各行业的资本投入。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2.核心解释变量:非国有资本份额(Inogrowth)
采用行业实收资本中非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金、法人资本金、个人资本金、港澳台资本金和外商资本金)占比的增长率进行衡量。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3.控制变量
(1)行业研发能力(Rec)。本文采用各行业R&D经费内部支出占工业R&D经费比例的增长率衡量行业的研发能力。该指标数据越大,说明行业的研发能力越强,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10]。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行业资产负债率(Lev)。王玉泽认为合理的杠杆率水平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而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侧面反映企业创新水平[17]。本文预期行业资产负债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会因行业性质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
三、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一)规模以上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过程与结果
本文运用Kerry Du教授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Stata命令malmq2测算我国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参考文献[10]测算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测算出2002—2017年我国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图1展示了2002—2017年我国自然垄断、完全垄断、政府偏爱的国有行业、市场开放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④。我国的现实背景似乎暗示当行业越处于竞争状态,即推行竞争型产业政策时,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图1 我国4种市场类型的全要素生产率趋势图
由图1可知,2002—2017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分行业性质看,自然垄断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2—2004陡然上升达到峰值,随后处于波动状态,201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与2002年持平;完全垄断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则呈现下降趋势;政府偏爱的国有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走势呈现“V”形,于2009年达到波谷;市场开放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则表现为上升趋势。不难发现,2017年我国市场开放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最高,其次是政府偏爱的国有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次之,完全垄断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最低。
(二)结果分析
1.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表1汇总了全样本及子样本下的回归结果。

表1 非国有资本份额与全要素生产率
列(1)为全样本回归结果,列(2)~(5)为子样本回归结果,其中子样本1描述的是自然垄断行业非国有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子样本2刻画的是完全垄断行业的非国有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子样本3反映的是政府偏爱的国有行业非国有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子样本4反映的是市场开放行业非国有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实证结果与预期保持一致,非国有资本份额增长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行业内非国有资本份额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从市场竞争分化角度来看,市场开放行业非国有资本份额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其他市场性质的行业,且随着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非国有资本份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
本文注意到,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控制变量——行业资产负债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因行业竞争性质不同而表现出异质影响。自然垄断和政府偏爱的国有行业的回归系数为负,虽然不显著,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针对国有企业的“去杠杆”政策取得积极成效;有超强政治联系的完全垄断行业(烟草制品业)因其稳定的政府隐性担保导致资产负债率显著促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样地,市场开放行业资产负债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比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资产负债率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异质性表现,恰恰佐证了中央提出的“结构性去杠杆”政策的合理性,即降低高负债国有控股行业的杠杆率,稳定其他行业杠杆率,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2.行业市场竞争异质性分析
为考察行业性质及其规制状态对非国有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引入行业性质及其规制状态与非国有资本份额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行业市场竞争异质性分析:非国有资本份额与全要素生产率
不难发现,完全垄断和自然垄断行业性质负向调节非国有资本份额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政府偏爱的国有和市场开放行业性质正向调节非国有资本份额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即非国有资本份额对非完全垄断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高于完全垄断行业全要素生产率;非国有资本份额对非自然垄断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强于自然垄断行业。这可能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相对于非完全垄断和非自然垄断行业,完全垄断和自然垄断行业基本是国有资本份额较大的行业,其非国有资本进入门槛较高,因而,非国有资本对非垄断性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第二,囿于国有控股行业存在产权不清晰、严重的委托代理等问题,国有控股行业对非国有资本的利用更为粗放和低效率,而非国有控股行业能够十分集约和有效地利用非国有资本,激活非国有资本在行业运营过程中的“创新本色”,从而能够有效促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与刘晔[8]的研究结果不同,本文发现政府偏爱的国有行业性质⑤与非国有资本份额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正,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政府偏爱的国有行业是现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然而改革需要一定的周期才能将政策落实到位,回归结果暗示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运营改革成效显著,但仍需继续深化。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市场经济二元结构角度分析了非国有资本份额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根据上述实证结果,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表明非国有资本份额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工业行业内非国有资本份额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符合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低下的事实判断。其次,政府偏爱和市场开放这两种市场性质对非国有资本份额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其中,这种调节作用在市场开放行业中更为显著,表明在市场开放行业中非国有资本份额越高,越有利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再者,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和强度也表现出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最后,从行业竞争异质性角度来看,非国有资本份额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相比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政府偏爱、市场竞争这两种市场类型对该种促进作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且这种调节效应在市场竞争领域中更为显著。
(二)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表明,无论产业性质如何,充分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皆具有促进作用,但强度上存在差异:与垄断性行业相比,在政府偏爱和市场开放的市场类型中,非国有资本份额和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相关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市场开放领域中正相关关系更强。研究结论一方面为相关部门针对不同行业调整其政策管控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揭示了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促进了充分竞争对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性。为此,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稳妥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运营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国企(行业)效率。国控因素较强的行业通过混合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不仅能淡化市场身份,促进不同类型的资本进行优势互补,而且还能提高国有控股行业的经济效率[8]75。当前,我国工业行业生产效率并不高,尤其国控行业更是逐渐成为低效率的代名词,通过混合不同资本来提高国控行业的效率,这对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第二,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当针对处于不同市场类型的企业采取差异化的改革策略,分类改革,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本研究发现,完全垄断行业(烟草制品业)目前主要采取“去杠杆”方式实现效率的优化,缘于其天然的政治联系和独特的行业属性约束以较小概率采取混合所有制,而市场开放和政府偏爱的国有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潜力巨大,应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着力点,激发全要素生产率梯度上升。
第三,思考如何平衡和协调产业政策同竞争政策的关系。事实证明,产业政策重点关照国有企业的做法,既破坏了公平竞争,也没有带来国有企业应有的效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若干重要行动来解决部门垄断问题和减少市场进入壁垒,如修订反垄断法,大力度改善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建设,这些举措减少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碰撞。要使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互为支持,在国有企业层面,应明晰实施产业政策的标准,缩小管制产业范围,采用非歧视的产业政策工具。有效的产业政策应该促进竞争和创新而不是损害竞争效率或带来市场竞争的负面影响。选择性产业政策重在关注市场失灵领域,例如,贯彻国家战略意图的产业,支持某些自然垄断行业,但要考虑政府行动的潜在成本,选择对市场公平竞争影响最小的政策工具,在自然垄断行业也要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我国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就必须实现产业政策的现代化[15]51-66。
第四,思考如何把国有企业纳入竞争政策的框架,让国有企业更充分地服从竞争市场和竞争政策体制的约束。前述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国有资本份额与全要素生产率呈反向相关关系,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发挥和竞争不充分,缺乏有效竞争,反映了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现状。我国国有企业构成了管制子经济体的核心,许多国有企业享有市场进入壁垒的保护和政府扶持,作为干预主义动向产业政策的执行者,大多数国有企业享有优惠待遇和资源的优先获取权,而不用在市场中通过竞争获取,这不但挤出了通过竞争配置的资源,而且还由于缺乏市场竞争的约束,削弱了国有企业提高效率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将国有企业纳入市场竞争体系的前提是准确定位国有经济的目标和作用,除市场失灵的产业、国防产业、公共产品和服务产业外,所有商业性国有企业都应该逐步推进参与市场竞争,缩小非竞争领域受管制的子经济体的规模和范围,扩大竞争性经济体的规模和范围。将国有企业纳入市场竞争框架,需要推进3个领域的改革:一是改革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和公司治理,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开展经营活动;二是政府改革确保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不受干扰,停止对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指令和政府限制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控制;三是确保国有企业受市场竞争约束,遵守有关市场竞争法律规范。改革国有企业,有利于确立竞争政策的框架体系。
注 释:
①关于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指标数据,例如工业生产总值、工业销售产值这两个核心产出指标,国家统计局现只公布到2017年。
②此处,若探讨自然垄断行业性质的调节作用,则将自然垄断行业量化为“1”,非自然垄断行业为“0”。同理,探讨其他行业性质的调节效应时,以此类推。
③该命令来源于:Kerry Du,2019.“MALMQ2:Stata module to compute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Statistical Software Components S458716,Boston Colleg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revised 02 May 2020。
④在同一市场性质下,本文将所属该性质的行业数据进行简单平均,以此代表该市场性质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⑤学者刘晔(2016)将本文中政府偏爱的国有行业划分为垄断性行业,认为在垄断性行业中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