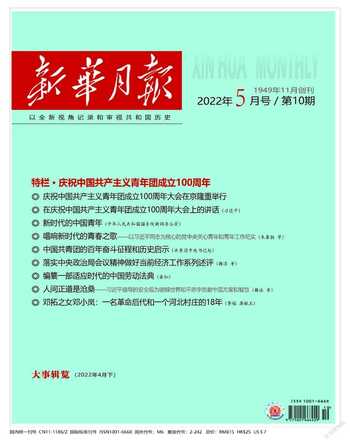林争平:心里至少上千个画家,才敢站在那儿
孙凌宇

在各样导航APP日渐精进的今天,大概没几个人能抵挡住出门在外依赖手机的诱惑。但不知是出于对智能时代的负隅顽抗,还是自信与生俱来拥有不一般的脑容量,反正过去几十年,林争平都是这么犟着过来的。
他是“行万里路”的忠实信徒,年过六十,仍北极南极地跑,疫情前2019年还去格陵兰岛爬冰川。他对各地的文化艺术痴迷,至今走访了120个国家。没人给他布置任务,说起来都是些不赶时间、自顾自的“文化考察”——哪怕到了玛雅文化的发源地尤卡坦半岛也不请向导,出门前,把地图“印”在脑海里,不留余地地出发,铆足了劲地观察。
不求看全但得深钻,他身上保留着过去一类旅人有所侧重的作风。“事先我对美术都了解,比如说看鲁本斯那幅《抢夺留希波斯的女儿们》,在慕尼黑。我到了博物馆,就是要看这画来了。如果是看勃鲁盖尔,要不就是布鲁塞尔的皇家美术馆,要不就是奥地利。(看的时候)我细心了,花心思了,态度认真了,所以就记得住。要带着问题,或者带着这种理解和综合的历史观美术观,和走马观花就不一样。”
凭借过去几十年脚踏实地的积淀,如今他的脑海里随时能摊开一张艺术地图,“巴黎有七个火车站。去吉维尼的莫奈故居是圣拉扎爾,你要去瑞士是东站,去荷兰是北站”,甚至形成了独有的搜索引擎。聊到具体的作品,他从创作始末到收藏脉络,直至如今存放在哪座美术馆都能脱口而出。
“昭陵六骏的那两骏,1914年被盗卖到国外,在宾大博物馆(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里面,没在大都会,也没在华盛顿。
“梵高的《向日葵》,就不说那小的,大的《向日葵》一共就四幅,两幅15朵,两幅12朵,15朵的一幅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还有一幅在伦敦国家美术馆,那个美术馆不在大英,在特拉法加广场,特拉法加就是当时英国跟法国两个舰队——还是帆船时代——打仗,英国人赢了,经此一役建立了海上霸权。广场立的大柱子上面就是当时的舰队司令纳尔逊将军,后边那一片楼就是国家美术馆。英文的画廊和美术馆是一个词,gallery,你不能翻成国家画廊,这不对的。
“还有两幅12朵的,背景不是黄色,而是蓝色,一幅就在费城,不是在宾大,是费城的博物馆,还有一幅在慕尼黑。还有一幅拍卖了,日本的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买的,但那幅有争议。欧洲的一些专家联名发表过一个声明,说他那幅是赝品。
“我去东京仔细看过,就搁在新宿西边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大厦的美术馆里。仔细看了以后会发现,它的笔触没有那么自然,有描的感觉。而且那四幅全有签名,他签名不是梵高,梵高是姓,他签的文森特,日本这幅的花瓶上没字。当然不能说没字就不是(真迹),这不能是唯一的证据。况且他也是拍来的。20世纪80年代拍了几千万(3900万)美金,当时听着我都晕菜了,80年代中国人才挣多少钱?三四十块钱养一家子!”
“拍卖会上买的也不排除有假?”
“这话说起来太复杂,”作为国内1997年拍卖法颁布后第一批考取资格证、从业二十多年的拍卖师,林争平笑道,“就这一件事咱能从早上聊到晚上。我们这一行挺有意思,好玩,一直到老了你看多有意思。咱俩就随便一聊,这刚聊出来小手指尖都不够。”
“他再无知也不能挖苦讽刺他”
早些年为了避免拍到仿作,有人到了拍卖场只买图录的封面作品。林争平解释,“封面不就是脸吗?肯定不会是假的,假的不就打脸了是吧?而且肯定是精品,升值空间有保障,这是从商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买封面肯定不会错。”
竞拍者思路不一,爱好各异,台下揣手坐着的,有财大气粗的商人,也有功力深厚的藏家,这就要求台上负责简短介绍藏品的拍卖师,既不能太浅薄,又不能太骄傲。“我们可以点一点基本的年份,鼎盛时期之类的,但是你不能说太多,而且得根据现场的气氛临时决定说什么,没法彩排,也没法做功课,只能靠你的功底。”
有一回林争平主持拍卖一张齐白石的画,“齐白石、张大千,都是拍场上最常见的,大概80%以上的拍卖图录都印齐白石,但也有少部分印齐璜,我们这行里谁说齐璜?我就说下一件123号齐白石《群虾图》。底下一个人,立马说拍卖师,念错了,这是齐璜。你想这种事它能发生吗?它就能发生。”
“按说我就应该损损他,连这都不知道,你还上拍卖场,回家去,先学去。但是你不能损他,他再无知也不能挖苦、讽刺他,来的都是客人,都是上帝。我就说对不起,先生,因为齐白石是1864年的,那都是清代的了。过去这些古人跟咱们不一样,他们有字有号,齐白石有好几十个号,白石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下边有业务经理,请他来跟您解释。说完不到5秒,那人便知趣地离场了。”
一口发自丹田的京腔,一双丹凤眼笑意盈盈,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作为拍卖师的林争平时刻谨记“一定要客气”。2021年12月,在他主持的北京华辰秋季拍卖会上,几个小时下来都是这副亲切做派。
在这场金钱游戏中,人们既体会到了数字飞涨的刺激,同时又享受着和煦的氛围,没有压迫感,但这在林争平看来,不过是拍卖师外显的风格,真正的内核在于,“没有这底子你上哪儿亲切去,你就全说的外行话,全踩不到点上是吧?”
主持拍卖绝非在台上喊个1234那么简单,林争平曾见过一些电视台出身、得过金话筒甚至主持过春晚的主持人尝试拍卖,很多时候都没有那么得心应手。原因就在于主持拍卖需要长年的准备,“拍书画,张大千、齐白石都分不清,怎么拍呀,心里至少上千个画家,才敢站在那儿。从陶到瓷、青铜器、家具、杂项,你全得知道。瓷器,那少说从唐代开始都差不多1500年了,玉器都8000年了,从红山就开始了,明清的古典家具也600年了,你得装多少知识?”4150D57C-C51C-4700-8F08-C18A603A0091
“还得学历史,因为它那东西都跟历史挂着,汉代就是有汉代历史氛围的东西才那样,唐代人都胖,所以它东西都是胖的。拍古琴,你至少仲尼、伏羲、蕉叶你都明白吧?你以为是松木做的,以为是榆木做的,以为是黄花梨做的,但它们都是梧桐木的,你都别提,那知识量太大了。这行不允许胡说八道,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装不了,没法假装。瞎侃,你侃不了。”
1997年他去上海参加国内第一届拍卖师资格证考前培训,那年一共举办了三次,共计几百名考生,到现在还在做拍卖师的寥寥无几。“这个行业难度比较大,因为它知识量太大了,别人一说齐白石一张画一九六几年画的,你还说这画不错挺好的,但齐白石1957年就去世了,你全得知道,要不然你会出错的。聊天都没法聊,你就出局了。”
“稍一走神,准错”
国内如今拍卖师资格考试的通过率仅为百分之十几,考试内容仍然是四门,三门理论加一门实际操作,唯一的变化是以往理论部分(拍卖基础、拍卖案例、经济基础)的最后一项取消了(由于涉及签合同,经济基础包含了消费法、合同法等条规以及GDP、GNP等经济概念),换成了拍卖常识。
拍卖分为艺术品和资产两个大类,房地产、破产企业、海关罚没,包括冠名权、知识产权都可以拍卖,还有汽车等物资。依据物品性质不同,拍卖速度的快慢也会有所变化,其中艺术品拍卖相对而言速度最慢。
林争平模仿起在东京码头看过的拍卖金枪鱼的场景,鱼从渔船上拿下来拍完就得进冷冻库,太阳晒一会儿就晒化了,因此必须快,叫价时嘴皮子几乎都没空隙合上,“1000、2000、3000,下一个。”
从第一次在国外走进拍卖场,拍卖师就给台下的林争平留下了“机智、聪慧、口才一流”的印象,至今过了近30年,他少说看过几千场。2015年大收藏家安思远去世,在纽约持续了一个星期的拍卖他也没错过。
艺术品拍卖虽不至于像其他品类那般火急火燎,但拍卖难度却有增无减。商品依据起拍价所在的区间在竞拍举牌过程中需要拍卖师按照不同的阶梯公式计算。一般国内现在通常分为三个阶梯,佳士得和苏富比则是四个等比阶梯:1-2之间是1,2-3之间是2,3-5之间是2、5、8,5-10之间是5,意思是起拍价在10万-20万之间的艺术品,台下每举一次牌就代表着出价增加1万;起拍价在20万-30万之间的艺术品,台下每举一次牌就代表着出价增加2万,依此类推。
拍品的出场顺序并非按照起拍价的高低依序排列,相隔拍品间的价格差异往往很大,需要不断调整计算方式,而且不同公司的拍卖会可能规则还不一样,都需要敏捷的反应。在拍卖协会做培训师时,林争平偶尔会遇到外语系出身的学员,即便英文能力扎实,但面对英文的数字拍卖瞬间还是反应不过来。“一磕巴自己就慌了,一慌那就全乱套了。”
出错是拍卖师的大忌。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不间断的拍卖中,拍卖师不仅要维系外部形象——站姿不能七扭八歪,身体得板着,拿着个劲;嗓子不能喊5分钟就劈了,“即使别着无线麦克风,但如果用的是平日说话的声音,会太薄,没有穿透力,打不出去。得用类似美声的发声方式,且语音至少得有抑扬顿挫。”林争平的基本功训练是念诗歌,“宋词比唐诗好,没那么规整,有助于对语言、词句的掌握和控制”;最后一点,“喝水还得不上厕所。”
这些体力的考验相对而言可能都算是小事,拍卖师面临的最大难关是丝毫不敢走神,“稍一走神,准错。”不但要高速计算,而且全部的器官都得高度集中,时刻关注台下竞拍者的神态,“下边好几百人,有些老行家,谁给你拿一牌老老实实举着,有的号牌都不举了,手指一晃,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犄角旮旯,你都得及时看见。”
毕竟拍卖不是单方面的表演,“我得知道他们的心态、举止,比如一幅张大千的山水画,通过对当今艺术市场的了解,假设值1000万,那么从100万起拍的时候,就叫得很轻松,快到八九百万的时候,则要开始引导,他们要考虑,要给他们充分思考的时间。买家里北方人南方人都不一样,北方率直,南方细腻,琢磨的事情多一点,山西的商人跟浙商能一样吗,所以拍卖时还得时刻把握人的心态。”
“只预测下限,往上能拍多少价,不知道”
置身艺术品交易的第一现场,身为拍卖师如何看待不同作品天壤之别的命运、抽象的价值如何被赤裸的价格定义,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林争平而言,一方面他直率地坦言,个人喜好上他对于时下涌现的新艺术确实欣赏不来。他称Kaws的作品为“叉叉眼”、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代表装置为“大气球狗”,“我可能理解稍微差一点,原来我们看什么破塑料,一百块钱我都不要,现在上万了。班克西(Banksy)的作品全是涂鸦,现在都上亿了”。这种破除崇拜的态度倒是和艺术家本人的嘲讽态度不谋而合,Banksy2021年在直播中被烧毁转化成NFT、賺足眼球的数字艺术作品名称便是:I cant believe you morons actually buy this shit(真不敢相信你们这些白痴会掏钱买这种垃圾)。
但另一方面,林争平也完全能理解这些作品的走红以及市场的追捧。疫情开始以后,传统行业受到冲击,多个短视频平台都曾前来找他入驻,希望他开个人频道讲艺术类的内容。在沟通的过程中,有负责人就表示,“我们这行三十多岁都算老的了,40岁早退休了。”
因此,在林争平的观察和理解里,“现在出来一批有钱的全是二三十岁的人,他们对传统那些东西不感兴趣了,所以买叉叉眼了,买大气球狗了。时代在变化,保利现在也在办潮玩展了。”
杰出艺术作品的观念不是自然出现的,而是一套繁复体系造成的结果,其中涉及资助关系、意识形态、金钱与教育,又受到大学课程与美术馆的支持——我们认为什么样的艺术作品特别值得注意,都受到这些因素的引导。
林争平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全在博物馆里,你怎么炒盘?市场还得活跃,它得维持流动,因为经济它得转,你没东西它怎么转?所以之前市场最主要的就是印象派的东西,印象派再往前,你看市场上就很少出现了。莫奈1926年才去世的,离咱们还不到100年,所以他这些东西市场保有量还相对多,但现在印象派也赚得差不多了。你得不断有新东西,印象派再往后,就是安迪·沃霍尔、巴斯奎亚等等,包括现在的Kaws、昆斯。”
1997《拍卖法》刚颁布的那年,北京一年也没有几场正式的拍卖。九几年林争平刚入行时听到拍出100万,都觉得“我的天”,“齐白石当时几万块钱一张,好一点的十几万就不错了。现在少说几百万,稍微好一点就卖上千万了。保证金如今也水涨船高。最开始只需要交一万块钱,后来就5万、10万,现在如果你要拍5000万的东西,提前交一两百万都很正常。”
到了2003年下半年,他切实感受到中国艺术市场的红火,“腾的一下,活儿太多了,一年大概我多的时候要拍100场,等于三天就拍一场,全中国大概除了西藏没去,我基本都去了。”见证了从无到有以及瞬间的爆发,2005年,他主持拍卖的傅抱石的《雨花台颂》成交价为4600万,创下当年全国最高纪录,再之后出现2009年的峰值,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亿元时代”,他便觉得没那么意外。
“我们这个行业一般只预测下限——最少能拍多少钱,往上不知道。社会在发展,它和人均GDP有关系。”
二十多年前入行时,他看到的是艺术品升值的巨大空间,“西方的艺术品基金,人家玩了至少一百多年,清代人家就开始玩了,一切都有迹可循。那些东西他们当时买的多少钱,现在多少钱,翻了一万倍!100年一万倍,一年10倍!”
到现在吸引着他仍然站在台上的,更多的是艺术世界的魅力,“为什么我现在愿意干这个?这个行业有意思,也没有退休这一说,经常拍的时候看到一个之前不知道的,你活到100岁,到100岁也学不完。”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22年第6期。作者为该刊记者)4150D57C-C51C-4700-8F08-C18A603A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