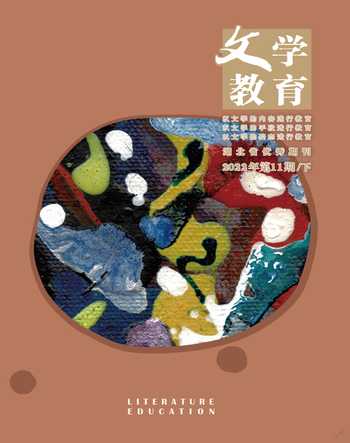电影《魂断威尼斯》中的疾病叙事及启示
朱雯熙 董家辰
内容摘要:电影《魂断威尼斯》(Morte a Venezia)是一部由电影大师卢奇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执导的剧情影片,于1971年在英国首次公映。该片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作曲家阿森巴赫因沉醉于追求青春与美,而不幸丧失性命的故事。本文将以“疾病”与“死亡”作为观察视角,探讨面对心理疾病时,情感与理性之间的纠结矛盾的心路历程,从而真实体悟影片中的疾病叙事手法,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疾病”带来的生存困境与社会影响。
关键词:《魂断威尼斯》 疾病叙事 死亡 理性 唯美
美国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一文中写道:“不同与生活的‘多彩,疾病即是‘阴暗的,它使得公民陷入麻烦的身份之后。当人降临世间时,往往拥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属于‘健康王国(The Health Kingdom),另一方面则属于‘疾病王国(The Kingdom of Disease)。尽管所有人都不断追逐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总有那么一些时间,我们不得不暂时成为疾病王国的公民。”[1]作为电影《魂断威尼斯》的重要组成要素,“疾病”以隐喻的方式推动着电影情节的发展,也如时代符号一般,影响着社会、道德与政治观念。[2]
德国作曲家阿森巴赫(Eisenbach)在经历丧女之痛后,来到水城威尼斯散心。在一次进餐时,他偶然遇见了“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喀索斯、无与伦比的艺术作品一般的”美少年——塔奇奥。经历惊鸿一瞥的他,从内敛自制、理性克制变得病态疯魔。看到少年行走的风度和俊美的容颜,他用“妙啊,妙”表达爱慕;看到少年在海滩玩耍,他的爱慕之心开始“变本加厉”。看到少年对讨厌的人恶狠狠一瞥时,他赞叹少年的“鄙弃庸俗的生活态度,对神圣而超然的生活赋予人情味”;看到少年在沙滩上呈现年轻的昳丽形貌时,他感慨“年轻而完美的形体体现出多么高的教养和深邃静谧的思想”;当老艺术家不断追随美少年的脚步,感受精神美的化身时,突出其来的霍乱席卷了威尼斯。陷入危险之中的阿森巴赫仍流连于少年的美,不愿离去。最终沉溺于唯美的艺术家在海边久久凝望着少年,悄然离世。
一.“疾病”——感官享受的描绘者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提出“中年期心理危机”的概念。在他看来,“我们愈到中年,愈易固守于个人之观点与社会之圈子,并觉得我们似乎已经寻到了该走的人生途径、适当的理想与行为准则。因此,就其外表看来,我们便视之为天经地义的事,然后便毫不考虑地固守住它不放了。我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即在社会上要想有所成就,便须以收敛我们的个性为代价。许许多多我们须真正去体验的生活经验,都聚集在一间盖满灰蒙蒙之记忆的杂物房里,甚至像是灰烬中那炯炯发光的煤屑。”可见,人到中年时,由于成家、立业,且已有一定的成就,看起来是最为幸福和谐的时期。但荣格指出,对于中年人来说,这也是新的自我评价的开始。此时的中年人往往由于体力的衰退、青春的消逝、理想的暗淡,从而出现心理危机,容易觉得人生失去欲争取的对象与奋斗的意义,注意力会从顺从外部世界转变为关注自己的内心,不断增加的压力会使其产生自我怀疑的倾向和“悬在半空中”般的失落感,并以“中年期心理危机”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中年人需要寻找到一种新的价值来充实自己,从而发现生活的意义。[3]影片的主角阿森巴赫身上正体现了这种典型的“疾病症状。
影片对小说中提及的主人公进行了虚构化处理,赋予其警官之孙与法官之子的身份背景,一方面,他的父辈“为君王与国家服务,过着严谨而简朴的生活”,并将严谨的品格、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遗传给了他,使他能“专门为一部作品呕心沥血、矢志不渝”,另一方面,他又从母亲那里承袭了艺术家的细腻与奔放,并将这种“蠢蠢欲动”压制在心底的无意识之中。此时的阿森巴赫为声名所累,连带身体也不堪重荷,对生命的厌倦,对艺术的迷惘将阿森巴赫推入了疲乏困倦的“深渊”。他不愿与外界接触而停留在自我封闭世界中,去探寻精神世界的意义。为了获得精神的暂时解脱和释放,他踏上了前往威尼斯的游轮。
在沉闷炎热的水城威尼斯,肆虐而致命的霍乱悄然而至。身处于这样的极端情形下,不免人心惶惶、纷繁不安。可见,疾病塑造了影片中的忧郁情调,而忧郁的情调又与少年俊朗的外表与蓬勃的朝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放大了少年“古希腊雕塑般的美颜”。沉迷不已而欲求不得的心理状态,正是中年阿森巴赫的“新的价值”。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说,“思想最深刻者,热爱生机盎然”[4]。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的威尼斯仍是一幅欣欣向荣、富有生机的图景,没有突出其来的霍乱,没有阴沉忧郁的天气,阿森巴赫可能无暇顾及美少年塔奇奥,也不会就此沉溺于感官感受,更不会失去原本的理性,疯狂地迷恋上他。可见,“疾病”在影片的开篇即有不容小觑的作用,不论是在营造焦灼的气氛,还是推动阿森巴赫的情感变化,都建立在疾病叙事的基础上。它让阿森巴赫敢于张扬情感,又让情感在疾疾病的衬托下不断升华。因此,疾病描绘并升华了感官所感受到的唯美。
二.“疾病”——隐匿情感的传递者
“同性之爱”无论放在当时的意大利,亦或现代社会都是一个晦涩的禁忌。然而,这正是纠缠了小说的作者托马斯·曼一生之久,但又不敢表达的内心困境。他曾对自己的妻子表示“我無法过多与你相伴,因为我无法在你这里得到全部幸福,因为我有我的使命”[5];也曾对哥哥表达了“对幸福怀有道德苦行憎”的疑虑。事实上,“隐匿性”与“消失性”是技术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必然影响,由此而来的“现实”与“实在”的界限模糊与个人情感的“脱域”都需要被再次探讨。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阿森巴的情感发生并未“并不按照具体的、可感知的、确定的现实所规定的路径,而是以一种隐去的看不见的形式对他本人与世界发生影响”[6]。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森巴赫的情感虽然是看不见的,但其实在性却从未减少。从这个层面出发,阿森巴赫正是“无法摆脱心理折磨”的托马斯·曼的化身。在主人公的心理危机与精神困境中,一种无法言说的爱欲被传递出来。
作为一位小有名气的作曲家,无论对创作的曲目还是自身的人格,阿森巴赫都恪守准则。然而,当他遇到塔奇奥之时,原本对于艺术的厌倦又重新坠入了极具震撼力的美感之中。一方面,他内心感叹于少年“臻于完美的极致”,另一方面又因自己轻易地受到诱惑而深感愧疚。即使阿森巴赫在精神上不愿承认对美少年的爱恋,但思想上也早已背叛了他。当塔奇奥在沙滩上玩耍,阿森巴赫一边观察着少年的一颦一笑中潜藏的魅力,一边以其为原型,刻画进自己的短篇小说里。在阿森巴赫看来,“他的灵性已与另一个肉体交往,并已结出果实!”此时的阿森巴赫似乎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不可言说的秘密,在内心的谴责中,他耗尽全身力气,整个身体垮掉。然而,当满怀忡憬的阿森巴赫看到少年再次对他微笑,他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情感,自言自语道,“你别像那样笑了,你别对任何人像那样笑。我爱你!”
纵观影片,主人公阿森巴赫与塔其奥之间从未有过对话,更多的是阿森巴赫个体的追逐、内心的纠结与塔其奥似有若无的“诱惑”。可见,当“疾病”通过肉体开始了对精神的控制,肉体的崩溃、行为的适宜都将逃离理性的控制。影片不仅以“疾病”为中介,为了我们传递了阿森马赫对于“禁忌之爱”的欲罢不能和无能为力,也展现了他对于“艺术唯美”的内心焦灼。[7]
三.“疾病”——“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失衡者
“自我”与“本我”原为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的概念,二者与“超我”同为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着人类的每一个行为。其中,“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初的部分,自出生开始即已存在,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本我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寻求即刻的满足。“自我”是个体出生后,基于现实环境自“本我”分化而来的。它因需考虑现实的限制,而无法实现即刻的满足,因此遵循“现实原则”。“自我”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对“本我”的冲动与“超我”的压制发挥缓冲与调节作用。“超我”是意识中的“最高部分”,它的形成基于个体在社会中接受的道德规范。一方面,“超我”可以通过“自我理想”,要求自身的行为符合理想标准;另一方面,它可以借由“良心”规定自身行为免于犯错。因此,超我是自我意识中的道德部分,遵循“道德原则”。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意识中的三个层次各在其位,各司其职。“本我”代表了人的生物本能,按照“快乐原则”行事,是“原始的人”;“自我”寻求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让本能冲动能够得到满足,是人格的执行者,按“现实原则“行事,是“现实的人”;“超我“追求完美,代表了人的社会性,是“道德的人”。现实生活中,三个层次要彼此制约,保持相对平衡。太过注重“本我”,易违反法律和道德,会受到惩罚;太注重“自我”,会感到受约束、不自由、内心充满矛盾和纠结;太注重“超我”会紧张、焦虑,从而产生心理疾病。[8]
影片的主人公阿森巴赫认为“艺术家必须为人师表”,于是他竭力地在精神上追求纯洁和美与肉体上本能的渴念之间寻求平衡。为了遏制自己的不理性,他只是远远观望美少年,想过离开威尼斯等等,但又因为邮寄行李的丢失,导致他无法离开威尼斯而感到兴奋窃喜。可见,当“本我”渐渐诱使“自我”倾向自己,而“超我”缺乏“自我”的支持,走向弱势。然而,“超我”并未屈服,而是以“自我理想”而实现自律,并通过现实中的处境,促使“自我”遵循现实原则而实现“理智”与“自控”。越是压抑,越是无法平衡,越是在不断的矛盾心理下纠结与斗争。“超我”与“本我”之间相互竞斗,互不相让,展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架势,导致“自我”在欲望和理智之间徘徊抉择,痛苦不堪。最终,属于阿森马赫内心的平衡支点开始不断倾斜,进而走向坍塌。原本严谨自律、工作为先的品质在“本我”中本能冲动的驱使下消失殆尽,“本我”的操控让他随心而动,随性生活。他开始出入风月场所,“穿着丝制衬衫在海滩上闲逛”,“去理发店将自己修剪成年轻的模样”,“穿着合适的夜礼服出现在餐桌旁”,这些曾在“超我”的信念中无数次鄙视的行为,却像是对他产生了魔力,让他着迷,使他快乐。即使腐臭气味横行的威尼斯,一时间也成为他心中的“乐土”,带给他新的欢愉。当阿森巴赫沉浸于流连“美景”与觊觎“美人”的逍遥时光中,“本我”的欲望完全取代了“超我”的功效与作用。当他直面“超我”嘲讽,开始整理自己的容貌,却在看似青春的表象下窥见一位“满身假货的老男人”;当他不顾“超我”的反抗,纵情描绘着一个个笑容和一丝丝轮廓,却在创作完成时,感受到“胸口的一阵绞痛”;当他不断抑制“超我”的操控,满心欢喜地走向少年,却借由他人之口得到了塔吉奥全家搬离的消息。对于阿森巴赫来说,“超我”被摒弃,“本我”亦不在,仅剩下孤独的“自我”在现实中摇曳。无法面对打击的阿森巴赫终于撒手而去,以“惨淡的死去”为艺术家对青春与美的擦身而过打上了悲剧与伤感的烙印。“疾病”削弱了阿森巴赫的美好品格,造成其精神的堕落,但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其内心“本我”、“自我”、“超我”的矛盾与失衡。
阿森巴赫的“死”让影片意味深长,它将艺术家对欧洲文明抱有的焦虑和不满推至极限,从而跃然纸上,引导观众对艺术与生活进行思考。导演维斯康蒂曾说,“在歌德之后我热衷于托马斯·曼……我所有的影片都沉浸于曼的艺术之中”[9]。维斯康蒂用《魂断威尼斯》创造了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感性与理性、讽刺与悲剧、激情与节制、“本我”与“超我”。[10]上述对立的二者在阿森巴赫身上相遇,以充满艺术的形式伴随他在精神世界中探索。他的艺术才华时常会让他由于时代的腐败与文化的解体而深感折磨,而這份“精神痛苦”又以自我放逐的文化属性在阿森巴赫淒美的死中实现了契合。换言之,无望的“禁忌之恋”使阿森巴赫开始了对美的追求,又坠入了精神“疾病”之渊,影片用强烈的哲学与美学思想留给了世人无限遐想:忘记疾病与痛苦,便可在精神上实现安宁与愉悦。
参考文献
[1]程巍译(美)苏珊·桑塔格著.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2]朱雯熙.德语电影《窃听风暴》中的叙事伦理分析[J].美与时代(下),2020, (04):111-113.
[3]张福全主编.简明西方心理学史[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
[4]张红艳译(德)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著.烟雨故园路—荷尔德林书信选[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5]黄燎宇.托马斯·曼[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6]朱雯熙.王国豫.从规范伦理到信息形而上学-普适计算时代的德国信息哲学与伦理学研究[J].哲学动态,2017,(2): 69-77.
[7]关熔珍.矛盾与挣扎——《魂断威尼斯》的人性解读[J].名作欣赏:文学研究旬刊,2006,(22):69-73.
[8](斯洛文尼亚)阿列西·艾尔雅维奇著;胡漫编;王杰主编.批判美学与当代艺术[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
[9]罗建新.从意象角度看《魂断威尼斯》[J].2010,(5):96-97.
[10]李安斌.程润峰.艺术·死亡·欲望:《死于威尼斯》和《魂断威尼斯》的互文性解读[J].电影评介,2009,(9):77-7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疾病叙事及伦理意蕴研究”(2021XJQN07)和2022年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人才培养对象委托课题“中德电影中的技术伦理思想与文化意蕴对比研究”(2022lslqnrcwtkt-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