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163窟壁画艺术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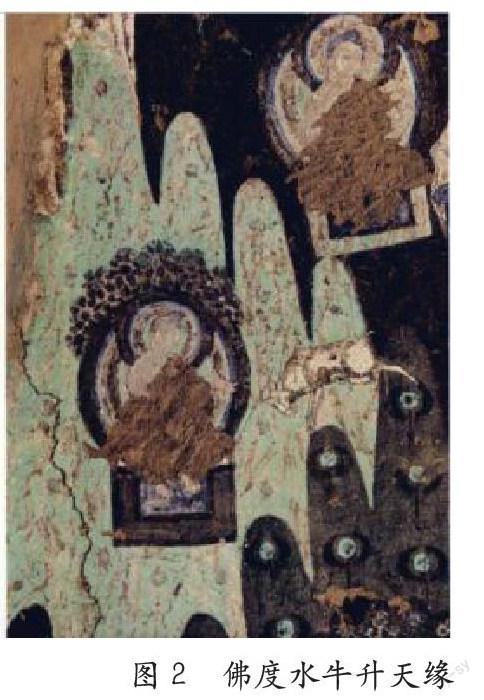

摘 要:克孜尔石窟163窟是目前已知壁画内容保存较好的洞窟。对该窟壁画艺术进行研究主要从洞窟的形制与壁画内容、富有装饰性的色彩与线条、壁画的风格特点及年代这几个方面着手,分析介绍克孜尔石窟第163窟的壁画艺术特征及其蕴含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克孜尔石窟;163窟;壁画
一、洞窟形制与壁画内容
163窟洞窟的石窟形制比较单纯,是典型的中心柱窟的类型,主室为长方形纵券顶,后室有带佛龛的中心柱,显示出环绕中心柱有左右甬道及后室的构造。这种一般的中心柱窟,主室和后室的关系经常是变化的,即后室的左右甬道的外侧壁与主室的左右侧壁相比,掘得有些窄或者掘得较宽;主室的左右侧壁和后室左右甬道的外侧壁,无间隔成一条直线,强调纵轴方向运动的构造;有的洞窟构造是以主室为中心、后室为从属,也有以中心柱的后室为中心、主室为从属的构造。在洞窟平面上克孜尔163窟主室和甬道、后甬道侧壁宽度相同,是以后室作为一个独立空间的构造。像这样的中心柱窟,自身构造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其壁画构成和编年也必然有一定微妙的转换关系。这种中心柱窟可能与印度的察依台亚石窟有一定关联,可以说克孜尔中心柱作为窣堵坡的意义几乎已经没有了[1]。
壁画的内容也比较单纯,在主室正壁塑立像,旁绘飞天;主室门道的上方前壁绘有佛说法图、门道两旁的前壁开龛塑像、侧壁绘有因缘说法图、券顶中脊绘天相图、券顶两侧券绘有因缘、本生故事图。在主室券顶右侧壁绘贤面受毒蛇身缘图(如图1),图中描绘了一富豪,名贤面,虽财宝无量,但为人贪吝,对前来乞讨者不仅不施舍,反而恶口大骂,其命终后,生为毒蛇,仍为害于民,佛知晓后,前往劝说,佛告说“汝于前身以吝贪故,受此弊形”。此故事的目的主要是宣讲佛教的因果报应。图中佛左侧的一个人就是贤面,其身下有一条毒蛇。佛作说法状,此为调伏贤面的情景。主室券顶的左壁绘有佛度水牛升天图(如图2),图中有一水池,其中有五百水牛,行人不敢通过,佛欲过此处,牧牛人劝阻。这时牛群中一大恶牛,凶猛无比,向佛祖扑来,佛用神通降伏了恶牛。(《撰集百缘经》卷六)。
甬道顶部绘有立佛;甬道内侧壁绘佛传图,佛的右侧坐一个裸体女子,此为长寿女;佛座下横卧一个裸体女子,此是长寿女的妹妹吉祥慧女;佛左侧亦坐一裸女。其上部有弹奏五弦的天人,起到歌颂佛说法的作用。甬道外侧壁绘立佛;立佛旁绘有婆罗门,婆罗门裸露的上身,以柔和的土红色晕染,鬓发则用石青色涂染,冷暖色对比强烈,十分醒目。右甬道内侧壁绘夜叉捧塔(如图3),夜叉赤裸上身,头发蓬散,下着绿色短裤。他单腿跪地,双手捧舍利置于头上。克孜尔石窟早期洞窟于左右甬道两侧绘出舍利塔,用夜叉捧塔形式表现,则仅此一例。左甬道内侧壁绘有多卢那,佛涅槃后,古印度的八个国家派兵前来索取佛舍利,为避免战争,拘尸那城婆罗门多罗那前来言说,将佛舍利分为八份。各国在分得舍利后,各自起塔供养。图4画面中四个身穿甲胄、手持弓箭骑于马上的武士列于拘尸那城门外,一副剑拔弩张的情形。这是八王分舍利图右下部分,描绘的是八国派兵打算以武力夺取佛舍利的场面。图中四身武士及马匹排列密集,形态如一,充满图案化的意趣。
后室正壁绘有涅槃图;后室前壁绘有焚棺;后室顶部绘着举哀天众;后甬道右侧壁绘善爱乾达婆王及眷属(如图5),其中白色皮肤的是男性乾达婆,棕色皮肤的是其眷属。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第三十七卷中记载:乐神善爱乾达婆王,自恃技艺高超,傲慢自大。帝释天曾在佛出生、成道、说法等时期,告知善爱要去供养,但都被善爱拒绝。佛即将涅槃时化作一乐神去善爱宫中与之比赛弹奏箜篌,佛胜善爱,使善爱悔悟,皈依佛法,成为佛最后度化的一位天神,善爱为报佛的度化之恩,即与眷属在佛涅槃时弹琴礼崇,它是克孜尔石窟繁盛期壁画中常见的题材。图中善爱都是双脚交叉,呈舞蹈姿态,其腋夹箜篌,手作弹奏状[2]。这一题材在佛教涅槃图像中也颇为重要,是佛法传承的展现。
二、壁画的色彩与线条分析
一切可视的艺术形象,最先吸引人的是它的整体氛围,即色彩和色调,克孜尔石窟壁画以其强烈的冷暖对比使人印象深刻。163窟壁画主要采用石青、石绿、土红、赭石、黑和白等几种颜色,这几种颜色在壁画中反复出现,其中白色、石青、石绿为冷色,并且占画面的大部分空间,给整体画面营造了冷色调的氛围,同时画家懂得用少量的赭石或土红色等暖色进行调节,可见其技术高超。画面中占比较大的石绿和白色都是高明度的颜色,石青也属于中明度,所以整个洞窟壁画的色调不至于看起来暗沉,显得比较轻松、明亮。
163窟壁画多采用装饰性的线条和色彩来塑造形象,壁画的颜色主要选用土红色,看起来显得沉稳、大气,将暖色调的土红色与冷色调的石绿、石青组合在一起,使整个画面形成冷暖对比色调,十分鲜艳明媚。同时,壁画中出现了鲜明的矿物质颜料,天青色与以前使用的明亮绿色并存,强烈的对比色彩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描绘的全部事物,特别是在表现人物方面更为明显。以强烈的对比色表现人物,头发用蓝、绿及红色涂染,脸部和身躯涂以赤色或蓝色,并施以晕染。婆罗门裸露的上身,以柔和的土红色晕染,鬓发则用石青色涂染,真实的头发不会是蓝色,但是画师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将发色表现为蓝色,使画面具有装饰性,十分醒目。窟顶右全景的右侧的壁画保存较好,画面上描绘有四排因缘故事图,下部半菱格中为本生故事画。菱格构图的底色分别为白色、石绿、石青、深棕色交错分布,色调对比鲜明。菱格中因缘故事画中的人物较小,而菱格外缘的山峰突出,使整体画面看起来有开阔明朗之感。有的壁画中则多使用暗褐色、红色,甚至绿色和蓝色对人物的肌肤进行涂染,而不遵循自然的规范。163窟壁画是冷色调,画面多用到石青、石绿色,壁画中出现的大量的蓝色,古罗马人称之为來自大海另一边的蓝。它是用一种名为青金石的宝石原料制成的,X衍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3]。
在用线方面,采用粗细均匀的线条,用大的弧线和直线较概括的表现形体的结构,不做细致的刻画,衣纹线为双线组合形式,壁画中线条的表现比较坚硬,是“曲铁盘丝”的铁线描形式,直接以线造型,线条不做晕染,失去了自然的意味。此时,画工用土红色勾出轮廓线,使画面非常具有装饰性。例如,飞天天衣的前端出现了幻想的装饰,衣纹由几条浓黑的线条勾出,白色的高光点被强调出来。另外,也会经常反复地使用比较规则的线条来表现衣纹,如弧线和涡纹等,用粗犷、简练的笔法处理衣纹的也不在少数。在表现人物的眼睛周围、颈部、腕部和胸部等都以强烈的红色晕染,经常使用习惯性的手法,反复表现定型化了的内容。在表现脸部和躯体的高光白线及暗色线条的时候,不使用晕染的也不少。
三、壁画的造型特点与风格分析
克孜尔163窟壁画造型中装饰性的因素加强,典型的龟兹风格出现[4]。表现为出现程式化的造型模式,人物体积的塑造手法相似,不表现肌肉的细节和人物形体的起伏变化,人物造型上采用适度的比例,不做夸张变形的处理,以适度的大弧线来概括形体结构,缺少变化。人物面部比较圆润,眉毛与眼睛之间的距离适中,眉梢微微挑起上扬,这是龟兹风格的典型特征。眉毛的轮廓线与鼻子的外结构线的相交点同上眼睑处在一个水平线上,或者比上眼睑略高一点。上眼睑的轮廓线和晕染不会和外眼角相连。鼻子的内侧面的结构不做晕染仅是以勾线来表现,形成了双线表现的形式,这种表现人物面部的方法也成为龟兹壁画的典型艺术样式,一直被沿用。
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展现了龟兹人民的汗水和智慧,很好地反映出了龟兹本土化的特点,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圆圆的头部、额头高而宽阔、眉毛到发际线的距离较长,两颊浑圆,下颌短而深陷两颊中,形成双下巴,整个脸型也几乎是方形,具有长眉、大眼、高鼻、小嘴的特点。脖颈又短又肥看起来几乎与头一样宽,这些特征与中原汉民族的面部特点不同,正是史书中记载的古龟兹人的特征[5]。
通过运用考古学与艺术风格学相结合的方法,对龟兹石窟壁画中的人物形体结构的划分、面部特点、衣纹、形体的晕染、画面的色调等具体因素的分析,王征划分出十种风格类型,其中克孜尔第3窟、第4窟、第7窟、第14窟、第17窟、161窟、163窟、171窟、172窟、187窟、188窟、205窟、206窟、224窟属于第三种类型,这种类型的壁画仅见于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色彩和线条非常具有装饰性,形成了典型的龟兹风格壁画。此类型壁画中菱格形的山峦的构图形式,成为探索壁画的年代关系的重要依据。这种类型的风格不是独立的,它与前两种风格类型有着继承性,同时也对后几种风格有着影响,每一种风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独立的,在历史的洪流中都会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
王征通过对龟兹壁画长达九年的临摹,充分掌握了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后,把龟兹壁画的风格划分为十个类型。对于龟兹壁画的风格研究最早始于德国的格伦威德尔,虽然他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研究成果不够全面,随着中国学者研究的深入,对他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质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格研究一直都是龟兹石窟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探究龟兹石窟年代问题的重要依据。关于克孜尔石窟的编年,众所周知,因缺乏题记、碑文、文献史料等较明确的印证资料,所以在断代上较为困难,洞窟的开窟年代和壁画的绘制年代可能不在同一时期,近年来,根据碳14测定,163窟壁画的年代大概推断为6至7世纪初。
四、结语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佛教文化的载体,是龟兹人民精神文明的结晶,是佛教文化传播的媒介,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它通过图像的形式向我们宣扬佛教的义理和基本思想,壁画图像是佛教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同时也是人类绘画史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存在也印证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绘画艺术的多样性,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当代的绘画技法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克孜尔石窟163窟壁画在龟兹克孜尔石窟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艺术繁荣发展的见证者,石窟的规模直接体现了当地佛教的兴盛程度,我们通过了解其壁画的形制内容和艺术风格可以想见昔日佛教文化在西域的辉煌。龟兹石窟的艺术内涵和文化价值可以从壁画的风格和绘画技法中清晰地展现出来,163窟的壁画题材内容和造型风格、充满装饰性的线条和色彩都深刻地反映了克孜尔壁画中辉煌的佛教艺术文化,那些说法图、本生、因缘故事画,是研究龟兹的社会历史、佛教文化以及中西方交流的重要依据。龟兹本地一直以来信奉小乘佛教,从整体的图像构成来看,弥勒菩萨和帝释窟禅定、弥勒菩萨和涅槃为特定的对应关系。这种图像的布局呈现出小乘佛教一切有部的“一佛一菩萨”的思想内涵。弥勒为释迦入灭后佛法的继承人,克孜尔石窟中弥勒说法图、涅槃、帝释窟禅定对应的形式体现的是小乘佛教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的理念。目前对龟兹地区克孜尔洞窟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深切关注,但是对163窟的独立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对163窟进行深入的研究,解开克孜尔石窟神秘的面纱,促进对西域文化的研究,这样也有利于加强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世界文化是多元一体的,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既要立足于本土文化又要推陈出新,不断革新变化,这样艺术才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宫治昭,唐启山.论克孜尔石窟——石窟構造、壁画样式、图像构成之间的关连[J].敦煌研究,1991(4):7-25+125-132.
[2]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七[M].大正藏:第24册.
[3]苏伯民,李最雄等.克孜尔石窟壁画颜料研究[J].敦煌研究2000(1):65-75.
[4]王征.龟兹石窟壁画风格研究[J].西域研究,2006(4):5.
[5]阳艳华.克孜尔石窟186窟壁画艺术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0.
作者简介:侯恩霞,江南大学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