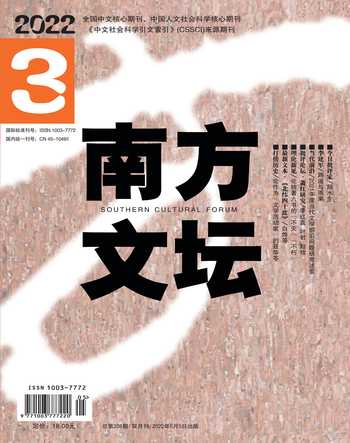萧红与戏剧
在萧红短暂的艺术生涯中,戏剧活动是重要的部分。她从少年时代就参加了募捐性质的话剧演出,成名之后还参与创作过两个剧本。尽管她从事的都是外来的新式戏剧的活动,但民间传统的戏剧是她最早接触的戏剧形式,也是她早年生活世界有机的组成部分,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她的戏剧观念,是她艺术修养的重要来源。所以,她的戏剧观念带有中西合璧的特征。而且中外戏剧在交叉渗透的融合中,影响到她其他文体的创作,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与表意策略。
一
萧红出生成长的黑龙江呼兰城是一个民间戏剧活动很昌盛的地方,从家庭型治病禳灾的萨满小戏(跳大神),到敬神与人神共娱的野台子戏,都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就连正月十五跳秧歌,也是化装演出,演员要扮成各种角色,也是原始戏剧的形态。现代商业演出的戏剧在呼兰也很繁荣,因为呼兰是黑龙江最古老的城市,处于南北交流的中心,作为哈尔滨的门户,是各县运粮的必经之路。故城内店铺林立,舟船辐辏,客商云集,娱乐业也由此兴起,戏园子和说书馆也是供市民文化消费的设施。据她母系亲属的回忆,萧红小时自创的一个游戏是以嘎啦哈(即羊拐)摆成城墙,以自己剪的纸人去破城,她对姥爷说,摆的是天门阵,自己是穆桂英,能破天门阵。可见,她有可能很小就观看过传统戏剧,以女英雄为自我镜像,以戏剧故事为原型,模仿英雄传奇,创造出独出心裁的游戏。长篇小说《马伯乐》中,有陷入困顿的马伯乐自伤自赏地吟唱《四郎探母》的情节,可见传统戏剧是她艺术修养重要的部分。作为移民地区,还有其他剧种随着方言流传过来,比如,《呼兰河传》第四章有粉坊的工人闲时唱秦腔的情节,内容是比穆桂英传奇还要古老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段子,秦腔作为最古老的戏剧形式和最古老的传奇内容高度耦合,带来关内民间特殊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是北部边陲的原住民所生疏的。萧红关于自己家人的叙事中,没有相关的情节,但据她的亲属回忆,其祖母“跳神赶鬼,无所不信”,童年萧红极可能在家里也看到过相关的演出,但祖母死的时候她只有六岁,就是亲历也印象不深,《呼兰河传》中记叙自家房客老胡家维持一冬的彻夜鼓声则强化了她对萨满小戏的记忆,所以成为她观察民间精神生活首选的项目。
在故乡民间的传统戏剧活动中,她的角色是观众或听众。比如,正月十五跳秧歌、七月十五盂兰节等仪式感极强的民间盛会,也带有戏剧从起源到基本功能的古老形态要素,她从小到大很可能不止一次地躬逢其盛,所以留下深刻印象;秋收之后的野台子戏是昼夜进行,据她初中同学傅秀兰回忆,曾在午休期间搭伴去看过,亲临现场的热闹与混乱使她的叙事充满了丰富的人间声色与生活细节,对于夜晚戏散之后旷野萧疏景象的凄凉感受与逼真描写也透露出她是有过夜间观戏的经历。
这些民间戏剧活动和民众的信仰世界高度重合,与婚丧嫁娶的制度互相渗透,成为她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生活世界中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文化记忆,与这些戏剧形式相关联的各种民间信仰,也影响着她的命运,形成心灵深度的创伤。比如,《呼兰河传》中记叙祖母死后的丧礼,从报庙、缝孝服、装米罐、炸打狗馍馍,到吹喇叭、搭灵棚、奔丧的亲属哭丧、和尚道士敲敲打打地做法事,一系列的仪式都带有戏剧的想象和表演性质。还有第五章,萨满巫师和道士驱鬼辟邪的仪式,也都有戏剧性的效果,前者是一旦一生对答如流的对手戏,后者则是一个人使出浑身解数的独角戏。第七章中冯歪嘴子弱小的儿子为难产而死“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母亲打着简陋的小纸幡送葬的情节,则是她在祖母、祖父、母亲之死叙述的仪式中最震撼人心的一段,简单、安静而庄严肃穆。这些素材进入她的艺术世界,就和乡土人生戏剧性的曲折命运血脉相通,成为她叙事的隐形结构方式。
二
萧红与戏剧关系的第二个阶段,是由观众成为演员。
1925年,萧红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适逢五卅运动爆发,她响应“县沪难后援会”的号召,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讲演、募捐。7月末,呼兰学生联合会在西岗公园举行了募捐义演,萧红在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话剧《傲霜枝》中,饰演一个小女孩儿。据说她虽然舞台经验不足,但演得还是很逼真,对人物感情掌握得还适度。这是她最初登台演出,由观众变成了演员,和戏剧的关系也由传统戏剧改为外来的“文明戏”。这是双重的转身,传统剧目也变成了五四以后兴起的新剧目,戏剧活动一开始就是她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方式,或者說是新的戏剧形式开启了她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最初门径,具有思想和艺术双重启蒙的意味。甚至早于文学写作,因为,呼兰学校严格遵守黑龙江教育厅的语文教学体制,以文言为教材,小学生也要以毛笔文言写作文,第二年的六月,萧红轰动全校的作文《大雨记》,以听同学讲述的五月三日暴雨之夜,一户贫苦农民父子跌入水坑溺水身亡,只留下一个寡妇的悲惨故事为题材,就是用文言写的。从观众到演员、从文言到白话的双重转身,也是她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她成为剧中人,挣扎在旧文化的罗网中,奔逃跋涉在战争的烽火里,彻底转身为旧制度的“二臣逆子”,以独立的姿态行进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沿。
这是她唯一的一次正式登台演出。1932年夏天,她被未婚夫从北京带回哈尔滨,回到呼兰不久就被带到阿城张家大本营,在封闭式的豪强地主庄园中被软禁半年之后,趁着“九一八”的混乱,在姑姑和小婶的帮助下,匆忙搭乘一辆往阿城送白菜的马车,在严寒中辗转到达哈尔滨,又遭遇亲戚闭门、好友搬走,被一个老妓女误为同类收留过夜才免于冻死。好容易住进堂姐妹的中学宿舍,取得学籍却无力支付费用。在战火逼近、学校提前放假之后,和未婚夫住进道外东兴顺旅馆。未婚夫家执意解除婚约且断绝经济,两个家族对簿公堂,未婚夫临阵变卦背弃承诺致使张家败诉,她一气之下跑回呼兰继母梁家,未婚夫追到呼兰,把她带回旅馆,从此靠赊账为生,欠下大笔钱款。哈尔滨沦陷后,未婚夫神秘失踪,她被老板扣作人质,并威胁要把她卖进妓院。她于临盆在即的极度困厄中投书《国际协报》文艺版主编裴馨园,得以结识舒群等一批左翼文学青年,并与萧军迅速结合,在洪水倾城的混乱中逃出封闭的旅馆,生下孩子被迫送人,几经曲折住进商市街二十五号的小耳房,从此走上左翼文化道路。81F69770-B60C-445C-A6A6-EA191ECEF075
萧红在病痛贫穷中参加了募捐画展,1933年元旦开始以白话小说被文坛认识接纳,后来还在金剑啸创办的“天马广告社”当副手。1932年夏天,地下党员金剑啸“发起维纳斯画会”,同仁聚集在一起谈文论艺,严冬来临的时候,萧红提议成立一个剧团,受到积极的响应,有十几个人参与商讨剧务,但三天就结束了,因为他们聚集出入的“左派名士”冯永秋“牵牛坊”的家在道外,日本特务已经在那里抓了不少工人,怕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1933年春夏之交,地下党哈尔滨道外区宣传委员罗峰和金剑啸又组织了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抗日文艺团体“星星剧团”。萧红是主要演员,他们排演了三个短剧,她在女作家白薇的独幕剧《娘姨》中饰演一个病妇。在民众教育馆排练了三个月,因为拒绝馆长配合日本和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的“九一五”纪念日演出,而被取消了演出场地。后来又联系了一家电影院,事情还没确定,一个主要演员就被捕,假释出狱后失踪。土肥原专程到哈尔滨,严格规范新闻出版等宣传领域的检查制度,剧团只好暂时偃旗息鼓。
这是萧红最后一次参与戏剧表演活动,此后她再也没有以演员的身份登台。但这次未实现的戏剧表演梦,使她比较系统地了解世界戏剧的前卫思潮,舒群通俄文,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戏剧大师的理论与实践不会陌生,对她会有助益;也会受到金剑啸等成熟艺术家的技术指点,后者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教育系图工科,曾经在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当演员,受过专业的训练,得中国最早的话剧大师们的真传。萧红这一次深度参与话剧舞台表演的实践,亲身体验了这个剧种舞台假定性的规范模式,积累了话剧艺术的知识与经验,为她以后戏剧活动的又一次转身打下了良好的经验基础。
三
1938年1月27日,萧红和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一行人,受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之邀,坐在铁皮的运兵车厢里,赴临汾出任艺术指导。到达临汾不久,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从潼关抵达,没几日,崔嵬、塞克、贺绿汀等人,同“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一队”也辗转来到临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汇合。2月间,日军攻陷太原之后,兵分两路进攻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决定疏散人员。他们在临汾待了二十天,就匆匆上路,随丁玲的西战团向运城转移。3月1日,他们到达潼关,本拟由风陵渡过黄河去延安,但丁玲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直接到西安,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他们在潼关短暂停留之后,很快就向西安进发。就是在这一次名家聚集的艺术之旅中,萧红完成了自己与戏剧关系的又一次转身。
她遇到了著名的话剧艺术家塞克,他也是从哈尔滨出来的,和萧红算得上半个老乡,还是金剑啸的好友,当年就是他推荐金剑啸到上海求学,朋友的朋友自然相见如故人。而且,在上海他们已经互有耳闻,彼此欣赏各自的性格与才华。塞克可称为话剧达人,科班出身,当演员一炮而红,组织醒狮剧社自任导演,还是《流民三千万》和《铁流》的编剧,此外还写新诗歌词,当时四处传唱的《抗日军歌》就出自他的手笔,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夜店》和许多苏联歌曲,成为中国救亡歌曲和新音乐运动的重要领军人物,可谓艺术全才。两个人在战火和硝烟中见面,格外激动,说笑谈艺,欢乐异常,这对于她对话剧艺术的理解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提升机会。面对沿途一片慌乱的逃难景象,丁玲提议这些作家、戏剧家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写一个剧本,到西安后演出。他们一口答应下来,边讨论边凑情节,理出人物,分出场次,由几个战地服务团的团员记录。他们表现了一群老百姓在日寇的血腥屠杀而家破人亡之后,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的伟大的复仇与牺牲精神,以及遭遇的种种苦难,取名《突击》。到西安以后,由塞克整理出剧本,为一出三幕话剧,交西战团日夜排练,连演三天共七场,场场观众爆满,也得到不菲的票房收入。三幕话剧剧本《突击》刊登在1938年4月1日出版的《七月》第十二期上,署名为塞克、端木蕻良、萧红、聂绀弩。萧红由此进入了编剧的行列。
1940年9月25日,适逢鲁迅六十年诞辰(虚岁),在文协香港分会倡议下,香港各个文化团体发起,以“国难方殷,正宜发扬鲁迅精神”为主旨,积极筹备纪念活动。时在香港的萧红、端木蕻良夫妇,正计划着撰写纪念文章,文协负责文艺宣传的理事杨刚,受文协之托找到萧红,建议她写一个剧本,排练演出纪念鲁迅。萧红推脱不过,只好勉力受命,好在有端木蕻良的鼎力相助。端木蕻良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参与过话剧运动,在《南开双周》上发表过剧本《斗争》,又发表过一系列关于鲁迅的论文,两个人合作也算珠联璧合。端木蕻良想起在南开上学的时候,曾经看见过一位外国哑剧大师的表演,建议萧红以庄严的哑剧形式来表现鲁迅一生的奋斗。这个构思受到文协同仁的赞同,后来冯亦代撰文专门肯定了这个设想:“它以沉默、严肃、表情动作的直接简单取胜,最适宜表现伟大端庄、垂为模范的人物。”端木蕻良用两天时间为她拟出提纲,两个人互相切磋、补充后定稿。为了适应演出,丁聪和徐迟又进行了改编,最后搬上舞台,收到了“传达鲁迅的崇高”,“予观众一种膜拜性的吸力”的效果。10月21—31日,四幕哑剧剧本《民族魂鲁迅》在《大公报》上连载,署名萧红。
至此,萧红算得上是一个成熟的剧作家了,只是天不假年,她没有继续发展的时间了,但从小到大的戏剧活动,渗透到她其他文体的写作中,成为重要的美学资源,影响到她的文体形式。
四
从观看、演出到编剧,萧红的戏剧活动滋养了她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结构功能。而且她具有文化人類学知识谱系的背景,特别是在鲁迅身边的见闻熏陶,激发着她丰富的联想。当时鲁迅正在写作《故事新编》,也是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谱系,寻找民族原始精神的古老文化空间,完成自我的镜像确立,在外来暴力的威胁中激发民族抗争的心灵能量,其中的一篇《过客》还是诗剧的形式。这对萧红是一次飞跃式地促进,因而善于把不同文化中的文体形式进行功能的类比归纳,以白话的形式而能复合中外文体的共通形式与基本功能,适应了表现中国民间情感方式与民族古老灵魂的艺术意图。81F69770-B60C-445C-A6A6-EA191ECEF075
戏剧是表演的艺术,话剧则更是以人物的言语动作推动情节发展的艺术形式。这对萧红小说创作的直接影响是她大量的小说都是以戏剧观众的视角进行叙事。比如成名作《生死场》原名《麦场》,是夹叙夹议地交代情节,所有的议论都是旁观者的角度,而且常常由居高临下开始,以仰视结束。比如第一节《麦场》,叙述完农民在大雨即将来临之前的忙乱嘈杂景象之后,是一句总结性的形容“农家好比鸡笼,向着鸡笼投下火去,鸡们会翻腾下去”;第三节《老马走进屠场》,王婆几经曲折地把老马卖进屠场之后,伤心欲绝地得到了一张马皮钱,回到家里就作为地租被地主家的人要走了,萧红的结语式议论是“王婆半日的痛苦没有代价了!王婆一生的痛苦也都是没有代价”;第四节《荒山》,叙述二月荒山上逐渐出现备耕的人,形容道“农民们蛰伏的虫子样又醒过来”;第六节《刑罚的日子》,叙述完金枝由于成业的不节制而早产之后,是互文性地叙述牛马在夜间的发情,总结性地归纳:“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农家”“农民们”“王婆”和“在乡村”,所有的主语和状语短句,都提示着叙事者的外来者身份,是一个乡村生活的旁观者。这种戏剧观众的视角几乎是她早年乡村叙事的基本视角,而且不限于外来者,乡土人物本身也经常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叙事,比如,短篇小说《出嫁》,就是许多人在封闭的庄园炮台上听着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的送亲响器声,从枪孔里远眺从庄园外路过的送嫁车队,看到的只是枫叶和马鞭上的红缨,关于新嫁娘的种种情态和故事,则是叙事者转述其他旁观者的讲述。
与旁观者视角共存的还有听众的记录形式,比如,《牛车上》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是一个离开乡下外祖父家返回城里自己家的外来探亲者,搭车的是外祖父家远亲女佣五云嫂,她要到城里看望在豆腐坊当学徒的儿子,而且是每年只去两次中的一次;赶车的则是“我”外祖父家的远房舅父,因当过兵、性格粗暴而使所有孩子惧怕。第一人称的“我”在缓慢的旅途中,几乎是睡眠状态,时断時续地听着他们一来一往地对话,偶然醒来发现他们各自情状的变化,由此交代了双重的故事情节:记忆中1921年枪毙了二十多个逃兵的地方大事,由此引出的深层故事是五云嫂的丈夫作为逃兵的头领被就地正法,连最后的一面也没见到,五云嫂与所有逃兵家属所经历的悲惨时刻心灵的惊颤体验,以及此后独自抚养幼小儿子的艰辛困苦生涯。表层的故事则是叙事者“我”每次在朦胧中醒来,看见五云嫂与远房表舅车把式之间精神情感状态的变化,而且是逐渐深入递进,在断断续续听到的简短而含蓄的对话中,见证了两个人由暧昧而逐渐明朗的情感发展过程,以及最终没有定局的尴尬停顿。车把式的身世也在简短的对话中清晰,作为亲历了那一年逃兵事件的幸存者,共同的历史记忆使坚硬粗粝的老兵被五云嫂的悲苦命运所感动而生出柔情。一直独自一人漂泊在外,因为贫困而无法返乡,和故土家人早已失去联系,面对五云嫂的情感试探,他只能以饮酒掩饰自己内心的纠结。“我”在朦胧中听着一来一去的对话,几次偶然醒来时发现他们异常的状态,每一次都是情感的深度递进,见证了他们逐渐完成情感的默契与陷入没有承诺的开放式结局中,最终结束于车把式和迎面而过的马车夫的彼此招呼中:“好大的雾!”“三月里大雾……不是兵灾,就是荒年……”很有“却道天凉好个秋”的留白式意境。这是戏剧观众视角的一个变体,而且是和观众视角互为补充,适应了叙事者与当事人之间特定的亲属关系,也适应了叙事者情窦未开的青涩少女懵懂的心智水平,视听知觉的全面调动,带给小说真切的拟原生态的魅力。这两个传奇人物以不同的方式标记着共同的历史刻度,又以共同的人生经验酝酿着新的传奇。正如诺思洛普·弗莱所言:“传奇是所有小说的结构核心,它直接来自民间故事,它比文学的其他方法让我们离小说的意义更近,它被作为一个整体,被视为生灵的史诗和人类作为一种追求的对自身生活的观照”。①
这样的戏剧观众视角几乎是萧红最习以为常的叙事方式,听众的叙述策略则是更切近小说本性的叙事方式,一如本雅明对作家“讲故事人”的定位,应该是比戏剧要古老得多的叙事样式。戏剧只是以表演的形式模仿重复故事的情节,而听众的叙事策略则是模仿故事的叙述者。而这两者在戏剧中几乎混融一体难解难分,在无声的小说叙事中则被分离出来,适应时空的自由变动而将旧的故事容纳在讲述者的新故事中,表达作者的伦理意愿,《牛车上》深层的传奇是悲剧性的,表层未完成的传奇体现着喜剧性,寄托着叙事者期望两个亲历的历史见证人修复历史创伤记忆建立新生活的期盼。而且这也是很适应女性作家的一种角度和策略,女性的活动空间是相对封闭的,而女性的话语空间也常常是狭小的,加上几乎没有话语权,最多的时候都是充当听众的角色,更不用说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从中可以看到萧红还原少年经验的自觉,成为她艺术表现的基本准则,就是在散文中也经常以返回心理现场的记忆而把读者带入具体的情感氛围中。比如《祖父死了的时候》等记叙自己情感经历与内心活动的文章。
戏剧交代情节的主要方式是靠对话完成,这也是萧红使用频率较多的一种叙述技巧,最典型的是《北中国》中新派乡绅耿大先生的家庭变故是由两个锯树工人的对话开始的,锯树已是家道败落的象征性行为,而长男从军抗日,耿大先生在日伪的骚扰中因长期忧虑而陷入精神衰弱,不停地投寄没有地址的信……直至被家人禁闭在后院凉亭而中煤气身亡,都在外人的观察和私密的谈话中悄悄发展,这一叙事的开端契合了表现日伪严密统治下社会状况的险恶以及主人公的精神压力和最终崩溃的过程。其他如《生死场》金枝与嫂子、母亲、王婆的对话,都是交代她悲苦命运的重要环节,也是乡土女性集体经验的表达。
五
萧红在运用戏剧观众视角的时候,是根据文体的需要借鉴中外戏剧的形式。
一般来说,她的短篇小说对民族民间的小戏形式多有倚重,比如《牛车上》两个人的对手戏几乎就是一生一旦的互问互答。但五云嫂显然在故事叙事中占有更多主动权,老兵车把式则是被她的情感节奏带着走,这就很像跳大神的萨满小戏中大神巫婆和二神男子之间表演的分工合作关系。一直到流传至今的二人转也还是沿用着这样的戏剧表演程式,女为主男为辅,这和边远地区母系氏族的强大遗存有着文化史的根源。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黄河》里羁旅途中的叙事者“我”所耳闻目睹的壮年艄公和年轻的八路军战士的往来对话,也是类似的结构,这是在战争的历史情境中,男性成为主体的在场性决定的,但一壮一少的组合仍然有着民间萨满小戏的结构特征,也可以归入传统戏剧中的生与末,而且是一个年轻英俊的武生和一个劲道沉稳的末。民间唱本中普遍存在的独角戏形式也是萧红自觉运用的叙事方式,比如她写于香港的短篇《梧桐》以东北流亡到四川的章家老太太一个人的经历与独白结构全篇,表现民众盼望胜利的焦虑心情,而人物言语的极尽絮叨与颠三倒四的非逻辑组织方式,符合她近乎神经质的精神状态,也符合一个生活范围狭窄的老年家庭妇女的性格特征,这简直就是《王婆骂鸡》的变体。而且在多个人物的故事叙事中,情节的发展也常常是以独角戏式的独白推向高潮。如以日军强修铁路为背景的《旷野的呼喊》中,破坏日军铁路、抢劫日军马匹物资的青年村民被日军杀害之后,他年老的父亲陈公公奔向旷野的呼喊,在一片死寂的村庄中回荡。又如《汾河的圆月》中,儿子死于军中、儿媳改嫁之后,陷入疯癫的瞎眼婆婆,不停地探问儿子回来了吗,每夜独自唠叨着走向汾河边……都是同一民间小戏的类型。81F69770-B60C-445C-A6A6-EA191ECEF075
在中长篇中,萧红则更多借鉴西方戏剧的形式。最典型的是《呼兰河传》的后三章,可以看作三个独立的短篇,分别讲述了三个人的故事,也完全可以看作一幕三场的戏剧。因为所有戏剧性的情节都发生在张家老宅的院子里,场景是统一的;所有的群众演员也是固定的,都是张家的亲属、佣工与左邻右舍,属于熟人社会。戏剧观众的视角与听众的叙事策略结合得天衣无缝,而且明显是巴赫金所谓复调的叙事方式,每个人物都有独立自主性,可以充分诉说自己道理,成为一套话语体系的承担者,而且三章都是对话的结构。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没有发现萧红直接接触过巴赫金的理论,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她在哈尔滨左翼文化圈中的朋友多有俄文方面的专业人才,比如后来翻译了《静静的顿河》的金人,她完全可以通过他们谈艺的片段获取巴赫金复调诗学的基本理念。间接接受的可能就更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的译介者是鲁迅组建的同仁刊物“未名社”中留苏归来的韦素园,巴赫金的理论是有可能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一起流传过来的。1929年巴赫金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彼时韦素园正在西山疗养院养病,病房墙上贴着陀氏的画像,可见他对陀氏的推崇,应该会不断收取关于其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萧红1934年底到上海之后,很快就进入鲁迅的核心圈子,也可以在那个尖端文学圈谈文论艺的交流中了解到巴氏的理论。而且她的长篇都写于鲁迅逝世之后,对复调对话与杂语的叙事方式的运用也在这个时期。不仅如此,鲁迅很可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翻译成中文之前,就通过其他语种(德文或日文)阅读过他的著作,作为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就是以文白同体、诗文互征的复调叙事展现对话的结构。萧红在早期的阅读中,也可以获得启发。总之,从直接的理论到对前人实践的揣摩,混融的影响方式使她的小说创作一开始就进入前卫的艺术潮流。就是在她晚期的短篇小说中,也普遍运用了这种对话的复调叙事方式,最典型的是《后花园》中的冯二成子与寡妇老王,他们各自承担着男性和女性最基本的话语体系。男人的超越性思维在一个贫穷磨倌单恋的爱情梦想破灭之后,开始质疑世人普遍的价值观念,其思维的穿透力近似《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公爵负伤之后躺在森林中的沉思;而寡妇老王对她的关爱与开导则使他从激情中沉静下来,回归像大地一样朴实自然的日常生活,泰然地接受命运的重重打击,日复一日在简单重复的劳作中度过平凡的一生。其他,如《小城三月》中翠姨和哥哥无法交集的两套话语体系的现实错位导致的人生悲剧,也是历史急剧变动时期无奈人生的悲情传奇。
此外,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戏剧理论也在她晚期作品的形式中大量出现。比如,《呼兰河传》中祖父与“我”、冯歪嘴子的谈话,就有对各种邪恶话语体系的间离效果。《马伯乐》中以人伦常情解构马家父子以及他们所关联的新型工商资本阶层的新式伪善和吝啬逐利的本性,也具有明显的陌生化的间离效果,而且是犀利地嘲讽。布莱希特在两次大战期间正当时,作为左翼剧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介绍到中国,影响了中国话剧的发展,萧红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相关的理念。从早期演剧的实践,到后期编剧和小说写作时的形式借鉴都可以看到布莱希特戏剧观念或隐或显的影响。特别是鲁迅通德文,和国际左翼艺术圈有着广泛的联系,尤其推崇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也会连带着注意到布莱希特的戏剧体系。萧红早年身处哈尔滨左翼文化圈时,五方杂处的国际化大都会迅速传播的国外文化艺术的先锋思潮使她近水楼台先得月。《生死场》对凯绥·珂勒惠支版画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同属一个语言文化圈的布莱希特戏剧及其理念也会以各种方式被她接触吸收。《生死场》旁观者疏离的议论与概括性的评价,明显体现着间离的效果。而这部作品一开始就受到了史诗的评价,也都透露出作家与批评家相近的艺术话语的关联域,布莱希特突破三一律的编剧方法,以史诗剧自由舒展的叙事方式表现多方面多层次的现实,在《生死场》中可谓显而易见。比如男性的生产和话语空间、女性的生产生活空间、城市女工房为中心的都市底层贫民女性的生活和话语空间,等等。20世纪世界前卫艺术和中国民间传统的艺术形式的交融,是萧红的创作一起步就体现出来的风格特征,先锋戏剧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而布莱希特是在中国京剧的启发下,使自己间离效果的理论发展成熟;萧红早年民间戏剧的积累与对世界先锋戏剧形式的自觉借鉴也就顺理成章。早在和塞克等合作编写《突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戏剧形式和布莱希特史诗剧理念的融通结合,人物分类涵盖了中国旧戏剧的所有角色类型,生末净旦丑搭配均衡,同时又是时空移动的三幕结构,从逃难、突击到回家,象征性地概括了中国抗战可能或理想的阶段性内容,因而具有史诗剧的特征。鲁迅也曾谈起自己写小说对旧戏剧形式的自觉借鉴,可见象征表现的手法是20世纪中外前卫大师们的艺术共识。《民族魂鲁迅》的结构就直接运用了布莱希特倡导的史诗剧结构形式,但作为哑剧又和中国皮影戏有类似之处,皮影戏去掉旁白和配唱就是平面化的哑剧,人物形象的夸张简单也和哑剧有相似性。尤其是进入鲁迅笔下的那些病态国民性的人物,特别符合皮影戏机械单调的动作特征,而仅仅用四幕就概括了鲁迅从少年到老年的一生奋斗,也由此象征性地聚焦了从晚清到民国民族文化激烈震动的历史时段民族精神的风范。而起源于宗教剧的哑剧和中国用以纪念伟大人物的墓志文,有着相似的特征和共通的功能,即“有褒无贬”的内容、庄严肃穆的形式与“吸引膜拜”的功能。按照本雅明对古代艺术以灵韵而被膜拜,现代艺术以机械复制而用于展示的功能性区别,《民族魂鲁迅》以动态的哑剧形式无疑兼有着因灵韵而被膜拜和以形体复制而具有展示(更确切地说是展现)的双重特征。
行文至此,已经超出了小说与戏剧的论题,但没有脱离萧红小说和散文基本文体的功能特征,“憑吊历史、超度亡灵”。归根结底,人类的历史进程与基本问题是相似而相通的。特别是在一个新兴的现代工商文明以铁血的暴力向全球迅速扩张的时代,全球文化的大交融带来艺术形式的相互渗透与借用,就是必然的现象。各种艺术理论,从复调诗学、交往对话理论、史诗剧、间离效果……一直到各种流派主义,都是人类面对现代性兴起的生存现状,为探索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努力,而寻找的艺术表现形式。而萧红特别善于以功能为通道,将古今中外戏剧形式与容纳着诗文传统的白话语体在类比中嫁接,以实现对人类艺术最基本功能的理解——终极的价值追问。
这也是中外文体大变动的艺术史进程的相通之处。历史文化的发展带来思想观念的发展,推动艺术形式的革新,带动了文体的大变动,形式翻转腾挪之间,基本的功能却绵延不绝。在中国“诗尽而史出”,在西方史诗也正是由神话故事向悲剧的过渡形态。中国起于民间的简单神话故事以传奇性转身为文字叙事,再返身为表演说唱传奇的时候,已经由口头的叙事经历文人整理创作、表演性平话,到以演出为主的戏剧。而且中外戏剧最早的起源都是祭神的仪式,只是进程有差异,随着印刷术兴起普及、阅读人口的增长而昌盛的小说,则一开始就保留了所有文体的特征和文学关注人类生活命运的基本功能,只是由神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再到普通人故事的题材变化,但都脱离不了命运、生死、离别、归来、情爱、生殖等基本主题。萧红深谙个中枢机,在古今中外艺术样式的融通中,延续起人类永恒的价值追问。这使她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古今中外同构的仪式场景,最典型的是《生死场·十三节·你要死灭吗》中,村民们在家破人亡的生存危机中,民族国家的意识开始逐步觉醒,最终汇聚到集体盟誓的仪式场景中:“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这与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场景何其相似。而《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婆婆和有二伯的大段独白,堪比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哈姆莱特大段独白中的自我辩难“生存还是死亡”?归根结底,是全球化的视野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抵制进化主义学派而兴起的以田野考察为主要方法的相对主义的功能学派,启发了萧红中外古今比较而又在基本功能的变动流转中,以新起的白话小说续写人类永恒梦想的智慧。用诺思洛普·弗莱的话说,根源在于:“小说是对传奇的现实替换,它自身并没有什么特有的结构特征。”②萧红正是将急剧动荡时代才会大量涌现的普通人由于历史苦难而经历的传奇故事,纳入传统叙事方式稳定的形式结构中,并接通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的仪式功能,将历史的书写与形式的创新融为一体,由此中外戏剧的形式在她的小说中起到了支撑结构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②[加]诺思洛普·弗莱:《世俗的经典:传奇故事结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6、6页。
(季红真,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本文系山东省人文社科奖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0-NDWX-09)81F69770-B60C-445C-A6A6-EA191ECEF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