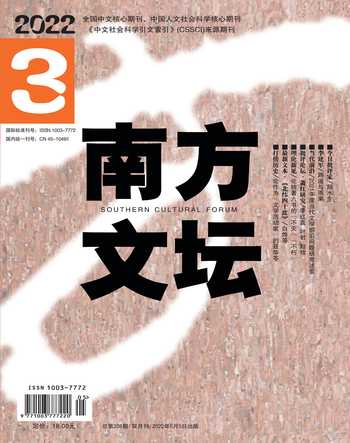儿童与儿童文学的精神深度
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米切尔·伊根认为,“儿童文学的严肃研究或许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因为正是他从民间故事和童话中发现了支撑其无意识理论的证据”①。肯尼斯·纪德则认为,尽管我们很难把儿童文学与精神分析直接或简单地联系在一起,但可以确定的是,“整个为儿童写作的规划都被精神分析学尤其是儿童精神分析的见解改变了”②。他在《精神分析与儿童文学》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儿童文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两者都为彼此带来了新的视野与方法的启迪③。
这一关系的确立有着多方面原因。首先,“童年”是儿童文学研究与精神分析理论发生关联的重要结点。自弗洛伊德以降,童年成为现代心理与精神分析学的重要范畴,其研究发现既常常建基于儿童或以儿童为对象的叙事作品,也对这类作品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儿童与童年在大部分精神分析理論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儿童文学与精神分析批评之间的选择亲和度比之一般层面心理学与文学的亲和度似乎更为自然。”④其次,不论儿童文学还是精神分析都可以理解为朝向个体“发展”的某种探询。从精神分析层面得到揭示的成长的秘密,往往与儿童期或类儿童期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这一话题也构成了儿童文学书写的核心。再次,精神分析擅长从日常话语及文学叙事的符号表层进入,从看似平常的表达中发现深藏的心理机制与精神原型,这一方法恰恰高度契合了儿童文学的文类特性。由此,儿童文学研究不但从精神分析理论中受益良多,也为这一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典型的文本案例。
一、儿童文学的精神分析与阅读治疗
在精神分析方法与儿童文学研究的早期结合中,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出版于1976年的《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⑤。该书继承并发扬了弗洛伊德以降童话心理分析的传统,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解读童话故事中蕴含的有关个体精神成长的深层内涵。在他看来,“童话故事比任何其他读物更深刻地道出了儿童精神与情感存在的真相”⑥。书中针对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经典童话如《三只小猪》《小红帽》《亨塞尔和格莱特尔》《杰克与豆茎》《白雪公主》《睡美人》《灰姑娘》《青蛙王子》《美女和野兽》等的心理分析,意在帮助读者领取童话背后的精神教益。作者用于剖析童话故事的术语,如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替代性满足、人格整合、自我统一、幻想的慰藉与修复功能等,均体现了心理与精神分析的典型特点。《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批评著作,但儿童文学与民间童话之间的深厚渊源,以及精神成长与儿童发展之间话题的高度重合,使它成为1970年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
沿着这一研究的方向,一是针对民间故事的心理学解读与精神分析持续发展。代表研究成果如玛丽亚·露易丝·冯弗朗兹的《童话中的个性发展过程》(Individuation in Fairy Tales,1977)、J.C.库柏的《童话:内在生命的寓言》(Fairy Tales:Allegories of the Inner Life,1983)、罗伯特·布莱的《铁约翰:一部男性之书》(Iron John:A Book About Men,1990)、露西·罗林的《摇篮与其他:童谣的文化与精神分析研究》(Cradle and All:A Cultural and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Nursery Rhymes,1992)、艾伦·B.知念的《从此以后:童话故事与人的后半生》(In the Ever After:Fairy Tales and the Second Half of Life,1989)、《童话中的男性进化史》(Beyond the Hero:Classic Stories of Men in Search of Soul,1993)、谢尔登·卡什丹的《女巫一定得死》(The Witch Must Die:The Hidden Meaning of Fairy Tales,1999)等系列著作。在《铁约翰:一部男性之书》中,布莱运用贝特尔海姆的方法,对主要取自格林童话的《铁约翰》故事做了男性成长隐喻的精神解读。在他看来,铁约翰象征着男性气概与男性力量,也是男性的自我原型。在《摇篮与其他:童谣的文化与精神分析研究》中,罗林提出了童谣在儿童精神成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歌谣既包含了理解世界的渴望,也传递出人类无法控制自然力量的困惑与失落,因而有助于教给孩子一种更真实、完整、充满矛盾的世界图式。
二是针对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精神分析方法得到探索。“童话从精神分析话语中发现其新的身份和意义之后不久,分析者们就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儿童文学经典。”⑦这一方向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米切尔·伊根对于詹姆斯·巴里代表作《彼得·潘》的分析(Michael Egan,“The Neverland of Id:Barrie,Peter Pan,and Freud”,1982)、马克·I.卫斯特关于《木偶奇遇记》的解读(Mark I. West,“Pinocchio’s Journey from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o the Reality Principle”,1999)、露西·罗林关于莫里斯·桑达克图画书的弗洛伊德解读(Lucy Rollin,“Childhood Fantasies and Frustrations in Maurice Sendak’s Picture Books”,1999)、苏珊·C.沃恩、瑞贝卡·亚当等针对莫里斯·桑达克的图画书《午夜厨房》的分析(Susan C. Vaughan,“In the Night Kitchen:What Are the Ingredients of Infantile Sexuality?”,2017;Rebecca V. L. Adams,Eric S. Rabkin,“Psyche and Society in Sendak’s In the Night Kitchen”,2007)等。伊根明确表示,其《本我的永无岛:巴里,彼得·潘与弗洛伊德》一文沿用的正是贝特尔海姆的弗洛伊德分析方法。伊根之前,已有不少针对《彼得·潘》隐藏的潜意识内容的研究,但其关注大多指向作家本人,亦即旨在揭示巴里本人的精神状态。伊根的解读则试图站在贝特尔海姆的立场上,将《彼得·潘》的故事视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原型。他认为,巴里在《彼得·潘》中创造的“永无岛”,乃是儿童本我的象征隐喻。永无岛的旅程是一场弗洛伊德之梦,在这里,本我脱出超我的管控,进入潜意识的世界。而永无岛上的彼得与他的对手霍克船长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俄狄浦斯情绪的投映。故事最后,彼得战胜霍克,正如俄狄浦斯杀死父亲,取代了他的位置。伊根认为,《彼得·潘》之所以会在儿童和成人读者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正是因为它触及了儿童精神成长中的重要原型⑧。在《莫里斯·桑达克图画书中的童年幻想与挫败》一文中,露西·罗林解读了弗洛伊德所说“每个人内心的孩子”在桑达克图画书中得到的诠释。而在《〈午夜厨房〉:幼儿性意识的构成》《桑达克〈午夜厨房〉中的精神与社会》等文中,性、快感、菲勒斯等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术语,构成了相关研究的关键词汇。作者认为,儿童文学文本提供的此类故事经验,为儿童的精神理解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撑。
总体上看,一方面不论从精神分析视角切入民间童话还是儿童文学名著的研究,都倾向于搁置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将特定的文本作为某种精神的隐喻,谈论其文学内涵与阅读意义。这一方法的长处在于文本符号解读的细致入微与别出心裁,短处则在于忽视文本自身的文化生产特性。例如,贝特尔海姆式的精神分析方法对民间童话作为一类始终处于自我改写进程中的文本的历史特性及内在的驳杂性,并不加以区分或细析。1980年代起,该研究方向在儿童文学研究界受到的最大批评,即指向其悬置历史、架空语境的研究方法。玛丽亚·塔特批评贝特尔海姆的童话研究毫不考虑儿童生活的现实。作为西方童话研究的重要代表学者,杰克·齐普斯也对这类童话批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针对布莱就《铁约翰》童话所做的精神分析解读,齐普斯不无揶揄地批评道:“布莱试图利用由荣格和坎贝尔所发明和发展出的原型将男性均质化,而这两位学者关于神话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恰恰忽视了真实情况下各类人的特性,模糊了文明进程中社会发生与心理发生两股力量间动态的相互作用,却鼓励人们对于那从未占据过重要位置的返祖基因模式的怀旧与渴念。”⑨在他看来,童话批评的当代意义和方法,恰恰是要揭示其诞生和演变的历史语境,进而揭开其文本与意义作为永恒“神话”的谎言。
但另一方面,这种从精神发展角度解读民间童话与儿童故事的趋向,又在新兴的儿童阅读治疗(Bibliotherapy)探索和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与发展。这是一个最初在图书馆学与阅读推广领域得到关注的童书理论与实践方向。1981年,贝丝·欧弗丝塔德在《阅读治疗:通过书籍帮助孩子》(Bibliotherapy:Books to Help Young Children)一书中将阅读治疗定义为通过文学达到促进精神健康的目的,或治疗意义上的书籍运用。1983年,玛丽·瑞克·加隆果在《阅读治疗:通过文学促进社会情感发展》(Bibliotherapy:Literature to Promote Socioemotional Growth)一文中,主要結合儿童文学在儿童社会适应与情感发展中的运用可能与探索,阐述了阅读治疗的基本观念及其实践策略。在加隆果的研究中,阅读治疗的概念与儿童成长中的各类精神问题隐在相关。她提到了通过儿童阅读促进残疾、病患、离异家庭、暴力受害等状况下儿童情感治愈与社会发展的既有实践。这一倾向或许与阅读治疗活动最初诞生于医院、诊所并被用于病患治疗的事实有关。在同年发表的《危机导向图书的儿童阅读运用》(Using Crisis-Oriented Books with Young Children)一文中,加隆果一方面强调了阅读治疗用于解决儿童生活危机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提出了将它运用于更广泛的儿童生活适应如自我认同、情感控制、同胞竞争等问题的建议。这就进一步将阅读治疗的观念从狭义的“治疗”推向了更普遍的儿童社会性发展干预。
事实上,前述针对民间故事与经典童书的精神分析解读,几乎都隐含了阅读是一种广义的精神治疗的命题。从多萝茜·巴特勒以其残障外孙女的阅读成长为素材的《卡索拉和她的书》(Cushla and Her Books,1979),到弗朗西斯·斯巴福德自传性的《书本塑造的孩子》(The Child That Books Built,2002),人们见证了童书和阅读如何拯救处在身体和精神压迫下的儿童。杰妮·普拉斯脱主编的论文集《故事与自我:儿童文学的精神分析视野》(The Story and the Self. Children’s Literature:Some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2008),很大程度上正是关于广义上的儿童文学精神疗愈功能的探讨。米切尔·霍华斯的著作《床底下,无声地爬行着:儿童文学中哥特元素的精神分析》(Under the Bed,Creeping:Psychoanalyzing the Gothic in Children’s Literature,2014)同样是关于文学阅读与精神治愈的研究。该书运用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解读儿童文学中的恐怖元素,阐述儿童读者如何从具有象征性的哥特元素的阅读中,克服生存恐惧,建立自我身份,进而理解自身与世界。2001年第4期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组织了围绕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怪异”(uncanny)范畴开展的儿童文学批评,包括专栏主持特瑞兹导言在内的五篇论文,探讨儿童文学文本如何表现、传递儿童对“怪异”的体验及如何接纳、克服这种体验。此外如埃伦·汉德勒·斯皮茨的《图画书中》(Inside Picture Books,1999)、大卫·纳什的《理解图画:教给交流障碍青少年的推论与叙述技能》(Getting the Picture:Inference and Narrative Skills for Young People with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2011)等著作,均关注图画书的儿童心理与精神疗愈功能。如果说根据弗洛伊德以降的精神分析理论,“故事讲述是像呼吸一样基础的人类生命程序”⑩,那么这一方向的研究者们相信,借助这一故事的通道,儿童期的许多精神发展需求与问题,都有可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决。
二、潜意识与儿童文学文本中“隐藏”的秘密
1990年,美国重要的儿童文学学术期刊《儿童文学》第18卷以儿童文学的精神分析研究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重点探讨精神分析理论在儿童文学批评中的运用。杰克·齐普斯在其收入专栏的论文《通过精神分析批评否定历史与男性幻想》开头明确指出:“针对文学的精神分析批评想要有效,它就必须不再否认作者心理与想象的历史,而从作品诞生的时代语境来考察作家及其作品。”11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儿童文学精神分析批评的发展,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回应着齐普斯的批评。相比于早期批评的“非历史”特性,相关批评开始有意识地转向作者及作品的历史,探讨文本背后深藏的精神内涵。
精神分析方法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儿童文学文本阅读的可能,也加强了这一阅读的深度。传统的儿童文学观念认为,儿童文学文本具有高度的透明度与可控性,即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作者有效地控制着文本语言的目的、内容、表意等。精神分析批評则揭示,儿童文学文本与其他所有文学文本一样,常常远远越出作者本人的意图甚至意识,成为反观作家自我精神世界的镜子。露西·罗林与马克·I.卫斯特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秉持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我们的语言表达传递出了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内涵与意义12。换句话说,在我们的语言文本内部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意义角落,正如在我们的意识深处隐藏着一个潜意识的深渊。哈米达·博斯马吉安甚至认为:“儿童文学是一个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成人文学更复杂的艺术、心理和社会现象,因为作家的记忆和力比多是通过伪装天真的形式得到投映的。”13
正是受到这一基本观念的影响,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从儿童文学作品中解读作家的精神世界,成为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的一个显要脉络。安徒生、卡洛尔、米尔恩、比阿特丽克斯·波特、格雷厄姆、刘易斯、詹姆斯·巴里、弗兰克·鲍姆、罗尔德·达尔等大量西方经典序列中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由此进入精神分析考察的视野。这类解读关注的同样是文本之下隐藏的精神讯息,但与前一节谈到的研究相比,它更关注经由作品得到传递的不为作家本人所知的潜意识内容。在不少研究者看来,作家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与精神治疗活动中病患与精神治疗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可类比的平行关系14。或者说,作品提供了关于作者的某些不但不为人知而且不为自己所知的秘密。
这一研究主要包含两个方向。一是结合作家个人尤其是童年时代的焦虑或创伤经验,重新解读其儿童文学作品与写作行为,代表研究包括《白雪皇后之吻:汉斯·克里斯蒂森·安徒生与经由女性的男性救赎》(WofgangMieder,Kiss of the Snow Queen: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nd Man’s Redemption by Woman,1986)、《衣橱里的骷髅:C.S.刘易斯的幻想》(The Skeleton in the Wardrobe:C.S. Lewis’s Fantasies:A Phenomenological Study,1991)、《不寻常的比阿特丽克斯·波特》(Alexander Grinstein,The Remarkable Beatrix Potter,1995)、《皮诺乔与皮诺乔学》(Jennifer Stone,“Pinocchio and Pinocchiology”,1994)等论著。沃尔夫冈·米德在其《白雪皇后之吻》一书中,结合安徒生生平经历的心理和精神分析,对其童话中风格怪异的《白雪皇后》做了条分缕析的重新拆解、阐释。在《不寻常的比阿特丽克斯·波特》一书中,亚历山大·格林施泰因运用精神分析解读了波特的经历与作品。他认为,波特借助其图画书创作克服了童年自我的焦虑与冲突,实现了潜意识的愿望与幻想,这一过程与精神分析师为其病患提供的心理治疗极其相近。更典型的或许是詹妮弗·斯通关于《木偶奇遇记》的研究。在《皮诺乔与皮诺乔学》一文中,斯通从《木偶奇遇记》里读出了科洛迪深切的童年创伤。与卫斯特关于这部童话中的“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分析不同,斯通认为,木偶皮诺乔的故事里隐藏的讯息,远远超出了一个光滑统一的精神成长寓言。皮诺乔的冒险不是欢乐的幻想,而是笔名科洛迪的意大利作家卡尔洛·洛伦齐尼童年创伤记忆的变形呈现。童话中皮诺乔那个著名的会变长的鼻子,生动地传递出他对自我身体的恐惧,深藏于其下的则是俄狄浦斯情结等遭受压迫和禁令的潜意识愿望。大卫·霍布鲁克的《衣橱里的骷髅:C.S.刘易斯的幻想》一书,同样是从精神分析视角对刘易斯著名的“纳尼亚”系列及作家本人展开的重读。霍布鲁克认为,“纳尼亚”系列并不像一些批评家阐述的那样,是以幻想故事形式呈现的基督教义寓言。相反,在刘易斯的幻想作品内部,充满了令人不安的语言与意义的裂缝。他从刘易斯幼年丧母、父亲缺席、校园生活暴力等童年创伤切入其“纳尼亚”系列等幻想文学作品的精神分析解读,指出它同时是一则有关作家潜意识的私人神话。
二是从精神分析视角切入,揭示儿童文学作品表层形式下隐藏的异类精神内涵。哈米达·博斯马吉安在其关于罗尔德·达尔的代表作《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知名解读中指出,成人或许怀着传递积极文化价值与传统的良好愿望创作童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有意无意地引导孩子接受我们文化和文明的缺憾。同样,在儿童文学作品天真、欢乐的表象下,有时掩藏着复杂、暴虐乃至自我颠覆的文化内涵。在他看来,《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表面上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童年幻想故事,主角查理以自己的善良、懂事,最终赢得了甜蜜的奖赏。但它事实上却是“一个挑衅、放纵的力比多幻想”15。与查理一起获得金券进入巧克力工厂的另四个贪食的孩子,是口腔贪欲与对象力比多的象征,他们都因贪食的本能而招致惩罚。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查理,则是一个清空的自我(empty ego),只有完全放弃自我的欲望,他才能成为旺卡先生选定的继承人。这一切象征着以旺卡先生为代表的文明对儿童自我的激烈攻击。但这整个故事的背后,却是作者达尔充满讽刺的笔调。作者显然并不站在旺卡先生一边,而是以针对这一切的意味深长的幽默与讽刺,完成了儿童潜意识欲望的隐在宣泄与释放。
这一从寻常字句间寻微索隐、解释发明的批评方法本身,极大地发掘、彰显了儿童文学文本阐释的潜力。正如米德在《白雪皇后之吻》一书前言中谈到,关于安徒生童话的这类解读,不仅会把我们带向作家的意图,甚至“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说得更多,或者比他自己知道的更多”16。杰妮·普拉斯脱也谈到,当学术界容易对儿童文学研究表示不屑一顾时,儿童文学的精神分析无疑会加深人们对这一看似简单的文类的理解。
但与此同时,随着这一阐释方法的演进,针对语言符号的隐喻发明的乐趣不断越过文本解释的初衷,造成对文本的诠释暴力,其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反思。如果说博斯马吉安的论述虽然包含了研究者本人的诸多解释发明,却并未越出达尔文本的边界,那么约翰·泰尔曼·威廉在《温尼·菩与心理学家》(Pooh and the Psychologists,2001)一书中对A.A.米尔恩的著名童话《小熊温尼·菩》所做的心理学解读,则是将儿童文学文本完全当作了精神分析理论自我演绎与操练的场所。在威廉的解读下,居住在百亩森林的所有动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心理发展问题,小熊温尼·菩则隐在地扮演着精神治疗师的角色,他巧妙地引导朋友们走出心理困境,更好地认识自我。此书封面上背手而行、大巧若拙的精神分析大师温尼·菩的形象,显然已经完全属于哲学博士威廉本人理论的产物。事实上,早在1963年,弗雷德里克·克鲁斯在其戏仿风格的《温尼·菩情结》(The Pooh Perplex)一书中,就嘲讽了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批评方法对这部童话的过度解读17。2001年,克鲁斯出版了《后现代温尼·菩》一书,延续了前一部著作中的批评话题。在克鲁斯看来,诉诸弗洛伊德运动的精神分析批评,助长了一大批自以为借此掌握了文本奥义的分析者的自负18,却恰恰反映了批评与智识本身的弱点。扬·苏斯那在《后现代温尼·菩》一书书评中谈到,克鲁斯关于《小熊温尼·菩》的两部著作证明了“想要揭示某种批评方法的弱点,就把它用到儿童文本上去”19。
针对精神分析研究的反思,意在提醒人们关注文学分析与精神分析的差异,或者说,关注文学文本自身的独特性。U.C.克诺普马赫指出,心理学批评应该充分考虑到文学的微妙与复杂20。正如罗林与卫斯特提醒的那样:“我们应该同时记住,尽管精神分析与文学批评之间的类比关系十分亲近——两者都致力于探询人类语言和情感中的‘隐藏’意义——它却并非是一种精确对位的关系。一件文学作品,不论是《夏洛的网》或艾伦·坡的《安娜贝尔·丽》,它当然是充满感觉与意义的人的表达,但那不是精神分析对象向精神分析师讲述时混乱的随心所欲,不是一个受困、痛苦中的个体在寻求治疗。哪怕没有任何外来意义的添加,我们还是会郑重对待这个文学文本。”21越过文本和文学的儿童文学精神分析当然不妨是文学研究的一种生态和趣味,但在儿童文学的批评语境中,精神分析要充分发挥其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独特意义,还是要回到儿童文学自身的艺术世界里去。
三、经典的重读与儿童的重观
2000年夏天,美国《儿童文学学会会刊》发表了一组从精神分析角度切入儿童文学批评的论文。R.S.特瑞兹在该期导言《儿童文学的精神分析方法》一文中提到,近来《会刊》收到的大量精神分析批评的来稿,说明了儿童文学研究一个趋向22。肯尼斯·纪德认为,将儿童文学与精神分析相结合的当代研究成果,总体可分为四类:一是运用精神分析解释儿童文学及其功能,二是运用儿童文学解释精神分析理论,三是探讨儿童文学如何促进儿童心理发展,四是梳理儿童文学与精神分析的研究历史。事实上,前三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关联,相互交叉。作为西方儿童文学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代表著作,凯伦·科茨出版于2004年的《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一书,虽然被纪德归为第二类,事实上也是一、三两类的典型代表。科茨在书中就《夏洛的网》《爱丽丝镜中漫游记》《彼得·潘》等儿童文学经典展开的精神分析,不仅是拉康理论的文学诠释,同样包含了针对儿童文学文本及其功能的重新思考与评价。透过精神分析的镜子可以发现,儿童文学为儿童提供的主体身份、位置与结构等,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通过运用精神分析开展文本解读,我们将更能胜任辨识个中精神内涵的职责,从而对文本及其阅读影响做出更好的回应。
正是在这样的重新思考和评价里,包含了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相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如果说透过科茨关于《夏洛的网》中威尔伯的精神成长过程的细致分析,我们看到的还是拉康的精神发展理论在一则儿童故事里的完美演绎与印证,那么在作者针对《爱丽丝镜中漫游记》《彼得·潘》的精神分析重读中,我们则看到了处于我们文化潜意识深处的某个儿童的形象。卡洛尔的“爱丽丝”系列,因其胡思乱想与胡言乱语式的荒诞不经,一直是当代儿童文学史述中代表童年精神的标本文本。在哈维·达顿等人的史述中,它被认为是儿童文学从教育中心转向娱乐中心的标志,其荒诞无稽的语言游戏与想象趣味,代表了一种新的儿童文学美学观念的兴起。然而,在精神分析的语境里,这种语言表面的表意错位与荒诞无稽,恰恰为精神分析视角的重新解读提供了另一种标本文本。在科茨看来,爱丽丝始终被卡洛尔的语言城堡困在精神成长的想象阶段,无法走向随后的象征阶段与现实阶段。“卡洛尔设计的这场爱丽丝的冒险,是令她从不能掌控自己是谁或做什么。”23“卡洛尔的作品中遍布着拉康所说的‘符号过剩’,他的每一张面具都想要通过一种不依循象征阶段规则的语言手段,将自己与爱丽丝混为一体。爱丽丝试图通过理解的途径走向下一阶段;卡洛尔借以阻止她的手段,始终是在能指与所指的空隙间玩出的语言游戏。”24“他想要告诉她,成长和长大是不必要的;它只是我们向象征世界的那种自以为是做出的妥协。”25
对于知晓卡洛尔本人的恋童癖好的读者来说,这一分析看似还是针对作家的精神解读。但它与过往潜意识索隐式研究的区别在于,它将关切的重心放到了儿童主角爱丽丝的身上,从儿童精神及其成长的视角,重观爱丽丝的这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对童年想象力的颂扬与赞美的幻想文学作品。如此一来,作品中的爱丽丝非但不再是理想童年的代表,反而代表了日常生活中儿童所受的某种普遍压迫与框范。玛丽亚·尼古拉耶娃在其关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分析中同样指出,奇境中的爱丽丝是无助(helpless)和无力(powerless)的,叙述者牢牢地控制着语言,这种语言构成了对爱丽丝和认同她的儿童读者的夺权与嘲弄。“很难说爱丽丝是一个榜样角色。她的历险是噩梦而非欢乐之梦。她持续的身体变形不但是令人不安和不适的,而且体现了贱斥(abjection),即一个少女对于自我身体的持续变化的恐惧与不快。”26这让我们想起1992年詹姆斯·金卡德在其《恋童:情色儿童与维多利亚文化》一书中提出的相近判断:对爱丽丝而言,奇境并非某个令人向往的欢乐之地,而是充满了烦扰和不安,它不是对童年的颂扬,而是对童年的威胁27。
对于“爱丽丝”故事的精神分析重读,揭示了儿童故事中潜藏的对于儿童的文化暴力,它可能还揭示了一直以来儿童文学的某种潜在的文化特质。这是精神分析批评带给当代儿童文学的重要思考。这一重思和重评的传统,或许可以上溯至杰奎琳·罗斯的《彼得·潘案例》(1984)一书。在这部著作中,罗斯多次引用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的精神分析理论,论证传统儿童文学观念中儿童的他者性质。在罗斯看来,儿童文学始终是成人对儿童的某种文化想象,而无从接近儿童自身。这与科茨在《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一书中关于《彼得·潘》的重读,在精神上是一致的。这部被认为是儿童文学经典的作品,最终呈现的很可能是作者对儿童的某种非儿童的愿望。“最终,永无岛是一个暴力之地,一个杀死记忆的地方,一个只有快感、没有欢乐的地方。”28
从罗斯到科茨,精神分析批评向儿童文学提出了这样的反诘:儿童文学中的“儿童”书写在何种程度上是成人对儿童的非法想象,又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儿童真实的愿望与权益?以及,带着对这种儿童书写的合法性的怀疑,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阅读、批评儿童文学?弗吉尼亚·布卢姆在其《躲猫猫:精神分析与小说之间的儿童》(Hide and Seek:The Child between Psychoanalysis and Fiction,1995)中谈道,我们的文学和文化对于各种想象的儿童形象的热衷,或许与其对于现实儿童的生活困境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以儿童为读者和目的的儿童文学,显然无从躲开这一“躲猫猫”的追问与反思。近年来,西方儿童文学精神分析研究越来越多地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方法融合,致力于接通文本儿童与现实儿童的彼此关联,推进文学童年与现实童年间的良性互塑。1994年,凯琳·莱丝尼克-奥贝斯坦在其《儿童文学:批评与虚构的儿童》一书中延续了《彼得·潘案例》提出的话题,批判了儿童文学及其批评中“儿童”书写和想象的非儿童性。该书末章取名“阅读的儿童与其他儿童:精神分析的儿童与精神分析的空间”(The Reading Child and Other Children:The Psychoanalytic Child and Psychoanalytic Space),嘗试从精神分析的方法与视角提出儿童文学语境下对“儿童”一词的个体性、独特性和不可化约性的理解与落实。在莱丝尼克-奥贝斯坦看来,精神分析——严格说来,是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式的精神分析方法——为实践一种真正以儿童为主体的当代儿童文学阅读与批评提供了重要的指示与启迪。在这里,儿童读者不但是文本的接受者,同时也是文本的创作者。“通过恰如其分地给予读者空间,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方式将文本铭刻入具有其自我情感意义的叙事,通过赋予读者发明其自身书本用途的任何可能,一本书籍将在任何时代带给任何读者他们所需的重要意义。”29尼古拉耶娃关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莱丝尼克-奥贝斯坦的观点。她认为,如果读者能够摆脱对爱丽丝的认同,从她的主体位置之外看进去,“她的经历就是关于一个孤单、困惑的孩子身处迷茫、荒诞的成人世界的深透书写”,就此而言,“这部作品的确充满了颠覆性”30。
通过深入质询儿童文学中的儿童书写,精神分析批评改变着人们理解儿童文学写作、阅读和批评的视角、方式与深度。儿童是难以把握的,同样,通过儿童文学探索、表现儿童的精神,也充满了驾驭的难度。正如肯尼斯·纪德就战争创伤题材儿童文学所说的那样,理解和书写儿童的精神创伤,不是简单地赋予儿童角色想象中的主体权力,而是在充分认识到走进儿童精神世界的难度的基础上,走向儿童文学表现的难度31。如果说一切儿童文学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某种朝向儿童的精神救赎或疗愈的意图,那么如何深入理解、揭示、突破这一写作意图的实践难度,既是精神分析批评向儿童文学提出的挑战,也是儿童文学精神分析批评自身无可推卸的职责。
【注释】
①⑧Michael Egan,“The Neverland of Id:Barrie,Peter Pan,and Freud”,Children’s Literature,Vol.10,1982,pp. 37-55.
②③Kenneth Kidd,“Psychoanalysis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The Case for Complementarity”,The Lion and the Unicorn,Vol. 28(1),2004,pp.109-130:115,109.
④Hamida Bosmajian,“Reading the Unconscious:Psychoanalytical Analysis”,in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2nd ed.,edited by Peter Hunt,NY:Routledge,2005,pp.103-113:103.
⑤兒童文学与精神分析的最初结盟以民间故事为中介。阿兰·邓迪斯曾说:“几乎每位重要的精神分析理论家都写过至少一篇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民间故事的论文。”Alan Dundes,“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Folklore”,in Alan Dundes,Parsing Through Customs:Essays by a Freudian Folklorist,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pp.3- 46. 20世纪初以来,精神分析理论开始重视民间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性质与功能。弗朗兹·里克林(Franz Ricklin)的《童话中的愿望满足与象征》(Wünscherfüllung und SymbolikimMärchen,1908)、夏洛特·伯勒(Charlotte Bühler)的《民间故事与儿童的幻想》(Das Märchen und die Phantasie des Kindes,1918)、布鲁诺·约克尔(Bruno Jöckel)的《通往童话之路》(Der WegzumMärchen,1939)、凯特·弗里德伦德(Friedlaender,Kate)的《潜伏期与前青春期的童书及其功能》[“Children’s Books and Their Function in Latency and Prepuberty”,American Imago 3,nos. 1- 2 (April),1942,pp.129- 50]等著作,关注童话对于儿童心理与精神发展的功能。1963年,尤利乌斯·E.豪切出版了《童话的精神治疗研究》(Julius E. Heuscher,A Psychiatric Study of Fairy Tales:Their Origin,Meaning,and Usefulness,Springfield:Charles C. Thomas,1963. 1974年,该书以A Psychiatric Study of Myths and Fairy Tales:Their Origin,Meaning,and Usefulness为题修订重版),此书奠定了贝特尔海姆《童话的魅力》的方法基础。
⑥Bettelheim,Bruno. The Uses of Enchantment. New York:Vintage,2010,p.5.
⑦31Kenneth B. Kidd,Freud in Oz:At the Intersections of Psychoanalysis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1,p.xii,185.
⑨[美]杰克·齐普斯:《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少年儿童出版社,第114页。
⑩Hugh Crago,“Healing Texts:Bibliotherapy and Psychology”,in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2nded.,edited by Peter Hunt,NY:Routledge,2005,pp.180-189:185.
11Jack Zipe,“Negating History and Male Fantasies through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Children’s Literature 18 (1990):141-43:141.
1221Lucy Rollin,Mark I. West,Psychoanalytic Responses to Children’s Literature,Jefferson & London:McFarland,1999,p.1,14.
1315Hamida Bosmajian,“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and Other Excremental Visions”,The Lion and the unicorn,Vol.9 (1),1985,pp.36-49:36.
14Jenny Plastow,ed.,The Story and the Self. Children’s Literature:Some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Hertford-shire: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Press,2008,p.11.
16WofgangMieder,Kiss of the Snow Queen: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nd Man’s Redemption by Wom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4.
17书中以一位弗洛伊德的信徒、医学博士卡尔·安肖尔恩(Karl Anschauung)的口吻,从精神分析角度谈论《小熊温尼·菩》中米尔恩的“蜂蜜—气球—坑洞—枪—尾巴—浴缸情结”,其过度的符号解读与意义附会,可谓生动地传达了精神分析批评的问题。参见Frederick Crews,The Pooh Perplex,London:Arthur Barker,1963/1964,pp.125-137.
18Frederick Crews,Skeptical Engagement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34.
19Jan Susina,“Postmodern Pooh(review)”,The Lion and the Unicorn,Vol.26 (2),2002,pp.274-278:276.
20U. C. Knoepflmacher,“The Doubtful Marriage:A Critical Fantasy”,Children’s Literature,Volume 18,1990,pp. 131-134.
22Roberta SeelingerTrites,“Psychoanalytic Approa-ches to Children’s Literature:Landmarks,Signposts,Maps”,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25(2),2000,pp.66-67.
23242528Karen Coats,Looking Glasses and Neverlands:Lacan,Desire,and Subjectivity in Children’s Literature,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04,p.88,88-89,89,96.
2630Maria Nikolajeva,Power,Voice and Subjectivity in Literature for Young Readers,New York:Routledge,2009,p.33.
27James R. Kincaid,Child-Loving:The Erotic Child and Victorian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1992,p.228.
29KarínLesnik-Oberstein,Children’s literature:Criticism and the Fictional Child,Oxford/New York: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26.
(趙霞,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CWW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