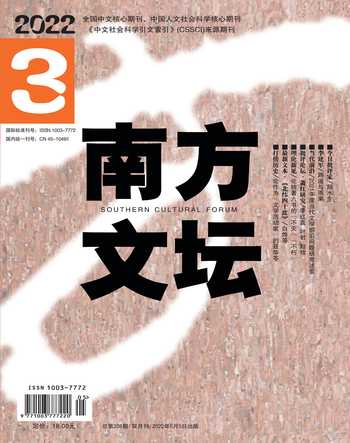原创图画书本土文化的视觉表达
王一典 陈晖
21世纪以来,原创图画书的兴起成为“一种自觉的、成规模的创作和出版行为,成为一种受到读者普遍关注的文学现象”①。与此相对应,儿童文学研究界也越来越关注原创图画书,针对其的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长。毫无疑问,对原创图画书的探讨已成为儿童文学特别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图画书是融合了语言文字和视觉艺术两套表意系统的儿童文学文类,其本身的文类规约决定其兼具儿童性、文学性、视觉性、创意性和开放性。因此,对图画书的研究也必然采取多维度、多层次和跨学科的方法。研究者既要关注主题、题材、故事等文本层面的因素,也要聚焦场景、构图、造型、色彩和媒材技法等图像层面的因素。以往对原创图画书的研究大多较为关注前者,对后者的分析往往一带而过,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图画书里,图书不是文字的附庸,不再可有可无,甚至可以说是图画书的生命了”②。本文聚焦原创图画书中本土文化的视觉表达,从图像层面对图画书的表意方式进行分析。
一、物象、景象与意象的刻画:场景描摹中呈现风土人情
直观可感的物象和景象往往充当本土文化的载体,投射出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原创图画书对物象与景象的呈现常常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如《荷花镇的早市》中的江南水乡、《驿马》中的塞外风光、《百鸟羽衣》中的湘西风情等。其中,《荷花镇的早市》被誉为“中国图画书优美而诗意的开端”,书中对江南水乡细致的刻画甚至让人忽略了文字内容。全书大部分采用跨页的形式,远景、中景及近景相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江南小镇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作品的第一幅跨页描绘了江南清晨烟云弥漫、雾气蒸腾的飘缈与氤氲。湖绿色占据画面三分之二,呈现出黎明时分水天一色的风光,与环衬中青绿色的浸染和涂抹相底部三分之一为错落有致的房舍。在画面左下角,一叶小舟漂浮在河面上,依稀可见主人公阳阳和姑妈。整个画面给人宁静祥和之感。随着叙事的推进,一个个小镇早市的物象依次展现:穿城而过的河流、河上的行舟、河面上的拱桥、临水而建的屋宇回廊、房顶上凸起的阁楼、白墙灰瓦以及沿街的小吃摊、早点铺、杂货店等,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显示出小康生活的富足和便利以及南方小镇的热闹与兴旺。
书中所描绘的是画家童年记忆中的江南小镇,这从扉页上“献给我的妈妈和世界上所有的妈妈们”的献词便可得知。因此,书中无论是房舍的装修还是人物的服饰都反映出特定的历史时代。在第11和14幅跨页的左侧,房屋的墙上写着“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的标语,更是直接将这一场景的时代定格在了20世纪80年代初。在跨页的另一侧,人们忙着做买卖、赶集、拜寿、嫁娶、唱大戏,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真实生活状态的混杂也可视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图画书的最后一页是对寿宴菜肴的特写,圆形的木桌正中央摆放着刻着“寿”字的蛋糕,米酒、鸡肉、咸鸭蛋、寿桃等围于四周。每道菜肴都以不同的形状造型摆放在盘子里,与前文故事中所涉及的购买物品相对应,同时也与扉页中的对话相呼應,制造出奇妙的图文关系。全书一头一尾为静态画面,其余为动态的场景刻画,动静结合,宁静恬淡中蕴藏着喧哗热闹,传达出淳朴的况味、欢乐的气息和充沛的活力。
由青年画家王文哲创作的《那些年 那座城》同样是一本聚焦20世纪80年代初生活场景的图画书。作品的初稿来自画家的毕业设计作品,同时也是图画书的封套。本书的封套是一幅80年代初淄博的全景图,而书中包括环衬在内的每一页图画都是这幅全景图中的一部分。图画书前后环衬一致,作者选取了二十多幅人物造型的图案:男孩子放学后勾肩搭背相约踢球、玩香烟盒的画面,青年男女约会的场景,孩子们坐在小人书摊前聚精会神看书的景象……环衬中,画家寥寥几笔勾勒出人物的线条,并未上色,但笔下的男女老少已有几分神韵。第一个跨页中,绿皮火车在晨光中穿城而过,工厂的烟囱冒着滚滚浓烟,无论是火车的样式还是工厂的外观都将读者拉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小城。书中的跨页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对特定地点做整体性的刻画,如第一幅跨页中对“妈妈”家的院子内外形象的展现:从院子内晾衣绳上的衣服被单、墙边斜靠着的木梯子,再到院子外围坐在小人书摊前看书的孩子,院子后站在树下打弹弓或站在房顶拿着竹竿偷鸟蛋的孩子等。单页中则聚焦特定的事件,如书中多次出现孩子聚众看小人书的场景,这是80年代生人童年常见的娱乐方式之一。在第五和第六页中,画家描绘了孩子偷偷看书被家长抓包后急忙去买豆腐的场景,从而对跨页中的内容进行了扩充,增强了故事性和戏剧效果,同时也反映出特定时代的亲子关系和儿童的家庭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90后的王文哲描绘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淄博。这并非来自画家的童年记忆,而是再现父母那一代记忆中的城市,也将自己父母从相识到相恋的过程画进了图里。身穿白色毛衣、蓝色长裙的年轻女孩和身穿10号球衣的男孩从扉页中的出场到最后一幅跨页中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每一页都有他们的身影:男孩帮女孩修车,在高校服务部门口道别,在豆腐摊前偶遇,在百货大楼前归还手帕再到在街上约会。“每次加入变化和进展,整本书便成了他们相识携手的过程。”③同时,画家在画中对其他年轻男女的恋爱场景亦有所刻画,他们与年轻的父母一起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人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代表。画家也以这种方式参与那样一个她不曾生活过的时代,让“记忆不是个人化的点状存在,而是亲情间彼此传承的红线”④。
作品不仅以细致的场景和人物刻画表现时代印记,而且在细节上颇下功夫。在作品的附录中,画家展示了许多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物品,如搪瓷罐子、不倒翁、黑肥皂等,并将它们与在画中出现的场景一一对应。这些“物证”对于画家进入特定的情境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增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感和厚重感,也让读者对那个相对遥远的时代有更为感性和直观的认识。
除了虚构类图画书,非虚构类图画书也会借助特定的意象表现中国的风貌、历史与现实,于大武的《北京——中轴线上的城市》和《一条大河》是其中的代表。前者以北京城古往今来的演变与传承为核心,以时间与空间为线索,将作为文明古国历史都城和现代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国北京,全方位、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后者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贯穿全书,将黄河流经地区的风景名胜依次展示给读者。值得注意的是,于大武在这两本书中均以写实的工笔真实而真切地描画地理风貌,但在客观冷静的描摹背后,蕴含着画家强烈的情感倾向。画家在作品中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地理风貌和古今演变,更是在向读者输出一种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观,唤起拥有相同文化背景读者的身份认同感。
总之,原创图画书对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特别是富有地域色彩的场景和风俗的表现,是本土文化最常见和直观的表现方式。
二、根植于传统的艺术形式:民族风的继承与戏仿
原创图画书在色彩、造型、构图以及媒材技法方面都向传统文化汲取资源,呈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剪纸、皮影戏、年画等民间传统元素在原创图画书的创作中多有体现。《兔儿爷丢了耳朵》中运用剪纸表现月亮、月兔和兔儿爷等角色,《空城计》中依据京剧来设计人物造型、动作和表情,《十面埋伏》中化用皮影戏的手法,白色虚线的场景、人物、轮廓与彩色的图案相得益彰,增强了画面的戏剧性,渲染了战争的紧张气氛等。
原创图画书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和汲取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化的层面,应“避免概念化、简单化及表面化,避免流于固化的中国符号”⑤,“对文化的‘民族性’应该有更为宽泛的理解,渗透在文字、图像表达中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才是最能体现民族性和文化底蕴的精神和气质元素”⑥。在这方面,蔡皋和朱成梁的创作非常具有代表性。
蔡皋《宝儿》的故事内容改编自《聊斋志异》中的《贾儿》。在书中,蔡皋主要运用了正红和墨黑两种具有强烈对比的颜色作为画面的主色调。相比于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红色,蔡皋在作品中对黑色的运用更具创新性。“强烈的、大肯定的块无疑是有冲击力的。但是,凝重而丰富的灰色色调是民间生活的基调……一切高昂的明艳都是从灰色调子里长出来的。”⑦作品中人物的服饰、马鞍和房内的被褥床幔为亮丽的红色,而四周的屋檐、门窗甚至屋内的家具以及荒园中的岩石都为墨黑色,这种强烈的对比在封面中表现尤为明显。画面采用俯视视角描绘了宝儿在巷子里跟踪狐妖仆人的场景。巷子两边的屋顶皆为黑色,仆人身着黑衣在前面,宝儿身着红衣红鞋绿裤跟随其后,地砖为浅灰色。四周的灰黑营造出阴森恐怖的气氛,两旁的黑屋更烘托出逼仄压抑、冲突一触即发的氛围。宝儿是整个画面中唯一的亮色,这样强烈的色调对比既反映出作者立足民間的美学追求,同时又呼应了故事的基调和人物的身份。正如蔡皋所言:“黑色成为一种氛围、一种结构、一种对比、一种冲突,甚至作为一种宽厚的形态而存在着。一切的冲动和亮丽都从那儿奔走而来,试图表达出它们的那份渴望,那份飞扬起来的精神。”⑧
朱成梁同样善于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资源以丰富画面的表现力。《团圆》和《打灯笼》分别表现了南方小镇和陕西关中春节时的场景和习俗。两部作品绘画风格趋近,都采用丙烯颜料,运用红色、棕色、绿色等色彩饱和度和对比度较高的颜色,着力渲染春节欢快喜庆的气氛。除了色调、色相、色彩的运用和选取,画家对传统文化的表现还反映在人物的造型动作以及构图视角上。如在《团圆》的前几页中,毛毛在画面的边缘微微抬起头打量父亲。这一人物位置和动作的安排形象地反映出毛毛对久未归家的父亲的陌生甚至是恐惧之感。第一幅跨页中夫妻许久未见,相谈甚欢但却又保持距离的状态以及母亲试穿新衣时父亲脸上洋溢的笑容,都体现出中国家庭夫妻间含蓄而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
《打灯笼》不仅描绘了陕西关中“打灯笼”这一特有的民俗,更表现了一个普通女孩伴随着灯笼的点亮与熄灭所经历的兴奋、担心、喜悦、惆怅与期待的情感过程。在图像层面,朱成梁通过对人物表情动作的刻画以及视角运镜的运用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如在小图中对刚拿到灯笼的招娣的正面特写。招娣张开双臂,头微微向下看地,小心翼翼地迈着碎步,充分表现出招娣对手中灯笼的在意和担心,对即将而来的灯笼游戏的期待。另外,门和窗在作品中不仅是特定地区房屋构造的体现,同时承担着画面边框分栏的作用。如母亲在屋外给招娣的牛粪灯点蜡烛时,画面左边一角展现出屋内家人团聚的场景,舅舅侧身坐着,回头微笑看着屋外的外甥女。屋内屋外不同的场景共同营造了节日氛围,也体现出亲人间的深厚情感。除此之外,在招娣坐在门槛上听屋外鞭炮的跨页中,画家借用门和窗将画面切割成了三幅小图。屋外的雪地上三只鸡在啄着米粒,农具柴草倚在墙边,屋檐下挂着牛粪灯;透过门框,屋内的矮桌上散落着果皮;再透过窗户,后院的孩子在雪地里放爆竹。借由景深和透视关系,画面呈现出纵深感和层次感。同时,招娣的寂寞和悲伤与后院中愉快的玩耍形成鲜明对比,更衬托出招娣对春节的不舍与眷恋。
另一幅跨页中,招娣趴在窗户上看着雪地里爆竹燃尽后的碎屑,神情落寞,暗自神伤。画面中间的木门两边仍旧张贴着春联,门头上依然悬挂着大红灯笼。门和窗的运用同样将这幅跨页分成了三幅小图:白雪皑皑的苍茫大地、充满年味的装饰以及孤独失落的少女。三幅情感基调不尽相同的画面凝聚在同一幅页面中,喜庆与寂寥、热闹与冷清、失落与期待,让画面充满张力和含混的意味,而这种意味也是中国人对春节特殊情感和寄托的外化。
在媒材和技法方面,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法及其写意的风格越来越受到画家们的青睐,周雅雯的《小雨后》、梁川的《漏》、蔡皋的《桃花源的故事》、王祖民的《我是老虎我怕谁》和《仓老鼠和老鹰借粮》等作品中都有对水墨画的习染和化用,其中《漏》对水墨技法的运用堪称绝妙。《漏》的故事改编自民间故事。讲述了在一个雨夜,老虎和小偷不约而同地惦记起农户家的小胖驴,碰巧听见老太太怕“漏”,由于做贼心虚,互把对方当成假想敌,于是有了从“失足”“相撞”“狂奔”到“折返”“相遇”“逃离”一系列状况。画家通过调配水墨的不同比例,运用墨色的浓淡,巧妙地区分出人物、动物与景物、场景间的不同色调,让画面充满层次和变化。为了表现那场疯狂的大雨,画家用毛笔饱蘸墨汁,朝桌子上、墙上尽情摔、甩、挥、洒,然后进行剪贴,同时兼顾图形的角度与距离,画面的雨滴呈放射状喷洒而出,大小深浅不同的雨点生动表现出雨势逐渐增大的动态过程,正是这种近乎泼洒式的画法赋予了画面极强的视觉震撼。作品围绕着“漏”展开,在有些画面中,“漏”字本身也以水墨的形式呈现为图内文,大小不同的漏字散落在画面的各个角落,以视觉图像的形式反映出老虎和小偷的惊讶和对“漏”的极度恐惧。
除了对传统绘画技法的继承与习染,有些图画书也会对经典的画作进行戏仿。《天啊!错啦!》就是原创图画书中为数不多具有后现代意味的作品。作品讲述了兔子把红裤衩当作帽子,动物们对此都发表了看法,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兔子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整个故事具有十足的游戏性和戏剧性。但是作品的前环衬和第一幅跨页中柔美的江南风景却与这种荒诞幽默的风格形成强烈反差和混搭。前环衬上散落的稿纸、钢笔、水杯及各种衣物,扉页上角楼外飘动的衣物,及起风的画面,共同交代了裤衩的由来。第一幅跨页中的江南山水画是扉页中小图的全景化。据画家所说,这幅画是从吴冠中的《怀乡》中汲取灵感,其中的意境之美让画家在画风景时更加得心应手。
这幅跨页的左边同样出现了角楼和拱桥,但右边却变成了紫色的山峦和田野。同时,与故事内容相呼应,红裤衩从左边的衣架上飘向右边,犹如从现实世界飘向幻想的世界。相比于原作传达出的宁静祥和之感,作品中的图画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营造出一种充满玄机的氛围,为之后的故事做了铺垫。森林的树木都呈现偏紫蓝色的色彩,给人一种亦真亦幻之感。
关于色彩的选取,画家认为“紫蓝色的树暗示了树林的深度及密度,以及森林的神秘性”⑨。同时,“绘画中的色彩仍借鉴传统绘画风格,如明代画家仇英《南溪图》中,树就是蓝色的”⑩。
另外,在构图布局方面画家也多借鉴传统绘画的表达方法,如作品中的多幅画面由一条路来贯穿,这种构图方式与敦煌莫高窟壁画《幻城喻品》中用弯曲的路将故事串联起来的方式相似。同时,“(画面中)人物都是不远不近的,视角好似低空俯视,好像边走边看一般”11。
可以看出,《天啊!错啦!》既有对传统绘画的致敬,也尝试对名作进行颠覆,将风格反差极大的景象、色彩混搭在一部作品甚至一幅画面中,对某些经典作品进行解构与重构,使其更符合作品的主题。更重要的是,相较于在图画书中对传统元素的直接继承,这种带有后现代意味的本土文化表现方式更能调动读者的主体性,激发读者主动探索的欲望,同时也赋予古老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
对原创图画书中本土文化造型、构图、色彩、媒材技法等艺术表现形式的分析其实都指向视觉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表征。依据霍尔的看法,表征实际上包含了事物、概念、符号三个要素,它们两两合对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关联系统。但是,“从现实世界到符号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镜子上的反射(再现)。首先,有一个从客观的物到主观的概念的转换;其次,还有一个从主观的概念再到客观的符号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也就是从指涉物到所指,再到能指的过程,其间充满不同的表征方式、方法、视角和技术”12。因此,图画书中对本土文化不同的表征方式,与画家的艺术理念和审美趋向以及作品本身的主题及题材息息相关。
三、本土文化表达的核心趋势:儿童性、艺术性与世界性
方卫平在谈到原创图画书的民族化问题时曾提到,“希望原创图画书在呈现鲜明而完美的中国气象和风格的同时,在图画书艺术特质自身的想象和创造方面,也能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提升”13。因此,怎样将本土文化与图画书本身的性质和特质相结合是未来原创图画书在本土文化视觉表达中首先要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若想要让本土文化在图画书视觉层面得以自然顺畅地表达,画家需要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儿童性、艺术性和世界性三者的关系。
首先,原创图画书的主要读者为学龄前和学龄初期的儿童。因此在本土文化视觉表达中,画家要站在儿童的立场,考虑到广泛的儿童接受性,能让儿童体验及享受阅读乐趣。如朱成梁的《别让太阳掉下来》中动物的形象分别取材于陕西凤翔的泥塑玩具和河南浚县的民间玩具。画家还从中国传统漆器技法和色彩中得到启示,选取红色、褐色和金色三个主色调来表现天空、山林、太阳;在构图上,画家巧妙地以方、圆、半圆来分割画面,这些都具有漆器的特点。与此同时,作品中小动物们捆、撬、托、顶、驮、抓太阳的动作既符合动物的习性,又充满着情趣与乐趣。温暖的色调与可爱的造型使这个原本就充满想象力的童话故事更加富有童趣。画家在充分考虑儿童读者的基础上,将民间艺术和色彩自然融入创作中,创造出既为儿童喜闻乐见又具有鲜明民族性的图画书。
如果说《别让太阳掉下来》无论从故事内容还是视觉效果上都以好玩和趣味取胜,那么九儿的无字书《纽扣士兵》则将失落、找寻、亲情、思念这些看似宏大的话题与儿童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枚纽扣被小男孩从马路上捡回,画上“兵”字,阴差阳错成了象棋盘上一个生龙活虎的士兵,骁勇善战,蹚过楚河,俘虏军师,和同伴一起活捉大将,最后赢得胜利。画家将象棋棋子拟人化,使其成为故事的主角之一深度参与叙事之中。通过纽扣变棋子的经历串联起祖孙相互陪伴的场景、对已故情人的思念之情乃至失落与找寻这一更为深刻、更具普适性的议题。画家并未流于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简单再现,而是借用象棋棋子这一本土文化意象,将儿童的生活情状与自身的生命体验融入视觉表达之中,和整个作品水乳交融。
其次,画家在进行图画书创作时常常会面临“为儿童”还是“为艺术”的选择。这里不妨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北师大版”)的《九色鹿》与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下简称“苏少社版”)的《九色鹿》的绘画风格作对比来说明这一问题。“在图画书里,风格可以从结构或观点的特有模式中体现,也可以通过对主题的选择而产生。”14由于两版《九色鹿》取材于同一个民间传说,因此这里主要对比线条、造型、色彩、技法、媒材等方面的差异。北师大版《九色鹿》的图画是刘巨德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精心绘制的。“画家深得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写意精髓,吸收与采纳了敦煌壁画式的绘画风格……画家用半透明的笔触描画出它的神秘高贵,以及无与伦比的美和超凡脱俗的仙气……”15“九色鹿并不拘泥于九种颜色的外在显现,而是以刚劲的线条勾勒轮廓,半透明的笔触涂抹出白色、米黄等梦幻、朦胧的色彩塑形。”16
在苏少社版的《九色鹿》中,画家廖健宏用黑色剪影勾勒九色鹿的轮廓,同时将许多小小的色點、色块点缀其中。这样的用色方式既延续了《进城》中以黑色塑造人物的自我风格,又有别于以往的技法,融入了色彩。除此之外,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和场景也大多采用低彩度的蓝与灰,加之画面底色为仿古丝绢的浅棕色,画面整体色调偏暗淡。相较而言,北师大版的《九色鹿》画面多以米黄、红色等暖色调为主,在视觉上更易于为低龄儿童所接受17。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明天出版社的《漏》与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漏》在读者接受上的差异。
有的作品对儿童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处理得当,既有对传统艺术的汲取和吸纳,又凸显出鲜明的儿童立场,在儿童读者中有着广泛的接受性。如王祖民的《我是老虎我怕谁》以及《仓老鼠和老鹰借粮》中,画家圆熟运用水墨技法勾勒人物、动物以及物品的线条,同时采用水粉上色。角色情态、体态十分鲜活,恰到好处的变形,让动物们举手投足的动作,都有幼儿似的天真,拟人角色被赋予了儿童性。
画家田宇在“点虫虫系列”的创作中运用中国传统的“兼工带写”的绘画技巧,用工笔画的方法工整精细地刻画蜻蜓、螳螂、蚂蚁等故事的主角,亦用写意的画法渲染周围的环境,如花卉、蔬菜、瓜果等。就图文关系而言,画家在对照呼应文字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延展和发散。《我是蜻蜓你是谁》中的许多画面内容都与古诗或谚语相对应,如提及蚂蚁的一幅跨页中,文字内容仅涉及蚂蚁的外形和名称,但在画面上却是小蚂蚁爬在一颗梨子上。据画家所言,这幅画面暗合杜甫的诗句“行蚁上枯梨”。在以蜻蜓和螳螂为主角的两幅跨页中,画家分别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隐藏其中,从而让图画对文字信息起到了“增容”的效果。儿童读者在阅读图画过程中既享受寻找和辨识昆虫所带来的乐趣,又体会到图画中丰富的视觉信息和艺术美感。
诚然,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原创图画书创作而言,“为儿童”或是“为艺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是两个主要的方向。“兼容并包当然更好,但创作者如果更多趋于成人化和个性化,他们的作品同样值得肯定和鼓励,图画书艺术的任何一种探索与实验,对中国图画书的成长都具有积极的意义。”18
再次,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合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使其具有面向世界的表达,是当前中国原创图画书创作所面临的又一难题。我们可以引入“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一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全球本土化的概念最先由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提出,他认为“全球本土化”是多樣文化的共存,“是普遍化趋势和个性化趋势的同在”19。它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转变由此带来的反应之一,“挪用全球化并将其本地化,然后给予外国元素以中国味道,将其以新的含义展示给世界”20。“全球本土化存在于同一性和本地化的复苏的辩证统一。”21“‘全球本土化’所呈现的核心问题具有鲜明的跨文化意味,文化多元主义是当代全球状况的结构性特征。”22
多元文化是图画书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原创图画书做出了可喜的尝试。中国作家与域外画家的合作是本土文化进行世界表达的路径之一。曹文轩与巴西罗杰·米罗合作的图画书《羽毛》就是其中的代表。罗杰·米罗用糅合了巴西与中国传统视觉艺术元素,作品汇集了很多代表中国的意象,各种形状的青花瓷瓶、游弋着红鲤的水缸、中国古代纹饰的鸟类造像等。特别是画面中用瓷器这一在英语中与“中国”相同的单词,去建构故事的景观。图画中各种夸张变异的鸟儿形象以及反差对比度极其强烈的色彩,又使画面洋溢着浓郁的南美风情。“米罗在插画中将南美热情奔放的色彩及奢华的纹饰与东方宁静淡泊的气质相结合,以纯色的背景与抽象的线条,对应原著简约的语言,并加以象征的文化符号,将原本的中国故事凝结成符号。”23
英籍华人画家郁蓉将剪纸和素描结合所形成的个人风格在当代原创图画书创作中独树一帜,在《烟》《云朵一样的八哥》以及《我是花木兰》等中都有所体现。在《云朵一样的八哥》中,郁蓉用深蓝色的宣纸去剪纸,对传统的剪纸艺术进行挑战。“在尊重传统剪纸的风格上,保持了剪纸的原生民间的情态和稚拙的技法。”24画家没有选用传统剪纸中常见的红色,而是用深蓝色表现出阴影感,这跟书中八哥给“框范”、笼罩起来的某种情绪之间形成对应,同时也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受。
在《我是花木兰》中,剪纸和素描的运用则更为圆熟,其中剪纸的部分几乎不见传统的中国风,尤其是花木兰身上的披风装饰感极强,但却用素描技法在背景里细致地仿画了很多传统的山水画。郁蓉将素描西为中用,将剪纸艺术中为西用,这种中西倒错正是其努力拓展剪纸艺术的结果。这种中西元素之间的混搭使画面超越了传统元素的表层体现,而是深入到文化与审美的内部。同时,在构图处理上,郁蓉也突破了传统剪纸注重边框和整体的形式,图画书完全艺术化了。
本土文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当下的现实文化。张之路与孙晴峰的《小黑和小白》表现了网络时代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疏远、隔离的生存状态,阿根廷画家耶尔·弗兰克尔以极简的抽象派的绘画风格塑造人物及场景,“用简单的颜色描绘了疏离与热情、恐惧与渴望、挫折与勇气、孤独与爱,用图画书的‘世界性语法’讲述当下中国人的故事,用图画书的‘典型表达方式’讲述与众不同的故事”25。
“中国文化在图画上的表意既是由表及里的也是由内而外的。不仅是情景和场景、物象和意象,还体现在传承及美学意义的情调及韵味。”26画家的创作要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及艺术的传统,并有符合儿童审美接受度的、富有个性及创作性的、面向世界的表达,这是原创图画书跻身于世界图画书之林的根基。
【注释】
①13方卫平:《享受图画书——图画书的艺术与鉴赏》,明天出版社,2016,第91、149页。
②彭懿:《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接力出版社,2011,第7页。
③④向华:《那些画 那个人》,见《那些年 那座城(导读手册)》,新世界出版社,2019。
⑤1826陈晖:《中国图画书创作的理论与实践》,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第119、167、37页。
⑥谈凤霞:《突围与束缚:中国本土图画书的民族化道路——国际视野中熊亮等的绘本创作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⑦⑧蔡皋:《黑色底蕴里走出的明艳》,见《宝儿(画者的话)》,明天出版社,2008。
⑨⑩11姬炤华:《用看电影的方式看绘本,拉一拉〈天啊!错啦!〉中的“彩蛋”》,https//mp.weixin.qq.com/s/q7RYG0OJRBwHJ2vrzSZ5VQ。
12周宪:《视觉建构、视觉表征与视觉性——视觉文化三个核心概念的考察》,《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14[加]佩里·诺德曼:《说说图画:儿童图画书的叙事艺术》,陈中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第114页。
1516萧萍:《盛宴、遥远的美,以及留白》,见《九色鹿(导读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7相关研究表明,暖色调比冷色调更受幼儿喜爱。参见林琛琛:《幼儿对图画书封面的审美偏好》,《幼儿教育》2015年第36期。
192021Anna Katrina Gutierrez:Mga Kwento ni Lola Basyang:A Tradition of Reconfiguring the Filipino Child,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Children’s Literature,2009,2(2),p160.
22李娟:《文学的“全球本土化”: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察》,《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
23王岫庐:《〈羽毛〉背后的中国声音与世界故事》,《南方文坛》2021年第6期。
24郁蓉、赵霞:《让当代想象力在传统文化艺术中爆发》,《文学报》2021年5月25日。
25常立:《那些看却看不见的一切》,见《小黑和小白(导语)》,明天出版社,2017。
(王一典、陈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资助项目“新世纪中国原创绘本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