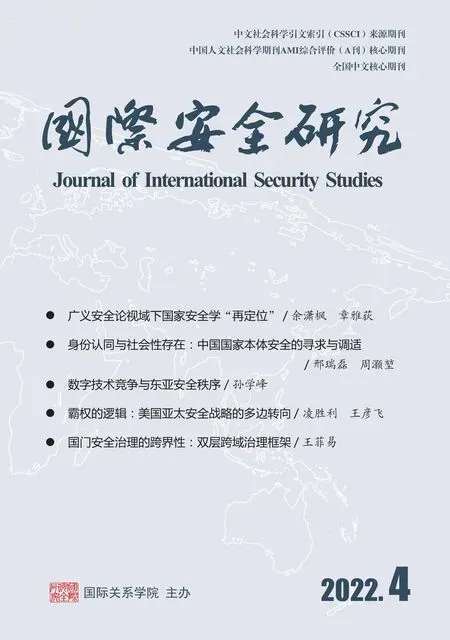身份认同与社会性存在:中国国家本体安全的寻求与调适∗
邢瑞磊 周灏堃
【内容提要】 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博弈中,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面临着多重身份认同、跨国沟通网络和群体情绪/情感等问题带来的新型挑战。多样的身份认同危机会导致国家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出于维系“社会性存在”的目的,国家会启动情绪/情感性自我保护机制,呈现以“焦虑感”为特征的“非理性行为”,可能带来国家间的安全对抗和冲突。获取国家本体安全取决于国家自传式叙事的连续性与“自我—他者”信任关系协调机制两条路径的均衡发展。在百年大变局下,“何为中国”的自传式叙事正由“内向型”的国家主体性向“外向型”的国际能动性身份转变。新时代中国国家身份转型和国家本体安全的获得,一方面,取决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成功建构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新型负责任大国叙事体系;另一方面,有赖于重塑和调适中国与西方大国和国际社会的“竞合型”与“和合型”两类信任关系,其调适结果不仅是实现“自我—他者”良性互动的前提,也是决定中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生态的关键。
导 言
近年来,在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转型的叠加影响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的界限日益模糊,国家安全的复杂性空前增加。现实变化迫切需要推动学术研究的相应转型。目前,针对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的国际安全环境,研究者已经从安全思想、战略历史沿革、政策分析、概念诠释、学科建设等角度展开了针对性的理论与实证探索。①相关代表性研究可参见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6期;谢卓芝、谢撼澜:《“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综述》,《理论视野》2016年第5期;黄纯艳:《朝贡体系与宋朝国家安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冯维江、张宇燕:《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李文良:《国家安全:问题、逻辑及其学科建设》,《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刘跃进:《安全领域“传统”“非传统”相关概念与理论辨析》,《学术论坛》2021年第1期;贾庆国:《对国家安全特点与治理原则的思考》,《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但是,有关安全理论的研究大多仍侧重于讨论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军事竞争等实体性安全因素。在充满复杂性、流动性与不确定性的全球化时代,次国家行为体能动性增强、“超国家化”趋势愈演愈烈、身份政治兴起、“后真相”时代到来以及全球南北国家地位对比转变带来的国家身份困境,已经成为威胁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生态的重要来源。事实上,近年来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民粹主义、自由国际秩序危机、大国间的战略对抗等国内国际问题的集中爆发,皆与全球化时代国家身份问题密切关联。因此,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局势的变化,需要我们加强对身份认同相关的关系性和过程性安全维度的关注。②季玲:《关系性安全与东盟的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9期,第122页。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关注大国政治和军事竞争的传统安全研究。本文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身份、集体情绪/情感与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状态的内在联系是什么?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安全诉求和国际安全状态的互动机制是什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我们充分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安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中国更有效地维护国内安全、参与国际安全治理提供理论启示。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方兴未艾的本体安全理论(Ontological Security)为基础,通过系统思维,为理解中国国家安全的理论认知提供补充。
一 国家身份困境与国际安全理论研究
21世纪以降,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叠加影响下,全球范围大多数功能领域的国际交往的相互依赖程度空前增长,软权力、技术权力和信息权力等新型要素,正在塑造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安全环境。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为我们理解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全球化带来的国家身份危机是当前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面临的一个新威胁,也暴露了传统国际安全理论研究中的不足与缺陷。
(一)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身份困境
全球化时代出现了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新问题,因此需要重新认识国家的身份建构问题,并理解上述问题对于国家安全造成的种种挑战。
首先,次国家行为体越发活跃,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主权国家在国家身份塑造方面的传统支配地位,呈现出各种身份叙事彼此冲突对立的困境。种族、性别、阶级、文化群体和职业团体等身份单位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凸显,全球化的深度推进更是造成各种次国家行为体在国家身份塑造方面产生差异化需求,具有身份叙事需要的能动者不断增多。①Margaret R.Somers, “The Narrative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A Relational and Network Approach,” Theory and Society, Vol.23, No.5, 1994, pp.629-633; Samuel P.Huntington, 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p.142.这一新的变化,导致过去由国家自上而下主导的身份叙事不得不与次国家行为体自下而上的亚叙事诉求展开竞争。过去单一且稳固的国家身份认同正在遭遇身份的碎片化、分散化和脆弱化带来的迷失,而这往往会造成国家解体和族群冲突等地区性或全球性安全后果。②甘均先:《国家身份与国际安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27-128页。
其次,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界限模糊化,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形成了“多孔化的”(即开放性和通透性)超国家安全空间结构,对国家内部的自我身份认知带来威胁。在“国际安全的国内化”和“国内安全的国际化”两个机制作用下,“多孔化的”安全空间结构为非传统安全转化为影响国家、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生态的因素创造条件。③贾庆国:《对国家安全特点与治理原则的思考》,《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第10页。在“多孔化的”安全空间结构中,国家身份的流动性和可塑性显著增强,身份安全面临的风险程度大幅上升。国家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过程中,既定的国家身份不再具有不可置疑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跨国因素的显著渗透使得国家间的边界逐步淡化,国民层面的国家身份认同正在逐步消解,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所属感正在增加。①郭丽双、付畅一:《消解与重塑:超国家主义、文化共同体、民族身份认同对国家身份认同的挑战》,《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39页;吴玉军:《全球化与“去中心化”:现代性语境下的国家认同困境》,《哲学分析》2020年第2期,第5页。这意味着民族国家稳固的身份叙事面临着超国家主义的侵蚀和威胁。②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1, 2000, p.21.例如研究者发现,“多孔化的”安全空间是欧洲难民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而难民危机的本质则是观点、情绪/情感、政治身份和选票的跨界迁移,③Ivan Krastev, After Europ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7, p.19.并且激发了欧洲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生态,是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传导的结果。
再次,通信技术和新兴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现代社会心理和认知结构的改变,出现信息时代向体验时代(Experience Age)的转向,并带来了“后真相状态”的非预期结果。④Gabriele Cosentino, Social Media and the Post-Truth World Order: The Global Dynamics of Disinformation,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p.9-10.“后真相状态”是理解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国内—国际政治生态变化的重要角度。后真相状态下,过去被理性政治范式忽视的情绪(emotion)和情感(affect),⑤在心理学中,情绪(emotion)是一种短期性的内在心理状态,其表现形式较为明显,因而也更容易被人们所识别,同时它也具有较强的变化性。相比而言,情感(affect)则是较为长期的心理状态,它往往难以被准确识别,也可能不受意识的调节,因而可能更具稳定性。详情可参见Emma Hutchison and Roland Bleiker, “Theorizing Emotion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Vol.6, No.3, 2014, p.502。成为集体政治行动的显著因素,也是塑造新群体身份的“标签”,即人们会更多关注发言者的群体身份和经验体会,关键变量不再是理性观点的可验证性,而是日常生活体验触发的集体情绪/情感,进而与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⑥Rhys Crill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Post-Truth’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4, No.2, 2018, p.418; 谢超:《右翼民粹主义动员的“后真相”状态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国际论坛》2021年第4期,第138-141页。更复杂的是,作为主体的经验,集体情绪和情感具有明显的“主体间性”,受特定社会互动方式和文化惯习的影响和塑造。⑦Neta C.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4, 2000, p.125.显然,后真相政治加大了社会身份对立和观点极化的危险,扩大了国家间不信任、对立和冲突的潜在风险,凸显了国家安全面临环境的高度复杂性。①Ignas Kalpokas, A Political Theory of Post-Trut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22-25; Emanuel Adler and Alena Drieschova, “The Epistemological Challenge of Truth Subversion to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5, No.2, 2021, pp.376-379.
最后,全球化的加速凸显了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身份裂痕。当代国际秩序建立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中心—边缘”权力结构基础之上,②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与欧洲开始丧失物质优势地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面临着衰落的危机。③Charles A.Kupchan, No 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和防范日渐升级,而中国意识到被动接纳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并不会给中国的国际身份和地位带来应有的承认与尊重。④戴晓东:《文化安全的三个辩证关系》,《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第40页。其结果是,西方大国对于中国正当国际身份和国际地位诉求产生焦虑情绪,加强对中国诉求的遏制和打压,导致形成基于身份和地位的安全螺旋困境,⑤Michelle Murray,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us, Revisionism,and Rising Pow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71-80; 曾向红、李琳琳:《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3期,第87-91页。从而造成国际关系信任基础破裂和国际安全结构不稳定的现实后果。
总之,全球化时代下因国家身份问题引发了上述四类安全风险,现代国家介于“全球”与“地方”之间,由于身处各种跨国的和功能分化的权力场域中,时刻面临因观念、人员、信息和资本要素跨国流动带来的国家身份碎片化、重叠化和竞争化困境。国家基础要素的跨国流动性与国家身份稳定性/连贯性间的张力关系,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身份困境的核心特征。⑥陈雪飞:《“超国家化”对现代国家的挑战: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96-199页。更重要的是,这种跨层次张力关系导致的国家身份困境凸显出群体身份、集体情绪/情感和国际安全生态的联系,是多元安全主体、安全空间、群体心理与认知结构等多种因素组合的复杂性结果。
(二)国家身份、情绪/情感与安全:理论定位
既往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全球化时代国家身份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细致分析。冷战时期,安全研究的现实主义路径秉持“原子式物质安全观”,安全被限定为客观物质意义上的国家生存和政治主权,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实现和维护,而其威胁主要来自他者真实意图和信息的“不确定性”导致的霍布斯式“自然恐惧”。①Jack Donnelly, “The Ethics of Realism,”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55; Tang Shipi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0, No.3,2008, pp.455-456;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刘丰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2-183页。在这样的条件下,巩固国家安全主要是通过均势、军备竞赛、先发制人和预防性战争等方式,实现自助式的权力积累。②Stephen M.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5, No.2, 1991, pp.213-214; David A.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48, No.1, 1995, p.121; Lawrence Freedm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nging Targets,”Foreign Policy, No.110, 1998, p.48.受制于现实主义路径的支配性地位,许多研究者把国家身份作为外生给定因素或常数(国家都是原子式单一理性的行为体)来对待,忽视了国家身份形成的过程性、互动性和主体间性。③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2010, pp.96-97;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p.336-337.针对这个不足,在建构主义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出现了“认识论”革新,在“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两种研究取向下,通过引入观念要素,以期对国家身份的动态性、过程性及其与国家安全状态的关系进行分析。
但是,主流的社会建构主义对于国家身份的理解主要是在“自我—他者”的互动和对比过程中讨论群体身份的形成,侧重于从制度性认同到集体身份的社会建构过程,属于“外生性”的身份形成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实际上意识到了单元层次“内生性”身份的重要意义,由于其理论旨趣在于调和主流的结构理论和“非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对集体身份的讨论进行了限定,较少讨论单元层次群体内国家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集体情感和心理依附感对于集体身份塑造的作用。
事实上,一些非西方世界的安全研究者已经敏锐捕捉到了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对群体内维度的忽视,并且尝试揭露隐藏在“安全”概念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在西方的语境中,安全是一个具有外部指向性的概念(群体间性),即威胁与不安全总是来源于领土之外的其他实体,并且一国的安全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密不可分。①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2010, pp.102-104.然而,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群体内稳固的国家身份尚未形成,核心安全关切往往是针对内部事务,尤其注重防止外部势力通过内部分裂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②Mohammed Ayoob, “Security in the Third World: The Worm about to Tur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0, No.1, 1983, pp.43-47; Amitav Acharya, “The Periphery as the Core: The Third World and Security Studies,” 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301-302; Laurie Nathan,“Domestic Instability and Security Communi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2,No.2, 2006, p.280.不仅如此,大量有关第三世界国家族群战争的研究发现,恐惧、荣誉、仇恨和愤怒之类的集体情绪/情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会切实影响人们对群己关系的界定,影响威胁感知和安全信息收集与解读方式,左右人们对于族群历史的认知与理解,从而对“群体间—群体内”的身份塑造产生影响,成为群体内冲突“外溢”为群体间国家战争的重要因素。③Mohammed Ayoob, “The Security Problematic of the Third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43,No.2, 1991, p.263; Neta C.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4, 2000, pp.134-140; 唐世平:《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李思缇译,《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4期。遗憾的是,建构主义在理解国家身份形成的过程中,仍然奉行理性主义的基本假设,未能充分认识到国家陷入代价高昂、风险巨大且全无必要的冲突中并非都是非理性的结果,而是在各种集体情绪/情感强烈驱动下诱发的多重身份博弈与竞争所致。④Alexandria J.Innes, “Everyday Ontological Security: Emotion and Migration in British Soap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11, No.4, 2017, p.384.
综上所述,伴随着安全理论数十年来的发展脉络和全球化时代对国家安全造成的新挑战,整合结构性约束和行动者的能动性,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在“群体间—群体内”政治动员过程的机制性作用,并把物质生存、身份形成和群体情绪/情感等诸多因素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内,已经成为国际安全理论研究的新需求。就此而论,21世纪以来方兴未艾的本体安全理论,可以为我们深入理解处于“晚期现代性”和全球化下的国家安全提供独特的理论视角。
二 自传式叙事、“自我—他者”信任机制与国家本体安全:一个分析框架
正如上文所述,身份认同、情绪/情感与安全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是当前国际安全理论研究的前沿性议题。本项研究拟在本体安全理论最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国家身份形成、群体心理情绪和国家安全之间的互动机制,及其对“主体间性”安全认知结构和国际安全生态的可能影响。
(一)本体安全理论的演进
本体安全理论源于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社会心理学,是关于自我、他者和客体世界关系的哲理和规范思考,旨在从本体论层次上追溯社会规范、自我认同及其产生施动能力的心理机制与根源。①李格琴:《国际政治本体安全理论的建构与争论》,《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20页。20世纪60年代末,心理学家罗纳德·莱恩(Ronald David Laing)提出了“基础性本体安全”假设,假定个体对其在社会中的存在位置,根源于意识形成萌芽阶段的确信感(assurance)。当这种确信感出现缺失或动摇时,个体就会缺少“存在于世”的连贯感或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②R.D.Laing, The Divided Self: 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p.39.此时,焦虑、无意义感和羞耻感等负面情绪/情感就会影响个体的判断和行动。
20世纪90年代初期,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把“基础本体安全”假设引入社会学,用于讨论现代社会结构和自我认同的紧张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本体安全是指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关系性存在”或社会身份的一种安全感。吉登斯认为,本体安全就是“主体对(社会)事件的延续感和秩序感”,③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页。是主体“对自然界与社会世界的表面反映了它们的内在性质这一点的信心或信任,包括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基本存在性衡量因素”。④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4页。在吉登斯看来,本体安全是行为主体稳定的、连续的社会存在性身份,是与“广义他者”(即其他主体和物质—社会环境)构成“主体间”基本信任关系的前提,而这种基本信任关系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石。
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本体安全理论是有关个体身份、情绪/情感和行为的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需要解决从个体到国家的“跨层次”应用问题,尤其是焦虑概念可否用于群体现象分析。就本体安全理论的“跨层次”应用问题,事实上传统国际安全理论同样采用了国家“拟人化”的方式,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研究者对于国际体系结构或状态的不同理解。传统国际安全理论预设了无政府状态假设,国家在自然状态下是彼此独立的理性个体。由于缺少必要的社会性联系,国家只能通过权力竞争和制衡策略塑造“脆弱的”均势秩序。因此,传统的国际安全理论基本上是权力政治的逻辑。
本体安全理论则首先承认了国家间存在社会性联系、国际秩序乃至国际社会,即本体安全理论是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内展开的理论讨论,其逻辑更接近于“承认政治”。在焦虑概念的问题上,卡尔·古斯塔夫森(Karl Gustafsson)和尼娜·克里克尔-崔(Nina C.Krickel-Choi)曾系统回溯了本体安全理论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根源,区分了“普通焦虑”(normal anxiety)和“神经性焦虑”(neurotic anxiety)两个概念。“普通焦虑”是一种基于环境不确定性而产生的负面情绪/情感,可以通过调整触发条件予以缓解,而“神经性焦虑”则是个体精神层面压抑或内在心理冲突的病理表现。古斯塔夫森和克里克尔-崔认为,“普通焦虑”不仅是个体的情绪/情感感受,也常以群体情绪/情感形式出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群体文化和社会现象中。因此,本体安全理论强调的焦虑概念同样可以应用于群体现象的情绪/情感分析。①Karl Gustafsson and Nina C.Krickel-Choi, “Returning to the Roots of Ontological Security:Insights from the Existentialist Anxiety Litera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6, No.3, 2020, pp.887-888.
在上述讨论基础之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家本体安全就被理解成一种相较于国家“自身”(Body)物质安全而言的国家“自我存在”(Sense of Self)的安全意识,意指国家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和国际规则互动过程中,在多重的身份、角色和“主体间”认知结构中,确保和维系国家“自我存在”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心理保障机制。②Felix Berenskötter, “Anxiety, Time, and Agency,”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12, No.2, 2020.就此而论,国家本体安全是一种过程和关系导向的国家安全观。
(二)本体安全的内涵
首先,国家本体安全是一种过程导向的心理安全机制,是保证国家行为连贯性的前提条件。国家本体安全理论认为,本体安全与国家的物质安全不同,并非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需要国家主动寻求才可以获得的一种防御性“茧壳”。①Brent J.Steele,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Power of Self-identity: British Neutrality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1, No.3, 2005; Chris Rossdale, “Enclosing Critique: The Limits of Ontologic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9, No.4, 2015, pp.370-373.作为一种安全保护机制,国家本体安全在实践活动过程中还承担着“过滤器”的职责,负责把危及国家“自我存在”的安全威胁隔离在外,确保国家“自我存在”叙事的延续性。国家本体安全的寻求过程即国家获得身份叙事连续性、社会动员能力和国际能动性的过程,②Jelena Subotić, “Narrative,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12, No.4, 2016, pp.612-617.而这三种能力构成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维系“自我存在”的基础。珍妮弗·米岑(Jennifer Mitzen)据此认为,本体安全是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行使国际能动性的前提条件,本体安全和物质安全都是最基本的国家安全需求。③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2, No.3, 2006, p.342; Catarina Kinnvall and Jennifer Mitz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tological Securities in World Politics,”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52, No.1, 2017, p.4.
其次,国家本体安全是一种关系性的安全能力,是塑造“自我”与“他者”信任关系的基本能力。在本体安全理论视域中,国家行动既不是现实主义“台球式”封闭实体之间的权力碰撞,也不是自由主义假定的具有渗透式边界和多元利益团体偏好的动态博弈,而是物质、观念、情绪/情感和符号等权力因素在社会结构、群体间和群体内复杂交互的权力实践过程。国家行动实际上是权力关系实践和效果的一种呈现(unfolding),而国家安全则是国家策略性地使用工具理性、适当行为和表演行为(performative act)塑造与“他者”信任关系的实践能力。因此,国家本体安全是指国家的“自我存在”在多重的权力网络和信任关系中获得“心理依存感”(attachment)和“他者”承认(recognition)的关系性能力。
最后,国家本体不安全是一种由焦虑引发的负面状态。相对于过程性和关系性导向的国家本体安全概念,国家本体不安全是指国家由于不知道具体威胁来源而表现出的“深深的无力感状态”(a deep incapacitating state of not knowing),或是国家不知道如何在世界中“自处”的焦虑状态。在本体安全理论看来,与其说焦虑是类似于恐惧的一种情绪/情感,不如说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表述为,焦虑是会引发一系列情绪/情感和行为的“对恐惧的恐惧”。④Catarina Kinnvall and Jennifer Mitzen, “Anxiety, Fear,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Thinking with and beyond Gidden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12, No.2, 2020, p.241.“不确定性”和“焦虑”是连接国家身份和本体安全的关键机制。因此,国家本体不安全状态可以源自对于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他者”的不承认,也可以是国家身份叙事的突然断裂和自我否定。
具体而言,本体不安全感主要有三个来源。其一,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主义哲学为焦虑和本体不安全提供了哲学基础。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焦虑源自主体“对确定死亡的未知体验”,是对存在在场(presence)稳定性缺乏的担忧,①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09-311页。即死亡对人类存在有限性的束缚。②其逻辑是:除非到死亡的那一天,自我的存在才最终完整。因此,人类的不完备性(incompleteness)使得自我安全感的建构始终处于一个生成(becoming)和呈现(unfolding)的过程,而非静态的完整整体;同时,死亡的发生是任意且随机的,这就让我们的存在带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偶然性。其二,现代风险社会和全球化带来的“自我”困境。吉登斯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个体介于“全球性”和“地方性”之间,受到“统一性与碎片化”“无力感与获得感”“权威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四对张力关系的拉扯,构成现代社会独特的“自我”困境。③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100-111.同时,在“无意义感造就威胁机制”的作用下,“自我”会生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消失的畏惧(dread)或焦虑情绪/情感,进而产生本体不安全感。其三,复杂系统效应、人类能动性与错误知觉造成的非预期后果,即复杂系统把理性行动引向意外且有违意愿的结局。④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61-67.例如,珍妮弗·米岑和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国际能动性赋予国家国际行动的自由裁量权,却也由此受困于“错位的确定性”(misplaced certainty)影响,从而在结构性的“不确定性”和国家“错位的确定性”共同作用下,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带来高度的“不可知性”乃至引发战争。⑤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L.Schweller, “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 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20, No.1, 2011, p.25.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或“原子式物质安全观”同样强调“不确定性”的机制作用。然而,这种对“不确定性”的指涉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因“生存危机”而对他者意图或信息的不确定,诱发的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生存安全的“恐惧”。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现实主义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即无政府状态下,其他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会被理性国家自动转化为最差情形,进而根据最坏情形采用“确定”方式(自助式权力积累)获取安全。①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董杰旻、朱鸣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60页。因此在原子式的物质安全理论框架下,理性国家不仅能够明确地感知到恐惧对象是其他拥有军事资源的国家,也知道化解恐惧情绪/情感的手段是权力最大化。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本体不安全是指当国家所处的物质—社会环境出现重大变迁,或关键情境引发国际秩序“失范”时,国家对自身身份认同或与“他者”关系出现的“不确信感”。“不确信感”是触发国家“焦虑感”或“羞耻感”等负面情绪/情感的前提,是导致国家陷入“本体不安全”状态的关键机制。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的国家认为其他国家具有破坏“自我—他者”信任关系的主观意图,导致“主体间性”安全观念结构和整体安全环境的恶化。更重要的是,相较于恐惧的对象是确定且具体的,焦虑的对象是抽象且游离的,这就意味着影响国家本体安全的主要因素是非实体性的,其修复过程也更为困难和复杂。②Paul Tillich, The Courage to B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7-38.
(三)国家本体安全获得的两个维度
国家本体安全理论强调稳定而连续的国家身份叙事和“自我—他者”信任关系对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生态的重要影响。国家本体安全的获得取决于两个维度:其一,国家自传式叙事(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的连贯性,即国家叙述“自我存在”的故事体系;其二,自我—他者信任关系的建构,即国家通过社会互动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形成彼此承认的良性关系,表现为基本的信任关系和稳定的“主体间性”安全观念结构。③王缅、范红:《国家身份建构:文化外交的基本理论命题》,《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9期,第274-275页;Pan Guangyi and Alexander Korolev, “The Struggle for Certainty: Ontological Security,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and Australia-China Tensions after COVID-19,”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6, No.1, 2021, p.120。
1.国家的自传式叙事
国家的自传式叙事是指在时间和空间中具有主体性、自组织性的知识和观念体系。自传式叙事源自日常的话语、对话和修辞,用于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断裂和歧义整合为连贯的故事整体,从而呈现我们对世界的独特体验,并赋予行为体行动特定的社会意义。①Felix Berenskoetter, “Parameters of a National Biograp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0, No.1, 2014, p.269.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的自传式叙事主要源于国家精英(领导人、官员和知识分子)对于本国身份与国际社会角色的认知和定位,表现为国家制定政策的原则、基本路线和世界观等观念结构。②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Kim,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4; 贺刚:《自传体叙述与身份进化的动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1期,第124页。这种故事体系赋予国家自我存在的独特性,确定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身份和地位,并因这种内外连贯的国家身份获得强大的国际行动能力。③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Charles Taylor and Amy Gutmann, eds.,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1; Molly Patterson and Kristen Renwick Monroe, “Narrative in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 No.1, 1998, pp.319-320; 景晓强:《身份、情感与对外政策——以本体安全研究为中心的讨论》,《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57-58页。
国家的自传式叙事是国家在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塑造国家身份、凝聚共识和政治动员的重要方式。国家自传式叙事的核心要素是精英和大众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共有认知,这需要将精英的观念结构“转译”成为与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相关的常识,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可。④Bentley B.Allan, Srdjan Vucetic and Ted Hopf, “The Distribution of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s Hegemonic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2, No.4, 2018, p.846.因而,国家自传式叙事的形成过程是国家文化观念、历史记忆和思想情感的选择、建构和再塑造过程,⑤Roberto Franzosi, “Narrative Analysis—Or Why (and How) Sociologists Should Be Interested in Narra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4, No.1, 1998, p.546; Robyn Fivush, “Speaking Silenc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ilence in Autobiographical and Cultural Narratives,” Memory, Vol.18, No.2, 2010, p.92.尤其是国家通过情感性的政治动员,形成特定的集体价值观、群体归属感和内部团结。政治精英经常会把历史集体记忆作为当前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来源,因为精英和民众共享的经历和记忆,可以为个人、团体和国家提供一种独特的情感性权力。⑥Richard Ned Lebow, “The Memory of Politics in Postwar Europe,” in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and Claudio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例如,有研究发现美国政治精英策略性地“唤醒”了民众对于二战前欧洲国家未能及时遏制希特勒扩张阴谋的历史记忆,引发美国民众强烈的不安全感,从而为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赢得了民众支持。①Henry L.Roediger III and James V.Wertsch, “Creating a New Discipline of Memory Studies,”Memory Studies, Vol.1, No.1, 2008, p.14.需要指出的是,创伤性或耻辱性历史记忆对于国家安全具有尤为重要的影响,因为创伤性或耻辱性记忆是保持国家自传式叙事连续性的关键情感,耻辱性叙事的“断裂”会从根本上破坏国家塑造的集体身份,给国家带来严重的本体不安全感。②Alexandria J.Innes and Brent J.Steele, “Memory, Trauma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Erica Resende and Dovile Budryte, eds., Memory and Trau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Cases and Deb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20; 汪舒明:《历史问题“安全化”及其对21世纪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3期,第45-46页。例如有研究发现,美、英、德三国坚持在科索沃危机中采取干涉主义立场,部分原因就是阿尔巴尼亚人的处境引起了他们历史记忆中隐喻性的“羞耻感”,为了缓解这种“羞耻感”导致的本体不安全,美英德三国为重建国家身份而选择集体安全行动。③Brent J.Steele,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115.还有研究发现,美国在反恐战争中之所以会多次出现“虐囚”现象,就是为了向外展示美国的政治军事力量,重塑美国因九一一事件遭到破坏的霸权身份和强力的国家形象。④Brent J.Steele, “‘Ideals that Were Really Never in Our Possession’: Torture, Honor and US Ident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2, No.2, 2008, p.253.
2.自我—他者信任关系机制
在本体安全理论中,国家的关系性存在内嵌在“自我—他者”信任关系的结构之中,连贯且稳定的基本信任关系是国家维持“自我存在”意识的基础。⑤Iver B.Neumann, “Self and Oth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 No.2, 1996, p.166;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43; Bahar Rumelili,“Identity and Desecuritisation: The Pitfalls of Conflating Ontological and Physical Secur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18, No.1, 2015, p.54.因而,在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为了维持连贯而稳定的国家身份,克服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带来的焦虑感,国家需要通过一定的惯例、仪式和习惯,确保自我—他者信任关系具有可预测性、稳定性与连贯性。⑥Carmina Yu Untalan, “Decentering the Self, Seeing Like the Other: Toward a Postcolonial Approach to Ontologic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14, No.1, 2020, p.42.
自我—他者信任关系的协调主要通过四个机制实现。其一,遵守和维护基本的国际规则,或英国学派所谓的“首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这些基本国际规则包括政治主权、领土权、均势、国际法、大国协调和民族主义等现代国际关系持久的国际实践。这些国际实践不仅界定了国家间关系的合法行为,更塑造了国际社会成员的集体身份资格。①Ba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ocietal Approac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17; Filip Ejdus, “Critical Situation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nd Ontological In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21, No.4, 2018, p.888.其二,积极参与现行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实践,在涉及当下和未来国际秩序的协商过程中,推动主要国家遵循以集体义务为导向的行为准则,抑制狭隘的激情和短期利益追求,②James G.March and Johan P.Olsen,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96; Felix Berenskoetter and Bastian Giegerich, “From NATO to ESDP: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nalysis of German Strategic Adjustmen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19, No.3, 2010, p.410.减少世界事务中的冒险行为、风险性和不可知性。③Robert O.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O.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80.其三,共同推动和塑造一种基于情感的,对“共同世界”的集体认知和相似经历。国家可以通过共同且重叠的道德空间,例如互惠、信任、开放、诚实、接纳和忠诚,自愿建立一种重视协商(deliberation)、非支配(nondomination)和互信合作的友谊关系。通过这种友谊关系塑造亲密感、互惠感和互助感以对抗存在性焦虑的威胁,为多方共同愿景奠定规范性基础。④Felix Berenskoetter, “Friends, There Are No Friends? An Intimate Refram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lennium, Vol.35, No.3, 2007, p.670; Heather Devere and Graham M.Smith,“Friendship and Politics,”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8, No.3, 2010, pp.347-349; Felix Berenskoetter,“Friendship, Security, and Power,” in Simon Koschut and Andrea Oelsner, eds., Friendship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57.其四,把焦虑感转化为明确的恐惧对象是国家维护本体安全的一种常用策略,为确保国家身份的独特性,国家有时需要塑造一个具有差异性的负面他者形象(参见图1)。⑤William E.Connolly,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p.64-65; 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 No.3, 2006, p.354.

图1 本体安全与国家能动性
在国际关系中,由于国家往往会同时拥有多重身份,这种多重身份源自内外两个层面,因此,同时具有多重身份也会从内外两条路径对国家和国际体系带来安全冲击风险。
首先,从自我—他者关系角度看,国家多重身份以及彼此间不同身份类型的互动方式,会产生多样的“主体间性”安全认知结构。多样的安全认知结构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塑造出冲突性的新制度,从而破坏国际秩序的制度基础和国家间的基本信任关系。其次,从国家内部看,国家的自传式叙事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取决于精英内部、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和协商关系,本国多重身份的历史记忆和叙事方式加大了产生分歧的风险和国家身份的不连续性。因而,国家常会在国际环境和国际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感受到内部叙事调整、多重身份和“主体间性”安全认知结构变迁导致的本体不安全状态。最后,国家本体不安全状态可能会带来国家身份连贯性断裂的结果,①Amir Lupovici, “Ontological Dissonance, Clashing Identities, and Israel’s Unilateral Steps towards the Palestinia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8, No.2, 2012, p.815.也可能引发整个国际社会或国际秩序基本信任瓦解的严重后果。如果在内外变化的冲击下,国家的本体不安全感显著增强,自传式叙事和自我—他者信任关系的连续与稳定也会遭到破坏,两者是一种相互建构、互相强化的关系。其主要表现是,在国家内部,无论是精英自身还是精英与民众之间会就国家的身份界定产生分歧;在对外交往维度,国家也会认为自身的身份认知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和主要国家的充分承认和尊重。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的焦虑感会大幅上升,基于身份地位的安全螺旋困境开始逐步显现。为此,国家不惜以牺牲物质利益为代价,试图通过改变现状而获取本体安全的行动便成为国家的可能选择。②Patricia Greve, “Ontological Security,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21, 2018, pp.870-874; Siavash Chavoshi and Mohammad reza Saeidabadi,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Case of China as a Rising Pow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views, Vol.9, No.2, 2021,p.392.
综上所述,本体安全理论在预设了秩序感存在的前提下,遵循着“承认政治”的基本逻辑,通过结合国家身份形成的内外两条路径,有效地把国家身份、群体情绪/情感、国家安全三者衔接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革期的国家安全新风险,也为以全球性大国身份开始尝试深度融入国际社会的新时代中国外交,提供了理解多元的国家安全威胁来源的一个初步分析框架。
三 国家自传式叙事:现代中国国家身份的“断裂”与“赓续”
如何在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和大国关系变化的当下,准确定位国家、国际安全风险和威胁,是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中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①习近平:《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载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38-539页。从历史长时段和国际角色相结合的视角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何为中国”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沿着这个核心议题,塑造新国家身份、以平等身份融入国际体系构成中国对外关系、国家安全诉求的基本主题,并且蕴含着中华民族集体情绪/情感以及理想和抱负的巨大转变。从国家本体安全寻求的角度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身份经历了由断裂到赓续的曲折过程,而且国家身份和叙事体系的塑造是“群体内—群体间”内外互动的结果,即国家身份是“自我塑造”以及在与“他者”对比的过程中同时完成的。本部分主要讨论中国国家身份“群体内”的形成过程,即国家自传式叙事的自我塑造过程。
(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传统国家身份的“断裂”
国家的自传式叙事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对于本国集体身份、核心特征与规范要求的自我理解。当然,国家的自传式叙事是多层次衍生故事交织而成的混合型存在,国家需要在不损害其叙事连贯性的情况下进行战略性运用。因而,保持国家自传式叙事或叙事网络的连贯性构成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自传式叙事的形成过程主要取决于国家的结构—制度设置和精英—大众的共有认知。一般而言,国家自传式叙事是相对稳定的,短时间“断裂”的风险主要来自外部压力。当外部环境施加的压力造成精英与民众对于国家基本制度和集体身份的认知出现巨大分歧时,国家叙事就可能在外部威胁下短时间内出现巨大波动乃至断裂。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外部压力对中华帝国“天朝上国”的传统叙事方式造成颠覆。①任剑涛:《中国的国际身份辨认》,《学海》2016年第1期,第146页;Hoo Tiang Boon,China’s Global Identity: Consider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reat Power,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5。晚清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下观念的崩解转向“列国”并列的新世界,传统文明型国家让位于全新的“民族国家”体制。中日甲午战争更是中国传统社会“失范”的关键情境,这场战争的失败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天朝上国”被“蕞尔岛夷”击败的残酷事实,让中国精英从中国国际地位下降的担心扩散至对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制度乃至文明的质疑和焦虑。“保国保种、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全社会的基本共识,新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也意味着中国传统国家叙事的彻底“断裂”。
自此之后,塑造新的国家身份,以平等成员身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族情感、抱负和信念。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诉求的两大核心主题就是新国家身份塑造和“国际化”。然而,近代中国的新国家身份塑造和“国际化”都严重依赖外部力量的支持和介入,国内的政治观念、制度选择和身份叙事呈现出“多国化”干预的特征,即中国是外部力量竞争的权力场和国际秩序变化的投影。②杨雪东:《内外互动、主体选择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4期,第4-5页。外部世界权力变动和分化还加剧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价值分化、政治对抗和对外关系阵营选择,导致中国社会精英难以就新国家身份及其连贯的叙事内容达成基本共识,更遑论精英和民众之间难以弥补的认知鸿沟。③Michael H.Hunt,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trong State: The Late Qing-Republican Crisis,”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67-68.中国社会共识的分歧与对立,不仅带来四分五裂的严重后果,也使得中国和外部世界处于两难困境,即外部介入式的“国际化”加剧了中国内部共识的分化与对立,而内部共识的分化与对立,无法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确立稳定的“主体间”信任关系。因此,在内外互动关系中,如何保持国家自主性,培育国家主体性意识和发挥国际能动性,就成为塑造中国国家身份和“国际化”的关键。
(二)新中国国家身份“赓续”的变迁逻辑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间,中国的国家身份主要经历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最大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的三次重大转换。①郭树勇:《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全球观念变迁的主要规律》,《国际观察》2021年第1期,第11页。这三次国家身份转换,不仅是中国领导人结合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对“国家自主性”“国家主体性”和“国际能动性”的阶段性侧重,更是在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演变过程中,②章百家:《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克服不同阶段面临的国家身份困境,实现传统“文明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确立具有中国特色全球性大国国家身份叙事体系的复杂过程。③Yan Xuetong,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7, No.2, 2014, pp.166-170; 薛晓芃:《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建构及发展历程》,《理论视野》2018年第12期,第71-72页。这个国家身份叙事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
1.“国家自主性”: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二元国家身份结构
国家自主性的国家身份建构象征着近代中国在文化观念、民族情感和物质基础三个维度的彻底改变。这首先体现在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从“欧风美雨”中的觉醒,“一边倒”的原则是凝聚社会共识和实现国家自主性的开端。毛泽东同志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相应地,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百年来中华民族集体创伤记忆的充分释放,⑤K.M.Fierke, “Whereof We Can Speak, Thereof We Must not Be Silent: Trauma, Political Solipsism an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4, 2004, p.476.而“两弹一星”等重大国防工程的顺利完成,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国家形象,奠定了“国家自主性”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国家,克服了晚清以来受外部势力干预带来的群体内认知分歧,确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的国家体系与国家间关系基本模式,推动国家利益导向的民族主义成为新中国国家身份叙事的核心部分。⑥Cao Qing,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Chin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Chris Shei,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Discourse Analysis,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432.同时,为了克服群体内身份叙事的张力,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系统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机制,可以经过各级党委、政府机构、传媒、教育界,把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集体记忆和屈辱感、①Zheng Wang,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2, No.4, 2008, pp.800-801; Anne-Marie Brady and Wang Juntao, “China’s Strengthened New Order and the Role of Propagand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8, No.62, 2009, pp.782-785; Karl Gustafsoon,“Memory Politics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38,No.1, 2014, p.76.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斗史和民族自豪感,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国家命运与个体命运的有机联系,实现了宏大国家叙事“内化”、凝聚共识的历史使命,②Alanna Krolikowski, “Shaking up and Making up China: How the Party-State Compromises and Creates Ontological Security for its Subjec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Vol.21, No.4, 2018, p.925.也由此确立了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人民利益紧密相关的现代国家安全观。
除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国家外,基于国际主义的国家身份同样在新中国的自传式叙事中迅速传播和扩散开来,形成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二元国家身份结构,也实现了民族性、革命性和情感性的内在统一。在正式的官方政策和各种重大场合表述中,存在大量通俗易懂的本土性政治话语,如“推翻三座大山”“人民万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等。同时,在政治沟通和群众动员过程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情感式表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对于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重要意义。这些本土性政治话语和情感式表达,构成“新中国”和“旧中国”强烈的反差,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产生的突破性意义和非凡历史成就。
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二元国家身份结构赋予了新中国国家自主性,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国家身份中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彼此强化,更赋予新中国强大的国际能动性。例如,毛泽东“三个世界”和“中间地带”理论,不仅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以夷制夷”的传统认知,还进一步推动“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③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而且,敢于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斗争,是中国成为国际政治中一支独立力量的关键,也是中国较早从冷战中脱身的重要原因。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二元国家身份结构出现失衡现象。中国的革命理想主义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高涨引发了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恐惧心理,是所谓“中国威胁论”之类“刻板成见”的根源之一。①杨明星、赵玉倩:《中国共产党外交叙事的百年演进与历史经验》,《国际观察》2021年第6期,第11页。中国的二元国家身份结构和叙事体系需要更具一致性和连贯性的调整。
2.“国家主体性”:“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面对“苏联模式”“革命外交”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国家身份张力,改革开放的实行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身份的系统性反思和结构性超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确保了社会主义底色不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更意味着中国“国家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原则指导下,中国“革命国家”的色彩逐渐淡化,政治性更强的“第三世界国家”逐渐让位于经济性的“发展中国家”。在“东西南北关系”、推动“南北对话”、发展“南南合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新的叙事中,中国自我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随着“国家主体性”意识和新国家身份的确立,中国领导人的战争观念、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观随之出现转型,以政治军事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开始转向经济安全。②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2-15页。这一系列的观念性变化,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解和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邓小平在多个场合明确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基本动因,也给中国人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未来愿景。
在国家安全观方面,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了“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邓小平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改变了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明确了军事安全不再是中国国家安全的迫切问题;第二个转变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转向了创造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邓小平说:“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为保证社会主义性质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表述。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家主体性”意识觉醒的情况下,逐渐形成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经济安全为基础,其他安全统筹发展的新国家安全观。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上下洋溢着向先进发达国家学习的积极乐观主义情绪,同时也隐藏着对于自身国际身份和地位的焦虑:一方面,改革开放让中国人认识到自身跟国际社会的差距,亟待奋起直追的“补课”和“追赶”;另一方面,当中国与世界差距缩小时,由于历史上中国始终与“大国身份”密不可分,自然需要重新思考厘清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责任与国际贡献。②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任剑涛:《中国的国际身份辨认》,《学海》2016年第1期,第145页;Hoo Tiang Boon, China’s Global Identity: Consider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reat Power, Washington: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33-36。
3.“国际能动性”:“负责任大国”与新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体系
方向图代表了一个指纹图像的固有属性,同时也定义出了局部邻域中脊、谷的固定坐标。通过原始指纹图像的方向纹理,我们对指纹图像方向场的估计采用以下算法[14]: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国内出现了有关中国国际身份未来定位的讨论,苏东剧变与冷战结束加剧了中国在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避免“扛旗当头”的两难境遇。针对国际格局变化和国家身份调整的现实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在选择性介入国际事务过程中,逐渐从“国际社会平等一员”转向“负责任大国”的新国家身份塑造,促使中国“国际能动性”能力的增强。
中国的“负责任大国”身份叙事是由内及外或是由单元层次向体系层次递进扩散的过程。对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负责任大国”意味着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和政权安全的统一,是对国内负责和对国际负责统一的前提。邓小平指出:“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地区集体身份也开始觉醒,周边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上升。经济上,中国积极地与东亚各国开展经济合作,推动建立自由贸易区;安全上,中国在“搁置争议”的自我约束基础上,积极开展与东亚国家双边、多边的安全对话合作,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和“负责任的地区大国”身份;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积极主动的建设性作用,促成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的妥善解决。①陈翔:《负责任大国:中国的新身份定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6期,第40-42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更是本着负责任大国的身份立场,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措施,赢得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巩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及其叙事的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综合国力得到快速提升,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和姿态更为明确。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飞速发展,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的国际格局转型,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意识显著增强。②Zhao Suisheng,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Strident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2, No.82, 2013, pp.543-546.与此同时,国际上有关“中国威胁论”的炒作甚嚣尘上,这既表现出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担忧和焦虑,也为中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自我界定带来挑战。为更好地凝聚共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叙事方式主要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展开,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核心概念,通过创造性的叙事策略,尝试推动国际体系向更公平合理方向发展。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叙事方式主要强调中国在全球治理规则和国际规范制定中相匹配的国际地位;指出自由国际秩序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内在缺陷;提出全球化带来的系统性变化以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正当的利益诉求。③Yi Edward Yang, “China’s Strategic Narratives i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under Xi Jinping,”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30, No.128, 2021.
国际体系层次上的身份叙事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国际政治本质、大国和大国间关系的再定义与再诠释。因而在国家层次上,中国重申了永不称霸和永不扩张的和平外交宗旨,以国际责任而非权力为基础重新定义“何为大国”的新尝试,表现了中国对于自身负责任大国身份及其特质性的强调,这也是中国对国际政治本质的规范性理解。对此,习近平主席指出:“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④《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20年9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9/22/c_1126527652.htm。这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领导人对国际体系和权力关系的重新理解,也清晰地提出了中国对于国际地位、国际权利与义务的正当诉求。
四 中国“自我—他者”信任关系调适与国际安全结构重塑
长期以来,信任问题都是国际安全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却常被忽视的议题,这与“无政府状态”概念对该领域的支配性影响密不可分: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国内社会民众对中央政府等级制、垂直型信任关系被转化为国际社会中水平型的“自我—他者”关系结构,这导致各国经常面临“囚徒困境”的困扰,容易激化国内社会团体对外国的敌对情绪,加剧各国彼此间的不信任感,使国家陷入敌意的安全螺旋,阻碍国家间信任关系的形成。①Jan Ruzicka and Vincent Charles Keating: “Going Global: Trust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Trust Research, Vol.5, No.1, 2015, pp.10-11.根据安德鲁·基德(Andrew Kydd)的界定,国际关系中理性主义范式的信任构建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其一,一国估计他国是以现状为导向而非修正主义的可能性;其二,一国相信他国是值得信赖的,愿意开展互惠合作;其三,一国相信自己的利益不会与他国产生过于剧烈的冲突。②Andrew Kydd, “Trust Building, Trust Breaking: The Dilemma of NATO Enlarge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4, 2001, p.810;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6-12.然而,与信任研究理性主义范式不同的是,本体安全理论采用的是更接近互动论的社会建构主义路径,即“自我—他者”信任关系的建立是国家与“广义他者”(包括其他行为体和物质社会环境与规则)相互承认和确立“社会性存在”的过程,是在社会化、内在化和制度化等机制作用下,通过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和角色身份(institutional identity)的形成,在“自我”和“他者”之间构建超越单纯利益关系之外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联结的复杂过程。③Aaron M.Hoffman, “A Conceptualization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8, No.3, 2002, pp.376-377.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集体身份形成的策略性机制是吉登斯所谓的辨识(identification)与投射(projection),④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米岑称之为识别(recognition)和依附(attachment)。⑤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2, No.3, 2006, pp.347-348.从本质上讲,两种策略性机制都旨在“自我”和“他者”的叙事体系及其象征性符号之间建立社会性联系,是“自我”成为“社会性存在”和集体身份形成的过程。在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中,温特从体系结构层次出发,依据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三种无政府文化的演进逻辑,细分了“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三种“他者”镜像,也是本分析框架的参考对象。相比建构主义,本文的分析框架增加了“角色身份”的分析维度,即“自我”对于外部物质—社会环境和规则的接受程度,在国际关系中主要是指国家通过加入国际组织,学习、融入与内化国际规范。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把加入国际组织限定为国家仅仅对基本的国际规则或英国学派所谓的“首要制度”,如主权、领土权、大国协调和民族主义等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接受与承认;学习、融入和内化国际规范是指国家进一步对主导性国际规范的全面学习、深度内化乃至主动创造新规则和规范的过程。据此,根据国家对于集体身份和角色身份的不同侧重,“自我”与“他者”会形成六种类型的信任关系模式,也是复杂多样的“主体间性”安全认知结构形成的基础(参见表1)。

表1 “自我—他者”的信任关系类型
本文将按照这六种类型的“自我—他者”信任关系模式,系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广义他者”的互动特征与转型过程,并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型期,中国与“广义他者”的信任关系调适进行讨论。
(一)介于“敌对式不信任”和“革命友谊式信任”之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由于美国把对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所谓“威胁”臆造为单一的“好斗的共产主义”,简单地把两极对立的欧洲冷战模式照搬到东亚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包围威胁和外交上孤立的政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互不承认的敌意和对抗,构建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对抗型”和“(准)战争型”的敌对关系模式,也给新政权带来国家本体安全和物质安全的双重威胁,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最大程度呈现。为缓解新政权面临的安全挑战,1950年2月,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国际斗争中“一边倒”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建立了以意识形态身份为基础的“排他型信任关系”,更同苏联确定了特殊的革命友谊关系。然而,由于中国秉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保持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排他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未完全接纳苏联阵营的国际规则与规范,为中苏关系之后的破裂埋下伏笔。
抗美援朝战争后,西方国家以联合国的名义在政治和外交上继续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并且在经济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二十多年的全方位制裁与封锁。①沈志华:《试论1951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第121-122页;Zhang Xiaoming, “China in the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English School’s Engagements with Chin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7, No.2, 2011, p.773。对此,中国认为联合国是美帝国主义实施强权政治的工具,有必要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同联合国“唱对台戏”。②《可以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世界知识》1965年第3期,第2页。这种状态下,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敌对型不信任关系持续强化,双方都没有意图和必要行动改变共有认知,也无法通过彼此认可的惯例进行接触与互动,③Anisa Heritage and Pak K.Lee, Order, Contestation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Seek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85.以至对彼此的存在都无法接受。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看到(美)帝国主义就不舒服。要帝国主义干什么?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也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75页。
20世纪50年末,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同苏联阵营“革命友谊式”的信任关系趋于瓦解,中国不得不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中苏关系破裂对于中国的国际身份和“世界革命”前景造成了剧烈冲击。出于阶级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中国不同意苏联提出的美苏和平共存主张,因为该主张意味着中国无法履行发动世界革命的承诺。①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78.事实上,随着苏联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中苏两国之间“选边站”,中国逐渐被社会主义阵营孤立,中国的社会存在性身份焦虑不断激化,无论是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无法安抚中国的国际集体身份困境所带来的紧张情绪/情感。②Zhang Yongji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Alienation and Beyond,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8, p.48.在无法与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正面互动的状态下,中国的本体不安全感在这个时期尤为突出。为解决这种存在性焦虑,中国先是将美国和西方国家明确地视作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头号敌人和首要威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我们的朋友与伙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苏联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明确的敌人形象(其造成的威胁程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甚至大于美国),寻求与不发达的亚非拉国家联合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第三世界”,强调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持续不断斗争,就成为中国新的国际身份认知归属。③Wu Baiyi, “The Chinese Security Concept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0, No .27, 2001, p.276; 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2,No.3, 2006, p.361.
(二)“互惠型”与“和合型”信任关系的形成:改革开放至中共十八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后,中国改变了过去二十多年间对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敌对革命态度,转而采取接受现状的温和立场。同时,中国尝试融入现有国际制度,选择性地接受维护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规则与规范。④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3, No.1, 2010, p.13.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把自身视为国际社会正常的一员,尝试与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建立基于国家利益的“互惠型信任关系”。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既是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从此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⑤张磊:《中国重返联合国五十年:发展历程与演进逻辑》,《国际观察》2021年第5期,第29页。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缓和以及随后两国正式建交,推动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在西方主导的主流国际社会中增强了中国作为正常成员的合法性资格。①Zhang Xiaoming, “China in the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English School’s Engagements with Chin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7, No.2, 2011, p.775.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方面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特别是开始尝试通过国际组织“为中国争取话语权和行为规则的解释权、制定权”,②李晓燕:《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历史发展与自主创新》,《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2期,第63页。并就全球性或地区性问题提出新的方案,塑造新的国际规范。③孙德刚、韦进深:《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规范塑造评析》,《国际展望》2016年第4期,第98页。对于本体安全理论来说,各种国际规则、机制和制度的作用不仅仅是管理或是限制主权国家的行为,也让国际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趋于可控、和谐与稳定,有助于增强国家的本体安全感。④Qin Yaq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 Institutions, Identities,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3, No.2, 2010, p.138.以国际裁军和军控机制为例,中国在逐步模仿和学习过程中,与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建立起惯例化的互动过程。一方面,中国外交官提交的工作文件和立场声明得到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国内的研究机构对于国际裁军的关注和分析也越来越多。⑤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4.此外,中国改变了以往谴责美苏两国破坏世界和平的话语模式,不再将类似的多边机制作为批评超级大国的舞台,而是着眼于涉及裁军和军控的实质议题,更为关注中国在该领域的贡献与收益。⑥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67-6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建立“和合型信任关系”的基础。⑦关于“和合”或“和合型信任关系”,可参阅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服从并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强有力的保障。⑧汪卫华:《中国的国际观变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评论》2021年第5期,第14页。中国积极推进招商引资和海外投资,鼓励中国企业大力发展跨国业务,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水平显著提升。在积极推动与世界主要的多边经济制度及其组织的合作过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也变得持续而稳定。随着中国在1980年全面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地位,中国逐渐采取世界通行的标准来评估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时向世界通报相关统计数据,促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变得更加直观和透明。①Zhang Yongji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Alienation and Beyond,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8, p.228.在这一时期,最为典型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既证明了中国愿意遵守主流国际规范和标准的坚定决心,强化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和合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也体现了美国及其他主要贸易国家对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认可,标志着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全面接受了中国的加入和深度参与。②Deng Yong, “The Power and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Status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omas J.Volgy et al, eds., Major Powers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lob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84.
相较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紧张对立,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形成了制度化、常态化、稳定化的“和合型信任关系”。无论是基本的国际规范和国际规则,还是各种重要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既得到了中国的充分支持与认可,也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尊重和接纳。在此情形下,就敌人形象的塑造来看,过去与美苏超级大国的直接针锋相对也被更加模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取代。正是因为中国与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对中国本体安全构成的威胁不再来自某个具体的国家,而是那些可能破坏整个国际安全环境稳定的不利因素。
(三)“排他型信任”与“竞合型信任”的调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信任关系重塑
中共十八大以来,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转型期,欧美国家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正经历权力分配、价值原则和多边机制的深层次本体安全危机。③Trine Flockhart, “Is This the End? Resilience,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Crisis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41, No.2, 2020, pp.226-230.国际社会未来前景的不可知性显著上升,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给人类的惯例式生活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焦虑感和各式议题的安全化在世界各国弥漫。④Bahar Rumelili, “[Our] Age of Anxiety: Existentialism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24, No.4, 2021, pp.1021-1022;Pan Guangyi and Alexander Korolev, “The Struggle for Certainty: Ontological Security,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and Australia-China Tensions after COVID-19,”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6, No.1, 2021, p.127.戴维·莱克(David A.Lake)等人认为,西方大国正是为了减轻这种存在性焦虑,错误地把中国视为现有国际秩序稳定的直接“威胁”。①David A.Lake, Lisa L.Martin and Thomas Risse, “Challenges to the Liberal Order: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5, No.2, 2021, pp.241-243.恰在此时,中国外交“有所作为”和寻求世界大国国际地位的正当诉求,进一步激化了西方大国的本体不安全感。在本体不安全感的影响下,美国、欧盟等关键“他者”很难给予中国正当的国际地位承认,中国也因此会经历国际身份错位的不受尊重感。②Michelle Murray,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us, Revisionism,and Rising Pow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71.当然,错误认知也存在各种微观的心理机制,诸如罗伯特·杰维斯提到的统一性知觉、过高估计自己作为影响者和影响对象的重要性愿望思维以及认知失调,对于错误认知的形成也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可参见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410-500。
更为重要的是,欧美大国对华形成竞争共识,明确地把中国塑造成为“竞争性对手”。美国为维持霸权国地位和加强对国际社会的掌控,更是不断强化价值观外交和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致力建构一种对华的“对抗型不信任关系”。相较之下,中国一方面强调要跟美国构建良性“竞合型信任关系”,③“竞合”或“竞合型信任关系”,可参阅储昭根:《竞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探索》,《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8期。避免中美滑向“对抗型敌对关系”;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权威的多边主义体系,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革新的新理念和新举措,尝试同国际社会建设一种新型的“和合型信任关系”。就此而言,建立良性的“竞合型信任关系”是决定中国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结构和安全生态的关键。
中国和欧美大国“竞合型信任关系”塑造的关键在于实现了双方“互惠信任”和“公平信任”的平衡,而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合型信任”则取决于“同质信任”和“声誉信任”的有机融合。④尹继武:《国际信任的起源:一项类型学的比较分析》,《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3期,第102-104页。首先,中国与西方大国的竞合型信任关系建立在风险管理与利益回报预期基础上,利益互惠过程中相对公平的感知可以巩固双方对利益互惠的心理认知。⑤黄海涛:《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与信任决策——基于中美战略互动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2期,第141-144页。国家间信任,尤其是大国间信任的起源与形成是一种过程性的互惠实践活动,是“对等回报”和“公平感觉”的有机结合。“对等回报”是一个由点及面逐步找到互惠积极预期的过程,而适度的自我约束和利他行为有利于建立“相对公平感觉”,推动互惠预期和信任关系的形成。
据此而言,中国同欧美大国塑造良性“竞合型信任关系”的共同点在于控制和管理大国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但在当前情况下,中美之间应优先侧重于设定双方的战略稳定目标,避免双方滑向“对抗型敌对关系”,在竞争性共存的基础上形成“对等回报”的互惠预期。中欧之间则重点在于强化彼此对等的互惠规则,在强化多边主义共识基础上从利益回报预期和现实收获感之间形成新平衡,以巩固双方的“竞合型信任关系”。
其次,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合型信任关系”取决于“同质信任”和“声誉信任”的有机融合,取决于中国对外释放的外交善意,对国际责任的充分承担,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合理维护,对信息披露的公开及时和信守承诺的良好实践。①陈遥:《信任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0期,第114-117页。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代中国与国际社会建立信任关系的规范性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同一性与独特性兼顾的“同质信任”规范取向,是在充分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权利基础上,扩大各国利益交汇点,推动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强调应对全人类各种挑战的同质性价值基础。②李孝天:《国家集体认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第137页。
同时,中国与现有多边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互动则旨在加强中国的“声誉信任”。一方面,中国始终维护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权威地位,积极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和使命,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核心作用;③王明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制度基础》,《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5期,第81页。另一方面,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包容性国际规则。“一带一路”倡议遵循成员资格开放化、议题范围包容化、决策程序透明化、治理结果协商化,它不仅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地区性公共产品,更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尝试与国际社会建立“声誉信任”的重要制度平台。④吴志成、吴宇:《习近平外交思想析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2期,第16页。就此而言,新时期的中国需要把“同质信任”和“声誉信任”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战略资产管理思维进行更精细化的设计和维护。
总之,重塑“自我—他者”基本信任关系是确保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繁荣的重要保障。由于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是稀缺的,而且其成因也极为复杂,通常是理性、情绪/情感和主观感知等多重因素交织构成的复杂组合。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大国的战略互信或“竞合型信任关系”需要双方在“互惠信任”和“公平信任”间取得平衡,而崛起大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信任则取决于“同质信任”和“声誉信任”的融合和认可程度。
结 论
国家身份和集体情绪/情感如何对国家安全及国际安全产生影响,近代以来塑造中国国家身份的互动机制是什么,这是两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研究问题。本文发现,随着整个国际系统演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和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世界,国家对物质生存的诉求基本得到满足。但是,全球化在“群体内—群体间”两个维度给国家的身份建构构成巨大威胁,从而引发国内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对国家本体不安全的一种深层焦虑感。这种焦虑不同于现实主义理论所关注的恐惧,因为一旦有关身份焦虑被激活,国家的集体情绪/情感保护机制就会开始运作,其结果便是各国都有可能以牺牲物质安全为代价换取本体安全水平的提升,从而对本国安全和国际安全格局造成负面影响。这一发现为在当前充满复杂性和不可知性的国际环境中,抓住主要国家安全风险和提出治理策略提供了启示。
通过本体安全理论,本文发现塑造国家身份的机制是有关国家自传式叙事和“自我—他者”信任关系的双向建构过程,为我们从历史变迁、民族情感和国际化相结合的角度,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安全观、对外关系以及国际秩序观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何为中国”一直是近代以来困扰中国保持自传式叙事稳定和连贯的重大核心问题,其背后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对于中国国家身份浓厚的情绪/情感。在晚清“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古代华夷观和“天下思想”为基础的自我身份叙事被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叙事彻底打破,中国不得不经历对国家身份自我认知的严重分歧。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以“国家自主性”方式重建了破碎的国家自传式叙事。改革开放后,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中国逐步实现了从“国家自主性”向“国家主体性”的转变。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尝试通过创造性的叙事策略,立足于“国际能动性”的身份定位,推动国际体系朝向更公平合理方向发展。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信任关系发生了阶段性变化,也进行了周期性调适。改革开放前,中国先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进行了系统性的对立和对抗,随后又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分道扬镳,其结果是中国被完全排斥在各种国际规范、规则、制度和组织之外。为此,只有通过以意识形态划分敌人和朋友的方式,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因无法与国际社会建立良性正常互动而引发的本体不安全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基于阵营身份选择的“排他型信任”和“特殊型信任”是两种占据主导地位的信任结构类型。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全面调整了与国际社会间的互动方式,双方稳定且持续的正面互动交往机制不断建立和巩固。中国的本体安全水平也因为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普遍型关系的出现而显著提升。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都在直面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新挑战,过去数十年间建立起来的“自我—他者”信任机制在不同程度上经历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存在性焦虑。值此重要时间节点,重建中国、大国和国际秩序之间相互承认的新型“竞合型信任”与“和合型信任”,既取决于现有大国和崛起国之间是否能够实现有效的风险管控和互利互惠,理解双方因国际体系新生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身份焦虑和由此产生的身份诉求,同时也要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同质信任”和“声誉信任”之间建立起巧妙的均衡关系。
总之,本文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转型期,因国家身份认同问题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为切入点,引入本体安全理论搭建起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并以近代中国寻求和调试国家本体安全为例,验证了国家本体安全分析框架的有效性。本体安全理论尤其适用于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转型期,由叙事、身份认同和群体情感问题引发的安全风险问题,这不仅能够用于分析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关系变化、地区安全秩序调整和国际秩序转型等传统国际政治问题,同时结合新兴的区域国别研究,可以通过本体安全理论分析框架的精炼和调整,深入讨论族群冲突、恐怖主义、移民问题和气候变化等新兴的安全议题,这也是未来值得期待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