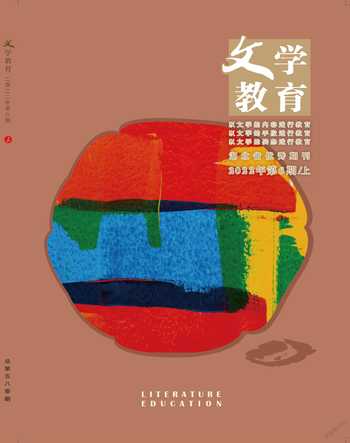写诗带来“隐秘的欢乐”

秦立彦是一位勤奋的诗人,因为她对诗人们所保有的“诗歌的能力”有着清醒的认知。她知晓大多数人作诗靠不了天赋,而主要是靠后天习得得来。近些年来,她对诗歌一直保持着一种孜孜以求的态度,也因此给人留下了“沉深好学,孳孳不倦”的印象。
秦立彦对诗歌有一种敬畏,同时也对诗歌充满信心。一方面,她相信诗不会死,另一方面,她将诗歌作为自己“活着”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她认为,生活中如果没有诗,就仅仅只是“活着”,人生的大部分都是如此。而有了诗则不同,“诗是平淡中的光”,所以异常珍贵。按常理而言,诗歌并不能给写诗的人带来什么“好处”,相反,还可能“有碍正常生活”。秦立彦根据写作的经验指出,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人写诗,“也许因为诗有一种好处,是写诗的人立即得到的。那是一种隐秘的欢乐。”(《隐秘的欢乐》,《诗刊(上半月)》2021年第8期)这种隐秘的欢乐深深地植根于诗人的写作过程之中,起始的时候,你产生一种写作的冲动;中间的过程里,你获得一种自由的气息和自我“掌控”的愉悦感;终了,面对一首崭新的诗歌,面对这“不曾有之物”,你生出一种像上帝“创造世界”的感觉。秦立彦非常深刻地体味到了这一点。当然,出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需要,诗歌也达成生命本身的诉求,秦立彦把它概括为“说出自己,留住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是人类高层次的需要,类似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自我实现”这一归属。不过,要真正达成这种“隐秘的欢乐”并不容易。它需要诗人有对诗歌理想的追求,有自己独觉的发现,有对艺术经验表达的高潮技能。
秦立彦对于诗歌品质的最高追求是“真”。她从中国古诗追求“情真意切”得到启示,认为“‘真’是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基本要求,也是诗有别于小说、戏剧等虚构文类的最大特点。”(《我相信的诗》,《诗刊(下半月)》2017年第11期)这一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无论是抒发情感,还是表达经验,甚至是打开想象,如果失去了内心的诚与真,诗歌将毫无立足之地。诗歌与“虚构文学”不同,它从不借助虚构成为理解世界的方式。尤其是秦立彦把“诗的语言”当作是“天下之公器,不是诗人的自言自语”,这就把诗歌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为此,她重视诗歌的伦理,尤其是对古典诗学中的那些伟岸的存在,那些把诗的境界与人的境界合一了的大诗人,如陶渊明、杜甫、苏轼,她认为他们是世界诗歌中“最独特的存在”,“是最好的诗人,也是最好的人。”因为“他们的诗最终是对世界的肯定,是容纳了矛盾与悲伤的动荡的智慧。”(《隐秘的欢乐》)在秦立彦看来,诗人要看到这个世界“合理”的成分,要将个人的“动荡”与人类的矛盾和悲伤形成共振,让整个世界与自己一同颤抖。当然,这需要诗人通过对诗歌的创造来达成一种共情的力量,这种共情的力量能够使他与人类成为一体,所谓“沉入自己”即“沉入人类”,“关进自己的房间”即“走入了众人共有的广大国土”。秦立彦将之形象地表述为“说出那共通之物”。诗人要有这样对世界的贡献,才能称之为诗人。放眼寰宇,世界上的那些大诗人之所以能成为大诗人,无不是因为如此。退一万步讲,即使你的诗歌只是表达私人情感,提供私人经验,与人交流,“真”也是基础,因为你期望通过文字得到别人的理解与同情。秦立彦把这一点也表达得很形象,她说:“诗是对他人的渴望,是向他人伸出的手,是写给他人的信。”并且指出,“诗人以为独有的许多私人情感与思绪,其实很可能是人所共有。”(《我相信的诗》)为此,如果失去了真,交流也不复存在。
当然,现代诗的最大功用仍是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表达现代经验。但由于“现代”是一个变动不居、常在常新的领域,它的很多“经验”尚未被诗人发现。或者已经被发现,而尚未被表达;或者已经被表达,但没有达成效果。因此,现代诗人的使命,一是发现经验,二是对经验进行有效的达成。这种有效性,一方面与现代诗的形式密切相关,同其他艺术建立的互文性质素(如音乐性、绘画性、对话性等)也不无关系。但首要的任务,还是应该去发现,去创造,去抵达,一如秦立彦从古诗那里发现的可能性:“诗是自我的,同时也是公共的,是服务于人的。诗中所描述的经验未必是完全私密的,诗的效果来自于言人所未言,此言未曾被他人道出。而说出众人的情感,说出众人想说而未说出的公共经验,追求共鸣,抵达尚未有语言抵达之处。”(《“拿来”自己的传统》,《诗刊(上半月)》2019年第3期)秦立彥的创作大都是朝着这些方向努力的。
赵目珍,青年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