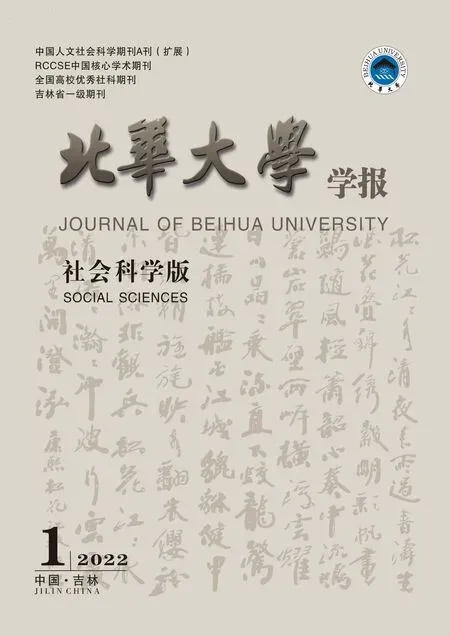晚清公共舆论中女性国民形象的认知与生成
——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马春霞
回溯传统儒学藩篱中女性角色的历史定格,无论是在室女性的从父(夫)传统,还是婚嫁女子的父母之命,女性始终局限于家庭之中,几无社会地位可言,更遑论跻身政治领域。所谓“寝门之内,妇人治其业也”。换言之,在传统社会的性别版图中,女性长期处于“失语”状态。晚清以降,身负发蒙启蔽重任的公共媒体率先聚焦于女智启蒙问题,将其纳入近代化语境之中。《大公报》因其地处津埠前沿和“开风气,牖民智”的办报宗旨,[1]在女国民塑造、倡言女权方面格外引人注目。学界对《大公报》与女智启蒙问题的关注较早,但多集中于吕碧城的公众形象生成和启蒙策略概述等方面,并未就女国民塑造的微观机理进行审察。检视20世纪初年的《大公报》,其中关于女智启蒙的报道并未单纯停留于女性陋俗的聒噪,而是上升到女权、国族意识的高度,最终通过资取域外范型,在批判和引介中完成理想女国民形象塑造。这种叙事策略有效地疏通了女性日常习尚和国家意识之间的路径,有力提升了舆论宣传的落地感和时效性。
一、缠足与国耻话语关联
作为束缚传统女性身心的标识,女子缠足首先被纳入近代公共舆论的批判中。因此,《大公报》在女智启蒙时,率先聚焦于女子缠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大公报》突破了纠缠于身体残疾的传统论调,将其与国耻话语相关联,上升到家国意识高度,完成日常陋俗与国家耻辱话语的关联。同时利用媒介舆论,不断强化巩固宣传效果,呼应民众关切,促使启蒙效果最优化。
首先,《大公报》通过海量报道直陈女性缠足弊端,同时利用典型事件适时发酵与国耻话语相关联。该报创刊伊始即关注到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缠足陋习,不遗余力地对这一身体“丑怪”大加挞伐。清末最后十余年中,其先后刊登了近370篇批判女性缠足的文章。如果说1903年以前,《大公报》对缠足的讨论措辞尚属平缓,大多指责其为囿于陋俗的“野蛮人”,[2]那么,1903年的“日本劝业博览会事件”(以下简称“博览会事件”)将“缠足”现象推向了舆论顶点。1903年3月9日,《大公报》援引一则日本新闻: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拟“描写”各国的文明野蛮风俗,中国女性缠足习俗赫然在列。因缠足形象“逼肖逼真,使万国环观,未免大失国人体面”,中国驻东京公使遣翻译前往日本外务省交涉,日方照会该博览会“暂缓部署”。[3]这则200余字的新闻深深戳动了国人的精神痛点,经由媒体舆论的放大效应,中国女性缠足形象上升到影响国家“颜面”层面。《大公报》也利用曝光博览会事件的契机实现了女性缠足与国耻话语紧实勾连。3月10日,该报社论就这一事件继续发酵,直言日本展览馆中的缠足形象是赤裸裸的“国耻”[4]。显然,《大公报》敏锐地抓住了国人不能容忍缠足在国际上“丢脸”这一心理,为其阐述缠足的国耻话语找到了舆论突破口。虽然后续《大公报》报道了该展览被“废止”的事实,[5]但反响甚微。
其次,《大公报》利用社论等栏目不断跟进报道,呼应民众关切,实现采编、读者双向建构。报纸在后续的社论中继续加码,提示性地敬告民众:缠足展览“既举而复废,我中国人即已挂名于野蛮之簿,列衔于野蛮之班,此一大耻”[6],也就是说,女性缠足形象已成既定的国耻事实。巧合的是,《大公报》上关于“博览会事件”的言论引起了驻华日本侨民山根虎之助的回应。他认为,日本人类馆展览仅是陈列“东西习尚之异,未可以为文野之界”[7],言下之意中国人大可不必对此反应如此激烈。
《大公报》为了回应山根虎之助的来函,再次补充材料详细回顾博览会展览女性缠足让中国颜面尽失的过程,并附带报道中国官员缠足眷属游会引起“轰动”一事。“金莲三寸,步履维艰”,于是被特别允许“乘轿周游会场”,“一时观者之视线咸集其身”。[8]至此,在《大公报》舆论导引下,日本博览会上的中国女性缠足形象已然成为时人难以抹去的国耻记忆,并且引来众多读者的来信及发文呼吁。譬如,一名自称“抱膝庐主人”的读者直抒胸臆,认为此系关乎中国“存亡关键绝大问题”,应该“设法力争挽回”,“以鼓同胞奋耻之心”。[9]另外,“博览会事件”话题还被引入该报鼓励放足的征文中。参与征文的朱莲鸳女士指出,人类馆中“缠足肖像”“坏我国体甚矣”,“辱我女界甚矣”;[10]郭恩泽亦曰:此乃“吾人之大辱”[11]。此后,这一事件时而被演绎为东西各国取笑“绘图传观”的莫大国耻。[12]同时,有识之士甚至倡言因“日本赛会至列缠足妇女于生番馆,我邦人士视为莫大之奇辱”,应及时设会立社,劝诫妇女放足,“立会几遍于十八行省”。[13]总之,在报章与读者的反复“叙述”中,缠足形象与“国耻”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
最后,《大公报》通过后续报道不断强化国人对缠足“耻辱”的认识,直至促动当局有所警醒。1903年11月,尽管“博览会事件”已过去近半年,《大公报》仍在利用舆论余波,以“最易动人之劝戒缠足说”为主题,发布征文广告,与读者展开互动,持续升级女性缠足与国耻形象的宣传。[14]1904年,该报及时抓取美国圣路易赛会会场中国留学生集资遣返作为“陈列品”的缠足女一事,继续发酵缠足与国耻的话题。《大公报》赞其曰:“为中国去一亡国之大辱”的“爱国者”。[15]此外,还援引“有外国人买出缠足妇女的鞋,要带回本国摆在博物院里,给大家观看”,[16]劝诫国人“知耻后勇”。
在报纸舆论的推动之下,女性缠足的“耻辱”形象得以广泛传播,并引起政府当局警醒。辛亥革命前夕,四川有人“将《大公报》上历来所论之天足事汇刻成册”,派人分送一些于府县。[17]地方官员逐渐知晓缠足被“邻国恣为笑谈”[18],“为五洲所非笑”[19],赞同妇女天足。[20]1910年资政院第二十二次会议的第七件议案为“审查报告提起创议禁止妇女缠足事”[21],最终由议长指定庄亲王“为特任股员,并案审查”[22]。虽然政府尚未将缠足列为禁律,然亦表明女性缠足在国耻记忆建构下,已进入国家视野。
综上,《大公报》在审视现代女性国民的基本素养时,首先直面缠足这一幽束女性身心的表征。在新闻报道的策略方面,《大公报》敏锐地抓取典型新闻素材,利用特殊的解读方式和舆论放送路径,让缠足在国际视野中不断发酵。尤其是通过把控“博览会事件”的新闻尺度,实现编读双方合力推动,反复阐述缠足与国耻之间的特殊关联,不断强化缠足国耻话语的舆论效应。
二、短装与奴婢身份互代
与缠足相仿,传统女性的服饰装束亦是《大公报》诘难的切入点。《大公报》对于女性服饰的关注因晚清女学堂制服论争而起。1906年,北洋高等女学堂建立,开启培养女教师的近代新风。[23]女学生作为扶衰振弱的“将来之国魂”,究竟以何种形象示人颇引人关注。因此,一时间女性服饰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热点。《大公报》适时援引热点,从1906年8月13日至9月15日,以《女学生服制议》为题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征文活动。而且《大公报》的这次征文论题具有一定的导向性:针对女学章程“不许长服”的提议,声称“女子宜长服为全球开明各国所公认”。(1)期间9月10日至14日未刊登。因此,在来稿中不少人将服装与国民仪表直接挂钩。譬如,读者刘仲元指出,女性短服是交际场中的“不类不伦之衣服,于形式上且不完全,何论其他”,其认同理想服饰应为“上狭下宽之长服”。[24]另一位来稿者“于天泽”直言,女性服饰事关“造未来之国民”“表通国之尚武”“完当代之人格”[25]“列世界之平等”[26]。因此,大多来稿都认为,中国“苟欲占一平等帝国之价值,则宜采取外界大同之文明”[27],中国女子以“长服为适宜,而尤以操衣下裳为宜”。这样的装束“不惟便于运动,而且严其威仪”,“内以结国家之大社会,外以登世界之大舞台”。[26]可见,两位读者除肯定女性着长服可标仪彰外,更重要的是,女性服饰是实现世界国民“平起平坐”的要项。
《大公报》利用读者来稿呼吁,就势将论争引向服饰关乎国民平等,渐进导出短装即女婢身份象征的舆论风标。《大公报》中诸多文章对传统女服尤其是短装展开批判。有文章指出,中国女装“短袄叉裤之服色”,与“长裙覆地、楚楚若仙之白色人种相较,无不自惭形秽”[28]。这种短装在长服“为全球所公认”的惯例中,自然难入潮流“低人一等”,甚至被形容为“不堪入目”的奴婢装束:

这样,《大公报》的宣传话语正式转向中国女性服饰逊色于域外女性,且呈现奴婢相,将女性外显的服饰形象等同于国民身份的外在表征。显然,《大公报》借服制征文热潮,将舆论热点引向国民形象塑造话题才是其本意。此后,对服装的讨论逐渐进入国民形象的论域。有文章指出:“国家欲占优胜于天演界,要当使人民整齐外表以焕发精神,一新天下之耳目。”[30]而中国女性“裩长覆足,服短于股”的形象在《大公报》看来“非独与制度之不相合,即仪表上亦不雅观”,会被他国人“诧为怪物”。[31]因此,作为现代国民,服饰改革的一项内容就是“女人之短衣”[32]。这种倡议也得到《大公报》主编英敛之的高度认同,他在奉天游览日记中描述当地女性:“无缠足丑德,无短衣陋风,所有女生,皆长身健硕,落落大方。”[33]由于《大公报》舆论不断强化服装与国民形象之间的联系,这种呼吁推动了晚清女性服饰变革。1909年,吉林某君亦通过《大公报》发出:“世界服制以‘满洲’为最适,而女子服制(即指旗装)尤为得男女平等之意”,藉此以影响学部釐订女学服制。[34]1910年,学部最终拟定了《女学服色章程折》(2)事实上,这一服制的适用性遭到诟病。此后,1911年学部拟定的关于女学事宜中第四条为“改订女学服制章程”,筹划修改女学生服制。。关于女生服饰的争论在现实影响力上初见成效。
可见,《大公报》对中国女性装束的报道超越了美丑雅俗的界限,将其与女婢身份互代,透过“国家之眼”审视,进而勾连起女装与国民形象的关系。由此,在检视女性的日常穿戴之余,《大公报》着意引导社会由对待服饰的大众心态向家国情感过渡,服饰“不再仅仅是生活中琐碎渺小的存在,而且成为政治变革中的一个元素,‘家国叙事’中的一个声部。”[35]
三、习尚与愚昧形象相契
随着女智启蒙呼声的不断深入,《大公报》对女性形象的关注范围逐渐延伸到日常习性和生活样式。在《大公报》看来,中国传统妇女不仅在身体、服饰等方面未能符合时代要求,而且在智识习性方面亦难如人意。“环顾全国,求夫博学多才、通明洞达杰出于巾帼中者”少之又少。考诸清末《大公报》关于女性的言论,大多为“酣睡漏舟之中,安巢覆幕之上”,“犹冥然而罔觉,嬉然而自得”等说辞。[36]首先,报纸对女性日常生活的陋俗颇有微词。譬如,迎神赛会中鸣锣击鼓的妇女被嘲笑为“聚众招摇”之无知愚民,[37]妇女缠足被指“以残忍为能事”[38],去寺庙医病求福的妇女则被视为“迷信之愚民”,大多女性“狃于陋俗”则被视为无知。[39]如此评议,皆因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不思殖财增收之心,尽遣娱乐靡费之中,与国家振兴几无关系:
所费之资财直无一文明之举动,率不过缠足者珠玉其履,画眉者脂粉其颜,春日流觞醉金谷之酒,良宵观剧结鞠部之欢,甚至大发慈悲出千金而佞佛,钟情儿女倾积产以完姻,事出多途不胜缕述。[40]
在婚礼仪式中亦是“繁文缛节,虚浮滥费,举皆无益”[41]。这样,《大公报》通过缠足修容、宴游观剧、礼佛、钟情儿女婚姻等日常习尚生动刻画出晚清女性的“蒙昧”与“无知”。
如果说日常生活习俗仅是着眼于个人生活的不文明,那么智识的缺乏则直接关乎其国民素质的评判。在《大公报》看来,中国女性对于自身的认识只限于“缠足修容,锢蔽于阃闱,智识欠缺,器量狭隘”,基本谈不上“强中国富中国可分任其功”。即便是国家危难之时,她们也是置若罔闻,几乎成为国家的“隐形人”。这也正是晚清媒介批判传统女性愚昧的第二个方面。《大公报》指出:“中国古代尚有如曹昭、木兰、梁红玉等不可胜数的卫国女杰”[42],而清末的女性不仅对国事鲜少参与,而且“豢伏帷闼之间,治乱不知,存亡弗念,一任异族之侵压我政权也,踞削我土地也,朘剥我财利也,将奴隶我也,瓜分我也,举若不闻不见而莫之惑恤焉”[36],更无国家情怀,“无国家思想者人之野蛮也,无爱国精神者人群之禽兽也”[43],如此激烈言辞与尖锐的形象冲突道出晚清女性思想亟待改变的迫切程度。正如陈东原所言:“取前此二千余年的妇女生活,倒捲而缫演之,如登刀山,愈登而刀愈尖,如扫落叶,愈扫而堆愈厚;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到了清代,算是‘登峰造极’了!”[44]
无论是日常生活习尚,还是智识精神,《大公报》都将近代国民不能进于文明、国家不能趋于强盛、黄种不能媲美于白种的时代问题,归咎于女性无知之故。[45]在其舆论话语中,女性陋俗不仅影响自身生活,更影响到国家命运。因此,《大公报》才发出“参用东西各国礼仪,将中国旧有之恶俗删除大半”[1]的呼吁。总而言之,《大公报》将女性日常习俗和愚昧形象连接起来的真正意图在于“使凡我女同胞人人以忠爱为怀,时时以富强为念,全体响应众志成城”,实现女性国民意识启蒙。[46]正如美国学者克兰所言,媒介不过是“通过呈现不同群体的各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提供“有关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详细资料”。[47]
四、域外范型与“理想”女国民重构
在深刻批判清末女性旧有形象的基础上,《大公报》对究竟何为“理想女国民”的议题进行了细致反思。在“西风东渐”的近代启蒙语境中,它通过资取域外的女性范型,从职业选择、教育开化、爱国勇毅三个维度生成了媒体眼中的“理想女国民”。
首先,职业分途,自立自强是现代女国民的首要素质。从男性主导的家庭境遇中解放出来,自谋职业、自主择业是现代国民首先直面的问题,也是《大公报》极力倡导的方向。《大公报》屡屡展示外国妇女自立、敢于担当的具体案例,来呈现媒体及知识界的殷切期待。譬如,有文章称,荷兰女子从事的职业中,最多为内外科医生、牙医、药剂师、照相师、园艺师等,“该国女子从事剂药者现有千数百人之多云”[48],甚至西方已有女子涉足商圈。美国沙丁省女子经营煤油公司“生意颇不寂寞”,且公司上到总办,下到佣役均为未婚女性,女性集资并自主经营,“一切条例亦其手订,至今数十年井然不乱,闻者皆羡诸女子之才”[49],就连在银行界亦不乏女性的身影:纽约“现有女子多人招集股本洋五百万元设立女银行一所,行中各事悉由妇人经理,专收女人存款,男子之款概不收存,现请亨汀敦国民银行司账狄克女士为银行总理”[50]。大体看来,这些女性的共同点是具有较强的自主谋生能力,也为国家创造了可观财富,支撑起国家富强的半壁江山。在“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中,《大公报》的这种论调不啻于一声惊雷。
此外,报纸还统计了一些国家的从业女性数量,藉此来充分说明国外女性自立之程度:“美国女子十岁以上劳力作工者五百五十万人,美术教习学生一千零二十一人,律师一千零十人,主笔访事二千一百九十三人,医生七千三百八十七人,会计七万四千一百五十三人,商贾三万四千三百四十五人,银行公司一千二百七十一人,简写印字排字刻书八万六千一百十八人,电务邮递二万二千二百五十六人”,因此“闺阁之英振振而起,其富强也宜哉”。[42]凡此种种,报纸反复说明世界范围内女性各安其业、自立自强,充分展示职业分途对于女性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舆论也指明了中国女性挣脱家庭藩篱的方向:先谋得一份生业,使自己生活独立,进而实现人格独立。
其次,生活独立的基础上,接受良好教育,启智化愚。西方女性国民之所以能够安居乐业,皆因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从《大公报》对各国教育的羡慕之辞即可发现其中端倪。例如荷兰“女子不毕高等女学堂之课程者殆属绝无。其课程重者为外国语,该国中流以上女子不解英、法、德三国语者群以无教育目之。”[48]甚或直言“女界中学问之进步在欧美文明国已将达于极点,……其程度直与学问渊深之男子埒而不稍让。”[51]也许类似“西方女性尽数接受教育”“精通外语”等说辞不免有溢美成分,但客观上反映了《大公报》热切期待激励中国女性奋发求知的心理。此外,《大公报》还通过搜求一些国外残障女性教育自强的事例来激励民众。如英国一位名为克尔的盲女,年仅24岁即硕士毕业,擅长政治、哲学、拉丁文、法文、德文等,报纸称赞其“不畏险阻潜心学问遂至今卒业得锡学位,不亦荣哉”,勉励我国女性“读此其亦知所发愤”。[52]在舆论看来,西方国家残障女性尚能如此,中国的普通女性智识怎能安于现状。这种情况更能说明中国女性兴学求职的必要性。总之,《大公报》指出,兴学受教是传统女性由“妇人”转化为现代“国民”的必由路径。
再次,勇毅担当,保国卫民。梁任公有言:传统民众“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53]但是,放眼现代,爱国尽职是每一位国民的应尽义务。尤其是在国难当头,报国勇毅,倾身而出更是被标榜为国民必备素养。在这种社会语境中,《大公报》通过舆论口径极力渲染国外女性在外敌入侵时,亦能同男子一样勇于担当、杀敌报国的典型事例。譬如,法国女子若安面对英军围困“城陷且在旦夕”,“勃然而起,号吊国民破除敌旅,克复国权,振兴旧业”。见英军纵火劫掠时“心伤泪涔涔下,慨然以扫荡英军济拔国民为己任”。“此何等气魄何等热诚,岂以女子限哉?为国民不当如是耶?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反观国内聚会歌舞的男女,“国破君亡为人奴隶而酣嬉若此,国事将委阿谁耶”。[43]无独有偶,另一位俄国女子依也瓦“武备精通,富于韬略”,到地方总督处“自告奋勇欲投俄营赴‘满洲’助战”,而总督则“壮其志,许之领率男女队赴远东”,依也瓦“初至‘满洲’即赴前敌,身先士卒”。[54]《大公报》登载这些消息的意图在于“为中国巾帼之鉴”,“而知所奋发”。[55]这样,国外女性勇毅报国的形象跃然纸上。总之,在和平时期,能自立谋生,为国殖财;在国家危难时,能够冲锋御侮,这些标准成为《大公报》认知和生成理想女国民形象的主要维度和内涵。
《大公报》通过资取域外女性自立、担当的事例为塑造中国女国民形象提供了范例。也许《大公报》对外国女性国民形象的呈现略带理想化,或者这些形象是媒体根据时势的“选择性呈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塑造方式首先指出清季社会女性启蒙的迫切性,同时也折射出媒介视域中女性启蒙的基本特征,即启蒙引介的本土资源缺失和社会启蒙的国际视野。这种特征某种程度上也暗合晚清知识界的舆论期待。
五、余论
重新检视《大公报》中有关“女国民”的论述可以发现,它并没有停留在女性缠足、服裳、陋俗等日常行为的批判、聒噪,而是将其关联到国家形象层面,并通过资取域外女性典范来模塑理想女国民形象。这种批判——重构的叙事路径既是对晚清女性现状的省思与认知,也是对未来理想国民的期待与构建。客观地讲,《大公报》的宣传并非尽是“写实”,而是经过“媒体之眼”的选择与加工来影响受众。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所言:“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个世界的模样而非这个世界的真正模样决定了我们的行为”[56]。换言之,《大公报》中的女国民可能是主流媒体以国际标准“去芜取菁”建构出来的。
这种建构路径亦得益于时任《大公报》主笔的吕碧城、英敛之等极力宣扬与扶持。更为关键的是,其中《大公报》的新闻叙事模式与吕碧城个人的女权思想相表里。1904年,吕碧城与《大公报》结缘,出任《大公报》编辑。随后,她紧锣密鼓地在“杂俎”栏发表了多篇“倡女学、兴女权”的文章,如《敬告中国女同胞》《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远征赋》以及《教育为立国之本》等。仔细爬梳这些文章可以发现,她的写作逻辑、叙事风格与《大公报》中塑造女国民的方式基本一致。譬如,谈及女性启蒙的要旨时,她也是从“身体”“生活”“职业”等几个方面展开。关于身体,她认为:“今欲激发个人之权利,姑先从个人之形体上论起。”关于女性职业问题,她指出:“视己之资格,能为何等之人,即为何等之人,视己之才干,能为何等之业,即为何等之业。”[57]对于未来女性国民的期待,她指出:“上以雪既往众女子之奇冤,下以造未来众女子之幸福,使之男女平等,无偏无颇。”[58]这样的女权启蒙思想与《大公报》中批评女性日常陋俗,通过职业取得独立的叙述逻辑别无二致。
这样的宣传路径与英敛之的办报理念和支持也分不开。英敛之秉持“忘己之为公,无私之为大”的公心,坚持报刊为“国民之耳目,社会之回声”理念,“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59]尤其是吕碧城推出关于“女权”专论后,他以“铁花馆主”的笔名附文唱和,更在代表报社立场宗旨的“论说”栏发表《读碧城女史诗词有感》等评论文章。随后,《大公报》即以持续的舆论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响与共鸣。因此,正是英敛之的惨淡经营,才将《大公报》“办女学、兴女智”的舆论声势推向社会公共空间与公共视野。[60]晚清时期《大公报》关于女国民形象的认知与构建,实质上是报章编辑理念、报人叙事风格、时代诉求三者的有机统一。这样才使得《大公报》模塑的女国民形象在晚清公共舆论中显得格外典型和特殊。
-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应急语言服务质量标准体系构建研究
- 欧洲委员会语言教育政策评析
- 在线教学资源开发模型的构建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