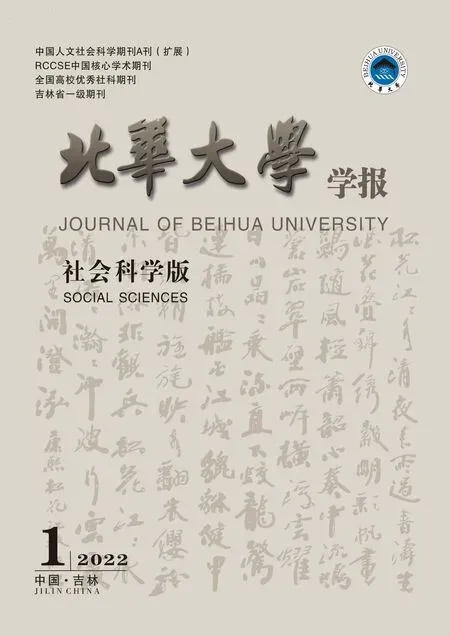中亚五国语言生态及政策的共性研究
张治国
引 言
中亚五国分别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前三国与中国领土接壤)。国名都以“斯坦”(-stan)结尾,所以,中亚五国也叫“斯坦五国”。“斯坦”是古波斯语中的一个后缀,意为“地方”或“国家”。五国总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1],截止到2020年总人口约7 000万[2]。中亚五国在地理、人文、民族、宗教、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点,所以,“中亚”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政治和文化概念,为此,国际上众多学科常把中亚五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同样,对于中亚五国的语言政策,我们除了需要进行国别研究外,[3-6]也需要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国外学界做得比较好,已有专著[7]或编著[8]等厚重学术成果出现。尽管国内学界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论文成果,[9-15]但总体上缺乏对中亚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的整体化研究。语言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语言生存的背景或环境,即语言生态。只有了解了大概的语言生态,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分析语言政策。故此,本文拟做一些这方面的尝试——探究中亚五国1991年独立后的语言生态变化及语言政策特点。
一、中亚五国语言生态的共同特点
(一)五国具有大体相同的社会语库结构
社会语库(linguistic repertoire)是指某一社会中所使用的各种语言及其变体的总和。中亚五国都属于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16]“无论是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多语都是中亚语言的一个显著特点”[17]157,各国语言的总数都百种左右,它们的社会语库结构大体相同,都由以下四类语言构成:
第一类是名义语言(titular language)。名义语言是指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即名义国家(titular nation)的国语。在苏联时期,这些语言在俄语的强势环境下显得黯然失色,仅有名义上的地位。这些加盟共和国独立后,其名义语言的地位开始凸显,都成了各国名副其实的国语,但名义语言术语仍在学术界使用。中亚五国的名义语言分别是其主体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即哈萨克语(Kazakh)、吉尔吉斯语(Kyrgyz)、塔吉克语(Tajik)、乌兹别克语(Uzbek)和土库曼语(Turkmen)。如表1所示,独立初期,各国名义语言在家庭域中的使用率都不算高,其中最高的是土库曼语(达62.8%),最低的是哈萨克语(33.6%)。[7]213但经过二十几年的语言改革和推广后,中亚五国名义语言的普及率已大有提高。中亚五国语言的总体特点是:以本国主体民族的语言为名义语言,同时也使用周边邻国的名义语言。如哈萨克斯坦的名义语言是哈萨克语,但同时也使用中亚其他四国的名义语言,只不过其他四国的名义语言只算是哈萨克斯坦的少数民族语言。其他四国的语言情况也是如此。

表1 中亚五国名义语言及俄语在家庭中的使用情况(1993) /%
第二类是俄语。在苏联时代,俄语是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地位显赫,影响深远。中亚五国独立后,俄语依然是这些国家的强势语和族际交际语,[18]这里仍算是俄语世界(Russophone)的一角。中亚五国的俄语影响度(或受俄语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7]201表1显示的俄语在中亚五国家庭中的使用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哈萨克斯坦之所以受俄语的影响最深,是因为在苏联时期,哈萨克族是苏联中亚地区各民族中俄罗斯化最高的民族,因而很多哈萨克族国民以俄语为第一语言。加之,哈萨克斯坦在地理位置上紧邻俄罗斯,境内具有中亚五国中比例最高的俄罗斯族人口。土库曼斯坦之所以在中亚五国中受俄语的影响最小,俄语地位较低,使用范围较窄,其原因是多重复杂的,如下几个因素是主要的:自1995年起土库曼斯坦成了一个中立国家,2005年退出独联体,也未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国内的俄罗斯族人仅占全国人口的1.8%,在俄罗斯工作的人是中亚五国中比例最小的。[8]
第三类是本国的非名义语言(non-titular language)或少数民族语言。这些语言是中亚五国除各自的名义语言和俄语外的其他语言。它们数量庞大,使用者不多,地位不高。各国非名义语言的主要语种大致相同,即其他四国的名义语言、阿塞拜疆语、德语、鞑靼语、维吾尔语、卡拉卡尔帕克语(Karakalpak)等。[19]中亚五国家庭语言的使用状况(见表2)也证明了这一事实。另外,表2还表明中亚五国之间的跨境语言较多,语言障碍较少。

表2 中亚五国非名义语言在家庭中的使用情况(1993) /%
第四类是外语。中亚五国的外语主要是欧洲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等)及东亚语言(如汉语、朝鲜语或韩语等),其中有些语言(如德语、土耳其语、朝鲜语或韩语)既属于外语,也属于本国的非名义语言。表3反映了中亚五国各国人民对外语的渴望度。

表3 中亚五国国民外语学习意愿情况(1993年) /%
表3显示,中亚五国各国人民最想学习的外语是英语,其次是土耳其语;俄语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大不如前,但在语言实践中,俄语的使用率还是不低的;此外,不想学习任何外语的比例在各国也不低,这说明中亚五国在建国初期对外接触不多,国际化程度不高,所以外语学习的动机还不强。
(二)五国名义语言具有大体相同的语言属性
在中亚五国的名义语言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和土库曼语都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Turkic languages),而塔吉克语则归为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Indo-Iranian languages)。突厥语族,也称土耳其语族,是阿尔泰语系中最大的一个语族。它包含了40多种语言,其中土耳其语的使用范围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突厥语族的人口分布很广,数量达1.65亿至2亿人,分布地域从东到西由中国一直伸展到俄罗斯及东欧。突厥语族分为东突厥语支(如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南突厥语支(如土库曼语),西突厥语支(如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和北突厥语支(如阿尔泰语、图瓦语)。印度—伊朗语族是印欧语系中最东方的一族,下分为印度—雅利安语支(Indo-Aryan)、伊朗语支和奴利斯塔尼语支(Nuristani)。伊朗语支分布在伊朗(古波斯)、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土耳其、高加索等地。该语支包括波斯语、普什图语、库尔德语、俾路支语、奥塞梯语、塔吉克语、法尔西语、达里语、回回语等。而塔吉克语与波斯语很相近,许多人把它看作是波斯语的一种方言或变体。可见,中亚五国的名义语言除塔吉克语属印度—伊朗语族外,其余四国的都属突厥语族。所以,人们根据名义语言的属性称塔吉克斯坦为波斯语国家,其余四国为突厥语国家(Turkic states)。
同语族的特性使得中亚五国名义语言(除塔吉克语)之间以及这些名义语言与其他部分非名义语言(如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鞑靼语、卡拉卡尔帕克语)之间的互懂度(intelligibility)较高。而且,现代突厥语族下的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别远小于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等语系中同语族语言之间的差别。突厥语族的各分支语言有许多共同的语汇、相似的语法和发音特点。加之,突厥人在欧亚大陆的分布区域极广,又彼此长期混居,同时还分别与操其他语言的民族相邻,这就使得突厥语内部诸语言的互懂度较高。
(三)五国都存在政治变革导致语言使用人数突变的情况
语言的地位和活力与语言的使用者数量存在一定的关系,从而影响语言政策的制定。[20]中亚地区社会政治的变化带来了民族结构及人口数量的变化,进而影响到语言的地位与活力。1990—2000年的十年是中亚五国的人口动荡和变化期,各国的人口总数、民族比例、俄语和各名义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比例等数据每年都有较大变化。中亚五国独立初期,都出现了人口大迁移或民族大洗牌现象:多数人都回归到以本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而且,五国的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导致各国人口总数减少。各国迁入人口主要是周边加盟共和国及其他国家的同族人口,迁出人口情况则正相反,但主要是俄罗斯族人(详见表4),他们大多都迁往俄罗斯联邦或其他西方国家。[21]

表4 中亚五国俄罗斯族人口统计(1989—2005年) /万
表4显示,俄罗斯族人口减少幅度最大的国家是塔吉克斯坦(64.7%),最小的是哈萨克斯坦(33.3%),各国平均减少率为52.68%。也就是说,中亚五国有一半多的俄罗斯族人口外迁。人口数量的大变化使各国的民族语言(尤其是名义语言和俄语)的地位和活力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名义语言的地位和活力上升,俄语的地位和活力下降。
中亚五国独立后之所以出现大量的人口移动和民族大洗牌现象,主要是出于民族身份及语言身份的考虑。语言一直是“集体身份”或“民族身份”两个概念中的核心内容,是人类集体文化感知中的关键因素。当人们意识到国家的语言政策会给自己的集体身份或民族身份带来威胁时,上述感觉就会更加强烈。中亚五国刚独立时,这些国家的许多人都遇到了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的问题。[7]5Katagoshchina指出:“身份危机是导致中亚五国少数民族外迁的一个重要原因。”[23]26于是,中亚五国独立后都吸引了周边国家中的同族人口迁入,自然,这些国家的主要外迁人口都不是各国主体民族。
(四)五国都受到同样的外国势力及其语言的影响
第一,受俄罗斯和俄语的影响。俄罗斯对中亚五国的影响历史悠久,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的俄罗斯族人都希望中亚各国保留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若国内名义语言与俄语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乃至引起国内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中亚各国的语言政策制定者都已经认识到俄罗斯政府对中亚各国俄罗斯族人口的支持。因此,俄罗斯的影响是这些国家在制定语言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外在因素,[7]209各国都不能无视俄语的存在。
第二,受土耳其和土耳其语的影响。土耳其原本在中亚就有一定的影响,自从中亚五国独立后,土耳其的一些机构和组织(如总部位于土耳其安卡拉的突厥文化国际组织)就更加不遗余力地在这里推广土耳其的语言和文化,并反复强调突厥人共同所具有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之根,试图把土耳其语打造为地区共同语。[24]土耳其想加强突厥族语言使用国家之间的联系,形成突厥语世界(Turkic World)。每年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的有关突厥语言和文化的学术会议也的确加强了中亚各国彼此的认同感。尽管土耳其竭力推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但中亚各国都想树立自己独有的国家身份,他们大多仅接受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的思想,尤其是语言文化方面的泛突厥主义。尽管土耳其语在中亚的传播速度很快,但土耳其语在中亚的推广也面临着各种域外语言的竞争:首先是欧洲语言(如俄语、英语、德语和法语),其次是亚洲语言(如朝鲜语或韩语、日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汉语)。[7]14因此,土耳其语“还算不上是该地区的通用语”[17]178。
第三,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英语等语言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大国在“9·11”事件后打着反恐的旗号开始更加关注和强势介入中亚事务,使得英语等西方强势语言在中亚的影响也随之扩大。[17]而且,中亚许多年轻一代由于受到美国流行文化及电脑等产品的影响而喜欢英语(表3数据反映的中亚五国国民的外语学习渴望度也说明了这一点),各国都有不少的英语培训中心,也建有一些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高校。
第四,受伊朗和波斯语的影响。伊朗一直声称在文化、宗教和语言方面对中亚(尤其是对塔吉克斯坦)有一定的影响力。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主体民族不是突厥族的国家,它属于波斯语国家,而且,塔吉克语被看作是伊朗波斯语的一种变体。出于语言、地理、历史和民族文化(ethnocultural)的考虑,塔吉克斯坦或多或少地受到伊朗及波斯语的影响。[17]语言的联系使得塔吉克斯坦与伊朗“走得更近,关系更好”,这是“中亚其他四国未有的现象,也是塔吉克斯坦与其余四国所不同的地方”[24]142。
第五,受东亚国家及其语言的影响。中国的语言(尤其是汉语普通话、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在中亚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中亚人想学或正在学汉语普通话,而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跨境语言,在词汇上会相互影响。此外,中亚本身有不少朝鲜族人口,加之,近年来韩国政府对韩语教学的积极推广,因此,朝鲜语或韩语在中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例如,韩国注重与中亚两个较强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经贸关系,而且,这两个国家分别有0.6%和1%的朝鲜族人口,这些因素推动了这两个国家的朝鲜和韩国研究,并建立了韩国语言文化教育中心,韩国政府为该中心提供经费及教材。而且,近来由于受到韩国多方面的影响,这两个国家的语言学习从原先的朝鲜语变体转向了韩语变体。[17]179-180
二、中亚五国语言政策的共同特点
(一)地位规划特点及分析
在语言的地位规划方面,主要是解决名义语言和俄语的地位之争问题,与此同时却都忽略了本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问题。
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皆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国名义语言与俄语的关系问题。“这些国家独立后都试图提高本国名义语言的地位,并以此来抗衡俄语(这是主要目的)和本国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这是次要目的),于是,它们纷纷对本国原有的语言政策进行修改”,[25]164并通过各自的宪法及语言法规定本国的名义语言为国语、官方语言,结果“各国都发生了语言转用,从原先的强势语言俄语转用现在的名义语言”[7]201。在这场自上而下的语言转用运动中,本国“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或非名义语言则被边缘化”[7]17。
诚然,国家独立有利于这些国家主体民族语言或名义语言的地位提升。但是,俄语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以及俄语作为高阶语言(H variety)的地位是这些名义语言无法在短期内所撼动的。不过,这些国家在语言政策上重名义语言、轻俄语及忽略非名义语言的做法也不是空穴来风,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这些国家独立后都遇到同样的一个身份困境,即如何处理国家在全球化变革时代由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地方身份(subnational identity)和跨国身份(transnational identity)所构成的身份多样性问题。[7]198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刚独立时都在寻找一种新的民族特性,以便树立自己的国家身份。[7]1国语是国家身份的一个象征,“在重新界定新的国家身份时,语言政策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24]165于是,中亚五国都必须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即去俄罗斯化(de-Rissianization)或去苏联化(de-Sovietization),然后才树立自己的国家身份。最显性的去俄罗斯化就是去俄语化,同时,加强国家身份的最显性方式是推广本国的名义语言,提升本国的名义语言地位。
把名义语言提升为强势语言的行为必然会带来语言排斥(language exclusion)现象,或者说,必然会降低其他语言的地位和作用。[7]3这些国家的语言地位规划都遇到程度不同的各种阻力,来自国家内部及外部的压力使得它们都无法摆脱俄语的影响,并对邻国名义语言予以适度考虑:在国内方面,各国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都变得紧张;有些国家的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也存在矛盾(如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乌兹别克族与吉尔吉斯族之间关系特别紧张)。在国外方面,中亚五国在制定语言的地位规划时都必须考虑本国俄语的地位及俄罗斯对此的感受;有些国家还不得不考虑邻国间的关系(如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曾存在紧张的外交关系),以免因语言地位规划带来外交冲突。此外,对于中亚五国的不少人而言,俄罗斯情结挥之不去,他们对俄语是爱恨交加:就实用性和国际性的角度而言,俄语更有用,但从情感和尊严的角度来说,他们情愿选择自己的名义语言或民族语言。后来,中亚五国都只好放宽了俄语在本国的使用限制,并恢复提高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如今俄语依然是这些国家上层社会以及知识界学人主要使用的语言,但俄语在中亚五国的地位、声望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使用范围有所收缩。
总之,中亚五国独立后,语言已经明显政治化,这些国家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制定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国政府首脑及相关的智囊团。[26-27]而且,他们尽力通过语言地位和语言使用的概念化来巩固国家的地位和加强国家的团结,[7]21但事实上,苏联的突然解体导致中亚五国各项语言政策的制定“准备不足”[1]序言,匆忙应对,且有些操之过急。
(二)本体规划特点及分析
在语言的本体规划方面,主要涉及名义语言书写符号系统的选用问题,同时,也有意抑制或消除俄语词在名义语言中的大量借用。
中亚五国在名义语言的书写系统上都大概经历了如下几个过程:最初使用了几十年的阿拉伯字母(Arabic script);20世纪20年代曾短暂地使用过拉丁字母(Latin script);并入苏联后(即20世纪40年代)则改用西里尔字母(Cyrillic script);1991年独立后就名义语言的书写系统问题又产生了分歧——是恢复拉丁字母或阿拉伯字母书写系统,还是保留西里尔字母书写系统的问题。[28]例如,吉尔吉斯斯坦想恢复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系统,赞同者认为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系统有助于同其他突厥族语言的使用者交流;反对者则认为应该保留西里尔字母书写系统,只要做些适当的修改即可,否则成本巨大;还有人提倡转用拉丁字母书写系统,以便与世界接轨。总之,在中亚五国刚独立的头几年,书写系统比较混乱(详见表5),而且“书写系统的变换使得不少人变成了文盲”[7]206。

表5 中亚五国书写符号系统的应用情况(1993年) /%
现在,俄罗斯族人口较多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仍有很多俄罗斯族人采用西里尔字母书写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塔吉克斯坦尽管拥有的俄罗斯族人口不多,却依然在其名义语言上坚持使用西里尔字母,足见塔吉克斯坦与俄罗斯的亲密关系。乌兹别克斯坦的名义语言则采用了双字母制(two parallel alphabets)——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有的领域(如学校)依然使西里尔字母书写乌兹别克语,有的领域(如公共场所)选用拉丁字母来书写路牌等公共标识,还有的领域(如网络)则两者均用,但国家的最终意图是要逐渐过渡到拉丁字母的使用。1993年土库曼斯坦时任总统尼亚佐夫(Niyazov)发出总统令——该国名义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将从1996年开始从西里尔字母改为拉丁字母。[7,27]
在语言的本体规划方面,中亚五国都试图将本国国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从原先的西里尔字母改为拉丁字母,但字母拉丁化(Latinization)的困难要比预想的大得多。此外,中亚五国在本体规划上还有意抑制或消除本国名义语言中的一些俄语词。中亚五国有些民族主义者把俄语看作是“苏联语言帝国主义的遗产”[7]4。
中亚五国独立后都试图实现名义语言的本国化或本土化(indigenization),尤其是恢复名义语言的书写系统以及净化名义语言的词汇。“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些语言改革都经常引起严重的语言混乱,并带来容易导致政治、文化冲突的新问题。”[29]
(三)习得规划特点及分析
在语言的习得规划方面,主要是竭力解决教学媒介语问题,同时,也重视英语教育。
教学媒介语(medium of instruction)是指学校的教学语言,它是语言习得规划的重要内容,也是语言重要性的反映。中亚五国独立后都试图解决本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媒介语问题,力求以本国名义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现在各国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如下:小学阶段以名义语言为主,俄语为辅,几个较大的非名义语言为点缀;中学阶段以名义语言为主,俄语为辅;大学阶段则正好与中学阶段相反,以俄语为主,[30]主要原因是名义语言在师资、教材、参考资料以及语言的现代化和书写符号系统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如名义语言缺乏许多现代科技术语的表达,其科技文献也很少),而且,不少学生及其家长也都更喜欢选择以俄语为教学媒介语的高校(详见表6)。

表6 中亚五国高校教学媒介语使用情况(2006年) /%
中亚五国的语言习得规划主要面临如下困境:新独立的主权国家当然首先应该是发展和推广国语(即名义语言);考虑到本国的地缘结构、语言文化渊源、外交关系及为数不少的俄罗斯族国民等因素,各国又必须重视和推广俄语;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受到各国教育部门及国民的青睐,各国还不能违背这种国际大趋势及民意,也须重视英语的教育;在国内少数民族母语诉求的压力下,各国也不能太忽视少数民族语言(即非名义语言)的教育,尤其是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因此,受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各国须往“四语”(即本国名义语言、俄语、英语和本国非名义语言)教育方向发展。但是,“四语”教育对国家、学校及家庭等都将带来经济、资源及精力等方面的压力,于是,权衡之后,各国都在向“三语”教育方向发展,即重视本国的名义语言、俄语和英语教育,而相对薄待本国的非名义语言教育了。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中亚五国的语言生态内容丰富,语言政策动荡较大,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复杂,但主要缘于社会政治的动荡变化。中亚五国在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但同时,也要看到塔吉克斯坦在名义语言的种类及由此带来的周边外交关系与其余四国存在一些差异。至于中亚五国语言政策施行的效果,现在评判也许还为时过早,因为语言政策的影响是缓慢的和漫长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本文的分析中获得如下两点启示。
(一)中亚语言生态及政策与我国关系密切
中亚五国的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与我国的“一带一路”及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关系密切。中亚五国连接欧亚大陆(Eurasia),无论是在地缘政治还是在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等方面,在世界上都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于中国更是如此。因为中亚五国是中国的邻国或近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的对象国,还是中国在反恐、缉毒等领域的合作国,其中四国与中国同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土库曼斯坦除外)。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政治互信、经济互惠、人员互通都需要以文化为背景、以语言为桥梁,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去了解、研究中亚五国的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以便建立更多更牢的语言桥梁,并通过语言桥梁增进彼此的了解,尊重彼此的文化,融洽彼此关系,为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合作与发展提供科学的语言管理和优质的语言服务。
(二)重视英语、俄语和中亚五国名义语言教育
我们从中亚五国的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可知,除了各国的名义语言外,俄语和英语是该地区最重要的语言。无论是从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还是从语言活力和语言安全来看,这两种语言也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外语,需要得到教育部门的重点关注。在中国,对英语教育的重视有目共睹,但俄语教育似乎还有提高的空间。尽管我们无需全面推广俄语,但鉴于我国与俄语国家、俄语使用区(如中亚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及上海合作组织都有许多密切的政治、外交、经济、人文等联系,我国还是要重视俄语教育的发展,尤其要重视俄语教育的区域性发展,强化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的俄语教育。同时,在国内尤其是东北和西北等地区,要加强对中亚五国名义语言的学习和交流。
致谢:感谢本文责编李开拓老师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及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王辉教授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