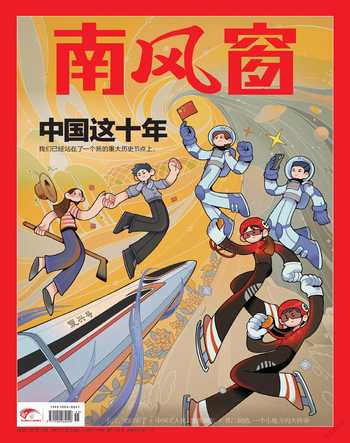为什么谷物在早期国家中这么重要?
董可馨
《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人类学家詹姆斯·C. 斯科特在新书《作茧自缚》里,延续了他一贯的价值取向和“无政府”视野,试图证明,对人类来说,国家生活的出现和延续并非理所当然,它与农耕文明的胜出关联紧密。
从一个问题开始:人类已经习惯了主食吃小麦、大麦、水稻、小米这些谷物,追溯人类历史,早期国家恰恰都是谷物国家,为什么谷物在早期国家中这么重要?为什么遍寻历史,找不到“扁豆国”“鹰嘴豆国”“芋头国”“山药国”“花生国”“西米国”?要知道,就它们的单位面积所能提供的卡路里来说,很多都超过了小麦和大麦,所需要的劳动力也不及谷物多。
这本书的英文原名为against the grain,直译为反谷。在斯科特看来,农耕文明对游牧等其他文明的胜出并不是一种进步,虽然谷物的种植使得粮食结余成为可能,人类得以在积累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和文明,但是从采集狩猎发展到农业和定居生活是人类的生命经验不断狭窄、文化和仪式意义也更为贫乏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看似驯化了农作物和饲养动物,但实际上自己也反过来被驯化。人不仅离不开它的作物,而且成为了作物的奴隶,除草、施肥、清理、浇水、保护,作物期待什么,人就要满足什么;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能否存续下去,也要依赖品种屈指可数的育成作物。
而且,由于从事农耕后人类开始定居生活,日复一日要进行长期的农业劳动,人的健康受到极大损害,跨物种间的瘟疫和疾病传播更为容易和频繁。这也是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书名“作茧自缚”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谷物有那么多的缺点,却能战胜其他农作物,在早期国家中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斯科特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只有谷物可以充当征税的基础,因为它们看得见、可分割、可估价、耐存储、易运输,可定量配给。对于计算、分割和评估来说,有着巨大的行政优势。其他的豆类、块茎和淀粉类植物,都只能满足部分,而不能兼具谷物的全部优点。
谷物生长于地上,大致在同一时间成熟,对于收税官员来说,是最便于管理的,可以一次性对全部收成进行收割、打包。假如敌军来袭,实行焦土政策也很容易,放一把火可以马上烧光庄稼,逼得农民逃亡或者饿死;要是土豆就很难了,它们藏在地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命令自己的子民,都种植马铃薯,如果敌军来了,驱散农民就没那么容易。
所以,谷物和国家的关系是:只有当先民依靠栽培谷物作为食物来源,而且没有其他选择时,国家方才可能形成。只要生存资源能够跨越多个食物链,如狩猎采集、刀耕火种、靠海吃海,国家就不太可能出现,因为征税的基础不存在。
在早期中国,国家权力只存在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内可耕种的地点。这些田地里种植着灌溉水稻,构成了早期中国的生态和政治核心地带,包围着这些中心地区的,是四散分布的游牧、狩猎采集以及游耕的群落。他们居无定所,当然也很难对他们课税。他们被定义为“生番”蛮族,是“尚未进入国家版图”的人。 又比如,在罗马人看来,所谓蛮族,区别于“文明人”的关键特征就是他们吃奶制品和肉,而不像罗马人那样吃谷物粮食。对于美索不达米亚人来说,“野蛮的”阿摩利人居然“五谷不分,茹毛饮血”。而在人类早期,这样的非谷物农业区域是大部分的,但这些地方并不和农业区隔绝,之间也存在着频繁的交流和贸易。
由于农耕国家的定居特性,所以往往需要修筑城墙把自己围起来。一堵墙的存在,意味着,有重要的东西被保护或者控制起来了。反向推论,墙体的存在,是证明某地出现过定居耕作和食物储藏的可靠指标。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必须保护自己的庄稼,防范其他人类或者动物的掠食,对于统治阶层来说,农田里的粮食和人口,也是他们权力和财富的根基,必须保护好。
对中国边疆研究甚深的拉铁摩尔曾有一观点:中国的长城的修筑,其目的不仅在于把游牧部落拒于墙外,还要将内部交税的农民阻隔在墙内。
所以在早期国家治理问题上,有两个问题很重要:其一是人口的获取;其二是对人口的控制和管理。
在第一个问题上,奴役制度发挥了核心作用。换句话说,国家谷物核心地带的扩张,是在掠夺奴隶以获取人力补给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人口最大化的要求,也使得育龄女性的生育功能成为一项重要资源,因而也催生了国家对育龄女性奴隶的捕获和驯化,从而奠定了父权制—它的核心逻辑是很残酷的。
在第二个问题上,借蒲鲁东的话—所谓被统治,指的是每一种经营、每一次交易,都必须被记录、被登记、被统计、被征税、被盖章、被度量、被编号、被评估、被授权、被警告、被预防、被修改、被纠正、被惩罚—看起来,发达的农业国家也都有早熟的官僚体制。
对于农民来说,国家的存在不是抽象的,就是上门调查人口、测量土地征收赋税的官员。他们明白,正是通过记录的保存,国家才能看见它的土地和人口。古代苏美尔人有言:你上有国王,有领主,但你真正要怕的是上门收税的。
叙述这样一部人类早期历史,斯科特的关怀是明确的—重新检视被人类视为文明核心的国家那不可置疑的地位。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的出现和存续只占很小的时间比例,集权王国更是罕见。当考古学家把视线离开金字塔顶端的伟大君主和宏伟建筑,重新发现那些构成人类生活的基底和基本单元,聚焦于人类的定居模式、贸易和交流的形态,观察降雨量、土壤结构以及生存策略,会发现,它们反而可以告诉人们更多的东西。
在斯科特看来,那些常常令人忧心的秩序的“崩溃”,实質上是更大规模同时也更脆弱的政治体,分解为较小规模但通常更稳定的构成单元。与其说它意味着某个文化的解体,不如说是那个文化的重构;更准确地说,是去中心化。正是那些更小的权力内核,才有可能长久存续;相比之下,它们所拼凑起来的王国或者帝国其实是短暂的,治国术的奇迹往往只能昙花一现。
不过,斯科特的经验更多基于人类早期历史和西方社会历史,把时间往后拉,我们却看到,中国的王朝更替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骤减,减少规模动辄达到人口的一半乃至2/3。只是到了从清末到民国的现代性转型,政治秩序重组的过程虽然同样伴随着激烈的权力较量,战争不断,但并没有发生古代王朝那样大规模的人口减少。不过,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权力较量确是那时候的核心问题,当然,最终,大一统的历史惯性再次胜出。
相比于大统一时代,斯科特对于历史的“断裂”和“崩溃”时期显然更感兴趣,也更为偏好。这些时期因为记录的缺失而留下了空白,但空白不意味着黑暗和落后。斯科特想要证明的是,正是这样的时代,反而见证了许多原来在国家治下的属民向往自由的纵身一跃,也发生了人类福祉的改善。
他的思路是:每当进入“黑暗”时代,就会出现人口的离散,而其中大多是一种逃离,躲避战争、税收、疫情、作物歉收、征召入伍。若是这样,原本在国家统治之下因密集的定居生活所可能导致的最严重损失,也可能有所挽回。而去中心化,不仅可以减轻国家所强加的负担,也可能使社会更为平等。
归根结底,斯科特的关怀是,打破权力集中的国家才会带来文化成就和文明发展的偏执,相信去中心化以及人口的离散也会带来文化生产的重组和多样态。
斯科特此前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国家的视角》《逃避统治的艺术》《六论自发性》,已经使我们熟悉了他对国家社会规划项目的批判、对平民运动的行动策略的分析、对人类的自主和自发性的强调。这本书继续提醒读者,世界是辩证的,一部人类文明史,何尝不是一部人类被驯化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