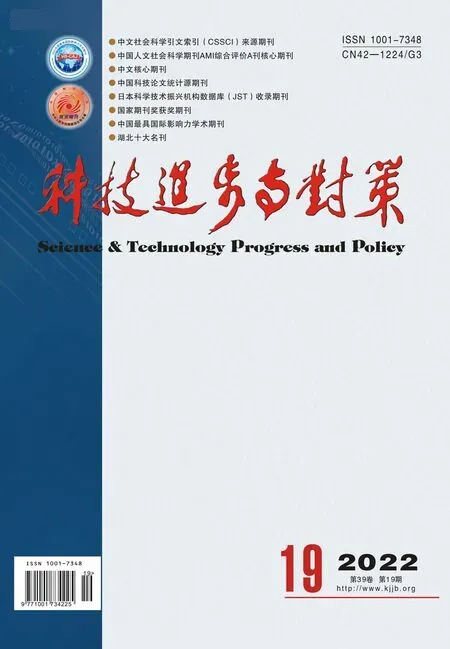中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波浪收敛规律的定量模拟与验证
曾 鹏,程 寅,魏 旭
(1.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广西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0 引言
城市群作为多个城市的集合体,逐渐成为引领我国科技发展的新动力源[1]。关于城市或城市群科技创新系统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主要集中在城市科技竞争力评价、城市群科技协同创新等方面。如有学者建立了核心城市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对核心城市科技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吴晓梅,石林芬,2005);胡翠萍[2]基于城市科技数据构建城市科技竞争力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陈诗波等[3]通过分析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协同创新基础能力,揭示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合作问题;朱鹏颐等[4]利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视窗模型研究2010-2014年各城市科技创新效率变化,并结合Malmquist指数探讨城市科技创新效率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李光龙等[5]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城市为样本,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变规律,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财政支出、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城市科技创新系统的研究较成熟,但对于科技创新系统能够承受的外界压力和干扰程度缺乏探讨,以中国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析区域科技脆弱性以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随着城市群空间集聚效应增强,城市群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日益提升。因此,本文将结合理论与实践,深入分析城市群整体的科技脆弱性,这对准确把握城市群科技创新系统敏感度、实现我国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脆弱性是指暴露于自然环境中的系统因受到压力与扰动而产生敏感性,并因缺乏足够适应能力或恢复能力导致自身受到损害的程度[6],具体包括恢复性、抵抗性、适应性、敏感性等多个方面。科技脆弱性概念由脆弱性概念衍生而来,是指科技系统在受到外界压力和干扰而产生的敏感性与恢复性(刘凯,任建兰,孙雪,等,2016)。
综合以上研究,本文认为科技脆弱性是脆弱性的一个具体分支,是指科技系统在外部环境扰动下因缺乏足够适应力而表现出的敏感状态以及在遭受扰动后的自身恢复能力。其中,敏感性由经济、社会、环境三大外部要素共同决定,反映科技系统在遭受外部环境扰动时表现出的敏感程度;恢复性由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基础三方面共同决定,反映科技系统在遭受外部不利影响后能够恢复到原有状态的能力。因此,科技脆弱性是敏感性与恢复性的综合反映。敏感性越强,科技系统脆弱性越高;恢复性越强,科技系统脆弱性越低。
本文的理论贡献包括以下方面:第一,运用几何推导并结合数值模拟方法,研究我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演变规律以及时空演化格局;第二,综合运用VHSD-EM法构建评价模型,对我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第三,从城市群发育角度,设计科技创新系统风险防御模型以及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计算方法,量化分析核心城市不断联合周边城市,进而形成城市群并不断扩张的演化过程。
1 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收敛规律的理论解析与几何表达
1.1 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呈波浪性收敛原理
我国经济发展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空间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与城市群成为重要的空间载体。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出,“应当建立健全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机制和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协调布局、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享、生态共建、环境共治”,为推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重要引领。因此,城市群科技创新系统发展就是中心城市通过与周边城市联合、降低科技系统脆弱性的过程。基于城市群的创新引领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本文提出城市群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范围,逐步具备面对不确定性的抗风险能力,但过密的内在联系易使城市群科技系统陷入锁定而缺乏有效应变[7],特别是面临外部冲击时会因科技系统的结构性衰退导致城市群科技系统脆弱性较高。伴随新城市不断加入,科技创新系统不断演化到一个合适状态,其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逐步趋于稳定。因此,随着城市间不断联合,形成一体化协调发展体,其科技系统脆弱性也呈现振幅缩小并最终趋于稳定的发展形态,具体见图1。

图1 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演变规律Fig.1 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ulnerability in urban agglomeration
当只有一个城市时,城市科技系统对外界反应较敏感,同时,科技系统本身的恢复能力也处于较低水平,此时城市科技系统尚不具备抵御外界潜在风险的能力。当多个城市形成城市群且发展到一定规模和程度后,城市间会产生集聚效应并通过整个城市群的一体化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但在城市集聚初期,由于新城市加入需要时间磨合,使得城市群科技系统面对外部冲击时处于较弱状态,因此整体科技脆弱性较高。此后,伴随磨合期结束以及新城市不断加入,城市群联合防控风险能力逐渐趋于稳定,科技系统抗风险能力和自身恢复能力提高,科技脆弱性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推动城市联合、形成一体化协调发展,是促使城市群科技脆弱性降低并维持相对稳定状态的重要路径。
综上所述,研究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演变规律以及科技系统融合扩张过程,对于解决“如何实现城市群科技系统稳定性”、 “城市群发展过程中核心城市如何联合周边城市共同承担风险”、“城市群内部科技系统如何顺畅运行”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2 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波浪式收敛曲线函数模型
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演化规律是指在时间序列下随着时间推移和联合城市数量增加而形成的非线性复合变化曲线,也称为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波浪收敛曲线。根据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演化原理,利用数理函数进行如下表示:

(1)
其中,Vt表示t时期城市群科技脆弱性;c表示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最终稳定值;Δt是函数波动周期,且Δt=π/β;α是三角函数振幅,表示城市群科技脆弱性阻滞系数;β表示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周期系数,π/β为三角函数频率。为了提高数理模型准确性,对其进行优化。对核心城市分别赋予科技脆弱性初始时间t0和初始值V0,分别代表初期时间和初期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指数。优化后的函数曲线模拟公式为:

(2)
X=xij(tk),i=1,2,…,m;j=1,2,….n;k=1,2,…,K
(3)
2 研究设计与计算
2.1 城市群样本选择
近年来城市群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空间组织形式上的新型主体单元[8]。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明确将城市群列为未来国家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本文参照国务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各省(直辖市、区)批复印发的19个城市群发展规划文件,以重点建设的五大国家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稳步建设的八大区域级城市群(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天山北坡)、引导培育的六大地区级城市群(晋中、呼包鄂榆、滇中、黔中、兰西、宁夏沿黄),共计227个城市为案例样本进行研究。
2.2 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以考察中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为目的,遵循全面性、系统性、典型性和数据可得性等原则,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科技脆弱性评价体系,具体包含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维度,共涉及经济要素、社会要素、环境要素、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基础6个要素层以及25个指标层。
本研究构建的科技脆弱性指标体系分为敏感性和恢复性两个维度。其中,敏感性反映科技系统对外界不利扰动的敏感程度,主要包括经济、社会、环境三大外部要素影响。本文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等指标表征经济要素,选取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人口密度等指标表征社会要素,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比重指数、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等表征环境要素。恢复性反映科技系统在遭受外部环境扰动后的系统自我恢复能力,主要由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基础三大系统要素共同决定。其中,选取科技强度指数、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比重等作为科技投入替代指标,选取发明专利授权量、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等作为科技产出替代指标,选取科学技术人员、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等作为科技发展基础替代指标。科技脆弱性最终取决于敏感性与恢复性的共同作用。
2.3 模型构建
2.3.1 “纵横向”拉开档次法(VHSD)
根据时间序列函数,可将科技脆弱性研究涉及的m个城市、n个基本指标和K个年份数据排列成矩阵,如下所示:
X=xij(tk),i=1,2,…,m;j=1,2,…,n;k=1,2,…,K
(4)
其中,X=xij(tk)表示第i个城市在第k年的第j项指标值。
城市科技脆弱性时序立体数据如表1所示。其中,ui代表第i个城市。

(5)

表1 城市科技脆弱性时序立体数据Tab.1 Time-series three-dimensional data of urb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ulnerability

其次,设定科技脆弱性评价函数为

(6)
式中,δj为指标权重,zi(tk)为样本i在第k年的综合评价值。利用公式(7)确定指标权重。

(7)

当δTδ=1时,取H的最大值对应的特征向量时,σ2得到最大值。权重向量δj由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
2.3.2 熵值赋权法(EM)
运用极差标准化法处理指标数据:

(8)
其中,第i个样本第j项指标在第k年的指标值经过极差标准化后得到yijk。
计算指标值的变异程度:

(9)
其中,第j项指标下第i个评价对象在第k年的特征比重表示为vijk。
由此,计算第j项指标的EM值,Ejk表示为:

(10)
其中,当vijk=0或1时,令vijkln(vijk)=0。令指标的差异系数为Djk,则:
Djk=1-Ejk
(11)
指标EM权重计算公式为:

(12)
2.3.3 VHSD-EM评价模型基本原理及检验
VHSD-EM分析可将通过VHSD法与EM法分别计算出的指标权重相结合,得到最终权重并计算各指标综合评价值。运用MATLAB(R2016a)对VHSD法和EM法计算结果进行Spearman相关性检验。表2显示,结果具有较强正相关性,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由此可知VHSD和EM法计算结果具有较高一致性。因此,本文建构的VHSD-EM模型具有较好稳健性。

表2 Spearman相关性检验结果Tab.2 Spearman correlation test results
将由VHSD法与EM法确定的权重δj和wjk组成如下矩阵:

(13)
每个指标的最终权重Wjk是由Cjk中的每行元素进行算术平均值得到。
将上述所得标准化值与相关权重加权求和,得到科技敏感性指数Si和科技恢复性指数Ri,由此计算城市科技脆弱性为:

(14)
2.4 城市群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实证方法
2.4.1 城市群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
通过构建城市群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模型反映科技系统风险分担需求强度,具体可分解为联合城市的科技脆弱性开方比上联合城市的科技强度指数开方与城市空间直线距离的平方。因此,不同城市科技系统的风险分担需求强度可表示如下:

(15)

(16)

2.4.2 城市群科技系统联合防控门槛
利用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模型计算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将所有城市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均值的1/2作为衡量核心城市是否应联合新城市提高科技系统联合防控门槛的标准,计算公式如下:

(17)
其中,λij表示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科技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Fij表示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i表示评价年数,j表示评价数量。
2.5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样本数据选为2009-2019年,由于城市群样本中包含部分地级市代管的县级市或省直管的县级市,数据样本可能出现重叠,同时,部分城市数据缺失严重,因此均予以剔除,最后选取201个地级市数据。其中,城市人口、经济总量与科技相关数据均来自2010-2020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数据来自201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缺漏数据通过搜寻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或各省市统计局官网予以补充。
3 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实证结果分析
3.1 城市科技脆弱性“纵横向”拉开档次法与熵值赋权法(VHSD-EM)分析
首先通过VHSD法中的综合评价函数计算各指标权重系数,再通过EM法将历年城市的各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得出各年份的评价指标值变异程度,进而运用熵权法计算各项科技指标权重系数;接着,对VHSD法中的权重系数与EM法中的权重系数取算术平均值,得到最终权重系数;最后,将各城市指标数据结合权重系数,通过线性加权法逐层进行加权汇总,得到历年中国城市群各城市科技脆弱性指数,而后对各城市科技脆弱性进行评价。根据历年各城市科技脆弱性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具体见表3。
由表3可知,2019年与2018年科技脆弱性分值最低的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深圳,其余年份最低值由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包揽,说明以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为代表的城市科技系统受外界不利影响与损害的可能性较低,即科技脆弱性较小。2019年与2018年科技脆弱性分值最高的是哈长城市群中的松原,其它年份除2015年外均由哈长城市群包揽。从分值看,哈长城市群科技系统运行情况不容乐观。
将城市群所辖城市的科技脆弱性分值进行算术平均,得到我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综合分值,并利用Stata将各城市群科技脆弱性评价值进行算数平均,得到城市群整体的科技脆弱性评价值并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3。同时,利用ArcGIS10.2绘制中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分级图,见图2。根据图表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差距较大,其中,重点建设的国家级城市群的科技脆弱性较低,特别是隶属于五大国家级城市群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科技脆弱性均处于较低水平,而哈长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的科技脆弱性均处于较高水平。从空间演化格局看,东部沿海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科技脆弱性较低,说明这些城市的科技系统受到外界经济、环境、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较小,对外界压力的敏感度也较小,同时,这些城市的科技系统结构较稳定,受到不利影响后的恢复能力也较强。

表3 城市科技脆弱性描述性统计结果Tab.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vulnerability of urb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图2 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分级结果Fig.2 Resul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ulnerability classifica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3.2 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演化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整体振幅渐小并最终趋于固定值。其中,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显著低于其它城市群且波动幅度较小,说明珠三角城市群科技系统较为稳定,面对外界压力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而哈长城市群科技系统脆弱性整体上略高于其它城市群,防御外界风险的能力较差、遭受破坏时的恢复能力也较弱。
3.3 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全局分析
以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为样本,绘制中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空间演化趋势,由于篇幅限制,仅展示2014年和2018年的趋势面分析,见图3。图中,X轴表示东方,Y轴表示北方,线1与线2分别代表我国城市群不同科技脆弱性在东西、南北方向上的投影。
从整体趋势看,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在东西方向上呈现“东低西高”的空间特征,表明东部地区城市群的整体科技脆弱性低于西部地区;在南北方向上呈现总体向下的空间发展趋势,即东南部两端较低,表明东南部地区城市群的整体科技脆弱性低于东北部和西北部地区。
从投影弧度看,东部地区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投影弧度与西部地区城市群极其相似,表明东部地区城市群的科技脆弱性差异程度也与西部地区相似;北部地区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投影弧度相较于南部地区更陡峭,表明北部地区城市群不仅整体科技脆弱性低于南部地区,而且北部地区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差异程度相较南方地区也更显著。
从时间序列看,2012年以前南北方城市群科技脆弱性相差不大,2012-2018年南北方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差距逐渐增大,特别是2014年后中西部地区科技脆弱性呈降低趋势。从整个时间范围看,东南部地区的科技脆弱性都优于其它地区。整体而言,我国东部、南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科技脆弱性显著低于华中、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城市群。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我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演化情况,结合不同城市群所辖城市的科技脆弱性值,运用ArcGIS10.2软件绘制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我国城市群脆弱性区域分级图,具体见图4。由于篇幅限制,仅展示2014年和2018年的演化图。

图3 城市群科技脆弱性空间演变趋势Fig.3 Spatial evolution tre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ulnerability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图4 我国城市群各城市脆弱性分级演化情况(2014年与2018年)Fig.4 Urban vulnerability classification evolu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2014 and 2018)
由图4可知,从整体空间演化格局看,内陆地区城市群科技脆弱性稍处劣势,而东南沿海地区城市群科技脆弱性较低,这与城市群区位优势、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政策密切相关。从时间演化格局看,整体来讲,城市群科技系统稳定性稳步提升,低科技脆弱性城市数量明显增多,高科技脆弱性城市数量明显减少。
4 城市群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实证分析
根据城市群分布,可划分为三大类城市群,具体包括5个国家级城市群、8个区域级城市群、6个地区级城市群。鉴于篇幅和图像空间有限,本文仅展示2009-2019年国家级城市群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高于科学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的城市,如图5所示。
从图5(a)- 5(d)中可以看到,2009-2019年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整体呈波浪式变化并最终趋于稳定,超过门槛值则表明该城市已融入其所属城市群,开始联合其它城市进行科技风险防控。2009-2019年国家级城市群科技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高达7.37,科技风险联合防控强度超过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的城市达到23个,其中,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等城市在2012年之前就已经融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南京、芜湖、镇江等城市相继于2013年、2014年融入;北京、天津处于京津冀城市群的中心,邻近的廊坊市于2009年融入该城市群,唐山、张家口于2014年才融入京津冀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联合较早,如珠海、佛山、惠州、中山等城市早在2009年就已融入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越过联合防控门槛值的城市仅有鄂州、孝感,它们相继于2014年、2015年融入其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各城市科技系统融合程度还不高。

图5 城市群科技风险联防过程演化Fig.5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isk joint prevention proces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区域级城市群科技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为0.893,而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高于联合防控门槛值的城市有38个,其中,铁岭早在2009年就已融入辽中南城市群,盘锦和葫芦岛相继于2012年、2013年融入该城市群;淄博、烟台、潍坊、泰安、德州早在2012年之前就已融入山东半岛城市群,东营、济宁、威海相继于2012年、2013年融入;海峡西岸城市群中的莆田、泉州、漳州早在2009年融入城市群,温州于2014年融入;哈长城市群中仅有吉林于2013年融入;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于2012年前就已融入中原城市群,晋城、漯河、周口于2012年融入该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中仅有咸阳早于2012年融入,铜川、商洛在2012年融入,宝鸡、渭南于2013年融入;北部湾城市群中的钦州、崇左于2012年融入,北海、防城港于2014年融入。
地区级城市群科技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为0.613,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高于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的城市有15个。其中,晋中城市群中只有临汾才于2014年融入,其余越过联合防控门槛的城市早在2009年就已融入;呼包鄂榆城市群中仅有包头于2014年融入;黔中城市群中仅有毕节于2012年才融入,其余越过联合防控门槛的城市均于2012年之前就已融入;兰西城市群中除海东在2014年才融入外,其余城市均于2012年前融入;宁夏沿黄城市群除吴忠早在2009年就已融入外,其余城市相继于2012年、2013年融入。综上可见,各城市融入时间大致与城市群发展过程同步,其中,国家级城市群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远高于其它两个层级城市群。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利用ArcGIS10.2绘制中国城市群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图,由于篇幅限制,故未展示。
由城市群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图可知, 2012年前越过科技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的城市有无锡、常州、苏州、杭州、宁波、珠海、佛山等42个城市;在2012年越过联合防控门槛值的城市有芜湖、威海、聊城、济宁、晋城、漯河、钦州等17个城市; 2014年后越过科技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的城市有镇江、唐山、张家口、鄂州、日照、温州、包头、鹤壁、宝鸡等18个城市。这些说明城市群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与所辖城市科技脆弱性正相关,与城市间距离负相关。
5 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波浪式收敛曲线模拟与验证


表4 中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波浪式变化曲线最优函数表达式Tab.4 Optimal function expression of wave-like change curv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ulnerability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China
拟合所用程序代码如下:
t=[t0;t1; t2; t3; …;tn];
y=[y0;y1; y2; y3; …;yn];
p=fittype('a+(b*sin(c*(t-t0)))/(d*(t-t0))', 'independent', 't');
plot(f,t,y);
f=fit(t,y,p);
cfun=fit(t,y,p)
以此绘制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模拟图,见图6。从图6可以看出,三大类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变化曲线与2009-2019年城市群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演化曲线具有较大相似性,说明从整体上看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演化曲线拟合效果较好,反映出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呈波浪式变化发展趋势,适合采用科技脆弱性变动函数模型分析与预测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发展走势。其中,由图6可以看出,国家级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波动较显著且波动频率适中,区域级城市群与地区级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波动幅度比国家级城市群平缓且波动频率低于国家级城市群。
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及讨论
本文通过构建科技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收敛规律及联合扩张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总体呈波浪式收敛特征,最后逐渐降低并趋于一个最佳稳定值,此外,不同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差距较大,重点建设的国家级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最低。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科技脆弱性均稳定在较低水平。另外,科技脆弱性长期处于较高值的是哈长和兰西城市群,科技脆弱性下降速度最快和最慢的城市群分别为宁夏沿黄与兰西城市群。通过对城市群科技脆弱性进行全局空间分析发现,我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分布具有不均衡性,主要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城市群科技系统的稳定性优于西部地区[9]。不同城市群科技发展质量差距显著,国家级城市群科技发展质量较高;脆弱性低值区由国家级城市群逐步向区域级和地区级城市群扩张。原因在于不同城市群区位条件不同,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国家级城市群政策比地方性城市群政策对城市群发展的扶持力更大[10]。
(2)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整体上趋于波浪式收敛且存在联合防控门槛效应,目前国家级城市群已有较多城市联合其它城市进行风险防控,区域级和地区级城市群则较少。研究发现,2009-2019年全国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整体上呈波浪式变化并最终趋于稳定形态;2009-2019年国家级城市群科技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高达7.37,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超过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的城市达到23个;区域级城市群科技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为0.893,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高于联合防控门槛值的城市有38个;地区级城市群科技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只有0.613,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高于系统联合防控门槛值的城市有15个。总体而言,各城市科技系统向城市群融合的时间点与城市群发展过程大致同步,其中,国家级城市群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远高于其它两个层级城市群。

图6 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波浪式收敛曲线拟合结果Fig.6 Wave-type convergence curve fitting results of technological vulnerability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3)各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拟合曲线的相似性较大,与各城市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演化趋势一致,且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演变规律与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收敛函数曲线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收敛曲线模拟效果较好。其中,国家级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最低,区域级城市群次之,地区级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最高。
6.2 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我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的分析,可以为我国城市群科技系统运行提供参考,有助于提升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科技系统稳定性,促进我国城市群科技进步。
第一,探索一体化科技创新规划。首先,各级政府应将企业、科研机构及大学、中介机构等联合起来,不断解决产学研过程中的困难,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形成辐射城市群其它城市的科技创新网络,提升城市群科技系统一体化程度[11];其次,在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中,形成市镇联动;最后,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手,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12]。
第二,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基于我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逐渐降低并趋于一个最佳稳定值,但仍存在区域差异的现实,具体建议如下:首先,城市群各级政府应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工作迈上新台阶[13];其次,不断创新发展路径、厚植区域发展优势,为我国经济发展开辟新空间;最后,应当激活人才福利,倡导“工匠精神”,激发人才创造力。
第三,孕育世界级科技创新生态。由于我国国家级城市群科技风险分担需求强度远高于其它两级城市群,因此建议如下:首先,城市群应当构建系统、开放的科技创新生态[14],形成融合科技、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等多维度价值的科技创新评价体系;其次,面向国际发展培养新型高端科技人才;最后,鼓励本土企业加大科技创新、调整与优化跨国布局,使我国城市群更具国际竞争力[15]。
第四,着眼系统性科技创新治理。首先,城市群应加强科技数据基础设施建设[16];其次,鼓励社会机构将科创成果推广科普给大众;最后,营造有助于科技人才涌现的良好环境,使他们能够为破解难题、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提供有效帮助。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对中国城市科技脆弱性进行了综合评价,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第一,中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指标体系构建有待完善。城市群作为区域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需从动静态结合角度体现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发展规律,但由于数据获取和研究尺度的局限性,相关研究有待深入。
第二,对中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波浪收敛规律的形成原因缺乏深度分析。囿于宏观经济数据获取的有限性,虽能保证数据分析结果的正确性,但未充分开展关于中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波浪收敛规律的原因分析,后续可进一步收集相关数据予以拓展。
第三,在数据预处理和计算过程中所用方法较单一。本文应用VHSD-EM法计算中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水平,计算过程中对指标体系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虽降低了数据偏差,但难免存在个别数据差异较大;在熵值法计算中,根据各指标权重相较于指标体系的重要性进行了评定,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但也存在权重漏洞,易造成结果偏差。因此,关于权重的处理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通过分析中国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水平,有助于为我国城市群科技系统运行提供参考,提高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但本文对城市群科技脆弱性波浪收敛规律的内在运行逻辑未作进一步研究,因此未来研究可从城市群科技脆弱性影响因素及产生原因进行深入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