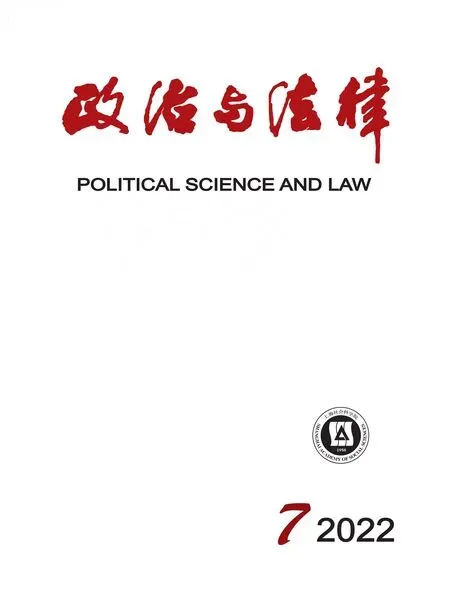美国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国家监管、强制性自我监管与刑事激励
梁 涛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一、问题的提出
合规的英文表述为Compliance,通常是指通过法规之遵守,主动预防违规风险(即遭受民事制裁、行政处罚以及信誉受损的风险)。〔1〕参见张远煌:《刑事合规国际趋势与中国实践》,载《检察日报》2019 年11 月2 日,第3 版。企业合规(Corporate Compliance)则主要是指企业为有效防范、识别、应对可能发生的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整套公司治理体系。〔2〕参见陈瑞华:《企业合规的基本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1 期。更直接地说,合规是企业用来确保员工“不违反适用的规则、条例或规范”所采用的一套流程。〔3〕See G.P.Miller,The compliance Function: An Overview,Law &Economics Research Series Working Paper No.14-36,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Nov.2014),https://www.law.nyu.edu/sites/default/files/upload_documents/The%20Compliance%20 Functiion%20an%20Overview.Miller.pdf#,last visited on Mar.18,2022.企业合规,起源于美国,并快速扩展至法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特别是随着ISO 37301: 2021《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已成为全球法律现象。
在我国,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方式,企业合规是一个舶来品。因此,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域外各国的企业合规模式。如张远煌将全球企业合规的立法与司法归纳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刑事激励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独立成罪模式、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司法审查模式和以法国为代表的强制合规模式四种类型。〔4〕参见张远煌:《刑事合规国际趋势与中国实践》,载《检察日报》2019 年11 月2 日,第3 版。刘晓光、金华捷和涂龙科则通过考察全球企业合规,分别总结出“三模式”和“四模式”。“三模式”为针对企业设置专门的监督过失罪名,实体层面作为责任加减的情节及程序上的不起诉。〔5〕参见刘晓光、金华捷:《企业刑事合规本土化转化探索思考》,载《检察日报》2021 年3 月31 日,第3 版。“四模式”则是立法上设立专门罪名,指控机关程序上分流,审判机关量刑从宽,以及在犯罪论体系中确立刑事合规评价。〔6〕参见涂龙科:《企业刑事合规评价的模式与选择》,载《检察日报》2021 年3 月23 日,第3 版。在域外各国普遍建立起各具特色的企业合规制度之时,我国构建本土化的企业合规制度的条件也趋于成熟。陈瑞华认为条件成熟主要表现为:首先,我国企业面临越发严格的国际合规管理要求;其次,我国的行政机构施加了强大的监管压力;最后,我国引入了西方公司治理理念。〔7〕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合规激励模式》,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6 期。
因为我国还未起草与企业合规相关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现有的企业合规研究主要是基于比较法的视角,聚焦于介绍域外经验,即域外各国是如何开展企业合规的,域外各国的模式对中国发展企业合规具有哪些借鉴意义。关注域外各国企业合规具体制度设计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更有必要探索隐藏在企业合规制度构建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因此,笔者以企业合规制度的发轫国美国为样本,通过考察美国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及发展过程,探究美国是如何推动企业合规发展以及美国在制度构建过程中的国家治理逻辑,并指出其对当今我国构建和发展企业合规制度的借鉴意义。
二、企业合规的源起:对国家监管的回应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美国一跃成为了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在这一时期,美国不仅完成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而且实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在经济取得空前繁荣的同时,美国社会也发生了一场深刻变革。由于美国政府实施自由放任的政策,过度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信奉无为而治,市场出现了失灵的状况: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并垄断在少数寡头手中,经济发展呈现出无序和失控状态。这使人们意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对市场不加管束不仅会造成市场垄断,经济资源无法实现有效配置,还会威胁社会公正,加大社会贫富差距,比如垄断寡头漠视职工权益,食品加工业无视消费者健康,企业贿赂立法机关等。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意图通过积极的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的缺陷,具体表现为以国家监管的方式迫使企业约束其行为,以合乎法律规范。
在萨缪尔森看来,国家监管是指国家通过颁布法律法规以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施加影响,进而实现政府对企业的调控与限制。〔8〕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高鸿业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年版,第864-865 页。实践中,美国政府通过颁布法律对企业进行监管以1877 年“穆恩诉伊利诺伊州案”为标志。1871 年,伊利诺伊州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谷物储存商不仅必须领取从业执照,而且其谷物仓库储量不得超过该州设定的最高储粮量,所收取的费率也不得超过规定的上限。拥有私人谷物仓库的穆恩和史考特因设定了高于上限的服务费率而被起诉。二人败诉后,以该法案干涉了他们的私人企业为由提起上诉,而后,最高联邦法院判决称当私人财产被用来服务公共利益时,必须遵守公共法规,〔9〕参见笪素林:《美国政府监管制度的演进及其内在逻辑》,载《江海学刊》2007 年第5 期。这一判决在实践上开启了政府通过颁布法律实现对企业的监管〔10〕参见笪素林:《美国政府监管制度的演进及其内在逻辑》,载《江海学刊》2007 年第5 期。和对经济的规制〔11〕参见邓峰:《组织、市场与政府的协调与调整——经济法的回顾与展望》,载《清华法治论衡》2005 年第2 期。的开端。
事实上,美国政府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引导企业合规的决心和努力远不止如此。1887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被视为最早以合规为导向的规则《商务管制法》(Act to Regulate Commerce)。〔12〕值得注意的是,1887 年美国联邦政府为加强州际监管所颁布的法律并非《州际商业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而是《商务管制法》。《州际商业法》直至1920 年才通过《交通法案》的修改而落地。参见方堃:《论美国独立管制委员会的兴衰》,华东政法大学2012 年博士学位论文。该法案首次对经济监管作了详尽规定,对后续的监管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有效解决州际贸易开始后日益严重的铁路问题(如铁路运输价格不合理且具有歧视性),加强铁路运输管制,该法律还创建了联邦政府第一个独立管制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ICC),这意味着具有现代意义的监管机构由此产生。以管制铁路运营为代表的国家监管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催生出的贪婪与垄断削弱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值得注意的是,监管的目标并不是惩罚,而是使企业的行为符合规则或标准。〔13〕See S.S.Simpson,Corporate Crime,Law,and Social Contro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86.可以说,我们现在对合规的兴趣即源自于监管者和立法者确保企业履行法定义务的努力。〔14〕See R.C.Bird &S.K.Park,The Domains of Corporate Counsel in An Era of Compliance,American Business Law Journal,Vol.53,p.203(2016).但是,作为独立管制机构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在创设之初因受司法权的强势打压,并没有太多实权,州际商务委员权力的巩固与增强有赖于20 世纪初三部法律的颁布。即1903 年颁布的《爱尔金斯法》(Elkins Act)规定铁路公司应对不合法的差别待遇负责,该法案对规制铁路公司的差别待遇起到了重要作用;1906 年颁布的《赫伯恩法案》(Hepburn Act),授权州际商务委员会获得交通管制问题上的市场定价权、监督权和裁决权;1910 年颁布的《曼—埃尔金斯法》(Mann-Elkins Act),授权州际商务委员会终止了铁路公司的普遍提价权,运价的修改取决于商务委员会的动议。州际商务委员会自此成为了集行政执法、准立法与准司法于一身的“第四部门”,是联邦政府最有权力的管制机构之一。〔15〕参见王立平:《规制与放松规制:美国铁路体制改革的启示》,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 年第6 期。虽然《商务管制法》的颁布及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设置只是为应对复杂的铁路形势而采取的权益之计,但是它们与之后颁布的一系列涉及企业监管的法律文件和之后设立的一批规制经济的独立管制机构一道,共同塑造着国家对企业监管的实践,进而促使企业履行法定义务,合乎法律规范。
此后,包括1890 年的《谢尔曼法案》(Sherman Act)、1906 年的《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The Pure Food and Drugs Act)、1913 年《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和1914 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等在内的、旨在强化政府对企业监管的法律文件相继颁布,并通过创建州际商务委员会、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联邦储备局、联邦贸易委员会等联邦管制机构的方式来遏制具有危害的过度商业化行为。美国联邦政府由此分别获得对交通基础设施、食品与药品、银行、虚假与欺诈的商业活动和垄断行为的控制。〔16〕参见宋华琳:《美国行政法上的独立规制机构》,载《清华法学》2010 年第4 期。
以美国联邦政府对食品、药品领域的监管为例,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于1904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屠场》(The Jungle),其中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中广泛存在的食品质量堪忧、劳工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恶劣等违法现象。该小说引起了全美的震动,民众对此非常愤怒。民众的愤怒切实推进了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监管改革,加快了国会的立法脚步。〔17〕参见[美]斯蒂芬·罗塞夫等:《欲望之狮:美国的白领犯罪与掠夺》,廖斌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5 页。其实,推动联邦政府实现对食品、药品领域的有效监管并非仅是消费者的单方诉求,以亨氏食品公司创始人亨利·汉斯(Henry Heinz)为代表的企业家们同样向国会表达了尽快出台全国性的规制食品生产的法案的诉求。在他们看来,各州不统一的监管法律与掺杂、掺假食品的泛滥也是对合规经营的企业的威胁。合规经营企业与一般消费者共同的利益促使二者“无条件支持”《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的颁布和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其中,《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中载明对食品和药品行业内的掺杂掺假、虚假商标等行为进行管制,并禁止这类产品在国内生产、运输和销售,对违反上述规定的企业苛以罚金刑。〔18〕参见吴强:《转型时期美国食品药品的法律监管研究——以1906 年《联邦食品与药品法》的出台为中心》,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12 期。因《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对保护食品、药品企业的市场利益和维护一般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均有助益,整个社会对联邦政府在更广泛的领域施加监管满怀希望。〔19〕参见卢玮:《美国食品安全法制与伦理耦合研究(1906-1938)》,华东政法大学2014 年博士学位论文。
事实上,美国政府也从未放弃致力于将合规经营的理念向更广泛的领域、更多的企业扩展的努力。1914 年,美国国会又分别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 of 1914)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以响应威尔逊总统希望国会通过新的反托拉斯法的建议,在他看来,托拉斯需要被管制,以防止被肆无忌惮的滥用,这是托拉斯存在下去而不被解散的前提。〔20〕参见王淑丽:《1900-1917 年美国联邦政府干预经济问题初探》,载《河北学刊》1994 年第5 期。其实,早在1890 年,《谢尔曼法案》就规定对限制、阻碍商业贸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惩处,并对企业进行监管以杜绝市场垄断行为,此外还授权司法部就反托拉斯案件进行调查,向法院起诉。〔21〕参见邢才:《美国的反垄断法:百年经验与总结》,载《唯实》2000 年第7 期。另外,美国国会还通过法案设立公司管理局这一专门机构对木材、石油、钢铁和烟草等行业内的垄断组织行为进行调查、研究,凭借舆论和司法施加压力,以实现对托拉斯经济活动的监管与干预。〔22〕参见王淑丽:《1900-1917 年美国联邦政府干预经济问题初探》,载《河北学刊》1994 年第5 期。1914 年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进一步强化了《谢尔曼法案》中的反托拉斯规制,对商业竞争中的诸如反竞争协议、削弱竞争的合并与价格歧视、独家交易与捆绑交易以及“连锁”董事等问题进行具体可操作的规定,被视为《谢尔曼法案》的重要补充。〔23〕参见张淑华:《1890-1914 年美国联邦政府反托拉斯政策述评》,载《泰山学院学报》2004 年第1 期。《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则在同年确定成立独立管制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基本接管了原公司管理局的工作,权限还得到了进一步扩张。在某种程度上,该委员会对各类企业所具有的监管权力与州际商务委员会对铁路运输行业所具有的监管权力相当,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规范和监管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不公平的、反竞争的商业行为,迫使企业合规经营。
第一波监管浪潮结束后,美国政府对企业的监管有放松趋势,所以20 世纪20 年代并没有产生重要的新监管法案,但也未对政府之前的监管政策予以否定,甚至对先前通过的法案进行了完善,〔24〕See S.S.Simpson,Corporate Crime,Law,and Social Contro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94.比如1920 年通过的《运输法案》将《商务管制法》更名为《州际商业法》。
美国政府放松监管的时间很短,随后便开启了第二波监管浪潮。20 世纪30 年代,美国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经济遭受空前破坏,商业被指应为此负责,企业更是被视为一股不稳定和不负责任的力量,需要严格控制。〔25〕See R.S.Karmel,Regulation by Prosecution: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vs.Corporate America,Simon &Schuster,1982,p.4.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强调政府需对经济施加更大的管控。
在新一轮监管潮中,首当其冲的是证券行业。为恢复投资者的信心,修复崩溃的证券市场,美国联邦政府决心对先前证券市场中普遍存在的恶性竞争和各地监管者对违法行为的容忍予以整改。为此,《证券法案》(the Securities Act)和《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相继于1933 年和1934 年出台,二者共同构成了美国证券监管的基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得以成立。在美国联邦政府对金融行业施加的监管中,合规监管是核心,即银行是否忠实执行了监管机构所制定的法律法规。〔26〕参见肖远企:《合规管理模式的变迁路径及其启示》,载《银行家》2006 年第9 期。也正是在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过程中,合规一词被首次提及。〔27〕参见万方:《企业合规刑事化的发展及启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 年第2 期。具体来说,《证券法案》主要规制证券发行一级市场,为证券注册、公开发行制定详细的流程和具体的信息披露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民事、行政、刑事制裁规则以规范证券发行中存在的虚假与欺诈。《证券交易法》则主要规制证券交易二级市场,亦如《证券法案》中规定的证券发行强制披露义务一样,要求上市交易后的信息需强制持续予以披露。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有助于防止虚假陈述、内幕交易以及操纵市场行为的发生,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实现国家对证券交易市场的监管。最后,《证券交易法》还创设了独立管制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具体负责执行以上规定,规范证券市场。
信奉实用主义的美国联邦政府除了对金融业加强监管外,还通过建立其他专业化监管机构,如规制电话、广播、电视产业的联邦通讯委员会(1934 年)、监管水电等能源的联邦电力监管委员会(1935年)、协调劳资关系的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1935 年)、管控航空公司成立和航线申请及运营价格的民用航空委员会(1938 年)等介入工业生产,克服市场失灵,规制社会经济生活。〔28〕1930 年代成立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联邦能源委员会(时称联邦电力监管委员会)、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和民用航空委员会与第一波监管浪潮中成立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并称为七大规制机构。

表1 美国主要监管法规、监管机构及主要职能(19 世纪末至20 世纪中期)
通过考察美国企业合规的源起可知,自19 世纪末始,美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过加强国家监管的方式促使企业有序参与市场竞争,使其行为合乎法律规范。企业不得不开始探索建立合规制度以应对国家的强监管。所以,企业合规也被认为是企业在监管部门施加压力后被迫进行自我监管和自我治理的方式。〔29〕参见陈瑞华:《企业合规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52 页。在这一时期,美国建立企业合规制度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为通过立法〔30〕如《商务管制法》《谢尔曼法案》《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联邦储备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证券法案》等。和成立独立管制机构〔31〕如州际商务委员会、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储备局、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联邦电力监管委员会、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民用航空委员会等。两种手段加强对企业的监管,迫使企业合规;其二为率先推动关系国计民生(食品与药品等)、易形成垄断(铁路运输、银行、通讯、能源和航空等)和信息不对称(证券等)的行业实现合规,进而带动全行业的合规;其三为在加强监管,推动企业合规的过程中始终秉承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每个领域法律的颁布与管制机构的成立都是为处理该领域的危机而应运而生。
三、企业合规的新进路:由国家监管向自我监管的转变
通过国家加强监管的方式迫使企业履行法定义务、合乎法律规范的效果并不理想,事实上还往往因理论依据不足、政治环境差、糟糕的计划与执行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32〕See P.N.Grabosky,Counterproductive Regul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w,Vol.23:4,p.347-369(1995).布雷思韦特也认为对企业违法行为的过度监管将导致更低而不是更高水平的合规。〔33〕See John Braithwaite,To Punish or Persuade,SUNY Press,1985,p.12.过度监管将导致企业否认和掩盖违法行为,疏远监管机构,使监管系统效率低下。〔34〕See Toni Makkai &John Braithwaite,Reintegrative Shaming and Compliance with Regulatory Standards,Criminology,Vol.32,p.361-386(1994).此外,国家也无力负担充分履行监管职责所花费的昂贵成本,〔35〕See J.Braithwaite,Enforced self-regulation: A New Strategy for Corporate Crime Control,Michigan law review,Vol.80:7,p.1466-1507(1982).例如,紧张的财政无法保证政府监管人员能够定期检查工作场所可能存在的安全违规行为、环境问题、账簿造假或产品缺陷。因此,企业的自我监管就成了国家监管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
在监管企业方面,因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对自身的商业惯例与潜在的不当行为更为了解,企业本身比政府更具有先天的优势,如监管的频率更高,监管的实施更有的放矢,等等。与此同时,企业自我监管还可避免政府对商业的过度干预,避免因干预影响企业创新。与除国家之外的外部监管机构相比,企业内部的合规团队也拥有更多可调动的资源和更大的调查权力。然而,尽管企业自我合规监管具有非常多的优势,绝大部分企业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也不会主动进行自我合规监管,追求利润最大化才是企业的第一要义。〔36〕See J.Braithwaite &B.Fisse,Self-regulation and the Control of Corporate Crime,Sag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nuals,Vol.23,p.221-246(1987).董事们只不过是闭着眼睛的哨兵。〔37〕See John C.Coffee Jr.,Beyond the Shut-eyed Sentry: Toward a Theoretical View of Corporate Misconduct and an Effective Legal Response,Virginia Law Review,Vol.93,p.1099-1278(1977).换句话说,只有外部的强制力才会迫使企业做正确的事情。为了解决企业不愿进行自我监管的问题,布雷思韦特提出了强制性自我监管的概念。在布雷思韦特看来,强制性自我监管的模式是推动企业合规所遇阻力最小的途径,具有自愿自我监管与国家强制力监管的优点,可以说,强制自我监管的概念既是对拖延、繁文缛节、成本和因政府对企业实施详尽监管而导致创新不能的反应,也是对相信企业能够主动实施自我监管天真想法的反应。在强制性自我监管模式下,政府将迫使企业制定一套为企业解决所面临的合规经营问题而量身定制的规则,并且监管机构有权要求企业对其不够严格的规则进行修改。企业在将外部监管法律、规章制度内化执行的同时,还需配备独立的检查员团队。监管机构督察员的主要职能就是监督企业执行规则的效率和力度以及企业检查员团队的独立性。〔38〕See J.Braithwaite,Enforced Self-regulation: A New Strategy for Corporate Crime Control,Michigan Law Review,Vol.80:7,p.1466-1507(1982).
事实上,20 世纪20 年代美国就曾出现过一段政府的强制性控制被企业主动自我限制所取代的时期,但随着20 世纪30 年代经济危机的出现而戛然而止。直至20 世纪70 年代-80 年代,美国政府才强制性地推动了新一轮企业自我监管。
1977 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这被视为推动合规计划发展和执行的催化剂。1972 年水门事件中,检察官发现总统竞选中存在大量来自企业的非法竞选捐款,后续调查进一步发现非法贿赂和回扣是企业界的惯例。与此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也被爆出使用公司资金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的丑闻。〔39〕See C.J.Walsh &A.Pyrich,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s as a Defense to Criminal Liability: Can a Corporation Save Its Soul,Rutgers Law Review,Vol.47,p.605(1994).以上背离美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行为,不仅使民众对自由市场丧失了信心,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40〕参见万方:《企业合规刑事化的发展及启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 年第2 期。美国国会为了遏制企业的海外腐败行为,挽救美国企业的国际形象,重拾国际社会对美国商业体系的信心,颁布了《反海外腐败法》。该法主要由《反贿赂条款》和《会计条款》组成,〔41〕参见肖扬宇:《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新动向及我国国内法表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 年第2 期。除了对为换取商业利益贿赂外国官员的个人处以刑事处罚外,还要求上市公司设计一套记录员工处置公司资产的账簿系统,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可以说,《反海外腐败法》同时采取对违规人员苛以刑罚和强制企业在其内部设置会计控制机制两种手段来进行企业腐败治理。根据《反海外腐败法》,企业或其他商业实体若违反《反贿赂条款》,可被处以200 万美元以下的罚金,违反《会计条款》,做虚假、误导性的陈述可被处以2500 万美元以下的罚金。〔42〕参见卢建平、张旭辉:《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对中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启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2 期。此后,《选择性罚金法案》(Alternative Fine Act),又将罚金数额由有固定上限变为最高可处企业非法所得或致他人经济损失数额的两倍。〔43〕参见万方:《反腐败合规法律实践的规范演进与实践展开——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为切入》,载《法治研究》2021 年第4 期。也就是说,《选择性罚金法案》使企业实际上可能面临的罚金高达数千万乃至数亿美元,这极大地提升了《反海外腐败法》的执法力度,对实施海外腐败行为的企业形成巨大威慑。〔44〕参见万方:《企业合规刑事化的发展及启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 年第2 期。此外,美国还不断将《反海外腐败法》的管辖权进行扩张,实现长臂管辖,成功地将该法的合规理念从美国国内推向国际社会,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合规发展。〔45〕参见肖扬宇:《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新动向及我国国内法表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 年第2 期。
在反腐败合规阶段性目标完成之后,20 世纪80 年代,美国又出现了一系列的企业内幕交易丑闻,对内幕交易的大量指控再一次揭露先前以国家监管的形式推动企业合规机制的不足。一系列的企业内幕交易丑闻推动了1988 年的《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执法》(Insider Trading and Securities Fraud Enforcement Act of 1988)的出台。为了推动证券公司更密切地参与对证券行业的监管,该法案要求经纪人和投资顾问建立和执行旨在防止滥用材料和非公开信息的书面程序。如果证券公司未能遵守建立、维持或执行合理书面政策和程序的法定要求,该公司将会被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自律性组织起诉,并有可能被处以罚款。此外,如果公司未能采取合规政策并实质上允许或促成了内幕交易行为,可能要承担三倍的损害赔偿责任。〔46〕See C.J.Walsh &A.Pyrich,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s as a Defense to Criminal Liability: Can a Corporation Save Its Soul,Rutgers Law Review,Vol.47,p.605(1994).该法案因强制证券企业履行其法定义务,进行合规监管,并规定证券企业如监管不力将面临起诉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所以对在证券行业推动企业合规计划起到了重要作用。〔47〕参见李本灿:《刑事合规的制度史考察:以美国法为切入点》,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 年第1 期。但是,该法案的强制力仅针对证券公司的内幕交易与欺诈,并未对证券市场上其他企业予以约束,所以,证券领域的企业合规远未完成。
21 世纪初,美国企业界又爆出一系列丑闻,这次丑闻集中在财务领域,其中以安然公司财务欺诈案最为典型。作为美国最大的能源交易商之一的安然公司因会计造假案事发而申请破产,其外部审计师——安达信会计公司也因审计问题而倒闭。〔48〕参见陆建桥:《后安然时代的会计与审计——评美国〈2002 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及其对会计、审计发展的影响》,载《会计研究》2002 年第10 期。此事件在动摇民众投资信心、引发资本市场恐慌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公司治理与监管问题的普遍质疑。企业治理系统无效,政府监管失败跃然纸上。在此背景下,为弥补制度性缺陷,美国参众两院快速立法,《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得以通过。该法案最为重要的条款之一 ——404 条款强调企业在编制年报时应当包括内部控制报告,且管理层有责任确保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充分有效,与此同时,会计师事务所需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测试与评价,担当企业合规的守门人。〔49〕参见孟焰、张军:《萨班斯法案404 条款执行效果及借鉴》,载《审计研究》2010 年第3 期。该条款强制要求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制作内控报告,且需会计师事务所予以测评。为了实现企业合规的目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设置了极为严苛的刑事责任,如,对进行欺诈和虚假陈述的行为人以及为虚假陈述背书的会计师可处以高达20 年的监禁和500 万美元的罚金,此外,对怠于履行合规义务的企业可处以高达违法金额4 倍的罚金。这不仅极大推动了企业合规的普及,而且促进了会计师事务所合法从事会计业务。〔50〕参见李本灿:《刑事合规的制度史考察:以美国法为切入点》,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 年第1 期。
美国政府除在证券领域内强制性要求企业实施自我合规监管外,还推动了以矿业安全与环境保护为代表的社会性监管领域的企业合规发展。以矿业安全领域为例,美国政府于1969 年颁布了《联邦煤矿健康与安全法》(Federal Coal Mine Health and Safety Act of 1969),该法明确规定矿工具有安全权,矿主有义务保证其权利的实现。〔51〕参见汤道路:《从对抗到合作:美国矿山安全卫生执法模式沿革与启示》,载《河北法学》2014 年第3 期。1977 年,美国政府又颁布了《联邦矿业安全与健康法案》(The Federal Coal Mine Safety and Health Act of 1977),将非煤矿山也纳入管辖,并规定矿主在保证所制定的安全规则不低于本法序言中所述的无法令人满意的最低安全保障水平的前提下,可向联邦矿山安全卫生管理局申请修改管理局对煤矿或其他矿业的强制性安全标准,管理局在后续的矿山监管中,负责例行检查,并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乃至移送司法部提起刑事检控。在众多修改安全标准的案例中,只有极少数企业因违反了修改后的具体标准而被处以民事罚款,多数企业都能按其承诺遵守他们所制定的规则。此外,联邦矿山安全卫生管理局还允许企业主自由设计和提交他们自己独特的通风和粉尘控制计划以及顶板支护计划并获得审批,这表明管理局将自己的部分权力让渡给了企业,在强制性自我监管的模式下,监管机构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企业的整体计划上,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一具体事项上。当然,一旦企业偏离经批准的控制计划,则该企业可能被提起刑事检控,如一名煤炭管理人员因未能遵守经批准的控制计划而被判处了60 天的监禁。〔52〕See J.Braithwaite,Enforced Self-regulation: A New Strategy for Corporate Crime Control,Michigan Law Review,Vol.80:7,p.1466-1507(1982).此外,根据《联邦矿业安全与健康法案》的规定,企业还需安排特定的矿工在换班前对矿井进行安全隐患检查,并记录违反强制性健康和安全标准的情况。在实践中,虽然立法者并不指望他们能够系统地审计煤矿经营者是否遵守法律,但他们确实在核查矿井工作区域是否存在严重隐患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联邦矿山安全卫生管理局的例行检查中,如被记录的违规行为仍存在,未进行整改,则予以引证,如已予以纠正,则不予理会。
就环保领域而言,企业内部应采取措施以遵守环境法,也越来越被强调和重视。1986 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发布的环境审计政策声明要求企业对与其相关的设施操作和实践进行系统的、书面的、定期的和客观的审查,以识别潜在的环境问题,并确保该公司的内部合规惯例有效。〔53〕See C.J.Walsh &A.Pyrich,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s as a Defense to Criminal Liability: Can a Corporation Save Its Soul,Rutgers Law Review,Vol.47,p.605(1994).例如,环境保护署要求参与石油生产、分销和存储的企业依照环境保护署的指导方针准备一份预防石油泄漏或应对石油泄漏的计划。一般情况下,该计划仅需由专业工程师予以认证,证明该计划符合良好的工程实践,只有石油发生泄漏时,这份计划才会由环境保护署予以审查。又比如,《有毒物质控制法》(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除授权环保署署长具有命令制造商检测可疑的化学物质、监督法案程序遵守情况、提出质量控制方案的权力外,署长还有权对其认为不合适的方案进行修订。
在布雷思韦特看来,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强制性自我监管模式的初步形成,模式中所有关键元素都可以在实践中找到,但最为契合该模式的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制药企业实施的良好实验室规范。〔54〕See J.Braithwaite,Enforced Self-regulation: A New Strategy for Corporate Crime Control,Michigan Law Review,Vol.80:7,p.1466-1507(1982).该规范设法通过严格保存记录和坚定的遵守科学协议以增加企业弄虚作假的难度,同时要求每个药物检测实验室都要配置一个质量保证部门作为内部的合规警察,质量保证部门的报告必须定期提交给实验室主任和企业管理层。这一安排不仅将监管的财政负担由政府转移到了企业身上,而且保证了管理层不能以不知情为借口,而对违规行为不作出反应,如果管理层确实不知道被发现的违规行为,企业就会因其不知情而犯罪。因此,这些规定实际上要求的是一种自我监管机制,以防止下属在坏消息传到负责人的耳朵之前过滤掉它。〔55〕See J.Braithwaite,Enforced Self-regulation: A New Strategy for Corporate Crime Control,Michigan Law Review,Vol.80:7,p.1466-1507(1982).
美国在以国家监管的方式推动企业合规乏力之后,又转而寻求以强制性自我监管的方式推动企业实施合规监管。通过考察美国企业合规的新进路,可以发现美国政府的着力点主要有三个:其一是重点推动上市公司的企业合规,主要表现为《反海外腐败法》和《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分别对上市公司资产处置的账簿系统与内部控制报告提出了专门要求;其二是一改国家监管模式下重点推动带有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领域和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企业合规的做法,转而强调强制性自我监管模式下包括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在内的社会性监管领域的企业合规建设;〔56〕社会性监管一般是指为达到健康、安全、环保等社会目标进行的跨行业、全范围监管。参见卞靖:《发达国家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共同特征及相关启示——以社会性监管为例》,载《当代经济管理》2015 年第37 期。其三是在这一时期,一系列爆发的丑闻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促使政府转换思路,以强制性自我监管模式推动企业进行合规监管。
四、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
近几十年来,美国国会越来越频繁地将刑法作为对企业行为进行经济和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57〕See S.H.Kadish,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Use of Criminal Sanctions in Enforcing Economic Regulation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30,p.423(1962).因企业怠于主动进行自我管制,国家除了强制要求企业进行自我监管外,还对企业合规许以刑事激励。例如,那些已建立有效合规项目的企业被给予更宽松的量刑,〔58〕See K.B.Huff,The Role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s in Determining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A Suggested Approach,Columbia Law Review,Vol.96:5,p.1252-1298(1996).抑或用较轻污名化和惩罚性的民事或行政诉讼替代刑事指控。〔59〕See C.C.Murnane,Criminal Sanctions For Deterrence Are a Needed Weapon,But Self-Initiated Auditing Is Even Better: Keeping the Environment Clean and Responsible Corporate Officers Out of Jail,Ohio State Law Journal,Vol.55,p.1181(1994).
美国企业合规制度的刑事激励萌芽于20 世纪60 年代以通用电气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垄断刑事诉讼,这些发生在重型电气设备行业的备受瞩目的反垄断刑事诉讼促使美国企业界广泛实施有效的合规计划。〔60〕参见李本灿:《刑事合规的制度史考察:以美国法为切入点》,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 年第1 期。此前,美国电气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以致电气企业意图通过价格战来抢占市场,在惨烈的价格战之后,几家大型电气企业互相串通,操纵价格,串通投标和分配市场。1961 年,在反垄断刑事指控中,29 家企业和45 个自然人对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指控进行了认罪或没有进行抗辩,政府最终判处了近200 万美元的刑事罚金及几项监禁。〔61〕See C.J.Walsh &A.Pyrich,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s as a Defense to Criminal Liability: Can a Corporation Save Its Soul,Rutgers Law Review,Vol.47,p.605(1994).其中,通用电气试图以实施了合规计划作为对刑事指控的辩护。〔62〕See R.C.Bird,&S.K.Park,The Domains of Corporate Counsel in An Era of Compliance,American Business Law Journal,Vol.53,p.203(2016).虽然通用电气的辩护没有成功,但是这种尝试刺激了反垄断合规计划被广泛采用。监管机构也表示,他们将考虑以合规计划是否存在作为违规是错误而非故意的证据。〔63〕See C.J.Walsh &A.Pyrich,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s as a Defense to Criminal Liability: Can a Corporation Save Its Soul,Rutgers Law Review,Vol.47,p.605(1994).这意味着合规管理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规避反垄断的刑事指控。因迫于反垄断的压力,全美各地越来越多被重点监管的垄断行业的企业开始制定并实施反垄断合规。〔64〕参见万方:《企业合规刑事化的发展及启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 年第2 期。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国防工业又爆出欺诈丑闻,迫使美国联邦政府对国防工业进行了改革,进而推动了企业合规计划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在国防采购中普遍存在的浪费和弄虚作假行为,罗纳德·里根总统建立了国防管理特别工作委员会(Blue Ribbon Commission on defense Management),即我们熟知的帕卡德委员会(Packard Commission)。该委员会除建议在国防承包行业内建立道德规范外,还主张建立一个计划来鼓励向国防部自愿披露承包商不当行为(DOD)。
1986 年,18 家主要的国防承包商起草了《国防工业商业伦理与行为倡议书》(Defense Industry Initiatives on Business Ethics and Conduct),该倡议书的以下六项基本原则强调了国防承包商有义务遵守商业伦理和行为守则、以及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不当行为。第一,供应商应具有成文的商业伦理及行为守则并遵守之;第二,供应商需对员工加以培训,使之遵守行为守则;第三,供应商有义务为员工举报不正当行为塑造良好的环境;第四,供应商有义务监测联邦采购法的遵守情况,并采取自愿披露和纠正非法行为的程序;第五,供应商具有遵守商业伦理的义务;第六,供应商需履行遵守以上原则的公共责任。〔65〕See C.J.Walsh &A.Pyrich,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s as a Defense to Criminal Liability: Can a Corporation Save Its Soul,Rutgers Law Review,Vol.47,p.605(1994).此外,国防部还采用了一项旨在鼓励内部调查和及早报告非法行为的自愿披露计划,并鼓励供应商将自愿披露作为企业合规的核心。在国防部看来,早期的自愿披露、充分合作和能够完全查阅必要的记录是承包商诚信态度的判断标准,也是国防部在决定是否对承包商进行行政处罚时考量的因素。
企业的自愿披露和配合查阅记录时的合作态度成为国防部进行行政处罚的考量因素,初步具有了行政法上的激励,但刑事激励却是直至1987 年美国司法部发布“自愿披露计划指引”并将其纳入《联邦检察官手册》(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才得以完成的。指引指出:司法部在治理国防采购欺诈时,除了威慑,还应通过起诉裁量激励供应商实行企业合规。可以说,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推动了企业合规理念的普及和制度化的实现。〔66〕参见李本灿:《刑事合规的制度史考察:以美国法为切入点》,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 年第1 期。
1991 年,美国企业合规推进过程中发生了里程碑式事件,即美国联邦量刑委员会修订了《联邦量刑指南》(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该指南的第八章“组织量刑指南”序言明确指出:“本章旨在维持预防、发现和举报犯罪的内在机制,使对组织及其代理人的制裁总体上能够提供公正的惩罚、足够的威慑和对组织的激励。”〔67〕参见韩轶:《刑事合规视阈下的企业腐败犯罪风险防控》,载《江西社会科学》2019 年第5 期。此处的“对组织的激励”主要是指罚金刑的减轻与企业缓刑。〔68〕参见李本灿:《刑事合规的制度史考察:以美国法为切入点》,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 年第1 期。例如,法院可对设有有效合规计划的企业显著减轻其罚金刑。具体来说,如犯罪企业有“合理的”合规计划,那么该企业作为被告的罪责分数〔69〕罪责分数(culpability scores)决定刑罚的严重程度。最多可以减少3 分,罪责分数的减少可进一步使罚金相应减少。又比如,一个犯罪企业缺乏用以预防和发现不法行为的有效合规计划,或该企业的雇员达到50 或以上,量刑指南便要求法院判处缓刑,并给予五年以下的考验期。〔70〕See S.S.Simpson,Corporate Crime,Law,and Social Contro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14.在判处缓刑的同时,法院可责令该组织以特定的形式与手段,公布其所实施犯罪的性质,定罪的事实,刑罚的性质,以及其所决定采取的预防此类行为再次发生的措施。另外,判处组织缓刑时还可附加以下条件:(1)组织应当将构建的合规计划以及实施合规计划的规划向法院呈报;(2)合规计划获法院批准后,组织应将其连同犯罪情况按法院要求的形式通知股东和员工;(3)组织应定期向法院或缓刑考验官汇报企业合规实施情况。如组织违背了以上缓刑考验的附加条件,法院可延长其考验期,或设置更严苛的附加条件,又或撤销该缓刑,予以重新量刑。〔71〕参见李本灿:《刑事合规的制度史考察:以美国法为切入点》,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 年第1 期。这可视为《联邦量刑指南》给予企业的“胡萝卜”,即在量刑时给予“负责任的企业”更宽松的待遇,从而避免了严厉的刑事处罚这根“大棒”。
在《联邦量刑指南》的刑事激励背景下,企业被鼓励制定有效的合规计划以实现自我监管,其强制意味较之前《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执法》和《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等文件的规定有所减弱。〔72〕See S.S.Simpson,Corporate Crime,Law,and Social Contro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32.另外,《联邦量刑指南》为有效的合规方案制定了七个基本要求,包括:(1)建立合规政策和标准以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2)由高层人员对合规政策和标准进行适当监督;(3)企业不得聘用有犯罪记录的高管;(4)向所有雇员有效普及合规政策和标准;(5)根据需要对合规政策和标准进行监测与更新;(6)通过建立惩戒机制,严格遵守并执行合规标准;(7)犯罪发生后,企业应采用相应措施予以应对,预防此类行为再次发生。〔73〕See C.Ford &D.Hess,Can Corporate Monitorships Improve Corporate Compliance,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Vol.34,p.679(2008).在实践中,很多企业合规监管体系均是在这七项基本标准的指导下构建的。更重要的是,《联邦量刑指南》超越了合规原本仅限于反垄断、反海外腐败及国防工业等领域的局限,使合规计划的普及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1991 年《联邦量刑指南》第八章“组织量刑指南”颁行后,其中关于企业合规的规定逐渐成为了检察官评估企业罪责的基础和法官对企业量刑的标准,同时也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监管的法律依据,但是,美国司法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制定与之配套的针对企业提起诉讼的政策和标准。〔74〕参见万方:《企业合规刑事化的发展及启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 年第2 期。因此,美国联邦副总检察长艾瑞克·霍尔德(Eric Holder)于1999 年发布了一个名为《联邦起诉商业组织原则》(Principles of Federal Prosecution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s)的备忘录(即“霍尔德备忘录”),其中规定了检察官起诉企业时可以考虑的八大因素:(1)犯罪的性质和严重性,包括对公众造成伤害的风险;(2)企业内部不法行为的普遍性,包括企业管理层对不法行为的共谋或纵容;(3)企业历史上的类似不当行为,包括以前对其采取的刑事、民事和监管执法行动;(4)企业及时和自愿地披露不当行为,并愿意配合调查;(5)企业是否具有合规计划以及合规计划的有效性;(6)企业的补救行动,包括实施有效的企业合规计划或改进现有计划的任何努力,包括更换管理层,惩戒或解雇不法行为者,支付赔偿金,以及与相关政府机构合作;(7)附带后果,包括是否对股东、养老金持有者、雇员和其他未被证明负有个人责任的人造成的过度伤害,以及起诉对公众的影响;(8)民事或监管执法行动等非刑事补救措施是否充分。〔75〕参见叶良芳:《美国法人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发展》,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 年第3 期。
以上八大因素共同构成了检察官对企业法人提起诉讼时考虑的核心要素,其中,企业是否具有合规计划及其合规计划的有效性直接影响检察官的裁量,如检察官认定企业的合规计划是有效的,可依职权不予指控。此外,《联邦起诉商业组织原则》还提示检察官需从企业违法行为的普遍性、企业合规计划拥有与否、以及企业采取补救措施与否来考察企业的合规状况。由此可见,《联邦起诉商业组织原则》除了对检察官诉讼业务具有指导意义外,还对引导企业建立合规计划意义重大。
在“霍尔德备忘录”的基础上,美国联邦副总检察长拉里·D.汤普森(Larry Thompson)又于2003年签署了“汤普森备忘录”,增加了检察官起诉企业时应予考虑的第九大因素——“追诉为企业犯罪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个人的充分程度”。“汤普森备忘录”要求检察官在起诉法人时“必须”逐一考量这九大因素,改变了“霍尔德备忘录”中“可以”考虑八大因素的措辞,这表明“汤普森备忘录”对检察官的诉讼业务具有强制性而非“霍尔德备忘录”中的指导性约束力。〔76〕参见叶良芳:《宪政视野下的美国法人犯罪审前协议制度——以Stein 案为中心》,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 年第4 期。与此同时,“汤普森备忘录”还建议检察官将本为未成年犯罪和毒品犯罪适用的审前分流协议适用于企业犯罪领域,合规计划随之成为了检察官对企业适用暂缓起诉和不起诉决定的法定事由。这直接推动了企业对合规的重视,使企业积极构建和实施合规计划,以赢得检察官的暂缓起诉或不起诉决定。〔77〕参见万方:《企业合规刑事化的发展及启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 年第2 期。另一方面,检察官在审前分流协议中对涉案企业所提出的合规要求与建议对该企业合规监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06 年,时任美国联邦副总检察长的保罗·J.麦克纳尔蒂(Paul J.McNulty)签署了“麦克纳尔蒂备忘录”,该备忘录在保留了“汤普森备忘录”中关于起诉法人的九大因素的同时,对企业合作的真诚性评估问题进行了细致规定,即检察官只有在具备“合理必要”时,才可要求企业提供受特免权保护的信息,如律师—当事人信息披露豁免权。衡量“合理必要”的要素主要为:该信息能够提供利益的多少,有无获取信息的替代性措施,企业是否自愿提供以及放弃特免权的消极影响。此外,检察官一般不应将法人为接受调查或起诉的员工支付律师费作为衡量企业真诚合作的考量因素,除非律师费的支付妨碍了刑事调查。〔78〕参见叶良芳:《美国法人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发展》,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 年第3 期。2008 年,马克·R.菲利普(Mark R.Filip)副总检察长又通过签署“菲利普备忘录”对“麦克纳尔蒂备忘录”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检察官在衡量企业合作的真诚性时,不可将企业自愿放弃律师—当事人信息披露豁免权和是否为其员工支付律师费(即使可能阻碍刑事调查)作为考量因素。〔79〕参见李本灿:《域外企业缓起诉制度比较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 年第6 期。
事实上,综观几十年来美国以刑事激励的方式推动企业实施合规监管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实施合规监管的兴趣始于企业将合规计划作为证明其违规是错误而非故意的证据以规避刑事指控。而后,以国防工业的《自愿披露计划指引》为突破口,通过起诉裁量鼓励供应商实施企业合规,美国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得以初具雏形。随后,修订的《联邦量刑指南》又明确规定了实施合规计划的企业罚金刑的减轻与企业缓刑的适用,使企业合规有了向各行业扩展的基础。最后,美国政府多次通过以美国联邦副总检察长备忘录的形式发布和丰富《联邦起诉商业组织原则》,通过制定和完善与《联邦量刑指南》配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针对企业提起诉讼的政策和标准,确定了企业是否具有合规计划及其合规计划的有效性是检察官起诉企业犯罪时考虑的核心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影响暂缓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核心要素之一。
五、结论
综观美国企业合规的构建过程,美国企业的合规管理起源于国家对企业监管的加强。早期的国家监管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通过立法和成立独立的管制机构两种方式率先在易形成垄断的行业、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和信息不对称的行业加强合规监管,应用范围有限。迫于国家强监管的压力,以上行业的企业不得不进行自我合规监管。可以说,19 世纪末至20 世纪60 年代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依赖国家监管的方式推动企业合规。20 世纪60 年代之后,美国政府结束了以国家监管的单一方式推动企业合规发展的历史,形成了以国家监管、强制性自我监管和刑事激励多种手段推动企业实施合规监管的新篇章。美国政府推动企业合规发展手段的多样化也进一步将企业合规的适用领域由带有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领域和关系国计民生领域向包括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在内的社会性监管领域和全行业扩展。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在以国家监管、强制性自我监管和刑事激励三种方式推动企业合规发展时,三种方式是彼此共存、彼此合作、互为补充的,而非以一种或两种方式取代前一种方式。以20 世纪60 年代通用电气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垄断刑事诉讼为例,其中既包括美国电气行业迫于国家监管压力实施反垄断合规的内容,又包括电气行业将合规计划作为违规是错误而非故意的证据以规避反垄断刑事指控的刑事激励内容。
美国通过国家监管、强制性自我监管和刑事激励三种方式推动本国企业合规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国家治理逻辑对我国企业合规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应强化政府部门、监管机构以及司法机关的协调联动,以多种方式互相配合,按计划,分步骤推动企业合规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美国曾在不同时期,先后以国家监管、强制性自我监管和刑事激励三种方式推动企业合规的发展,三种方式之间互相配合、互为补充,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但反观我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以国资委为代表的政府部门,以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为代表的监管部门和以检察机关为代表的司法机关,纷纷在合规潮中“一哄而上”,各自依其职权,以各具特色的方式推动企业合规的发展,而各部门之间却鲜有联系与协调。甚至,在司法机关内部,公安和法院系统都未能为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合规不起诉探索提供实质帮助。结合我国特点,美国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为我国提供了经验支持,即,需要通过协调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之间,以及司法机关内部之间的关系,〔80〕参见张阳:《企业刑事合规本土探索的实践偏误与路径回归》,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1 年第6 期。以多种方式并举,合力推动我国企业合规制度建设。
具体而言,我国应首先通过监管机构发布规范性文件的方式迫使金融行业实现合规监管。美国对金融行业的合规关切由来已久,甚至,合规一词就是在对证券市场进行合规监管的过程中被首次提及的。美国政府通过国家监管和强制性自我监管的方式率先实现了对金融行业的合规监管。在我国,因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分别对商业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具有监管职能,这使监管机构通过发布规范性文件强制以上企业率先实现合规监管,具有现实基础。
其次,国家还应通过合规指引、行政指导、预防性监管、强制合规和行政激励等方式发挥行政机关的合规监管作用。〔81〕参见陈瑞华:《论企业合规在行政监管机制中的地位》,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 年第6 期。不难发现,与企业合规的检察主导相比,〔82〕参见董坤:《论企业合规检察主导的中国路径》,载《政法论坛》2022 年第1 期。我国行政机关在推动企业构建合规体系时,显现出了一定的滞后性,这与美国在构建企业合规制度的过程中,充分的发挥国家监管和强制性自我监管的作用,甚至二者在构建过程的中前期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刑事激励,形成了对比。因而,以行政机关合规监管的方式推动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应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最后,检察机关通过刑事激励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引导更广泛的市场主体主动构建合规制度。美国的经验也表明刑事激励的措施能调动更庞大的企业群体进行合规监管的兴趣。诚然,我国能够通过监管机构发布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监管强制要求部分企业在短时间内建立合规制度,积累合规管理经验,但更广大的市场主体主动构建合规监管体系则有赖于以刑事激励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进行引导。在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激励下,多为中小微企业的民营企业拥有了改造经营模式,进行合规体系建设的动力。〔83〕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合规激励模式》,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6 期。
第二,应根据行业和企业类型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推动方式。美国推动本国企业实现合规监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分行业、有层次、按部就班地进行,先是通过国家监管的方式率先推动关系国计民生、易形成垄断和信息不对称行业内的企业实现合规,继而通过强制性自我监管的方式重点推动上市公司和社会性监管领域的企业合规,最后通过刑事激励的方式推动企业合规向全行业扩展。同样,我国也应有针对性地探索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企业合规推进路径,具体就是,监管机构强制性地要求金融行业和上市公司进行合规监管,以行政主导机制推进央企、地方国企构建合规管理体系,以发布合规指引的方式引导外向型企业顺应国际合规潮流。检察机关以合规不起诉的刑事激励与行政机关合规监管相配合的方式推进民营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最终形成多种方式互相配合、互为补充、有的放矢的推进模式。
第三,企业合规的适用范围应包括中小微企业。域外企业合规监管体系几乎都是为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量身定制的,并且这些企业有完整并能有效运转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所以他们具有建立合规监管体系的基础。但我国检察机关在试点改革中,中小微企业是合规考察的主要对象,这一直为学者所诟病。〔84〕参见陈瑞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八大争议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 年第4 期。在他们看来,合规制度的建立是有门槛和标准的,是需要企业在人财物上投入高昂成本的,〔85〕参见李玉华:《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对象》,载《法学论坛》2021 年第6 期。这使得中小微企业难以达到无差别的有效合规标准。〔86〕参见唐彬彬:《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裁量权限制的三种模式》,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1 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企业合规经验使得企业合规应适用于大型企业貌似成了“金科玉律”。持异见者以此做法与我国法律平等适用原则相违背回应,主张企业规模不应成为企业合规适用对象的考量因素,〔87〕参见曾文革、郑达:《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在企业犯罪中的应用及其启示》,载《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20 年第6 期。但这一回应略显苍白无力。
美国所建立的企业合规制度适用的对象确实多为大型企业,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其原因在于建立企业合规的初衷是出于国家监管的需要,出于反垄断、反海外腐败、反欺诈、反内幕交易的需要,中小微企业自然不会也无力成为国家重点监管和规制的对象。但同样应引起注意的是,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扩展企业合规的适用对象,特别是以刑事激励的方式促使企业合规向更多行业扩展。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企业合规发展的历程就是美国政府扩展企业合规适用对象的过程。美国政府不是不愿意中小微企业普遍建立企业合规制度,相反,这是其想要努力达成的愿景,只不过在其现有的制度下,一段时间内无法达成。
反观我国建立企业合规制度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顺应国际合规潮流,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考虑。我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在对民营企业予以特殊保护的初衷下,企业合规的适用范围应包括中小微企业是应有之义,这与美国政府实现对大企业的国家监管和规制的初衷截然不同。又如前文所述,美国在推动企业合规制度发展时,也曾以刑事激励方式扩展企业合规的适用对象至更广泛的领域,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刑事激励手段本就是为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更广泛的适用群体而量身打造的。特别是当我国可以其他替代手段推动其他类型企业实现合规监管的前提下,中小微企业甚至应当成为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主要激励对象。至于中小微企业因无力承担高昂合规成本,难以达到无差别的有效合规标准的问题,则可以通过设置相对较短的合规考察期,制定相对简化的专项合规计划等措施予以解决。〔88〕参见周新:《涉罪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重点问题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2022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