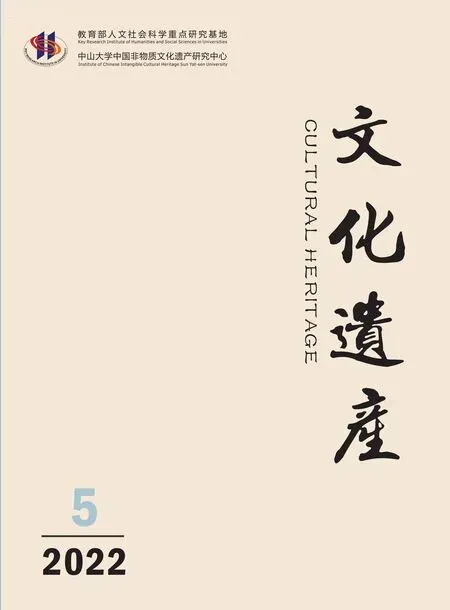官府与民间对立共生:清代乡村丧葬演剧的治理*
姚春敏 李成生
引 言
丧葬演剧是一种纯粹的民间习俗,它源于丧礼上人们本能的歌哭擗踊和用乐,滥觞已久,《史记》中就有:“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早期的丧葬演剧以歌舞鼓乐俳优为主,直到明朝初期,在丧葬活动中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戏曲演出,清代丧葬演剧在民间社会中发展得更加完善。丧礼出殡本是哀伤之事,但民间却以演剧相伴,颇为人所诟病,因与儒家礼法不和,而被历代禁止和约束。关于民间演剧的国家治理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甚多,成果颇丰。同时也出版了一些禁毁戏剧的史料合集,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历代的戏剧政策的发展不无裨益。但是,丧戏之盛与丧戏之禁作为民间和官府的两个维度并未十分明晰。作为千年来普遍存在的民俗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大多偏爱国家制度选择忽视民间自治,然,仅从国家治理单面特征尚不足以说明为何民间丧葬演剧现象屡禁不止且愈禁愈烈。笔者因多年从事山西田野调查和碑刻研究,发现民间村社组织对丧葬演剧也有一些管理,只是与国家制度表现方式大为迥异。那么,在传统社会中,与民间丧葬演剧发生在同一个空间领域的村社组织,对所辖民众丧葬演剧的态度如何?又是如何具体管理?以及这一规训与国家制度的异同?等等,这些问题学界均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事实上,民间村社对丧葬演剧管理亦是传统社会层级治理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它与上层管控构成统一整体,它的态度和管理能力直接决定了民间丧葬演剧的发展和变化。本研究以笔者数十年的田野调查中所收集的大量民间碑刻为基础史料,为了更加清晰地进行共时性的比对,本研究主要以清代三晋村社碑刻为中心,同时辅以地方文本和口述资料,尝试对民间丧葬演剧官府和村社双重治理的对立共生状态进行分析,同时也尝试从另一个维度回答这个持续千年的丧葬演剧民俗是如何根深枝茂,愈禁愈旺。
一、清代官府对民间丧葬演剧的治理
有清一代,王朝高层对于民间丧葬演剧严格治理,从未停息。《清史稿·礼志》记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禁居丧演戏饮博。”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庚戌记有“严禁兵民等出殡时前列诸戏,及前一日,聚集亲友,设筵演戏”等内容。雍正十三年(1735)又再次严令:著各省督抚等,通行明切晓谕,嗣后民间遇有丧葬之事,不许仍习陋风,聚饮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类,违者按律究处。务在实力奉行,毋得姑为宽纵。清王朝禁止丧葬演剧的态度非常明显,之后的乾隆五年(1740)和嘉庆十六年(1811)大清律例均重申丧葬演搬杂剧禁令。如乾隆五年(1740)《大清律例》卷一七《礼律·仪制》有:“民间丧葬之事,凡有聚集演戏及扮演杂剧等类,或用丝竹管弦演唱佛戏者,该地方官严行禁止。违者,照违制律治罪。”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但,整个清代二百余年对此的管控略有松动,如《高宗纯皇帝实录(一)》记有乾隆对丧葬演剧一事的详细谕旨:
(十一月)丁酉……命丧葬循礼,谕曰:“朕闻外省百姓,有生计稍裕之家,每遇丧葬之事,多务虚文,侈靡过费。其甚者,至于招集亲朋邻族,开筵剧饮,谓之闹丧。且有于停丧处所,连日演戏,而举殡之时,又复在途扮演杂剧戏具者。从来事亲之道,生事死祭,皆必以礼……况当哀痛迫切之时,而顾聚集亲朋,饮酒演剧,相习成风,恬不知怪,非惟于礼不合,抑亦于情何忍?此甚有关于风俗人心,不可不严行禁止。”
上文中,虽见乾隆对民间丧葬演剧作为传统习俗,态度有所转换,但仍持禁止态度。在乾隆谕旨下达后的第二年,便有地方大员上奏夸赞乾隆所言民间丧葬不许聚饮演戏、扮演杂剧之事是“仁孝居心,中正立极”之举,同时认为“婚丧祭祀之礼多不循法,或趋尚浮华,或过于简略,非惟省与省异,亦且郡与郡殊,恐因循日久,礼教失传,甚有关于风俗”,希望乾隆下旨“令天下臣民,一切祭祀、婚丧,务遵朱子《家礼》以为准则。”但乾隆对此的回复则是“此奏是,但其中尚有应斟酌者,必须尽美尽善,然后行之久而无弊,于以化民成俗不难矣。若苟且从事,亦不过虚文而已,究于治道何补?待朕徐徐经理之。”可见,虽然乾隆在前一年提出要严禁丧葬演剧,但面对民间社会的繁杂,禁限之后究竟该如何施行,还是有待斟酌。毕竟仅仅依靠强行禁止是难以解决问题的,民间社会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想要进行有效治理,就要全面考虑,而非一概论之。
总体来讲,清王朝高层对丧葬演剧的态度,虽略有徘徊,但严禁是主调。同时期,清代地方官府和高层保持着一致的禁绝态度。尹会一曾任河南巡抚,有《抚豫条教》四卷,其中记有:
今闻豫省陋习,凡遇丧葬之事,往往聚集亲朋,广招邻族,开张筵宴……其富户有力之家,则鼓吹音乐,演戏跑马,并装扎人物纸作以为饬观……本部院前于规劝条约内,曾经注明示禁;而此风尚未尽息,总缘人心不能反本细思,合行严饬禁止……遇有丧葬之事,务须遵循礼制,屏绝虚文,不得仍蹈陋习,违者按律治罪。
从巡抚尹会一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之前“于规劝条约内,曾经注明示禁”,但结果并不明显,“此风尚未尽息”,于是才“严饬禁止”。乾隆十年(1745)陈宏谋在陕西巡抚任上也有关于禁丧戏的告令:
丧中宴饮,已属非礼,而陕省更有丧中演戏之事,或亲友送戏,或本家自演,名为敬死,其实忘亲,哀戚之时,恒舞酣歌,男女聚观,悖理伤化,莫此为甚。从前屡经禁止,至今恶习未除,风化攸系,未便因循。嗣后应先从绅士为始,凡有丧事,禁止演戏,违者无论乡保地邻,许其首告。
从告令中可知,当地丧葬演剧,或为亲友送戏,或为本家自演,已是一种较为成熟的风俗,且“从前屡经禁止,至今恶习未除”,治理甚难。再如洛阳知县龚崧林《严禁出丧演戏示文》记有:
讵洛邑素号名都,近日竟成恶习,居丧者,不但不哀毁躃踊,且于含殡之时,卜宅之际,富家竟令优人演戏,贫者即觅乐人吹戏,谓之闹丧……况绝无哀戚之情,颇有忻愉之色,显以演戏为丧家之乐,鼓吹博亲友之欢,为人子者,情安忍乎!此等颓风亟宜力挽。
直到光绪六年(1880)河南通许知县潘江颁发《禁丧戏示》仍记有:
为严禁丧戏,以正风俗事。照得临丧以哀为本,演戏以乐为怀。凡酬神、敬祖及寿诞、婚姻、生子育孙诸喜庆,开筵唱戏,犹可言也。未闻丧务在堂,为之演戏,以取乐者。查此地殷实之家为父母殡葬,必须唱戏二三日或四五日,以为美观。且有妇女病故或自尽,其母家闻讣车来,混行滋闹,谓之做假命,除衣衾、棺椁、修斋拜谶而外,又必演戏几台方肯了事,否则不依……违礼犯法,败俗伤风,莫此为甚,深堪痛恨……自示之后,凡居丧演戏及母家因女物故,迫令婿家演戏,此等不法之徒,许尔地保、巡役及族邻人等,赴县指名禀控,本县定即拿究,决不姑宽。倘敢通同隐匿,一经查出,或别经告发,其罪与犯事者同科。本县言出法随,切勿视为具文。
首先,这通告示明示,从清代初年到清末这种禁止丧葬演剧的官方告示从未停止,暗含之意是民间丧葬演剧也从未停止。告示首先指出“临丧以哀为本,演戏以乐为怀”,点明了二者针锋相对的特性,继而提出,凡酬神、敬祖、寿诞、婚姻、生育等喜庆之事,开筵唱戏,是可以理解的,官方并未一概禁绝。但丧务在堂,演戏取乐实在难以接受。特别是两种情形,一是殷实之家为父母殡葬须唱戏二至五日,耗时长久,尤为严重;二则是有妇女病故或自尽,母家闻讣赶来竟要求必演戏,否则不依,试想丧女之悲竟要以演剧来弥补,实属不能理解。因而官府发文严禁,并明言不得视为具文。
上见,清代官府对民间丧葬演剧的治理态度如出一辙,有清一代二百余年,这一政策几乎未有实质性的更改,即民间丧葬演剧有悖礼法,必须严格管控,加以禁绝。
二、民间村社对本地丧葬演剧的治理
传统民间村社起自于“社”,“社”来源已久,《说文》有:“社,地主也。”段玉裁注引《五经异义》:“今《孝经》说:‘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为社。’”先秦时期,立社奉祀土地之神是贵族阶层的特权。自汉代以降,由于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社”开始进入基层成为村落区域的象征。唐宋之后,“社”由土地神演化为各村落的保护神,由社祭而形成的村落组织开始形成,村社概念形成,明清时期是其发展的高峰期。民国以后伴随着废庙兴学,社庙开始衰败,传统意义上的村社逐渐消失。村社制度迄今千余年,它集礼仪、民俗、信仰、社交、管理于一体,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翟宣颖曾道:“唯社为遍及人群,于是社为人民结合之所,为饮食宴乐之资,则宗教性渐移入政治性,又渐移入社会性矣。汉氏以来,社为人民活动最有力之表现,始为社交团体,继为文艺结合,为乡里自卫组织,为自治机关。”千年以来,村社所缔造的中国传统村落的文化印象影响至今。村社与历代王朝统治、社区认同、仪式传统、水利组织、跨村网络等各种因素交相作用,与地方官府、宗族、家族、商人等人群关系紧密,有着千年传统的村社,具备顽强的生命力和持续力,成为中国传统乡村最重要的基层组织。
明清时期是村社制度发展的高潮期,这一时期村社组织实现了对区域内乡村社会的全面治理。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是民间村社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事情,村社是明清社会中的基础细胞,再小的村落中也有婚丧嫁娶。“我村地虽弹丸,岂无丧祭婚嫁之事;人即贫乏,难免工厨鼓乐之需。”传统社会的民间村社直面本聚落的丧葬之事,应该对本聚落的民间丧葬演剧基本情况了如指掌,那么,作为一个村落民间自治组织对其的治理亦是天经地义。但是,遍寻三晋石刻,在数以十万计的碑刻中,仅发现十八通,可见表1。

表1 山西村社民间丧葬演剧管理碑刻一览表
上见,清代村社对民间丧葬演剧的管理碑刻中,有且仅有一通是村社奉劝村民减少演戏,即嘉庆三年(1798)《公议乡风十二劝》载:“除春祈秋报,不许演戏(包括丧葬)”。这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和清代官府对丧葬演剧禁止态度一致的民间村社碑刻。
此外,有两通是对村民占用村社庙宇办理丧葬之事的规定,有一通规定了村民遇有红白事不允许和允许占用村社庙宇,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永记碑》载:庙内不许做棺木以及一切窝铺。另一通乾隆三十七年(1772)《修造暖宫并桌椅杌凳碑记》载:
至于桌、椅、杌凳,则人人可以借用。使无规例,则损坏可立而待。三班社首议定。大社任意使用,自不待言。村中人等,或还愿酬神,或有红白大事,或有大小会事,在庙中办事,俱许借用,但不许搬移下庙;如搬一件下庙者,罚银一两。即在庙戏台上使用,亦止许使帮桌二张、条桌一张、椅四把、小橙二条;如多搬一件上台者,罚钱一百文。
这两通碑文基本意思相似,第二通完美地诠释了第一通碑刻的含义,文告中不仅未有限制村民丧葬演剧之意,甚至还暗含有丧葬可以占用村庙在此演剧之意。这两通碑的出发点并不是限制民众丧葬演剧,而是防止演剧规模过大破坏村社的庙宇。
其余的丧葬演剧治理重点均集中在对执事乐户的管理中,这其中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村社对乐户科地的管理,另一部分是村社对在丧葬演剧中执事乐户待遇的规定。
关于对科地的规定,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大社五班社首公议条规碑记》记有:“大社五班拜首公议,因吹手郭宗继屡来肆行无忌,凡事涂赖,永远革退;今□着郭宗信永远入社伺候。将议定一应条规开列于后。”这通碑清晰地记载了村社和从前执事乐户的矛盾,中断和之前乐户的关系,重新选择了一位郭姓乐户作为本村村民丧葬活动的执事乐人。另外,《原头村为乐户勒索遵屡定案暨严示章程志》记述了当地村民和乐户之间的数次纠纷,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四十八年(1783)和道光十六年(1836)各有一次。经过当地县令的数次裁决,村社重新认定在该村红白事中乐户的规矩。
大量的碑刻记载了村社对丧葬演剧中乐户待遇的规定,包括执事时候的工钱、执事时候的着装,以及饮食等。关于丧葬演剧中乐工的工钱,乾隆四十九年(1784)《公议乐工计工付银碑》载:
大社公议,村中吉凶等事所用乐工并无一定条规,以致临事漫为科派,深属未便。今于乾隆四十九年三月议定:嗣后有事用伊伺候,照乐工人数,一工付尝银五分,不许额外生枝。恐事久无稽,今勒于石,永遵为例耳。
另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李诠庄村立婚丧事各役身钱开销规程碑记》:“鼓手乐工,遇婚丧事,身钱各依本村旧规,艮四分,门前伺候。”道光十六年(1836)《原头村为乐户勒索遵屡定案暨严示章程志》:“自示之后,凡遇婚丧事件,即遵照旧章程,婚事每名日给工钱壹百八十文,喜钱十文;丧事每名日给工钱壹百三十文,折孝帽钱二十文,坐门工钱八十文,毋得减少。”此不赘列。
有的村社在公示碑刻中亦规定丧葬演剧期间乐户的着装,且着装和工钱相联系,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大社五班社首公议条规碑记》:“有白事者,(吹手)穿白布号衣,每人筭给工银五分,穿白细氅每一人加银五分,如愿迎馔者,每一人加银五分。”
甚至一些规定更是细微到了极致,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大社五班社首公议条规碑记》:“其余客祭、引祭、引干丧,一应在内,不得额外筭工;凡有发引之日,每一人筭给工银一钱;如行一天事,不拘使吹手几名,止满折头孝钱五十文,如行三天事,每吹手一名折头孝布八十,有愿出给孝布者,任其自便;凡使吹手八名、六名者,外加科头一工,如使吹手四名者,无有科头工钱;凡村中围村、放路灯,每使吹手一名,止付给白面一斤。”
这一通碑包含着乐户具体在主家所做一切事情的收入,包括给不给孝布等。笔者在当地田野调查时,了解了一些当地丧葬习俗,只要去吊唁的亲友,主家一律给其一定数量的孝布作为答谢。这里便是规定给执事的乐户的孝布数量。另外,丧事七天内要放灯也使用乐户奏乐,另加白面一斤。再如,道光三十年(1850)《窑头村婚丧用乐规》载:
每吹手二名各工钱壹百六十文,其余人等各工钱壹百文。彼仍不遵,閤里公议。凡遇丧事本日全工,前日化纸算工半个,带辞灵者全工,堂祭祭干骨每名加工钱卅文,点主加工半个,送灯加工半个,祭七全工,带开吊者工壹个半。……迎送礼仪干粮、孝帽一应杂事俱无,不许争要。
关于乐户在丧葬演剧的伙食,乾隆五十六年(1791)《李诠庄村立婚丧事各役身钱开销规程碑记》记:“鼓手乐工,遇婚丧事……管早饭午饭,动荤者,与荤菜一碗,蒸食足用,折酒钱二十文;动素者,与素菜一碗,蒸食足用,无酒钱。俱无开销。早饭后出殡者,只管早饭,无酒钱亦无开销。”再如,道光十六年(1836)《原头村为乐户勒索遵屡定案暨严示章程志》载:“该吹鼓役人等一应吃食,随主自便,杂项全无,事主用几名来几名,均不得格外需索。”丧葬演剧乐户伙食看来是各村有各村的规矩。
要之,在三晋数万通碑刻中,所存村社管理碑刻数以千记,对乡村社会的管理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按照比例来看,对本村落丧葬演剧管理较为鲜见,且清代村社对民间丧葬演剧管理几乎都指向外部的乐户群体。这主要是因为,雍正朝之后,乐户的贱籍被废除,他们开始大量进入民间谋生,并将村社作为其服务的主体,这一时期乐户与村社之间最大的矛盾便是乐户想要抱团提高收入,而村社则想按照旧有规定去操作。在其与村社的合作中经常会因为价格或其他各项要求未达成共识而产生矛盾冲突,导致双方产生纠纷。但因为村社中婚丧等事不能没有鼓乐,因而必须设法解决,同时为避免后续再生事端,故立碑为证。由于山西是乐户集中的区域,因而在许多村社中都可以找到与此相关的碑刻,这对于了解乐籍制度废除对村社治理的影响有很大帮助。但是,从碑刻看,清代村社这种管理自己村落丧葬演剧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即村社默认这一现象的存在,同时还利用自己在地方社会中的组织优势一定程度上维护这种行为的持续。
三、对立共生的层级丧葬演剧治理
清代官府对民间丧葬演剧的治理主要集中在禁绝上,这一点学界已成共识。但,作为基层组织的民间村社对自己本村落的丧葬演剧治理和国家的治理方针则大相径庭,目前几乎未看到对其的严厉禁止。相对于官府一概而禁的治理用语,民间村社对其的治理则较为具体,几乎未提及官方治理中的演剧过度以及不合礼法等问题,而是针对丧葬演剧中所雇佣的乐户问题,大书特书,实际上默认了丧葬演剧在本村落的状态,村社对其整体是认同且不加阻止。比对同一时期的三晋碑刻,村社对聚落内部其它部分的治理基本与国家和地方官府制度保持一致,比如对待乞丐和流民等,始终保持着驱逐和禁绝的态度。即使是民间赛社,村社也时不时发出节俭开支和控制规模的管理制度,但是唯有对村落内民众丧葬演剧的态度,村社对国家的管控几乎视而不见。窃以为,造成此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清代官府和村社本身的立场和价值观严重不同。
传统社会的村社组织生于斯长于斯,村社对地方习俗高度认同,这是村社组织扎根民间的基础。风俗一旦形成,要想改变绝非易事。民间丧葬演剧由来已久,民众习以为常,早已内化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加以禁绝,甚至被认为是“黑葬”“不孝之举”,与国家儒教治国理念完全不同的是,村社反而认为丧葬演剧是孝的表现。
我们在清代山西的地方志中,可以看到丧葬演剧一般都被载于“风俗”中,如临汾县:“至于出殡之日,幢幡遍野,百戏俱陈,力不能备则以为耻,宁停柩焉。”寿阳县:“吊奠之客,辄用鼓吹盛筵以待之;若有必如是,乃称为孝,否则为人所鄙嗤者,失礼殊甚。”平遥县:“葬日,始设铭旌。奠用鼓吹、演戏,陈刍灵、幢纸……及发引,以僧道鼓吹导丧。”这类记载比比皆是。可见根深蒂固,影响之深。民间丧葬演剧相沿成俗,村社既然无法禁绝,倒不如因俗而治,加强对其具体问题的管理。这便是虽然国家和地方官府一致抱有对丧葬演剧禁绝的态度,但是民间社会却愈演愈烈的核心问题所在。
目前学术界虽对有清一代“皇权不下县”的统治模式有所争议,但清代县下地方统治薄弱当属不争的事实。乡村社会治理主要通过宗族和以神庙为依托的地方村社组织来维系,作为最基层的组织,其对聚落广泛存在的丧葬演剧应该负有管理职责。但,村社组织作为一种最接地气的民间自治组织,首先来源于村落中,首领均为村落民众遴选或者士绅充任,而这些组织与地方官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构成利益共同体,反而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处于相同地缘,血缘关系极为紧密,对于乡民热衷的习俗更多的是认同,主观上并不想禁绝。除此之外,一些政府要员致仕回乡,即使进入了地方村社的管理组织中,但出于对“天子不压社”的乡土情怀,仍是这些民间权威不敢发言的忌惮所在。
清代政府过分倚重基层自治,必然会造成政令难以通畅下达和严格执行,也正是这一问题的存在导致民间丧葬演剧在整个清代都在不断加强管控与不断失效中徘徊逡巡。然有清一代民间丧葬演剧虽普遍存在,却并未对整个社会秩序造成颠覆性的后果,从始至终也只存在于“劣俗”之中。民间村社在国家和地方官府的治理之下,主流管理一致,同时亦能在本土民俗的压力之下灵活变通,客观上来看,恰好是这种对立共生的治理模式起到了良好的减压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