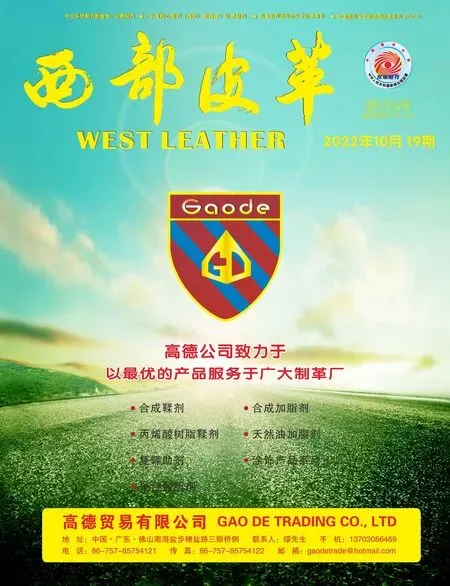关于左衽服饰的几个问题
郑子稷
(宁夏大学 民族与历史学院,宁夏 银川750000)
所谓“左衽”就是将上衣两襟中的左右衣襟交叉,右衣襟掩于左衣襟之上的襟式,“右衽”则与之相反。因孔子及后世诸多史家曾将“左衽”与北方“蛮夷之族”相对应,目前学界对左衽服饰多泛指“北方民族服饰”或“北方民族”,使之成为一种模式化的“概念”,但这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实际。邢义田先生运用图像史料得出左衽服饰只是华夏民族给夷狄人为建立的一种模式化形象[1],这是很有意义的。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北方民族服饰多左衽的现象、不同历史时期左衽意义的演变、汉服体系下的左衽服饰进行分析探讨,以期弥补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
1 北方民族服饰多左衽的现象
从商周时期甲骨文、金文中“衣”字的字形上,可以推知起初服饰衣衽的左右并不分夷夏。许慎在《说文解字》[2]中对“衣”字进行过解释,“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同时对衣字部的“袭”字也进行了解释:“袭,左衽袍。”《说文解字》解释的字形是“篆书”,其中不论是“衣”还是“袭”字的“衣”部,其字形的衣衽部分都是“左衽”状,且对于“袭”,许慎还专门指出是“左衽袍”,这说明了商周时期甲骨文,金文对衣衽中“左衽”的反映是可信的。之后篆书文字定型,凡为“衣部”的文字皆为“左衽”样式,从这里也能看出“左衽”服饰在先秦时期的中原地区应该不在少数。
左衽在汉族服饰中确有体现,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未占主导地位,真正以左衽服饰为主导的是北方民族。具体情况如表1 所示。
可见,先秦时期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服饰描述虽然未能直接说明其服饰的衣衽方向,但我们可结合先秦的文献记载“四夷左衽,罔不咸赖”“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22,23]推断出,当时戎狄的服饰应是普遍存在“左衽”现象。

表1 历代关于左衽服饰的记载Tab.1 The record of leftfront dress in previous dynasties
除以上有明确文字史料记载之外,回纥作为铁勒(敕勒)部的分支,其服饰我们推测应与敕勒相同,即为左衽。党项族服饰的左右衽在史料中并未有详细的记载,但从图2 榆林29 窟女供养人像和图3 西夏译经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党项人的服饰中是存在右衽现象的。清军入关后,满人的服饰衣衽方向也未有明确描述。但从保留下来的图像资料来看,除去立领圆领等不作讨论的形制,其服饰衣衽多为右大襟。

图2 榆林窟29 窟女供养人画像Fig.2 Portraits of female donors in Cave 29 of Yulin Grottoes

图3 西夏译经图Fig.3 Translated Sutras from the Tangut

图4 清代努尔哈赤像Fig.4 Statue of Nurhachi in Qing Dynasty
综上所述,自春秋至辽宋西夏金时期,北方民族服饰多以“左衽”为主。(西夏服饰虽主要为“右衽”,但这与其政权的形成本身受中原以及周边民族的影响较大有关。)但是,自元以后,不论是北方民族还是汉民族所建立起的大一统王朝,其服饰皆以右衽为主,且相关史料在记载服饰本身时很少去刻意突出衣衽的左右。
虽然“左衽”并非所有北方民族服饰的特征,但“左衽”在北方民族服饰中仍具有广泛性。运用广泛性的特征来对整体进行称谓,“左衽”并不是独有。比如“china”一词也是因为中国凭瓷器闻名世界,遂取瓷器的音译“china”来称中国[24]。
同时,以“左衽”来代指北方民族的观念大致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之后华夷的民族观念在秦汉时期逐渐定型。而中原汉民族地区在此时又普遍“尊右卑左”,如春秋时期《老子·道德经》中“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25],上将军位高于偏将军,故而“右”在春秋时期地位要高于“左”;其次《礼记·王制》记载,“执左道以乱政,杀”,疏“左道,邪道也。地道尊右,右为贵,右贵左贱,故正道为右,不正道为左”[4];再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26]。以上文字记载皆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普遍“尊右卑左”。《白虎通义》记载,“质家为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27],周朝作为崇尚文礼的朝代,“尊右”有其合理性,春秋战国作为东周的一部分和延续,在中原地区“尊右”亦能说得通。秦汉时期,《史记·陈涉世家》中“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的“闾左”即为“居住于里门左侧的平民百姓”,说明“左”地位更低;《史记·陈丞相世家》“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26],说明“右”比“左”尊;汉武帝时期制有“左官之律”,以法律的形式卑“左”;《汉书·王莽传》“然颇采其言,左迁鲁匡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5]中的“左迁”亦是如此。上述文献均证明在汉代中原地区主要尚右卑左。
同一时期的北方民族则主要“尚左卑右”。如《汉书·匈奴传》中“(单于)其坐,长左而北向”,说明左边的位置较为尊贵。同样《汉书》中亦载:“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单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长其众,居右地。”[5]因为是投降而来,纵使匈奴单于予以优待,但也不可能是将其安置在最好的地方,且文字记载既然突出了“右”这个方位词,由此推知,“右地”应是相对于“左地”较次的地方。再者匈奴官职中设“左、右贤王”,《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匈奴俗……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11],其中“左贤王”便是由太子充任,位高于“右贤王”。
2 不同历史时期左衽意义的演变
“左衽”一词本是服饰形制的名词,因时代需要,被赋予了政治意义且影响深远。但历史上不论是左衽的实际意义还是它的政治意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受时局以及“夷夏之辨”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左衽的意义会时常发生变化。
自“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在《论语》中出现,往后历代文献中多有直接的引用。如汉代《论衡》中有“周衰诸侯背畔,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8],唐五代《北齐书》载“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当右,尚书敬显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29],《宋史》中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裳之俗而为左衽之乡”[17],皆是对孔子关于左衽言论的直接引用。除此之外,关于左衽单独代指北方民族的文献记载更是数不胜数,如《晋书》“微禹之德,左衽将及”[30],《南齐书》“晋氏中微,宋德将谢,番臣外叛……左衽乱华,巢穴神州”[7],《旧唐书》“金者天地垂祥,祖宗垂佑,左衽输款,边垒连降,刷耻建功,所谋必克”[14],《宋史》“华缨就列,左衽来王”[17],等等。据此可知,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多将“左衽”单独与北方民族对应起来,进一步加深了“左衽”的政治意义。
虽然“左衽”一词代指北方民族的政治意义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但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政局的变化,儒家文化中关于“夷夏”思想的影响,其政治意义的程度还是有些许的不同。
如秦汉时期《史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噣,大膺大胸,脩下而冯,左衽界乘”[26]即为对赵武灵王的相貌和服饰的描述;《汉书》“殆将有解编发,削左衽,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5],《后汉书》“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11]都是对当时夷狄之人外在特征的描写。
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关记载有《晋书》“微禹之德,左衽将及”“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向若违左衽于伊川,建右社于淮服”[30],《南齐书》“是以编发左衽之酋,款关请吏,木衣卉服之长,航海来庭”“晋氏中微,宋德将谢,番臣外叛……左衽乱华,巢穴神州”“卿等傅文秀厚赂胡师,规为外援,察其徒党,何能必就左衽”[7],《陈书》“虽左衽已戡,干戈载戢”[31],《北齐书》“自东晋之违难……左衽浃于四方”[29]《北史》“编发左衽,声教所罕及”[32],等等。这些文字记载结合前文表格中同时期的内容可知,在魏晋南北朝的正史里,“左衽”既有代指服饰形制的实际意义,也有代指北方民族的政治意义,而且这种政治意义较为普遍且强烈,多与国仇家恨相关,明显体现了魏晋南北朝这一动乱时期的华夷对立。
关于隋唐五代时期“左衽”的记载有:《隋书》“其余被发左衽之人,控弦待发”“此其戎呼,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无复微管之功”[13],《旧唐书》“今上天垂佑,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于是御幸北门,受其献食,于时百僚端笏,戎夷左衽,虔奉欢宴,皆承德音”“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臣所以明左衽之叹,宣圣奖贤之深”[14],《新五代史》“而毡裘左衽,胡马奚车,罗列阶陛”[33]。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先前的民族融合以及唐王朝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并未有过多激烈的民族对抗,整体态势较为平和。所以,即使这一时期正史里关于“左衽”的记载除了服饰本身的实际意义之外,仍然存在以“左衽”代指北方民族的政治意义,但其语气相较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缓和了许多。纵然出现了“俾十九郡生民,竟沦为左衽,仅能自保,功何取焉”“晋武帝以采择之失,中原化为左衽”这类语气较重的言论,但结合史书上下文可知,“俾十九郡生民,竟沦左衽”是以唐朝中晚期唐与吐蕃发生战争为背景,而“晋武帝以采择之失,中原化为左衽”则是在借晋武帝的例子来劝谏唐文宗,两者皆是存在特殊背景。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史料中“左衽”的政治意义较为平和,无太强的对立色彩。五代时期,虽然政局较为动乱,但多为中原内部纷争,故而在相关史料中,对左衽的记载为纯粹的服饰描述。
辽宋西夏金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多民族政权并立时期,这一时期正史中关于左衽的记载较多,且主要集中在《宋史》一书中。《宋史》“又有渤海首领大锡里高模翰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华缨就列,左衽来王”“杞既受袭衣之赐,且以长为解,将辞复左衽”“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彼日益强,我日益怠……天下有被发左衽之忧”“金人讳其言,命邈被发左衽”“增募兵号三十万,而不改左衽,朝廷颇以为虑”“曦既僭位,议行削发左衽之令”[17];《金史》“妇人服襜裙……上衣谓之团衫……直领左衽”[18];《辽史》“番汉诸司使以上并戎装,衣皆左衽”[16]。以上史料显示,在这一时期,辽金正史中对左衽的记载皆为客观的服饰描述,而在《宋史》中,左衽的实际意义与政治意义并存。且从“祖宗数百年赤子尽为左衽”“天下有被发左衽之忧”等诸如此类的言辞里可以看出“左衽”一词在宋朝政治家眼里带有着极强的民族色彩。
因为史料浩如烟海,无法全部将其罗列,故而这一部分主要选择了相关时期的正史或较为官方的史书中关于左衽的内容来进行探讨分析。据上文分析,可得知一个大致的规律:“左衽”一词代指北方民族的情况自春秋滥觞,往后在相对稳定的大一统王朝的正史记载中,“左衽”多为北方民族服饰的客观描述。然而,在几次民族政权并立时期,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辽宋西夏金时期,在中原王朝的正史记载里,“左衽”一词更多的成为北方民族的代称,且含有极强的民族色彩,突出了“华夷对立”的思想。这一点与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的演变基本契合。“夷夏之辨”思想自春秋萌芽,后世儒家不断将其进行完善系统化,并极大程度地运用到了政治舞台,受时局影响或强或弱的体现:中原王朝实力越是强劲,“夷夏之辨”观念的体现越为模糊,且“华夷一体”思想逐渐凸显,如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原王朝实力越弱,为捍卫自身正统地位,“夷夏之辨”的思想愈为活跃,这不光在历史文献中有所体现,在时人的文学作品中亦有体现。如谢灵运《撰征赋》“中华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缓带”[34],又如陆游《感兴二首·其一》“尔来十五年,残虏尚游魂,移民沦左衽,何由血烦冤”[35]皆是如此。但是,自元起,官方史料中关于“左衽”一词的明确记载却大幅度变少,且不论是北方民族还是汉民族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关于“左衽”代指北方民族的用法都在急剧减少。特别是清代,即使是作为服饰的客观描述,“左衽”在官方史料中也难寻踪迹。其他文献虽仍有“左衽”政治意义的引用,但那大多是对儒家文化中孔子思想的单纯继承或是对史料记载的考证罢了,而这段时期“左衽”意义的变化在“夷夏之辨”思想的演变中亦能得到体现。元朝作为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王朝,在疆域上实现了大一统,同时在对边疆各民族的控制上也由原来的“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转变为了和中原汉族一体的“行省制度”,极大程度上削弱了“华夷”之间的区别。在清代,更是出现了“华夷一体”的观念,清军入关后不久,皇太极便提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36],将满汉等族视为一体[37]。
针对这种现象来分析,这并不是一种偶然。“左衽”政治意义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应运而生,由此发挥它的特定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长期碰撞交融,关于“中国”的认同趋于一种共识,“夷夏之辨”的思想濒于崩溃,华夷之间界限渐于模糊,各民族相互融合,形成了共同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中华文化,左衽的政治意义便不再适于历史的舞台,随时代而生的它也终究随着时代而没落。
3 汉服体系下的左衽服饰——民族交融的产物
“汉服”是一个出现于秦汉史籍,兴起于当代的服饰名词,关于其具体内涵有多种认识,其中较为广泛认同的解释是“汉民族传统服饰”[38]。
与“左衽”相对,“右衽”历来被认为是汉服的衣衽特征(仅为区别左衽,故不将对襟,圆领等形制列入)如唐颜师古曰:“右衽,从中国化”,唐刘景复《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中“麻衣右衽皆汉民”[39],清刘宝楠曰:“中夏礼服皆右衽”[40]等。针对这种绝对的观点,史料证明也不尽然。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记载,洛阳金村战国韩墓曾出土一组对舞妇女佩玉(图5),两舞女所着服饰衣衽方向为左、右衽皆存[41]。

图5 洛阳战国韩墓出土对舞妇女佩玉Fig.5 Dancing women wearing jade unearthed from the Han Tomb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Luoyang

图6 铜山西汉崖墓玉片舞人Fig.6 Jade dancer in the cliff tomb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Tongshan

图7 南昌东郊西汉墓出土汉代象牙饰舞人Fig.7 Ivory dancers of the Han Dynasty unearthed from the West Han Tomb in the eastern suburbs of Nanchang
《中国服饰史》一书中收录了一幅铜山西汉崖墓玉片舞人图以及一幅江西南昌西汉墓出土的汉代象牙饰舞人图。这两幅图中的舞人服饰皆有明显的左衽特征[42]。
崔溥在《漂海录》里记载了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 年)服饰衣衽的“左”“右”情况。“江南人皆穿宽大黑襦裤……妇女所服皆左衽……自沧州以北,女服之衽或左或右,至通州以后皆右衽”[43]。这就说明了在明代女子虽然普遍身着右衽服饰的,但是身着左衽服饰的现象也时有存在。
以上现象究其根本,实为民族交融后的结果。春秋战国,夷狄南下,诸侯争霸,为提升自身军队战斗力,中原诸侯力行改革,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虽然没有具体的史料证明当时胡服骑射里的胡服衣衽究竟为左还是为右,但从骑兵作战时需要搭弓射箭的特性以及当时北方民族普遍穿着“左衽”的习性来看,赵武灵王改革中的“胡服”应当为“左衽”。而中原服饰的这一重大变化也为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在服饰上更进一步的融合奠定了基础。北宋《梦溪笔谈》记载,“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44],生动地说明了长期的民族交往给服饰方面带来的影响。此外,明代女子服饰中出现左衽的情况也是民族交融后的产物。针对《漂海录》中记载的妇女服左衽的现象,崔浦后来给出了“辽为南京,金为中都,元亦为大都,夷狄之君相继建都,其民风土俗皆袭胡风”[43]的解释。因为辽金服饰多为左衽,在明朝之前又相继建都于此,受辽金风俗影响,所以此地出现“左衽”服饰亦不足为奇。
4 “左衽”殓服之辨
“左衽”服饰除了被视作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之外,在传统的汉文献中还被视为汉民族逝者服饰——殓服的特征。
历来学者研究中国古代丧葬礼仪的服饰一般都是从丧服入手,很少有人去涉及逝者所穿的殓服。此处区分一下“丧服”和“殓服”的概念,“丧服”是指在生者给逝者“服丧”时所着的服饰,通俗点来讲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披麻戴孝”中的麻衣和孝衣,只是在丧葬制度中划分更为仔细,而“殓服”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寿衣,为逝世者入殓时所着,两者服用对象不同。
4.1 “左衽”服饰缘何被认定为“殓服”
《礼记·丧大记》中记载:“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45]古人信奉阴阳,左阴右阳,阳即为在生,阴即为逝后。东汉郑玄为《礼记》做注时称“左衽,衽乡左,反生时”,唐代孔颖达继而疏解时称“生乡右,左手解抽带,便也。死则襟乡左,示不复解也”,二人皆将左衽服饰与逝者服饰联系起来,认为在生时服饰为“右衽”,死后应与生时相反,服饰便为“左衽”。故后人认为逝者殓服皆为“左衽”。如《汉族风俗史·第一卷》的丧礼风俗中提到逝者小敛时“然后举尸于衣上,先殓衣,皆左衽”,将逝者所有的殓衣都归为“左衽”[46]。
4.2 “殓服”并非都是“左衽”
针对前文的“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礼记今注今释》中解释为“小敛大敛的时候,不可以将祭服颠倒过来,衣衽都是向左开的,而且是用布条打结而不用纽扣”[47](这里的祭服只是指逝者众多殓服中的一类)。但在《礼记》原文中的此句,左衽的主语是“祭服”,而并非所有殓服,况且在该句之前还有一段类似的文字“小敛之衣,祭服不倒”[45],同样提到“祭服不倒”。古人服装分为上衣下裳,衣,裳分别很是明显,所以不存在是将衣,裳颠倒来穿,《礼记》的两段文字联系起来,只能是祭服的衣衽掩盖方向不能颠倒。此外《礼记》中所有有关丧礼制度介绍的文字中,仅在此处有明显“左衽”字样,且在另一本礼制著作《仪礼》中的《士丧礼》篇中也仅有“幂用苇席,北面左衽”一处有明显的“左衽”字样,但此处的“左衽”又并非指殓服。此外,清代万斯大在《仪礼商》中记载:“古人死者惟袭衣亲身,服如生时,而左衽为异。小敛、大敛,则取衣包裹。”①说明逝者服饰除了衣襟居左的袭衣之外,小敛大敛时都是取衣物直接包裹尸体,并没有刻意去区分服饰的左右衽。况且,《老子》一书中有“凶事尚右”[48]的记载,若此为事实,那么对于丧事中,殓服不用右衽而皆为左衽之说便就有些说不通了。且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图8)同样是逝者死后所着的殓服,却是右衽而非左衽。据此认为在丧礼制度下,殓服的确存在“左衽”现象,但仅限于殓服中的少数服饰,并非所有。所以,以“左衽”代指汉民族逝者殓服实为以偏概全不严谨的说法。

图8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Fig.8 A plain-woven excavated from the Han tombs in Wawangdui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历史上,服饰的“左、右衽”并不是区分“华夷”的实际标准,左衽也没有在汉民族逝者的殓服中得到普遍的运用,它只是一个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特定的需要而被赋予了政治意义的形象化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加强,华夷界限的模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左衽”这种政治化的产物也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注释:
①[清]万斯大《仪礼商·卷二》。此处转自2015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晨阳、张珂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辞典》第61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