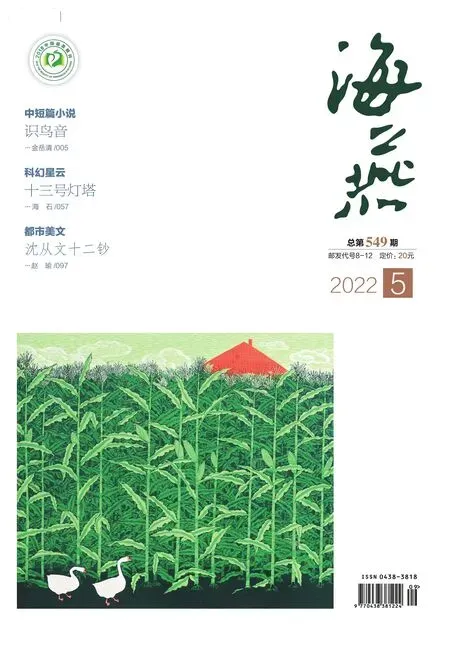沈从文十二钞
文 赵 瑜
之一:《我的家庭》
沈从文是一个有苗族血统的汉人。
他的父亲,是一个苗族女人生的,后来过继给他的爷爷。
他的母亲懂诗书,教会了他很多。
我以前读沈从文的文字总是躺在床上,发现沈从文是一个调皮的孩子。
今天,我坐在电脑前读沈从文的文字,发现他是一个爱炫耀的孩子。
是啊,如果不是懂得炫耀记忆中的美好和温暖,他是不会成为一个作家的。
我们多数人都有美好的情怀,只是,我们把这些情怀都掩埋在自己的心中。那么,我们只能逐渐地忘记,让草把美好的情怀荒芜。
沈从文在《我的家庭》一文中炫耀了他的祖父,真实的情况是他的继祖父,叫作沈洪富,卖马发家,后来做了大清朝云南昭通镇守使、贵州总督。
他还炫耀了他的外公,叫作黄河清,是一个贡生,是当地唯一的读书人。他的舅父办了他们县第一个照相馆,还办了当地第一个邮局。他的母亲懂得医方,会照相。
说他炫耀,有些牵强,沈从文不过是一种很平常的叙述。但是,此段中的炫耀并无不敬,只是说明一下,沈先生有很好的家教,是幼小时的那种氛围给了他营养,让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知名作家。
之二:《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沈从文的认字速度很快,不到一年就认识了600个字。那时候他只有4岁。
生了蛔虫的沈从文当时的治疗方法是,用草药蒸鸡肝当饭。
6岁的时候,沈从文又出了疹子。他和弟弟一起得了病。发烧、咳嗽。家人为了让他能凉快一些,竟然用两张竹席子把他和弟弟包裹起来,竖在客厅中,就那样站着睡。
现在想一下,尿尿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时候医疗条件很差,有很多病是不能得的,一旦得了,治不好就只好扔掉。
所以,沈从文在文章中写道,两个人在房子里被竹席子卷着,外面的院子里放着两口小棺材,备用。
沈从文的逃学是出了名的。他的父亲曾经对他的逃学很恼火,威胁他说,如果再逃学的话,就要剁掉他的一根手指。
沈从文的逃学有他自身的原因,因为他是一个早慧的孩子,很早他就已经学会了那些书上的内容,这个时候他就会认为自己比同龄的孩子水平高,所以,他不愿意和那些平庸的孩子在一起。
这种逃离集体的行为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恰恰因为他的逃学,让他更为细致地观察了乡村里正在发生的一切细节。那些细节像一些花和草的种子一样生长在他的记忆里,直到多年以后的一天,长成了一篇又一篇优美的文字。
湘西有美丽的水,沈从文回忆自己对美的认识也是从水开始的。
是啊,当夏天的炎热到来时,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水,那是多么美的一种享受。
沈从文写到学校私塾里的一个不能下河的规定:老师在孩子们的手心里写下一个“红”字。但沈从文的一个张姓表哥就教他在游泳的时候把一只手举起来,那手自然就湿不了。这样的对策相当管用,让他知道,撒谎也是需要智慧的。
沈从文自从尝到说谎的好处以后,开始根据各种经验来制作各种谎言。
他不喜欢学校,喜欢一个人到校外去看看。他感觉,那样的自己才是自由的。
他像一个群众演员,在大自然里旁若无人地走着。为了能走到无人认识的地方,他通常要走二三十里路,看别人编织竹簟、做香,有时候也会看别人下棋。如果有人打架,他也是乐于做观众的。看人家如何对骂,最后结局如何。总之,他满目新鲜,所“阅读”的内容绝不比书本上的内容逊色。
练习想象力是被老师发现逃课以后的事情。
沈从文的这段文字给所有爱玩的成人一面回忆,他在这段文字里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被处罚的时候练习想象力的。
相反,每一次老师处罚他,他甚至感觉是一种想象力的享受,譬如他会根据季节不同,把心里的想法插上翅膀飞出校园。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他会想到河中鳜鱼被钓起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歌呼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
他的这种想象力练习为他成为一个作家提供了可能。
沈从文喜欢光着脚在路上走。把鞋子脱下来拿在手上,然后光着脚在路上走。
这让我联想到,他成长的湘西的土路的柔软,一定是适合一个孩子到处乱跑的湘西,一定是适合一个人寻找自己的梦境,坐在一棵树下或者一潭水边发呆的湘西。
我准备遇到这样的湘西。
杀人或者杀牛本来是一件极其血腥的事情,可是在沈从文的笔下却来得轻巧,像一场童话中的黑色背景音乐。
沈从文描述的杀人是犯人被杀掉以后的事情,作为一个孩子,他喜欢去看看人死了以后到底还会不会动。于是他拿着一根木棍往那些碎断了的死人身上撬来撬去,发现那些人已经不会动,终于心里产生一股害怕,吓得快跑离去。
杀牛是他每天都看到的事情。由于每天杀牛的时间不太相同,有时候他路过杀牛场的时候是刚开始磨刀,有时候是刀已经捅进了牛的肚子里,那牛已经慢慢倒下,有时候那牛已经完全断了气,肚子里的东西已经被掏了出来,像博物馆里的展品一样地摆在地上。
长期地路过一个杀牛场,他对一头牛的死去非常熟悉。在我的想象中,死亡一定是一件哲学的事情。在一个孩子眼里,一头牛的死亡像一场舞蹈,像一场悲伤的歌唱,像一个无助的眼神,像一棵树倒下,且枣子都落到水里被冲走。
鞋子对于沈从文来说是一种音乐。
下雨的时候,他的家里按规定要穿一种钉鞋的。现在,我们已经想象不出钉鞋的样子了,大概是布鞋的下面钉了铁的东西,以免被雨水泥泞湿透。
沈从文在文字中描述的钉鞋是这样的:“虽然在半夜时有人从街巷里过身,钉鞋的声音实在好听,大白天对于钉鞋我依然毫无兴味。”
捉虫子也是一种人生哲学。
沈从文不动声色地讲述他捉蟋蟀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当他两只手各捉住一只蟋蟀的时候,还会听到第三只蟋蟀的叫声。于是,他就又去捉第三只,但伸手的一瞬间,手里的蟋蟀已经逃跑。
因此,他捉来捉去,到最后手里仍然只有两只。
这是一个人生的比喻,我们的一生有许多事情是缘定好了的,不论我们如何努力,我们的两只手就只能捉两只蟋蟀。因此,有了这两只蟋蟀,大可不必去捉另外的了。
当然,作为孩子的沈从文当时不会明白这些的。
有些问题,我现在也不明白。
譬如: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在烧红的时候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什么雕刻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为什么小铜匠在一个铜板上钻一个圆眼?
我现在仍然不熟悉这些声音。
譬如:蝙蝠的声音,一头黄牛当屠户把刀刺进它喉中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泼剌的微声。
之三:《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想象力。这大概与四周的环境有关系。
生长在四周有流水的地方总比四周只有院落的孩子好一些。
整天看到青草和羊群的孩子的想象力要好过在城市里住六楼的孩子。
沈从文说到了湘西的树。他和几个孩子一起比赛爬树,爬不同的树,于是,他自然地就认识了很多种树。爬树时摔破了脚或者刺破了手,那么几个小伙伴就一起去采草药,自然地,他又认识了数十种草药。
我们的一生学习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是靠书本或者别人的口述,有时候却需要自身的经历。
我们的想象力也和这些经历有关系。
湘西水多,沈从文每隔数百字就会写到游泳的细节。
每一次游泳都有好玩的情节。譬如他写到“水马”,大致情形是这样的,把裤管泡湿了,扎紧了裤管,向空中急急的一兜,捕捉了满满的一裤管空气,再用带子捆上,便成了“水马”。这样,即使不会游泳,也可以把自己漂起来。
只是,此方法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用。
苗族人的赶集和中原的人大同小异。
不过是卖东西的人在那里发誓似的讨价还价,卖鸡蛋的、卖山货的。唯一不同的是,那时候有小型的赌场吸引赶集的人们。
也有卖不同小吃的扎堆在集市上,那些希望改善生活的人,逛累了,买一份汤水,解解馋。
最值得一提的是,“竹筏上常常有长眉秀目脸儿极白奶头高肿的青年苗族女人,用绣花大衣袖掩着口笑”。
沈从文的描述极其简洁,却一下子击中我的心,我想去看看那青春娇美的苗族女人。
湘西传统的赶场极有气氛,适合孩子们扎堆去玩耍。
沈从文的文字中描述了那山路两边物品的丰硕,譬如无数的桃树和李树,果实把树枝压得弯弯的,等待赶场的小孩子们去为它们减除一份负担。还有黄泥地里的红萝卜大得如小猪头一样,没有这些饥饿的小孩子去挖它们、吃它们、赞美它们,那萝卜便始终委屈地在那深土里默默地沉思着。路边还杂生着莓类或者野生的樱桃,还有甜滋滋的枇杷,还有到处可以采摘的山果。
那画面堆积的甜美让我的味觉瞬间复苏,想骑着自行车,沿着沈从文的描述去一棵树一棵树地采摘,品尝湘西甜美的意味。
那个在沈从文之前并不出名的湘西,一下子被大家阅读。
沈从文把自己生长的这个地方比喻为一本大书,他认为:“总而言之,这样玩一次,就只一次,也似乎比读半年书还有益处。若把一本好书同这种好地方尽我拣选一种,直到如今,我还觉得不必看这本弄虚作伪千篇一律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却应当去读那本色香俱全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
是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以后要天天去走路,哪怕只是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厕所。
之四:《怀化镇》
怀化镇,沈从文的人生在这里有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他认字比较多,又喜欢写字,在怀化,沈从文成了一名上士司书。
在怀化镇的一年零四个月里,沈从文看到过有七百多人被杀死的全过程。
他在文章中这样记忆:“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头被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的心上有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读‘子曰’的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
沈从文比鲁迅等其他作家晚生了几年,但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同,但当同时代的作家都一一被战争的怒火吞食时,沈从文却用独特的视角,安静地描述了那个年代的悲伤。
是啊,人性中的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不是因为战争就全部改变了。
杨姓祠堂,是沈从文的部队所在的地方。
不知道现在的怀化还有没有这个地方,在沈从文的笔下,是个热闹的所在。
“祠堂对门有十来个大小铺子,那个豆腐作坊门前常是一汪黑水。那个南货铺有冰糖红糖,海带蜇皮,有陈旧的芙蓉酥同核桃酥。”
最有趣的,应该是他所描述的烟馆的情景了:“那个烟馆门前常常坐一个年纪四十来岁的妇人,扁扁的脸上擦了很厚的一层白粉,眉毛扯得细细的,故意把五倍子染绿的家机布裤子提得高高的,露出水红色洋袜子来。见兵士同伙夫过身时,就把脸掉向里面,看也不看,表示正派贞静。若过身的是穿着长衣或是军官,她很巧妙地做一个眼风,把嘴角略动,且故意娇声娇气喊叫屋中男子,为她做点事情。这点富于人性的姿态,我当时就很能欣赏她。”
沈从文的思考渗透在湘西的山山水水里,曲折的道路、多姿的人生里。
沈从文的职业困惑在怀化镇的时候就产生了。
他虽然是个文书,但有时候还要兼职做一下厨子,原因是他懂得煮狗肉。
安静而腼腆的沈从文在对待杀人或者杀狗这件事情上,显得有些态度硬朗,他认为,弱肉强食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他在文章中详细地记录了做狗肉的经过:“一个人拿过修械处打铁炉上去,把那一腿狗肉皮肤烧烧,再同一个小副兵到溪边水里去刮尽皮上的焦处,砍成小块,用钵头装好,上街去购买各样作料,又回到修械处把有铁丝贯耳的瓦钵,悬系在打铁炉上面,自己努力去拉动风箱,直到把狗肉炖得稀烂。”
看沈从文做得如此专业,不由得羡慕和他一起当过兵的朋友们。
怀化在沈从文的笔下有很多鱼。
“可以在晚上拿了火炬镰刀到小溪里去砍鱼,用鸡笼到田中去罩鱼。”
砍鱼,可见那鱼之大;在田中罩鱼,可见那鱼之密。
黄鼠狼是一个贬义词。
在沈从文的笔下,竟然也成了有用的动物。
“上山装套设阱,捕捉野狸同黄鼠狼。把黄鼠狼皮整个剥来,用米糠填满它的空处,晒干时用它装零件东西。”
试想一下,我们现在的再好的真皮包具,也没有沈从文的创意来得自然而有趣。
和我的童年差不多,沈从文是一个看到什么东西都能喜欢上的家伙。
在怀化,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熔铁工厂。立个高过一切的泥炉在大罩棚下喘气冒烟。那么,沈从文像儿时发现了可以游泳的水池一样兴奋。
“当我发现了那个制铁处以后,就常常一个人跑到那里看他们工作。因此明白那个地方制铁分四项手续,第一,收买从别处担来的黄褐色原铁矿,七个小钱一斤,按分量算账。其次,把买来的原铁矿每一层矿石夹一层炭,再在上面压一大堆矿块,从下面升火让它慢慢燃。第三,等到六七天后矿已烘酥冷却,再把它同木炭放到黄泥做成可以倾侧的炉子里面去。一个人把炉旁风箱拉动,送空气进炉腹,等铁汁已熔化时,就把炉下一个泥塞子敲去,把黑色矿石渣先扒出来,再把炉倾倒,放光的白色溶液,泻出倒画成方形的砂地上,再过一会儿白汁一凝结,便成生铁板了。”
读沈从文的文字,我常常会想起后来的一些作家,譬如汪曾祺、贾平凹等,这些人的细节描写大概有沈从文的影响在里面。
但我又想到了我自己写童年的事情,也写得很细,事实上,我并没有读过多少沈从文的作品。看来,有很多经验,是我们长期积累在心中的一些反应,和我们读过谁的作品没有关系的。
作为一个写作者,有时候,我拒绝读别人的小说,原因就是怕它们影响我的写作欲望。
好在我读书挑剔,遇到太好的,或者太不好的作品,我都会放下。
之五:《女难》
沈从文喜欢辰州(现在的沅陵)的一个河滩。
那里大概泥沙均匀,适合散步。
河滩上来来回回停留的船只很多,有个别样式独特的船横在泥泞里,制造了让人联想的意境。
沈从文每一次看到都会添出一段忧愁来。
这是沈从文的一句名言:“美丽总是愁人的。”
在《女难》这篇文章里,沈从文一改过往调皮的回忆,竟然走婉约派风格,写出了很多忧伤。
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又写到了那个卖汤圆的老人。他和老人聊天,看看街道。忽然就感觉寂寞了。
关于寂寞的描写,沈从文的文字极其排比。
“我感觉我是寂寞的。记得大白天太阳很好时,我就常常爬到墙头上看驻扎在考棚的卫队上操。有时候又跑到井边去,看人家轮流接水,看人家洗衣,看他们做豆芽菜的如何浇水进高桶里去。我坐在那井栏一看就是半天。有时来了一个挑水的老妇人,就帮着这妇人做做事,把桶递过去,把瓢递过去……”
寂寞有时候表现为自己无事可做,有时候表现出喜悦。
譬如,沈从文当时已经升职为士官,可他还穿着普通的士兵服装,于是,走在街上的时候,别人还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士兵来对待。
他心里有一股暗暗的欢喜。不过,这种欢喜持续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转变为失落或者寂寞。
寂寞可以让人沉沦,也可以让人发愤。
沈从文显然属于后者。他有时候会为自己身上的那身衣服感觉羞涩。
沈从文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读书人,他希望大家都能知道这一事实,并给他以尊敬。这一点我也是,呵呵。
于是,在经过寂寞的街道行走以后,他会回到自己的宿舍里,发愤地练习半天小楷字。
事实证明,这种发愤改变了他的一生。
人生没有什么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有追求。不信,你试试。
部队生活结束以后,沈从文的职业变化很多。先是在警察局工作,负责抄写每天的处罚条例。
后来,警察局把税收的工作也接管了过来。于是,他又负责填写税单,譬如要登记每只猪抽收六百四十文的税捐,一头牛要收一千文。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沈从文开始受到别人的款待。
对了,那个时候的沈从文的月收入是十二千文。
因为沈从文的舅父和另外的亲戚喜欢作诗,所以就找来沈从文替他们抄写诗歌。
时间久了,沈从文也有写诗的欲望。
十七岁那年,这个自称是乡下人的沈从文已经月收入十六千文,并吸引了众多的女孩子。
到此,我才明白,这篇文章的名字为什么叫作“女难”。是啊,是女人喜欢他,并给他的人生带了难处。
结果,那个女孩子不过是喜欢上他的钱,骗了他的钱以后,借着战争的借口,消失了。
他的人生从此得到了教育。
在这个笔记的最后,我仍然想把沈从文的这段话做一个摘录:“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就那么的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该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有财产的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县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还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是啊,生活总会有出乎意料的情节安排,这样,我们活得才有意思。
之六:《辛亥革命的一课》
关于童年的文字,更多的时候是成年人交换的阅读。
也就是说,不管是谁的童年,都不会引起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往往那些写儿童时代的文字,都是一些大人或者老人去看。
沈从文的文字也是如此,他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一开篇就写道:“有一天,我那表哥又从乡下来了,见了他我非常快乐。我问他那些水车,那些碾坊,我又问他许多我在乡下所熟习的东西。可是我不明白,这次他竟然不大理我,不大同我亲热。”
沈从文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一下就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只有有过童年生活经验的人才能读出其美妙。
我在读的时候忽然笑出声来,不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的文字,是因我想起被我拴住的一只青蛙。它唱歌唱得声音很大,穿过二十余年的光阴,终于传到我的耳朵里。
之七:《一个大王》
沈从文去四川的经历改变了中国的现代文学史。
因为,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他写出了惊世的《边城》。
那时候,沈从文是贺龙的部下,贺龙是团长,他大概是文件收发员。
那时候部队里都流行去四川,从湘西去四川的男兵们都说,一是可以讨漂亮媳妇,二是可以捞一些银子。
沈从文在文章中写道:“我所想的还不是钱、不是女人。我那时候自然是很穷的,六块钱的薪水,扣去伙食两块,每个月手中就只有四块钱,但假若有了更多的钱,我还是不会用它。得了钱除了充大爷邀请朋友上街去吃面,实在就无别的用处。”
对于女人,在《女难》中沈从文已经描写过了,他自从被女人骗过以后,就不再对女人感兴趣,相反的,他很在意上司的肯定。
最终,促使沈从文入四川的原因是巫峡。
热爱行走,甚至连一条河街都不放过的沈从文怎么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呢?
“我听他们说起巫峡的大处、高处和险处,有趣味处,实在神往倾心。乡下人所想的,就正是把自己全个生命押到极危险的注上去,玩一个尽兴。”
于是,沈从文遇到了那传奇的人物:山寨大王。
有必要介绍一下,沈从文入四川时的全部家当:一双值一块二毛钱的丝袜子,半斤冰糖,旧棉袄一件,旧夹袄一件,手巾一条,夹裤一条,青毛细呢的响皮底鞋子一双,白大布单衣裤一套。另外还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褚遂良《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集》,一双自由天竺筷子,一把牙刷,一个搪瓷碗。
沈从文形容自己的全部产业时,用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词语:动人。
是啊,那真是一个动人的产业,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全部细节。
沈从文从湘西入四川的路线非常经典,值得在这里推荐一下,这一定是很好的自助游线路。
先从湖南边境的茶峒到贵州边境的松桃,又到四川边境的秀山。沈从文步行用了六天,后来到四川的龙潭。
按照现在的自行车速度,应该两三天就行了。
我有这样的试验兴趣。当然,要依靠当地的天气和现行的路况而定。
在贵州和湖南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高坡叫作“棉花岭”,上去三十二里,下来三十五里。爬上去以后,可以看到一群小山,在云雾里妖绕。
离这儿不远,有一个大场,是一个牛马交易的专业市场。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沈从文的描述中,每一次赶场的时候到了,都会有五千牛马在那里交易,那场景一定很壮观!
离牛马场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古寺院,照例,寺院必有古松,古松很粗,六人合抱也抱不完。
终于到了四川东边上的龙潭。龙潭因为有一个龙洞得名。
龙洞流出来一股泉水,冷如冰水,即使在炎夏季节,行人也不敢洗手洗脚,手一入水,骨节便疼痛麻木,失去知觉。
沈从文常常用一个大葫芦贮满了生水回去,用那冰水招待朋友。
沈从文年轻时对书法很有追求,曾写这两句贴在自己的房间:“胜过钟王,压倒曾李。”
大概那个时期沈从文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钟、王二人,钟是谁呢?王应该是王羲之或者王铎。活着的却有曾庆髯和李梅庵。
在四川的时候,沈从文的月薪是九块钱。可是,他不注重穿衣,喜欢吃面食,于是,衣服没有增加一件。
一次下雨了,他刚洗的衣服还没有晒干,不好意思光着身子去食堂里打饭,于是,饿了半天。
这个时间,他认识了那个大王。大王叫作刘云亭,很有传奇经历。
譬如他曾经一个人徒手打死过两百个敌人,还娶了十七位押寨夫人。有一年,在辰州的时候,大冬天有人说:“谁现在敢下水,谁不要命。”这个山大王什么话也不说,脱了衣服就跳进水里,而且还在水里游泳了一个小时。
他还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主儿,有谁钱包被掏了,告诉他,他一准会追回来。这个大王被沈从文部队的司令官救了一命,于是就投靠了司令。
大王天天给沈从文讲故事,有时候还给沈从文唱戏。他甚至也爱好书法,还会画两笔兰花。于是,他们两个熟悉起来。
两个人还一起去监狱里探望大王旧时的相识,一个女土匪。
后来,那大王喜欢上了一个洗衣妇。结果司令员不许,于是,大王就请假回家,想继续过自己的山大王生活,顺便也想邀请沈从文加入他占山为王的行列。
但是没有走成,大王被司令官绑了,杀了。
沈从文从此离开了那个司令官,离开了四川,又重新回到了保靖。这种情节在沈从文的散文中并不多见,像极了小说。
自然,沈从文以后作小说,也常常会想起这个大王的。因为,他的传奇经历让沈从文认识到,人生可以庸庸碌碌、平平淡淡,也可以杀人放火、烧杀抢掠。
之八:《一个转机》
从四川回到湘西之后,沈从文迷上了历史和古典画卷。
他像一块干涸的土地一样,吸收可能到来的所有水滴。
后来,他有机会进入刚办的湘西乡报馆做了校对。
那时候的沈从文不过二十岁,看到报纸上有人做好事,帮助别人。他也就模仿着,把自己的工资全都买成邮票,装进了一个信封里,另外又写了一张信笺,说明自己捐款兴学的意思,并署名为“隐名兵士”,悄悄地把信寄到上海《民国日报觉悟》编辑处,请求转交工读团。
沈从文每每想起自己偷偷做的这件事情,还总会感觉到有一种秘密的快乐。
这是一种私人的快乐。
在报馆工作不久,沈从文就又被部队抽调了回去。
但很快他就被一场大病折磨,高烧得不能进食,头痛得像被斧子劈开,血一碗一碗地流。沈从文支撑了四十天,竟然活了下来。
然而就在同时,他的一位乐意同他谈论生活和理想的好友陆弢却被河里的流水冲去,淹死了。
这给了沈从文又一个教育。他想,如果自己活着还有许多事情不明白就死了,那是多么悲伤的一件事情。
于是,他向部队里的领导打报告,说要去北京读书。
沈从文的理想是,如果读书不成就去当警察。警察也做不了的话,那就只好认输,不再做别的好打算了。
沈从文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人,他自己身体孱弱,且性格并不外向。所以,常想象着自己能有一个不用求别人也能生活滋润的职业,譬如警察。他的这种可爱让我想起了他同时代的豪华女人张爱玲。张爱玲年轻时也曾经有过这样烂漫的想法,看到有人受欺负,她就想自己应该嫁给警察局长做老婆,那样就可以帮助被欺负的人了。
这种性情,着实可以赞美。
沈从文进北京的路线竟然要路过郑州。那时候郑州已经是中国铁路的十字交叉口。
他的路线大致是这样的:从湘西到长沙,从长沙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到天津。然后,这一下走了十九天,才到达首都北京。
他被一个拉车的送到北京西河沿的一个小旅馆,并在小旅馆里用自己漂亮的虞世南体的小楷写下:沈从文 年二十岁 学生 湖南凤凰县人。
于是,沈从文的另一个人生开始了,从此,他走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之九:《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沈从文喜欢这个好色的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这个朋友的花草逸事。
“他也可以说是一个渔人,因为他的头上戴的是一顶价值四十八元的水獭皮帽子,这顶帽子经过沿路地方时,却很能引起一些年轻娘儿们的注意。这老友是武陵(常德)地域中心春申君墓旁杰云旅馆的主人。常德、河伏、周溪、桃源,沿河近百里路以内吃四方饭的标致娘儿们,他无一不特别熟悉。”
接下来,沈从文又补充介绍:“他二十五岁左右时,大约就有过一百个女人净白的胸膛被他亲近过。我坐在这样一个朋友的身边,想起国内无数中学生,在国文班上很认真地读陶靖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情形,真觉得十分好笑。同这样一个朋友坐了汽车到桃源去,似乎太幽默了。”
路上的风景像水墨山水画,这是值得注意的风景。
“从汽车眺望平堤远处,薄雾里错落有致的平田、房子、树木全如敷了一层蓝灰,一切极爽心悦目。”
两个人一致认为,这窗外的景致像极了沈周的画卷。
可是,船行到一半,到周溪的时候,天落了雪,夜晚也到来了。这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突然想起大周溪的一个长眉毛白脸庞的小女人,于是,便开始打扮自己,穿了自己随身带的崭新的绛色缎子猞猁皮马褂,从那被冰雪冻结了的大小木筏上慢慢地爬过去,谁知,大概是过于心急,他一下落了水。他一面叫着沈从文的名字,大呼自己要完了,一面挣扎着上岸。
虽然全身已经湿透,冻得浑身打战,可是他还是换上了一件新棉军服,又一次高兴地爬到岸上,到他心中惦念的女人身边睡觉去了。
沈从文在自己的文字里细致描述着这个有趣人的形象,同时在表达着湘西的女人的诱惑力。
落水了,还要再一次爬到岸上去,那个女人一定有着姣好的容颜和温暖的身体。
作为一个读书人,沈从文有数不清的羡慕对象。譬如羡慕铁匠能打一手好铁,羡慕牧羊的人能听懂羊的叫声。
同样,沈从文也羡慕这个好色的戴水獭帽子的朋友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
“辰河沿岸的码头的税收、烟价、妓女的价格及白嫩程度,桐油、朱砂的出处行价,包括各个码头上管事的头目的姓名爱好,他知道的似乎比县衙门里的那些人知道的还多。”
这个时候,沈从文又一次痒痒地写到了他年轻时亲近过的那一百个年轻的女人。“他事情懂得多哩,只要想想,人家还只在二十五岁左右,就有一百个青年妇人在他面前裸露过胸膛和心灵,从一个普通读书人看来,这是一种如何丰富吓人的经验!”
言外之意,沈从文想说什么,我不好恶意猜测。毕竟,我喜欢沈先生的朴实的文字。
从常德到桃源坐汽车竟然很近,旧时的路和车只用一个半小时。如今,我想,会更快了吧。
之十:《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我和沈从文一样,羡慕那些水手。
有的水手没有相好的情人,只好在天亮的时候诅咒那些有情人的水手。
那些个水手都是多情的,我看着沈从文的文字也觉得有趣。
“大木筏都得在天明时漂滩,正预备开头,寄宿在岸上的人已陆续下了河,与宿在筏上的水手共同开始从各处移动木料,筏上有斧斤声与大摇槌彭彭敲打木桩的声音。许多在吊脚楼寄宿的人,从妇人热被窝里脱身,皆在河滩大石间踉跄走着,回归船上。妇人们恩情所结,也多和衣靠在窗边,与河下人遥遥传述那种种‘后会有期各自珍重’的话语。很显然的事,这些人从昨天那点露水恩情上,已经各在那里支付分上一把眼泪与一把埋怨。想到这些眼泪与埋怨,如何糅进这些人的生命中,成为生活之一部分时,使人心中柔和得很。”
这个时候,叫作牛保的多情水手依旧在他的风流乡里不舍得出来。
沈从文的船将要离开了,忽然就听到,邻居船上的水手在大叫:“牛保,牛保,不早了,开船了呀。”
许久没有人回答,于是那两个水手就又重复地大声叫喊:“牛保,牛保,你不来当真船开动了。”
再过一阵儿,催促就变为辱骂,吊脚楼上的那个牛保被骂醒了,从热被窝里的女人手臂中起来,光着身子爬到窗边来答话:“宋宋,宋宋,你喊什么,天气还早咧。”
“早你的娘,人家木排全开了,你疯了一夜还尽不够!”
“好兄弟,忙什么?今天到白鹿潭好好地喝一杯,天气早得很!”
“天气早得很,哼,早你的娘!”
“就算是早我的娘吧。”
叫作牛保的多情水手,光着身子趴在冬天的窗口和下面同事说话的这句台词真叫作快感。可是,我们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灵纯净无比,丝毫没有淫念,这大概就是沈从文先生下笔时的那股冷净。
年轻时的沈从文是个爱探听别人隐私的人。
当然,这也是他的职业敏感而已,他想见见这个叫作牛保的水手。
“河岸上有个蓝布短衣青年水手,正从半山高处人家下来,到一只小船上去。因为必须从我小船边过身,故我把这人看得清清楚楚。大眼,宽脸,鼻子短,宽阔肩膊下挂着两只大手(手上还提了一个棕衣口袋,里面填得满满的),走路时肩背微微向前弯曲,看来处处皆证明这个人是一个能干得力的水手。我就冒昧地喊他,同他说话:‘牛保,牛保,你玩得好。’”
那个水手竟然真的是牛保。
正在沈从文和牛保搭话的时候,吊脚楼里突然探出那个头发散乱的妇人来。
对着牛保大声喊:“牛保,牛保,我同你说的话,你记着吗?”
牛保有些担心那妇人,就大声回话:“哎哎,我记得到!……冷,你是怎么了啊,快上床去!”
妇人似乎不太理解牛保那一瞬僵硬的回话,认为牛保太理智了,一出被窝就这么生分,有些生气,说:“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说着,“嘭”的一声就把格子窗放下了。
这一番对话,让我充分相信,身体之间的碰撞说不定才是真正的爱情。
什么精神之恋就过分虚无了。
我真的被下面的细节感动了。
大概这是最平常的一些细节了,但往往动人的,就是它们。沈从文的文字在这一段并不出色,但也不必过分修饰,最美好的情感,有时候是不需要修饰的。
“我的小船行将开时,那个青年水手牛保却跑来送了我一包核桃。我以为他是拿来卖给我的,赶快取了一张值五角的票子给他。这人见钱只是笑。他把钱交还,把那包核桃从我手里抢了回去,说:‘先生,你买我的核桃我不卖。我不是做生意的人(他把手向吊脚楼指了一下,话说得轻了些),那婊子同我要好,她送我的。送了我那么多,还有栗子、干鱼,还说了许多痴话,等我回来过年呢……’”
沈从文为了报答牛保,就随手拿了四个烟台的苹果给了他,且问他:“你回不回来过年?”
他只笑嘻嘻地把头点点,就带了那四个苹果飞奔而去。
船要开了,沈从文又听到隔壁船上的水手在大声骂,“牛保,牛保,你是怎么的?还不下河,我翻你的三代,还……”
听到水手的骂娘声,沈从文才明白,原来,那四个外地带来的苹果,牛保不舍得吃,就跑到吊脚楼去,送给了那妇人。沈从文猜测,那牛保一定会告诉那妇人这苹果的来源,说来说去,那妇人一定又会说一些痴情的话。
告别多情水手牛保之后,沈从文来到一个很好玩的河滩。
“在一个小滩上,因为河面太宽,小漕河水过浅,小船缆绳不够长不能拉纤,必须尽手足之力用篙撑上,我的小船一连上了五次皆被急流冲下。船头全是水。到后来想把船从对河另一处大漕走去,漂流过河时,从白浪中钻出钻进,篷上也沾了水。在大漕中又上了两次,还花钱加了个临时水手,方把这只小船弄上了滩。上过滩后,问水手是什么滩,方知道这滩的名字叫作‘骂娘滩’,也叫作‘说野话的滩’。因为这滩实在太难上了,即使是父子弄船,一边弄船一边也互相骂各种野话,而且越骂各种野话,越容易上这个滩,所以,当地人一到这里就骂娘,长期下来,就叫作‘骂娘滩’。”
这个滩在辰河,不到杨家嘴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一次去湘西,能不能找到这个地方。
既然有多情水手,那么,下面还是要介绍一下多情的妇人。
那是一个年方十九的漂亮女子,叫夭夭,却嫁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这个男人爱好抽大烟,因此,只要有人给他钱或者给他大烟抽,他就立即把床让给其他男人睡,当然,一起让的,还有夭夭。
夭夭终于还是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水手,大概叫作杨金保,或许叫牛保也说不定。
总之,沈从文并没有介绍清楚。
夭夭总是希望能天天看到那个年轻有力的水手。于是,见到船就出来看看。
但只要她出来,她的男人就在后面污浊不堪的各种叫骂,小妇人夭夭就把小嘴收敛做出一个撒娇的姿势,带着不高兴的语气自言自语说:“叫驴子又叫了,夭夭小婊子偷人去了,投河吊颈去了。”说着话,还咬着下唇很有情致地盯着沈从文看一眼,拉开门,就消失了。
看到这里,我不仅佩服起沈从文的自作多情,不仅仅湘女多情,男人更多情。
叫作夭夭的女子有故事。
这个整天被丈夫出卖的小女子,终于看上了一个水手。
那个水手只出现过一次,就再也没有来过,但那个水手仿佛答应过夭夭什么,或者没有,只是用眼神多看了她一眼。
但夭夭就一厢情愿地在那里盼望着,希望有一天那个男人带她离开这里。
当别人把夭夭的故事讲给沈从文听的时候,沈从文忽然沉思起来,并感慨起“命运”这个词语来。
我却从夭夭的故事中看到了金基德的电影《弓》,或者是张艺谋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
难道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有这样的痴情女子?
之十一:《保靖》
从常德出来,最后,沈从文和表弟落脚到了保靖。
找不到工作的他有大把的时间去细细吞咽自己的失落和郁闷。
有时候他会一个人爬山,或者躺在河边无人的地方默默地想自己的人生。那是一种漫无边际的想象,时间像云彩一样地在天上飘,在风里飘,在自己的心事中飘来飘去。
这个时候他开始敏感起来。有一天晚上,因为几句话和表弟吵了架,已经是半夜了,他决定不和表弟睡在一起,于是爬到马厩里,睡在了马槽里。
天亮时,表弟道歉才算完事。
一个人的他乡生活,总能让这个人快速成长起来,总能记忆丰富起来。
终于,沈从文在保靖还是谋到了一个书记员的抄写差事。
有了工作的他,终于有了生活的依赖,性格也开始开放起来。
他又有了给别人做狗肉的兴致。
想必沈先生炖狗肉的技巧了得,他一次又一次地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及。
沈从文写到了山里的狼。
保靖的郊界有山,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几个人就相伴去爬山,爬山必随身携带一根木棒,是用来防备狼的。
“我们每次到那小坡上去,总得带一大棒,就为的是恐怕被狼袭击,有木棒可以自卫。这畜生大白天见人时也并不逃跑,只静静地坐在坟头上望着你,眼睛光光的,牙齿白白的,你不惹它它也不惹你。等待你想用石头抛过去时,它却在石头近身以前,飞奔跑了。”
保靖除了有狼偷偷地吃坟里的尸体以外,还有老虎在夜里的时候下山跑到农家里来偷吃院子里的小猪。
每一次沈从文都听得很清晰,那老虎是从哪条路上来的,进了哪家的院子,偷了哪一头猪,然后又从哪条路上回山里去了。
所以,每一次听猪惊天动地的叫声,他们也不再过分地在意,该说话照样说话,该吃酒照旧吃酒。
保靖离永顺大概很近。
沈从文特地写到赶场时从永顺过来的船只。
那河美极了,那船只也美极了。
是啊,如果热爱生活,哪怕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草地,看起来,也是生动的。
沈从文在保靖待了十个月之久,然后,才有机会去四川。
之十二:《老伴》
这是一篇好读的故事。老伴并非现在字面上的意思,还是旧时的伙伴的意思。
这个女人的名字叫作小翠,而正是这个女孩,就变成了《边城》里的翠翠。
开头的文字很美。
“我平日想到沪溪县时,回忆中就浸透了摇船人催橹歌声,且为印象中一点儿小雨,仿佛把心也弄湿了。这地方在我的生活中占了一个位置,提起来真使我又痛苦又快乐。”
这是促使我想细细读下去的原因,是什么样的生活情节让沈从文在这里记忆深刻,又痛苦又快乐呢?
沪溪县界于辰州与浦市两地的中间,上距离浦市六十里,下达辰州也恰好六十里。四面是山,对河的高山逼近河边。沪溪县城的位置又正好处于洞河和沅水的交汇处,因此,这是一个行船的必停之地。
然而,即便是如此重要的码头,却没有公家设定的青石停靠站,那个年代的建筑意识尚差,所以,停稳了船只以后,上岸的人群中总有不少的人被那泥泞滑倒,场景很是好看。
沈从文回忆起十七年前在沪溪过夜的情景。
因为天气的关系,许多人在白天都光着身子泡在河水里,到了晚上,就爬到泥堤上睡觉,枕头是不远处船户人家讨来的一捆稻草。
枕着稻草光着身子过夜的情景让沈从文记忆犹新:躺在尚有些微余热的泥土上,身贴大地,脸面向天,看尾部闪放宝蓝色光辉的萤火虫匆匆促促飞过头顶。沿河是细碎人语声、蒲扇拍打声与烟杆剥剥地敲着船舷声。半夜后天空有流星划了长长的光明下坠。滩声长流,如对历史有所陈诉埋怨。这一种夜景,实在是我终生不能忘掉的夜景。
一同行走的伙伴有十三个人。
十三个人中,有两个是沈从文要好的朋友。有一个叫沈万林的,是沈从文的同宗兄弟,也是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在部队里的同事。他和他的上司打了一架,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另一个年纪很轻的叫作赵开明,是个独生子。他是个勇敢的孩子,因为想做将军,所以混在了部队。
这个叫作赵开明的孩子,在沪溪县城的街上转了三次,就看中了一个绒线铺的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向沈从文借钱跑到那家绒线铺里买了三次白棉线草鞋带子,目的是想和那个女孩说话。事实上,让沈从文感到好笑的是,虽然他买了三双绒线鞋带子,可他连一双多余的草鞋也没有。
回到船上以后,赵开明就当着大家面说:“我将来若做了副官,当天赌咒,一定要回来讨那个女孩子做媳妇。”
因为连续去了三次绒线铺,沈从文知道了那个女孩的名字叫作小翠。后来,沈从文写了《边城》,那个弄渡船的外孙女翠翠的品性就是凭着这一次在沪溪县绒线铺的女孩的印象得来的。
好玩儿的情节接着出现。
三年以后,要去四川的路上,沈从文和赵开明一起路过沪溪县,当时天已经是半夜时分。可是,那个执拗的孩子竟然强行拉着沈从文陪他一起去拍那家绒线铺的门,又一次从那个女孩的手中买了一双鞋带子。
这个情节,现在想来,实在浪漫。
机缘巧合,沈从文和这个叫作赵开明的小伙伴,在部队又一次被分到了辰州城的某部。
沈从文做文书,而赵开明就在留守部做勤务兵。两个人一起去城外的荷塘里去给他们的顶头上司钓蛤蟆。
钓蛤蟆的时候,沈从文才知道,这个家伙,居然又偷偷跑去沪溪县城的绒线铺里买了一双鞋带子。
过了一年,沈从文和赵开明分开,他领到三个月的遣散费,离开了辰州,走到了盛产香草香花的芷江县。他的工作也变了,每天要拿个紫色的木戳,到各个屠桌边验猪羊税。
这样一分开,就是十七年。
十七年以后的一天,沈从文乘船又一次路过沪溪县,那码头的堤岸在冬天有些枯萎。石头城的样子也大有改变。
但是,那个沈从文陪着小伙伴一起去了四次的绒线铺的地址,他记得清楚。
接下来的情节,我用沈从文的原话来描述更好:“我居然没有错误,不久就走到了那绒线铺门前了。恰好有个船上人来买棉线,当他推门进去时,我紧跟着进了那个铺子。有这样稀奇的事情吗?我见到的不正是那个女孩吗?我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十七年前那个小女孩就成天站在铺柜里一堵机棉纱边,两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目前我所见到,还是那么一个样子。难道我如浮士德一样,当真回到那个过去了吗?我认识那眼睛、鼻子和薄薄小嘴。我毫不含糊,敢肯定现在的这一个就是当年的那一个。”
这就是情景美好的故事情节,十七年了,那个女孩没有变化。除非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她长得太像她的母亲了。
然而,更让沈从文惊奇的是,那个女孩的父亲,竟然是和他一同买鞋带子、一同钓蛤蟆的赵开明。
只是,十七年没有见面,赵开明被鸦片烟害了,成了一个老人。
虽然赵开明没有当上副官,但他还是实现了另一个愿望,就是娶小翠为妻。甚至,他还给自己的女儿取名作小翠。
这篇文章的结尾,沈从文却忽然抒情起来。之所以说他忽然,是因为他的抒情有些转折或者有些牵强。
但文字有一股婉约的美丽。
“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黑暗河面起了缥缈快乐的橹歌。河中心一只商船正想靠码头停泊。歌声在黑暗中流动,从歌声里我俨然彻悟了什么。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面前,谁人能够不感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