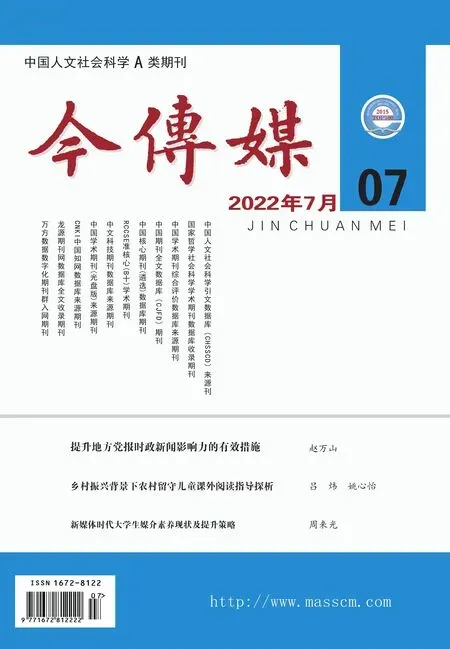抗疫英文新闻纪录片的叙事话语比较研究
李 娜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天津 300204)
一、引 言
2020年1月23日,依据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研判,武汉采取了封城措施来遏制疫情的蔓延势头,这一史无前例的举措引起了全球人民的关注。然而,部分西方媒体将此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进行了泛政治化报道,对封城的举措持批判态度,认为封城侵犯了公民权利,缺乏人道主义。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于2月28日发布了名为“The lockdown:One Month in Wuhan(中文名:《武汉抗疫记》)”的纪录片,纪录了武汉封城一个月来发生的真实故事,也是疫情发生后,首部展现武汉“抗疫”历程的英语新闻纪录片。随后,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推出了相同主题的纪录片——“Wuhan:Life under Lockdown(中文名 《武汉:封城人生》)”。两部纪录片都以各自的视角回应了全世界关切的问题。那么,对同一主题的叙事,CGTN和BBC分别使用了怎样的叙事策略来构建封城后武汉人民的生活,这便是本研究的中心议题。本研究将以两部纪录片为个案,从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情境和叙事修辞四个方面进行叙事话语的比较,分析其叙事策略的异同,以探究我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外传播的有效方式。
二、叙事话语的比较分析
叙事话语是承担叙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陈述,包括口头或书面的话语 (Genette 1990),而新闻纪录片是以文字、声音和图像多模态结合的方式对故事进行叙事的一种形式。叙事学中的话语分析主要研究叙事文本与故事、叙事行为之间的关系 (Genette 1995)。就新闻纪录片而言,叙事话语研究即研究“怎么说”“怎么制作”等叙事技术问题,从而挖掘出“隐藏在意识中的深层逻辑,它在暗中控制语言的表达方式、思维以及所有不同群体行为的标准”(Shapiro 1984)。何纯通过分析指出,新闻的话语形式既是文本的构成因素,也是制作文本的技术与方法,与受众的理解过程紧密相连,与新闻制作的认知和社会环境相关,并将新闻叙事话语的研究对象明确为新闻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情境和叙事修辞 (何纯2006)。据此,本文以两部英文新闻纪录片为研究对象,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比较其叙事的异同,分析各自的叙事特点和策略。
(一)叙事时间
通常情况下,由于叙事的编排,话语时间和故事时间会存在多种变形,呈现出线性和多维的对立,这些变形在热奈特和托多罗夫等叙事学者的眼中涉及到时序、时长和频率等因素。这些因素在新闻纪录片中也有所体现。
1.时序
托多罗夫认为,既然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不可能平行,则必然会导致逆时序 (托多罗夫1989)。在 《武汉抗疫记》和 《武汉:封城人生》两部纪录片中,主要表现为追述和插叙:
CGTN的 (《武汉抗疫记》)整体上是按照封城的先后顺序进行叙事的,但在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着重采用了插叙的方式,插入与中心事件有紧密关联的其他事件。比如,在纪录封城第二天时,展现的中心事件是火神山医院方案的启动,插叙的内容为中国农历新年第一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强调要把人民群众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紧急派遣医护人员纷纷赶赴武汉驰援。1月31日,封城进入第七天,故事讲述聚焦于武汉某医院重症监护区的医护人员,此时插叙的内容为国际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以上例证可以看出,话语的时间是线性的,故事时间是多维的,插叙的使用是多维叙事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能够让整个故事更加丰富和立体,避免了按时间线性叙事的片段化、孤立化,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武汉封城这一公共卫生事件清晰全面地展现在受众面前。
BBC的 《武汉:封城人生》在按照先后顺序进行叙事的基础上,多以追述 (或回顾)的方式来进行叙事。追述是在事件发生后,讲述所发生的事情。在该记录片中,一位医护患者的丈夫作为讲述人,回顾了妻子在发病初期、居家隔离、医院收治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完成了追述叙事,这种个体感受的叙事话语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与同情。
2.时长
时长所要探讨的问题,是考察由故事事件所包含的时间总量与描述这一事件所包含的时间总量的关系(何纯2006)。二者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概括、省略和场景等方式在新闻纪录片中呈现。
概括是把故事时间进行压缩的叙事方式。两部纪录片的片头都采用了概括的方式,通过加快速度,能够使观众迅速、直观地了解所述主题 (封城),呈现出新闻话语的倒金字塔结构特点。
省略是对整个故事时间的免述。两部纪录片分别聚焦于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武汉抗疫记》中的1月23日、1月29日、2月11日、2月17日和1月23日;《武汉:封城人生》中的封城第二天、第四天、第七天等。省略叙事把封城时间浓缩于约20分钟的纪录片里,通过选择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有效实现了叙事的符号化、意义化。
场景在新闻纪录片中主要指对话,即直接引语。《武汉抗疫记》中有大量对话,有助于提高新闻纪录片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武汉:封城人生》的场景则是随着叙述个体生活轨迹的变化而实现的,通过叙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与对话,实现场景的再现,情节化较为突出。
(二)叙事结构
董小英将叙事结构定义为文本内部的叙事方式安排,并进一步细分为内结构与外结构 (董小英2005)。在新闻纪录片中,叙事话语的内结构即新闻事实内部事件之间的组织和连接,这是叙事的核心。
在 《武汉抗疫记》中,新闻事实表现为一系列事件的有序排列,多个人物、事件、场景按时间线层层推动,构成武汉战疫的全景式立体化叙事特征。《武汉:封城人生》的叙事结构采用了双线交叉叙事的形式,通过亲历者的讲述,构建了多维时序和空间的局部立体式叙事。
(三)叙事情境
在叙事学中,叙事情境指叙事角度,是由叙事者采取不同视角讲述故事而创造出来的文本语境 (何纯2006)。在 《武汉抗疫记》中,叙事者 (新闻记者)就是故事的讲述者,并以第一人称的多元化的视角来进行叙事。多元化视角体现了多种“声音”,具体表现为新闻记者对抗疫战场上各界人士的采访与日常生活纪实,比如,因封城而被迫滞留在武汉的民众、医护人员、确诊病人、快递小哥、志愿者、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等等。新闻记者作为目击者和亲历者,以第一人称的多元化视角叙事保证了新闻纪录片的专业性、客观性和平衡性。
《武汉:封城人生》则属于“他者叙事”,具有外视角的特点,在叙事情境里,叙事视角的不同会造成受众与所述事件的距离有远有近。在 《武汉:封城人生》中,武汉市民为故事的讲述者,纪录片制作方化身为隐指作者,通过市民自行拍摄的Vlog来纪录封城后武汉人民的生活状态,并以画外音的方式承担故事讲述的过渡、衔接、评论等。这种叙事方式巧妙地把外视角转变为内视角,能让观众感同身受,体现了创作者部分叙事权力的让渡 (任桐,丁伯铃2018)。
(四)叙事修辞
话语作为一种言语行为,既具有语内行为功能,还要达成一定的目的和效果。新闻修辞不仅限于使用常见的修辞方法,还包括为增加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合理性、精确性、正确性和可信度而使用的策略性手段 (梵·迪克2003)。作为修辞的叙事,梵·迪克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新闻纪录片。
纪录片是一种多模态的叙事,其修辞充分体现在声音、画面和文字的结合上。两部纪录片都善于利用隐喻修辞来进行叙事。《武汉:封城人生》在讲述武汉封城的第一天时,故事从当地志愿者的VLOG展开讲述,该志愿者以vlog的形式纪录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镜头先后出现封城后空荡的街道、停业的商场、入口处漆黑的地下通道……此时,作为他者叙事的画外音响起:“The lockdown is a huge gamble…There is no word when itwill end.”这一画面、文字、声音相结合的隐喻,以及开篇的叙事修辞为整个纪录片奠定了基调。
隐喻修辞在 《武汉抗疫记》的结尾处也有体现:片尾以一名医生的采访结束,他说:“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灾难、恐惧、疾病都跳出来了,这个盒子里面最后一样东西,是希腊神话里说的,就是希望,只要希望还在,之前的就都不是问题。”此时,画面定格在晨光下的东湖,安静美好。这处叙事修辞的使用与整个纪录片的主旨相呼应,氛围相契合,观众可以深切感受到武汉人民经历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从而产生共情,达到较好的传播目的。
除了直接采用修辞手法以外,《武汉抗疫记》和《武汉:封城人生》还采用了情境事实的叙事手法来增强纪录片的语义张力。“报道的直接性和记者对事件的接近性都是确保报道真实性的重要修辞手段”(梵·迪克2003)。面对“封城”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举措,全球人民都对武汉及武汉人民抱有极强的关注度,在此形势下,更需要用事实说话、纪录事实。因此,通过记者深入重症病房、集中隔离点、方舱医院和居民家中,用最直接的情景再现武汉人民的真实生活就非常有必要了。值得一提的是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赵志刚医生的采访,专业人士的访谈记录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消除外界疑惑,防止将疫情防控措施泛政治化解读。
《武汉:封城人生》借助两位Vlogger的讲述,注重叙事的情节化,突出故事的冲突和悬念:vlogger翟先生拍摄记录了自己从妻子患病初期的担心焦虑,到后来获得救治如释重负的心路历程;vlogger林先生记录了自己做志愿者的经过,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密切接触需要帮助的人,每一次志愿工作结束后,都会直面镜头向观众描述自己感动与悲伤交织的复杂情绪。这种注重细节的叙事策略,其可感性较高,能够起到增强新闻故事真实性的效果。
三、结 语
通过对叙事话语进行比较分析会发现,两部纪录片都运用了概括、省略和场景等叙事策略,主题更加明确、节奏更加紧凑、叙事更加真实可信。
在叙事结构上,《武汉抗疫记》以时间顺序为轴对事件进行了有序排列,构建出武汉战疫的多角度、立体化叙事模式;第一人称多元化的叙事视角也展现出活跃在防疫抗疫一线的各个“中国面孔”——外表坚强,看到镜头里儿子的一瞬间泪流满面的年轻护士、挨家挨户排查却遭遇各种困难的社区工作者、热心公益却不被家人理解的志愿者、紧张忙碌的快递小哥,等等,这些画面都有助于观众全面客观地了解当时武汉人民的生活状态。《武汉:封城人生》采用了双线结构和内视角的叙事方式,将武汉封城的故事聚焦于个体命运,以细节化、碎片化的Vlog形式记录了当时武汉人民的真实生活,突出了个人经历中的冲突和矛盾,构建了多维时序和空间的局部叙事特征。此外,讲述者的独白也起到了引起观众共鸣和共情的叙事目的。
在叙事修辞上,《武汉抗疫记》并未采用传统的宏大叙事表现手法,而是以讲故事的方式,以小见大地投射出武汉封城后的现实生活。同时,隐喻和情境事实的叙事修辞也客观地呈现出武汉封城是一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有助于观众了解封城举措的原因和重要意义。《武汉抗疫记》在国外引发了较大的反响,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媒体都对该纪录片进行了转播,截至2020年3月,其在YouTube上的播放量已突破900万次。《武汉:封城人生》中多次出现配合画外音的喻体:灰蒙蒙的天空,成排的路障、警车,漫长昏暗的地下通道,或是将封城诠释为一次“豪赌 (huge gamble)”,或多或少地体现出西方媒体“他述”中国时的“刻板印象”。虽然,《武汉:封城人生》巧妙地运用Vlog来记录当时武汉人民的现实生活,但是,将武汉封城这样一个涉及到中国现实状况的复杂问题降格为孤立的个人经历,这种个人视角下的真实和客观无疑存在盲点,遮蔽了中国社会宏观上的现实、历史、文化传统等特殊情况 (王鑫2018)。
西方媒体出于惯性思维,将封城举措过度解读为政治行为。因此,在复杂多元的国际信息传播体系中,中国的主流媒体要充分了解和掌握叙事话语的特点,采用恰当的叙事策略进行叙事,讲好中国的抗疫故事,CGTN在这一点无疑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