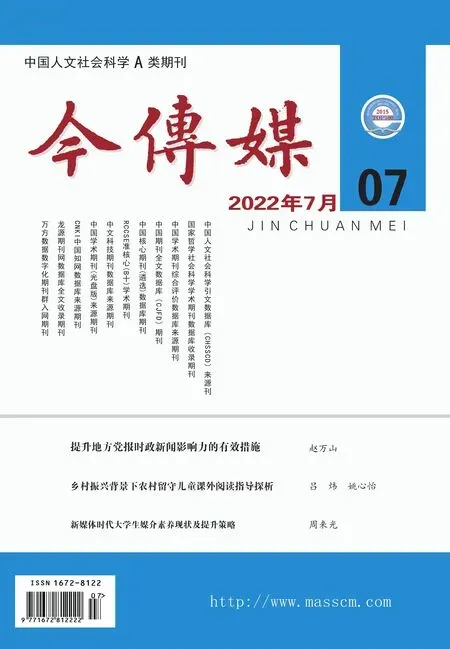“电影作者论”视阈下“沉默三部曲”风格研究
夏诗媛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072)
一、悲剧化影像中的残酷诗意
(一)默默窥探一切的长镜头
《雾中风景》中的长镜头随处可见,其中27:28-29:20共计112秒的长镜头是最能体现影片残酷诗意这一风格特点的。
寻找父亲的姐弟俩路过一家酒店,他们目睹了逃跑新娘是被拖回酒店,又碰见濒临死亡的马拖着车在雪地里前行。镜头由一个固定的远景镜头,逐渐转成一个慢摇镜头,并将视觉中心定格在姐弟俩与雪地中的马之间。
一个以姐弟二人观察雪地中濒临死亡的马为画面中心的长镜头开始了。马躺在姐弟二人中间,他们三个将画面分成三个部分,占到了画面的总面积的二分之一。马处于画面的中心,它在喘气的时候艰难地举起脑袋,姐弟俩也随之起身,眼睛却目不转睛地盯着马。姐姐注视着一起一伏的马头,时不时还瞟一眼画外焦虑伤心的弟弟。倔强的马头在姐弟俩腿部以下的视线区域时而出画时而入画,一抬一倒之间,都意味着生命在挣扎中走向消亡。过了很久,马儿终于不再抬头。器乐的奏鸣声渐渐出现,镜头缓缓上摇,为婚礼欢庆的人群从酒店里冲了出来。这时,镜头虽然处于虚焦状态,但是欢呼热舞的身影、整齐热烈的掌声、器乐的奏鸣都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影像,压制着靠近镜头的姐弟二人。弟弟在奏乐中放声大哭,人群在奏乐中欢庆热舞,队伍里的人群唱着歌、鼓着掌,蹦蹦跳跳地出画;姐姐起身,目光却始终不离开地上的已经死去的马儿。
姐弟俩与马始终占据着整个长镜头的视觉中心,直到庆祝婚礼的人群从旅馆涌出,画面被一分为二,人群在上,姐弟在下;人群为虚,姐弟为实。这是极端残忍的场景,两个孩子在冰雪地里守候着被拖车拖着的那匹濒临死亡的马,除了姐弟俩在行注视礼给它送终,它一无所有。
在这个场景中,由不同的景深镜头所形成的景别关系,传达出了极端强烈的安哲罗普罗斯式的残酷诗意。这份诗意叩问着,关于生命和死亡,关于现实与人,关于我们内心是否还有一点点柔软的地方可以放置对他人、对世界、对生命的关注和同情。
(二)诗意却残酷的画面空间
安哲电影作品里的诗意让电影评论者们津津乐道。张成成将安哲的电影美学风格总结为“在历史废墟上营造诗意”;无独有偶,任欣也表示“安哲的一生就是一首含蓄隽永的抒情诗”。
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与它融合了其他六大艺术的特点密不可分,而最值得分析的是其中的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在电影中,故事的发展、情节的产生以及矛盾冲突的更迭是由空间和时间的共同作用进行推动的,构成了银幕上流动的影像空间,“这正是电影叙事的重要条件和基本特征。画面是片断的,依靠剪辑技巧构成完整的时空复合体,创造出一种非连续的连续性,画面又是整体展现的,能指和所指呈共时性存在,空间词语成为主要语言手段”。
虽然“沉默三部曲”故事发生的背景和环境各有不同,都有着共同的无奈。首先,这三个故事都发生在潮湿阴冷、多雾有雨的气候环境下,风和日丽的景象几乎没有;其次,大多都为黑、白、灰三色;最后,这三部影片都具有相同的场景元素,比如,地广人稀的城市、昏暗的街道房屋、身穿暗色的路人以及固定的地点 (车站、海边、旅馆、街头)等,这些元素共同建构出一个沉重阴暗的物理空间。同时,长镜头与配乐的渲染,这一空间成为安氏表达的途径,也象征着影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的部分心理活动得以外化。
在影片 《塞瑟岛之旅》父亲斯皮罗回到家乡的场景中,当邮轮的客梯缓缓落下,旅人一个接着一个下楼,身穿黑色大衣、头戴灰帽的老人也随之而下。斯皮罗在巨轮旁边站定,轮船的巨大显出老人的矮小,他的儿子和女儿站在楼上,沉默地向下望去,父亲的出现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情绪波动。此时三人的站位呈现出一个三角形,儿子和女儿成为与父亲相对的视角,画面的重心是儿子和女儿望着父亲的方向,随后,镜头由儿女推向父亲,观众开始与儿女的视角平行重合。
斯皮罗在俯拍镜头与三角形站位下,显得格外瘦小;儿子和女儿在镜头的前景,与轮船接近同一水平线,显得十分高大。安哲在这里的安排是有深意的,斯皮罗第一次出场就以这样的形象出现,显示出父亲与儿女关系的不对等。影片中的人物都很克制、沉默,向观众传达出三人之间的疏离与冷漠,这种情绪张力与周遭潮湿阴暗的环境形成了呼应,也为随后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斯皮罗与故乡的人和景格格不入,最终孤游于海面埋下了伏笔。
二、安哲的诗意哲学
安哲的作品总是透露出浓浓的诗意,这与他从小热爱文学诗歌及写作密不可分。作为一名希腊青年,安哲自小就沐浴在古希腊文明以及悲剧诗作的熏陶之下,而他所处的整个希腊的文化环境也为安哲悲剧诗人气质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在影片 《塞瑟岛之旅》中,尽管斯皮罗与周围的环境、人物格格不入,处于被排斥的境地,但镜头的表达仍然是克制、冷静的。斯皮罗的妻子在见到丈夫后,沉默地退回房间平复情绪,在平淡的场景中,两人默契地流露出厮守的决心。父亲与母亲之间永恒且坚定的感情好似一首隽永的诗。用安哲的话说:“诗歌是湿润的露水,让严酷的现实温和起来,变得可以忍受。它让影像有了深度,将你带向别处,在那里,所有事物都能显得如此迷人。”由此可见,安哲十分善于将诗意元素与自己的故事融合,为观众带来别样的思考。
在影片 《养蜂人》中,养蜂人斯皮罗前半生一直从事教学行业,整日庸庸碌碌。影片开场,斯皮罗参加完女儿的婚礼,准备告别家人,带上父亲留给自己的一车蜜蜂开始养蜂之旅。旅程中,斯皮罗遇到了一位青春洋溢的少女,少女为了讨口饭吃,决定跟着这位老实的养蜂人上路。然而,两人从年龄到性格的巨大的差异使得斯皮罗对少女的暗恋无疾而终,斯皮罗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希望随着少女的告别而消失殆尽。在去看望海边养病的老友之后,他在一个春天晴朗的早晨,将数十箱蜂巢打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边是蓬勃生长的蜂群,一边是绝望的养蜂人,巨大的反差给予观众强烈的的荒诞感。除此之外,那只在婚礼上引起所有人注目的小鸟,也被赋予了太多的涵义,可以被解读成爱情、幸福或者青春,无论是哪一种,这些美好的事物都不期而遇、稍纵即逝,它的出现,与影片结尾,斯皮罗的自杀形成呼应。
三、藏于影像中作者安哲的“签名”
在“电影作者论”视阈下,安哲的作品不仅呈现出电影主题的相关性和连续性,还突出了更鲜明的个人风格特征。他将自己父亲的真实姓名——斯皮罗,赠与“沉默三部曲”中的每一位父亲,向观众、向世界传达了自己对电影深沉的情感。
(一)“沉默三部曲”中的父亲——斯皮罗
在影片 《雾中风景》中,“父亲”成为被寻找的对象;在影片 《塞瑟岛之旅》中,“父亲”成为寻找精神家园与慰藉的主体;在影片 《养蜂人》中,“父亲”在旅途中捕捉春天,回望青春。“沉默三部曲”的主题也是分别围绕“寻父”“父的归乡”以及“父的流浪”而展开的。
“父亲”形象的频繁出现与安哲童年的经历密切相关。1944年,希腊正值内战爆发,安哲的父亲斯皮罗被卷入政治斗争,不断地被抓捕、流放,安哲也曾与母亲在尸横遍野中寻找过父亲的尸体。于是,他多部电影中的情节正是以父亲的人生经历为基础的。在“沉默三部曲”中,“斯皮罗”这个名字成为其中“父亲”的象征,安哲通过这样的方式,向观众传达了他对父亲的缅怀,也让观众理解了他以“父”为主体对历史与民族的哲学反思、对生命存在价值的思考。
(二)对电影的热爱与致敬——安氏“签名”
在“沉默三部曲”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与情节、主题无关的片段,但实际上都是指涉电影本身。比如,在影片 《养蜂人》中,斯皮罗与少女约会的地点是一家旧影院的银幕前,作为全剧重要片段的背景,影院地点的选择、银幕出现的意义不言而喻。
在影片 《雾中风景》中,弟弟捡到了一截废底片,一直陪伴着姐弟俩的小伙开心地为弟弟科普底片的意义,并暗示里面有美好的事物存在……这些片段都是安哲通过巧思妙想将与电影相关的元素刻入镜头之中,是安哲对电影的表白。在安哲心中,电影是永不消亡的浪漫。
四、结 语
三部影片在视听语言上,运用长镜头、背景音乐,使每一次“旅途”都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此外,“沉默三部曲”的主题都具有悲剧色彩,而表达方式却充满了诗意。
作为世界电影大师,安哲像他电影里的主人公一样,在创作中旅行,从镜头中窥视世间百态。他的一生,就是寻找电影生命之根的一生。安哲的作品闪耀着哲思的光芒,镜头成为故事里冷静却温柔的旁观者,剖析社会历史,关注个体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