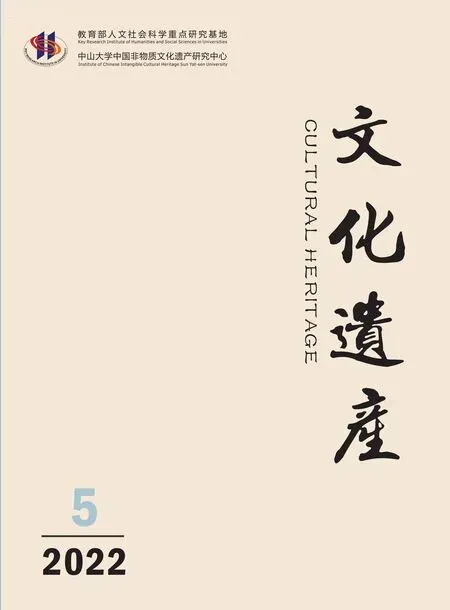国庆视觉形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孟凡行 傅国群
国庆日是重要的政治节日,设立初衷在于庆祝国家成立、展示国家力量、凝聚集体情感、增强国民信心和整合社会价值。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为此设置法定假期,期间各地区、各民族中华儿女以举行盛大集会、餐饮聚会、出游旅行等多种方式来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在此过程中,国庆节通过不断重构多维政治仪式形象系统,借助可见、可听、可触的形象载体,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和价值得以显现,并广泛传播。时下正处于图像时代,视觉形象的展示和传播方式,不但易于抓住受众的注意力,大大扩展受众范围,而且也为民众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想象提供了绝好媒介,从而使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得以实在化。与此同时,国庆的视觉化也丰富了国庆仪式信息的内涵和外延,提高了国庆仪式信息的价值和功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着典范作用。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定位
通过视觉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集体记忆、文化象征、政治仪式等方面有历史和逻辑关联,学界已有一定研究。
在集体记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以往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讨论了集体记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集体记忆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的重要部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的历史,由共同的记忆和生活构成。另一方面,集体记忆的时空重构被认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通过塑造集体记忆可以形成观念认同,进而达成社会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这就意味着作为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基底的集体记忆,需要通过“社会功能的意识和群体机构的传送”,实现“共同体社会化”来达成民族认同。
在文化象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以往研究主要从文化象征的生成和运用两方面展开阐释。从前者来看,文化符号是文化象征生成的基础和表征,其中的民族政治与民族文化类符号、民族团结和民族共同体类符号、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类符号等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关联,可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认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认同、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形象。就后者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抽象概念,需要借助文化象征催生主体的情感体验,进而强化共同历史记忆、促进成员身份认同、形塑民族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政治仪式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政治仪式是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政治仪式因具有时间性、空间性、公共性和共同性,刻写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脉络、构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发场域、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民属性、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遵循。政治仪式可以强化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知,构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和塑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信仰,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
以上研究涉及的三大方面,基本上涵盖了通过视觉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然而,前人所论多立足宏观,从理论和应然的角度,阐释用视觉形象和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较少从中观视角出发,通过具体典型的视觉形象和文化符号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和路径。是故,本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型对象——国庆视觉形象为个案,先厘清国庆视觉形象不同维度的构成和价值,进而分析国庆视觉形象的生成逻辑和发挥作用的机制,最后探索运用国庆视觉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
二、多重维度下的国庆视觉形象
国庆视觉形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类主体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而设计和制作的视觉形象。从表现形式来说,可将国庆视觉形象分为动态视觉形象和静态视觉形象。前者如庆祝国庆节仪式实景(最典型的是国庆阅兵式和升旗仪式)、各种集会庆祝现场,以短视频、联欢晚会、电影等呈现的庆祝活动和形象;后者如各类庆祝旗帜、服装、工艺品、图像、雕塑、展板、宣传画册等。从呈现载体来看,可将国庆视觉形象分为现实视觉形象和虚拟视觉形象,前者如以实物呈现的各类庆祝国庆的旗帜、服装、工艺品等,后者如以网络为载体呈现出的图片、视频、文字等。从接受和认同的层次来看,可将国庆视觉形象分为多民族共享的视觉形象和各民族自享的视觉形象,前者如国旗、国徽、中国红,后者如各民族服饰、民族歌舞等。相对于其它符号,国庆视觉形象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期待,这决定了需要将国庆视觉形象置于多重维度中理解。
第一、历史维度。“历史中国”是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基石。国庆视觉形象必须以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为基础,展现国家和民族的底蕴与发展脉络。如历次国庆节均采用大量历史中国符号,如长城、黄河、长江、故宫、华表、布达拉宫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历史传承也包括近代革命中国的历史传承,比如每年国庆期间都在天安门广场展出的巨幅孙中山先生画像。
第二、民族维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具体体现在多元的56个民族构成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对国庆节的庆祝方式体现出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其共性是使用各民族共享的形象和方式庆祝国庆节:体现在行动上,是在同一时间过节、多民族群众一起参加国庆活动、收看同一庆祝节目等等;表现在视觉形象上,是传递共享性视觉形象,如国旗、国徽、灯笼、花卉等等;其个性则是各少数民族以本民族自身文化为依托传递国庆视觉形象,如各民族身穿民族服装庆祝国庆节,或者将民族传统与国庆节结合起来庆祝,如国庆节和中秋节有时重逢,而中秋节是中国多民族共享的节日,每逢此时,国庆典型的视觉形象如国徽、国旗、长城等形象就与中秋节视觉形象月亮、玉兔等重构出现,寄托各族人民对祖国和美好生活的祝福。
第三、政治维度。国庆作为典型的政治仪式,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着政治传递作用,其传达的讯息往往引起国内外社会的高度关注,是“政治社会化载体、政治沟通桥梁、政治整合的象征、政治记忆的印迹、政治认同的标志”。这类视觉形象如阅兵仪式、升旗仪式、《瞬间中国》短视频等。阅兵仪式是这方面的典型表征。中国阅兵式规模宏大、仪式威严,徒步方阵、车辆方阵和空中列队等等构成的综合形象集中展示了中国日益强大的国防力量,提升了中华儿女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老兵方阵呈现了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历史形象,而历史是构建民族认同最重要的合法性资源。群众方阵塑造了军民一家的形象,其中的少年儿童的活泼形象则将现实中国推向未来。人们对这些形象的综合感知和记忆在最有气势的分列式中得以升华,国家和民族、政治和文化、历史和未来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中融为一体。
第四、文化维度。传统文化是国庆视觉形象建构的重要资源和依据。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合到国庆视觉形象之中,如将灯笼、狮子、中国龙、中国红等传统视觉形象与国旗、国徽、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形象组合展示。每年国庆期间,天安门广场、各大城市广场一般采用制作大型雕塑、摆花篮等形式营造节日场景,制作大型雕塑常将长城等传统形象与国徽、国旗、革命先烈等形象组合创作。第二,利用传统的庆祝方式展示国庆视觉形象,最典型的是将日期临近或重合的传统节日与国庆节结合起来进行视觉形象建构。如重阳节与国庆节、中秋节与国庆节的视觉形象建构。
三、国庆视觉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
国庆视觉形象主要通过情感生成、历史生成、社会生成三种机制发挥民族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用。
(一)国庆视觉形象通过情感生成机制加深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情感
共同情感是集体记忆产生的重要因素,是开展集体沟通,形成共同话语的重要条件。然而,共同情感的生成是集体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经过特定的共情机制建构完成的,这离不开个体对同一事物、事件的认识。国庆视觉形象的情感凝结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感不断认知和强化的结果。
国庆视觉形象的情感生成有历史和当下两种趋向,即由历史生发出来的情感和由当下情境激发出来的情感。历史情感会影响当下情感的形成,当下情感又会升华、强化和延伸历史情感。国庆情感就是在历史情感和当下情感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国庆节期间“人们所有的行为举止和心理体验都与日常生活迥然有别”,体现出节日的庄严性、神圣性、狂欢性。由于国庆小长假带来的假日经济对国庆节的神圣性有所冲淡,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国庆节很难被描述为一个神圣时空,但其中却存在若干神圣时刻和空间。比如在10月1日这天,人们参观升旗仪式、聆听最高领导人讲话、观看阅兵式,参加各种游行和纪念活动的时候,毫无疑问是进入了神圣情境。亿万民众观看同一幅画面、聆听同一种声音、经历同一个时刻,会生发出对祖国和民族的情感。在情感迸发的高峰,很少会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而更多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共情,炙热的情感过后凝结为爱国、爱民族的情结。这种情结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促使其成员展开分享和传递行动,以便尽可能将爱国热情笼罩每一位成员。如2021年10月1日,网络上广泛流传着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的文字和图片。这种流传使得每位中华儿女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情感与当代情感融合起来,不断确认“我们是一家人”。再如,近年来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辈》《长津湖》等,拉近了当代中国人与本国本民族历史的距离,达成了与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情与共鸣,这种情感共鸣在国庆节氛围下特别凸显,不断强化中华儿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总之,国庆视觉形象是中华儿女对祖国情感的具象化呈现,其参与了国庆神圣氛围的营造,在集中呈现中华民族的历史情感的同时引燃了中华儿女的当下情感,并将其沉淀、符号化后加诸自身,成为下一次国庆节或爱国情景营造的情感资源。
(二)国庆视觉形象通过历史生成机制强化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
卡西尔认为人类生活在由符号编织成的思想和经验网络中。形象和符号既是文化事实,也是相互连缀不可分割的文化系统。扬·阿斯曼认为,在一个社会群体中,要想得到身份认同必须依靠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的产生主要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也就是说,符号的产生依赖于相关的文化系统,而文化系统形成的基础则是历史。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厚的记忆资源,这些资源不断传承内化形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和符号,成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接纽带。
国庆视觉形象的历史生成也遵循此逻辑,其指向性和意涵与国家、民族密切相关,既可以成为内部成员的身份认同标志,又可以成为外部世界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国的窗口。内部认同和外部认可都会强化国家、民族的集体归属。如“中国红”形象,既勾起了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悠久尚红文化传统的集体记忆,又让人联想到了近代中华民族为抵御外辱,一致对外、浴血奋战的革命历程,从而内化为中华儿女的共同认知与集体意识。换言之,“中国红”不仅仅是一种颜色的审美呈现,更因为其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革命印记,成为中华民族的典型象征形象和符号。类似中国红的视觉形象经过不断重复,有效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体系大体包括具有历史记忆的史实和缅怀历史记忆的行为两个层面,其中历史记忆史实承载和传递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脉络,历史记忆行为则体现出民族成员对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网络聚合,交叉形成的记忆“诱导遗忘的程度会伴随传递次数而增加, 从而使个体围绕着对过去的共同描述会产生更大范围的趋同”。国庆视觉形象以国庆为依托,提取各民族共享的最大公约数符号和形象,以直观(或可触)的形式循环展示中华各民族勠力建设伟大祖国的历史征程,从而引导各族人民将中华民族一体理念内化为对中华民族共识的认同,外显为民族团结行动的具体实践。内化——外显、观念——行动协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王明珂指出,“一个族群,常以共同的仪式来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此集体记忆,或以建立永久性的实质纪念物来维持此集体记忆,或民族国家以历史教育来制度化地传递此集体记忆。”其中,共同仪式中的政治仪式最具影响力。扬·阿曼斯认为集体记忆最易受到政治化记忆方式的影响。政治化深层记忆方式的核心是利用事实和有感染力的口号来争取大众的支持,以实现政治目标。国庆节就是一种政治仪式,它被赋予了以爱国主义为主调的意义和期待,通过反复展演、传播国庆视觉形象,讲述各民族在共创中国、共建中华历史过程中“我们一起”的故事,以及“我们一起”对祖国和民族未来的构想。从而达到加深中华民族历史集体记忆,激发中华民族集体情感,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
(三)国庆视觉形象通过社会生成机制增强共同体成员的民族认同
人的行动离不开社会交往与互动。布鲁默认为社会互动有两种,即“符号互动”和“非符号互动”,两者最大的区别是“符号互动”引发了“解释过程”。可见,符号互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社会互动是符号产生的必要条件,国庆视觉形象和符号就是一种有意识的互动的产物。当然从结构和能动性相互构建的角度来看,不仅仅是社会互动产生符号,符号互动也产生社会。从符号互动生成社会的角度来看,国庆视觉形象对中华民族身份的塑造主要体现在三大层次。
第一、国庆视觉形象表征中华民族自身。中华民族既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也是由有血有肉的全体中华儿女构成的超大群体,还是一个由人、组织和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理念。这一理念集中体现为以“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所构成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中华民族理念有其现实基础,一是中华民族的物质构成及其运动;二是历史时期,特别是20世纪以来广大仁人智士在相关理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的概念和理论建构。人们更多考虑的是中华民族的物质构成及其运动,学界可能会涉及到中华民族的理论建构,但却较少考虑中华民族理念本身。实际上中华民族能够团结一心并展开行动,离不开中华民族理念本身作用的发挥。作为一个具有实体对象的理念,其形成和存续也不可能仅依靠思考,而是需要对应的文化形式的支撑和互动。国庆视觉形象包含形式多样的形式,这些形式的互动共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理念展现和生长的过程。
第二、国庆视觉形象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国庆视觉形象究其本质是中华文化的呈现,“文化是一种润无声的存在,凝聚文化共识可促进共同体成员的聚合”,进而潜移默化地激活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国庆视觉符号作为国庆仪式中最为直观的呈现,从“物性”和“象征性”两个层面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意识,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物性”的国庆视觉形象为中华民族成员分享、交流文化共识、集体记忆、个人情感提供了“有形”载体。国庆视觉形象的“象征性”则为中华民族成员分享、交流文化共识、集体记忆、个人情感提供了内容。如2009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呈现的56根民族团结柱,从“物性”的层面来看,56根团结柱呈现了我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共同体;就“象征性”层面而言,56根团结柱象征56个平等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迈向新生活的愿景。
第三、国庆视觉形象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个体。无论形而上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理念,还是现实中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均需沉淀到个体层次并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完成民族认同。提取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要素设计的国庆视觉形象“为个体认同于民族群体提供了必要的意义背景,也为共同体意识的代际传递提供了基础”,相信中华民族是建立在“共同的神话和记忆之上的共同体”。国庆视觉形象所呈现出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是基于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为基础而达成的,即依托国庆视觉符号找准“我是谁”的定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所在。这种基于集体性的个体身份意识的实现和确认离不开他者反观。在现实中,人们往往通过与“他者”的交往实现对“自我”的认同。全球化与网络时代,中华民族成员和他族交往交流的机遇和频率加速,他者反观机制频繁启动,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成员审视自己和认同自身的需要。国庆视觉形象是中华文化独特性的集中体现,存在“我”区别于“他”的特征,因而成为中华民族成员与他族交往交流的时表征自我身份的标识,他族对此标识的识别和评价会反向增强中华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
四、运用国庆视觉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
按照符号学对能指和所指的界定,国庆视觉形象的能指,可对应其各类表现形式,其所指则是借助其形式传达出的国庆仪式的内涵和意义。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遵循任意搭配原则,这是就语言符号的生成来说的。需要注意的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一旦搭配,往往会形成相对牢固的结构。因此,在运用国庆视觉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国庆视觉形象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从多维视角建构国庆视觉形象,实现国庆视觉形象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充分发挥其作用。
第一、传播具象性国庆视觉形象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共鸣。
视觉形象的优点是能够借助便于传播的直观形象表达深层意涵。在当今“视觉(visuality)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社会”,视觉传播很自然地成为人们达成意愿、实现价值的重要手段。随着新媒体技术全面介入当代生活,视觉形象占领了每一个角落,其简明、直观的表达方式便于转载、传播和理解,有助于人们内心情愫的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抽象概念,其内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单元、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有着密切关联。抽象观念不易理解,而视觉表达方式能够突破这一局限。具象化的视觉形象能够使抽象观念更好落地,便于广大中华儿女领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视觉传播用图像叙事代替文本叙事,通过信息的视觉图像转化,打破文字传播知识盲区,让信息变得简单易懂。
首先,创新国庆视觉形象及其呈现方式,为国家和民族认同提供合适载体。视觉形象是由文字、图像、形体、线条、色彩、光线等元素构成的复杂形体,有静态和动态两种呈现方式,不同元素和方式的搭配调整,可呈现出丰富多变的视觉形象,带给受众不同的感受。2019年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推出“56个民族任你选,快秀出你的爱国style”节目,个人可通过换装56个民族服饰,表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共同体情怀。又如自2019年国庆以来推出的“快闪中国”系列节目,为全国人们提供了以自己方式庆祝祖国生日的平台和机会,同时也不断充实着多元一体的国庆视觉形象体系。
其次,利用多维空间展示国庆视觉形象,扩展国家和民族认同场域。国庆节期间,通过建构历史空间、扩展现实空间、整合虚拟空间、利用公共空间传播具象性国庆视觉形象,将饱含中华韵味的国庆画面呈现出来,不断激发人们的集体记忆,唤起中华民族的集体情感。如,2021年国庆节期间,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五星红旗、“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等宣传海报或宣传图册,网络世界中各种国庆主题图片、音乐与视频等形象直击人们内心,让人们情不自禁地将自己与祖国联系起来,爱国情怀油然而生。
再次,多面向传递国庆视觉形象,促进国家和民族认同活动的全民参与。在我国法定假日制度的支持下,国庆节不仅是仪式庆典,还是集政治文化、民族文化、风情旅游、特色消费等于一体的“黄金周”。不同类型的活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符号域’,将各族人民整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共同的群体”,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多维互动,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职业、不同空间、不同载体的相互交织,扩大了民众参与的范围和机会。
第二、利用象征性国庆视觉形象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信仰价值。
国庆视觉形象主要通过“物质形态利用与再生产”和“非物质形态利用与再生产”两个层面来传递其象征性。
首先,物质形态利用与再生产。空间和载体形式是国庆视觉符号物质形态象征再生产可利用的重要元素。就空间来说,整个国家疆域都是国庆节的文化空间,国庆视觉符号一方面可以通过固定空间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传递中国情怀和中国精神;另一方面可以将国家制度、当代发展和未来建设与空间同构,展示当代中国成就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2019年国庆节,北京开展了主体为“普天同庆·共筑中国梦”的“十园风采”盛大游园活动,通过对天坛公园、地坛公园、北海公园等进行空间布局安排,建构了“共筑中国梦”“龙腾盛世”“歌唱祖国”等花坛,展示了“大国轴线”“非遗传承”“古都新韵”等国庆主题,将历史中国、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连接起来,激发中华儿女的自信和自豪,凝聚共同情感。就载体形式而言,通过不同材质、光线、色彩等对国庆视觉形象进行重塑,提高象征物多元意义的表达力。如2019年国庆节经过60多次修改设计制作的“凝心铸魂”彩车,以火炬、基石和多彩年轮为主体形象,火炬象征了核心领导思想,基石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多彩年轮暗喻时代年轮,辅以“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文字,四部分结构相辅相成,用简明、诗意的语言表达思想主旨。国家主导的视觉形象高大宏伟,振奋人心,民间自发制作的视觉形象虽然规模有限,却也“微言大义”。
其次,非物质形态利用与再生产。国庆视觉形象的非物质形态利用与再生产主要通过“拟人化”和“拟亲属”等手法实现。如通过带有情感和象征意义的视觉形象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情感表现出来。人们将“祖国”人格化,进一步建立起“我们”和“祖国”的亲密关系。中华民族是“大家庭”,祖国是“母亲”,每个民族是兄弟姐妹。国庆节是“祖国妈妈的生日”等等。显而易见,“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百年征程,盛世华诞”“祖国生日快乐”等视觉符号所传达的不是物性情感,而是人性温情。在中华文化家国同构传统的影响下,这种表达方式更容易被民众接受。国庆视觉形象的传递具有特殊的时间意义,此时间“既借助‘国庆’重复了‘国家时刻’”,又使个人情感、社会情感和国家情感得以聚合。国庆视觉形象非物质形态利用和生产是共同体精神化育和弥散的过程,以此构建起与人民需要相符合、与时代相契合的共同精神世界。
第三、运用多种国庆视觉形象叙事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运用视觉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是国庆视觉形象的重要实践目的。从叙事主体来看,虽然政府、党派、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个人等皆可有灵活多样的国庆视觉形象叙事手段和展现方式,但其主要是一种官方主导的叙事。如2020年CCTV1推出的《中国梦·祖国颂》国庆特别节目,设立“风雨同舟,激荡爱国情怀”“疫情防控,坚定制度自信”“开放包容,彰显大国担当”“团结奋斗,决战脱贫攻坚”“携手同行,奔向幸福小康”“不忘初心,喜迎建党百年”六大主题,通过歌舞、杂技、沉浸式讲述等节目展示了脱贫攻坚伟大成果,彰显家国情怀、弘扬中国精神。2021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国庆特别节目《瞬间中国》系列节目,从小切口讲述大故事,展示人民对安定团结、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
从叙事语境来说,国庆视觉形象叙事体现出“高语境文化叙事”风格。“高语境文化叙事”传达信息含蓄节制,将信息蕴藏在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如2021年国庆特别节目《榜样的力量》,通过展示钟南山、张桂梅、黄大发、叶培建等人的光辉事迹,传达出英雄人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爱岗敬业、敢于担当、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等中华民族精神品格。从叙事功能来看,国庆视觉形象叙事通过多种方式讲述中华民族的历史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为国家和民族认同提供历史依据,坚定人民走向未来的信心。这些故事注重真实性、形象性和情感表达,有利于人们把握故事背后的意义,唤起人们的共通情感,传达主流价值,促进各族群众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五、 结语
党的十九大以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研究的主题。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演讲,明确指出要通过“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内容丰富,其中的视觉形象具有他种形象少有的直观性和易传播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而国庆视觉形象是其中的典型形象,在国家和民族认同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研究发现,国庆视觉形象的建构基本考虑到了民族认同不可缺少的历史、民族、政治、文化等维度,呈现了我国悠久历史和文化脉络,展示了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展现了国家强大的组织和运行能力。国庆视觉形象通过情感生成机制、历史生成机制、社会生成机制强化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增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传播具象性国庆视觉形象、象征性国庆视觉形象,利用多种国庆视觉形象叙事等形式讲好中国故事,激发共同体成员情感共鸣,促进民族共同体价值凝结,从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国通过视觉形象方式庆祝国家生日已有较长历史,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但在党中央提出通过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前,各界对中华民族形象,特别是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鲜见,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存在大量亟待研究之处,这在国庆视觉形象的设计和使用上也有体现。如本文提到的2009年国庆节民族团结柱设计就存在改善空间。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一个形象和符号体系,用56根团结柱来展现中华民族的面貌固然能给人带来较强的视觉冲击,但由于这种设计易于体现各民族的个性,难以表现多民族的共性,对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表现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觉形象设计实现尚有较大研究空间,有关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基础理论研究亦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