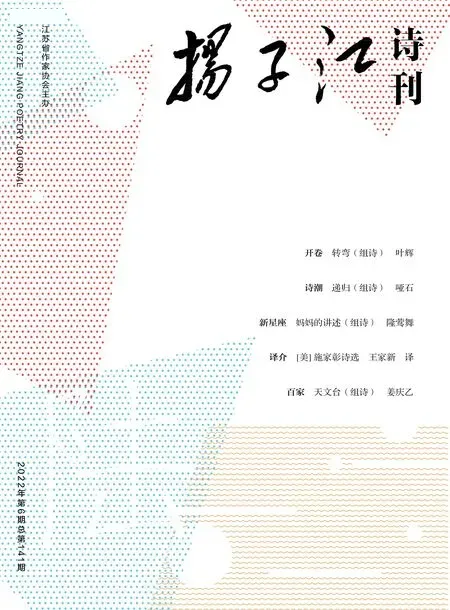沉思的弧度
——叶辉诗歌读札
吕静瑶
叶辉是一位难以被标签化的诗人,因为他诗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不是一两个词可以概括的。叶辉是现代的,但这种现代又借助传统来表达;叶辉打磨语词,但不像张枣那样专注于语词;叶辉诗歌有江南的阴柔,但没有朱朱的绮靡、潘维的妩媚。叶辉诗歌中存在某种精神气质,让人一眼辨识出来。那是一种智性之美,一种沉思的超然,但这种超然又借助尘世空间的辗转挪移得以实现。
叶辉的新组诗《转弯》正体现了他一贯的沉思的精神特质:这些沉思始于日常生活的片段,但日常场景的铺陈往往不是为了表现日常本身,而是为想法的灵光一现做准备。他虽着眼日常,却能够从日常抽离开来。日常在他的诗歌里常常成为功能性的存在。《转弯》中,“我们/更多时候看不到自己/两侧的灰暗”,这个想法在开车转弯的过程中产生。诗人耐心地叙述转弯,只为了让沉思出现得更加自然。
叶辉这组诗不仅赋予了日常以深度,而且借助这些伪装的日常,完成了对世界的瞭望。叶辉关注生命、灵魂这些话题,沉思的主体在场而又隐匿。《驻地》中,“我突然想知道/灵魂的居所,在煤烟气味中”,但在之后呈现的场景中,诗人不再出现,只凭借一种叙述语调表征其存在。《机场》从下机这件事生发出彻悟,“世界在我们之后会继续存在”。尽管诗人是事件的经历者,却从事件中超脱出来,视野由眼前扩大到世界,保持着旁观而不介入的姿态。他有时也以孩童般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从人们习焉不察的现象中发现悖谬。《属相》中诗人追问 “是谁/在我们身体里塞进这些”,但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而是将镜头匆匆扫过沉睡的属相,之后镜头再度转向我们,一连串的“我们”以急促的语势带动画面的切换,最后定格在“我们孤独”,由实入虚,诗人也将自我隐身在了“我们”之间。
组诗中的日常意象是精心选择的,往往和诗人的思考密切相关。《机场》选择机场这样一个场所,为的是借助这个旅途的中转站表达对生命的认识。人生如逆旅,机场具有象征意味,但诗人又分明在描述一场具体的旅行。《光》来自日常,又具有隐喻意味,“无论怎样,你都无法/描述真正的光亮”令人浮想联翩,但叶辉又很快将场景拉回当下的日常,自始至终没有透露隐喻的指涉。就是借助这个可实可虚的意象,诗人自由地往返于沉思的星空和日常的土地,不断进行着“在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在清醒的经验主义与我们对不可见之物的迷醉之间、在我们具体而特殊的生活与神性之间的谈判”。
叶辉擅长借助语词的多义性和隐喻性敞开诗歌的丰富性。值得注意的是,叶辉诗歌中的能指有时并不对应具体的所指,而是召唤着读者去填补意义的空白。《机场》中,“走向‘到达’”用词性的转化突出了过程而非结果,传输带上的人们“超越”了我们,而不是超过,一字之差就从现实跨越到形而上层面,至于一天的“降落、起飞”,明指飞机,却令人自然而然想到生命。诗人如同语言的炼金术士,发明了汉语的多种可能性。
这组诗歌音域低沉。他写道:“风起时/世界露出了它荒芜的本性”(《风起时》),但诗人有着向死而生的达观,《机场》中,面对物比人长久这个事实,诗人丝毫没有惆怅,反倒“涌起一阵喜悦”。这是知晓造物不完满却坦然以待、欣然接受的大豁达。从这组诗中,也能感受到一种隐秘的力量。“我们之间隔着窗玻璃/但不是这片(在世界的另一边?)”(《光》)令人感到冥冥之中,世界上有另一个人与你相对应,类似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两生花》。
叶辉拒绝抒情,诗歌也极少涉及情感,但这组诗中有一首特别的诗:《母亲不在了》。这首诗写母亲去世,感情极为节制。诗人反复陈述母亲 “不在”的事实,却刻意回避了“我”的感受。“空寂的厨房里一阵雨水的气息/一直弥漫到过去”,还原了母亲生前的生活场景。曾经,厨房里是母亲忙碌的身影,而现在厨房里变得空寂,那雨水的声音还和过去一样,但转眼已经物是人非。结尾,诗人恍恍惚惚仿佛见到了母亲,在那个刹那,诗人叫出了“妈妈”——那个孩童时的称呼。这首诗中,诗人放弃了沉思,因为在至亲去世时是没有能力思考的。但就在这貌似平平淡淡的叙述中,母子间的情感显露无疑。
事实上,叶辉新组诗的这些特质在他过去的写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叶辉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创作的。就表现日常而言,他最早的诗集《在糖果店》(1998)就是对“日常主义”的实践,但诗人无意于还原日常的平庸琐碎,甚至不以描述日常为目的。《在糖果店》一诗从“有一回我在糖果店”的日常起笔,用“我”想着的其他事情和糖果店里的现实作对照,营构出第二重空间。然后,诗人用一个类比再次跳转,引出小山上的杂草和荒凉的庭院。一个轻灵的转身,把读者的视线引向远方,完成了时空的叠加与交错,使得在糖果店这个日常本身成为了一个写作的契机,而非全部的内容。通过日常细节的剪裁,叶辉表现了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状态。
在早期,叶辉就显示出对神秘事物的关注。《一首中国人关于命运的诗》通过不同的事件传达出一种宿命;《遗传》从“桌沿上的压痕”是数代主人的创造到女同事漂亮的眼睛来自上一代人,昭示出遗传的存在;《先知》则塑造了一个能够预言未来的女性形象。但在这些诗歌中,叶辉都只是通过叙事,传达他对生活的理解。这些叙事往往省略很多细节,只保留必要的碎片。正如作为建筑师的叶辉偏爱以简约的线条营造出高级感,叶辉诗歌里的场景也只是简单勾勒。《在乡村》中,没有一句多余的渲染,但寥寥数语足以令人浮想联翩。
在场景描述之外加入思考,要到叶辉的第二本诗集《对应》才出现。在这本诗集中,日常作为一种伪装,将思考包裹进来。《一颗葡萄》中的释梦人、《信徒》中的住持,都是诗人用以引出思考的人物。叶辉很好地将思考和形象结合在一起,在空间的转换中,思考自然地浮现。《一颗葡萄》中,思考并非作为结论得出。在说出“要知道,人在这世上/会有另一样东西和他承受/相同的命运”之后,诗人来了一句亲昵的“你信不信”,营造出对话的氛围,吸引读者顺着那个语调,将视线由葡萄转向女人,诗歌由此进入另一个层次。《信徒》中,诗人设置了下雨的情境,借住持之口说出“这些人是真正的信徒/因为他们懂得/怜惜自己的膝盖”。但诗人没有接着谈玄,而是将镜头转向远处的池塘。为了短短三行的思考,诗人耐心地铺陈寺庙内部的场景,让读者进入情境,从而让那句话的说出那样自然而然,思考的痕迹也被悄悄抹除了。
如同这组新诗里的《院门敞开》一样,叶辉诗集《对应》中的一些诗篇,也表现日常不起眼的场景。这样的诗篇在叶辉的诗中虽然不多,却难得地显出温暖宁谧的色调。《慢跑》中“我”调整自己的步伐,让自己和女儿的距离不远不近;《考试》中“我”和女儿的交流;《远眺》中“我”顺着邻居的小男孩手指的方向看。这些事件经过诗人的叙述显得趣味盎然,带着生活的温度。
尽管叶辉在上世纪90年代就说“我是一个练习者,现在我练习隐秘这个主题”,但叶辉诗歌最集中体现隐秘主题的,还是《对应》这本诗集。诗集《在糖果店》尽管涉及人世变化之无常,却没有点明超验的存在;而到诗集《对应》里,叶辉的诗歌增添了通灵的成分,于日常事物中寻找隐秘的联系。《对应》这样写道:
你照过镜子后
那人从背面离开,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那个和你几乎一样的人
不过命运将你左脸的胎记
放在他右边
但他不在乎,而且他还有一个
与你相近的名字
只是总与你背道而驰:你坐着时
他正躺下,你走在沙漠中
他却在热带避着雨
只有一次你们有机会擦肩而过
当中隔着很高的围墙。
这组新诗《光》中隔着窗玻璃的“我们”可以追溯至此,但事实上,《在糖果店》的《胎记》中——“我上中学时,改掉了我的名/以便和另一个区分。我毕业时一个和我/酷似的人上了前线//现在他回来了,只是脸上多了一道/战火灼伤的痕迹。如同在其他地方和时刻里/辨别我俩的胎记”——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一想法的雏形。而不同时期,叶辉对此的表达也体现出不同。《胎记》带有一些猎奇的意味,而《对应》中诗人则仿佛居于造物主的位置,控制着全局,到了新的组诗中,诗人又回归常人,语调的犹疑显示出人的有限性,也加深了不确定性。
事实上,《对应》不仅选取了一些超验对象如家神、空神、魔鬼等加以叙述,叙述的口吻也笃定如先知。《萤火虫》中,“萤火虫,总是这样忽明忽暗/正像我们活着/却用尽了照亮身后的智慧”,这一睿智的声音,是非人间的。这一语调的获得来自于《易经》。作为研究《易经》数十年的诗人,叶辉擅于从现实的表象中提取相互勾连的符咒。《一颗葡萄》结尾死去的杂草如同一个谶语,诗歌里的葡萄、榆树、石头、黑鸟也类似一个个符号,互相感应,画面暗藏玄机。而诗人拥有着超人的掌控力和通晓一切的慧眼。
这种情形到了诗集《遗址》时期有了改变。此时诗人发现了对应之外错位的存在。这一发现让诗人失去了万物皆有对应的笃信,因而开始关注偏离,用他的话说“就是离靶心有意远一点”。这种远离让诗人居于旁观者的位置,不再具有操纵一切的力量,但依旧以智者的形象出现,“我不代表世界/但我知道,它的存在已被什么人允许”。叶辉的诗歌并非一开始就获得了世界的广度,而《遗址》正是诗人将触角从小镇延伸到世界的尝试。这本诗集中,出现了上海、临安、泰晤士河、巴黎,空间的拓展增加了诗歌的包容度,也使得诗歌更具有普适性。
如果说《对应》中的思考还是以遮遮掩掩的方式呈现,那么在《遗址》中,诗人叶辉的思考从幕后来到了台前。《远观》中,诗人写道,“大雾看起来像是预言/涌入了城市。当它们散去后//没有独角兽和刀剑/只有真理被揭示后的虚空”,《月亮》中,诗人说,“永恒,就是衰老/就是淬火后的,灰暗、冰冷”,《谬误》则全篇由思考而来。
《谬误》这样开头:“蛇的谬误在于没有水它却在游动//蝙蝠的困境是总会面对/两个可供选择的世界,因此它倒挂像一笔欠账”。由蛇和蝙蝠这两种日常习见的动物展开,在临近说理的边缘时,诗人又一次次以具象将读者拉回现实世界,及至追问“为什么短暂的人类/有如此多含混不清的历史”,旋即搁置问题,以“黎明时分的困倦”这样一个比喻中断思绪,并赋予了“历史”这个词以感官性,让形而上的思考有了物质的肉身。
《遗址》里,叶辉就开始把握一些顿悟时刻,即便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他要周密地布置舞台。他以语调的变化,操纵着读者的注意力,尽显汉语的柔韧与灵活。《候车室》就由一个冥想的瞬间生发开去。诗歌从场景的铺陈开始。候车室睡梦时刻的灰暗给人一种私密感,使其成为一个适宜汇聚诗性的空间。当行色匆匆的旅人各奔东西,沉寂的画面被一个声音打破:
生活就是一个幻觉
一位年长的诗人告诉我
(他刚刚在瞌睡中醒来)
就如同你在雨水冰冷的站台
手里拎着越来越重的
总感觉是别人的一个包裹
诗人以真理的顿悟结束了对场景的描绘,又切断了叙述的进行,以第三人称转述的方式让音高降低,并构成一种轻微的反讽。最后画面中站台上拎着包裹的旅客也是每个人的抽象化身,使得场景本身变成一个象征。诗人的这段话可以解释这首诗:“我们的生活可能就是其他生活的影像,可能是历史生活的影像,也可能是未来生活的影像。我们生活的真实性,也可能是复制以前的生活或其他人的生活。”
某种程度上,叶辉的诗歌和阿什贝利有相似之处。这两位诗人都是沉思型的,都偏爱碎片式的表达,都需要耐心去理解……海伦·文德勒认为“直觉、预感、怀疑和推测是阿什贝利典型的表达形式”,叶辉也是如此。但二者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两人无法等而论之,就内容而言,叶辉对灵魂和生命的关注是他独有的。“灵魂”这个词,在叶辉的诗歌中反复出现。诗集《在糖果店》里,诗人就写过《雨的灵魂》;诗集《对应》里,《面孔》一诗中有“飞逝而去的灵魂”;诗歌《果树开花、发芽的季节》里有“少年的灵魂”;诗集《遗址》中“灵魂”则更频繁地出现,及至新的组诗中诗人试图寻找灵魂的居所,可谓一脉相承。
叶辉的诗歌以灰色调为主,这也许缘于他对阴影的偏爱。正如他的诗歌《幸福总是在傍晚到来》,在诗人看来,正是这种半明半暗的光线能够让人看清很多东西。这种想法在他新的组诗《光》中也得以体现。叶辉的诗歌偏冷,因为其中有造化弄人的残酷。但他不厌世,正如诗人所写,“我,一个平凡生活的爱好者/一个喜欢真实蜂蜜的人”。因为他从存在本身的不完满中看到“过往人类的反光”,“是废墟?也可以/是未完成的城堡。我也可能/只是提前到来”。这样一种眼光使得他始终怀抱希望。
叶辉诗歌的冷还体现在他感情的节制上。叶辉的《信》写自己感情的失落,只是写了一些交往的片段,淡淡道,“你可能不记得了,而我可能也会/在接下来的另一天忘掉”。漫不经心的口吻,带有几分浮纨的姿态,仿佛诗人对此并不在意。接着诗人以故作轻松的语调穿插了一个神秘传闻:
上个月我听人说:如果
人失去一种爱情,就会梦到一个抽屉
失去一片灵魂(假定它像羽毛)
就会捡到一把钥匙
紧接着,诗人说自己找到一把钥匙。爱情的失落和灵魂勾连起来。对诗人而言,爱情是触及灵魂的。但诗人没有渲染自己情爱失落的悲伤,始终保持着波澜不惊的语调。这种语调延续到了《转弯》组诗里的《母亲不在了》,只是那首诗没有以诙谐化解悲痛,因为那会打破庄重。
叶辉有一句诗“拐弯处的弧度会给沉思带来愉悦”(《高速列车》),恰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叶辉的诗歌中充满了沉思,但诗人一方面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思考,另一方面,这种思考又和画面的叠加、空间的挪移结合在一起,不借助抽象的概念,而让具象的事物成为思考的载体,这种“拐弯”让诗歌显得曲径通幽、充满意趣。尽管叶辉的诗歌充满了东方古老的神秘主义色彩,但他的诗歌本质上是现代的,不论从技法还是从精神上说,而他诗歌中的传统元素,佛禅也好,本土习俗、传说也罢,都只是他抵达现代的“拐弯”。通过营造这些优美的弧度,叶辉诗歌的沉思缓慢地从语词中流淌而出,沁润人们的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