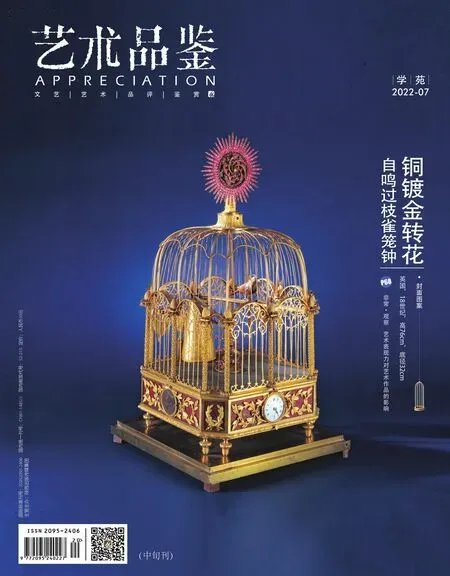地域文化差异与文化整合*
——地域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史研究之关系
孙赛赛(信阳学院音乐学院)
我以为,强化具有独特性的“区域音乐史”的研究,能大大丰富“中国音乐史研究”,并能体现出中国音乐史的多样性。也即是说,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共同构成了文化的整合,“地域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构成了中国音乐历史的多样性。文章将从三个方面谈二者的关系。
一、地域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史的属性问题
关于“地域音乐文化”的基本概念,从人类学意义上来说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与音乐活动相关的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总和。不同地域内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不同,便导致了地域音乐文化的差异性。其中,体现群体人格的深层次文化是判断地域文化差异性的主要依据之一。一定地域内历史形成并被人们所感知和认同的各种音乐文化现象就是地域音乐文化,其学科归属涉及音乐学、音乐史、历史地理学、文化学、文化史、社会学等的交叉学科。研究地域音乐文化,必须牢牢把握它的历史性、地域性和音乐文化特色。
“地域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史”都属于音乐史研究,二者的关系表现在都属于“音乐史学”学科体系中的一部分——“音乐史研究”。我国的“地域音乐史”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一部分。根据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教授对音乐史学学科体系的构架认为:“音乐史”即是由客观存在的“音乐事实”与主观阐释的“音乐史研究”组成,它是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最终体现;音乐史学方法或称音乐史学理论,是我们赖以研究前者的重要手段与途径;音乐史学史是总结经验并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的必备条件。而在此,关于“地域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史”研究都属于“音乐史研究”,是“音乐史学”体系构架中的第一部分,所不同的是二者在研究范围上的差异。
“地域音乐史”主要以研究某一空间范围内与音乐相关的一切音乐“事实”,将曾存在于此地域的本土音乐、外来音乐和混合音乐都纳入其研究视野。如“湖北音乐史”作为“地域音乐史”的范畴,研究范围包括曾存在于湖北的本土音乐、外来音乐和混合音乐;而“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华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与文明史,960 万平方千米的地域内,56 个民族的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的研究。
当然,由于地域不同,造成的文明的差异,导致各地域音乐史研究范围、甚至是方法的不尽相同。首先,在观念上必须把地域音乐文化视作一个整体,其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互相影响,某一局部发生改变导致其他环节做出连锁反应。关注取材于其他音乐或各音乐事项内部相互的影响,以及个体、群体及其音乐若发生质的改变,势必联动整体的关系链。同时,有共同特性的单一环境中的不同人群及其音乐,其生存与互相影响成社会背景下地域音乐文化的特色各不相同。以上多是在横向上的把握,相对而言,对“地域音乐史”的研究其“历史”的纵向思考则同样关键。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正是本文论述所基于的观点。
这首先就对音乐学家提出了要求,尤其是音乐史学家。音乐历史本身就有已存在的“历史”和“写的历史”之分,写的历史里面注定有主观因素的存在,这就牵涉到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史学家。因为史学家写史本身就是一个史实。与此同时,不同地域的人们对待音乐的态度和理解存在差异,这就对音乐历史研究者有了更高的要求,应具备最起码的尊严感与严肃感,具有深厚的知识体系,写出可以信任的音乐历史。余英时曾在《历史与思想》一书中提出:“历史家关心的并不是饮食男女这类简单的事实,而是人类思想所创造出来以安顿饮食男女等欲望的种种社会习惯的构架”。
其次,关于地域音乐史研究的手段与方法。目前来看,关于“地域音乐史”研究最基本的手段之一,其史料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史学的发展必须要建立在翔实的史料根基基础之上。西方史家伯伦汉(E.Bernheim)认为人类社会不可缺少史学,他认为:“具有演化动作之人类社会,苟一日存在,则史及史学亦将与之俱存,而就史料之性质而言,可知其前途并无止境可言。”由此可见,史料对史学的意义。对“地域音乐史”而言,它与“中国音乐史”一样,其音乐史料包括文字史料(包括正史和野史)、曲谱史料、图片史料、实物史料、音响史料等,且注重因前人所忽略而渐见亡逸之史迹,早已偻指难计的口述史的发掘与研究。按马克·布洛赫所说:史学家应当像任何科学研究人员一样“面对众多纷繁的现实”做出“自己的选择”。但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或简单地收集资料,而是需要科学地收集资料,并应通过这种资料的分析来达到重建和解释过去的目的。所以说,“史学的努力更像是一种哲学的努力,而不像是科学的努力。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史学更多的是加以阐述,而不是进行解释。”
对音乐史料的收集、整理及考据等“处理”过程完成后,将其溶于整个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对产生的“音乐事实”进行“为什么”的分析。也即是说,从历史的角度关注音乐事件在时间的先后次序,并研究出一个使这些音乐时间相联系的因果关系链,着重强调社会生活中被意识到的方面:如可考证的音乐历史事件、人类思想的原因及生活环境与条件的记录;从理论和分析的方法上研究现象而非音乐事件,着重于音乐事件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以及“为什么”,寻找揭示隐藏在复杂现象中的组织规则,如音乐风格的形成等。
当然,对“地域音乐史”的方法论而言,则需要累积多人多年经验,借鉴其他学科的手段和方法,在经验中得出适应音乐史研究的道路。可以说,在“地域音乐史”研究的过程中,方法论并非固定的,同样也是无止境的。它随着科学与学科的发展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更需要不断尝试新的方法、开拓新的论题。目前,从实际研究的研究来看,主要借助于“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民族学”等。同时,对地域音乐的研究既要涉及音乐学的方法,又要借助地理学的手段,甚至是与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生态学、气候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密切关系。
笔者以为,因地域音乐史先天差异基因的存在,历史学中的计量,即“计量史学”的方法,尤其是根据音乐历史事实产生的图表各栏目等对史学的填补,应该被学界关注和重视。由于“中国音乐史”对涵盖中国范围内音乐事项并不能完全容纳,对处理甚至涉及音乐历史现实的一些重要部分无能为力,这就更需要计量。从本质上说,音乐事项的量变到质变的程序,包括一系列根据同一性建立的音乐事实。当这些音乐事实的时间变化表现出一系列周期时,就能反映人们所称的稳定中的音乐变动,因此也反映着一种平衡分析。但当一个或数个音乐事实在时间中的变动表现出一种累计增加的趋势,那么时间性的结构转变,即音乐事实变化节奏的转变就从这一时间界限开始的,相反亦然。如此,中国音乐史能够对具有差异性的各地域音乐在空间中具有差异性的各地域在空间中具有差异分布的局势的研究,又能把握各地域音乐史中所揭示的内部转变趋势。
总之,从微观上描绘和分析地域音乐文化的问题,也从宏观视角概括地域音乐史研究的对象、视角和理论方法;从横向上把握音乐的形态,也从纵向上关注音乐事实发生的前因后果。笔者以为,“地域音乐史”作为“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一部分,二者虽研究范围不同,但在研究手段与方法上,目前“地域音乐史”的研究可多借鉴“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方法与手段。
二、“地域音乐史”对“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补充与完善
迄今为止,对中国音乐通史的研究著作已书盈四壁,但作为通史研究完善与补充的“区域音乐史”的研究,则还相对滞后。同时,由于主客观的原因,目前所见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尤其是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近代化程度较早的地区,尤其是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研究,以及对居住在中心城市的作曲家及其作品、音乐表演以及音乐教育等的研究。“地域音乐史”作为“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一部分,虽然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关于“地域音乐史”研究的成果较丰,但作为对通史研究完善与补充的区域音乐史的研究则尚待挖掘。在当下的“区域音乐史”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中心向边缘扩散,以地域为研究范畴的“区域音乐史”已日益成为学科建设的需要。以下将以“湖北音乐史”为例加以说明。
如1978 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的曾侯乙编钟,是目前所见的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物的巅峰之作,“曾侯乙编钟”也成为各中国音乐通史著作中必不可少的音乐史实。湖北省作为“曾侯乙编钟”的故乡,研究湖北音乐历史中的“曾侯乙编钟”的义务责无旁贷,对其钟体铭文的研究,更是弥补了中国古代乐律记载方面的不足和缺失,而这即是“湖北音乐史”研究对“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补充与完善,更是对1978 年之前的音乐史的“重写”。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前问世的,至今被音乐学界所推崇的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这部皇皇巨著问世时,对音乐史而言意义非凡的“曾侯乙编钟”并未被世人挖掘,这造成了“重写音乐史”的事实便是对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补充与完善。
再如,进入近代,湖北地区为近代化程度发展较早的内陆地区之一,它以武汉为龙头,成为中国中部现代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地带。所以,“地域音乐史”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一部分,故二者在审美上具有共同性,二者的研究也都能够促进彼此的理解。关于“湖北音乐史”的挖掘不仅仅表现在以上所列举的曾侯乙编钟、音乐教育、音乐思潮等内容,随着音乐资料的不断挖掘,将中国音乐通史著作中忽略的边缘音乐事项进行整合,将势必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起到补充和完善的作用,丰富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
三、独特性与多样性共存
“地域音乐史”因其得天独厚的拥有某种独特的音乐资源,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多样性,对丰富和丰满“中国音乐史”研究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因拥有共通的审美性,各“地域音乐史”研究的差异性,并不会阻碍整个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共同性,反而会促进多样性的产生。在音乐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自我与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野中,来看各种音乐事实,人们才能够谈及整个中国音乐的“文化认同”。
近些年来出现的地域音乐史研究的著作,如《哈尔滨西洋音乐史》《东北现代音乐史》《乐人之都——上海: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的发轫》《区域音乐的历史回首》《上海音乐志》《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1850~1950,1998~2005)》《浙江音乐史》《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山西乐户研究》《台湾音乐史》《西藏音乐史话》《西域音乐史》《福建音乐史》《江南音乐史》《山西音乐史》等。此外,还有大量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及期刊论文。
楚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早在20世纪30 年代,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湖北是楚国的发祥地、楚地中心、楚音乐文化的主要影响区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秦楚国遗址、墓葬等的发现,更是激起了学界探索楚文化的热情。研究范围涵盖了文学、地理、经济、军事、文字、服饰、哲学、历史、科技、风俗、建筑、歌乐舞等各文化领域。在音乐领域,其研究方法也随着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文献学、图像学等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渗透,逐步向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楚乐舞的研究也受到学界学者的青睐。毫无疑问,楚乐舞的种类、职能和形态特征以及对汉、唐乐舞具有深刻的影响。湖北传统乐舞体制恢宏的形态特征,至今还可以在湖北的一些地方寻觅到。如鄂西南地区数百人以鼓为节,边歌边跳巴山舞和在丧事活动中数十上百人在雄浑的鼓乐声中和高亢的歌声里,如醉如狂地进行跳丧鼓表演的场景,是湖北传统乐舞这一形态特征的折射。
曾侯乙编钟在随县的出土更是反映了我国音乐文化在战国初期的高度发展水平。鄂西在楚国灭亡后,仍存有“巴哥”“楚舞”,至南宋时期还在流传。明清史料记载的鄂西民歌“姊妹歌”与唐代竹枝词的渊源等,以致清末民初在张之洞带领下成为全国的教育“示范省”,以及近现代音乐教育、音乐家、作曲家的贡献等,这一切对以前局限于上海、北京为中心的中国音乐通史的研究渐渐丰满起来。
湖北省是中国“中部崛起”战略的支点中心,全国的交通枢纽,科教文化实力位居全国前列,是全世界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城市,所以深入挖掘湖北音乐史和学科建设迫在眉睫。武汉这一地域早已受到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城市建设、环境等各个领域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对于湖北音乐史的研究自20 世纪末才受到关注,但还有待于形成系统。截至目前,对武汉地区音乐发展历程的关注,主要有田可文教授的著作《近现代武汉的音乐生活》(即将在2022 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另外的论著《湖北音乐文化史》(即将在2022 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也涉及武汉城市音乐文化的研究。此外,田可文教授率领他的研究生们,深入到湖北音乐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进行研究,在从事湖北省《湖北当代音乐史研究》的课题研究。所以,田可文教授的研究生在毕业论文撰写时,也有较多关于武汉音乐生活研究的论文(其有9 篇硕士学位论文),田可文教授的研究生发表的涉及武汉音乐史内容的期刊论文达14 篇以上。
尽管在近些年地域音乐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青睐,出现了一些地方音乐史的研究成果,但对浩繁的音乐通史著作而言则还相对滞后。在当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并开始从中心城市的音乐史研究向内陆及少数民族地区扩散,以某一地域为研究范畴的地方音乐专门史已有诸多优异成果。而目前对于“湖北音乐史”研究而言,其研究成果略显单薄,并不足以展现湖北音乐当年的风采,亦不足以体味湖北音乐发展背后的故事。故而有效利用湖北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其进行研究与总结,力图展现湖北音乐生活的波澜壮阔,并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浓重的一墨,已日益成为学科建设的需要。
当然,音乐事实的形成既与生成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历史的继承性与独特的艺术规律,因而对音乐与文化关系的理解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否则,容易陷入牵强附会的境地。但是,应该肯定的是,各“区域音乐史”研究的独特性共同构成“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多样性。在当下,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给我们提出紧迫要求,必须更好地理解音乐文化差异及特殊性,只有这样,才能丰盈整个中国音乐史。
四、结语
总之,“地域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史”都属于“音乐史学”体系中的“音乐史研究”,而“地域音乐史研究”为“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一部分,因“地域音乐史”有其独特的地理、历史特征,以及有着无可替代的“音乐历史事实”,必然成为“中国音乐史研究”亟须补充的部分历史史实。只有各地域的音乐史研究得以深入挖掘和建设,各地域文化的差异共同构成整个文化的整合,才能使整个“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趋于丰满。在不断完善“地域音乐史”的过程中,应该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其一,以正确研究解释建立人类过去活动的重要音乐事实,使后人在音乐研究中有足够资料选择如何“以史为鉴”开创新的音乐未来;其二,选择当代重要音乐史实、音乐思想、音乐行为、制度构架、社会生活、音乐组织等作以记录,以备后世学者研究;其三,建立与完善音乐史理论体系,得以使世人与后人的理解,并为人类音乐活动作指导。因为,“历史家的任务既不是喜爱过去,也不是脱离过去,而是控制和了解过去,作为了解现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