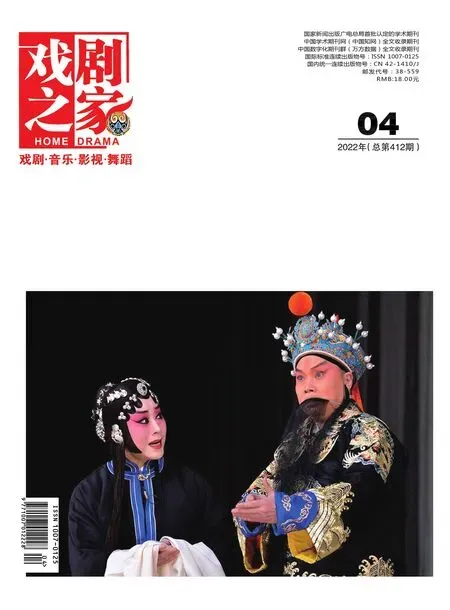《马拉/萨德》
——不只是戏剧
赵 莹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4)
众所周知,戏剧因其特征具有难以存留的特点,我们喜欢按照录像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以便留存和研究。但很有意思的是,观众在观看时,很少把这种录像等同于电影艺术。他们会说:“我今天看了一部戏。”即便这些录像故事有演员,有故事,有镜头的剪切,但我们在观看时,仍然是没有电影意识的。电影,作为一个复制的手段,当然可以复制著名的舞剧,歌剧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即使假定这类复制力符合银幕的特殊要求,它们至多也就是将其“储存”起来而已,我们在这里对之是不感兴趣的。而创作于1967年的《马拉/萨德》却是一个另类,他不仅仅是研究戏剧《马拉/萨德》必观摩的录像资料,更具有电影艺术价值。
一、空间的叙事性
(一)空的空间
《马拉/萨德》这部影片中,空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它严格尊重布鲁克的同名戏剧舞台剧场景,完整呈现出当年演出实况。而《马拉/萨德》这部戏剧,和一般戏剧不太一样的是,他的影片(戏剧)的背景始终如一,故事只发生在疗养院的现代浴室,整个戏剧演出过程中,没有任何背景的改变,不会一会儿换一个幕布,也不会一会儿加一个背景,布鲁克试图用意象化的演出来营造空间的诗意。
剧场灯光的使用也极具特色,光线的存在感被降到最低,舞台灯光的分布极为均匀且从头至尾没有丝毫变化,布鲁克认为戏剧形式必须尽量简单,通俗易懂又意味深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布鲁克导演的戏剧都像一幅中国画一样,舞台上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是“空的空间”。
(二)演员的空间
演员的表演也极具意象性,道具数量被减少到最低,《皮鞭下的萨德》这一场中,本应是萨德被科黛手中的皮鞭抽打,而布鲁克的处理方式非常写意,萨德脱去上衣跪在镜头前,喃喃自语,而饰演科黛的女演员在其身后,低下头弯下腰用头发模拟鞭子,随着萨德的台词,一下一下地抽打着萨德的背部,其他角色则围在四周观看。
电影中多增加的一层叙事:《马拉/萨德》这部戏,采用的是剧中剧的结构叙事模式,三层时间关系,第一层即20 世纪60 年代,戏剧《马拉/萨德》上演;第二层即本戏——1808 年,萨德侯爵指导戏剧,库尔米和妻女现场观看戏剧;第三层即戏中戏,1793 年,科黛刺杀马拉事件。而在这三层时间关系中,1808 年的时间线和1793 年是不断切换交织在一起的,加之以合唱队时不时地进入,由此构成间离效果。布鲁克除去真实呈现戏剧场景和表演外,在影片中还加入了一层观众,摄影机给了我们一个大全景,正在上演的戏剧《马拉/萨德》正在由一群黑压压的观众观看。也就是说在这部影片中,布鲁克设置了四层时间关系,在前文说到的60年代前,加入了一层现在时:电影观众观看60 年代的戏剧观众观看上演的戏剧。但也就是这多加的一层,使得戏剧空间成功地转化成了电影空间。
如何转换的呢?观众在观看由摄影机录制的戏剧影像时,脑海里是有着深刻的舞台空间的意识的,也就是说在影像中呈现给我们的空间位置,已经被预设为“舞台上的戏剧空间”,同时,一般的记录戏剧的影像也会有意识地如此呈现:舞台全景,演员表演的中景,近景,特写相互切换。所以我们看到的表演是戏剧表演,感受到的空间是舞台空间,镜头的切换变更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看到演员在演出中的状态。
二、视角的叙事性
布鲁克在他的戏剧理论书《空的空间》中,第一句话便说道: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注视下走过这个空间,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也就是说“别人的注视”(视角)“走”(表演)和“空间”(舞台)构成了戏剧的最基本要素。其中“别人的注视”只是叙事接受者的基本视角,而一个文本的视角是包含了叙事视角和接受视角的综合视角。
(一)叙事的视角
布鲁克本人对观众的注视非常重视,《敞开的门》中他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工作时,他常常会用一块地毯作为排练区域,地毯外属于日常生活,想做什么都可以,而当演员进入到这个地毯的时候,一定要有明确的动机,一定要积极主动。也就是说,当演员在某一特定空间中被注视的时候,他便不是他自己了,而是戏剧的一部分,凝视在布鲁克的创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三重视角的构成:在戏剧《马拉/萨德》中,萨德作为导演指导疗养院病人拍戏,观察演员演出,以便不时指导,这是第一层注视视角。其次,库尔米和他的妻女观看精神病疗养院剧团演出的让·保尔·马拉的迫害与谋杀事件,这是第二层注视视角。最后的一层注视视角则是戏剧上演时,观众对戏剧的观看。这三重视角使得戏剧变成了嵌套式的结构,1793 年,1808 年,以及60 年代戏剧上演三重时间三种观看同时交织呈现在一起,构成了“此时此刻”。布鲁克本人也曾说过:“戏剧指的不是剧场,也不是文本,演员,风格或形式。而是一个叫做‘此时此刻’的迷里面。”
(二)接受的视角
第四重视角的构成:在影片《马拉/萨德》中,多添加的一层叙事,不仅仅使得戏剧空间转化为了电影场景,更是在影片叙事中增添了一丝意味。再加上电影观众在银幕前的凝视,这就构成了四重观看模式,更有意思的是,导演在影片中还增加了一层凝视,即演员看向摄影机(电影观众),影片中大量的这类型的特写镜头,舞台上的演员念念叨叨地说着自己的台词,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镜头。导演在这里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名叫“此时此刻”的幻觉。它把过去和将来都变成现在的一部分,它帮我们从深陷其中的地方超脱出来,又把我们和本来距离遥远的人和事联系到一起。
加上上文提到的四重时间的关系,形成了嵌套式的影片模式。打开一层还有一层,时空的不断变化,戏剧时空和电影时空不断交织,每个角色在凝视其他人的时候,同时也被凝视着,封闭式的结构把各个观众锁在一部影片中。而影片添加的这层叙事关系,在这部典型的布莱希特式的叙事体戏剧中又不显突兀,魏斯剧本中多层时空的切换叙事放到电影中来也只是多加了一层套子而已。
三、镜头语言的叙事性
我们一般看到的戏剧影像资料,为了最大限度地模拟观众观剧时的状态,通常是用固定的摄影机从观众席的角度来记录剧情,一定程度上来说,摄影机就是观众。电影导演必须选定一个特定的摄影角度,他就能规定哪些东西出现在画面上,他可以隐藏起某些他不愿意显示或不愿意立刻显示的东西,他可以突出表现他认为重要的东西,而同时又很可能并不直接表现他们在场面中的重要地位……一种只有把摄影机放在某一特定位置上才能为人看到的东西。让我们继续回顾影片《马拉/萨德》在镜头上的处理方式。
(一)镜头语言的叙事性
《马拉/萨德》中的镜头运用比一般记录戏剧的影像丰富得多。摄影机并没有拘泥于在观众席上,它在不断地变化,时而从观众席拍摄,时而进入舞台中央跟着演员的移动而变化,甚至它还出现了几个主观镜头,大量考究的构图,小景深的运用,这都是典型的电影思维。我们来看看第一幕中,夏朗东的开场白部分,布鲁克是如何用电影的手段处理的:镜头的起始部分是严格的居中构图的电影构图模式,紧接着镜头往后拉,夏朗东往前走,栅栏便显现出来,镜头右移,坐定在妻女旁边。这一个镜头对于银幕前的观众而言,是有一个心理层次的变化的,即:布朗东在开场。到:原来布朗东是在一个被封锁住的地方念这一段开场白。
(二)布鲁克的艺术生涯
真正从事戏剧之前,布鲁克学习的是电影制作,除去《马拉/萨德》之外,布鲁克的代表电影作品有《琴声如诉》(1960),《蝇王》(1960),《告诉我的谎言》(1963),《与奇人相遇》(1968)。当然他最为人知的身份还是戏剧导演,《摩柯婆罗达》《惊奇的山谷》都为世人所称赞,我们可以看到,创作于1967 年的影片《马拉/萨德》,在整个创作上都与一般的戏剧影像资料有所区别,典型的电影化的处理方式,明显的电影化的场景,景别和景深的使用,角度在舞台上的不停切换,这些都使其成为电影《马拉/萨德》而非记录戏剧《马拉/萨德》的影像。可与此同时,影片又完全符合彼得·布鲁克的戏剧思想,无论是空间的处理,还是观众与演员之间的“凝视”,甚至是他给观众的关于“此时此刻”的幻觉,无一不在引导观众往更深的戏剧方向走去。笔者认为,能够游刃于电影和戏剧之间的《马拉/萨德》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布鲁克的“空的空间”这一创作基础。
四、总结
众所周知,戏剧的表演空间虽只有一个舞台,但如果要涉及到时间和场景的变化,就要分场或是分幕,这个时候需要有背景和道具的变化,让观众的心理空间产生变化,以此来告诉观众:“表演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空。”可对布鲁克来说这一特性显得没那么重要,因为他所追求的便是“空的空间”,一个没有任何布景的空间,是真正意义上的“唯一的舞台”。而这种“空”,能够将观众们最大程度地代入戏剧,“一个赤裸裸的空间无法讲述任何一个故事,这样每个观众的想象,注意力和思绪都会是自由不拘的。”同样也是这种空,让电影所呈现出的空间也只剩下那唯一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