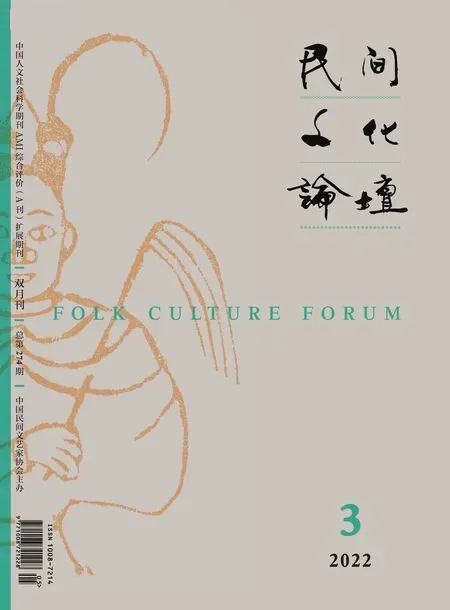通俗化实践与新中国文艺:《赵树理与通俗文艺运动改造(1930—1955)》的评议与对话
毛巧晖 杨天舒 李超宇 张 霖
[导语] 解放区所开创的“文学通俗化”道路对新中国文艺有极大影响,赵树理则是通俗化实践的典型个案。《赵树理与通俗文艺运动改造(1930—1955)》以赵树理在20世纪30—50年代的文学活动为线索,首先考察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大批新文学作家与工农读者、民间艺人的文化互动和文学探索;在此基础上主要聚焦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赵树理等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进入城市,在全国各地展开城市通俗文艺改造的活动,在描述北京的通俗文艺改造过程的同时,分析赵树理所创办的全国性通俗文艺杂志《说说唱唱》获得成功的原因,以及最后走向失败的复杂背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复旦大学中文系康凌副研究员负责组织的“对话作者”活动策划了对《赵树理与通俗文艺运动改造(1930—1955)》一书的评议与对话,这既是促动学界的交流,更是对《讲话》精神的致敬。毛巧晖从文艺通俗化实践、杨天舒从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李超宇从民间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复杂的文化互动关系等进行了对话,作者张霖则对不同的评述进行了回应。
构建文艺通俗化实践的图景
毛巧晖
19世纪中后期,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流入中国,中国的知识人逐步意识到言文分离所形成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进步的文化人开始注重提升民众智识,关注民众文化,并致力于民众启蒙、塑造新民。对于这一问题,中国文学研究者进行了大量讨论,尤其关注白话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具体论述在不同时期又赋予其新的意涵。近年来,很多研究者意识到,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除了新文学运动外,文艺大众化、通俗文艺运动以及延安文艺、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影响被忽略或弱化了,尤其是延安文艺,只是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研究者才开始更多以历史的眼光对其进行阐述与分析。这当然与文学史梳理中,逐步从注重重大政治历史事件,转向了以研究本体为中心的讨论,即对文学发展脉络、文学史料的梳理,更加注重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从对事件的分析到注重围绕问题、社团、报纸与刊物等为中心进行爬梳等等这些转向有一定关系。但在众多研究者中,更多会将文艺大众化、国民党的通俗文艺运动、延安文艺进行区隔。另外,由于学科区分、研究群体的知识差异,又出现了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同视域。张霖《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以下简称张著)一书突破了学科区隔与单一研究视域,同时也打破了一般的文学史时段划分,而是以赵树理为个案,在左翼文学兴起到1955年《说说唱唱》停刊这一时期内梳理了文学通俗化实践的理论前提、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初期的通俗化实践脉络。
张著采取文学史和新文化史结合的方法对1930—1955年文学通俗化实践(书中称为“通俗文艺改造运动”)进行阐释。这一阐释是在对“重写文学史”的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的。“重写文学史”反对以政治作为文学表述的唯一标准,注重文学的审美和文学性,这使得在文学史和文学评价中忽略了通俗文艺(含民间文艺)的价值,因为对于他们的分析不能脱离社会运动。所以在张著的分析中,赵树理及这一时期其他的通俗文艺创作不能仅仅从审美和文学性进行分析,而应将其视为社会改造运动,这样作者的阐述就不仅局限于对文学文本的分析,而是注重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挪用,在这样的脉络中勾勒和构建了1930—1955年文艺通俗化实践的图景。在张著所构建的这一图景中,特别引起我关注的是张霖所展示的新文学和民间文艺(书中更多表述为通俗文艺)的互相渗透、涵化,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文化互动,尤其是民众和民间文化的能动性。她的这些思考拓展和深化了文学史中对通俗文艺创作机制和文学价值的讨论,同时也为理解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范围、搜集整理等基本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新的学术生长点。
在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史的梳理中,离不开对大众化、通俗化的讨论。在很多讨论中,这两个词被混淆使用或者只是被关注其中之一,其变化的脉络并未得到梳理。但在张著中,首先就简要梳理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政治表述,如何从大众化、通俗化并行使用,到统一于通俗化之下,再进而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下进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改造的轨道。在这一发展轨辙中,张霖意识到了新文学与通俗文艺的互动。这一思想使得作者对于新文学的论述跳出了“启蒙”和新文学的成就阐述的窠臼,这也就避免了在对这一段文学史的阐释中对新文学与通俗文艺关系的单面相思考,而是关注到“通俗文艺改造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同意识形态相互交织、政治与文学相互裹挟的发展状态”①张霖:《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5页。以下参考此书的内容,仅随文标出页码。。这样,对于从文学大众化到通俗化、民族形式论争、民间文学形式运用的发展脉络就不能只在文学史中进行阐述,而要将其置于20世纪30至40年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去思考。从新文学运动之后,左翼文人、共产党知识分子都希望改变新文学运动中“只有几个教员学生(就是以前的士大夫阶级)做工作,这运动是浮面”②顾颉刚讲、钟敬文记:《圣贤文化与大众文化——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在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演讲》,《民俗》第五期,1928年4月17日。的局面,希冀文艺能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并在不断推进中思考到底是应该基于五四新文学还是中国传统的民间形式建立文艺新秩序。在彼此争论的过程中,政治精英的介入解决了通俗化实践的理论问题。张著通过对赵树理通俗化实践思想起源的分析,阐述了他所认为的通俗化就是可以充当“文化”和“大众”桥梁的文学样式。在着力于对赵树理通俗化样式选择的论述中,作者意识到了对民间文艺样式的熟悉,使赵树理能游刃有余地实现了创作形式的突破。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和作协在新的人民文艺认知上差异的开端。张著在论述中既超越了传统文学史领域对赵树理仅是借鉴民间文艺形式对民众进行宣传的意义,忽略了其创作从《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话》政治评价标准在根据地、解放区文学中介入的过程;同时也与民间文学视域的研究者不同。延安时期的民间文学因为知识人、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其存在样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大多民间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往往不将其视为研究对象,即使纳入其研究范畴者也未关注赵树理创作。我在对延安时期解放区民间文学的梳理中,关注到这一现象,但是更多注重分析他创作中对民间文学的叙事框架、叙事方式、人物形象的关注及接受对象、传播范围等,而没有注意到张著所言赵树理在通俗文艺实践中对不同民间文艺样式的尝试及其借鉴山西评书的独特创作样式“有韵话”。赵树理在编辑《中国人》报纸时,就关照到新文学、古典文献、通俗文学,其中通俗文学占一半以上,通俗文学中又涉及故事、笑话、有韵话、快板、鼓词、相声、小调、儿歌、民谣、童谣、偈语等,虽然这些表述并非严格意义上民间文学文类区分,与当下民间文学的文类划分也有出入,但恰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间文学、俗文学交织状况的体现,基本与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所提及的文类相近。另外,他也注重地方流传的民间文艺文类,比如“有韵话”,这也成为他创作中独特的样式。这些都标明,他更多是从创作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概念或者大众化理论出发。所以在通俗化实践中,采用或借鉴民间文艺形式推广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和抗日战争的并非赵树理一人,但只有他较为成功。他的创作,突破了从形式或内容借鉴民间文艺的模式,进而关注到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不同的传播和言说方式。以北京大学歌谣运动为开端的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从其兴起之时,就有研究者注意到其相较作家文学而言最大的改变是从“目治之学”转向“耳治之学”①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趋势》,《歌谣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7日。,而赵树理的创作就意识到了从文本向说唱的转化,他所创作的作品能看、能说、能唱,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说说唱唱》创办期间得到进一步落实。这触及了近年来民间文学领域所讨论的“口头传统”和“书写传统”,两者是不同的创作机制。所以赵树理借鉴民间文艺的创作,实现了“突破”,除了张著所言“从案头文学到说唱文学”“两种话语的互译”外,更多是他超越了同时代的人,意识到了通俗文艺只有实现了“口头”和“书面”两种文艺样式的结合才能实现“新文学”和“大众”的沟通,也才能实现新启蒙运动,同时也才能为文人和民众都接受,《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接受差异及在当时文学领域引起的讨论就是这一过程的反映。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张霖对《小二黑结婚》在民众多种艺术形式中的接受,尤其是《小二黑结婚》被改编为很多剧种,在山西武乡、河北涉县等多地演出,这也为其后面对《说说唱唱》和“两条胡同是是非非”的分析进行了铺垫,赵树理注重文学作品看、说、唱并行,这也是他认为的进入民众的最好路径。但是在张著的分析中,没有继续深入,这其实恰是民间文艺的独特之处。罗伯特·莱顿等在《中国山东省传统艺术的留存与复兴》中以山东的木版年画、鲁锦、玩具制作为个案,讨论了同一地域中民间文学艺术样式的交流及艺术主题的共享。①[英]罗伯特·莱顿(Robert Layton) 、[英]詹姆希德 · 德黑兰尼(Jamsid Tehrani) 等著:《中国山东省传统艺术的留存与复兴》,张彰译,《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2期。赵树理的创作是在实践中意识到了民间文艺的这一特殊性,如果沿着这个脉络进一步分析他创作中为何同一故事有小说、曲艺两个文本,及其后来将田间《赶车传》改编成鼓词《石不烂赶车》,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藉此可进一步丰富张著对新中国成立后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与作协、赵树理与丁玲之间的冲突、分歧的论述。
在张著中,对于通俗文艺实践的分析一改从前作家文学领域对文艺大众化中作家对民众的启蒙和改造、民间被动接受的思想,而是注意到民间文艺的反向影响及民众接受的能动性。解放区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的合作在新文化史研究中引起了关注,比如洪长泰《改造盲书匠——韩起祥和延安的说书运动》中所言,虽然知识分子在这次运动中充当了监督人、领导者的角色,但这次民间艺人与知识分子合作的实践,从政治和宣传上是成功的。②Changtai Hung, Reeducation a BIindStoryteller: HanQixi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Storytelling Campaign, Modern China,1993(4).张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在合作中,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民间艺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由于知识分子持启蒙思想和“眼光向下”的态度,更多看到其“思想中还存在着许多落后的东西”③林山:《盲艺人韩起祥》,钟敬文主编:《民间文艺新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1年,第161页。,忽略了民间艺人在表演中的创编和因民众接受度所做的自我调适,这就使得两者合作中会出现一些问题,在解放区这些问题还不明显,只是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抱怨和民间艺人接受上的偏差。但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在城市推广中,这一问题就凸显出来,也成为了通俗文艺改造的一个危机。通俗文艺长期以来形成的生产、接受、传播机制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民众在接受中的选择与自我调适,甚至一度催生出现“新瓶装旧酒”的局面。赵树理等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通俗文艺作家、艺人等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在寻找更加贴合的路径,但是从抗日根据地时期开始探寻的“多种趣味的平衡”(第113—131页)到这一时期被打破,文人注重作品的政治性和阶级立场,但是民众却有自己的文化习惯和意识,他们基于自己的接受能力消化解放区的文艺作品。这在以往的讨论中较少涉及,对于左翼作家内部通俗化实践的差异也关注度不高。张著的研究启迪了我们未来文学史书写中对文化群体异质性的关注。
最后特别需要提出的就是张著虽然是站在作家文学立场对1930—1955年通俗化改造运动进行书写与讨论,但是作者在论述中,旁及了民间文学的话题,甚至涵括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困扰民间文学的基本问题,如民间文学的范围、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等。在对赵树理通俗化实践的分析中,已经提及了民间文学样式和文类在赵树理编辑《中国人》和写作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中,专辟一节讨论民间艺人,论述了他们如何与知识分子合作,在合作中他们的交往对通俗文艺实践的影响。在对《说说唱唱》讨论中,也提及了对民间艺人的合作与改造。更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作者主要集中于从通俗文艺实践的理论储备到赵树理的具体实践,没有深入讨论民间文学的研究,但在她的讨论中恰恰弥补了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对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实践关注的缺失,在这一时期民间文学与通俗文艺、作家创作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合作产生的新秧歌、新说书等实践,以及赵树理、李季等运用民间文艺形式进行的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在新形势下的文艺推广、《说说唱唱》的文艺实践,这些讨论为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领域集中出现的民间文学范围和界限、民间文学主流论等争议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脉络,也为我们思考长期影响民间文学研究的十六字方针(“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提供了新的视角。赵树理从主持编辑《中国人》开始,就尝试了新故事的创作,这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故事及其讨论是否有关联?《说说唱唱》与停刊后创办的《民间文学》,从编委到编辑人员都有重合,他们之后在编辑《民间文学》时,是否承续了《说说唱唱》的方针或者有何影响?这些至今尚未有人专门研究。
当然,一本著作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每个人都有“椰壳碗”的边界①[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壳碗外的人生》,徐德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难免有些疏漏或讨论不及之处,如在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的合作中,比较武断地认为知识人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民间文艺的价值,其实从延安时期就开始接触民间文艺搜集和创作的贾芝、董均伦、江源等很多人都自此走上了民间文学研究的道路。张著对燕京大学开设民间文艺课的写作非常精彩,也为学界提供了新材料,但是以此作为“民间文学研究由人类学、民俗学的纯学术道路,引向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路径”(第196页)的判断还是过于简单和武断了。不过,正如张著序言中张均所说:“张霖对‘通俗化实践’的研究尚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②张霖:《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序”,第6页。,期待未来张霖能在此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深入对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及之后通俗化实践的讨论。
观察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新视角
杨天舒
[作者简介]杨天舒,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通俗文艺改造运动作为一个流布广泛、持续时间较长的文艺实践潮流,不但关联着20世纪中国文艺的思潮、论争、理论、观念等诸多文学史问题,而且也牵涉到启蒙运动、平民教育、政治动员、社会改造等诸多社会史议题,从文学史、思想史、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等多个学科多种角度,都有广泛的讨论空间。同时,由于这一议题的驳杂性和跨学科等特点,也给如何形成一种有效的整体性研究框架带来一定难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张霖老师的新著《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以赵树理在20世纪30-50年代的文学活动为线索,将通俗文艺改造运动中相当驳杂的问题勾连起来,从共产主义文艺运动的视角,考察1930-1955年间华北地区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整体历史进程。作者通过大量20世纪中国民众文化生活资料、文献、采访记录等,将研究从作家流派、文学论争、文学文本等层面,拓展到文学生产、传播和文化互动等领域,揭示了共产主义文艺运动内部各种文化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将从问题与方法、各章主要内容和问题的深化三个方面,对张霖老师的新著进行简要评述。
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开始面临研究范式的转型。从“革命”到“告别革命”,从“政治性”到“文学性”,从“现代性”到反思“现代性”并提出各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再到近年来注重文学生态的“大文学史”研究思路的提出,以及将文学重新置于“社会史视野”之下展开考察的诸多实践,逐渐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多元开放的文学史观,也大大拓展了学科研究的边界。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强调利用大量史料和文献还原历史细节、返回历史“现场”,呈现历史面貌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注意打通学科边界,力图在社会、文化、政治等更广阔的动态关联中,重新发现在单一的文学史维度中可能被遮蔽的问题。
在学科不断“跨界”和“扩容”的过程中,区别于精英文学的各种通俗文艺形态和文化现象开始被纳入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对于新旧、雅俗的相关议题,研究者尝试打破从前“界限分明”“分而述之”的研究框架,形成综合性的文化史视野。张霖老师对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研究,即是此研究思路下的一个重要成果。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梳理通俗文艺改造相关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30年代初期,左翼作家之间展开“文艺大众化”论争,通俗文艺的改造问题就被提及,“通俗化”与“大众化”两个概念在当时常常交织混用。另一方面,部分民间文化团体和国民党政府也不同程度地推动或参与了相关领域的文化实践。如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晏阳初、陶行知、顾颉刚等知识分子进行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等等。抗战爆发后,在政治动员的目标下,文艺的通俗化和通俗文艺改造运动较为广泛地展开,大量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不少作家进行了文艺通俗化创作实践。“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就是这一时代潮流的直接反映。这一时期,左翼作家内部展开“民族形式”的论争,并引发了关于“旧瓶”与“新酒”的持续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及各根据地的工农兵文艺实践,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创作转型之外,也包含各种群众性的文艺改造,影响较大的如改造说书人、秧歌剧运动、旧戏改革等。50年代初期,系统性的城市通俗文艺改造工作自上而下地展开,包括戏曲改革、改造旧艺人、整顿通俗读物等不同面向。其中围绕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和《说说唱唱》产生的一系列争议,背后是国家、文化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多边文化博弈。
通过以上对于20世纪30-50年代相关问题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通俗文艺改造运动实际上常常与文艺通俗化的文学思潮交织在一起。前者侧重民间文艺、通俗文艺形态的现代改造,后者侧重于精英文学在内容与形式上的通俗化改造。在研究领域,文艺通俗化的相关研究,长期以来有着相对固定的叙述模式,关于启蒙与救亡、新文学本位与民间文学本位等二元对立的研究思路较为常见。相比之下,通俗文艺改造的相关研究,近年来随着社会史视野的引入,在戏曲改革、说书人改造、新故事运动、群众文艺与情感实践等方面,产生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不过,这些成果一般聚焦特定的研究专题,整体性文化史视角下的通俗文艺改造运动,仍未得到更充分的讨论。
那么,如何将文艺的通俗化和通俗文艺的改造这两条动态交织的线索同时纳入研究视野,并获得一种整体性研究视角?如何在研究中跳出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立场的局限,同时也避免民间文艺本位主义的褊狭,形成交互性的考察空间?本书选择作家赵树理作为线索性人物和主要考察视角,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赵树理是中国共产党方面通俗文艺改造的倡导者和最重要的实践者之一,以他为线索,可以通过“具体而微”的个案模型,为这一内容驳杂的文学运动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历史脉络。更重要的是,赵树理主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化实践,几乎都同时交织在文艺的通俗化和通俗文艺的改造这两条线索中。作为一种文化实践,通俗文艺改造运动并非单纯同质的封闭体系。在这一复杂动态的过程中,赵树理兼具农民、民间文艺家、左翼新文学作家、共产党的文化干部等多重身份,以他作为观照视角,有利于打开各种文化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呈现新文艺、通俗文艺和政治宣传文艺等不同文艺形态在共产主义文艺系统内互相竞争的复杂样态。同时,以赵树理为结构线索,也有助于将有关大众化的讨论、“民族形式”的论争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理论辨析的问题推置于研究背景中,避免在既有的叙述框架中过多缠绕。
除了整体性研究框架方面的特色,本书在研究的细部也颇有个性和见解。例如,对于赵树理选择通俗文化道路的原因,此前的研究或者强调他的农民出身与农民趣味,或者强调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与启蒙诉求,或者干脆将二者作为赵树理的一体两面,对这两种颇有内在冲突的原因背后的症候,则很少深究。本书突破了传统研究中的泛泛之谈,在史料细读的基础上,结合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实践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对赵树理早期思想资源进行探源。在社会史视野之下,20世纪中国的乡土文化实践,与多种“社会改造”思潮密切相关。歌谣运动、平民教育、乡村建设、土还主义等诸多讨论与实践,构成其重要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氛围,对通俗文艺改造实践的伦理意涵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赵树理通俗化实践道路的选择中,增加久被学术界所忽视的陶行知和陈伯达之影响这一环,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则更加清晰。作者由此指出,他对通俗文艺形式的偏爱和对农民娱乐趣味的重视,并不是他出身农民的褊狭趣味,而是作为深受陶行知影响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从事下层社会改造过程中对工农大众的文化生活现实所进行的理性选择,这一结论也更具有说服力和内在的自恰性。
此外,本书对于“赵树理方向”的文学史内涵的重新阐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各派系文化干部、作家和民众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等分析,也相当精彩,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采用文学史与新文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文史结合、多边互动”的研究特色。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其研究方法来自于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关于文学与历史具有亲缘性的学术构想,并受到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本书主要尝试将新文化史中有关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学史研究,突出新文学和通俗文艺在新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区通俗文艺改造的相关章节中,如旧艺人对政治改造的态度,市民文化趣味对革命文艺政治性的消解与挪用、变形等研究,都体现了政治、传播媒介和民众社会生活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较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研究思路,也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种视角。
本书“多边互动”的研究思路,则能看出美国汉学家洪长泰(Chang-tai Hung)的影响。洪长泰在《战争与通俗文化》《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这两本专著中,对于战争与通俗文化之关系的研究、政治文化与民众反应的研究,运用了大量文学、绘画、新闻、图像、建筑、舞蹈等跨学科的历史材料,对历史进行动态的描述。这种多边动态的历史研究方法,也构成本书研究的总体性思路。在动态多边互动关系中勾勒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基本面貌,避免了论述中的单一立场或价值取向的盲区,带来整体性研究视野的突破。
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可以看出作者受洪子诚老师当代文学史观的影响,将“通俗文艺改造”视作一种社会文化实践,一种可交互的社会行为,强调在这一文学史现象的研究中,包括写作、评价、筛选、传播、接受和再生产等实践层面的丰富性,比文本层面的艺术性研究更有价值,进而在反思“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基础上,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视野的局限,批评精英文化立场对文学审美标准的固执。
同时,本书也尽量避免对西方理论的直接套用,立足于中国问题和本土经验,继承中国“文史结合”的学术传统,秉持严谨、平实的学术态度。在研究中,每当遇到由于史料的缺失或散佚而不能得出确凿结论时,作者都能以严谨的态度进行说明。例如关于赵树理的通俗化创作思想是否受到大后方通俗文艺运动的直接影响的问题,因现有材料不足,作者只谨慎地提出二者思路的接近,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以论代史的研究倾向。在史料的使用方面,作者注意到以往研究大多更关注知识分子作家和政党对文学运动的影响,较少注意民众在文艺运动中的态度、要求和反作用。基于以往研究中史料采选的文化精英立场,作者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包括原始期刊、回忆录、日记、见闻录、政策文件、地方志等,还访问了参与或了解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有关人士与研究学者,包括赵树理研究专家黄修己和李士德、《说说唱唱》的编辑邓友梅、赵树理故友邢野的女儿邢小群等,通过这些工作掌握了大量关涉底层民众与旧艺人的一手材料,使研究视野更加中正、客观。
本书正文部分共分五章,以历时性的时间线索,勾勒了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其中上半部分侧重新文学通俗化道路的探讨和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下半部分侧重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通俗文艺改造过程和围绕《说说唱唱》产生的争议。
第一章通俗文艺改造的理论准备,将文艺通俗化的相关思潮和论争置于历史线索中作为理论背景,重点探讨赵树理通俗化创作的思想资源。在本章中,作者以“文艺大众化”的思潮作为历史起点,指出无论是20世纪初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民众并进行思想启蒙的大众化运动,还是30年代左翼文化人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动员的大众化运动,都仍局限在城市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之中,并没有对大多数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社会产生影响。由此,一部分左翼文化人推动了“五四”新文学由以文化精英为主导的方向转向以民众为主导的共产主义文艺运动方向。正是在文化权力的让渡和转向过程中,关涉文艺的通俗化问题的“旧瓶装新酒”“民族形式”等重要论争渐次登场。随着政治精英的强势介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其提供了系统的政治纲领和实践理论,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由此在延安及各根据地蓬勃展开。
在本章的第二部分,作者在辨析赵树理30年代大众化文学主张的基础上,结合赵树理早期的乡村教师经历和对陶行知教育救国理论的践行,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塑造了他“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①张霖:《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第71页。,成为他身份意识和文化选择的思想源头之一;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倡导的“新启蒙运动”,站在民族文化复兴的立场上对“五四”启蒙运动进行反思,则为赵树理提供了民族主义立场和新文学民族化实践的早期理论资源。
第二章根据地、解放区的通俗文艺改造运动,选取作家赵树理和改造说书人运动两个个案,讨论赵树理的通俗化形式实验及对新文学史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刘志仁、李卜、韩起祥等民间艺人在通俗文艺改造运动中与根据地知识分子合作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习惯从小说《有个人》(1933)或《盘龙峪》(1935)开始讨论赵树理文学创作的通俗化转向。本书作者则将讨论提前至《打卦歌》(1931)和《歌生》(1932)两篇诗歌。这两篇诗歌分别以游荡的“卜士”和流浪的“说书人”为题材,形式上融合了新旧诗体和各种民间曲艺,带有明显的通俗化和底层色彩。作者认为,赵树理在《打卦歌》“附言”中说“我所以要拿旧体格来写,不过是想试试难易,并没有缩回中世纪去的野心”②赵树理:《打卦歌》,《赵树理全集》第1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3页。,正说明他已经尝试放弃知识分子的“新文艺腔”,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学的通俗化实践。在编辑《中国人》报时期,赵树理又进行了丰富的文体类型实践,其中著名的“有韵话”和“有韵小剧”等文体,正是受到流行于山西一代的有韵评书和鼓词的影响创制而成。作者认为,这一实践有助于新文学由案头走向说唱,并实现了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不同话语体系的互译。
基于这样的创作准备,《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两篇小说,实现了较为成熟的新文学通俗化风格。作者进一步梳理了两篇小说从文本实践到文化传播实践的过程,指出由于政治标准的介入,使得后者获得了党的文化干部和文化精英们更多的认可,赵树理的通俗化实践由此被赋予了阶级启蒙和政治动员的社会价值。在重新阐释“赵树理方向”的文学史内涵时,作者认为,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体现了对农民、知识分子、共产党的文化干部三方面文化取向的准确把握,赵树理方向的成功,就在于“他找到了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思想性、农民读者的审美习惯和共产党的文化干部的政治诉求三者之间的平衡点”。①张霖:《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第130页。
在本章中,作者还提供了观察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关系的一个新视角。民间艺人作为农村文化的媒介,在沟通新文学与工农大众的文化隔阂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作者列举了在《讲话》之后大规模学习民间文艺的运动中,刘志仁、李卜等民间艺人或用农民熟悉的传统曲调表演新剧,或在剧团中担任唱功和做功指导,利用社火、秧歌等民间形式帮助知识分子们将新文艺形式通俗化。在说书人改造运动中,作者以韩起祥和他的《刘巧团圆》为例,分析通过举办培训班和发动知识分子与说书人合作,不断记录和修正其口头创作,从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其进行监督和改造。作者认为,这意味着通俗文艺改造运动已经从向民间文化学习而逐渐走向对民间文化的改造。
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通俗文艺改造运动,主要讨论城市革命文艺的生产和传播。为了争夺北京天桥的旧文艺市场,赵树理等人发起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作为一个民间文化团体,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以团结大量新旧艺人、进行统战和思想改造为目的,展开理论研究、文学创作、文艺培训和书报编辑等工作,在改造城市通俗文艺的同时,普及和推广新通俗文艺。《说说唱唱》的创刊,代表了解放区通俗文艺改造运动和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双重经验,开始向新北京乃至全国城市推广,也是工农兵文艺与旧的城市文化的一场角力。因此,其创刊得到了高层文化领导的重视,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繁荣,发表了赵树理的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说《登记》,陈登科的《活人塘》等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有了新通俗文艺创作之后,如何开辟城市传播渠道,向社会普及?作者列举了四种主要推广方式:通过组织戏曲艺人讲习班、盲艺人讲习班,对艺人进行思想改造和新通俗文艺倡导;通过电台广播和大众游艺社,面向社会播讲和演出;通过赵树理与燕京大学教授林庚合授民间文艺课,向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推广民间文艺的改造成果;通过与宝文堂等旧书店合作,推广发行唱本、连环画等各种新通俗文艺。
第四章通俗文艺改造运动中的派别纷争,主要讨论50年代初期,围绕通俗文艺改造产生的新文学阵营内部的矛盾与交锋。在本章中,作者追溯40年代赵树理所在的太行文艺界,以徐懋庸和蒋弼等人为代表、以《华北文艺》为阵地的“新派”,同以李伯钊和杨献珍等人为代表、以《抗战生活》为阵地的“旧派”之争。双方在民族形式的论争和是否应排演大戏等问题上,早有观念上的龃龉,自赵树理等人公开提倡文艺通俗化之后,矛盾加剧。作者认为,1942年黎城县的封建会道门离卦道挑动民众冲击抗日民主政府的暴乱活动,促使边区军政领导认识到深入农村、了解农民、以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启蒙和教化的重要性。但是,在边区文联为此举行的文化人座谈会上,新旧两派知识分子仍然就如何大众化的问题展开激烈的正面交锋。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小二黑结婚》的出版,赵树理的创作和通俗化实践始终没有得到“新派”知识分子的认可。随着《讲话》传播至太行文艺界,赵树理为代表的“旧派”开始压过“新派”,夺得话语权。不久,徐懋庸调离,“赵树理方向”确立,新旧两派的“门户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随着50年代赵树理获得的文化权力的增加,他再一次不可避免地卷入北京文艺界复杂的是非之中。本书这一部分,以相当细腻的史料和开阔的论述视野,分析了以丁玲为代表、坐落于东总布胡同的中国作协文化人群体,与以赵树理为代表、坐落于西总布胡同的工人出版社文化人群体之间的三次明争暗斗。最初,赵树理以不登大雅之堂的鼓词形式,将田间的新民歌体叙事长诗《赶车传》改写成《石不烂赶车》,取得明显超越《赶车传》的艺术成就,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演播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令两边产生嫌隙。随后,丁玲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以“面包和窝头”之喻,对赵树理等人的通俗文化实践表示不满,进一步激化了矛盾,间接造成《说说唱唱》与《北京文艺》的合并,包括赵树理本人在内的编辑部不断受到批评与打压。在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提名之争中,官方推荐的作品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但最终获奖的是另找渠道推荐到苏联方面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使双方矛盾达到顶峰。作者强调,“东、西总布胡同矛盾的实质,反映了新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不同派别间对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的争夺。”①张霖:《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第253页。“土包子”文艺和“洋学生”文艺之争,赵树理与丁玲等文化人之争,周扬与胡乔木等文化领导之争,无不以复杂和多边的样态深深交织在一起。
第五章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危机,主要讨论在文化精英的合力之下,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落潮。在本章中,作者认为带有明显市民趣味的城市通俗文艺,同工农兵文艺标准和正统的新文学诉求之间确有抵牾。市民们表面上热情参与到新的文化运动中,却以各种隐晦的方式进行挪用、改写或抵抗,包括对移植到城市的解放区文艺的猎奇化接受,在革命宣传品中夹杂色情贴画等等。这种市民趣味中的色情、暴力、封建等因素和政治觉悟的低下,遭到精英文化人的严厉批判与监督。这也使得赵树理等人相对温和的主要依靠民间力量进行的文化改造,被认为是一种妥协和错误。由此,带来对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不断升级的批判、整改、合并和最终停刊,诸多编辑和文化工作者也被卷入其中,昭示着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落潮,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严格和激进的文化管理。
本书的研究始于作者博士期间的学术兴趣和博士论文选题。部分成果在发表时曾引起广泛的关注。笔者注意到,书中也有不少近年新发表的文献资料,经过多年学术积累与不断补充,成书后更见厚重与平实。如果说在研究中还有未尽之意,在笔者看来,以《说说唱唱》的停刊作为当代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落潮,似乎仍可进一步斟酌。
一方面,通俗文艺改造的实践涉及内容非常驳杂而广泛,在50—60年代也有相当成功的实践。以新评书广播为例,早在1949年9月,评书名家连阔如就开始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文艺节目”中演播评书《红军万里长征渡乌江天险》。②参见洪霞:《当代曲艺声像传播的流变探析》,《四川戏剧》,2016年第12期。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地人民广播电台的发展,新评书名家辈出,非常繁荣。在通俗文艺改造运动中,传统评书艺人纷纷开始播讲新评书,主要包括新编历史评书、新创作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评书和改变自当代文学作品的评书三种类型。在50-60年代产生较大影响的新评书广播,主要有1952年唐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袁阔成播讲的《吕梁英雄传》,1957年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杨田荣播讲的《三里湾》,1963年袁阔成播讲的《烈火金刚》《林海雪原》《赤胆忠心》《野火春风斗古城》,60年代初中央电台录制播出的李鑫荃播讲的《红岩》《平原枪声》,以及连阔如播讲的《夜渡乌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智取娄山关》等原创新评书。①参见艾红红、张素艳:《广播评书的历史回顾与特色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第10期。[作者简介]李超宇,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50—60年代的新评书收听热潮,是新的文艺传播媒介与传统通俗文艺改造相结合的成功范例,新的文艺介质在传统通俗文艺改造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以及有固定播讲时间、对受众作息规律有一定要求的评书播讲活动与城市新工人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新评书播讲在城市与农村的不同实践形态等,都是在文艺通俗化改造的议题下,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来看,《说说唱唱》的终刊也并非其通俗文艺改造实践的终点。被调到《曲艺》杂志后的赵树理,仍进行了一系列的文艺通俗化实践,除了在曲艺方面发表了不少讲话、文章之外,还在1958年创作了评书《灵泉洞》,在1961年改编了传统戏曲上党梆子《三关排宴》。1964年,赵树理受当时在南方蓬勃发展的“新故事”活动鼓舞,创作发表了新故事《卖烟叶》。在淡出东西总布胡同的是是非非之后,赵树理结束了集体性的通俗文艺改造活动,其个人的通俗文化实践也呈现出新的特点。赵树理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化实践有何新的特点?是否围绕《曲艺》和旧戏改革等形成了新的文化实践圈层?这些问题都是笔者较为关心的研究面向。
此外,通过本书的阅读,笔者对通俗化与大众化两种文艺实践的互动关系,产生较为浓厚的兴趣。以1938年开始兴起于延安的文艺小组活动为例,当时兴起了在工厂、部队和农村建立文艺通讯网、成立文艺小组和文艺社的活动,吸收喜欢文艺、有一定写作才能的工农兵大众加入文艺组织,并给与必要的写作教育与训练。这一群众文艺活动,由延安“文抗”直接领导,是新文学精英文化人领导下的一次文艺大众化运动。事实上,这种由文化精英指导或带动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仍有所延续。笔者设想,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上,将精英文化人倡导的文艺大众化实践引入研究视野,同赵树理等人所倡导的文艺通俗化实践形成一种多边对照,也许可以避免由文化精英立场直接“对阵”文艺通俗化运动。这样,是否可以形成一种更有意思也更具对话性的研究框架?当然,如本书作者所说,对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研究还有相当广阔的研究空间。一种研究设想是否成立,还有待于今后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
“调皮鬼”与“正经人”
李超宇
在近些年来的“赵树理研究热”中,张霖的新著《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可谓别具一格。她没有选择最“热门”也最容易上手的小说研究,而是剑走偏锋,选择了较少被关注的通俗文艺改造运动,从而使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填补空白的意义。如“新启蒙运动”与陶行知教育思想对赵树理的影响,触及了赵树理本人明确提及但一直鲜有研究成果的思想资源,从而更深入更全面地印证并复杂化了周扬的著名论断:“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①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编:《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上),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87页。再如对《说说唱唱》从创刊到终刊历程的研究,不仅填补了一份重要通俗刊物的研究空白,更由此牵扯出“两条胡同”的是是非非,折射出新中国初期文坛的权力格局和“通俗”在其中的位置,是典型的“小切口做出大文章”。而当张霖从通俗文艺改造的整体性视野再回看赵树理的小说时,又照亮了赵树理小说中一些较少被关注的部分,尤其是赵树理小说平衡了农民、文化人和共产党干部三种趣味的结论,可以说是张霖对赵树理研究的一大推进。
这三种趣味在近年来受到较多研究者的关注,比如钱理群在《岁月沧桑》一书中就采用了“党员—农民—自我主体(知识分子)”②参见钱理群:《岁月沧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80页。的架构来分析赵树理,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果说钱理群的研究更多侧重于赵树理的“知识分子”身份,指向的是赵树理“这一个”;那么张霖的研究则从赵树理的“农民”身份出发,最终指向了与之相对应的农民趣味,指向了更为广阔的“民间”。张霖在书中明确表示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以下简称《民间的浮沉》)对本书有着“重大启发”:“把‘民间’作为以国家权力为支撑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西方外来文化形态之外的文化形态,引入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③张霖:《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第10页。为“民间”正名也成为张霖写作本书时的一个自觉追求:“站在民众的角度,重新考察20世纪文学,特别是共产主义文艺运动,以期展现以往研究所忽略的民众意志与民众参与的历史因素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④同上,第5页。应该说,本书部分地实现了这样的追求,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新材料和较少被研究者注意的旧材料,尽力勾勒出了一幅民间文化生活的图景,揭示了民间的思想、趣味与悲欢。由于有扎实的史料作为支撑,这幅图景无疑是真实可信的,但能否认定它就是历史的全貌,仍然需要做一些辨析。
一
回到对本书有重大影响的《民间的浮沉》一文,它从诞生之初就饱受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一段恰是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赵树理本想写《李有才板话》的续编,结果却用极其曲折的笔调写出了欲哭无泪的《锻炼锻炼》。……他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揭露的仍然是农村基层干部中的‘坏人’,……像‘小腿疼’、‘吃不饱’这些可怜的农村妇女形象,即使用丑化的白粉涂在她们脸上,仍然挡不住读者对她们真实遭遇的同情。这篇小说从文本表面上看,等于是把西门庆写成英雄,把武大郎写成自私者,但从文本潜在的话语里,真实地流露了民间艺人赵树理悲愤的心理。”⑤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贺桂梅编著:《“50—7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49—50页。明眼人都能看出,陈思和把“小腿疼”“吃不饱”当作了“民间”的代表,但“民间”显然不能一概而论。抛却小说叙述者的倾向,甚至抛却被陈思和视为“坏人”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态度,只看小说中群众的态度,就可以发现——早在“大跃进”之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小腿疼”和“吃不饱”就已经为多数群众所不齿,因为她俩的所作所为早已违背了乡村基本的伦理道德。小说开头专门强调:“倒不是因为杨小四是副主任,也不是因为他编得顺溜写得整齐才引得大家这样注意,最引人注意的是他批评的两个主要对象是‘争先社’的两个有名人物——一个外号叫‘小腿疼’,那一个外号叫‘吃不饱’。”①赵树理:《“锻炼锻炼”》,《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21页。这说明群众并没有盲目地顺从政治权威,他们对“小腿疼”和“吃不饱”的不满完全源自自己的判断。那么,这些对两位“名人”不满的群众算不算“民间”呢?
或许是由于受到陈思和论述的影响,张霖在个别章节对“民间”的理解也多少带上了一点“一概而论”的色彩。比如在第五章第二节中,张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市民在适应工农兵文艺标准的同时,也在为他们自己的文化生活积极寻找着变通的渠道。”②张霖:《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第259页。“更客观地说,他们是在以阳奉阴违的办法,在表面的服从中,对工农兵文艺的政治训导意图进行着局部的消解和本能的拒绝。”③同上,第262页。而张霖所举的例子,大多是书报商人在宣传品中插入暴力、色情的图画和文字说明,给月份牌女工的指甲上涂上蔻丹等等,似乎“市民”的趣味只有这些。虽然在经典名著和当时不少文艺工作者的口中,“市民”确实不是什么好词,它往往成为“小市民”“市侩”的同义语。但在对具体的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中,我们不应带着同样的感情色彩去看待“市民”,“市民”应该是一个不含褒贬的中性概念。与《“锻炼锻炼”》中的农民同理,“市民”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上述书商的做法是否能够代表所有市民的趣味呢?事实上,当时一些关于“市民”的资料和说法呈现出了另外一种情形——根据王秀涛在《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一书中的研究,新中国对于反动、淫秽、荒诞等在道德上有缺陷和危害的图书的处理“获得了很多人的理解和支持”④王秀涛:《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34页。,这“很多人”自然大多是市民。王秀涛的书中还引用了一句摊贩的话:“坏书像毒药,好书是补药,天下父母都爱子女,不能把毒药给别人吃。”⑤参见《1955—1956年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工作及对私营摊捕的安排改造》,《上海图书馆事业志》,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6年,第501页。可见,即使是以追求利润为主的书商,也并不可以一概而论。
本书的主角赵树理也早已发现了“民间不能一概而论”的情况:“摸住读者的喜好了,还须进一步研究大家所喜好的东西,看看其中哪些说法是高明的,应该学习的,哪些是俗气的、油滑的、调皮鬼喜好而正经人厌恶的,学不得的,把值得学习的办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一套写法。”⑥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赵树理全集》第6卷,第166页。这段话虽然主要是在说明作者对“民间”的取舍,但也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民间”至少要分为“调皮鬼”和“正经人”两类。陈思和与张霖的洞见在于关注到了“调皮鬼”这个群体,但进一步把“调皮鬼”视为“民间”整体就未免对“正经人”太不公平了。
相对于城市而言,张霖在论及农村接受者时基本上兼顾了“正经人”和“调皮鬼”这两个群体,既看到了农民愚昧落后,需要改造的一面;也看到了农民勤劳朴实、敦厚善良、有正义感的一面,后者恰是农民接受赵树理作品的心理基础。张霖敏锐地发现:与知识分子更喜欢的《李有才板话》相比,农民更喜爱《小二黑结婚》。这一事实同样展现出了“精英”与“民间”的差异,展现了“民间”自己的文化选择,但这里的“民间”趣味显然是“正经人”的趣味,比张霖描述的市民趣味要健康得多。“正经人”的存在对于张霖的“民间”概念是一个有力的补充,不仅兼顾了更多的接受人群,还使得“民间”不再简单地作为“官方”“精英”的对立项而存在。在张霖论述赵树理平衡三种趣味的过程中,我们明显感到农民、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干部之间几乎没有了冲突和对抗,他们完全可以相互影响,通力合作,共同向着一个积极正面的目标迈进。这是赵树理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也是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最为理想的状态。
二
该书的论述随着《说说唱唱》的停刊而急遽结束,赵树理与作为“运动”的通俗文艺改造之间的关联确实可以在1955年画上句号,但赵树理对通俗文艺改造的困惑与思考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些困惑与思考甚至有着与本书同等重要的意义,目前张霖对1955年到1970年的赵树理的论述还是略显仓促了。比如1962年,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指出:“物资保证没有,只凭思想教育是不行的”①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6卷,第78页。。这就道出了处于文艺范畴之外,但又对通俗文艺改造效果,特别是读者接受效果具有重大影响的范畴——物质基础,目前本书对这一范畴的讨论还略显不够。再如张霖举出的由赵树理主编的《曲艺》杂志,同样大有文章可做——1963年刊登在《曲艺》第3期上的一篇题为《农村听众对广播曲艺节目的反映》的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喜欢听故事性强,结构严谨,人物个性突出,爱憎分明,语言通俗易懂的曲艺节目。这样的表述与赵树理的观念非常相近——如1957年,赵树理在谈论《花好月圆》时就说过:“农民喜欢看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作品”②赵树理:《谈〈花好月圆〉》,《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1页。。这表明,不仅赵树理仍然在自己主持的园地坚守着通俗文艺改造的理想,而且通俗文艺本身也获得了广播、电影等新的传播媒介,似不能被一笔带过。除了赵树理和他的朋友们之外,1950—1960年代从事通俗文艺改造的文艺工作者还有很多。张霖在结尾略显武断地指出:“通俗文艺改造运动再也没有能够从危机中走出,在精英的合力之下,这一文学创作潮流悄无声息地中止了。”③张霖:《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第295页。似乎《说说唱唱》的停刊就标志了通俗文艺的终结,但这样就无法解释在1955年以后不断涌现的“革命通俗小说”:《林海雪原》(1957)、《敌后武工队》(1958)、《烈火金钢》(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这类作品及其不同形式的改编版本都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当时的多数“精英”也从不吝惜他们对这类小说的由衷赞美,如侯金镜为《林海雪原》写的评论题目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文章充分肯定了这类作品“具有民族风格的某些特点,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有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风貌,它们的普及性也很大,读者面更广,能够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④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节录)——读〈林海雪原〉》,洪子诚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7页。这说明“精英”对于“通俗文艺”并非总是起着阻挠作用,相反,在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以极大的热情去宣传、推介这类作品的。根据姚丹等的研究,恰恰是“精英”与“民间”的合力铸就了这些通俗文艺的经典之作。⑤参见姚丹《“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由此看来,张霖对于“精英”的理解也略显单一了。事实上,从张霖讨论的1930年代开始,很多的“精英”就不能简单地作为“民众”的对立面进行讨论了,特别是从“左联”到延安再到新中国的大部分文艺工作者,都怀揣着一颗“为工农兵服务”的心,只是服务的数量有多有少,方式方法有差异而已。因此,我们在看到他们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偶尔泛起的精英观念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每一个人在深入生活、接近民众、融入民众方面的努力;看到在改造民间艺人的同时,精英们向民间艺人的虚心求教和对自身创作的痛彻反思;看到精英为民间文艺的抢救、搜集、整理所付出的心血;看到他们在一系列的实践中日渐坚定的群众观点和人民立场……只有这样,我们通俗文艺改造的图景才能更加动态,更加完整,我们也才能更好地把握赵树理的工作在全局中的位置、意义与独特性。
正如张霖在“结语”与“后记”中所说:“对这一文学实践的研究才刚刚展开,它的研究空间还相当广阔。”①张霖:《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第303页。“在这个领域中我们仍然有很多更细致、更艰苦的工作有待完成。”②同上,第323—324页。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张霖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展了新的疆域,也很愿意与张霖一起继续完成这些更细致、更艰苦的工作。
边缘与互动
张 霖
[作者简介]张霖,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如果说,拙作《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有什么值得读者阅读的理由的话,我想说,它诚实地记录了一个初学者独立研究课题的笨拙过程。这本小书完成于2005年,是以我的博士论文《赵树理与新文学的通俗化实践》为基础,略加修改完成的。它从成书到出版,一共花费了15年的时间,如此缓慢的速度与“十年磨一剑”的雄心毫无关系,不过是我求学心路的迷惘和个人命运的曲折使然。好在,漫长的拖延反而让我获得了向更多良师益友求教的契机。直到2020年,承蒙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慷慨赞助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的错爱,拙作幸运地得以出版。它又意外地得到中国与比较研究学会(CCSA)的注意,并约请到三位资深同仁慷慨惠赐长篇书评。我衷心地感谢三位老师抽出宝贵时间阅读拙作,并做出如此深入的评论。限于学力,我只能试着对三篇文章中的部分问题做出一点力所能及的回应。
一、选题的发现
首先,非常感谢三篇书评对拙作选题的肯定,其中两位书评人都注意到拙作打破了不同学科的研究壁垒,在方法上做了一些跨学科的尝试。“跨界”和“扩容”似乎是近年来学界的研究潮流,但拙作的“跨界”和“扩容”不是我的主动选择,而是选题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因此,我想先从拙作选题的发现入手,从方法论角度谈谈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粗浅体会,兼及回应书评中有关拙作与赵树理研究之关系的问题。①一位书评人提到,拙作对赵树理对三种趣味的平衡受到钱理群《岁月沧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的影响,而钱理群的观点来自李国华的博士论文《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文学政治》(上海:上海书店,2016年)。拙作中有关“赵树理方向:多种文化趣味的平衡”的内容来自我的博士论文。本人的博士学位于2005年取得。相关论文先后在2006—2009年在《文学评论》等处发表。据我所知,李国华是2012年取得博士学位的。李国华的作品出版后,我曾拜读过他的大作。他的研究与拙作观点并无交叉,我没有引用上述成果中的任何观点。但为方便后来的研究者,我在绪论和参考书目中提到了李国华的著作。特此说明。
(一)地方性与赵树理研究
拙作的写作开始于2002年,当时我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我计划研究赵树理,主要是希望找到赵树理文学成功之路的秘钥。特别幸运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大家黄修己仍然给博士授课。在有关赵树理的讨论课中,我向老师请教,赵树理为什么要嘲笑“三仙姑”而同情“小腿疼”“吃不饱”,并怀疑赵树理是一个有小农意识和男权思想的作家。黄老师既没有批评我的观点,也没有直接给出他的看法,只是分享了自己去山西实地采访的经验。②参见黄修己:《我说山西好风光》,《上海文学》,2005年第10期。他发现,山西的山区地少贫穷,男性结婚不易,惧内的情况很常见,甚至依然存在一女多夫的“拉边套”的婚俗;在农业生产中,女性不下地劳动是常态,在特殊年代,夹带公粮作物算不上什么罪过,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民自保的方法。如果不了解这些当地的情况,把《锻炼锻炼》里的“懒”“偷”“泼”和三仙姑的“老来俏”按照普通的道德标准加以判断,就无从把握农民的生存处境和情感体验,也难以理解赵树理为农民代言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追求。
黄老师给我的启发并没有马上让我明白田野考察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后来,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我读到了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对于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强调,他指出,人类学要从“当地人”的角度来了解事物,而不应该作为研究者,将外来偏见加诸当地人身上③格尔茨的原话是,“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9页。;之后,我又读到高王凌的《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对山西农民的怠工和偷盗行为的历史研究,我才比较清晰地意识到从“地方性”出发理解赵树理作品的重要性。
“地方性”,正是赵树理与其他新文学作家的根本区别。在他的成长环境、个人爱好和文学创作中,民间文艺占据非常大的比重。他最受读者欢迎的,也是那些最富有地方性色彩的、类似于民间文学风格的作品。因此,要回答赵树理文学成功的秘密,不能固守现代文学研究中潜藏的“世界性”眼光,对赵树理和他的作品进行想当然的预判。经过反复考量,我决定将考察重点从小说文本转向赵树理研究的边缘材料——他所写的大量说唱作品。④在2006年赵树理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获得赵树理研究会的邀请,参观了赵树理故乡沁水,看到了“八音会”、上党梆子和说书艺人的表演,实地感受到山西民间艺术的生命力,在田野中印证了我对赵树理与民间文学关系的判断。
(二)将民间文学资料引入现代文学研究
为研究赵树理的说唱作品,我不得不跃出现代文学的资料范围,去翻阅民间文学资料。在中山大学丰富的民俗学藏书中,我意外地发现了由赵树理主编的全国性大型通俗文艺月刊《说说唱唱》(1950—1955,共63期)。相比民俗学研究者,我翻看《说说唱唱》有一个优势,当时我已经看熟了赵树理的资料,就对杂志的编辑信息比较敏感。特别是它的创编团队的人员构成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在20世纪50年代,《说说唱唱》没给人壁垒分明的印象,反而是个新旧文化人、新旧文学作品的大杂烩。我很好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杂志?特别是杂志的编辑者署名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这是个什么组织?赵树理担任《说说唱唱》主编又辞去职务的风波是怎样的?这本销路很好的杂志为什么忽然终刊?这些问题在2002年左右尚未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连赵树理研究专家都语焉不详,但是民间文学的基础辞书就帮我打捞到不少重要的研究线索。经过一番艰苦的文献追踪,我基本锁定了选题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一个作家”(赵树理)、“一个杂志”(《说说唱唱》)、“一个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
(三)历史坐标中的个案研究
研究对象确立之后,我最初只计划完成一个文学期刊、文学社团研究。我以为研究的边界非常清晰,并不需要“跨学科”的方法。不过,当我真正进入这个课题之后,我发现研究对象具有特殊性。《说说唱唱》刊登的通俗文学作品多采用口传形式,内容多配合当时的政治时事,且全部出自某个作家(或业余作者)之手,而不是从民间集体创作中搜集而来。因此,这些通俗作品能否纳入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围尚存在争议,更不要说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了。在我做博士论文的时期,“重写文学史”的研究思路依然占据主流。我要么从“文学性”角度勉强论述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要么从“现代性”角度质疑它们的思想内涵,要么从“政治性”角度阐释它们的革命意义。不过,这三种现成的思路都不适合我的研究对象,非但不能揭示,反而遮蔽了作品中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在我犹豫是否要放弃这个课题的时候,法国年鉴学派有关“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的思考引起了我的注意。比如,布罗代尔就指出,对综合体的研究“必然不能脱离它的历史发展背景,它也许根源于遥远的过去”①[法]布罗代尔:《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848页。。我意识到,只有不陷入琐碎的、孤立的、事件的研究,才能在历史网络中打开材料更丰富的阐释空间。因此,必须把我要研究的“一个作家、一个杂志、一个组织”纳入一个相对长的历史背景中,使“个案”成为能够囊括历史全貌的具体而微的“模型”或“胚胎”。
循着历史学的研究思路,通过爬梳20世纪的启蒙思想史、民俗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一条有关“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历史线索在我面前逐渐呈现出来。自20世纪以降,通俗文艺改造的实践一直伴随着知识分子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它也是“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论争”“工农兵文艺”等文艺思潮的具体文学实践,同时也与20世纪中期一系列战争动员、乡村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等社会运动息息相关。当我把“通俗文艺改造运动”放置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当中,我发现,原来被隔绝在中国现代文学、民间文学、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中的单个人物、普通事件、通俗作品和零碎史料都被重新赋予了意义与联系。文学实践与社会实践,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文学运动与社会运动,不再是相互区隔的领域,反而呈现出交叉和联合的全新局面。
二、对书评中主要问题的回应
三位书评人帮助我重新回顾了选题生成的过程,让我有机会在多年以后以更为客观的态度反省自己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将对书评中富有启发性的提问做力所能及的回应。
(一)“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时间下限定在1955年是否妥当?兼及1955年后的通俗文艺实践。
三位书评人都在文中提到,拙作研究的时间范围是以1955年《说说唱唱》终刊为下限的。其中一位特别细心地指出,这个时间下限的设置不同于一般的左翼文学史的分期。另外两位书评人举出了若干实例,证明这一运动在《说说唱唱》终刊之后依然方兴未艾,余绪流布不绝,并指出以1955年《说说唱唱》终刊作为这个运动的结点不妥。的确,如何设定研究的时间范围也曾是困扰我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过,在对历史叙事的理解上,我有必要做两点说明。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历史叙事的开端和终点并不真实存在,根据法国年鉴学派对历史叙事的理解,时间是无法用短时段的事件来计量的。①[法]布罗代尔:《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第834页。换言之,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会因某个事件的出现就突然发生或完全终结。如果我们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关注的就不是事件,而是背景和环境。在拙作的“绪论”中,我反复强调,“通俗文艺改造是一个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文学创作潮流”,这就是说,通俗文艺改造运动并非一系列因果关系明确的文学事件的聚合,而是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拙作标题中所设定的时间1930—1955年,并不是“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起止点,而是从“长时段”的背景中截取出的一个时间片段,一个人为设置的“时间上限”和“时间下限”。
其次,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选择1955年3月《说说唱唱》的终刊作为时间下限?其正如海登·怀特所言,无论历史学家选择任何一个时间,或排斥另一个时间,从历史叙事的策略上来看并无本质的不同,它意味着历史学家对某个事件的意义进行了人为地加强。②[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3页。拙作对于通俗文艺的叙事也是如此。我之所以选择《说说唱唱》的终刊这一文学事件为叙事的终点,就是希望以戏剧性手法强化我对整个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历史判断。而我的判断涉及到我对“通俗文艺”概念的理解。
拙作中使用的“通俗文艺”,实际上类似于新文化史中常用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概念。因为我的研究对象虽然看上去像“民间文学”(folk literature),但它并不是典型的、天然的民间文学,而是知识分子为下层民众生产的仿制品,为了避开“大众”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明显阶级意味的概念,我使用了“通俗”一词来对应popular的概念。
但是,刘禾指出,现代文学史上所谓的“通俗”也是一个非常驳杂的概念。它既包括“市民通俗”(popular urban literature),也有“民间通俗”(popular ethnic folk literature),甚至还包括李陀的“革命通俗文艺”。③刘禾:《一场难断的“山歌案”:民俗学与现代通俗文艺》,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批判纲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60—161页。有两位朋友指出,1955年之后还有很多通俗文艺实践,但我认为这些基本属于李陀的“革命通俗文艺”范畴。它和我所关注的通俗文艺最大不同之处并不在于文学层面,而在于受众层面。就赵树理而言,通俗文艺所服务的对象是天然的、具体的、新旧观念杂陈的下层民众,而“红色经典”作品的读者则是作家被提纯的、抽象的、有鲜明阶级意识的“大众”。我之所以把1955年《说说唱唱》终刊定为研究的下限,是因为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解散后,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文化关系发生了质变。
在此,特别感谢几位朋友为读者提供了《说说唱唱》结束之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后续线索。我对此也有一些了解。《说说唱唱》终刊之后,编辑部原班人马中的一部分转入《民间文学》杂志,但《民间文学》的办刊宗旨发生了重大改变,由通俗化转向了学术化、专业化。这是否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文化关系发生了改变?尽管赵树理在1956年出任《曲艺》主编,但这份杂志的影响力无法与《说说唱唱》比肩,似乎更可以证明,赵树理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文艺改造观相对边缘化了。至于赵树理在《中国人》时期所写的“新故事”与60年代的“新故事”运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目前我尚无明确的资料可以提供佐证。不过,如果跃出民间文艺的知识框架,从新中国的大众文化建构的角度去思考它们的关系,或许也是一个有效的研究思路?
再次感谢朋友们注意到了我对“时间下限”的设定,这个选择的确打破了现有的文学史叙事成规,但恰恰表达了我对“通俗文艺改造运动”的理解。
(二)拙作对“精英”与“民众”的理解是否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
一位书评人认为,拙作受到了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一文的重大影响,并认为我的写作对“民间”和“精英”的理解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要回应这个问题,我想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拙作与陈思和的观点的异同。
我在“绪论”中提到,拙作以“民众—精英”来划分通俗文艺阵营的思路受到陈思和所提出的“庙堂—广场—民间”文学史观的启发。不过,当我真正进入历史现场之后,我发现一个严重的困难,就是现有的史料对精英文化生活的记录极其详备,但有关民众文化生活的记载又极其匮乏。我们只能根据报章、日记、回忆录、口述史中的只言片语来拼凑民众的生活图景。而且,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都出自精英之手、精英之口,必然流露出精英的立场和价值观。这就无怪乎读者看到我所呈现的市民文化往往是负面形象。这种态度不是我的态度,而是史料本身带有的态度。按照意大利微观史学家金兹伯格的说法,哪怕民众的记录被留下来了,也是被歪曲的。我们所能见到的大众文化,是精英眼中的大众文化,而非大众自己理解的文化。如何超越史料的局限,不仅是拙作遇到的困难,也是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民众史研究的所有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困难。
在文学史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陈思和有关“民间”具有独立性,庙堂—广场—民间三个文化空间可以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的设想难免引起质疑。①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王晓明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第260页。拙作所考察的历史时段(1930—1955)与陈思和所论时段有大幅度的重合,最初我试图采用“新文化史”和“民众史”研究方法,使用更为广泛的通俗文艺史料验证他的观点。但我发现,与其说抗战的特殊语境让民间文化的独立性加强了,不如说,战争反而呼唤出了民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同一性”。换言之,拙作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对陈思和的判断做出了修正。我和他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在通俗文艺改造运动中,民间文化的独立地位并没有被真正承认过。即使赵树理也不认为应该放任民间文化自由发展,他始终以“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打入天桥去”为己任。②张霖:《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第62、159页。
其次,当代文学中并不存在民间文化的“隐形结构”。陈思和把“藏污纳垢”作为民间文化的特点。但是,这种文化的混杂性并不是民间文化独有的。在战争的特殊语境下,精英文化与通俗文艺出现了明显的融合。在通俗文艺的改造中,尽管精英居于主导地位,但这个实践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运动,它包含生产(production)、传播(dissemination)、接受(reception)和挪用(appropriation)等多个环节。在每个环节中,民众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文化能动性。这种动态关系使得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文化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改造,纯粹的文化形态不复存在。我们之所以能从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作品中看到通俗文艺的影子,这恰恰是革命文学与通俗文艺长期杂交的结果。①陈思和称之为“民间隐形结构”。参见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王晓明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第260、271页。
另外,有书评人认为我试图为“民间”正名,但却对市民文化存在偏见。我要说明的是,拙作无意对任何文化形态进行价值判断,拙作研究的不是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全貌。实际上,它描述的是民众与精英在通俗文化改造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通过搜集各种边缘材料对民众文化的记述,我发现,精英与民众的文化关系是非常动态的,他们有时合作、有时冲突,有时彼此欣赏,有时相互妥协,有时互相排斥。在抗击日本侵略战争时期,二者有过一些成功的合作,赵树理的通俗化实践和陕北的改造说书运动就是典型代表;但民众与精英间的文化冲突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公开化。比如当时《人民日报》和《文艺报》时常撰文批评通俗文艺中的各种错误,甚至还会对市民文化中种种不够“革命”的表现加以抨击。如果说,这些现象只是个别作者、个别群众的落后表现,何必引起重要的批评家和官方媒体的关注呢?这种有趣的现象让我意识到,在“赞同”与“合作”之下,也许还存在一个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②[美]詹姆斯·C.斯科特:《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王佳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7页。也就是说,一方面精英通过“妥协”“让步”“审查”“纠正”“批评”“教育”等方式试图彻底改造下层民众的文化生活,而另一方面,下层民众也以“迎合”“敷衍”“排斥”“拒绝”等方法努力延续本来的文化习俗。不管民众表现出的是赞同,还是其他含糊的态度,都可以看作从属阶层为谋求生存做出的随机应变的反应。
拙作之所以比较集中地展现了城市通俗文艺异质性的一面,绝不认为这就是市民文化的本质,而是因为只有这些材料才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精英与民众的文化差异,只有在差异中才能看到动态的历史。当然,因为民众史材料的缺乏,我的部分论述会出现比较武断的情况。幸运的是,近几年我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如祝鹏程的《文体的社会建构:以“十七年”(1949—1966)的相声为考察对象》一书中看到了大量关于20世纪50年代普通相声艺人的口述史采访,这些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拙作论证的不足。③参见祝鹏程:《文体的社会建构:以“十七年”(1949—1966)的相声为考察对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93—225页。
特别感谢一位评论者指出,拙作中有关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贡献的认识存在明显的不足。有关民间文艺学思想史的内容未被纳入我的研究视野,这是拙作最大的缺憾。
最后,我想以民众史研究者王笛的一段话结束我的回应,并表明我的立场:“无论是强调大众文化与正统文化的同一性,还是强调大众文化的独立性,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实,‘同一性’和‘独立性’自始至终都存在于大众文化之中,但由于时间、空间和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大众文化某些自身的特征等原因,其‘同一性’和‘独立性’在大众文化中或强或弱、或显或隐,交错地发生着变化。充分认识到这种交叉重叠的游离关系对研究和理解大众文化将是至关重要的。”④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最底层看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8页。
综上所述,这本小书如果对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些许价值的话,也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即:现代文学史中民众与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的强调;现代文学研究对于边缘材料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