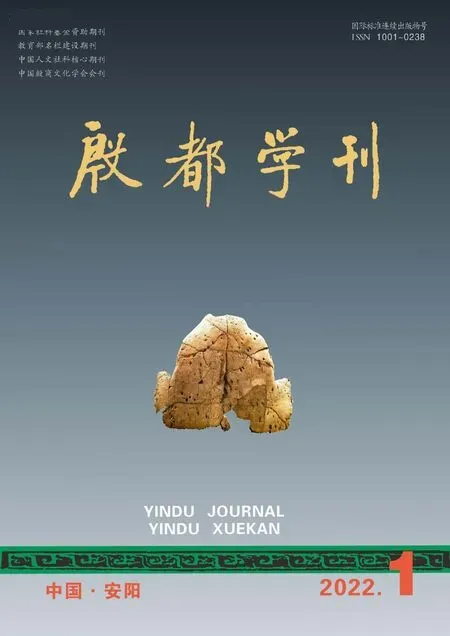宗教、民间信仰与王闽政权
傅绍磊,郑兴华
(宁波财经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
唐末五代,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起兵入闽,历经征战、经营,占据全闽五州,建立王闽政权,却很快陷入激烈的政治斗争,导致政权分崩离析,深刻影响东南沿海历史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入闽前夕,宗教、民间信仰就逐渐与王氏兄弟形成密切关系,后来又在王闽政权建立、王氏兄弟内争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深度介入王闽政权的运作体系之中,几乎与整个王闽政权相始终,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1)何灿浩勾勒王闽政权自太祖到景宗时期宗教政策嬗变,堪称力作,但其论证集中在王闽政权宗教政策层面,而关于宗教对王闽政权的复杂影响挖掘不够全面、细致,且时间跨度也没有延伸到王潮时代,民间信仰更是缺乏关注(《王闽的宗教政策与政教关系》,《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74-78页)。值得注意的是,王延钧继位之后,巫觋进入权力中心,虽然与道教关系密切,但是毕竟不能够等同,所以,本文也归入民间信仰。。本文试图系统梳理宗教、民间信仰与王闽政权在各个阶段的互动关系,从而为王闽政权的兴衰提供新的认识角度。
一
中和年间,作为光州固始人的王氏兄弟受到寿春人王绪裹胁而起兵,加入王绪集团,因为与蔡州军阀秦宗权矛盾激化而被迫离开江淮本土,南下赣、闽,行军途中就已经与佛教建立联系。《五代史补》卷二:“初,王潮尝假道于洪州,时钟传为洪州节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为己患,阴欲诛之。有僧上蓝者,通于术数,动皆先知,大为钟所重。因入谒,察传词气,惊曰:‘令公何故起恶意,是欲杀王潮否?’传不敢隐,尽以告之。上蓝曰:‘老僧观王潮与福建有缘,必变,彼时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礼厚待。若必杀之,令公之福去矣。’于是传加以援送。”(2)《五代史补》卷二,《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2490页。当时王潮假道洪州,形同孤军深入,很难抵御钟传攻击,所以上蓝之言几乎救王潮于危难之间,不可能是凭空而发,结合后来王审知又问政上蓝,可以肯定王氏兄弟与上蓝有密切互动,才能够让上蓝为王潮劝谏钟传。
王绪集团深入闽中之后,成为流寇,引起强烈不满,推动权力更迭,又有宗教因素推波助澜。《资治通鉴》卷二五六:“有望气者谓绪曰:‘军中有王者气。’于是绪见将卒有勇略逾己及气质魁岸者皆杀之。刘行全亦死,众皆自危,曰:‘行全亲也,且军锋之冠,犹不免,况吾属乎!’行至南安,王潮说其前锋将曰:‘吾属违坟墓,捐妻子,羁旅外乡为群盗,岂所欲哉!乃为绪所迫胁故也。今绪猜刻不仁,妄杀无辜,军中孑孑者受诛且尽。子须眉若神,骑射绝伦,又为前锋,吾窃为子危之!’前锋将执潮手泣,问计安出。潮为之谋,伏壮士数十人于篁竹中,伺绪至,挺剑大呼跃出,就马上擒之,反缚以徇,军中皆呼万岁。潮推前锋将为主,前锋将曰:‘吾属今日不为鱼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为主,谁敢先之!’相推让数四,卒奉潮为将军。绪叹曰:‘此子在吾网中不能杀,岂非天哉!’潮引兵将还光州,约其属,所过秋豪无犯。行及沙县,泉州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3)《资治通鉴》卷二五六,中华书局,1956年,第8325页。刘行全之死与王氏兄弟,特别是王审知颇有关系,《十国春秋·司空世家》注引《闽书》:“行全与弟德全、待全勠力而行,王绪忌而杀之;王审知有国,悼其死非罪,为立庙漳州。”(4)《十国春秋》卷九○《闽一·司空世家》,《五代史书汇编》,第4566页。王审知为刘行全立庙祭祀是因为刘行全参与反对王绪,支持王潮,《新唐书·王潮传》:“时望气者言军中当有暴兴者,绪潜视魁梧雄才,皆以事诛之,众惧。次南安,潮语行全曰:‘子美须眉,才绝众,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与左右数十人伏丛翳,狙缚绪以徇。众呼万岁,推行全为将军,辞曰:‘我不及潮,请以为主。’潮苦让不克,乃除地剚剑祝曰:‘拜而剑三动者,我以为主。’至审知,剑跃于地,众以为神,皆拜之。审知让潮,自为副。绪叹曰:‘我不能杀是子,非天乎!’潮令于军曰:‘天子蒙难,今当出交、广,入巴、蜀,以干王室。’于是悉师将行,会泉州刺史廖彦若贪暴,闻潮治军有法,故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围城,岁余克之,杀彦若,遂有其地。”(5)《新唐书》卷一九○,中华书局,1975年,第5491、5492页。王潮取代王绪之后,第一时间提出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获得普遍响应,由此可知,王绪与王潮之间的矛盾不但是权力之争,更是路线之争。因为王绪率领江淮子弟,背井离乡,流落闽中却不知所措,所以失去威信,遭到抛弃;而王潮则思路清晰,主张离开闽中,所以获得拥护。而且王绪出身寿春屠者,身份卑微;而王氏兄弟则是光州豪强,起兵之前就已经极有势力,就此而论,王潮取代王绪一方面有着深刻的必然性,所以连王绪的心腹刘行全等人也倒向王潮;另一方面,王潮取代王绪应该是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王审知应该是颇有力焉,甚至策反刘行全等人的正是王审知,所以能够与刘行全等人形成深厚的渊源,后来还为刘行全等人立庙祭祀。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唐书·王潮传》的记载虽然颇有错讹,但反而能够以“通性的真实”的形式反映出王审知在王潮取代王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6)陈寅恪:《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92页。以此推论,所谓“军中有王者气”等谣谚的传播,幕后操纵者应该就是王审知,目的是为王潮取代王绪进行舆论准备。
光启元年,王潮占据泉州,景福元年,以从弟彦复为都统,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陷入僵局。《资治通鉴》卷二五九:“王彦复、王审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晖求救于威胜节度使董昌,昌与陈岩婚姻,发温、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彦复、审知以城坚,援兵且至,士卒死伤多,白王潮,欲罢兵更图后举,潮不许。请潮自临行营,潮报曰:‘兵尽添兵,将尽添将,兵将俱尽,吾当自来。’彦复、审知惧,亲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尽,晖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监军,弃城走,援兵亦还。庚子,彦复等入城。辛丑,晖亡抵沿海都,为将士所杀。潮入福州,自称留后,素服葬陈岩,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抚其家。汀、建二州降,岭海间群盗二十余辈皆降溃。”(7)《资治通鉴》卷二五九,第8444页。攻占福州对于王闽政权的建立有着决定性意义,王审知自然明白福州的重要性,只是因为伤亡过大而有所犹豫,当确认王潮的坚定态度之后,也就不再动摇,加强攻势。《新唐书·王潮传》:“审知乘白马履行阵,望者披靡,号‘白马将军’。”(8)《新唐书》卷一九○,第5492页。“白马将军”也叫“白马三郎”,《新五代史·闽世家》:“审知为人状儿雄伟,隆准方口,常乘白马,军中号‘白马三郎’。”(9)《新五代史》卷六八,中华书局,1974年,第846页。王审知以自己为“白马三郎”,并不是偶然,而是有所象征。《淳熙三山志·祠庙》:“昔闽粤王郢第三子有勇力,射中大鳝于此潭,其长三丈。土人因为立庙,号白马三郎。唐贞元十年,观察使王翃旱祷得雨,崇饰庙貌。自后,太守躬祷辄应。唐咸通六年,观察使李瓒奏封龙骧侯。梁贞明中,闽忠懿王奏封弘润王。”(10)《淳熙三山志》卷八,《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7860页。白马三郎庙就在福州,自立庙以来,长盛不衰,直到明清,一直都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传统祠庙。由此可知,王审知是在充分运用民间信仰资源鼓舞士气,震慑福州守军,终于攻占福州。
二
随着王闽政权的基本建立,王氏兄弟之间因为权力继承而出现的矛盾逐渐表面化,佛教再次介入其中。
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三人,无论是就排行序列,还是性格气质,即使是以兄终弟及的方式进行权力继承,王审知都没有绝对的优势,而王审邽似乎更加适合守成。《新唐书·王审邽传》:“喜儒术,通《书》、《春秋》。善吏治,流民还者假牛犁,兴完庐舍。中原乱,公卿多来依之,振赋以财,如杨承休、郑璘、韩偓、归传懿、杨赞图、郑戬等赖以免祸,审邽遣子延彬作招贤院以礼之。”(11)《新唐书》卷一九○,第5492、5493页。所以王审知再次运用宗教资源进行政治宣传,为自己获得权力继承资格提供合法性解释,《吴越备史》卷一:“岩为福州数年而卒,以晖继之,至是为王潮所害。时福州尝有僧记之曰:‘潮水来,岩头没;潮水去,矢口出。’矢口,盖言将来继潮之人也。”(12)《吴越备史》卷一,《五代史书汇编》,第6181页。《五国故事》卷下:“初,碎石僧为谶辞曰:‘岩高潮水没,潮退矢口出。’盖言潮破福州陈岩,而审知终嗣其地也。”(13)《五国故事》卷下,《五代史书汇编》,第3194页。王氏兄弟是因为获得闽人支持而占据泉州;福州之战,同样获得闽人大力支持,《资治通鉴》卷二五九:“范晖骄侈失众心,王潮以从弟彦复为都统,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14)《资治通鉴》卷二五九,第8427页。福州之战虽然一度陷入僵局,但是范晖的失败是大势所趋,势在必然,这也是为什么董昌援军行动迟缓、直到福州失陷也没有发挥作用的原因,因为连董昌也明白福州之战的形势,所以所谓的“潮水来,岩头没”“岩高潮水没”云云,并没有实质性意义,真正具有指向性的是“潮水去,矢口出”“潮退矢口出”云云。由此推测,谶语应该就是王审知在幕后操纵。一方面当时王氏兄弟尚未攻占全闽,权力继承尚未提上日程;但另一方面,王氏兄弟已经成为闽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获得闽人最广泛的支持,攻占全闽、权力继承都只是时间问题。对于王审知而言,当时是政治宣传的最佳时间,而且在事实上也确实获得了妇孺皆知的最佳效果,《册府元龟·总录部·谣言》:“先是,闽中有童谣云:‘潮水来,岩头没。潮水去,矢口出。’矢口知字也。果陈岩死,王潮代之。潮死,审知继位。”(15)《册府元龟》卷八九四,中华书局,1960年,第4902页。童谣的形成说明传播范围已经深入到最基层,也就达到了政治宣传的目的。这引起了王潮的注意,《五国故事》卷下:“潮当使日者视己兄弟,曰:‘一个胜一个。’审知方侍其侧,沾汗而退。”(16)《五国故事》卷下,第3194页。王审知虽然“沾汗而退”,但是并没有停止政治宣传,乾宁年间他成为福建观察副使之后,反而进一步彰显自己在王氏兄弟中的特殊地位。《十国春秋·闽一·太祖世家》:“乾宁时,为福建观察副使,有僧涅盘者于众中骇而指之日:‘金轮王第三子降人间,专生杀柄。’”(17)《十国春秋》卷九○,第4569页。《十国春秋》卷九四《闽五·王延兴传》:“延兴,太祖伯兄司空之子也。延兴有弟延虹、延丰、延休,司空皆舍之而让太祖知军务事,后不知所终。又延晦亦司空子,疑先卒。”王潮死后,王延兴等人都在王闽政权销声匿迹,足以说明当时王氏兄弟权力斗争之激烈。第4627页。僧涅盘在大庭广众下称王审知为金轮王第三子,足以说明当时王审知已经羽翼丰满,不再需要太多顾虑,所以不久在王潮死后能够继承权力。
宗教、民间信仰资源,特别是佛教资源在王闽政权建立、王氏兄弟权力继承过程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在王审知继位之后也继续深刻影响政局走向。《五代史补》卷二:“及审知之嗣位也,杨行密方盛,常有吞东南之志气。审知居常忧之,因其先人常为上蓝所知,乃使人赍金帛往遗之,号曰‘送供’,且问国之休咎。使回,上蓝以十字为报,其词曰:‘不怕羊入屋,只怕钱入腹。’审知得之,叹曰:‘羊者杨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杨行密而在钱氏乎?令内外将吏无姓钱者,必为子孙后世之忧矣。’”(18)《五代史补》卷二,《五代史书汇编》,第2490页。杨吴与后梁交恶,周边分别与后梁、吴越、王闽、刘汉、马楚等接壤,而吴越则称臣后梁,周边只有杨吴、王闽,所以杨吴攻击王闽难度远高于吴越,威胁也就更小,上蓝与钟传等地方军阀颇有接触,对东南政治格局有所认识,且又是旁观者,所以也就能够相对客观地揭示王闽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从而为王审知外交方向决策提供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王闽外交方向的形成应与上蓝之言有一定关系,佛教对于王闽政权的影响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民间信仰资源也在王闽政权地方治理层面发挥作用,《北梦琐言》卷七:“福建道以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闽王琅琊王审知思欲制置,惮于力役。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话于宾僚,因命判官刘山甫躬往设祭,具述所梦之事,三奠未终,海内灵怪具见。山甫乃憩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鬣赤。凡三日,风雷止霁,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当时录奏,赐号甘棠港。”(19)《北梦琐言》卷七,中华书局,2002年,第97页。吴安王就是伍子胥,是越、闽民间信仰的海神,有着极大的影响。以吴安王助力开凿甘棠港,不但大大加快甘棠港开凿的进度,推动海上贸易往来,而且获得闽人高度认同,有效提升王审知的德政形象,从而达到经济、政治双赢的局面。《新五代史·闽世家》:“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海上黄崎,波涛为阴,一夕风雨雷电震击,开以为港,闽人以为审知德政所致,号为甘棠港。”(20)《新五代史》卷六八,第846页。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王闽政权事实上的开创者,王潮死后也进入民间信仰的行列,逐渐形成影响。《太平广记·陈岘》:“闽王审知初入晋安,开府多事,经费不给。孔目吏陈岘献计,请以富人补和市官,恣所征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岘由是宠,迁为支计官。数年,有二吏执文书诣岘里中,问陈支计家所在。人问其故,对曰:‘渠献计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众,凡破家者祖考,皆诉于水西大王,王使来追尔。’岘方有势,人惧不敢言。翌日,岘自府驰归,急召家人,设斋置祭,意色慞惶。是日,里中复见二吏入岘家,遂暴卒。初审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审知据闽中,为潮立庙于水西,故俗谓之水西大王云。”(21)《太平广记》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61年,第894、895页。王潮死后,他的形象成为王审知反对者的寄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王氏兄弟的矛盾由来已久,广为人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民间信仰不断介入王闽政权运作的各个层面,甚至引起政治风波。《资治通鉴》卷二七一:“初,闽王审知承制加其从子泉州刺史延彬领平卢节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会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为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骄纵,密遣使浮海入贡,求为泉州节度使。事觉,审知诛浩源及其党,黜延彬归私第。”(22)《资治通鉴》卷二七一,第8860页。王延彬事件并不是偶然,《五国故事》卷下:“初,圭领兵至泉州,舍于开化寺,始生延彬于寺之堂。既生,而有白雀一,栖于堂中。迄延彬之终,方失其所在。”(23)《五国故事》卷下,第3197页。由此可知,王延彬是蓄谋已久,参与谋划的也就不可能只有僧浩源一人,说明宗教、民间信仰介入王闽政权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而王闽政权中运用宗教、民间信仰资源来获取利益的也大有人在。
三
同光三年十二月,王审知薨,王延翰继位;天成元年十二月,王延禀弑君,王延钧继位,王闽政权逐渐陷入内讧,推动道教后来居上直接干预政局,引用巫觋,形成极为消极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推动政局持续动荡,导致王闽政权的分崩离析。
早在王氏兄弟入闽之初,道教谶语就已经出现,《五代史补》卷二:“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即王氏之远祖,为道士。居于福州之怡山时,爱二皂荚树,因其下筑坛,为朝礼之所。其后丹成,冲虚而去。霸尝云:‘吾之子孙,当有王于此方者。’乃自为谶,藏之于地。唐光启中,烂柯道士徐景玄,因于坛东北隅取土,获其词曰:‘树枯不用伐,坛坏不须结。不满一千年,自有系孙列。’又曰:‘后来是三王,潮水荡祸殃。岩逢二乍间,未免有销亡。子孙依吾道,代代封闽疆。’议者以为‘潮荡祸殃’,谓王潮除其祸患以开基业也;‘岩逢二乍间’,谓陈岩逢王潮未几而亡,土地为其所有也;代代封闽疆,谓潮与审知也,代代盖两世之称,明封崇不过潮与审知两世耳。”(24)《五代史补》卷二,第2489、2490页。王潮占据泉州是在光启元年,数年经营逐渐获得闽人更加广泛支持,才能够在景福二年攻占福州,进而占据全闽五州。从光启元年到景福二年,王氏兄弟虽然入闽,但是闽中形势还是有一个从混沌到明朗的过程,所以谶语也在逐渐嬗变,但指向性总是不够明确,后来议者的所谓解读也颇为牵强。而且,王霸其人作为闽人与光州固始人王氏兄弟之间的关系过于疏远,以此衍生的谶语也就难以起到宣传王闽政权权力合法性的政治作用,所以并没有引起王氏兄弟的太多注意。虽然谶语的制作颇为仓促、粗糙,但是透露出的道教介入政治的强烈意愿却极为明显,这为道教在王延钧时代登上政治舞台埋下伏笔。
王延钧是在王延禀弑君之后,由王延禀拥立。他继位之后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于是王延钧重用闽人,加快王闽政权本土化转型,从而巩固统治。(25)何灿浩注意到王闽政权有一个本土化的嬗变过程,表现为闽人地位的提升(《试论王闽政权的构成及其变化》,《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41-47页;《王闽三次福州兵变及其原因》,《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75-78页)。但可以补充的是,作为本土化程度更高的道教、民间信仰进入权力中心,也是王闽政权本土化嬗变过程的表现。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道教从原来的边缘状态迅速进入权力中心。《资治通鉴》卷二七七:“闽王延钧好神仙之术,道士陈守元、巫者徐彦与盛韬共诱之作宝皇宫,极土木之盛,以守元为宫主。”注引《旧五代史》:“福州城中有王霸坛、炼丹井。坛旁有皂荚木,久枯,一旦忽生枝叶。井中有白龟浮出,掘地得石铭,有‘王霸裔孙’之文,昶以为己应之,于坛侧建宝皇宫。”(26)《资治通鉴》卷二七八,第9061页。王延钧以“王霸裔孙”自居,目的是以王霸为中介将自己的籍贯本土化,拉近与闽人的关系,从而推动王闽政权的本土化转型。道教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提供了足够的本土化资源而获得王延钧的信任,从而形成以陈守元为主,巫者徐彦、盛韬等为辅的宗教集团,进一步推动王闽政权脱离中原王朝的藩属,《资治通鉴》卷二七七:
闽陈守元等称宝皇之命,谓闽王延钧曰:“苟能避位受道,当为天子六十年。”延钧信之,丙子,命其子节度副使继鹏权军府事。延钧避位受箓,道名玄锡。
闽王廷钧谓陈守元曰:“为我问宝皇:既为六十年天子,后当何如?”明日,守元入曰:“昨夕奏章,得宝皇旨,当为大罗仙主。”徐彦等亦曰:“北庙崇顺王尝见宝皇,其言与守元同。”延钧益自负,始谋称帝。表朝廷云:“钱镠卒,请以臣为吴越王;马殷卒,请以臣为尚书令。”朝廷不报,自是职贡遂绝。(27)《资治通鉴》卷二七八,第9063、9073页。
王延钧避位受箓,获得道士身份,将道教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为王闽政权独立于中原王朝进行政治宣传。《十国春秋·闽二·惠宗本纪》注引《闽海丛谈》:“闽王鏻日祈太乙神册,逾年,双鹤徘徊而下,遂谋僭号。”(28)《十国春秋》卷九一,第4592页。《资治通鉴》卷二七八:“闽人有言真封宅龙见者,闽王延钧更命其宅曰龙跃宫。遂诣宝皇宫受册,备仪卫,入府,即皇帝位,国号大闽,大赦,改元龙启;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庙。”(29)《资治通鉴》卷二七八,第9081页。陈守元宗教集团参与筹划、操作王延钧登基称帝的整个过程,使道教正式进入王闽政权权力中心,在多个方面对王闽政权产生重要影响。如财政聚敛,《资治通鉴》卷二七八:
初,福建中军使薛文杰,性巧佞,璘喜奢侈,文杰以聚敛求媚,璘以为国计使,亲任之。文杰阴求富民之罪,籍没其财,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铜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吴光入朝,文杰利其财,求其罪,将治之;光怨怒,帅其众且万人叛奔吴。
闽主好鬼神,巫盛韬等皆有宠。薛文杰言于闽主曰:“陛下左右多奸臣,非质诸鬼神,不能知也。盛韬善视鬼,宜使察之。”闽主从之。(30)《资治通鉴》卷二七八,第9086、9096页。《十国春秋》卷九八《闽九·薛文杰传》:“文杰善数术,自占过三日可无患。”所以,薛文杰很可能也是出身巫者,如徐彦、盛韬之流,第4660页。就薛文杰对吴光的态度而言,实际上是严重侵犯闽人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闽政权本土化是极为复杂的政治过程,并不意味着所有闽人都获益。
薛文杰与盛韬等人互为奥援,关系密切,很明显是陈守元宗教集团成员,成为王延钧政治意图的执行者,改变了王审知以来的财政路线。《十国春秋·闽六·张睦传》:“张睦,光州固始人,唐末从太祖入闽。太祖封琅琊王,授睦三品官,领榷货务。睦扰攘之际,雍容下士,招徕蛮商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累封梁国公。卒,葬福州赤塘山。后以薛文杰代其职,闽人益思睦,立社城中祀焉。”(31)《十国春秋》卷九五,第4637页。
如抑挫宗室。《资治通鉴》卷二七八:
闽内枢密使薛文杰说闽王抑挫诸宗室;从子继图不胜忿,谋反,坐诛,连坐者千余人。
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有擒王延禀之功,性慷慨,言事无所避。闽主恶之,尝私谓左右曰:“仁达智有余,吾犹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诬以叛,族诛之。(32)《资治通鉴》卷二七八,第9090、9098页。
王继图、王仁达之死都与掌握兵权有关,操作者应该都是薛文杰。(33)《十国春秋》卷九四,第4629页。
另如控制军队,《资治通鉴》卷二七八:“文杰恶枢密使吴勖,勖在疾,文杰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罢公近密,仆言公但小苦头痛耳,将愈矣。主上或遣使来问,慎勿以它疾对也。’勖许诺。明日,文杰使韬言于闽主曰:‘适见北庙崇顺王讯吴勖谋反,以铜钉钉其脑,金椎击之。’闽主以告文杰,文杰曰:‘未可信也,宜遣使问之。’果以头痛对,即收下狱,遣文杰及狱吏杂治之,勖自诬服,并其妻子诛之。由是国人益怒。”(34)《资治通鉴》卷二七八,第9096页。吴勖在军中颇有威信,《十国春秋·闽九·薛文杰传》:“勖常主军政,得士卒心,士卒闻勖死,皆怒。”(35)《十国春秋》卷九八,第4660页。所以薛文杰所谓“主上以公久疾,欲罢公近密”云云,是弦外有音,真正的原因在于王延钧对吴勖的猜忌,必欲除之而后快,从而控制军队,而薛文杰充当的则是实际操作者的角色。结合徐彦等人劝进王延钧也是以北庙崇顺王的名义,那么在剪除吴勖的过程中,操作者应该不止薛文杰一人,因为吴勖位高权重,势力盘根错节,所以应该是陈守元宗教集团的共同行动。
陈守元宗教集团在财政、宗室、军事等领域全线出击,过于激进且树敌太多,终于激化矛盾,《资治通鉴》卷二七八:
吴光请兵于吴,吴信州刺史蒋延徽不俟朝命,引兵会光攻建州,闽主遣使求救于吴越。
吴蒋延徽败闽兵于浦城,遂围建州,闽主璘遣上军张彦柔、骠骑大将军王延宗将兵万人救建州。延宗军及中涂,士卒不进,曰:“不得薛文杰,不能讨贼。”延宗驰使以闻,国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继鹏泣谓璘曰:“吾无如卿何,卿自为谋。”文杰出,继鹏伺之于启圣门外,以笏击之仆地,槛车送军前,市人争持瓦砾击之。文杰善术数,自云过三日则无患。部送者闻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见之踊跃,脔食之;闽主亟遣赦之,不及。……并诛盛韬。(36)《资治通鉴》卷二七八,第9096、9100、9101页。事实上,陈守元宗教集团影响的范围还包括后宫,《十国春秋》卷九九《闽十·陈靖姑传》:“靖姑,守元女弟也。常饷守元于山中,遇馁妪,发箪饭饭之,遂授以秘篆符箓。与鬼物交通,驱使五丁,鞭笞百魅。永福有白蛇为孽,数害郡县,或隐迹宫禁,幻为人形。惠宗召靖姑驱之,靖姑率弟子作丹书符,夜围宫,斩蛇为三。蛇化三女子溃围出,飞入古田井中。靖姑围井三匝,乃就擒。惠宗诏曰:‘蛇魅行妖术,逆天理,隐沦后宫,诳欺百姓。靖姑亲率神兵,服其余孽,以安元元,功莫大焉。其封靖姑为顺懿夫人,食古田三百户,以一子为舍人。’靖姑辞食邑不受,乃赐宫女三十六人为弟子。”结合王延钧对陈守元的信任,则陈靖姑也是陈守元宗教集团重要成员,参与政治斗争。王延钧对陈靖姑封赐规格之高说明的是政治斗争之激烈、陈靖姑发挥的作用之大,只是因为宫闱暧昧,所以语焉不详。第4678页。
薛文杰之死本质上是王闽军队、宗室,甚至市人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针对陈守元宗教集团,联合反对王延钧的结果。虽然是内忧外患之际,但王延钧却只是有限度地妥协,甚至一度心存侥幸,想要赦免薛文杰,更谈不上抛弃陈守元宗教集团。所以薛文杰之死并不意味着陈守元宗教集团与王闽政权关系的结束。事实上,蒋延徽攻建州垂克,只是因为杨吴内讧和吴越援兵而不得不撤兵,足以说明当时王闽政权政局已经混乱不堪,所以薛文杰之死不久,王延钧就遇弑。
王继鹏继位之后,不但没有改变王延钧的政治方向,反而在各个方面更加激进,甚至不惜赋予陈守元宗教集团更大的权柄。《资治通鉴》卷二七九:“闽主赐洞真先生陈守元号天师,信重之,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守元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37)《资治通鉴》卷二七九,第9137页。王继鹏在长兴二年、龙启元年王延钧逊位、避位期间监国,是事实上的储君,所以继位之后不存在权力合法性问题,也就没有必要改变王延钧的政治方向,而且他自龙启元年四月就充宝皇宫使,应该与陈守元关系密切。陈守元受赂请托显然是获得王继鹏的授意,实际上是变相的财政聚敛,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居然形成制度。《资治通鉴》卷二八一:“时百役繁兴,用度不足,闽主谓吏部侍郎、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闻有司除官皆受赂,有诸?’对曰:‘浮言无足信也。’闽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择贤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第令纳赂,籍而献之。’守蒙素廉,以为不可;闽主怒,守蒙惧而从之。自是除官但以货多寡为差。闽主又以空名堂牒使医工陈究卖官于外,专务聚敛,无有盈厌。又诏民有隐年者杖背,隐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鸡豚,皆重征之。”(38)《资治通鉴》卷二八一,第9176页。蔡守蒙、陈究内外呼应,财政聚敛的范围从富民扩大到各个阶层,而且已经制度化。
值得注意的是,王继鹏抑挫宗室也更加肆无忌惮,《资治通鉴》卷二八二:“闽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户部尚书延望才名,巫者林兴与延武有怨,托鬼神语云:‘延武、延望将为变。’闽主不复诘,使兴帅壮士就第杀之,并其五子。闽主用陈守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祀,求神丹。政无大小,皆林兴传宝皇命决之。”[注]《资治通鉴》卷二八二,第9201、9202页。林兴是陈守元宗教集团的成员,继薛文杰之后扮演同样的角色,此时陈守元集团权柄更大,所以其能量已经不是薛文杰可以相提并论,他不但可以全权处置宗室成员,而且形成“政无大小,皆林兴传宝皇命决之”的局面,进一步加剧王闽政权的危机。《资治通鉴》卷二八二:“闽判六军诸卫建王继严得士心,闽主忌之,六月,罢其兵柄,更名继裕;以弟继镛判六军,去诸卫字。林兴诈觉,流泉州。望气者言宫中有灾,乙未,闽主徙居长春宫。”[注]《资治通鉴》卷二八二,第9203页。泉州是王闽政权的发迹之地,不可能用来流放犯人。所以,合理的解释是,林兴抑挫宗室引起反弹,不得不引咎远离权力中心,所谓的“流泉州”只是王继鹏为了安抚宗室的权宜之计。由此可见当时的王闽政权已经危机重重,于是数月之后,王闽政权内部再次爆发政变,王继鹏遇弑。[注]随着王闽政权危机的加剧,陈守元宗教集团也在悄然分化,《资治通鉴》卷二七九:“以建王继严权判六军诸卫,以六军判官永泰叶翘为内宣徽使、参政事。翘博学质直,闽惠宗擢为福王友,昶以师傅礼待之,多所裨益,宫中谓之‘国翁’。昶既嗣位,骄纵,不与翘议国事。一旦,昶方视事,翘衣道士服过庭中趋出,昶召还,拜之,曰:‘军国事殷,久不接对,孤之过也。’翘顿首曰:‘老臣辅导无状,致陛下即位以来无一善可称,愿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属公,政令不善,公当极言,奈何弃孤去!’厚赐金帛,慰谕令复位。昶元妃梁国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燕,待夫人甚薄。翘谏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礼,奈何以新爱而弃之!’昶不说,由是疏之。未几,复上书言事,昶批其纸尾曰:‘一叶随风落御沟。’遂放归永泰,以寿终。”叶翘也是陈守元宗教集团成员,所以能够在王延钧、王继鹏两朝身居高位,只是因为与王继鹏政见不同而遭到冷落。《南唐书》卷一七《谭紫霄传》:“谭紫霄,泉州人,幼为道士,初,有陈守元者,亦道士,地得木札数十。贮铜盎中,皆汗张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尽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疾病,多效,闽王王昶尊事之,号金门羽客,正一先生,闽亡,遁居庐山楼隐洞,学者百余人。”谭紫霄虽然与陈守元渊源深厚,但关系并不密切,虽获得尊崇,却实际上远离权力中心,所以后来能够逃离王闽政权。
在此次政变的过程中,陈守元宗教集团已经声名狼藉,政治形象极为不堪,成为众矢之的,终于遭到王闽政权的抛弃。《资治通鉴》卷二八二:“连重遇之攻康宗也,陈守元在宫中,易服将逃,兵人杀之。重遇执蔡守蒙,数以卖官之罪而斩之。闽王曦既立,遣使诛林兴于泉州。”(39)《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屡以猜怒诛宗室,叔父左仆射、同平章事延羲阳为狂愚以避祸,闽主赐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寻复召还,幽于私第。”由此推测,王延羲能够躲过王继鹏的诛杀,应该是陈守元在起作用。事实上,政变前夕陈守元已经与王延羲暗通款曲,《五国故事》:“延羲,审知第二十八子也。先时得罪于昶,昶囚之私第。有庭石一根。一日,有白烟一穗起于石上,久之方散。延羲惧,乃密召道士陈守元,即伪号陈天师者也,使禳克之。守元曰:‘未必不为嘉兆也。’”(40)《五国故事》卷下,第3196页。王延羲诛杀林兴针对的不仅是林兴一人,而是整个陈守元宗教集团,所以陈守元的政治投机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守元之死并不是偶然,因为陈守元就算是侥幸在政变中保全性命,也难逃王延羲的诛杀。作为陈守元宗教集团的核心成员,林兴之死也意味着陈守元宗教集团的消亡。但是王延羲在抛弃陈守元宗教集团之后,却并没有消除政治危机,从而导致王闽政权走向分崩离析,直到入宋之后终于再次迎来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