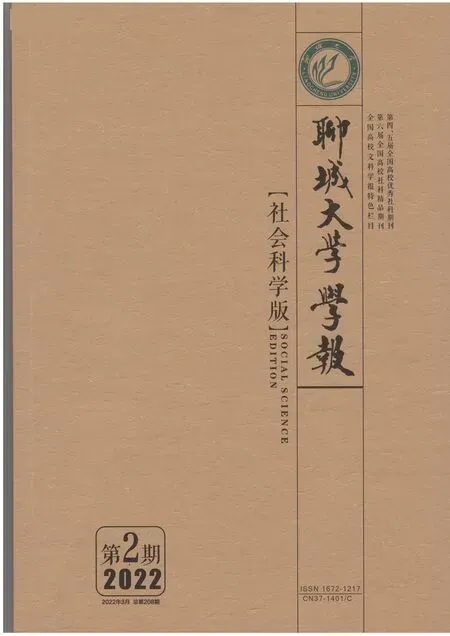新中国成立以来“探母戏”浮沉研究
——以《四郎探母》《三关排宴》为例
令狐兆鹏
(1.西南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重庆 400400;2.运城学院 中文系,山西 运城 044000)
戏曲是深受中国民众欢迎的文艺形式,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集体情感,体现了百姓日常生活道德伦理。戏曲为意识形态与老百姓情感体验、生命诉求的相互碰撞的产物,包含着整个民族的生存密码,凝缩了社会民众的情感诉求和文化品性,在满足老百姓娱乐的同时,承载着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自南宋以来,杨家将的故事就在民间广泛流传。人们津津乐道的大都是杨家满门忠烈的故事,要么是歌颂杨家男儿浴血沙场,舍身成义(如《金沙滩》《两狼山》等);要么讲述杨门女将,挂帅西征,巾帼不让须眉(如《穆柯寨》《演伙棍》等)。但是,杨四郎的故事则是另类,金沙滩一役他并没有与父兄一道殉国,而是选择了忍辱偷生,还当上了敌国的驸马。关于杨四郎的戏剧,流传最广的当属京剧《四郎探母》和上党梆子《三关排宴》。而颇有意味的是,两部作品中杨四郎最终的归宿完全相反,前者杨四郎探母后最终返回辽国,虽经历种种风波,却也阖家团圆;后者则被生母佘太君责备,自尽而亡。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围绕两部“探母戏”,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分歧、争议,乃至批判,从中可以窥见意识形态迭变之痕迹。
一、“探母戏”的冷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
作为一门雅俗共赏的艺术,戏曲的生产、传播、消费不仅仅有着自身的规律,还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戏曲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教化功能,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戏曲批评就是意识形态的晴雨表。
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迫在眉睫——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旗帜,以阶级论为核心,以“人情论”为标靶,从而展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文化宣传战。文艺就成了宣传革命的武器,正如毛泽东所言:“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8页。而《四郎探母》宣传亲情至上,家庭和谐,无形之中削减了民族斗争的主题,必然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之间发生强烈的碰撞,难免会成为被官方意识形态所批判的反面教材。
建国以后对《四郎探母》的批判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
第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反面教材。新中国成立后,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弘扬爱国主义运动。“爱国主义是我们新中国建设的原动力之一。”②黄芝冈作,范正明录校:《黄芝冈日记选录》(十二),《艺海》2015年第2期,第29页。1951年5月5日中国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戏改纲领性文件《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五五指示”):“人民戏曲是以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武器”,“应以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和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内容”。爱国主义教育自有其标准,“凡宣传反抗侵略、反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③转引自 张炼红:《历练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第271页。
意识形态不是独立运行的物自体,它需要一个“他者”来确定自己的正确性。“不存在任何不借助将自己与另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划清界限的方法坚持自己权利的意识形态。一个从属于意识形态的个体永远不可能独自说‘我处于意识形态之中’,为了使他自己‘真正的’立场与意识形态区别开来,他永远要求另外一部信念大全。”④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幽灵:图绘意识形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页。新中国意识形态要求建立动员机制,爱国主义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必须确立一个他者——叛徒,来完成对自我的界定。《三关排宴》对于叛徒的声讨正好宣扬了爱国主义的情操,是佘太君还是杨四郎成为褒扬的对象,这是一个问题。杨四郎成为叛徒的代表受到批判在当时是历史的必然。“他乞望在壁垒分明的两个对立的国家之间,用他那汉奸的哲学把叛徒和爱国混淆在一起,模糊是非界限,为他的叛国忘家寻找安慰和借口,以便继续过着无耻的叛徒生活。”⑤曲六乙:《驳〈上党戏“三关排宴”的导演处理〉一文的人性论》,晋东南行署文化局戏剧研究组:《三关排宴》专辑,《戏剧资料》1984年第3期,第167页。杨四郎最大的“污点”在于战争期间附敌,而《四郎探母》却没有任何谴责之意,被认为是宣传汉奸思想,对人民缺乏教育意义。
第二,作为批判资产阶级“人情论”的典型案例。“人情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受到强烈批判。1957年初,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背景下,巴人发表了《论人情》一文,对“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的现象进行批评,呼吁作品中应当出现人情味。文章出来就受到了指责,后来,王淑明撰文对巴人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和发挥。他们认为人情、人性、人道主义是优秀的文艺作品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1960年“反修”文学思潮兴起,巴人关于人情、人性问题的观点受到全面批判,姚文元发表《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一文,认为“巴人的声音确实代表了一种没落阶级的声音,它提醒我们:资产阶级人情的阴魂,并没有绝迹。”⑥姚文元:《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文艺思想论争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356页。
《四郎探母》因宣扬“人情论”在五六十年代受到强烈的批判。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人情”是资产阶级掩盖剥削的伎俩,《四郎探母》中的“人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⑦郭汉城:《对几个传统剧目的分析》,《戏剧报》1963年第9期,第8-14页。《四郎探母》中的“人情”也被当作是对阶级、阶级斗争的亵渎,从而抹杀了敌我之间的界限,甚至被当作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靶子而受到批判,“这些思想(‘和平主义’——引者注)与今天我们所要坚决反对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与和平主义的修正主义论调,恰相吻合。资产阶级宣传‘人性的爱’,要求戏剧中要有他们的这种‘人情味’,‘人和人之间相通的东西’,即‘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⑧南大中文系地方戏研究小组:《〈四郎探母〉〈南北合〉的反动思想必须批判》,《百花》1960年第15期,第18页。
当学术界将火力对准《四郎探母》的时候,上党梆子《三关排宴》被当作了正面的典型。同样是杨四郎探母的故事,《三关排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演绎。与《四郎探母》相比,《三关排宴》更能符合建国后的意识形态。《三关排宴》讲究政治站位,痛斥叛徒,谴责投降主义,弘扬爱国主义,正是新中国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佘太君的忠君思想被巧妙地置换成忠于社会主义,热爱祖国。①天生:《对目前继承传统讨论的浅见——兼及〈三关排宴〉讨论中的某些问题》,晋东南行署文化局戏剧研究组:《三关排宴》专辑,《戏剧资料》1984年第3期,第171页。有学者从爱国主义角度高度评价《三关排宴》,认为佘太君大义灭亲的行为体现了“敌我分明的、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②安娥:《谈“四郎探母”在思想内容上的问题》,《戏剧报》1956年第9期,第31页。
《三关排宴》对叛徒的指责,对爱国主义的弘扬非常适合新中国意识形态的建构。张炼红曾经在分析《梁祝》时,指出“全剧高度宣扬的坚贞不渝、至死不屈、就情感专一和信念的忠诚度而言,不正是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汲汲所需的伦理核心与精神向度?”③张炼红:《历练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第323页,第318页。这种观点更适合于《三关排宴》。新中国成立伊始,内忧外患,急需建立起一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面是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藉此来动员和组织全民力量,稳定统治局面,保障国家民族生计和国家利益;一面倒也不妨赖以此慰藉个体生存的艰险与困顿,让死者流芳百世,生者保全性命。”④张炼红:《历练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第323页,第318页。这是有历史的原因的,新中国虽然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权,但一直处在被西方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在西方冷战思维的操控下,新中国不得不以敌我关系来判断中外关系。尽管杨家将所处的时代与《三关排宴》编剧所处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都随时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战争思维下人们的思考方式必然是斗争第一,而在斗争中,英勇牺牲者要受到嘉奖,叛徒则要受到惩罚。在杨家将故事中,杨四郎和他的父兄们只能被处于两端——苟延残喘地活着还是英勇地献身。因此,对于佘太君而言,宽恕杨四郎则无疑于背叛了杨家的满门忠义。《三关排宴》竭力强调爱国主义立场,正是战争思维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
二、新时期以来意识形态的转变与“探母戏”的翻转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成为中国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总纲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有一定的斗争,但总体而言,和谐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前进的总体方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改变,阶级斗争为中心已经一去不复返,由此而带来的是阶级话语的冷遇和阶层概念的兴起,建立和谐社会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的整体诉求。
意识形态的变化带来的是文艺批评的翻转。《四郎探母》所面临的关于破环阶级斗争、给爱国主义教育蒙羞、为叛徒张目等指控的社会舆论已经消失,杨四郎重新得到观众的青睐。在思想界,不少有识之士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的禁区,开始从民族和谐的角度努力挖掘《四郎探母》的历史价值。有学者认为,“就《探母》的总体看,它的主旨在于要求民族通好和睦相处,对杨四郎也主要表现的是隐姓埋名十五年,不忘亲人故土的正当行为,……今天,我国各族人民已经实现了‘平等的联合’,《探母》所表达的民族和睦的意愿,对于促进国内各族人民的团结共进该是有利的吧 !”⑤史若虚、贯涌:《铁镜公主与〈四郎探母〉的思想性》,《中国戏剧》1980年5期,第47-48页。
1981年,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著名历史学家李一氓在《文艺研究》第4期发表了《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 〉》,为京剧《四郎探母》鸣锣开道。李一氓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辽史与民间传说杨家将之关系,划清了历史与演绎的界限,提出了“和谐”至上的观点:“我觉得凡涉及今天民族现存关系的历史著作和文艺著作应该慎重其事。团结的方针,平等的方针,和谐的方针是正确的。稍为偏离一点,以汉族为主体,无视兄弟民族的存在和今天已融合为一个中华大民族的方针都是有害的。”⑥李一氓:《读辽史 —兼论〈四郎探母〉》,《文艺研究》1981年4期,第79页。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文学作品中的民族冲突本质化,文章结束时,呼吁我们应当“拿出大民族的气魄,就让这个冒牌将门子弟,以辽驸马的面目出现在舞台上,从 [西皮慢板 ]唱起;让这个不伦不类搔首弄姿的旗妆公主同时出现在同一舞台上,从 [西皮摇板 ]唱起,不知有何不可?”①李一氓:《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文艺研究》1981年4期,第79页。
《四郎探母》终于浮出历史地表。1980年11月30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应广大读者和观众的要求,《四郎探母》即将公演”。12月3日起,《四郎探母》在北京容纳观众最多的天桥剧场,连演七天。这场由中国戏曲学院大专班和实验京剧团联合演出的京剧《四郎探母》引起巨大轰动。
从此,《四郎探母》终于走出历史的禁区,成为京剧的经典曲目,不但在国内戏曲界大受欢迎,而且走向世界,成为最受海外华人欢迎的经典曲目。根据吴钢的回忆,自2003年起,每两年一届的法国巴黎中国传统戏曲节上,《四郎探母》表演场场爆满,戏票供不应求,作者感慨道:“古老的《四郎探母》,没有说教、没有宣讲,却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带到了海外、带到了法国,让法国人民真正了解中国人民善良、孝顺、亲情等优秀品质的传承和历史渊源。”②吴钢:《〈四郎探母〉复出四十年记》(五),《中国戏剧》2019年11期,第75页。
相对而言,新时期以来,《三关排宴》受到关注的程度就小得可怜。对学术界发表的相关论文做一调查,即可发现两者巨大差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网共收录以《四郎探母》为主题的论文82篇。其中上世纪80、90年代发表15篇;2000年至2010年,发表论文17篇;近十年来发表论文50篇,其中博士论文1篇(王真峥:《四郎探母》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从中可以看到《四郎探母》在学术界逐步形成研究的热潮,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视,《四郎探母》研究形成了一个热潮。再看《三关排宴》,改革开放以来,以《三关排宴》为题的论文仅有4篇,学术价值突出的只有两篇,分别为张炼红的《罪与罚:〈四郎探母〉、〈三关排宴〉的‘政治’和‘伦理’》和张永峰的《〈三关排宴〉改编与戏曲改革的两个难题》,而且都是新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知网上收录以《三关排宴》为主题的论文数目为零,令人唏嘘。颇有意味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剧作家吴祖光曾受命改编了京剧版《三关排宴》,名为《三关宴》,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八十年代以后,《三关宴》并没有受到追捧。
三、“探母戏”盛衰背后的文化基因
《四郎探母》之所以能够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经典剧目,在于它承载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基因。这就是对于“情义”的坚守。“杨四郎虽然不像其他杨家将故事里的英雄主人公那样令人崇敬,却依然有他清晰的伦理底线,杨四郎是有道德内涵的人物,而且他所遵循的道德信念,是人们能够接受的。”③傅谨:《老戏的前世今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中国文化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所谓的“大传统”,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传统,比如儒家的忠君爱国、三纲五常的思想伦理。而“小传统”则是民间社会流传的老百姓默默遵守的习焉不察的文化惯习,它可能是与“大传统”相吻合的(比如忠孝节义),但也不乏超越其樊篱之处。受到大传统的影响,小传统也讲究忠孝节义,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小传统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情义”(所谓有情有义,指的是情是义的基础)作为人际交往的基础。
戏曲伦理虽然有大传统宣教之功能,但受众多为普通民众,并非士大夫阶层,因此,小传统的影响更加深远。换言之,戏曲之所以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一定是传达了他们内心的集体无意识——相对于精忠报国、铁肩担道义等关乎大传统的主题而言,小传统中的“情义”对于人性的理解就比较有弹性,它肯定了人性的丰富性——人们有以感恩之心来回报对你善意的人的义务,这是做人的底线。忘恩负义之所以成为千夫所指,就在于其人性之凉薄足以让善意蒙羞。人与人相知相守,都是以情义为基础而建立的以彼此信任为表征的契约。“《四郎探母》的故事之所以成立以及感人,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原因,就是大宋的杨四郎和番邦的铁镜公主相互之间通过十五年的婚姻生活建立起来的跨文化的信任。”①傅谨:《老戏的前世今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第105页,第105页,第48页。因为信任,杨四郎发誓探母即归,也因为信任,公主才舍命去盗符。“遵守承诺,言而有信,并且知恩图报,就是通常所说的‘义’的主要内容之一。”②傅谨:《老戏的前世今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第105页,第105页,第48页。
“四郎可以思母探母,公主也可以为他盗令,但是公主对他的承诺和他对公主的承诺必须相互遵守,这是‘信义’,而且加上他与贤惠的铁镜公主以及襁褓中的孩子的感情,这‘信义’就更有分量。”③傅谨:《老戏的前世今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第105页,第105页,第48页。这种信义不仅存在于杨四郎与公主之间,也存在于杨四郎与佘太君之间。佘太君不舍得四郎见一面就要马上离开,杨四郎痛苦地回答:“哎呀母亲哪!儿岂不知天地为大,忠孝当先;儿若不回去,可怜你那番邦的媳妇、孙儿,俱要受那一刀之苦……”。④长治专区人民剧团:《三关排宴(上党梆子)·四郎探母(京剧)》,北京:北京宝文堂书店,1957年,第67页。而佘太君之所以没有再苦苦挽留,就在于她也认同了这个盟约的重要性。没有这个盟约,杨四郎根本没有机会探母,背叛这个盟约,则失去了做人的根本。因此,对“情义”的坚守在某种条件下成为可以超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因此,《四郎探母》不能没有“回令”,没有了“回令”,杨四郎和公主这个盟约也就背叛了,整个故事的民间信仰的基础也随之坍塌。
由此,我们可以反观《杨家将》种种故事,为何上党梆子《雁门关》中——杨八郎深入敌穴,杀死萧太后,带着公主投奔大宋,为阻断追兵,最终战死疆场,成全了杨家满门忠烈——这个故事没有广泛流传。究其原因在于他为了忠而背叛了情义。如果一个人为了抽象的忠,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可以背叛、杀戮,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爱之处,这大概就是所谓“卧底”之先天道德之瑕疵——以欺骗情感为始,以背叛情感为终。无独有偶,台湾的《新四郎探母》和大陆的《三关明月》都竭力想将杨四郎美化成为卧底英雄,“但是很令人丧气的是这些所谓政治、伦理、道德正确的戏并没有受到观众的欢迎,人们直到今天爱看的仍然是老版的《四郎探母》,而不是新编的《四郎探母》,更不是《三关明月》。”⑤张默翰:《个人意识与集体理性之争:关于〈四郎探母〉的讨论》,《戏剧文学》2011年第2期,第90页。而在民间社会里,这个窝窝囊囊、哭哭啼啼的杨四郎虽然不够忠孝,但至少在家庭情义方面,做得无可挑剔。这不正是家庭牢固的根基吗?因此,《四郎探母》终究表达的是民间文化对于家庭操守的要求,是对于男人忠于家庭的要求,这是社会安稳的基础。
《四郎探母》在民众间的流行,也反映出民众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思想。“《四郎探母》等传统戏中之所以喜欢用天伦人情来淡化政治斗争的严酷记忆,这也恰恰反映出那种渴望在精神和肉体上彻底摆脱政治性压迫的民众集体记忆。”⑥张炼红:《历练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第323页。从大传统上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有为国尽忠的义务,这也是杨家将故事历代相传的基础。但从小传统上讲,每个人都有保持善良之本性活下去的权利,即便在战争频仍的年代,对活着的渴望乃至对家庭完整的追求依然是中国民众最基本的心愿。许纪霖在《周作人:现代隐士的一幕悲剧》中说中国人长久以来注重“生、乐、和”的哲学。中国人以生为第一位,肯定现实生命的存在为一切哲学之前提。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习惯于接受现实,顺天知命。“和”指的是“顺世和乐之音”,追求“天人合一”,以中庸为至高境界。⑦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7-110页。观众看《四郎探母》,没有把他当作一位将军,一位战士,而是就把他当作一位普通人,他可以在公主跟前忏悔、可以在母亲面前痛哭,也可以在岳母面前求饶,这是“生”。探母之后,杨四郎向萧太后认罪,公主求情,国舅出主意,逗得太后一乐,所有的怒火都烟消云散了,这就是“乐”与“和”。因此,杨四郎与公主大团圆的结局意味着在老百姓心中,“家和”是第一位的。“中国戏曲的成功之作,往往是展示平民乌托邦式的理想乐园。”⑧傅谨:《老戏的前世今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第105页,第105页,第48页。“家和万事兴”正是中国老百姓的乌托邦。赵树理曾经说:“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得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我们也应该懂得团圆。”①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赵树理全集》(四),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14-415页。大团圆是中国人对幸福的最基本的追求,尤其是在动荡的年代,更是百姓维系生存的精神支柱,这就是《四郎探母》自诞生以来深受广大民众欢迎的原因。
《三关排宴》体现了中国传统戏剧载道的传统,具有很强的教化功能。这个“道”不是小传统中以家庭为中心的情义,而是大传统中以国家为中心的“忠孝节义”。《三关排宴》改编自上党传统戏《忠孝节》,所宣扬的终究是为国捐躯的社会伦理,它讲述的是一个投降者认罪伏法的故事,是母亲“大义灭亲”的故事,而这种故事其实并不符合中国人自古以来讲情义,讲孝道的小传统。《论语》曾讲:“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②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7页。孔子认为基于血亲基础的父子关系是不应该怀疑的,否则社会将陷入尔虞我诈的境地。如果说孔子所认为的父子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础的话,那么母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人伦关系的源泉。而《三关排宴》恰恰就以伤害母子关系为前提,佘太君见到久别的儿子没有关心其生活状况,而是一味地要求“大义灭亲”,确实有点不近人情。“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此强势的正义能在多大程度上容纳和吸收普通民众的感受,才会真正落地生根?如果这种强势的正义越来越高调,越来越教条,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身心感受,那它就越加异化,日久势必为民众所疏离和抛弃。”③张炼红:《历练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第323页。这大概就是“大义灭亲”之类的戏曲流传的越来越少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