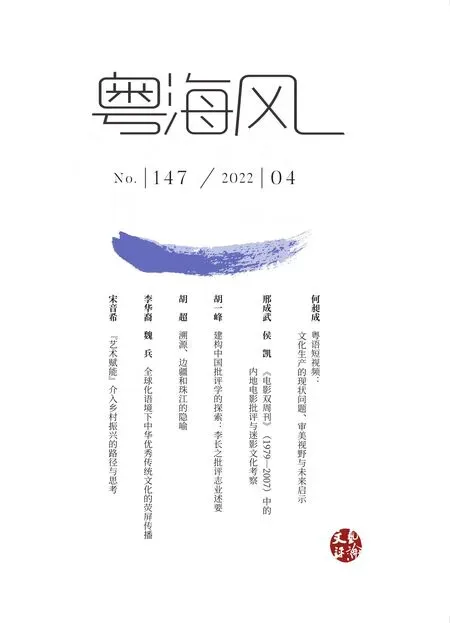电影《梅艳芳》的叙事策略与湾区文化内质读解
文/刘文昭
近期,随着电影《梅艳芳》的上映,关于影片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与香港文化,文艺界多有讨论与快评。香港人物传记电影这一曾历辉煌、渐趋式微的类型,再度成为文化市场的焦点之一。客观而论,现代电影技术为传统的传记文学创作开辟了全新的表现域。媒介的发展满足了大众的名人崇拜意识,运动蒙太奇结构则生动化了传主的形象传达。如论者所言:“强化个体意识、追觅多元价值所导致的英雄崇拜与理想期待,以及大众文艺繁荣所带来的传记电影热潮,使人类保存自身实录的文化行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1]而艺术家与影视明星的传记电影,因其历史呈现的真实性,及题材与媒介之间交融的娱乐性,更易在反映时代文化的同时被市场接受,《梅艳芳》亦如是。此一特质,也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关于艺术之情感功能的界说深相契合。《乐记》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2]名人的生平记述,实现了普罗大众的“观看”需要;歌舞的镜头演绎,丰富了观影情绪的艺术感知。由此,本文拟从电影《梅艳芳》的人物形象塑造出发,透析影片所体现的历史语境与时代精神,并由此解读粤港澳大湾区所独有的、兼具传统与现代性的文化内质。
一、人像之维:“主客叙事”的平衡
优秀的传记片,须实现“主体叙事”与“客体叙事”的和谐。叙事客体通常指传主本身,即影片所呈现的历史人物。作为艺术创作的传记电影,不应抱有纪录片式“绝对真实且完整”的内容追求;而作为叙事主体的主创,如何使影片在真实性之上,展现出普遍的人格精神与文化内蕴,自为叙事的首要目标。《梅艳芳》于此一维度的处理,可分解为有限的视点、肉身的聚焦、怀旧的虚构三方面。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电影首先追求的是“有限视点”的叙事伦理。传记电影中的“有限视点主义”,指“既不使用全知视点,也不假装影片所描述的人物形象是百分之百的客观无误,而是根据与传主密切相关的回忆、采访、讲述来引导观众认知传主”[3]。就《梅艳芳》而言,传主生活的时代距今不过数十年,与之关系甚密的亲朋故旧大多在世,且多是仍在活跃的公众人物。因此,影片在内容上不可能做到完整且真实,选择性的叙事视点尤为关键。作为梅艳芳传奇人生的起点,电影以温情的基调勾勒了梅家姐妹童年的演艺生活,刻意回避幼年飘零的窘迫与凄苦,从而表现传主坚韧且乐观的天性,亦追忆彼时港人之间粗放却真挚的情感状态。被迫修炼的“童子功”是梅艳芳出道时惊为天人的业务基础,而自幼形成的艺术追求、职业态度乃至姐妹间复杂的亲密关系,均伴随一生,且成为表现传主人格特征的核心要素。影片借唱片公司老板之口表达“慢歌是唱唏嘘”“快歌是唱反叛”的论点,“唏嘘”“反叛”恰是梅艳芳人生际遇与生命精神的总结;而“望着他唱,唱到他服”“不可以失场”的信念,也正是其要强性格的精准呈现。影片对姐妹关系一波三折的刻画,同样体现了性格冲突背后,梅艳芳与姐姐相互扶持、野蛮生长,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决心。由此,通过有限视点下的叙事策略,影片实现了其美学价值的表达。电影对梅艳芳生平的呈现可能并不完整,却符合大众期待中的传主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传记片就是“一种编导与观者必须自我伦理约束以达成某种契约的‘信用’体裁”[4],这种文艺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形成的默契,是创作优秀传记电影的前提条件。
其次,影片聚集演员肉身的类真性,以此传达“反物化”的女性人物形象。“肉身的类真性是传记电影的核心叙事元素之一”[5],在此可引申为以传主人格特征为基础,借由演员的身体表演所展现的欲望或生命能量。就此而言,国产传记片的表达往往含蓄而克制,此一倾向在暗合国人审美习惯的同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影片创作的自由。如电影《梅兰芳》对传主表演状态与情感关系的展现,与礼教相契却失于平淡,肉身表现的疏离难以刻画天才艺术家敏感多变的内心世界,故使影片留下遗憾。相较之下,《梅艳芳》对传主身体的描绘就显得适度。公司为新秀时期的梅艳芳进行形象设计,借由演员的身段及量体裁衣的过程,导演完成了客体肉身的聚焦。前往夜总会走穴时,梅艳芳驾轻就熟的歌舞展演,一颦一笑间征服了港、台、日三方观众。而“烈焰红唇”的舞台呈现,作为彼时娱乐圈的标志性演出,既是影片无法回避的环节,便在衣着、体态上大胆还原。上述片段中,演员的肉身虽是“被观看”的对象,但“被观看”本就是传主的主观意愿,是其人格理想的艺术化呈现。此外,在“跨国恋”描写中,影片通过外出约会、肢体接触、相互喂食等镜头,展现了如寻常女子的梅艳芳。彼时,娱乐明星的恋情如洪水猛兽,蔓延滋长的情愫并不能见光。但身体在情爱关系中的自然舒展,缓释了身处“禁忌之恋”的不安,讲述着传主真实的情感与欲望。由此,影片通过肉身的真实性表达,消解了女明星普遍存在的“物化”焦虑,使梅艳芳“香港女儿”的独立女性形象更为立体。纵观香港传记电影发展史,如《阮玲玉》《川岛芳子》《宋家王朝》《黄金时代》等传记片,均有针对女性形象的个性化展演[6]。
复次,影片引入纪实影像,突出其创作手法上“怀旧的虚构”。现代演艺明星的传记电影拍摄,在艺术上的重要维度,是舞台戏仿桥段与真实影像资料之间的关系处理。就此而论,从表演能力或期待视野的角度,演艺巨星的舞台风韵是任何模仿都难以再现的。因此,在影片中适度引入舞台表演的记录影像,无疑是推动客体叙事张力的必由之途。然而如何平衡记录与演绎的比重,使传记电影与纪录影片相区别,同样是叙事主体的重要课题。参考关锦鹏导演在《阮玲玉》中的处理,影片存在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的三条叙事线索:一是张曼玉所扮演的传主;二是阮玲玉亲自出演的默片资料;三是主创人员创作该片的幕后纪实片段。层次丰富、时空交错的结构更新了传记片观影的方式:记录与演绎的交织满足了观众的怀旧心理,同时也在提醒观者,往日的真实终究不再,暂时性的怀旧正是影片所提供的虚构满足。如张英进所言:“关锦鹏在展现怀旧的同时也揭示了怀旧的虚构性。”[7]落实在《梅艳芳》的艺术表现上,记录与演绎的镜头切换同样纯熟自然。一鸣惊人的自信果敢,大红大紫的风华绝代,承担社会责任时的坚韧与深沉,甚至诀别舞台上坚毅与不舍。客观来说,纪录原片的引入有效补足了主角王丹妮的青涩稚嫩;随片尾字幕同步播放的、梅艳芳本人的珍贵影像资料,更使观者的怀旧心绪久久难平,从而实现更为浓烈的情感表达与氛围烘托。
二、时代之维:香港的“自我反思”
美国学者卡斯滕就其电影研究提出的数据表明:以娱乐明星、艺术家为传主,或与之密切相关的传记电影,占据经典传记片总量的36%;关于该现象的缘由,他认为是传记电影具有“自我反思”的特征。[8]张英进继而阐释:“自我反思的最佳例证是明星表演。明星一贯是真实呈现历史的载体,而经典纪录片中的表演也成为建构‘社会共识’的工具。”[9]就此而论,梅艳芳作为20世纪香港演艺界首屈一指的女性艺人代表,亦被冠以“香港女儿”的时代标签;其生平故事的艺术性回顾,兼有时间跨度之长久、社会影响之巨大、集体记忆之深远等三个层面。由此,影片由记述梅艳芳生平而形成时代阐释空间,堪为2020世纪香港社会的一次“自我反思”实践。
首先,电影《梅艳芳》关于20世纪以来香港社会历史、文化氛围的呈现丰富而立体。六十年代歌舞升平的荔园、七十年代烟火蒸腾的大排档、八十年代群星璀璨的颁奖典礼、九十年代光怪陆离的夜场、21世纪初疫情之下沉寂肃杀的街道……凡此种种,既作为传主经历的背景嵌入,又为观者展现了往日不再的香港旧景。片中所述的历史事件及其电影语汇,不论是幼年歌女卖艺谋生,或是粤剧大师提携后辈,或是艺人受黑社会势力的威胁操纵。上述体现彼时“香港特色”的事件,既能唤醒亲历者的生命体验,又忠实记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历史。“90年代以来基于真实人物与事件的香港传记电影,具有香港社会历史‘影像民族志’的意义,以个体生命的历程参证香港的历史际遇……这些呈现香港文化形态的传记电影,也在无形中通过媒介记忆和价值建构,形塑香港观众对本土社会历史的认知。”[10]可见,社会历史的记载与再现,是传记片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梅艳芳》由此动机出发,在场景布置、事件考证等方面的不懈努力,丰富了时代精神的影视化展演,从而实现了影片作为“民族志”的独特价值。此一方面的基础固然是梅艳芳人生经历的传奇性,却仍需辅以精致的艺术呈示。
其次,传记片要展现传主在舞台背后的点滴,则能适度满足观者的猎奇欲望。演艺明星的生活细节,或不为人知或谣传已久,若得以搬演在大屏幕上,方可以此为认知途径,实现对偶像行为方式的模仿。总之,由名人效应产生的大众崇拜意识与猎奇心理,无疑是当下的文化市场中,传记电影所持商业逻辑的重点之一。此一方面,电影《梅艳芳》的演绎也是颇为丰富且多元的。影片开头,新秀梅艳芳初到录音室,录音师们以完成专辑录制的时间为赌注,她本人也极其自信地参与其中。这一情节本是为突显梅艳芳的歌唱实力,无意中却展现了颇具兴味的歌坛文化。针对梅艳芳的跨国初恋,影片用充分的时间加以表现,刻画了二人由相识到热恋再被迫分手的全过程。该情节实为传主“大姐大”形象的祛魅,细致呈现了“少女梅艳芳”的情感世界,既拉近了传主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又为彼时香港的国际化身份刻下注脚。至于轰动一时的“掌掴事件”,相关的传说一时间甚嚣尘上。电影虽省略了其背后盘根错节的黑社会背景,但对事发现场进行了具体生动的还原,并以此作为梅艳芳生命境界与人格理想的转折性叙述。综上,影片对时代风貌的展演绝非泛泛,戏剧化冲突的显现与丰富的细节刻画,能有效满足观者的期待视野;其基于“有限视点”的叙事策略,在观众对传记片“契约伦理”的体认中也得到理解。作为一部传主过世尚不足20年的传记片,已实属不易。
复次,影片借由对传主及其所处时代的缅怀,实现了公共记忆的追溯与文化创伤的疗愈。2004年,张国荣与梅艳芳二人兼具传奇性与悲剧性色彩的离世,是当时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亦是十余年间未曾消散的文化创伤。时至当下,每逢二位的忌日,仍会引起文化圈层的集体举哀。如论者所言,“创伤经验以及对创伤经验的感知和体认是由每个个体在地化的日常生活所体现的,但对创伤经验的呈现、表达和修复却有可能上升到集体或社会的层面,成为一种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11]客观而论,现代社会中的媒介记忆,对于文化创伤记忆方式的改变显而易见。“媒介更是已然摆脱了它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的束缚,成为逻辑自洽的主体。”[12]因此,对此类公共记忆的处理是否得当,亦是衡量该片艺术性与真实性的关键标准。影片就此选择了三个有代表性的事件:针对2003年困扰港人生活的“非典”病毒,时任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梅艳芳,决心举办一场“帮香港打气”的大型室外演唱会。导演忠实地展现了这一过程,继而传达梅艳芳强烈的责任意识与乐观心态。针对张国荣的离世,梅艳芳在极度悲哀的情绪中,仍选择疗愈伤痛。“唱着歌等咯”这句台词,便是导演想要表现的,传主与友人、与自己的和解。最终,病入膏肓的梅艳芳,势必要以舞台绝唱的方式与自己的生命告别。结尾处的《夕阳之歌》交织着记录与演绎,营造出如泣如诉、亦真亦幻的观影体验,观者对传主内心世界的共情达到高潮。由此,《梅艳芳》由传记电影的媒介方式,完成了文化创伤记忆的集体呈现、表达和疗愈,这符合共同情感的需要,相信亦是主创人员的初衷。
三、文化之维:“群体个性”的展演
关于“群体个性”的呈现效果,是同为传记文学的文本与影像,由载体生发的差异特征。不同于文本,“传记电影创作的个性主体是复数的,其接受过程也是公共性的……由于审美中介的公共化以及中介群体内部个性的调和,传记电影文本从具体的审美传达和个性展示上升为一种群体意志的实现和某种公共观念或美学精神的召唤,形成‘群体个性’。”[13]换言之,影片借由记述传主生平,所承载的绝非孤立个体的悲欢离合,而是集体性乃至时代性的精神文化。表现由民族性、地域性所致深沉的文化特征,值得优秀的传记电影为之不懈努力。由此,《梅艳芳》所呈现的文化内质,是影片进行人像描摹与时代追忆的深层动机,亦可看作粤港澳大湾区人民精神世界的具象表达。
其一,影片体现了大湾区文化拼搏进取的精神内核。20世纪下半叶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人民以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直面时代所赋予的种种挑战,以筚路蓝缕的姿态开创了个体与群体生活的新纪元。此一方面,更早接触西方社会的香港人民,率先形成了独特且强大的主体意识。如陈冠中先生所言:“我这一代香港人很幸运,继承了父辈传统中国人的功夫精神和流徙克难时期为了在殖民地生存被迫生出的实干心态。”[14]这种开拓进取的“香港精神”,于电影《梅艳芳》中多有体现。出道前的积极无畏,分手后的果敢坚毅,甚至面对死亡时的踏实与持守,影片对传主乐天性格、进取心志的表现一贯到底。诊断出喉疾被要求停演时,她以“我没打算听他”回应;事业陷入瓶颈流落异国时,“作为香港人,不那么容易认输”是她的心声;纵使面临死亡的恐惧,仍是以“嫁给舞台”的方式,为自己书写最浓墨重彩的悼词。应当说,拼搏进取的梅艳芳是影片着力塑造的核心形象,更是香港人对自身群体个性的恰当表达,体现了电影作为文化产品参与当代大湾区文化建构的努力。
本文选取了2008—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2008—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同时为了克服数据波动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所有变量数据均已作对数化处理。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其二,影片突出了大湾区文化宽厚包容的情感特征。从文化地理学的概念透析,湾区文化是以岭南文化为根基,融合中原主流文化、客家文化、侨乡文化,同时包容西方文化的多元兼容的文化。此一多元要素并存的文化格局,亦造就了其宽厚包容的情感特征。电影《梅艳芳》由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引起广泛的共情,传达其内在情感的包容性。与初恋男友交流时的语言障碍,被流溢的亲密情愫所弥合;面对性情古怪的无家可归者,传主留有余地的处理方式,使其性格中宽厚的一面尽致展现;收到年幼歌迷送上的礼物,纵使身心俱疲,仍报以真挚的笑容。由此,大众通过对梅艳芳柔情侧面的观看,完成了对传主情感特征的崇高认知。
其三,影片展现了大湾区文化感性世俗的交往方式。为梅艳芳传奇而短暂的一生作传,影片的整体氛围却不失温暖亲切,其重要原因在于主创人员为全片设置的感性、世俗的基调。由荔园、大排档、KTV等场景的设置可见,电影着重表现香港社会的市井气息,以此忠实还原时代风貌。关于影片的人物关系刻画,不论是传主交友时的义薄云天,与亲人的相濡以沫,对后辈的悉心提携,均带有真实可感的在地性,堪为彼时港人交往行为的缩影。自古粤港澳地区偏安岭南、远离政治中心,加之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发,城镇平民阶层的基础较为广阔。世俗化的价值导向与感性直接的交往方式,由此植根于大湾区文化的血脉之中。
综上,传记电影《梅艳芳》以其有针对性的形象塑造和情节刻画,忠实且精彩地呈现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香港社会及其时代精神的变迁发展,并由此表达了深层次的文化特征。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15],艺术所反馈的是审美性的社会生活,其接受美学的重点在于普遍且精要的文化体认。而好的传记电影是一面“更完整的镜”,其背后是“人类曲折前进的脚步,是社会由落后走向进步的声响,是克服异化、恢复人类本性的艺术的必然属性。”[16]在此意义上,《梅艳芳》由小见大、所呈现的大湾区文化内质,即是影片创作的核心价值所在。
注释:
[1]朱平:《当代传记电影的历史源流探微》,《电影文学》,2008年,第15期,第20页。
[2][15]胡平生,张萌译注:《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礼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14,719页。
[3]侯军,胡慧:《传记电影的人物形象建构》,《当代电影》,2016年,第1期,第45页。
[4]王成军:《传记电影叙事中的“契约论理”》,《电影艺术》,2009年,第5期,第87页。
[6]朱雁翎:《九十年代以来香港传记电影研究》,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6年。
[7][9]张英进:《传记电影的叙事主体与客体:多层次生命写作的选择》,《文艺研究》,2017年,第2期,第91,87页。
[8]G. F. Custen.Bio/Pics: How Hollywood Constructed Public History,New Brunswick,N. 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2,page 149.
[10][12]陈可唯:《香港传记电影的历史与身份镜像》,《四川戏剧》,2018年,第6期,第50页。
[11]赵静蓉:《文化创伤建构中的媒介记忆策略》,《江海学刊》,2021年,第4期,第227页。
[13]吕鐄:《简论传记电影文本真实性的三种维度》,《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158页。
[14]陈冠中:《我们这一代香港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
[16]曲德煊:《论传记电影的完整镜像》,《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