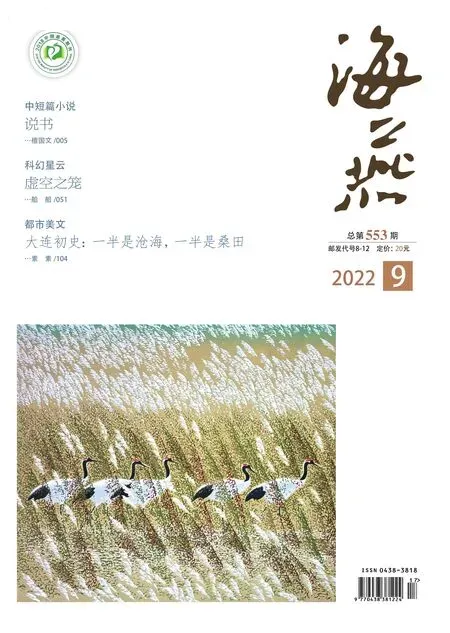思想者的怕与爱
——评张楚小说集《略知她一二》
文 陈 曦
我们依旧能在张楚的小说里读到先锋的余韵。当然,这种先锋早已经褪去了作为文学概念刚出现时那种轰轰烈烈的实验特质,在张楚的小说里呈现出了一种“铅华洗尽”的质感。其光泽与温度无关那些技法上更接近于故弄玄虚的“术”,而直接逼近思想与精神层面的“道”。换言之,我们在《略知她一二》中看到了最传统的写法,与最新锐的表达。这或许是张楚作为一名作家最本质的“执”——以思想者的站位去观察,去思考,去焦虑,去找寻常态背后的意义与针对无解的破解之法。
坦坦荡荡地迷惘
毫无疑问,张楚是讲故事的高手。小城公务员的生活给了他热烈诡谲又朴实真挚的人间所见,他的写作犹如酿酒,生活的食粮在他视野的酒瓮里不断发酵,经由不懈的思考和无数长夜的积淀成为了热辣而疗愈的佳酿。类似城乡接合部的小镇生活是张楚最有特点的“酒种”,其令人念念不忘的“回甘”在于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追探。批评家张莉曾一语道破张楚创作的异质性或言其当代价值:“张楚是一位从不以小城镇为小,也从不以那花花世界为大,不以传奇为传奇,也不以日常仅为日常的小说家。”确乎如此,张楚着力要打开的是不同的生活纵深背后,处境迥然相异的人们那带有永恒色彩的共性内容,所以无论他的故事多么“先锋”,都让人感到真实,因为他指向的是活着的本质。
《略知她一二》在张楚的众多作品中又是不同的,小说集中所收录的十篇小说是张楚创作谱系中带有明显“迷惘”特性的小说。这些小说没有作者其他作品冷峻,却保有了一种举重若轻的荒诞,恰到好处的隐痛。我们能读到作者投影于主人公身上的那种日常又久远的迷茫,能在故事并不算惊涛骇浪的起伏波澜里沉浮漂荡,小说所着力的就在这样的讲述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迷惘的“场”,让读者感同身受,由此让每一个直关“个体”的现实回味深长。
每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迷惘的。《草莓冰山》中那个渴望到大城市去的商店售货员,《曲别针》中那个具有工人、诗人、小商人和“曲别针工艺师”多重身份的刘志国,乃至是《略知她一二》中那个阴差阳错与宿管阿姨偷情的导演系学生……他们都是迷惘的,身份不同,处境不同,却有着类似的情绪。他们对自己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未来有着强烈的憧憬,却也无时无刻不在憧憬的破灭中自我攻伐,他们面对冰冷甚至是吊诡的现实,充满迷惑,混沌着参与,犹如风中的芦苇。作者却似乎并不打算“解决”这些迷惘,他以一种坦坦荡荡的形式让迷惘本身产生意义,即一种直面的“破”与“立”。当文学不再伪饰,它才更加贴近生活,无常便是俗常,而迷惘也未必只是痛苦,还有一种韧性的力量,其根源仍旧在于心存愿想,心存一种对价值与意义寻找的我执。
所以张楚让这些迷惘的代言者于生活中撞破那些同样是芸芸众生的“秘辛”,由此揭开一重更加苦痛的现实,哪怕这些现实如此的离奇,如此的动魄惊心。或是一个经历了“买”与“卖”的东南亚女子(《草莓冰山》)或是保存着爱女心脏的农妇(《略知她一二》),抑或是为了脑瘫儿子而兼职跳钢管舞的二百多斤的医院护工(《野象小姐》),这些被“撞破”的秘密,当然没有让迷惘的“主人公”如同注射强心针般振作起来,却无疑让他们在一种近似悲哀、庆幸、心痛与释然的复杂情绪中继续一日三餐地“过生活”。这些小说无一不是在写不幸,却又没有任何一种不幸让人心如死灰,反而是让人一声长叹后淡忘了所找寻的“意义”。他在诉说一种“平常”,一种波澜不惊的哲学。这种小说的味道或是落笔的力道,让张楚的小说具备了一种永恒的智性的价值,他确实太懂得人生了。
“她”,来了又走
女性,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最闪亮也是最沉重的关键词。小说中出现的“种种女性”和作者着力呈现或天成于文本内外的“女性种种”,都是令人嗟叹的。这让我们在地母般的丰饶里看到现实给予女性的贫瘠,让我们在肉体与欲望的缠绕中看到命运施加给女性的冷峻。
《野象小姐》是一篇令人读之难忘的小说。一副被人嘲笑的巨大身躯以一种喜剧演员般的登场形式出现在了妇癌病房,不顾肮脏与鄙夷,坚持着捡拾塑料瓶的“游击”。她的存在让沉重压抑的病房多了谈资也多了一丝人间气息。她总是以一种置身事外者又入乎其内的姿态参与到四个失去乳房的女人们各自的生活话语中,以朴素而真实的拥抱,口无遮拦的嬉笑,让病房有了一束光。然而,这又是一道如此沉重的光。当“我”被野象小姐约出去看她的夜场表演,看她在众人审丑的“欣赏”中自信的展露舞姿;当她一定要请“我”吃西餐,由此我看到她那没有父亲的脑瘫儿子;当“我”出院后在无聊的电视广告中看到那个做完假药广告然后在电视上滑稽舞动的巨大身躯时,那束大大咧咧、庸俗无比的光才彻底照亮了生命的全部暗夜。是的,沉重的光,那样滚烫。她从没有想过“疗愈”自己命运的伤,她只是努力活着,然后为又一次打败了困顿而咧嘴一笑。“说实话,那是我漫长、卑微、琐碎的一生中看到过的最动人的笑容。”那笑容,那光照亮的又何止是一个“我”?又有谁的一生不是“漫长、卑微、琐碎”的?这个来了又走的女人,也关心过灵魂的重量,只是她与祥林嫂那样不同,她的救赎,来源于她的本身,她自己牢牢把握住了那轻如气息又重有千钧的灵魂。
在《略知她一二》里,那个其貌不扬的宿舍管理员如此短暂地出现在二十岁的“他”的生命中。她们的偷情犹如彼此的慰藉,一者关乎迷惘的青春,一者关于逼仄而惨淡的生活。直到“他”发现那个冰箱,发现那颗早已经无法跳动,成为了永恒伤痛与爱之纪念的心脏。他们彼此,落荒而逃。短暂的相逢以及那以情事铸造起的乌托邦,给了她情感的抚慰与精神的宣泄,在失去爱女的痛与不幸生活的消磨中,她得以暂时感受身体与欲望的在场,让她忘了日子狰狞的面目。然而,毕竟这也只是金风玉露,是水月镜花。“我们这些人呢,就是沙滩上的贝壳,谁知道会被海浪冲到哪儿去呢。”确实,他只是“略知她一二”,在他漫长的人生里,这段插曲只能是往事不堪回首中一个短暂的片段。然而,他却在最为无所事事的迷惘青春里,切肤地感受到了,生活与宿命。
事实上,无论是《曲别针》里被杀害的卖淫女,还是《夜鸟》里住在楼上捉摸不定的女孩,甚或是《草莓冰山》里“小东西”那做皮肉生意的母亲,她们都以过客的形式出现在主人公人生的某个时段。无论是激烈的刺激还是古怪的相伴,抑或是只作为一个新闻般事件的参与者,但毫无例外,她们背后都有着一个生活的黑洞,那些秘而不宣的沉痛的事实被主人公探取到了些微细节,然后澎湃地冲击到了自己的人生。似乎只有《水仙》是不同的,作者反其道而行之,让“她”目睹了“他”。突然出现在她生命里的男人魔幻又真切,在一个闭塞的单调的历史时空中,呈现出了一种烂漫的幻想,尽管这幻想最终只能被一把镰刀割碎。但是这神话般的叙说是否出自现实?会否只是“她”在迷惘孤寂中幻想出的场景与若有若无的爱情泡沫?那个忽然被打碎,消失于凭空的,也许是她一生中最后的浪漫。“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妹妹,突然出现,突然消失了,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日子还长着呢!”是啊,亲手砍向这浪漫的人说的自然没错,日子还长着,这漫长的琐碎的不必急于找意义的生活,指向所有人。就像《夜鸟》中那个即使“看破”了生活也还是会在深夜被“她”说服去救治野鸟的男人所言:“意义本身就是指的怀疑的伪命题。”但是这伪命题却一直被人津津乐道,苦苦寻找。
在小说中,这些女性总是“来了又走”,总是以一种强烈的撞击和久不消散的余震让读者再难释怀。而“她们”的命运也便这样被深深地烙印在了读者脑海的深处。作者似乎是着意以“虚妄”抵达“真实”,让那些来了又走的女性犹如出走的娜拉,永远被人挂怀。
思想者的怕与爱
张楚写的永远都是生活。确实,“生活在意识觉醒的年代是令人振奋的事情,它可以使人困惑不解、迷失方向、无所萦怀”,也当然地给思想者以追探、辨别和求索的契机。生活本身所构成的意义,往往只在巨大的沉默背后,人们依旧在柏拉图的洞穴里,为着自认为真实的世界与人生的影像而陶醉抑或苦闷。而作为观察者与思考者的作家,却必须冷静地看清这些生活的“影像”,以及其背后的本相,张楚亦然。作为思想型而非抒情型的作家,他在《略知她一二》中流露出了出于自我又不仅观照于自我的“怕”与“爱”。
庸常,是值得畏惧的。这是张楚用文字表达出的最真切的呼告。就像《草莓冰山》里那个作为旁观者的商店管理员,他有强健的体魄和一颗充满了同情的柔软的心,然而却也在庸碌无为中慢慢于日子里“腐朽”,直到目睹邻家那惨淡而激烈的生活,才让他决定出走,去打破,哪怕一无所获。又如《关于雪的部分说法》中那个老实平常而又充满了文艺气息的丈夫,如若不是颜路的“闯入”与阴差阳错间目睹了妻子的出轨,他依旧不会感受到庸常生活对人的腐蚀与压迫。还有《略知她一二》中在日子里混沌的艺术系学生,《水仙》里那个被时代洪流淘洗成套中人的女孩,《蜂房》里那个对自己的残疾已然习以为常到麻木的中年男子……他们被冠以“命运”和“常理”的庸常慢慢解构,成为了面目模糊、喜悲不清的“单向度的人”。
作者就是因为对这种庸常的“怕”,才让他们目睹甚或是参与到一场“事件”中,短暂地卷入别人的生命,碰撞出对于苦痛的敏感,由此激活麻木的神经,闭合的灵魂。这些事件都是带有明显先锋意味的。《关于雪的部分说法》中的颜路因为爱而不得,选择越城杀死自己的爱人,直到他“收藏”的人体器官被发现,才在自我营造的喋喋不休的谎言中清醒过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略知她一二》中宿管安秀茹背负着女儿死去的沉痛事实,在波澜不惊的生活中默默饮泣,直到那个搅乱她“常规”人生的大学生情人发现她冰藏在冰箱中的女儿的心脏,才在被爱的幻境中转醒,消失在人海。还有《水仙》里那个真幻难辨的鱼仙男子,直到镰刀砍到自己身上才结束了漫长的优美的舞蹈,在打破界限的陶醉中离去,成为了一个疯妇口中悲伤的传说。尤其是《穿睡衣跑步的女人》中那个一心想自然流产的马小莉,她厌倦了工具化的生产,更恐惧于一个个女儿被送到“富贵人家”,她选择的是疯狂干活儿,甚至是不断奔跑,冲刺,成为了众人眼中一道疯癫的带有田径天分的虚影。
这些故事都是那样的令人惊诧,似乎这绝不是我们身边的生活,却又那样逼真地指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这种先锋是节制的,在若即若离地讲述中,让人难以质疑其真实性,现实永远比虚构更离奇,但虚构与现实却在先锋意识中成为了表意的“一体两面”,在张楚笔下,先锋,即是对庸常的反抗。
当然,《略知她一二》里不单单体现张楚作为一名思想者的怕,其内里有着一份柔软,一份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爱。如若不是对生活有着一份“爱”,便不会对庸常表现出“怕”;如若不是对遭逢苦楚的压抑者有着一份感同身受,便不会将那些“撞破”写到无常的极致。归根结底,张楚的写作是在“大道”上行进的文学创作,他从未忘记辛辣的背后应是同情的体察,撕开的目的是心灵的疗愈。文学本应如此,只是太多的文学从业者,忘记了这个闪亮的基石。因为有着这份“怕”与“爱”,张楚这位酿酒师,才以文字的佳酿让我们在辣与痛里品尝到了一种希望的芳香,然后犹如酒徒般,在故事里沉醉,生活里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