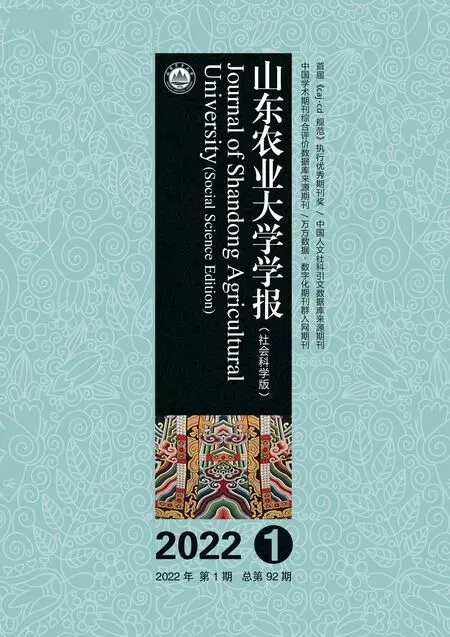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疏解《论语·八佾》结构与逻辑,走进孔子精神
□董雪霏
[内容提要]所谓结构,即是将《论语》的独立篇章作为单元,探索其内容主旨的“结构形制”;所谓逻辑,即是将《论语》的独立章句作为单元,探索其意义背后的“逻辑关联”。通过疏解《论语·八佾》的结构与逻辑,得出“原点”、“毁废”、“维护”三层意象。推导出“礼”之后的“义”与“仁”,由此走进真正的孔子精神,以提升我们的家国认同与文化自信。
《老子》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P25)可谓结构形式与内容承载的关系之论。观察早或晚于先秦时期的许多独立经籍,均有着不同程度的“结构与逻辑”安排。比如,《诗经》的“风雅颂”呈现出整体的结构安排;《春秋》及《传》遵循着整体的时间叙事;《易经·序卦传》依从着整体的逻辑铺陈。《论语》被前人称为“《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是否也有“结构与逻辑”安排?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尝试着对《论语》的结构进行了探索。目的在于,重新挖掘其深意和新意,更益于接近孔子精神,利于学以致其道。
探索的原则是:以《论语》本身的内容为基色;以探寻章句承载的意义—显现的和隐含的—为主线;以“著其明、彰其显、探其赜、索其隐”为目的进行疏解。例如,《论语》中,子贡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2](P4)之问,夫子答以:“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引《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试探对夫子之答的理解,夫子复答以“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2](P11)之问,夫子答以:“绘事后素。”子夏复问:“礼后乎?”夫子欣慰地复答:“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上述两则问答中,我们明显的看到,子贡与子夏所问及夫子的所答,均不是字面意义的“骨角玉石的切磋与琢磨”“美人面容的巧笑与目盼”,而是字面背后隐含着的另一个维度的意象。
再如,王孙贾有“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2](P12)之问,夫子给出“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之答;冉求有“夫子为卫君乎”[2](P34)之问,子贡借“夷齐怨乎”代问,夫子给出“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之答。子贡从“夷齐让国”与卫君“父子争国”的比照中已得出“夫子不为也”的判断。两章问答中,王孙贾与子贡均只字未提“卫君”(卫灵公与卫出公)二字,二者却都能“以心得意”。上述列举来自《论语》本身的章句启发我们,解构《论语》当不可拘泥固守于“以言求迹”。设若编纂者非“以形赋意”而随机编排,也就失去了“编纂”和“优选”的意义。依此推论,编纂者所拟之“形”自然有结构设想;所赋之“意”理应有逻辑安排。
一、梳理《八佾》篇的三层结构意象
纵览《八佾》篇,可以清晰地发现,“礼”是核心主旨。其一是,强调“本与末”“表与里”“先与后”的对立统一;二是,主线围绕“上位者”与“下位者”两个主体展开,显见的是,以季氏为代表的“上位者”大多违礼失序,而以孔子为代表的“下位者”却全力在维护和守护着“礼之本”;三是,篇首的“失礼”之叹与篇尾的“尽善尽美”之期许形成呼应,从而触发时人及后世启发。
通过疏解《八佾》篇的“赋意”安排,得出本篇有三层结构意象:第一层为“原点”,第二层为“毁废”,第三层为“维护”。《八佾》篇每一章都能放入这三层意象,分为一章多意和一章一意,但整体传递的信息一致。
所谓“原点”层是指,古代圣王制定的礼乐典章制度类,虽经朝代更迭有所“损益”,但其轴心性和价值核心未变,体现在:“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3](P107)背后指向“天下平”,如“夏礼”“禘礼”“告朔”“八佾”等。《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4](P1)因此很多学者认为“礼”与早期巫文化有关,周公的“制礼作乐”就是把上古巫文化转化为适应周王朝的文化传统。李泽厚说:“‘德’和‘礼’是这一理性化完成形态的标志。孔子释‘礼’归‘仁’,则完成了内在巫术情感理性化的最终过程。”[5](P26)无论是巫文化时期还是史文化时期,物质条件发展,社会环境变化,但人性未变,人作为群体中的一员而生存的状况未变,因此我们回到先秦典籍查看有关“礼”的论述会更加清晰其本质含义。
《左传·隐公十一年》有一句经典定义:“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6](P88)“礼”是为了“经”“定”“序”“利”。经典的奥妙在于总是以简约精辟的几个字把亘古不变的道理说清楚,词约义丰。《左传·文公七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6](P629)“德”、“礼”、“义”在不同情境语境中含义不同,但背后的价值指向是一致的——为了人类和谐共存!如荀子所言,“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7](P300)人,既存活于群体之间,又有不同的欲求,容易产生争斗,所以靠“礼”去维持一种秩序与和谐至关重要。“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3](P885)一个有德行的人,其行为结果是可以预知的;一个守礼的团体或国家也必然是和谐向上的。章学诚说:“孔子曰:‘吾学周礼’,学于天也,非仅尊周制而私周公也。”[8](P134)我们仰头观察宇宙会发现,宇宙一直处于一种和谐稳定的状态,日月星辰包括地球在内都有自己的运动轨迹,因此人类自古就通过观察星象建立了天文学。先秦典籍中的“天”有“人格天”和“形上天”两种内涵,无论哪种,给予人类启发的都是其自然之态。既然“礼”学于“天”,学的自然是天地运转的秩序。效法天地在《论语》中比比皆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设若统治阶层,仁德不足又不遵循礼法,其后果如何?由此而引出结构的第二层——“毁废”层。所谓“毁废”层是指,统治阶层德不配位僭越礼制,有致“天下倾”之势。已经“毁废”的,如:“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正在“毁废”的,如:“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行将“毁废”的,如:“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春秋时局衰颓日甚,源于当时为政者的“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9](P61)这段描述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战事频繁、民不聊生的局面,解释了孔子作《春秋》的发心,还把孔子作《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治平放在一起,说明这三件事对中华民族的重要价值。
通过《谷梁传》记载的春秋后期的一个事例,可见当时政治局面的荒诞性。鲁成公元年,“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侄子处台上而笑之。”[10](P412)曹国、晋国、鲁国、卫国的大夫一同出使齐国,正好四位大夫身体有些缺陷,结果齐国在国内找了四个对应有相同身体缺陷的车夫接应,四国大夫恼羞成怒,齐国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9](P88)作为大国,不仅没有大国风度担当,还如小丑一样捉弄戏耍,只能走上自毁之路。在《论语》其他篇章中也展示了春秋晚期的倾颓之势。第二篇《为政》有四则“问孝”连在一起,而“问孝”四人中,孟懿子与孟武伯为父子关系,子游与子夏是同学关系,且并列“孔门十哲文学第一”。可以想见的是,这四则问答断然不会发生于同一时间、同一空间,而呈现的文字却有序的映在眼前。且夫子所答之意,为前两者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而对后两者则更具象。第一则是“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第二则是“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关键在于“疾”,这个字指的仅是身体的疾病么?联系这两则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会发现孔子之意是谴责三桓,孔子告诉孟武伯,如果不去守礼,继续以下犯上,你们家族会衰落,传达的寓意与对孟懿子说的“无违”一样。《论语》中还有一则也明确表达了孔子对三桓的谴责:“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国君不修己以敬,臣子以下犯上,这座由周王朝建立的金字塔逐层坍塌,因此引发了孔子的忧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不仅忧虑于当世,还怀虑于将来的“十世”与“百世”。“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由是引出了第三层——“维护”层。所谓“维护”层是指,针对当时的“礼崩乐坏”,孔子极力维护和修复。行为性“维护”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言语性“维护”如:“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防御性“维护”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如司马迁所言:“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11](P2845)事实并非真相,事实所意味的才是真实的,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还是“存”与“继”,史学的目的是为了预见未来、指引未来。孔子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作史书不仅仅为了记载史实,得出规律性认识,更为了导向“德”。
孔子对于上位者的规劝主要在一个“正”字。《颜渊》篇中有三则“季康子问政”紧排在一起,孔子依次回答,“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位者自正其身,下位者自然会归顺,“近者悦,远者来”。孔子对臣子,即士大夫阶层的培养是多向度的,体现在他对弟子们的日常教学中,当然无论《论语》中他与弟子们谈论什么都是围绕为政展开的。《子路》篇前三则有着巧妙的结构安排,较难发现,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疏解。三则依次引出“问政”之“三先”:首章,夫子告之子路,先亲“劳之”,尔后“无倦”;次章,夫子告之为季氏宰的仲弓,先让部属(有司)尽职守,尔后“赦小过,举贤才”;三章,子路设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夫子则从为政“邦国”的视角答之以“正名”为先,尔后“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安顿”。三者之“先”,一是为政的地理空间有递进性,二是为政的关键,由“亲劳”递进到“让部属”,再由前两者的“行为形态”而递进到“正名”的“意识形态”。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变”在孔子这里非常重要,也很难掌握,多数人可以做到谨遵规则,很难做到随时而变。因此多向度培养弟子从政,使弟子们涵养仁心又能守经达权,是孔子为了维护周礼、为了形成理想的政治蓝图所做的志业。从宏观视角审视《论语》时,会发现前十篇未出现一处“问政”,而后十篇却多达十几处“问政”,并相对集中于《颜渊篇》和《子路篇》。值得玩味的是,弟子已明确“从政”者,又排在“问政”之后,且集中于后十篇中。整部《论语》有着:前十篇寓“生”,后十篇寓“成”之意象,总体呈现出“生成”契应“春秋”之格局与气象。
二、疏解《八佾》篇的逻辑“赋意”安排
《八佾》篇共二十六章,我们以每章为单元,试着从首章到末章连成一条逻辑义理线。
首章“孔子谓季氏”,开宗明义批判季孙氏违礼,滥用天子之乐。《祭统》云:“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次章“三家者以《雍》彻”,由一家僭越扩展到三家僭越。周盛守礼乐,周衰失礼序。三家“离礼”、“越乐”,皆因不守“仁德”,因此引出第三章的孔子之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仲尼燕居》云:“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游酢曰:“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其如礼乐,何哉?”[12](P36)没有仁作为礼乐之本,礼乐则成为了贵族彰显身份、消费权威的工具。因此第四章“林放问礼之本”,本立而道生,位尊者之守,却成位卑者之问,孔子赞叹“大哉问”。知本无君也明,舍本有君亦晦,衔接第五章“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此章历来解法诸多,程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越,反无上下之分也。”这种解释太过牵强。尹焞曰:“孔子伤时之乱而叹之也。亡,非实亡也,虽有之,不能进其道尔。”“伤时之叹”是肯定的,《论语》中孔子的感叹无不是针对当时礼崩乐坏、大夫执政所发。为何诸夏之君“亡”还超过夷狄之君“有”?因为诸夏有“礼”。释慧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12](P38)这种解释是比较切合历史背景及本篇主旨的。虽然,有君者未必有“本”,无君者未必无“质”,但春秋晚期就是层层僭越、战争频繁时期,而“礼”就是维持世间秩序的法宝。季氏们正在“进行”的,正如同一铲铲将诸夏“礼之大夏”毁掉,则将诸夏引向无序,引向野蛮,引向夷狄。
季氏仍未收手,由“室内”走向了“室外”-引出第六章“季氏旅于泰山”。马融曰:“旅,祭名也。礼,诸侯祭山川在其封内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礼也。”[12](P39)林放尚且知道追问“礼之本”,而贵族们却带头僭越礼制,倘若泰山有神,真会受享么?《曲礼》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季氏们践踏礼乐,引起社会动荡,导致天下滑落到崩裂边缘的原因只有一个字——争!由此导入第七章“君子无所争”,君子内心是不争的,即使形式上争,也用射礼表现。《射义》云,“失诸正鹄,还求诸身”,“射仁道也,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老子云:“惟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先秦经典传递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这些正向的价值观也促成了中国人外柔内刚、谦逊守敬的优良品质。此章所传递的信息与《中庸》也一致,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季氏们所言所行不是君子,只重礼乐形式,偏离了“礼之质”,第八章以一则“诗经”解答了何谓“礼之质”。子曰:“绘事后素。”此章也可以看出孔子日常教学的灵活多样,以及对《诗经》的体悟极深。朱熹曰:“素,粉地,画之质也。绚,采色,画之饰也。”[12](P40)礼为表,其质则为忠信恭让。自夏、殷之后,如季氏等当权者皆因重表亏质,渐渐至“礼之本”毁废,故不足征,紧接着第九章“文献不足故也”。此章也是“文献”的出处,原义为“典籍与贤才”,《中庸》云“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弗从”。自二代至“不能征”之时,三个东西渐渐丢失了,一是丢了礼的“形与行”;二是丢了礼的“文与闻”,三是丢了礼的“献与线”。“不能征”正是因为“空对空”,能征应是“实对实”。为何不能“征”?透过下面的“镜头”便可窥视一二。第十、十一两章,一是“禘自既灌而往者”,一是“或问禘之说”。孔安国曰:“禘祫之礼,为序昭穆,故毁庙之主及群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灌者,酌郁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后,列尊卑,序昭穆。而鲁逆祀,跻僖公,乱昭穆,故不欲观之矣。”[12](P40)鲁文公时,举行祭祀先祖的禘礼时,把其父僖公排在闵公前面,僖公是继承闵公当国君的,因此这种行为违礼,因此孔子曰“吾不欲观之矣”。“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事物从本始上乱,其后果一定会乱,夫子“不欲观”的原因恐怕在此。与下章谈论“禘之说”孔子回答“不知也”一样,一是为鲁君讳,二是传达了礼之核心,在于内心有敬,禘礼在于彰显祖先的功德,强化源头之“序”。
孔子对于鲁君的所为,深表遗憾,因其内心“无祖、无神”,引出第十二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范祖禹曰:“诚为实,礼为虚也。”[12](P44)内生之敬,缘于祖先神灵的“功与德”、“恩与情”。万不可因为看不见,就只媚眼前的“功利”之器,因此第十三章为“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卫国大夫王孙贾暗示孔子奉承自己,可满足你的要求,孔子以“获罪于天”回应。夫子不舍本逐末,不苟且眼前利益,并在第十四章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追求,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所以“郁郁”,其核心在于“从二代”。刘宝楠云:“夫子此言‘吾从周’,是据鲁所存之周礼言。”[12](P45)“礼”需要从和守,需要维和系。第十五章为孔子所做示范,“子入太庙,每事问”。“敬慎谨”尚不足以守得住,况非乎?礼贵在守,不在“知”。孔子所言所行的背后,也不是拘泥于“守”或“知”,而是“礼”可以维系天下得治的价值指向。因此第十六章为“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说文》:“科,程也。”围绕“射礼”,文献学家们有诸多探讨,如惟大射有皮,宾射则用采侯,或者古经师相传指第三次射而言。我们诵读《论语》,自然要学习孔子的治学精神,就像体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寓意一样,把重心放在文字背后传递的核心信息。此章传递也跟《中庸》的“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类似。联系上章可知:太庙之礼,重守不重知;乡射之礼,重的不重贯。诸侯比“力”而争,偏离了天下得治的初心,导致周衰。此章,“力”为表,“的”为里,重里不重表,无里表不存;第十七章“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贡所为,将导致“无表里不存”。郑玄曰:“牲生曰饩。礼,人君每月告朔于庙有祭,谓之朝享。鲁自文公始不视朔。子贡见其礼废,故欲去其羊。”[12](P47)礼以羊存,羊以礼附;礼重羊轻,去羊礼废。大家都不守礼,致使礼废。而尽礼者,反而显得在谄媚。
紧接着第十八章“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上一章君已失礼,本章表示臣者不可再失礼。《论语》言“礼”的专篇是《八佾》和《乡党》,孔子在《乡党》篇里在朝为君办事时动作之严谨,态度之恭敬令人动容,但《乡党》篇也被诸多学者质疑摒弃。“言谄”现象,说明大多数为臣者未尽礼,究其根源,还是为君者未达礼在先。因此第十九章定公问君臣之礼,孔子答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三桓控制鲁国已久,顽疾已固,君臣之间纠葛颇深。孔子认为君臣之间要掌握平衡,是相互关系,而不是“一头热”。这道理看似简单,但真正体悟并付之实践难之又难,我们所接触的上下级关系很多都是命令式,很少有真正的沟通交流乃至尊重,这也是《论语》从古至今诵读不绝,引人入胜的原因。第二十章“《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学者从乐篇去解读,认为“乐而不淫”指《关雎》《葛覃》,“哀而不伤”指《卷耳》。大多学者把此章抽离出来,从纯粹赏析《诗经》的角度解读,如果抱有《论语》有结构与逻辑的视角去理解,此章与上一章是紧密联系的。孔安国读出了此章的气息,曰:“言其和也。”[12](P48)本章主旨为“和与正”,君臣要和,目标为正,只有双方“不淫”、“不伤”才能得治。钱穆说:“孔子言仁常兼言知,言礼常兼言乐,言诗又常兼言礼,两端并举,新境界。”[12](P76)其实“礼乐”是“仁”的载体,无论“礼乐”还是“仁”,价值指向是一致的,即“大道之行”的和谐画面。而下面两章,主要讲为臣者也要起到应有的作用。“宰我”和“管仲”,分别在言语和行为上,都失“正”了。首先第二十一章“哀公问社于宰我”,鲁《论语》为“问主”,古《论语》为“问社”。《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无所依据,孝子以主继心焉。宗庙之主,所以用木为之者,木有终始,又与人相似也。”孔安国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宰我不本其意,妄为之说。”[12](P52)三代所取其木,均以图朝代长久,而非宰我片面理解的“古者戮人于社”,因此夫子责之。或许哀公想得到控制三桓的依据和声援,而宰我之答投其所好。夫子责之在于:国家治理为公,投其所好为私。如朱熹云:“孔子以宰我所对,非立社之本意,又启时君杀伐之心……”接着第二十二章“管仲之器小哉”,是为臣者在“行”上有失。管仲是唯一一个在《论语》中被孔子称赞“仁”的人,原因是“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但作为臣子,管仲有“三归”“树塞门”等行为还是违礼,违礼必然造成动荡不安。“三归”自古有多种解法,可能韩非子解释为三处房宅更妥帖些。君臣各行其“道”,且行且远,导致天下失序、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是君臣不能“合和”。因此,引出第二十三章孔子阐述的理想治理模式,即“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此章诸家基本都解释为谈论音乐,我们注意前面背景是“子语鲁大师乐”,孔子一向谦虚好学,怎么会以告知的态度对乐师说明音乐的理想模式呢?此章也跟孔子讨论“诗”一样,含有寓意。“翕”是聚合的意思,“纯”是和谐,“皦”是音节分明。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的背后依然服务于治理的旨意。实现治理成功,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君臣先“合”——翕;过程中各守其职,还要“谋其政”——纯;停留在“谋其政”还不行,还要“有成效、出成果”——皦;停留在成果上还不行,还要有延续性——绎,这样才算“成”。本篇至此已接近尾声。从现有的“居上位”者所为来看,离这样的要求相去甚远,至背道而驰。天下无道久矣,时代需要“醒”者,时代需要“木铎”,第二十四章为“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值得玩味的是,处于政治中心的季氏们违礼背道,而处于政治边缘的边官仪封人却从夫子身上看到了天下重归正道的希望。两千多年来,无论时代如何跌宕起伏,无论朝代如何升平衰微,夫子的“木铎”之声都环绕在天地间。“木铎”之声召唤的是“尽善尽美”,因此第二十五章为孔子谈论《韶》与《武》。《韶》和《武》是反映“朝代更迭,土地易主”的印记,其共性在于“尽美”,不同在于《韶》尽善《武》未尽善。孔安国曰:“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12](P53)“尽美”指内容上均秉承了“德”;“尽善”指形式上“舜绍尧致治”、“圣德受禅”;“未尽善”指形式上武王“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让而得。”[12](P54)“德”体现在为民上,上一篇讲到,“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礼,有耻且格”,夫子心目中一直装着民。最后一章为整篇点睛之笔,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反观夫子生活的时代,无序而乱,是因为居上者“失德”。刘宝楠认为:“‘居上’者,有位者居民上,礼乐所自出也。‘为礼’‘临丧’,并指居上者言之。”[12](P55)居上者“守”着三不,已无希望,孔子只能发动另一个阶层培养之,来寻求天下归道。
三、走进真正的孔子精神
《八佾》开篇,便描述了处于权力中心的季氏们,肆无忌惮突破底线的违礼背道;而在篇尾,处于权力边缘的“封人”却道出了蕴含着力量、包含着希望的警世之言——“天将以夫子为木绎”。面对当时的时局,相信有许多有志之士向夫子讨要过救世“药方”,耐人寻味的是,编纂者却独取边官“封人”之语置于篇尾,这本身就体现了天下有道的希望之种,已根植于夫子弟子们心中,编纂者们也将藉着《论语》以承孔子精神,从而将希望与文明的火种传给后世。
我们将孔子精神概略为“一个旨归、两个向度、三个德举”,即:孔子精神的旨归是家国安定、社会安稳、黎民安顿;孔子精神的影响投射到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孔子精神的体现彰显于培贤育士、周游列国、定制明章的三个盛德之举。这里,将主要围绕孔子精神的旨归加以浅论。
《论语》记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吴国居高位的太宰将夫子定位为“圣者”,他的认知里“圣者”不应该如此“多能”,“多能”属于鄙事者,于是向夫子最亲近的弟子子贡寻求答案,子贡肯定且自豪地认为,夫子的多能来源于“超验”的上天,同时,上天又附带着将“多能”赐予孔子。可是夫子却答以“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少也贱”而非“少也贵”,夫子之答,跟他少年时期所遭遇的父母早逝、家族式微、世局纷乱有很大关系。为了生存,年少的孔子必须得学会社会底层的“鄙事”技能,且只掌握一个“工种”的“鄙事”还不行,必须得“多能”才能填饱肚子。这无疑让他对底层百姓的生存有了充分的体悟。以已推人而“哀民生之多艰。”“仁”的种子也从此根植于心中。孔子的一生,适值“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天下失序期。据《中国古代战争辞典》春秋二百多年间发生700余次战争。诸侯纷争、大夫分权、陪臣执国的乱象,无限地挤压了底层社会的生存空间,这更加深了孔子对百姓疾苦的感同身受。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写到:“《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13](P48)上位者们“欲败度,纵败礼”导致的天下失序之“多米诺骨牌”的恶果,最终将以“苦、伤、杀”的形式由底层民众承受。从这段描述里,我们读出了孔子对民众的鲜明立场与浓浓情怀。
孔子对民众的态度,还自然流露于现实生活中,《论语》记载:“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如果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没有对民众深厚的仁爱、同情和悲悯,是断然不会出现这样的画面的。很多学者把孔子之道理解为君子修身之道,这与孔子“一心为民”的“大道之行”不违背,只是有“小大之分”而已。如果把《论语》章句割裂开来研究,每一章似乎都是从个人层面说明君子之道。但《论语》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里面的每一章都可以拿出来单独学习,也可以把每一章放入整体篇章中打通上下关系,从宏观角度审视。例如《宪问》篇孔子两个得意门生子路和子贡都对管仲是否是“仁”产生质疑,孔子义正言辞的为管仲声辩,盛赞其“如其仁!如其仁!”究其原因,莫过于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让当时处于战火的百姓得到了安宁,这就是“仁”,这也是《论语》中唯一一个被孔子重复称“仁”的人物。“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所谓“至德”,就是应时而动,为保全更多百姓,减少争乱而“以天下让”。此篇还有一章,“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修己以敬”的目的是为了“修己以安百姓”,由一人扩大至群体。个人修行、提高修养固然重要,但如果国破家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请问又有多少深山老林供个人修行呢?
孔子所构设的“天下有道、民众有归”是怎样的画面?《论语》记载,有次,夫子让几名弟子谈论志向,有的要治理大国,有的要治理小国,有的要作外交官等,这都没引起夫子的共鸣,唯独曾皙(曾子之父)的志向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大意说,春暖花开的季节,穿着当季衣服,几个成人带上几个孩子,一起在河边洗洗尘、吹吹风,然而唱着歌回家。没想到夫子说:“吾与点也。”我跟曾皙的志向一样。《礼运大同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3]可见“浓浓的烟火气、厚厚的人间性”,才是夫子历经波折困境、出生入死,毕其一生所构设的蓝图。然而,孔子没有止于此,没有将“天下有道”寄于“超验”、托于“彼岸”,而是发“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之叹,坚奉着“人能弘道”,选择不避世肥遁,而砥节励行、行走丈量,始终心向光明,这才是真正的孔子精神。
《论语》中“家国天下、治国理政”的章句有130余处之多,占整部《论语》的四分之一篇幅。孔子深思着平治天下之策,集思练精、绍续道脉,其思想中有着明显的“天下为公”的空间向度和“百世不迁”的时间向度。《论语》记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作为被周人所代的殷人后裔,却如此推崇周人之治,其公心昭然。《论语》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读起来有一种狂妄之气,实际上是以文王为代表的古代德政之治带给孔子的自信。他深知古代良政的经验智慧汇于“经文”之中,“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14](P7),“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
孔子依然没有止于此。《论语》记载:“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大多学者都着力于“叩其两端”,把它与《中庸》的“执其两端”对应,固然无妨,但此章的情境“鄙夫问于我”值得深思,“鄙夫”到底问了什么问题,让以博学著称的孔子哑口无言?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鄙夫”的问题既不是治国之方,也不是学问义理,应该就是一般民众最关心的生命安全问题,例如战争何时结束、幼童何时能够安心上学等等。面对这样的问题,孔子是无言以对的。紧接着下章,出现了孔子“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之叹,凤鸟河图是孔子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祥瑞之景。无疑,“鄙夫”之问更印证了孔子毕生所为的盛德之举的伟大意义!
我们通过疏解《八佾》篇的逻辑结构,可以推导出“原点—毁废—维护”三层意象,可以跨越时空感受到孔子于礼崩乐坏之时力挽狂澜、勾画蓝图的强烈意志。结合孔子一生轨迹,更可以体会到孔子积极培养学生出仕、拼尽全力传承文化的苦心。某种程度上说,孔子是确立了我国文化传统的人,上承三代典籍,下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士大夫执政体系。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P57)孔子不仅确立了我国文化传统,而且为国家大一统、长治久安制定了操作性极强的方案。“一切固保天命之方案,皆明言在人事之中。”中国古代经籍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站在国家民族未来的角度,将这份韫裹着厚重的文明种子,深植于新时代的土壤里,需要我们重新发现其要旨和释放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