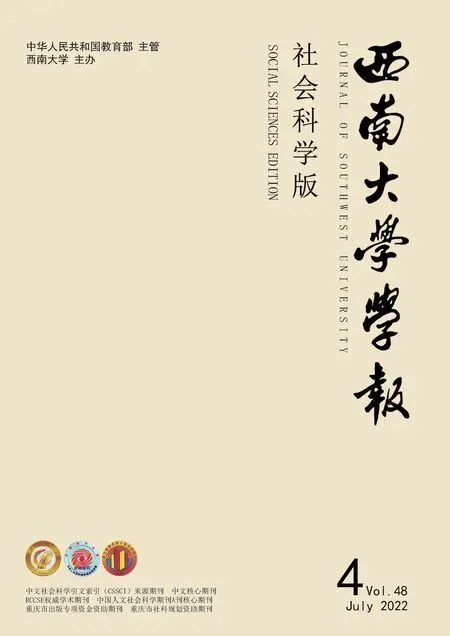诗礼相酬:唐人诗化社交方式与唐诗通俗化机制
冯 海 燕,黄 大 宏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715)
满足社交需求是古人作诗的重要动机之一,诗歌也是一种社交方式。从《诗经》《楚辞》可以发现,赠诗同时往往伴随赠物,“表面上是物质的往来,实际则是整个礼仪文化秩序的运作”[1],赠诗与赠物同时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媒介,共同成为致礼、达礼的途径和因素。汉末以来,诗与物的融合与对话逐渐成长,到唐人手中全面完成“诗礼相酬”的文人社交模式。这一模式将诗歌创作与礼物赠答相结合,具有沟通雅俗、关联不同社会阶层与整合文化品格的功能,不但是文人别具一格的诗化社交方式,也是强化唐诗创作通俗化倾向的内在机制。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诗礼相酬是诗歌交际与礼物馈赠的结合
“汉魏之际尤其是建安时期出现了文人以文学构建彼此关系的新情况”[2],诗歌交际渐成文人自觉,“唱和诗”“赠答诗”“送别诗”“应制诗”“联句”等一系列交际诗应运而生,在文人作品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到了唐代,据《新唐书》统计,唐代结集的酬唱诗集就有二十多种,诗歌交际成为文人最普遍的日常交往途径之一。在“诗礼相酬”的社交方式中,诗歌交际与礼物馈赠相结合,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使得文人的社交方式与诗歌的发展走向发生了显著变化,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与意义。
诗礼相酬是诗与礼的紧密结合,包含诗歌交际与礼物馈赠两大部分。关于诗歌交际,历代诗论家多有点评,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关注点。赵以武认为唱和诗是异于赠答诗“自立门户”的诗体,“借鉴了中国古代‘歌诗’唱和的传统,综合了乐府诗相和歌与江南吴歌、西曲的体制,受到了文人诗赠答诸体的启发,也接受了佛教传译的影响”,在多种因素影响作用下得以发展成型[3]。贾晋华通过辑校唐太宗朝宫廷诗人群、浙东诗人群、浙西诗人群、东都闲适诗人群、襄阳诗人群、咸通苏州诗人群等诗人群体的酬唱作品,对群体作品的诗风、诗体进行评述,研究了唐代集会总集与文人交往[4]。蒋寅研究了大历时期代表诗人个案,认为以鲍防、颜真卿为中心的浙东、浙西的诗会是诗人群体诗歌互动的结果[5]。他们主要从宏观角度对交际类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等方面进行整体观照,注重本事钩沉与历史政治背景稽考,借唱和诗微观考察文人“心灵曲线的波动和色彩斑驳的抒情主人公形象”[6],揭示了“独特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7]。
在诗歌交际的相关研究中,涉及礼物馈赠的内容关联到诗礼相酬,现代学者倾向于将礼物作为诗歌题材进行论述,如认为“赠物是上古先民纯朴、自然的求爱方式。花草子实,俪皮美玉皆是他们传情的媒介”[8]。“《诗》载木桃、木李、握椒、芍药之类,皆相赠问之物”[9],魏晋六朝文人诗中屡屡出现的赠物就多是《诗经》赠物寄情的延续,其中亦有新变,如赠物“不拘于男女之间的感情,发展为亲人之间和朋友之间”,“体现了赠物诗从‘物贵’到‘情贵’、从‘送物’到‘送情’的转化”[10]。后世文人强化了诗、礼的社交属性,礼物不只是作为诗歌题材,更是作为新的诗歌类型进入学术视野。杨玉锋认为唐人“乞物诗”可以“追溯到源远流长的赠物诗和南北朝的乞食诗”[11]。苏碧铨意识到礼物酬答是文人特殊的交游体验,在侧重“以物相交往、以诗相酬答的人情往来”过程中,“留下了诸多或跌宕起伏或妙趣横生或耐人寻味的有趣故事”[12]。胡健指出,“惠贶诗以写朋友交往中的赠物、受物为中心,是由魏晋以来诗歌赠答形式和赠物传统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诗歌题材”,“宋人惠贶诗赠物种类的繁多,则典型体现了宋诗生活化、日常化的特征”[13]。邓淞露以苏轼的礼物赠答诗为例,将赠物诗、谢物诗、乞物诗统称为“礼物馈酬诗”,指出诗歌创作与关系网络构建具有强大的文化效力,文章提出的“物的诗化”和“诗的物化”,不仅“部分回应了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重要命题”[1],而且指出了礼物与诗歌在交际方面的交互作用,较深入地探讨了诗与物的关系。
以上研究主要从诗歌题材与诗歌类型两个方面来分析诗、礼作品,阐释其在文人交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文化内涵,但忽略了礼物馈赠作为社会交往生活内容本身所具备的交际功能,它并不是诗歌交际的附属部分,而是独立自主的交际途径。在二者基础之上融合形成的诗礼相酬,更是独特的存在,其性质合乎礼,酬答行为的实现需要依赖器物和言语的表意功能。礼的本义是祭祀礼仪,《说文》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14]从示神以礼到以礼相交,诗礼相酬是神事向人事衍化转变的结果,行礼过程中的言语与器物是礼的物化显现,而致礼、成礼的媒介和要素源于赠物、赠言(诗)的行为。因此,礼物馈赠与诗歌交际均属于礼的范畴,二者本质相通,且“礼由物质的赠送酬答为主转向‘言’(诗)赠送酬答,与春秋时期的赋诗赠答有重要关联”,“体现着礼的赠送酬答的调和人际关系的精神本质”[15]。
显然,诗礼相酬的社交途径与涉及赠物的诗篇不同,前者的诗与礼处于平等地位,同样发挥着交际效力,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相辅相成,通过“物的诗化”与“诗的物化”相互作用以引起文人交往方式与诗歌风格的发展变化;后者只是一种关于赠物的诗歌类型,“物”的交际作用弱化,主要强调“物”作为诗歌题材、类型的价值意义。诗与礼的酬赠目的均在于思想情感和人际关系的沟通维系,通过礼物馈赠与诗歌交际所结合而成的诗礼相酬方式,不仅可以探究诗歌题材风格、文人交往的方式特征,亦可发掘出一种关于唐诗通俗化的重要机制。此种特殊的社交途径发挥着极大的交际效力,影响了文人交往方式与诗歌发展的方向。但在唐以前诗礼相酬的发展尚处于肇始阶段,要进一步强化诗礼相酬的社交属性,就其实现而言,尚有待唐人的社交及创作实践。
二、唐人诗礼相酬的主要类型与特点
诗至唐代,交际功能获得空前发挥,现存唐诗中与交际相关的作品占总量的半数以上,以应制、赠答、唱和等方式为多,诗题中“应制”“奉和”“赠”“答”“和”“酬”“寄”“送”“别”“联句”等比比皆是。白居易《与元九书》言:“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16]2795伴随频繁多样的交际行为,唐人与赠物相关的往来篇章日渐增长,反映出诗礼相酬行为获得长足发展。唐前诗与物的结合方式有随诗赠物和以诗酬赠两种,分别以赠予者和受赠者身份创作,前者表达赠物之意,后者因受赠而酬应,进入唐代又扩展出诗礼互赠和以诗索赠两种新类型,诗礼相酬模式获得长足发展。
(一)赠物附诗:表心著迹
情是礼的内涵,物是礼的媒介,礼无轻重,都是深厚情谊的载体,故白居易《寄两银榼与裴侍郎因题两绝句》云“贫无好物堪为信,双榼虽轻意不轻”[16]1907。诗人赠物一般含有情意寄托,故常附诗以表心迹,这一传统亦为唐人所继承,《文镜秘府论·赠物阶》称“虽复表心著迹,还以赠物为名”[17],简明道出赠物传情的目的,此举有助于淡化赠物行为的物欲痕迹,带上了文人色彩和艺术趣味。
诗人赠物极夥,含义亦丰,此待后文讨论。对赠物原因的说明则关乎赠者情意之所在,自然也关乎作诗内容。诗人之心迹,或急人之所急,或临别牵挂,或饷人之所好,以及某种心知的默契与情趣,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具体来说,有解危救困的义举,如王维《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记赠米救人,胡居士久卧病榻,无以谋食,故诗人“聊持数斗米,且救浮生取”,并以“居士素通达,随宜善抖擞”[18]劝其莫拘俗礼。以物赠别者,如刘叉《姚秀才爱予小剑因赠》以水喻剑,故以“泻赠”为语,因友人所好而慷慨解剑,并予忠告。有些赠物,不论琐细、昂贵与否,都可体会到诗人“赠人玫瑰”的快乐,也使抽象的思念亲切可感,张籍有句云“以此持相赠,君应惬素怀”[19]4320,可作此类赠物之举的注语。唐人赠物附诗之举,既有赠物之实,亦有明确对象,情意真切深致,不再有《古诗十九首》赠物于所思的莫名惆怅,这是唐人诗礼相酬行为日常生活化的重要体现。
(二)以诗酬赠:无以为报
礼物承载心意与祝福,故受赠不仅是受物,更是接受情意,自然不能没有回应。这种回应有以诗与物相酬者,此点下文将详细论述,此处不赘;或一时无适当礼物回赠,径以诗篇回报,即司空曙《卫明府寄枇杷叶以诗答》所谓“全胜甘蕉赠,空投谢氏篇”[19]3312。这种做法仍不失文人本色,并且更显礼物的珍贵与特别。
唐人以诗酬赠在内容上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盛赞礼物之珍贵,赞美角度随物而定。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详述受赠新茶的生长环境,以突显“咄此蓬瀛侣,无乃贵流霞”[20]之意。第二,盛赞友人择物而赠的用心精到。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直言友人所送之茶甚合心意,以致“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16]844。言辞虽不免虚美,但礼节与情意本就不以过度为嫌,反映的是文人获赠佳物后内心荡起的强烈情绪,言辞略显夸张并不为病。当没有合适礼物回报时,通常在诗题点明“无以为报”“无以答之”,如刘禹锡《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李德裕《临海太守惠予赤城石报以是诗》等。白居易此类酬答甚多,《崔湖州赠红石琴荐焕如锦文无以答之以诗酬谢》以琴荐、古琴比拟与崔玄亮的友情,“人间无可比,比我与君心”[16]1404,恰切点出友人的赠礼初衷,“无以答之”实是最好的回答。以诗酬赠始自《古诗十九首》,出现频率较高,从受赠者角度赋诗作答,加强了唐诗的日常化书写,加强了文学与生活的联系。
(三)诗礼互赠:永以为好
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投木报琼”等互赠行为不是为了获取物,而是借物“示”意,传达“永以为好”的愿望,表现“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21]的深层语境。作为赠物附诗与以诗酬赠的融合,诗礼互赠是唐人的诗礼相酬新类型,主要发生在“诗敌文友”之间,并因此催生了大量唱和之作,这是其特殊之处。
元稹、白居易是文人交谊深笃的楷模,也是唱和赠答的巨匠,颇多诗礼互赠,可谓礼物与诗篇齐飞。元和五年(810),元稹因劾奏河南尹房式为不法事,又与内官刘士元争驿房,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初贬时为瘴气所病。乐天寄去药物并作《闻微之江陵卧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云膏寄之因题四韵》,“未必能治江上瘴”“且图遥慰病中情”[16]811;元稹答诗盛赞药物之妙,倾诉“唯有思君治不得,膏销雪尽意还生”[22]202-203;二人诗礼互赠由此开始。元稹量移通州后,乐天贬至江州,在著名的通江唱和中仍不乏礼物的参与,乐天寄夏衣并附《寄生衣与微之因题封上》,元稹收到时已是“痎疟”“瘴云”四起的秋天,故以“欲将文服却还君”[22]236诙谐答之,为下一轮资助埋下了伏笔。果然,乐天又为其寄去蕲州簟,元稹作《酬乐天寄蕲州簟》以答之。当他境遇好转后,便以绿丝布、白轻褣回赠乐天,以“春草绿茸云色白,想君骑马好仪容”[22]235,安抚乐天“欲著却休知不称,折腰无复旧形容”[16]1062的担忧。元、白二人在贬谪期间以诗文相互慰藉,以赠物为支撑,往来细节与温暖汩汩而出。晚唐皮日休、陆龟蒙延续元、白的诗礼互赠,将生活中的点滴微澜纳入唱和,不禁疑惑他们是因赠物而作诗,还是为了作诗而赠物!显然,诗礼互赠是以礼为媒而形成的诗篇往复创作方式,赠予者和受赠者处于平等关系之中,既是文坛的神仙诗侣,也是人生的知交密友,才形成赠礼附诗、以诗酬赠的双向融通,真挚情谊相互链接在作品之中,生发出这样的美与趣结合、诗与物相融的佳话。
(四)以诗索赠:以俗为趣
以诗索赠为唐人新创,别有一番况味。欲饮新茶,姚合《乞新茶》“不将钱买将诗乞,借问山翁有几人”[23]429;欲装点庭院,王建《题江寺兼求药子》“愿乞野人三两粒,归家将助小庭幽”[19]3405。借诗语之委婉,或显示放旷情怀,或化解尴尬处境,或突显交往深笃,总之,以物为媒,似俗而雅,展示出人情之美善,透露出不拘常行的性情。
文人因贫困而以诗索赠者,可以杜甫为代表,流落蜀地时多次寄诗求助,《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诣徐卿觅果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等皆是此类,仇兆鳌称“觅桃、觅竹、觅桤、觅松、觅果,皆营草堂时渐次栽种者”[24]731,均是从亲友处觅来。“诗主含蓄不露”[25],杜公以诗索赠,既化解求助的尴尬,又获得了物质帮助,不失文人身份,但生活之艰辛不是用“戏笔”可以掩盖的,不过是处之以淡然而已。面对杜甫的求助,亲友们不认为可鄙,总是尽量给予帮助。也有因所嗜不足而索赠者,鲍溶《寄王璠侍御求蜀笺》“闻说王家最有余”,便以“石楠红叶不堪书”[19]5537为由寄诗;有因所好而求者,以索取茶酒为多,常被视为风雅韵事,姚合《乞酒》“闻君有美酒,与我正相宜”[23]427,毫不掩饰索饮意图;《寄卫拾遗乞酒》盛夸卫洙的美酒如“花上露”“洞中泉”,能让其“一杯三日眠”[23]428。显然,“诗乞”大多得到了满足,彼此在分享中其乐融融,有助于交往的持续与升华。难以启齿的乞物俗举因诗的介入而具雅意,以高雅的诗情通于俗物,既是唐人心胸开阔的表现,也是充分发挥物为礼之媒介的表现。当然也有求而未得的情况,杜甫因王录事许诺的营茅屋赀未能及时到账,便云“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24]1133?在似嗔似诘中提醒友人施以援手,“借助诗的形式,巧妙地维护了作为贫者、穷者、弱者的颜面,维护了文人的清高和尊严”[26],而这些为求物不得而写诗诘之、征之、催促之,论行为出人意表,论情感又似在意中,虽不多见,恰恰表明纯真性情与真挚友谊的难得。
在实际的诗礼相酬行为中,上文所述四种类型常有交织。韦应物《寄释子良史酒》叙其盛酒于瓢相送,并嘱其“还寄此瓢来”[27]175;释良史收下美酒后,又寄还此瓢,韦氏重寄美酒,《重寄》并言“若不打瓢破,终当费酒材”[27]176;韦氏又作《答释子良史送酒瓢》向其索赠“寒塘水”[27]176。三首诗蕴含了一段赠物附诗与以诗索赠的往来过程,唐诗此类情况不少。
随着唐人诗礼相酬诗篇的空前增长,赠物的丰富广泛性也远超前代,主要有以下九类:
(1)文房雅具之属,如桃竹书筒、书画、叠石砚、紫石砚、太湖砚、端溪砚、砚瓦、墨、纸笔、剡纸、蜀笺、彩笺、红石琴荐、太湖石、赤城石、青苔石、秦筝、新琴、剑、鞭、古镜、扇子、麈尾、竹蝇拂、香、山水簇子、二龙障子等;
(2)起居坐卧之属,如竹杖、茸毡、褥段、绿罽、乌龙养和、簟、竹夹膝、南榴卓子等;
(3)衣冠巾饰之属,如剑、鞭、古镜、牙簪、麈尾、生衣、罗衣、绫素、紫霞绮、杨柳枝舞衫、乌纱帽、纱帽、白角冠、葛巾、华阳巾、袍衣、褐裘、缭绫手帛子、鞋、靴、猿皮等;
(4)食器酒具之属,如瓷碗、银匙、银觥、银榼、酒瓢、药瓢、诃陵樽、炭等;
(5)茶酒果品之属,如仙人掌茶、新茶、新蜀茶、鸟觜茶、蜡面茶、灉湖茶、乳酒、桑落酒、绿酒、白酒、名酝、新酝、斗酒、酒肉、葡萄、蒲桃、樱桃、杏、梨、柑子、青橘等;
(6)生鲜饮食之属,如米、酱、野蔬、饧粥、胡饼、石鲫鲙、白鱼、巨鱼、双鱼、虾、海蟹、树鸡等;
(7)养生医药之属:松英丸、诃黎勒叶、大通中散、碧腴垂云膏、枇杷叶、金石棱、车前子、茯苓、人参、石芥、丹药等;
(8)禽草花木之属:白鹇、鹤、马、青桂及花、李花、菊花、霜菊、山姜花、玉蕊花、海棠梨花、早梅、红桂树、桃树、桤木、绵竹、松树子、蕙草、萱草等;
(9)土地田园之属:瀼西果园等。
这只是一份按物品属性而非赠物缘由整理的清单,但已可简洁直观地呈现出赠物的种类和范围,另如“修草堂赀”等因不能指实而无法入列。这份清单并不是考察诗礼相酬行为特点的最好归类方式,仍需结合赠物行为与诗篇内容,总结唐人择物酬赠的特点和相关认识价值。唐人择物酬赠最重要的两个特点是对物的象征性与实用性的抉择,很多时候这两个特点兼而有之。择物酬赠的象征性与实用性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特点,既与物的属性有关,也与诗礼相酬的传统有关。事实上,唐人择物酬赠的象征性特点是在诗与物的对话中形成的,而实用性特点则影响到唐诗的通俗化趋势。
择物的象征性原则主要关注礼物的内涵。象征本来是借某一事物寓意、暗示特定的人、事或情感等,经过文学描述变成一种稳定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如赠人花草,《诗经》《楚辞》载有大量表达爱意的象征物。魏晋以来,花草所承载的相思意味拓展至友情,如陆凯折梅遥赠范晔,王筠摘安石榴寄赠刘孝威等。而在浪漫的唐人笔下,花草的象征性意蕴更为丰富,演变出趣味、解忧、惜时等多重含义,尤其是“折柳赠别”之举已成为一种社交习俗,“柳”与“留”同音,蕴含挽留惜别之意,经过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折柳”更是固化为赠别的审美意象。“鹤”是唐人往来中富于新意的象征之物,因颈长毛白被赋予洁身自好等品质,很受文人喜爱,在白居易、裴度、刘禹锡、张籍围绕“华亭鹤”所作的诗礼相酬篇章里,鹤是乐天的伴侣、孩子,亦是其化身,无怪乎皮日休《七爱诗·白太傅》称其“处世似孤鹤”[28]。
择物而赠的实用性原则关注物的使用价值,相对于唐前赠物的象征性倾向,唐人赠物的实用性明显增强,茶、酒、鱼、砚、墨、纸、笔、笺、绮、帽等实用之物俯拾即是,与生活息息相关,赠物变得更为日常亲切。而最好的赠礼莫过于暗合对方的需求,如在韩愈“正著书”之际,李伯康寄来纸笔;刘禹锡“正草玄”,唐秀才赠以端州紫石砚;孟郊友人选择在寒冷冬日赠炭,为之“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19]4262,等等。急人所难的情谊历来为人所重,往来实用之物对彼此生活都有裨益,成为赠礼的重要原则。
还有许多赠物,既有实用性,又满足精神需求。文人相赠竹杖的传统由来已久,寓意关切、扶持,尤其在友人年老时,希望能借以扶持清羸之躯,李商隐《赠宗鲁筇竹杖》“静怜穿树远,滑想过苔迟”[29],虽是寻常之物,却兼具象征性与实用性。唐人尤以筇竹杖、斑竹杖的赠送频率最高。筇竹又称罗汉竹,竹节匀称、坚硬挺拔,与文人气质相符,高骈《筇竹杖寄僧》云“坚轻筇竹杖,一枝有九节”[19]6919。斑竹富于文化意蕴,又名湘妃竹、泪竹,制成的拄杖既实用又兼有斑竹的文人气质与自身的相思情意,是内涵丰富的意象载体,李嘉祐《裴侍御见赠斑竹杖》直言“万点湘妃泪,三年贾谊心”[19]2147,刘禹锡《吴兴敬郎中见惠斑竹杖兼示一绝聊以谢之》寄寓“拄到高山未登处,青云路上愿逢君”[30]1359的心愿。文人通过诗与物传递情愫,在相互认同与信任中缔结和维系友谊。
事由和季节等要素也对赠物特点有重要影响。赠物事由可从诗题、内容得知,杜甫将离蜀,故以瀼西果园赠南卿兄;友人抱疾卧床,可赠以药物。赠物之事由纷呈,所赠物类也因之变化,此不赘述。季节的更替也会造成赠物的变化,春赠茶、花,夏送果、衣,秋赠帽、菊,冬送炭、药,而空间距离、运输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则为这些赠物增添了特殊的价值。当然,即使是赠予季节性的物品,称心仍是最重要的原则。一席夏簟有助于友人度过炎炎盛夏,无疑是夏季最佳礼物。唐代最有名的“簟”是蕲州簟,由簟竹(一名笛竹)制成。韩愈收到郑群所赠蕲州簟后,盛赞“蕲州笛竹天下知,郑君所宝尤瑰奇”,蝇虱躲避、清飙吹拂,以致“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31],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与‘携来当昼不得卧’,俱透过一层法”[32];乐天又将之赠予元稹,《寄蕲州簟与元九因题六韵》言“通州炎瘴地,此物最关身”[16]1000,希望为元稹送去避暑安睡的保障。事实上,在唐诗里,每个季节都有代表性的礼物,传递出诗人因时而动的情思。
诗礼相酬集合了诗与物两种要素,物即“豊”是实践礼的载体,是寄托情意的媒介;诗即“示”作为表达礼的手段,把赠予与受赠的情意明确表达出来。诗礼相酬类型的多元化以及赠物品类的繁富,彰显了此种社交方式的特点,体现了唐人社交行为的丰富性与生动性,由此产生的作品是别具认识价值的诗歌类型。
三、诗礼相酬强化唐诗通俗化倾向
产生于诗礼相酬行为的诗歌属于交际诗范畴,交际诗的发展是推进诗歌通俗化的重要途径。诗歌的通俗化是指诗歌创作有通于世俗的倾向与特征,记世俗之人,写世俗之事,从世俗之情,涉世俗之物,用世俗之语。这里的“世俗”与凡琐庸俗不能说毫无关联,但也并非不雅,而是世所常习、世所常见、世所常有。研究交际诗的产生与发展,学界多以“诗可以群”为理论指导,认为“诗歌可以表现、反映、沟通、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3],用以揭示创作上的集体性和“用诗歌来交流、沟通思想感情,达到协和群体的作用”[34]。魏晋以来,诗歌已有“转变为士人日常生活的言说”之倾向,“注重的是个体日常生活之‘用’”[35],且“交际诗的功能从实用性转向了美用合一,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36]。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些针对交际诗与士人日常生活关系的理论言说,主要关注诗歌本身的致礼、成礼性质,即以礼的达成为“个体日常生活之‘用’”的体现,并未关注到两个特别的内涵,一是礼的载体是物,二是交际对象不限于士人,正是这两个要素的加入强化了诗歌由“雅”向“俗”的变化,成为推动唐诗通俗化进程和特点的内在机制。
其一,诗礼相酬通于世俗之事。诗礼相酬反映的是日常人际交往情事,与物的交流馈赠直接相关,是“缘事而发”“因事为文”的结果,其诗不仅涉及大量世俗物品,在表现手法上也与“诗缘情而绮靡”的抒情传统相异,它们长于对物的描写,炽热的情感蕴藏于礼物之中,借助赠物、谢赠、索赠之辞缓缓吐之。如朱昼《赠友人古镜》四联皆言“古镜”,开篇交代“初自坏陵得”,颔联“蛟龙犹泥蟠,魑魅幸月蚀”是形貌描写,从颈联“摩久”一词可知作者对之爱不释手,而将如此爱物赠予对方“照色”的目的是“无使心受惑”[19]5561,仇兆鳌评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只寻常器皿,经此点染,便成韵事矣”[24]734,可作此类诗总评。叙述性文字的增加又降低了诗歌理解的难度,杜甫《从人觅小胡孙许寄》因对猢狲形声情状的细致描写而显得“意义短浅,恐属率尔之作”[24]631,令邵宝“疑其可删”;在其求赠诸篇中仅《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不露一松字,却句句切松,较之他章,独有蕴藉”[24]733,指出此篇蕴藉笔法与他篇铺叙摹写之别。细品此类诗旨,的确与其他诗篇在意蕴深广程度上大相径庭,也透露出杜甫为了交际需要而注重礼物的描摹刻画,在诗歌表现手法上更趋于通俗浅切的追求,渐渐“实现了从表现性抒情到传达性信息的转变”[37]。纵观唐人此类诗作,皆是有实用功能的文字,侧重对赠物及背景的描述,诗歌从抒情言志的一面转向注重实用性功能,使唐诗的通俗化得到长足发展。
其二,诗礼相酬通于世俗之人,在扩大增强同一社会阶层联系的同时,也具有纵向贯通不同社会阶层联系的作用,强化各个社会层次的交流。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酬唱诗歌正是中国这个几千年以来形成且沿袭不断的‘关系本位’社会状态的艺术反映”[38],酬唱之作可以沟通参与者的社会阶层,诗礼相酬的交际效果更佳。李白的诗礼相酬在与普通民众的交往上超越了前人,其《赠汪伦》是为酬谢汪伦的邀请款待以及“赠名马八匹,官锦十端,而亲送之”[39]的情谊;另有答谢小吏的《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文人的朋友不一定是文人,也可能是寻常百姓,未必能诗擅文,馈赠礼物是他们表达情谊的质朴方式,而诗人的赠诗也更称其心意。诗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作士大夫禁脔,李白将其下移到世俗生活,从交际对象上革新了诗歌的通俗化进程。诗礼相酬还暗含复杂的阶层关系,礼物的馈赠多呈非对称性流动,一般是自下而上的,收礼成为所谓“声望”的体现。但自上而下的礼物流动也很多,此举不仅能给赠物者带来名望,受赠者也因位尊者的殊遇而荣身。裴度赠马一事在当时轰动不小,张籍酬以《谢裴司空寄马》,夸耀马之俊逸,担忧其无法适应“贫家”生活;裴度《酬张秘书因寄马赠诗》自谦所赠并非“逸足”,称张诗为“高文”,结句“飞控著鞭能顾我,当时王粲亦从军”[19]3755则自有深意,张籍也的确是因为裴度、韩愈等人的举荐而由国子助教、秘书郎改迁国子博士,暗合了白居易《和张十八秘书谢裴司空寄马》“丞相寄来应有意,遣君骑去上云衢”[16]1225的祈愿。“籍得一马,而诸公争为之咏若此,诚以其人耶?”[40]元、白、韩从张籍的角度酬和,李绛、张贾及刘禹锡奉和裴度答诗,“赠马”唱和微妙地揭示了众人的关系。肖瑞峰针对刘诗结句总结说:“在‘王侯’与‘词客’,‘富贵’与‘清才’之间,裴度看重的是后者而非前者,赠马予张籍,便昭示了他的选择。这正是裴度的超凡脱俗之处,也是包括刘禹锡在内的所有集贤殿学士最为感佩的一点。”[6]总之,裴度因赠马获得了士林声誉,张籍得到了名马、荣誉和升迁的机会。由此可见,即使同处于文人群体,也有身份地位的差距,诗礼相酬的互动较易打开阶层缺口,沟通不同阶层,比一般交际诗的社交功能更为强大。
其三,诗礼相酬通于世俗之情。赠“物”回“礼”的传统由来已久,作为一种日常社交方式,在接受他人赠物时予以答谢,或在赠物之时附上问候,是世所习见的人之常情。显然,礼物承载一定的礼节、礼仪,必然浸染着送礼者的精神情感,即“不是礼物的精神而是人的精神将馈赠双方联系在一起”[41]228,情意交通是礼物相赠的重要目的。据刘商《山翁持酒相访以画松酬之》、方干《袁明府以家酝寄余余以山梅答赠非唯四韵兼亦双关》等诗所述,以书画酬美酒,山梅答家酿,礼物的互赠互惠强化了人情,人情则推动着社会交往的发展,很多时候“‘赠物’变成一种手段,实际是为了‘寄情’”[10],从而使诗礼相酬必然具有行礼从宜、处事从俗的含义。而文人在赠物时加入诗的成分,“日常经验也同步向诗性经验转换”[42],一来表明礼物的内在价值之重,二是提升赠物行为的文化内涵。其本质仍与世俗大众的情感相通,或分享好物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如郎士元《寄李袁州桑落酒》“十千提携一斗,远送潇湘故人”[19]2787;或感谢对方的惠赠之情,如薛能《蜀州郑史君寄鸟觜茶因以赠答八韵》“千惭故人意,此惠敌丹砂”[19]6494;或凭借物的沟通维系人际关系,如白居易《谢杨东川寄衣服》“唯有巢兄不相忘,春茶未断寄秋衣”[16]2357。这些都不过是换了形式的社交,内在的世俗之情贯穿交往始末。即使是再蕴藉含蓄的表达方式,与其他类型的诗歌比较起来,其阅读理解的难度也会降低许多。事实上,唐人并不讳言恋物癖好,而是以此为雅,白居易《太湖石记》云“古之达人,皆有所嗜”[16]3936,素以“爱琴爱酒爱诗客”[16]2178自称,姚合《拾得古砚》言“僻性爱古物”[23]534,而崔玄亮曾寄梦得《三癖诗》“自言癖在诗与琴酒”[30]759-760,文人们“爱物”“恋物”所助长的“赠物”之风,使礼物往来愈加频繁,势必伴随大量诗礼相酬之作产生,展现出文人贴近世俗生活的情趣。总之,诗礼相酬因世俗之情而愈显,世俗之情因诗礼相酬而弥彰,最终发展为集物质交流、人情往来、文化意义、仪式情境于一体的社交方式,进一步推动了诗歌的通俗化发展。
又如前文所述,唐前已出现诗礼相酬行为,但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深广程度,在体现诗的日常交往功用与突破交往阶层的方面有限,也限制了诗的通俗化程度,这几个方面都只是在唐代才得到了充分发展。有唐一代,诗礼相酬在诗歌通俗化方面的贡献有迹可循。
初唐时期的诗歌概貌,“在七世纪初期,诗歌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程式化的社交形式,主要创作于宫廷圈子里”[43],此时诗歌绝大多数是为社交而作,且多为宫廷应制,鲜少涉及“礼物”往来。皇帝赐物与日常礼物往来不同,群臣应制自然与寻常酬谢相异,文人阶层的诗礼相酬现象并不普遍。卢照邻两封书信涉及礼物往来,《寄裴舍人遗衣药直书》是对裴舍人等“并有书问余疾,兼致束帛之礼,以供东山衣药之费”[44]393的感谢信;而《与洛阳名流朝士乞药直书》提及以诗索药之事,“今力疾赋诗一篇,遍呈当代博雅君子”,并且请求朝英贵士及博济好仁者“故知与不知,咸送诗告”[44]388-392。显然,诗歌在索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交际角色,推动了诗礼相酬的进程,虽然相关诗作散佚不见,但亦可窥探诗礼相酬发生发展的冰山一角。张九龄《和王司马折梅寄京邑昆弟》《答陈拾遗赠竹簪》是真正意义上的诗礼相酬之作,凭借折梅、竹簪表达棠棣兄弟之情、茂林修竹品质,明白晓畅地传达情愫。
盛唐时期,在诗礼相酬的交往中,李白还增加了序文的叙述,便于交际对象与后世读者准确迅速地把握诗歌主旨与创作背景。譬如《赠黄山胡公求白鹇并序》云:“予平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辍赠于我,唯求一诗,闻之欣然,适会宿意。因援笔三叫,文不加点以赠之。”[45]635李白本想“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鹇”,但胡公唯爱太白诗,二人各取所好,李白求鹇,胡公求诗,因而有作;而《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也详细说明了仙人掌茶是“因(族侄僧中孚)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45]897。酬谢之诗是因物之交流与应族侄要求而作,同时阐明仙人掌茶的命名由来,并希望借助此诗流传,自我标榜之意明显。李白在诗礼相酬的写作上超越前人之处更体现在与普通民众的交往上,其《赠汪伦》《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等皆是为酬谢普通民众的赠物而作,将诗歌交际从文人圈子里走出来,扩大了诗歌交际的适用范畴,正是诗礼相酬的社交魅力。
中唐的诗礼相酬已相当成熟,杜甫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不仅表现在使用频率上,更体现在对礼物的刻画、形式的选择以及诗歌功能的变化等多方面,呈现出与言志抒情传统相异的表现特征。为了化解频繁求助的尴尬,杜甫使用以诗索赠的方式,将文人偶然的诗礼相酬行为日常生活化,直面惨淡人生的现实经历。杜甫长期处在以诗索赠的境遇中,大量日常生活用品成为主要描写对象。随后,元、白在理论与实践上将诗歌通俗化推向高潮,“老妪能解”的创作要求直接强化了通俗诗风,大量俗字俗语入诗,且少用典,口语化倾向明显。与以往不同的是,二人势均力敌的诗情才华使得诗礼互动以均衡力量进行,诗、礼不再只是以诗索赠、以诗酬赠的单向沟通方式,而是赠礼附诗、以诗谢赠的双向交流。在如此对称的诗礼互赠对话结构里,无论是单篇吟诵还是对比阅读,借助的诸多文字资料更易对诗歌进行释读,无怪乎苏轼用“元轻白俗”[46]来概括二人诗风。在诗礼相酬上,元、白对前人的巨大超越是以诗人群体的力量推动诗歌的通俗化进程,新乐府运动中与李绅、张籍等人的诗歌交际,在文坛掀起“重写实”“尚通俗”浪潮,张籍《酬浙东元尚书见寄绫素》《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分别写给元稹、白居易,在诗礼相赠过程中情深意笃。“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47]元和时期,韩孟诗派崇尚奇崛怪力,与元白诗派看似格格不入,其实都是在努力创新求变,韩愈、孟郊与白居易、张籍等人多有诗歌往来,张籍成为连接两个诗派的关键人物。韩愈诗风也受到白、张平易诗风的影响,《李花赠张十一署》《郑群赠簟》《答道士寄树鸡》等诗礼赠答之作自然通俗,正是向元白诗派学习交流的结果。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以群体力量共同促进了通俗诗风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发展。
晚唐时期,皮日休、陆龟蒙紧随元、白之后,进一步借助诗礼相酬推进了诗歌的通俗化发展。晚唐文人心态多避世隐居,生活细碎,万物成诗,关于“物”的赠答愈加频繁,几乎达到了有赠物必有唱和的程度。皮、陆二人不仅互赠礼物,亦转赠其他友人的礼物,如《病中有人惠海蟹转寄鲁望》《酬袭美见寄海蟹》;皮日休对其他友人惠赠的回复,陆龟蒙也主动酬以《奉和袭美谢友人惠人参》《和袭美友人许惠酒以诗征之》,积极参与对方的社交活动,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诗礼相酬的社交方式。皮日休还将诗礼相酬的社交方式融入“求雅物”“成雅思”的文化交流,谓之“真古人之雅贶”[19]7058,试图提升诗礼相酬的文化内涵,社交方式与文化交流合而为一,将原本高深的文人文化交流通过诗礼相酬的方式通俗化。
诗礼相酬既强化了诗歌的日常交际作用,又可以解释诗材、诗情、诗语“尚俗”倾向的产生。《释名》曰“俗,欲也,俗人之所欲也”[48],满足“俗人”的需求,正是通俗的基本动机。从人际交往角度看诗礼相酬行为,是诗的创作因便于物的交流、人的交往而通于俗,文人凭借礼物的联结将诗歌从雅交之端拉回,社交范围由文人阶层扩至普通民众,使世俗交往审美化与交往秩序世俗化,增强诗歌交际的普适性,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交方式。从诗歌创作角度看诗礼相酬行为,则是因言及俗物、涉及俗事、使用俗语而通于俗,从各个角度加强和促进了唐诗的通俗化发展。唐代文人频繁地对琐碎平凡之物进行艺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渐渐成为自觉意识,越来越多的日常题材进入诗歌范畴,尤其是关于礼物的往来赠答诗作,成为“创造、维持并强化各种社会关系的文化机制”[41]107,出现了题材内容趋于日常、表现手法注重描写、大量俗语入诗以及诗歌实用功能的加强等变化,引领了中唐以降“近乎鄙俚”的诗风,以大量创作实践丰富了唐诗“俗”的内涵。
迨至宋朝情况愈甚,每有馈赠皆系以诗,往往以俗为雅,在诗歌表现领域大量引入日常生活用品,多以文房用具、禽草花木、生鲜饮食等物相馈赠,造成宋诗题材的日常化,甚至在编纂诗集时专立“惠贶”一类,直接展示了诗礼相酬之作数量上的增加与重视程度的提高。比如,梅尧臣的礼物酬答诗多达150首,所记之事多为“文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以物相交往、以诗相酬答的人情往来”[12]。和唐诗一样,这些表现皆是宋代通俗诗风形成的重要因素。显然,唐代文人诗礼相酬的社交方式所造成的诗风通俗化,无疑对宋代平淡直白诗风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
诗礼相酬兴于汉魏,盛于唐宋,与其他社交方式明显不同,在于将诗歌交际与礼物馈赠融合为一,既适应了日常交际的需要,又富于文人品格趣味,丰富拓展了文人构建关系的渠道,最重要的是它在诗歌发展历程中的诗学价值与意义,成为研究唐诗通俗化的一个重要机制,为唐诗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重新审视、补充与修正相关诗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