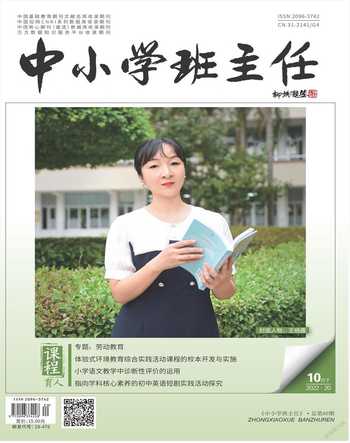小说阅读要摆脱与情节的纠缠
吴贤友 李群
[摘要] 把故事等同于小说的现象既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小说阅读中,很多人过于关注故事和情节,甚至认为没有情节就没有小说。在语文课堂实际教学中,情节作为小说三要素之一,依然是教学的重点且颇受关注,但情节并非构成小说的必然。现代小说更看重的是内在气韵和节奏,散文化是现代小说的重要特点,追逐情节的传统读法已经很难把握小说这种文体的诸多魅力。
[关键词] 小说文体;散文化;考情分析
一、小说崇尚情节的历史渊源
小说崇尚情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小说是用来“讲”和“听”的,小说的受众是听众而不是读者,对故事和情节的追逐自然是小说的首选。西方的《一千零一夜》,中国的话本小说,皆是如此。
小说关注故事和情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讲究情节的完整性。这样的小说一般遵循时间线性流程,一般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无论是悲剧还是大团圆结局,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刨根究底的欲望,因而深受人们的欢迎。在阅读还是少数人专享,“说书”和“听书”还是主要的文化传播形式的时代尤其如此。二是追求情节的曲折性。说书人如果不能吸引听众,他们就没有了谋生的饭碗。因此,我们今天见到的那些传记或演义类的文学作品,会着意于生活及历史中的矛盾冲突,在起伏的波澜中展现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
应该说,对小说自古有之的倾听和阅读反过来也培养了我们的精神心性和审美品格。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如果过于追求情节完整性和曲折性,就无法忽视事件的因果关系,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环环相扣的情节安排是很难实现的。如果过于强调巧合,把生活中的偶然写得太“紧”了,就必然导致故事失真。比如,余华的小说《活着》,福贵的一生坎坷其实有太多的“巧合”,从小说整体上说,不太可信。汪曾祺曾评判莫泊桑与欧·亨利,看似耍了一辈子的结构,但他们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这里就是批评部分小说当中存在有失生活常理的弊病。况且,过于关注情节的紧凑,也导致生活中丰富的内容很难进入故事之中,小说的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
从阅读层面看,曲折紧凑的结构安排,固然能牢牢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的主动创造性容易受到过于饱满紧凑的情节挤压。这是接受美学不能认同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作品的生命价值同样需要读者的发掘和创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废除以后,读书不再为少数人所专享,这使得故事不再是听,而是读,这为小说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新的可能和要求。
二、散文化小说的发展流变
新文化运动之后,国门打开,西风东渐,西方现代小说的理念同期传入中国。读书人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小说形式,其内容构成、艺术结构、表现手段和语言风格都与中国传统小说大异其趣。散文化的小说写作便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的。散文化小说融合了小说、散文和诗歌等多种文体,在叙述中插入抒情、描写、议论及说明等非情节因素,冲淡了小说固有的情节要素,有一种文体杂交、兼容散淡的审美效果。
散文化小说的提法由来已久,早在民国时期,郁达夫称之“散文小说”,周作人称之“抒情诗的小说”“随笔风的小说”等。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在《小说的散文化》与《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等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散文化小说”的创作理念,并在理论上对这种类型的小说作了精要阐释:散文化小说是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小说文体。这类小说情节淡化,结构散化,不以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也少有冲突,缺乏悬念,呈现给读者的多是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这类小说主张事实都恢复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散文化小说首先发生于短篇小说。在这种文体的初创时期,根本没有传统小说和以张恨水等为代表的通俗小说传播范围广阔。这种新型文体不追求宏大叙事,也很少写出像巴金“激流三部曲”和茅盾《子夜》这样宏大的作品。散文化小说的作者一般在散文和小说两个领域都成绩斐然,有些作品甚至很难分出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
在创作实践上,以小说“散文化”特征闻名的作家代不乏人,奠基者有鲁迅、郁达夫;继起者有废名、沈从文、萧红、艾芜、师陀和孙犁;新时期复出的作家以汪曾祺和林斤澜为代表;后起之秀则有阿城、何立伟等,既络绎不绝,又一脉相承。
鲁迅的小说中,同样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呈现出小说的散文化,《呐喊》中的《社戏》《一件小事》《故乡》等,都谈不上有什么完整的情节,只能说叙事散文,但鲁迅认为是小说。相反,《朝花夕拾》中的《狗·猫·鼠》《五猖会》《阿长和山海经》,鲁迅称之为叙事散文。其实,就情节的生动性而言,后者远胜《呐喊》中的那几篇。郁达夫以《沉沦》闻名,作者采用片段连缀的方式,将所见、所闻、所遭、所感绾合起来,结构显得松散而随意。
废名以《竹林的故事》闻名于世,他借鉴古典诗歌和国画中的“空白”艺术,在淡美的情景中烘托人物性格。“三姑娘小小的手掌,这时跟着她的欢跃的叫声热闹起来,一直等到碰跳碰跳好容易给捉住了,才又坐下草地望着爸爸。”他用语洁净新奇,三言两语中便能勾勒出人物形态。萧红的《呼兰河传》,结构零散,笔致跳脱,既没有严密的谋篇布局,也没有严谨的事情叙述。“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茅盾曾评价“《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
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沈从文的《边城》《萧萧》这类小说,按照他本人的说法,自觉地注入了散文诗的情愫。艾芜的《南行記》中的许多篇章明显带有报告文学的痕迹。
改革开放以来,开放变革的时代语境再次推动着文学观念的变革,散文化小说重新走向前台。随着汪曾祺、林斤澜的复出,阿城、何立伟等新锐的加盟,一大批带有散文化特征的小说涌现,为小说界带来了新鲜气息。阿城《遍地风流》系列,干净冷峻,文风利落;何立伟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创作了《白色鸟》《小城无故事》等。
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自觉主张情节淡化,既有理论又有创作实践,成就最突出的作家非汪曾祺莫属。他认为小说的故事性如果太强了,就不太真实。“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要耍花招。”无论是《受戒》《大淖记事》等“高邮系列”小说,还是《安乐居》《小芳》等现实题材小说,其故事情节都很简单,小说的结构松散而随意。如作者写大淖周围的环境,写卖紫萝卜、卖风菱,写挑砖瓦石灰、挑鲜货,只有细致观察过生活,才会有如此的絮叨和松散,这种闲散却又真实地反映了生活,营造出故事的氛围。娓娓道来的篇章,显得真实生动,散而有味。
三、教材里的小说文本类型解读
散文化小说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到今天星光灿烂,已经被学界和世人广泛而普遍接受。在基础教育阶段,也得到充分体现。以部编高中语文教材为例,必修教材共收录小说7篇,其中《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促织》属于传统小说,另外4篇小说《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变形记》《百合花》《哦,香雪》则不以情节取胜。
《祝福》打破了传统小说以时间为序的叙事逻辑,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间杂抒情、描写和议论,使整篇小说显得摇曳多姿。《装在套子里的人》充分体现了契诃夫善于透过平凡的日常生活揭示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题的写作特色,小说的这个结尾余意不尽,耐人寻味。《变形记》是寓言小说。没有谁能像卡夫卡那样,用如此平淡冷静的笔调,来表述变形这种不可思议又荒诞无稽的事情。作者不求社会生活画面的丰富多彩,但求深刻的哲理和寓意包蕴其中。《百合花》无论情节还是结构都极为单纯,但作者善于布置细节,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内心变化在细节的描寫中缓缓展开,有很强的节奏感。《哦,香雪》最能见得铁凝以小见大、平中求奇的创作个性,孙犁说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这样的小说在阅读时,需要放慢节奏,细细品味。
故事不等于小说,更不能把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混为一谈,小说家绝不会单纯地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现代小说家早就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活力,已经不能给我们带来当初的激动,那些千百年来给我们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
小说阅读教材的编写也应时而动。21世纪初,人教社高中语文实验教科书就对小说阅读教材进行了调整,选修教材之一的《外国小说欣赏》更是以小说的基本元素设定单元,分别以叙述、场景、主题、人物、情节、结构、情感、虚构为关键词,选择小说文本,并结合话题和所学的小说作简要分析,让学生了解小说尤其是西方小说的基本理论,并勾勒出这一理论的发展渊源和变化脉络。附录的思考和实践,可以帮助师生走出既往的阅读模式,发掘打开小说的另一种方式。
我们非常遗憾地发现,很多老师拿到那些散文化的抒情小说却无从下手,很多学校的选修课程基本不用这套《外国小说欣赏》,理由是这些小说没有情节,没有典型人物形象,不好把控分析。必须承认,长期浸淫于通俗小说的读者,审美感觉渐趋钝化。面对这样的抒情文本,如果还是人物、情节和环境三板斧地去分析,那就不会有真正的小说教学和学习。
四、高考命题中的小说文本选择及命题方式的嬗变
基础教育的深刻变革也带来了高考阅读理解文本选择和考查模式的巨大变化。注重情节曲折的传统小说在高考试题中零星出现过(如2007年海南卷《林冲和差拨》),但散文化的抒情小说才是高考选文的主流。那些以小说散文化特征著称的作家和作品陆续进入高考试题,如废名《放猖》《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鲁迅《理水》、沈从文《会明》、萧红《呼兰河传》、叶紫《古渡头》、师陀《邮差先生》、汪曾祺《捡烂纸的老头》《侯银匠》、林斤澜《表妹》、刘震云《塾师老汪》、阿城《溜索》《赵一曼女士》、谈歌《秦琼卖马》、卞之琳《石门阵》等。仔细梳理这些年的高考小说试题,我们也发现,高考小说选文大多不以情节取胜,有些篇目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人物虚化,甚至没有主要人物;意境优美,富有情调和意蕴。这也回应了小说美学的嬗变——故事在现代小说中正逐渐消解,传统故事中的转折、发展、高潮等因素被渐次抽离,取而代之的往往只是一种趣味、一种思索方式,甚至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妙悟。总结下来,当下的小说阅读应当摆脱与情节的纠缠,在意义的获得之外,更需要关注其独具意味的形式。
除掉散文化抒情小说文本的选择,考查角度和命题方式也出现了新动向。散文化小说打破传统小说叙述故事多以时间为序、层层推进的线性结构模式,不再关注故事的连贯性与完整性,有时错综跳跃,时断时续;有时盘根错节,枝蔓横生。所谓的中心事件往往只是起着穿线作用,克服了线状结构简单化的不足,增加了小说生活和情感的容量,使小说更富有立体感,更加丰满。正因如此,如果我们还执意从情节出发,对小说展开所谓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分析,既牵强又尴尬,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由此,单纯梳理、概括情节的命题方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从视角、人称、场景、留白、节奏和腔调等角度鉴赏小说。这对考生的文本细读、深读能力要求大幅提升。
今天很多学生说自己读不懂小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现代小说还融入了诗歌、散文等题材中常用的跳跃、留白和省略等手法。作家的任务不是给读者提供一个目的地,而是体验一段旅程,至于这段旅程能够带给读者什么样的收获,就不是作家考虑的范畴了。好的小说,一定能把读者的思绪延伸到文本之外。接受美学理论也因此进入高考命题的范围。
当然,现代小说一样注重布局安排,并讲究埋伏和照应,但更看重的是内在气韵和节奏。这就要求我们,无论课堂教学还是复习迎考,都应该引导学生把握现代小说的基本特征,摆脱与情节的纠缠,真正提高学生的阅读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