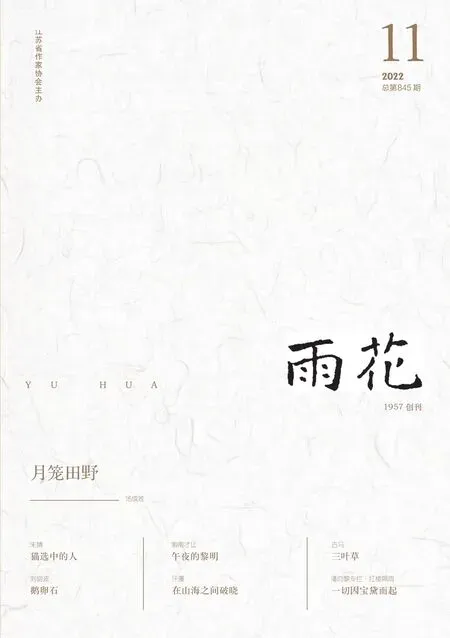明亮的落地窗
焦 冲
女主人和画家离婚后不到两个月,唐晓蕾就嫁给了画家。
在这之前,唐晓蕾从未有过非分之想,五年如一日,一声不响地做着分内之事:打扫、收拾这个足有三百多平方米的家,每一个角落、细节都不放过,按时做饭、洗衣服、遛狗、外出采购、给花草浇水等。作为男主人,画家似乎也从未对她有过超出雇佣关系的言行,甚至话都很少说,唯一一次较为近距离的接触是让她当模特,画了两幅她的半身照,穿得很严实,不该露的地方都没露。那两幅用色大胆、细腻逼真的油画在画廊挂了三周后以两万美金的价格售给了一位西班牙的收藏者。女主人看过之后曾说,大朴很少画人像,除非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大朴”是画家的艺名,夫妻俩说起对方都是如此称呼,就像他常称呼她为“卓杨”。
如果非要挑出一点儿与保姆身份不相符的念头,那就是每次清扫二楼的主卧时,唐晓蕾都极度渴望在这间房里睡到自然醒,只要一夜就已足够。不是和画家同床共枕,而是她一个人,四仰八叉躺在大床上,随便翻滚,把这里当成自己家,窗帘不拉,任星光、灯光穿过玻璃,洒进室内,等到早晨被阳光叫醒,一睁眼就看到亮堂堂的白天。不过她没这个机会,每次主人出远门,主卧和画室都会上锁,而她睡的保姆房朝北,两扇小窗户,唯有的阳光是别人家的玻璃窗反射过来的夕照,朝外望出去,只有茂密的树冠及其背后若隐若现的其他别墅。
婚后第一次有机会霸占整个卧室时,唐晓蕾兴奋得差点儿失眠,过了十二点依然毫无睡意,找到以前女主人偶尔会吃的安眠药吞下一粒后才渐渐入梦。早上还未完全清醒,身体已感觉到了阳光的热度,以及模糊、梦幻的光影变化。慢慢睁开眼,高大的落地窗像一面透明发亮的悬崖,矗立在她的面前,阳光涌入,几乎充满整个卧室。她揉揉惺忪睡眼,依然不敢相信自己成为这里的女主人已经一个多月的事实。阳光在她裸露的皮肤上跳跃、闪耀,她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才起身去淋浴,然后穿上真丝浴袍来到厨房。保姆已做好早餐。
早餐有烤吐司、花生酱、鲜榨橙汁、绿叶沙拉和只煎一面的太阳蛋。在此生活了五年多,她已习惯两位主人偏西式的饮食习惯。只是偶尔,她会想念刚来到这座城市时在一家大众餐厅做服务员的那几年里吃过的豆腐脑、小米粥、小笼包、茶叶蛋和咸菜丝。男主人和女主人每次吃早餐都充满仪式感,很少使用筷子,多用刀叉,不说话,拒绝发出声响,喝茶或咖啡也是小口小口地啜饮,擦完嘴巴的餐巾依然平整。耳濡目染,唐晓蕾逐渐接受了这种优雅、文明的进食方式,每次放假回到老家目睹父母和亲戚大口咀嚼、吧唧嘴,便会产生生理性厌恶。
用过面包、一个煎蛋和半杯橙汁后,唐晓蕾刚想收拾,马上意识到自己已非保姆,遂起身。自从画家第一次同她睡了之后,就不再把她当保姆看待,不再让她干任何活儿。保姆过来收拾,并询问中午画家是否回家吃饭,以便安排餐食。唐晓蕾说,等我问大朴。她回到卧室,给老公发了微信,半天没有回复。昨晚他肯定在画室休息了,除了家里,还有个更为专业的画室,就在以“大朴”命名的艺术馆内。他的绝大部分成品都在那里展出,除了油画、国画、水彩画和素描,还有雕塑、书法、剪纸、木刻等其他形式的艺术品,共千余件。做保姆的第二年,出于好奇,唐晓蕾曾去馆内参观,她看不出那些作品好在哪里,也不懂大朴想要表达什么,但看上去就是高端、上档次,就像大朴和卓杨的日常生活一样令她这个旁观者觉得舒服、愉悦,进而羡慕。唯有临近出口的小店内售卖的周边产品,比如台历、玩具和挂件,让她觉得可爱,且价格合理,于是买了一件钥匙扣,上面挂着树脂材质的小狗,比原件雕塑缩小了无数倍。她一直挂在身上,有一次被大朴无意中看见,他一个字没说,只淡淡地嗤笑,目光中包含的宽容和轻蔑,是她很久以后回忆时才体味出来的。
主卧旁边是书房,有书架、桌子和椅子等,以前这里主要是女主人的地盘。她是位作家,“卓杨”是她的笔名。不招待客人、不外出的时候,她会坐在这里打字,目光端凝,心无旁骛,每次唐晓蕾给她端上红茶和曲奇饼时都小心翼翼,大气不敢出。卓杨搬走后,室内摆设基本没动,她出版过的几本小说堂而皇之地摆在书架上,与卡夫卡、昆德拉、艾丽斯·门罗等人的著作为伍。唐晓蕾注视着一排排书脊,呼吸着书页在阳光下散发出的气息,带着一点儿霉味。隔上一段时间,她便将它们仔细地擦拭一遍,但从未想过翻开阅读。从小她就不爱读书,成绩差,勉强混了一张初中文凭便辍了学。她永远记得离开校园时的如释重负之感,简直如同刑满释放之人。妈妈在家唠叨了她几日,无非说她白花了这么多年的学费,一点儿脸也不给她长,还有年纪这么小,以后可怎么办之类的话。她没让父母操心,几日后跟随一个比她大两岁的同村小姐妹来到了省城,先在超市做收银员,干了两年多才到北京做服务员。后来听说保姆工资高,且不用伺候各种各样刁蛮的食客,她果断参加了培训班,先后换了三家主顾,直到进入大朴和卓杨的家才算稳定。
椅子很舒适,贴合身体曲线,软硬适度。那天晚上,她也是坐在这儿,几乎要睡着时,突然被轻微的声响惊醒。睁开眼,只见画家站在门口,盯着她,像在欣赏一幅刚刚完成的画。她愣怔片刻,正要起身时,对方按住她的肩膀,随后坐到她对面,用命令的口吻乞求道,陪我说会儿话。他的眼睛发红,酒气从嘴里喷出。她只得坐在那儿,听他发着牢骚。在语无伦次的控诉中,她大概听出了原委:卓杨移情别恋,和一个90 后畅销书作家上了床,当他得知此事时,卓杨提出了离婚,要抛弃大朴。画家很激动,骂道,这个婊子,我以为她跟那些女人不一样,到头来竟是一路货色,只不过心机更深,都想从我这儿沾光,把我当成垫脚石,出了名就过河拆桥!畅销书作家有什么稀罕?比我有钱吗?还是比我有人脉、有名气?她还不是和我一样被利用,等着吧,甭得意,有她被甩的一天!我对她那么好,她要什么我给她什么,她还有什么不满足?
唐晓蕾不知该如何安慰他,大朴和卓杨的世界她一直搞不懂,也看不透。她只觉得女主人这么做应该自有道理,但她委实无法理解,如果换成自己,她是不会主动离婚的,也不会做对不起画家的事,这么好的家,这么优渥的生活,她是不敢也不想破坏的。她就是嫌我老,你说是不是?画家冲着唐晓蕾嘶吼,仿佛她就是卓杨。唐晓蕾被吓得一激灵,随即强作镇静道,也许她有苦衷。说完,她伸出手摸了摸画家颤抖的手。画家反手抓住她的手腕,凑上前道,你不用替她说话,你们女人都一样。唐晓蕾的手被攥得生疼,挣扎着,委屈得差点儿流泪。画家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道歉,随即用胡子拉碴的嘴吻住了她。就在书房的地板上,画家把她占有了。消停后,他说,对不起,我会负责的。唐晓蕾闪着无辜的大眼睛道,负什么责?画家“扑哧”一笑,像逗弄猫狗那样揉搓她的脑袋道,你真是笨得可爱。
第二次发生在画家和卓杨办理离婚手续的当天,第三次是看见卓杨和畅销书作家晒蜜月旅行照之后,第四次是因为一幅画的售价破了之前的最高纪录,第五次是他的画作入选了今年加拿大的圣诞贺卡图案之后……唐晓蕾总结出一个规律,大朴和她做爱总是因为有着不同往常的情绪,不管是伤心的还是快乐的,不管是需要庆祝还是需要宣泄,只有这时才会做爱。而他们领证结婚的当天晚上,风平浪静,缺少外因刺激,反倒没有做,只是抱了一会儿便背对背各睡各的,像一对老夫老妻。在最近的一次交欢中,画家捧着她的脸说,见你第一面我就想睡了你。她“哼”了一声,不信。他又说,知道吗?你像一个人。她问,谁?你上学时暗恋过的姑娘?他道,不是。她问,那是谁?他道,说了你也不认识。她问,做什么的?他道,算演员吧,但一点儿都不出名,很漂亮,你也漂亮,还比她清纯。她道,得了吧。他道,真的,我喜欢你。她问,除了长得好看,我真没什么值得你喜欢的,脑子笨,还懒。他道,好看就够了,女人不需要太聪明,起码对男人来说是这样,而且你很乖,我喜欢听话的。
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母亲让唐晓蕾带大朴一起回老家。
自从她在城里落下脚后每年只回一两次,有时母亲会给她打电话,不管前头铺垫多少家常,最后总归落到钱上。挂掉电话,唐晓蕾就会给家里打钱,次数一多,她不等母亲唠叨完就问她需要多少,随后挂断,继而转账。当初母亲并不想让她去城里,她认为女孩子干伺候人的活儿就是自降身价,会影响名声,将来找不到好婆家。但唐晓蕾不想在镇上的服装厂做缝纫工,也不想在附近找男人——老家哪有好男人呢?有能耐的早出去了。母亲明知她在给人当保姆,却从不过问,似乎毫不关心,要起钱来却理直气壮。母亲嫌弃她,唐晓蕾很小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她不像姐姐那样听话、没主见,也不如哥哥孝顺、嘴巴甜。母亲要的钱不是给了大哥,就是给了大姐,这一点唐晓蕾也很清楚:大姐没上过几年学,从小就帮父母分担了诸多家务,确实过得比她苦;大哥是儿子,能给老唐家传宗接代;只有她像个多余的,没有任何实用功能,如今赚了钱,自然要拿出来报答养育之恩。
当母亲得知唐晓蕾嫁给了一个老男人时,冷冷地说,你们别回来,我以后尽量不联系你。然而,没多久母亲便食言,主动联系了唐晓蕾。原来父亲犯了病,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心脏问题,前些年吃点药还能维持正常,但那次检查后,医生明确告知必须马上做搭桥,否则会危及性命。大哥大姐皆摸不着门路,母亲慌得没了主意,只得给唐晓蕾打电话。大朴得知后,一脸淡定,先是安慰了唐晓蕾,让她不要着急和担心,次日打了几个电话,轻而易举安排好了三甲医院和心脏科专家,等到下午岳父一到北京便被接到医院,迅速办理手续,住进了单人病房,省却了在唐晓蕾看来非常繁琐和困难的就医程序。隔天检查后,确定了方案。手术做得很成功,父亲在医院里被照顾得很好。每天只有下午三点以后能探视,且不超过一个小时,唐晓蕾来过两次,大朴一次都没来过。
经历了这一遭,家里人对大朴的印象大有改观,因此母亲才会邀请他们回家。唐晓蕾跟大朴说了此事,他并没有不高兴,更无排斥,还说,早该去看看,毕竟是你的娘家,我也许多年没到过农村了,不知道变成了什么样儿,说不定还能找到灵感。虽如此说,可唐晓蕾明白他肯定受不了乡下生活的粗糙和简陋,就算饮食上能将就,住宿方面也成问题,别说他,就连她自己都已睡不惯农村的大火炕,何况房间根本不够用。她说,我们只在初二回,吃完午饭待一会儿就返程,看看爸妈就够了。大朴说,怎么着都行,听你的。
大朴不想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们,她能理解,其实她也不太想让自己的亲戚们见到他,只因他年纪太大,大到可以做她的父亲,她不怕亲戚们如何看她,但她担心大朴受不了。为此,唐晓蕾没有提前告知父母要回家的消息,但在他们抵达老家后不久,亲戚们陆续赶来,她明白是父母通知了他们。大朴却一点儿都不尴尬,明显掌握了话语权,似乎不管什么话题他都能聊,就算不懂,别人稍微一解释,他立马就能输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从而成为本次家宴的绝对主角。当然了,唐晓蕾觉得,多半是因为红包的关系,来之前他就准备了很多红包,其中两个厚的给了父母,其余的都给了孩子,不管远近亲疏,见者有份。明明都是第一次见,亲戚们却一点儿不认生,围着他问东问西,大朴也一点儿架子都没有,根本不像平时那般高冷。唐晓蕾转身去了厨房,除了母亲,姐姐和嫂子也在里面帮忙。
妈,你看,小姑父给我的,整整十张哈。唐晓蕾的侄子拿着红包跟他妈炫耀。
给我!嫂子试图抢走,可孩子早有防备,装兜里跑开了。给他那么多钱只会买用不着的。说完,嫂子对唐晓蕾道,他小姑父可真大方,有钱还会来事儿,你真是拣到宝了。
唐晓蕾的姐姐听了这话,忙道,大方是大方,可年龄也忒大了点儿,快赶上咱爸了吧?
年龄大又咋啦?懂得疼人。嫂子道,你哥年轻,可他知道啥?就是个土老帽儿。
瞧你说的。哪有那么老?唐母道,就算年纪大,看着也不像,城里人懂得保养。再说,这都是次要的,有钱的人多了,可瞧得起你,把你的亲戚也当家人看待的能有几个?大朴这人实在,上次你爸做手术多亏了人家,一个电话就搞定了,又是专家,又是高级病房,你爸这辈子哪享过这种福?再看你们,一听要做手术就吓得傻了、怕了,又没钱,又没本事,真要交给你们,怕是连门都摸不着,怕是你爸的手术现在也做不成。
妈,您这话可不公平。姐姐道,平时还不是我哥我嫂子伺候着你和爸?再说,吃穿用度上我们也没亏着你们,您不能因为我们没能耐就把我们的好处一笔勾销。这可当真是远的香近的臭了,有本事您去北京和老姑爷住几天,看人家给不给你脸色!
我才不去呢。唐母转头对唐晓蕾道,好姑爷能顶半个儿,你可要跟他好好过,收起小姐脾气,别总耍性子。唐晓蕾笑笑,欲言又止。母亲接着道,你不知道村里人有多羡慕你,连带着我和你爸脸上也有光。嫂子道,对,好好过,后年你侄女就毕业了,学的是设计,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还得麻烦她姑父。唐晓蕾一声不吭,望着案板上收拾好的鱼想,难道自己活着仅仅是为了对别人有用吗?
走出厨房,走出家门,唐晓蕾来到兰泉河岸边。冰封大地,衰草瑟瑟,白杨树们沉默着,天空蓝得叫人心碎。阳光照在冰面上,反射着寒意。几个孩子在冰面上放“二踢脚”,偶尔一声清脆的炮声响彻高空,抬头只见一团烟雾,像一朵游云曼妙地卷起,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硫磺气味。故乡变了不少,房子多了、高了;人少了,老了,死了。也许,某一天这个小村将不复存在,变成城市,建成工厂,高楼大厦,或是一片墓地。
唐晓蕾低头沿着河岸行走,踩着厚厚的落叶,漫无边际地遐想,忽然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抬头,只见一对男女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站在她面前,男人头发短得像是刚从号子里出来,露出锃亮的头皮,女人烫的爆炸头,染黄了,发质不好,看上去像是肩头堆着干草。
不认识我了吗?男人问。
男人那两道像毛毛虫一样的粗眉让唐晓蕾想了起来,叫道,黄津宇?
是啊,老同学,多少年没见了,你怎么越来越年轻,吃了防腐剂吗?黄津宇拙劣地调侃道。
看你说的。唐晓蕾再次打量这三人,问道,你儿子?
黄津宇道,对啊,我的老婆和孩子,听说你嫁入豪门了?
别瞎说。唐晓蕾问,你们在哪儿发财?
上哪儿发财去?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他道,我们俩就在县城,做点儿小买卖。
挺好的。唐晓蕾不知该说什么,又聊了几句,便借口要去二叔家,与他们分道扬镳。黄津宇说,有空来我家坐坐。她敷衍道,好。那一家三口越走越远,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唐晓蕾抬头望着光秃秃的树枝,旧时光像书页中夹着的干花赫然浮现于脑海中。黄津宇是她的小学和初中同学,和她一样没有念高中,跟着他爸卖了几年菜。上学时,他就给她写过情书,后来又曾托媒人说过媒。他长得不错,人也好,可当时她刚进城两年多,根本不想嫁给农村人。好不容易出去了,怎么可能开倒车呢?所以她一口回绝,因此还曾被老家的人奚落,说她异想天开,只想攀高枝。如果当时她答应了……嗐,人生哪有什么如果呢?
午饭后没多久,唐晓蕾就撺掇着大朴回京。大朴余兴未了,边开车边对唐家的人评头论足,说唐晓蕾的嫂子一定有外遇,就算没有,估计也过不长,又说唐晓蕾的外甥女是个厉害角色,将来能成大事。唐晓蕾哂笑道,什么叫成大事?像我一样嫁个著名画家吗?大朴严肃地说,非也,这姑娘不仅有才,还有个性,说不定能成为女强人。她看着窗外,一声没言语,只觉得以后再没回来的必要,这里早已不是她的家,她的人和心只能在大朴这儿寻求安居。
大朴虽是自由画家,可闲暇不多,大多数时候在画室,还要参加各种活动,真正陪伴唐晓蕾的时间很少。一旦不需要做家务,她感觉时间好像多到用不完。既然大朴爱的是她的脸蛋和身体,那她只能花他的钱,尽量保持这份本钱,就像他常说的: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大朴给了她一张信用卡,让她随便刷。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吗?唐晓蕾没有迟疑和忸怩,敞开了欲望:定期到美容院做光子嫩肤、补水保湿、瘦脸针、水疗、全身去角质、修眉、按摩推拿等各种保养;每周四次到健身房,跳操、练瑜伽、减脂塑身;每周去一次理发店,保持发型、发色和发质;定期到各大商场采购昂贵的化妆品、护肤品和衣服、首饰等。她身上的衣服越来越贵,包包也都是名牌,她活得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像个贵妇,那些专门招待她的美容师、售货员、理发师全认识她,巴结她,对她毕恭毕敬,殷勤备至,嘘寒问暖,端茶递水,称赞她瘦了,白了,比以前更年轻更漂亮,称赞她的衣服首饰高端大气,称赞她有品味。不过半年多的时间,她华丽转身,麻雀飞上青天变成了凤凰。每次看到她购买的各种奢侈品,大朴眉都不皱一下,只是在床上要求的花样渐多,他希望她能放得开,不要像以前那样矜持。食色性也,他说。
在上述活动中,唐晓蕾结识了若干和她一样有钱又有时间的妇人,几个人隔三岔五相约一起逛街、喝下午茶,聊最近上映的大片、明星八卦、保养心得,分享一些听上去相当私人的苦闷,实则典型的“凡尔赛”言论。聚会地点先是在外面的餐馆或咖啡厅,后来改成轮流到每个人的家中。有一次,唐晓蕾和另外四个女人围坐于客厅原木茶几旁,享受意大利咖啡和自制玛芬蛋糕,不知谁说了句稍微带了点儿颜色的话,惹得女人们笑得花枝乱颤,仿佛蓬勃的蘑菇从树根处往外蹿。而这时,画家刚好外出归来,望着几个人,一脸严肃中带着几分嫌弃,招呼都没打,直接“噔噔噔”上楼,随即传来一声不算太响却足以震慑客人的关门声。唐晓蕾脸上挂不住,马上解释道,他今天肯定画得不顺利,没有灵感。其余人忙解围道,没事儿,艺术家都古怪。意兴阑珊的妇女们逐一起身告辞,唐晓蕾抱歉地笑着,送她们到门口。
想了又想,唐晓蕾决定不能忍着,于是上楼。大朴正在书房看书,她坐到他对面,他眼皮都没抬一下。她说,你怎么回事?就算讨厌她们,也不用表现得那么明显吧?他斜睨了她一眼道,以后你最好跟她们断绝来往。她质问,为什么?你还不让我社交了?他冷哼道,社交?那些俗不可耐的妇女只会攀比、八卦、搬弄是非,你和她们混在一起,半点儿好处都没有,还没准闹矛盾。她道,那我干什么?你又不能天天陪着我!他道,看电影、看书、听听音乐,就算发呆、冥想,也比跟那些人瞎混强得多。她道,你说的那些我都不喜欢,再说,我总不能天天闷在家吧,不接触人还不成个傻子。他终于放下书道,人是要接触,但也得看什么人。她道,可我能接触到的就是这些人,我又不像你,身边都是文化人,不是画家、作家,就是导演,那么高端。他“哼”了一声道,他们也未必高端,社交的本质区别并不大。她道,那你怎么从来不把我介绍给你的朋友们,还不是嫌我俗,怕带着我掉价。他道,你别多心,我可从没看低过你,但我明白你和他们不是一类人,肯定说不到一块,跟他们在一起,我怕你觉得无聊。她道,不试试怎么知道?他直视着她的眼睛,那好,再过几天就是元旦,届时有个新年酒会,我带你参加,本来我还犹豫要不要去呢,没多大意思。
算是得到了满意答复,唐晓蕾离开书房。她想起自己做保姆那会儿,主人家中经常会来一些看起来非常体面、有涵养、有素质的客人。其中有男有女,有年轻的,也有头发灰白的、皱纹较多的;有好看的,也有其貌不扬的;有胖的,也有瘦的。穿着上看似随意,其实是一种刻意经营出的随性,不动声色地从细节渗透出精致的品位,这是唐晓蕾在主人家做得久了之后,认识了一些名牌服饰才得出的结论。他们往往聚在客厅,不时喝酒,也抽烟,谈论着文学、艺术和她不知道该归为哪类学问的内容,偶尔夹杂着几个英文单词,大多数时候氛围不算热烈,却不会冷场,有时也会爆发激烈的争论或是放肆的笑声。女人们修长的手指夹着细长的香烟,徐徐喷出一缕青烟,烟雾笼罩在他们头顶,形成一张飘渺的网,似乎自带磁场,不容外人进入或置喙。每当那时候,除了上茶、上果盘和点心,唐晓蕾都会躲在远处静静地观望。她羡慕那些女人,尽管她们有着各种各样肉眼可见的缺点,可是无一例外,她们都充满自信,是一种能够主宰生活和命运的自信,那让她们气质出众,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她明白,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她们,永远都不可能活得像她们那样肆意而洒脱。
和以往的诸多聚会相比,这次参加酒会的人更多,女人们更加光鲜靓丽,食物酒水更加丰盛,地方更加宽敞、富丽堂皇,彩灯等装饰营造的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唐晓蕾和大朴来得稍晚了点儿,他们到的时候,人们好像已经喝过一轮了。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场合,且之前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期待,因此刚进去时唐晓蕾有点儿亢奋,一张本来在车里闷得红扑扑的脸显得更加红润。除了大朴,没有一个人认识她,有几个人看着脸熟,但她叫不出名字。大朴的一些老相识围着大朴客套、寒暄。一个身穿露肩抹胸晚礼服的女人盯着唐晓蕾,对大朴说,嘿,快点儿介绍一下,哪儿来的这么漂亮的人。大朴说,这是我的内人。人们啧啧称赞,露肩女人道,哎呀,长得真标致,你要是被绑架来的,就跟我们眨眨眼。周围的人发出哄笑声,几个男人将大朴拥向酒桌处,嚷着要罚酒,问他迟到了是不是因为金屋藏娇。
露肩女人招手叫来服务生,让唐晓蕾从盘内取一杯红酒,并逼着她喝了一口。女人问,感觉怎么样?说是法国来的,不知哪个酒庄,我觉得还不如家里常喝的蒙塔齐诺。唐晓蕾不知如何回答,抿嘴一笑。对方用那双在上流社会修炼而成的火眼金睛一下便看透了她的窘迫。接着道,干吗那么娇羞?难怪大朴会喜欢你,可爱死了。老家哪儿的?唐晓蕾道,武安。女人夸张道,听说那里矿山很多,空气质量很差啊。唐晓蕾道,治理得好多了。女人并不答茬儿,兀自感叹道,你真是长得好命也好,要不大朴怎么放着那么多作家、画家、演员、主持人不要,偏偏娶了你,这可真是你的造化、他的福气哟。唐晓蕾尴尬地笑笑,很快咂摸出这话不是味儿,对方分明是在嘲笑她凭美色勾引到一个有钱的老男人,而这个男人也不是什么拔尖的,很可能那些作家、画家、演员都看不上他,只想和他搞暧昧,从中得到好处。女人的兴致似乎突然间消失,转身和其他几个女人热络地聊起来。
唐晓蕾杵在原地,听着那些漫无边际的谈话,失去了想要加入的欲望,甚至连动都不想动一下。人们在她面前鱼一般游弋,从这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角落,游刃有余而又充满计划和目的性,好像这是一场战役,而他们在不断占据着有利的战略位置。笑声和酒杯碰撞的清脆声不时短促地爆破,房间内的温暖让落地窗的玻璃蒙上一层水汽,变得朦胧。她觉得浑身燥热,可心坎里却又荡漾着一股接一股的冰冷。她看到大朴在和几个人谈笑风生,沉浸其中,看见露肩女人在热烈地谈笑,话语声如潮水一般涌进唐晓蕾的耳膜,将她推向深深的海底。好像有人说了一个词——保姆,她如梦初醒,定睛细看,眼前一派迷离。她上前和大朴打招呼,说自己想回去。大朴目光涣散地望了她一眼道,行吧,你先回,我还没到时候呢。说完,他扭过头,迫不及待再次融进那群人的热闹中。唐晓蕾并不渴望大朴挽留,因她亟欲逃离此地,可他的表现还是让她心里泛起一股酸涩。她迈着机械的步子,乘电梯,出大门,来到马路上,在冷风中拦下一辆出租车。
回到别墅,唐晓蕾进了卧室。没有开灯,她躺在柔软的地毯上,跌进了巨大的寂静中,偏头望向窗外,黑魆魆的,她听见血液在血管里静静地流淌。多么宽敞的房子啊,简直像宇宙一样空旷。以前她曾想象住在大房子里的人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后来她曾亲眼目睹并且艳羡这样的生活,而现在她得到了这样的生活,可是她想象过在这里生活的幸福,见过别人在这里过得开心而惬意,却始终没有预想到住在里面的寂寞、孤独和寒冷。她想要的是一个家,可大朴给她的只是居住空间。她买的那些奢侈品装满了抽屉、衣柜和其他空间,满满当当,可她的心空得仿佛一栋废弃多年的豪宅。
躺了许久,她才打开灯,去了书房。也许应该听取大朴的意见,看看书或者电影,充实自己。大朴的笔记本电脑就在书桌上,没有关。她移动鼠标,用惯了手机和平板的触摸屏,因而动作略显生疏,但并不妨碍她打开一个个文件夹和其中的文件。确实存着许多电影,可都是外国片子,就算有字幕,她也没兴趣看下去。无意中打开一个文件夹,里面存满了女人的照片,她们一律穿得很少,或是干脆一丝不挂,对镜头做出诱惑而羞耻的动作。她看得出来,这些都是从事色情行业的日本女人。随着不断点击,其中一个女人引起了唐晓蕾的注意,越来越觉得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那眉眼,那脸型,哦!她怔住了,这个人长得很像自己。一瞬间,她想起了大朴对她说过的话,说她长得像一个女人,还说那女人算是个演员……
唐晓蕾来到卧室,在黑暗中倒在大床上,感觉置身深井,仿佛自己不属于任何时空,被所有人抛弃,连自己也弄丢了自己,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她,她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坐标。我想要的只是一点理解和尊重,为何这么难呢?她因为痛苦而无比清醒地思考着,难道自己有勇气离开这栋别墅,去寻找新生和尊严吗?还会有其他可能吗?还不是像从前一样伺候人,步步为营地禁锢着灵魂,渴望着得到目前已拥有的,日子犹如在恶性循环,再也走不出去了。生命原来是场虚无啊,她叹了口气,起身开灯,注意到了床头柜上的安眠药。
起身,她抓起那瓶安眠药,来到浴室,打开水龙头,调好温度,看着水流注入洁白的浴缸。浴室内也是落地窗,灯光穿透玻璃,在黑暗中照出一块惨白的长方形。唐晓蕾脱光自己,躺进浴缸内,刚好望见窗外几根枯瘦的树枝,反射着微弱的光,宛如嶙峋白骨。她打开药瓶,全部吞了进去。渐渐地,她觉得眼皮发沉,身体在不断地坠落,坠落,坠向深渊和自由。
酒会凌晨四点多才结束,大朴先去了画室休息,直到次日下午方回家。发现不对劲时,唐晓蕾已没了呼吸,身体冰凉。她的头枕着浴缸的边缘,一只胳膊和部分长发垂在外面。大朴刚想移动她,灵感倏忽袭上心头,赶紧搬来画架和颜料等东西,调整到最佳角度,开始作画。她为什么要自杀呢?这么优质的生活,我对她又这么好,她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大朴边画边想,这时他注意到她的人中又窄又短,据某个面相大师说这是短命的象征。哎,他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是个没福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