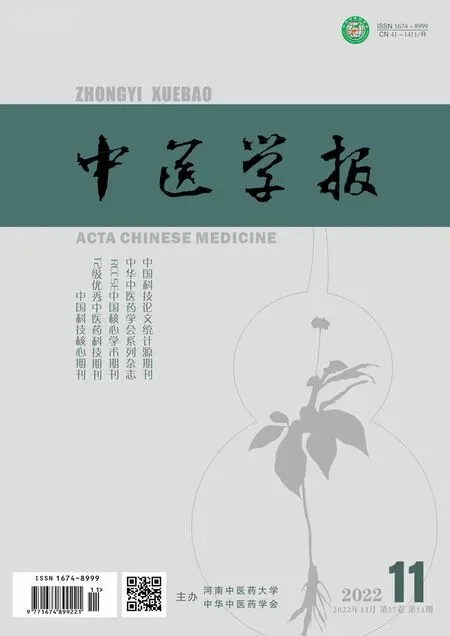《脾胃论》用药将息法初探*
翟付平,白海燕,王力普,李春蕾,马伟
1.河北中医学院研究生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2.河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1
《脾胃论》是由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晚年所著,是东垣学说中理论精华最为集中的部分。李东垣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开创了疾病的内伤学说,强调“元气为人身之本,脾胃是元气之源,脾胃伤则元气损,元气损则诸疾生”,开创了中医对脾胃的新认识,重视脾胃在精气升降中的作用,独树一帜地形成了脾胃学派,对后世影响极大。脾胃为元气之源、气机升降枢纽,是贯穿《脾胃论》的一大思想特色[1]。书中同时论述的还有五证五药、升降浮沉、分经随病、因时随病制方、君臣佐使制方以及用药宜禁、药后将息事宜,以上几个方面共同构成了脾胃学说的内涵。
1 脾胃为元气之源
元者,为万物之本也[2]。元气首次记载于《春秋繁露》,与《黄帝内经》中所提的真气内涵具有重叠性,故在《黄帝内经》及《难经》中称之为真气、原气[3],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和最基本的精微物质,化源于肾,为先天之本,并依赖脾胃所化生的水谷之精充养,中医经典多重视肾气的充足与否,而李东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认识到诸疾的形成是由于自身气的不足,究其根源是由于脾胃功能受损所致。正如《脾胃虚实传变论》所载:“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
元气的充裕与否和机体功能的正常发挥密切相关。元气的主要功能一方面为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和生殖,另一方面为激发和推动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活动[4]。元气充裕,各脏腑、经络得以充养,功能旺盛,机体强健。反之,则会因元气亏虚而产生种种疾病。“养生当实先天之元气,而欲实元气,当重视调理脾胃”[5]。元气为人身之本,脾胃为元气之源,脾胃虚损,元气失充,诸疾得生。故欲使疾病得愈,先使脾胃得调。
2 脾胃为气机升降枢纽
同时,李东垣在注重脾升胃降中尤其强调脾生长、升发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精微之气上输心肺,流转周身,元气才得以充实,身体机能才得以活跃,阴火才得以下潜。反之,精微之气不升,脾气下行,元气亏虚,机能消沉,阴火上逆,诸病以生。故在临床治疗疾病时,喜用补气升阳药,诸如升麻、柴胡等,以从其生升之性[7]。
3 五证五药
李东垣在长期的临床经验中总结出一套脾胃病的常规处理方法,称之为“五证五药”,用之如臂使指,无不效。因脾居中州主运化,其性喜躁而恶湿,机体湿邪较著时,阻滞于中焦,脾失健运,湿邪愈重,气机阻滞,出现怠倦嗜卧,四肢沉重,口淡乏味,大便溏泻,此应燥湿运脾,治从平胃散加减;脾肺二脏在五行生克制化的关系中属母子相生,脾胃亏虚,脾不生金,肺脾两虚,肺卫不固,气弱自汗,身发低热,大便泄泻,皮糙毛枯,毛发脱落,此应益气建中,治从黄芪建中汤加减;《黄帝内经》载:“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若胃气虚衰,胃之受纳、腐熟功能受损,脾之运化、升清功能不全,阳虚不能生阴血,气血生化乏源,营血虚滞,脉虚而细涩,此应调和阴阳,补血活血,使得阳生阴长,阴阳和合,治从四物汤加减;脾胃元气虚弱,运化乏力,气血生化不足,面色萎黄,言语低微,气短脉弱,此应健运中焦,治从四君子汤加减;脾之运化水湿失常,脾土乘肾水,脾湿下流,下焦气化失司,头目晕眩,烦渴欲饮,脐下动悸,小便闭涩,黄赤而少,此应温和脾阳,化气利湿,治从五苓散加减[8]。
4 升降浮沉
升降浮沉理论源于《黄帝内经》,后世历代医家对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9],尤其是金元时期,名家辈出,从不同角度对升降浮沉理论进行补充。李东垣在继承其师张元素脏腑辨证学说的基础上,创立内伤学说[10],《脾胃论》中所载补中益气汤,可充分体现李东垣对升降浮沉理论的理解[11]。《黄帝内经素问》提出人体活动基础为“升降出入,无器不有”,针对疾病的病因病势不同给予不同的治法,提出“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以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等[12]。
李东垣所创补中益气汤是针对因起居不时、劳倦内伤造成脾胃虚弱、气虚下陷的患者而设,强调病变脏腑在中焦脾胃,脾升胃降功能失常,纳运乏力,清阳下陷,故治疗时以益气补中,举阳升陷为主[13]。在选药组方中根据药性寒、热、温、凉之别,药味酸、苦、甘、辛、咸、淡之差,作用趋势之升降浮沉的不同,分阴阳下药,以对应春夏的升浮和秋冬的沉降之性[11]。方中黄芪、甘草、人参三药同用,为除湿热烦热之圣药,可祛气虚发热,身烦躁扰之症;“脾始虚,肺气先绝”,故加性温味甘的黄芪益气补中,升阳固表,大补脾肺之气,以资化源,使气旺血生[14],故全方用量最大,为君药,配以少量轻清升散的柴胡(性寒味辛)引清气,行少阳,少许性寒味辛的升麻引阳明清气上升以复本位,达到“益皮毛之气,而闭腠理,不令自汗而损其元气”的效果;上喘少气懒言,不足之症,少量性平味甘的人参徐徐补之;脾胃虚弱,脾不升清,精微下流,心肺阴虚,虚热内生,此为阴火[15],少量性温味甘的炙甘草、性温味甘苦的白术培补脾胃,除胃中火热;阴火中生,以伤阳气,恐其耗血,故加性温味甘辛的酒当归养血和血脉;脾胃虚弱,运化无力,方中滋阴药偏多,恐清浊相干,故加性温味苦辛的橘皮助清气上升而导滞气,使全方补而不滞。本方药量普遍较小,皆因脾胃虚弱类疾病为慢性久病,治疗时恐过犹不及,故以少量药物微微扶持,正所谓“欲虚而下陷之气,有升而上浮之机”,待脾胃升清降浊功能得以正常,方可见功[16]。
5 分经随病
李东垣在《分经随病制方》中以通气防风汤[17]和羌活胜湿汤为例,讲述了察一症状而知所犯何病,归于何经,用何引经药[18]。如风寒汗出,肩背痛,小便频而短,归属于手太阴肺经;肩背痛,不可回顾,颊颌肿,归属于手太阳小肠经;脊痛项强,腰似折,项似拔,归属于足太阳膀胱经;嗌痛颌肿,脉洪大,归属于足阳明胃经。在用药时,根据患者具体病情,选用合适的引经药物,直达病所,如脚腿沉重无力,加汉防己、附子,重则加乌头少许,引经疗病,散其寒;肺胀,膨膨而喘,胸高气满,壅盛而咳,加五味子、人参、麦冬、黄连,散其热,敛其气,养其津,止其咳;耳明目黄,颊颌肿,颈、肩、肘、臂外后兼痛而面赤,加防风、羌活、藁本、甘草、黄连、黄芪以通其经血、消其肿痛、益其元气[19]。亦如书中所言:“脾胃不足之证,须少用升麻,乃足阳明、太阴引经之药也……更少加柴胡,使诸经右迁,生发阳明之气。”
6 因时随病
李东垣在《脾胃虚弱随时为病随病制方》中以黄芪人参汤和除风湿羌活汤及调中益气汤为例,讲述了治病用药因病症的不同、发病时节的差异而选用合适的治疗方法及药物,此亦迎合了《伤寒杂病论》中辨证论治的观点[20]。在治疗夏月飧泄,完谷不化,胸闷短气,便后赤白下血,所用调中益气汤益气健脾,祛湿和中,无不见效。若治疗期间兼夹其他变化,诸如身体燥热、虚烦,此为下焦阴火蒸腾而上所致,可酌加生地黄、黄柏少许,以滋阴泻火除蒸;大便时有时无,排之不净,此为机体血虚不得濡养所致,可酌加当归身少许,以补血润肠通便;身体沉重,小便频数,此为足太阴脾病,运化无力所致,可酌加茯苓、苍术少许,以健脾利湿排浊;恶热而烦渴或偶有腹痛,此为中焦热盛,烧灼胃阴所致,可酌加白芍、黄芩少许,以清热缓急止痛;恶寒而腹痛,此为中焦阴气较盛所致,可酌加桂枝少许,以通阳化气散寒。
李东垣治病养生思想秉承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治病养生用药皆须遵循自然界规律,则机体阴阳平衡,精神乃治,邪不可干[21]。其主张不当于五脏中用药法治之,当从《素问·脏气法时论》中升降浮沉法用药耳[22]。治疗用药方面,李东垣常根据四时节气差异而选用不同性味的方药,春月加清凉之药,夏月加苦寒之品,秋月加温气之药,冬月加辛热之品,依据四时用药方可“不绝生化之源”[18]。《随时加减用药法》中以治疗咽喉堵塞为例,以辛甘气味俱阳之药畅胃气治其本,堵塞之药调气机泻其标,另随四时节气进行加减,夏月阳气旺,于方中加理气之青皮等散寒气,泻上逆之阴火;冬月阴气盛,于方中加辛热之吴茱萸泻阴寒之气。又如食物不下,阻于胃中,在治疗该证基础上,可另加以下诸药,初春时节,寒气犹存,稍加辛热之品,益智仁以增春气;春三月,阳气渐胜,稍加风药,青皮、陈皮以退胃上之寒;夏月阳气旺盛,湿邪偏重,稍佐黄连以燥湿清热;秋月气燥,津液耗伤,胃中失润,稍佐生津益胃的沙参配合行气开胃消食之白豆蔻以滋而不滞;冬月阴气寒重,稍加温脾和中益气之益智仁以散脾胃寒邪。此即正合《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所记载的养生思想,“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23]。”
7 君臣佐使
李东垣在《君臣佐使法》中遵《黄帝内经》原则指出主病为君,佐君为臣,应臣为使,又受张师所提力大者为君的影响,认为君药分量最重,臣药次之,使药又次之,君臣有序,主次有别。故纵观全书63首方,101味药,君药皆为治疗主病主证,臣药辅之,法度严明,相与宣摄。是以《肠澼下血论》中升阳除湿防风汤为例,该方在原文中为治疗或大便秘结,或里急后重,或赤白下血,而不可妄用泻下之剂,究其原因为脾胃亏虚,阳气下陷,升举无力所致,故方中以苍术四两为君,燥湿健脾益胃;防风二钱为臣,祛风胜湿,除肠风飧泄而升阳;白术、白茯苓、白芍各一钱为使药,燥湿利湿,柔肝缓急,防土病木乘而和脾。诸药合用,使阳气自升,阴气自降,病症得愈,此充分体现了以君臣佐使为法则,使得方药结构严谨有序,机理明晰,疗效切实可靠,体现中医药诊疗特色[24]。
8 用药宜禁
李东垣在对脾胃病的治疗中,突出重点,考虑周详。在《用药宜禁论》中所提四禁,为时禁、经禁、病禁、药禁[25]。时禁与四时随病用药原理大致相同,用药需遵循四时升降之理,春宜吐,夏宜汗,秋宜下,冬宜藏,莫要失天信,伐天和。正如《黄帝内经》所言:“夫四时阴阳者,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逆其根伐其本,坏其真矣。”又有冬不言白虎,夏不言青龙,春夏避桂枝,秋冬防麻黄之说。经禁为遣方用药需遵循经络自身特性,分经用药,足太阳膀胱经为风寒所伤,宜汗法,传入肾经则利小便,万不可用下法;足阳明胃经为多气多血之经,如有腹满胀,宜下法,禁发汗、利小便,恐伤津液;足少阳胆经行身之两侧,病有往来寒热,宜和法,禁发汗、下法、利小便,恐生他病。病禁为根据患者所犯疾病的特点,分而用药,若自身阳气偏弱,阴气旺盛,则用药饮食应助阳泻阴;淡食及淡味药皆升,苦药及厚重之品皆降,用药时注重调节平衡;诸辛热之品助火而泻元气,诸生冷之品损伤元气,亦当禁。药禁为根据病情特征决定禁用何药,大便秘结,当用和血润肠之品,诸如当归、桃仁、麻子仁等,禁用燥热性药物;胃气不行,口干欲饮,非津液枯涸,而是输布障碍,可应用辛酸健脾胃之药,禁用淡渗之品。在临床中应做到察时、辨经、审病,而后用药。
9 药后将息
李东垣在给予患者诊治后十分注重药后调理,主要归结为两方面,为“摄养”“远欲”。其“摄养”主要为生活起居方面,如沐浴后应避风寒,及时对所穿衣物进行加减,对于冷食,可依时暂食,切勿贪耽嗜。“远欲”则为摆正自身心态,淡薄情志,省语养神[26],人有五脏化五气,五气太过则伤其脏。《省箴言》载:“积气以成精,积精以全神,必清必静,御之以道,可以为天人矣[6]”。
10 结语
通过对李东垣治疗脾胃病所运用的学术思想及遣方用药所遵循的不同细则进行总结,其治疗疾病时始终牢记脾胃为人体升降之枢,紧扣病机,不被表象所迷惑,所著《脾胃论》为其思想之大成,为后世医家所传诵,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