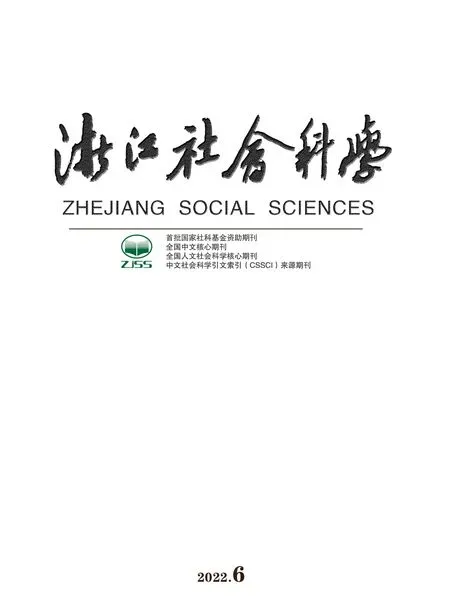来华外国人“居民化”融入:社区组织的角色担当及行动策略*
——以义乌市L社区为例
□ 陈建胜
内容提要 自来华外国人由定点酒店居住转向当地社区聚居以来,社区融入问题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议题,政府相关政策已经从偏重治安管理服务发展到倡导“居民化”社区融入。本文以义乌市L 社区为例,着重探讨社区组织在来华外国人“居民化”融入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行动策略。作为党的领导和政府行政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延伸,我国的社区组织同时也是基层社会的建制性设置,其角色担当和行动策略也必然与国外社区组织有所不同。通过解剖分析L 社区的实践案例可发现,社区组织不但要负责政府的“居民化”融入政策在社区层面落地见效,同时还要负责回应或平衡来华外国人的非常规性社区融入需求,负责重塑与“居民化”融入利益相关的多元主体整合机制,确保整个社区的和谐融洽和稳定有序;此外,社区组织还会基于自身角色定位以及社区实际情况,灵活采取诸如以治理平台化夯实来华外国人社区服务、以组织分支化吸纳来华外国人社区参与、以关系圈层化培育来华外国人社区认同等具体行动策略,以便更有效地把来华外国人的“居民化”融入落到实处。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研究的文献简述
(一)问题的提出与“居民化”融入
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来华外国人由定点酒店居住转向当地社区聚居,管理与服务如何跟进、社区内部整合如何实现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相关部门及当地社区。虽说在国家层面上,2016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促进社会融入、加强社会服务、完善日常管理”,并于2018年成立了国家移民局,专司管理来华外国人签证、居留、移民等事务,在减少“多头管理”、“重管理轻服务”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来看,在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问题上,迄今仍未跳出本国居民与外籍人员的“二元区分”模式,而且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也尚未出台可涵盖永久居留与非永久居留来华外国人的社区融入政策。从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情况看,在当地社区聚居的来华外国人,取得永久居留权证(俗称“中国绿卡”)的只是少数,绝大多数都属于非永久居留人员,而在笔者做田野调查的浙江省义乌市L 社区,占比更是高达99%,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在当地社区居住五年甚或十年以上。这无疑是讨论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问题所应关注的重点。义乌市作为商贸型来华外国人较多的城市,L 社区作为来华外国人居住较集中的社区,在这方面所做的实践探索及其经验,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借鉴意义。本文拟通过对L 社区的解剖分析,提出并回答以下问题,即在推进来华外国人“居民化”社区融入的过程中,作为基层建制性设置的社区组织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在相应的角色定位下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策略?
L 社区地处义乌市主城区东部,是由城中村和现代都市小区组成的社区,目前在该社区合计居住有4900 多人,其中中国户籍人口3500 多人、来华外籍人口近1400 人。从人口构成特征上看,属于较为典型的“国际化社区”,外籍人口涵盖74国家和地区,有来自也门、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埃及等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也有来自俄罗斯、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其中大部分从事商贸、咨询、餐饮服务等行业,经济收入普遍较好。L 社区是义乌市也是国内最早开展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的示范社区,2006年被义乌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列为“境外人员社区融入”试点单位,2014年在浙江省率先设置首个境外人员社区服务站,2019年服务站升级为社区境外人员服务中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L 社区已成为义乌市“国际化社区”建设及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的响亮名片。笔者从2019年开始对L 社区做追踪调研,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田野观察和访谈资料,因而本文的相关叙述和讨论,主要是以该社区作为实践案例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国家法律法规的角度看,绝大多数来华外国人都不属于“中国公民身份”意义上的“中国居民”,但他们来华后因长期居住和生活在当地社区,实际上已逐渐成为“社区成员身份”意义上的“社区居民”,——哪怕在当地社区干部以及户籍居民眼里,也已经不再是陌生的外来者,而是多少有些熟悉的社区成员。“从大的身份看,他们是护照,我们是身份证,那是有差别的,但在我们社区里面,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就一个身份,都是我们社区大家庭的成员。我们是按照社区居民的要求来推动他们融入的,要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要推动他们参与社区治理、参与社区服务,做好文化交流,建立良好关系等”(摘自L 社区组织负责人访谈资料)。因此,本文所说的“居民化”,不是一个法律或法权地位的概念,而是一个社区融入或社会整合的概念,因而“‘居民化’融入”主要是指,来华外国人在其聚居地社区,可平等地享有与当地社区居民相同或相似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与当地社区居民相同或相似的赋权、管理和服务等。
(二)相关研究的文献简述
国际学术界关于跨国移民社区或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大多沿着移民与当地社区或主流社会的关系展开,“同化主义”与“多元主义”往往被视为两种主要的融入模式。这两种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区组织所要扮演的角色,例如有研究者指出,与同化主义模式相比,多元主义模式更倾向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支持个体的自由整合①。更有研究者提出了“两阶段说”,认为在早期的“种族中心主义阶段”,社区组织主要扮演“差异的否认、防御及最小化”的角色,而在后来的“种族相对主义阶段”,则主要扮演“差异的接受、适应及整合”的角色②。移民与当地主流社会的关系问题,虽然触及到了社区或社会融入的核心,但仍需要考虑移民群体的特定需求和权利。曾有研究者指出,在英美国家中,社会融入侧重于提供平等机会及消除犯罪、保障参与权利和自由,而在欧洲大陆国家中,社会融入主要意指社会团结或社会凝聚,以消解市场一体化对特定群体的不利影响③。在社会融入概念的不同指向下,英国的社区组织更多地是扮演消除障碍与服务资源配置的角色,强调与“半市场”或“市场”机制合作推进移民及边缘人群参与社区,而法国的社区组织则扮演着垂直一体化角色,强调它是联结国家与公民的资源与权力的双向管道④。
在移民社区融入的具体实践场景中,政府融入政策、移民融入需求、当地社区组织等,都是影响融入过程以及融入方式的重要因素,其中,社区组织尤其是建制性的社区正式组织,扮演着“衔接”政府融入政策与移民融入需求的关键角色,担负着融入政策的纵向连接及其在社区的具体实施⑤。社区组织在移民社区融入中的重要性还表现在,移民通过融入社区正式组织,有机会获得高质量的社区社会资本,而移民群体关系网络及自组织等社区非正式组织,也对移民融入社区、发展社区社会资本等有着积极作用⑥。此外,近年来也有研究者依据政府融入政策、移民融入需求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对社区组织的不同影响,来探讨社区组织在移民融入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并结合社区组织的不同角色来说明不同的行动策略⑦。
在给定情境下,社区组织根据自身的角色定位,去选择推动移民社区融入的行动策略,例如,注重增进社会公平的社区组织,往往更倾向于采取那些有利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均衡资源配置、减少不平等的行动策略⑧;而注重增进社会团结的社区组织,其行动策略会更加偏重于提升组织维度的融入以及移民群体的社会资本,例如深化组织结构、发展支持性组织、改善社区管理等⑨。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发展粘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Capital)、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Capital)、联结型社会资本(Linking Capital)的行动策略,特别是联结性社会资本,通过嵌入在职业性、行政性结构及社区中,并与主流机构及主流人物建立联系,对促进移民融入主流社群有积极功能⑩。
相比较而言,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较为自觉地注意到了我国“社区”的独特性质,即“一轴多元”治理结构,以及党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有机结合⑪。在话语表述上,也大多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视为最重要的社区组织,强调它们在推进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例如有学者指出,由党组织和基层精英领导的社区组织特性,是“国际化社区”建设的支撑力量⑫。同样的,国内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政府融入政策及其变迁对社区组织的影响,有学者指出,随着政府的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政策从“特殊主义” 进到“居民化管理”,要求社区组织更好地承接公共服务以及更多地开展融合性治理⑬。
值得注意的是,“来华外国人”虽然“跨国”而来,因工作和生活需要而常住在当地社区,但他们大多数不是移民性质的,即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移民”,因而“来华外国人的社区融入”问题,不宜直接混同于“移民的社区融入”。此外,“社区”以及“社区组织”的属性或性质定位,在不同的国家往往也是差异很大的,作为党的领导和政府行政在基层社会的延伸,我国的社区组织同时也是基层社会的建制性设置,因而它们作为基层社会场域的行动主体,其角色定位和行动逻辑也必然是与国外社区组织有所不同的。我国社区组织在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中的具体角色担当及行动策略,除了受政府融入政策和来华外国人融入需求等因素影响外,还必须结合来华外国人在种族、宗教、收入、阶层、流动性等方面的个体特征,做出因人制宜的灵活处置或差异化回应,并围绕政府所倡导的“居民化”融入目标,重塑各利益相关方的多元主体整合机制,确保整个社区的和谐融洽和稳定有序。
不用说,国际学术界对社区组织在“移民社区融入”中的角色及行动策略问题,已经有长期的研究和丰富的积累,做得比较细也比较专业化,但涉及到社区组织在“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中的角色及行动策略,感觉还是国内学者更了解我国社区以及社区组织的独特性质和运行机制,相关研究也更加“接地气”一些。不过,理论研究与社区实践的关联仍然比较薄弱,对社区组织在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行动策略的讨论也显得较为粗糙或“碎片化”,而本文要做的,是通过深入解剖L 社区这个实践案例,对社区组织在推动来华外国人居民化融入过程中的角色担当及行动策略做出系统的分析和阐述。
二、“居民化”融入政策下社区组织的角色担当
(一)负责“居民化”融入政策在社区落地见效
义乌市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工作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06年至2013年为起步阶段,主要由公安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和社区参与,侧重于强化以户口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治安管理与服务;2014年以来为发展阶段,主要由民政部门牵头、社区主责、其他部门参与,侧重于构建有助于促进“居民化”融入的社区管理与服务,探索建设国际化融合性社区。
在起步阶段,公安部门开始试点“境外人员社区融入”,通过民警入驻社区将境外人员户口临时申报延伸到社区,建立起基于临时户口的管理服务机制,社区组织主要起配合作用,即辅助公安及相关部门开展法律及社区知识宣传,建立“语言培训站”和开展文化交流,以及发动热心居民参与社区调解、计生、巡逻等。这个阶段的相关措施或政策,着眼于为来华外国人社区生活提供便利,尽管个别政策也开启了“居民化”待遇,但总体来说,政策导向仍然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对待”特征,例如,在来华外国人子女就学方面,开放公办学校较少且所处位置偏远,难以像本地户籍居民子女那样享受就近入学;在社区治理方面,往往将社区内聚居外国人视为一个特殊群体,治安管理多于公共服务。
地方政府的政策优化或创制,一方面是立足于现实问题导向,另一方面则需借势于上位政策的目标要求。具体就义乌市来看,这个上位政策是2014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深化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若干意见》,该文件对义乌市提出了建设“宜商宜游宜居国际商贸名城”的战略要求。在这一背景下,义乌市迅即出台了《义乌市境外人员社区管理和服务实施办法(试行)》,在全国率先提出要“让境外人员平等地享有社区服务、参与社区决策、促进社区交流、建立境外人员社区归属感和责任感、共同营造国际性融合社区”的具体政策目标,这意味着来华外国人的“居民化”社区融入进入了实质性的发展阶段,包括回应他们在住房、生活、教育、医疗、社区参与、文化活动、社会交往、证件办理等多方面的现实需求,进行社区居民化的赋权、管理与服务。
为推动来华外国人的社区居民化进程,义乌市相关部门也加快了政策供给。例如,2014年民政部门出台关于“国际性融合社区建设”的文件,将来华外国人纳入社区居民自治体系,要求“引导鼓励境外人员有序参加社区的居民议事会、居务监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等居民自治组织”,并要求加快推进平等的“一站式”社区公共服务,促进文化交流与社区融合;2015年住建部门做出相关规定,允许在义乌境内工作、学习时间超过一年的境外个人购买符合实际需要的自用、自住商品房,为部分来华外国人在义乌当地长期安家立业创造条件;2016年教育部门进一步降低了来华外国人子女就学门槛,将具有招收外籍学生资格的学校从19 所增加到25 所,尤其是加大了公办中小学的学校数量,基本上满足了来华外国人女子就近入读的需求; 人社部门还就来华外国人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做出相关规定,在享受范围、报销比例及报销额度等方面可参照本地参保居民待遇;2016年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首创 “外籍商友卡”,其形制和功能类似于市民卡,汇聚有公共交通、泊车、图书借阅、就医、金融无障碍支付、信用查询、特约商户优惠等数十项服务功能,方便来华外国人获得当地城市或社区公共服务。
以上各项推动来华外国人“居民化”融入的政策,有些是由政府相关部门直接实施的,例如关于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社区组织不具有相应的界定和管辖权,但仍需要积极协助并负责在社区层面上落实,包括政策宣传、资源衔接、细化操作等;而有些则以社区组织为主要承接和实施主体,例如关于社区参与、社区融入、社区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政府相关部门往往只是给出指导性意见或原则性要求,需要社区组织根据所在社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负责贯彻落实。由此可见,作为党的领导和政府行政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延伸,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等建制性社区组织,也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即“居民化” 融入政策在社区层面落地见效的责任主体。
(二)回应来华外国人的非常规性社区融入需求
社区组织向上要面对政策法规或制度环境,向下要面对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需求,而这种需求往往与他们的个体或群体特征密切相关。聚居在L 社区的来华外国人绝大多数是来自中东、北非等地区的商贸型人员,虽说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但受教育程度不高、流动性较大,在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等方面,也与义乌当地居民有较大差异。因为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他们一般很少提及与经济权利分配或利益共享相关的融入要求,也不大会考虑劳动力或人才市场的平等问题,而且他们已经感受和认识到,我国的“社区”是社会单元而非包含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地方单元。商务的忙碌以及原生国家的政治生活传统,使得他们很少提及政治参与或权力分配方面的融入要求; 较大的流动性以及严格的出入境管理制度,使得他们更为关注社区安全、证件办理等公共服务。他们既希望多了解中国文化,多些文化交流活动,与社区居民保持友善关系,又希望活动场地、内容、仪式等能体现伊斯兰教特色,宗教生活及文化习俗能受到社区居民的尊重。
换句话说,L 社区来华外国人比较关心的,是社区生活的安全性、便利性、友善性,以及保持自己原有的宗教文化习俗。他们的社区融入需求,主要集中在出入境证件办理、房屋租赁、就近医疗、教育资源配置、纠纷调处、日常生活及法律政策咨询、志愿服务积分、语言培训及文化交流、宗教与文体活动、邻里友善等,部分在义乌当地居住时间较长的来华外国人,则有社区参与、交友联谊等更进一步的融入需求。除了希望在社区设置宗教场所、露天烧烤场外,他们的绝大部分融入需求都与政策指向较为一致,其缘由主要在于,政策制定部门较好开展了实地调研并吸收了试点社区的意见。在社区管理方面,由于文化习俗或制度传统方面的差异,来华外国人普遍倾向于“更少些管理”,但涉及卫生习惯与垃圾分类、信息登记与入户核对、聚会噪音控制、治安或安全检查等事项,“更少的管理”往往会衍生出其他问题,难免与“居民化”融入政策有较大的出入。
从L 社区的情况看,来华外国人一方面希望社区组织能提供“更多些服务”,特别是那些与他们需求相匹配的社区公共服务,也有兴趣参与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社区组织,并愿意与社区工作者建立良好关系,但另一方面又倾向于社区组织“更少些管理”,尤其是不愿意社区管理者干预他们的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不难发现,来华外国人对社区组织角色的期待,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互有矛盾的,如何回应来华外国人的非常规性社区融入需求,在“更多些服务、更少些管理”的角色期待中找到平衡点,对社区组织来说是一个考验。
(三)重塑“居民化”融入的多元主体整合机制
在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政策方面,义乌市无疑是国内探索较早也起步较早的城市,从相关政策构成看,虽然明确了总的原则和目标等,但内容和措施等环节还不够具体化,政策选项及其边界也往往较为模糊。这意味着政策的实施成效,会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社区组织的角色担当。社区组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既要坚持并致力于实现政府提出的“居民化”社区融入的政策目标,又要回应和平衡来华外国人期望的“更多些服务、更少些管理”的社区融入需求,同时还要考虑确保本地户籍居民的社区福利和生活秩序等不会受到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组织主要扮演以“整合”促“融合”的角色,即通过对政府部门、来华外国人、本地居民等不同主体需求的有效整合,达到促进或推动来华外国人“居民化”社区融入的目标。
L 社区组织负责人在接受访谈时,曾就社区组织在来华外国人居民化融入中的角色,做了较详细的如下叙述:“社区是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的结合体,这是我们的定位。我们要站在这个位置上去落实政策、去创新,去满足外国人的融入需要。现在我们义乌讲让外国人平等享有、平等参与,政府就是这么要求的。但是一些政策主体不是我们,像医保、社保、教育等,我们主要是负责那些落到社区内的,像社区服务、社区治理等,但这方面政策里面也没讲太清楚。外国人也有些特殊需要,如宗教文化、社会习俗等,所以我们提供和规范化了他们的宗教场所,这对本地居民也有好处,同时我们也拓展了一些政策上没有考虑到的服务内容,如一些陪护服务、邻里服务等。说白了,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把政府、社区、外国人、本地人、社会组织等整合起来,让大家都感到比较满意。”(摘自L社区组织负责人访谈资料)
由此看来,社区组织需要从科层体系与自治体系的结合点上,去考量和兼顾不同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或期待,重塑与“居民化”融入相关的多元主体利益整合机制。既要坚持政府的政策目标,把“居民化”融入政策嵌入到社区组织的角色定位中,另一方面又要鉴别来华外国人融入需求的合理性,在满足其合理或正当需求的基础上,保障社区全体居民的利益以及整个社区的和谐有序。社区组织所扮演的这种社区整合融入角色,与西方较为流行的同化融入角色、文化多元主义融入角色等有所不同。同化融入角色强调的是公民化过程和移入国价值观,注重公民权利在社区身份中的嵌套; 文化多元主义融入角色强调的是文化身份相对于社区身份的自主性,偏重于少数族裔权利、文化价值观的保护及社会包容性政策的落实;而社区整合融入角色所强调的,是居住身份与社区身份的统一,以及社区秩序、社区生活和社区文化的融合性特征,注重对居住生活等方面社会权利的尊重、落实与管理。
三、社区组织推进“居民化”融入的行动策略
(一)以治理平台化夯实来华外国人社区服务
从“街居制”转向“社区制”是国家改革和完善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举措,自2000年中办发布《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 以来,城市社区相继建立起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公共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等“三位一体”的社区组织架构,并由此推动了社区治理与服务的平台化发展。不仅如此,政府相关部门为拓展或延伸自己的职能,还会根据需要在社区增设新的平台,例如,政法部门在社区设置的网格化管理平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社区设置的退役军人事务站等;社区组织为有效回应不同方面或不同性质的居民需求,也会结合区域内居民特点及重要事项等设置相应平台,例如,针对少数民族居民较多设置“同心圆”服务站,为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设置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以及基于信息技术应用的数字化治理与服务平台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平台化” 已经成为基层社区组织回应上级任务部署与社区居民需求的重要行动策略,以至于有研究者提出,我国社区已进入了“平台化治理”阶段⑭。
L 社区在推进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工作中,首先想到的也是搭建融入服务与管理平台,经向政府相关部门汇报并获得支持后,于2014年正式建立起“境外人员社区服务站”。该服务站通过整合社区工作者、引入社工服务机构、开展志愿活动、成立自组织载体等方式,为来华外国人提供社区生活和交往融入等方面服务,同时也植入一些管理内容。其服务和管理工作主要包括:设立外商咨询服务热线及招募志愿者,开展交通出行、卫生医疗、法律知识、心理健康等咨询服务;成立社区跨文化交流协会,组织开展融合型的文体娱乐活动;开展基础翻译、中文培训、公共事务陪同等交往服务;开展社区安全、预防犯罪、噪音减控、邻里关系和谐等社区秩序与规则宣传。基础翻译、中文培训、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咨询等,颇受来华外国人欢迎,如中文培训项目自2014年推出以来,每届都有30 多名外国人报名学习,遍及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些学员已成为参与社区治理、志愿者服务的重要力量。
由L 社区首创的“境外人员社区服务站”受到义乌市政府的肯定和来华外国人的认可,其做法已被推广到义乌当地其他外国人居住社区,一些成果甚至被当地政府固化为政策文件。但与此同时,社区工作者也发现,来华外国人办理出入境登记、出租房屋管理、司法援助咨询等事项,仍然要跑到社区警务室或公共服务站,他们比较关注的就医就学、金融支付、公交服务、治安管理、志愿服务积分兑换等事项,仍然需要寻求社区协助。及至2019年,在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下,“境外人员社区服务站”升级为“社区境外人员服务中心”,除了增加办公场地面积和软硬件设施之外,将原来由社区警务室、社区公共服务站分担的来华外国人服务与管理功能整合进来,同时积极推动并吸纳其他相关部门及社区社会组织等入驻服务,形成集来华外国人服务与管理、公共服务与志愿服务、社区交流互动等功能的综合性平台。例如在该平台下实施护照志愿积分制,以1 小时计1 分,积满72 分即可兑换一学期免费培训课程。截至到2021年底,累计有来自25 个国家和地区的650 名外籍人员参加志愿服务4 万余小时,兑换免费课程600 余期,既培育和增强了社区志愿服务力量,又提升了外籍人员对于社区的归属感以及汉语水平和日常交往能力。
这种“平台化”的行动策略,把来华外国人的管理与服务、科层力量与自治力量、公共服务与自助服务等汇聚到平台上,通过“一门式”或“数字化”的整合,较好地实现了来华外国人社区管理与服务的高效便捷。无论是当地政府及L 社区居民,还是聚居在社区的来华外国人,都对“社区境外人员服务中心” 这一平台的建立及其在来华外国人居民化社区融入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较高的认可和评价。
(二)以组织分支化吸纳来华外国人社区参与
组织融入是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的重要环节,而能否融入正式社区组织,更是衡量社区融入水平的核心指标。按照社区组织在法律上的规制,不具有中国国籍的来华外国人一般不允许加入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但可以加入社区“两委”管理的社区其他组织,亦可采用兼职社区居委会成员等方式融入。为推动来华外国人的社区组织融入,L 社区采取了“组织分支化”策略,包括在社区组织中设立其管理的融合性组织,在社区组织下延网络中设置来华外国人管理服务岗位等。
在面对来华外国人因文化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差异所引起的邻里纠纷、社区纠纷时,原有的社区调解委员会往往感到难以有效应对,同时,一些在社区居住时间较长的来华外国人,也再三表示希望能加入社区组织。为此,L 社区于2018年成立了由社区两委指导的“中外居民之家自治委员会”,开展纠纷调解、议事协商、外籍志愿者统筹、外籍人员群体性需求等方面工作,并聘请在本社区居住十多年并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外籍人员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伊朗籍商人哈米担任会长。哈米掌握波斯语、汉语、英语、土耳其语等6 种语言,拥有义乌伊朗商会会长身份,既有语言上的便利,又有商会资源以及与其他外籍商会沟通方面的优势,便于开展多方位的调解和协商工作。“中外居民之家自治委员会”为进一步拓展自身职能和带动更多来华外国人融入,还下设了“国际老娘舅”和“洋更夫志愿服务队”,合计有来自近30个国家的50 多人参加,其中“国际老娘舅”已协助调解涉外纠纷90 余起,涉外纠纷调解金额达到1300 余万元。
在社区组织既有下延网络中设置便于来华外国人参与的管理服务岗位,也是组织分支化策略的重要举措。L 社区的具体做法包括:在居务监督委员会下设置“社区监督岗”,除了中国籍居民外,聘任了4-5 名外籍人员担任联络监督员,以外籍人员视角监督社区治理事务; 针对出租房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组建了由房东、楼(栋)长、本地与外籍协管员组成的组织网络,其中外籍协管员负责与外籍人士沟通、信息反馈、需求调查等;遴选和吸纳在社区外籍居民中有一定代表性的热心人士,如伊朗的哈米、也门的巴沙塔、埃及的库里亚等,担任作为居民委员会重要延伸力量“居民骨干”。正如库里亚所谈到的:“社区选我当联络监督员、居民骨干,我感到很自豪!社区的事情一起做,社区很相信我们。我也是(义乌)埃及商会的,我跟住在这里的埃及人说,要遵守规则,遵守出入门(社区大门)的疫情防控规定,有事情和我说。我经常向社区反映一些情况,社区都很支持。”(摘自L社区外籍居民访谈资料)
一般情况下,各种类型社区组织的整合,可分为纵向整合与横向整合,前者强调纵向一体化,后者强调横向合作化⑮。就当前我国的社区组织而言,纵向一体化可借助于“科层”方式来推进,特别是像来华外国人的社区融入问题,往往牵扯到国家或政府层面的涉外关系,基层社区组织更倾向于采取纵向整合的组织分支化策略,即主要通过构建社区组织管理的融合性组织或岗位等,来实现“以我为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来华外国人社区组织融入。
(三)以关系圈层化培育来华外国人社区认同
关系融入是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的重要方面,其中,来华外国人与社区工作者以及与邻里、房东等的关系融洽程度,是体现社区融入水平的主要表征。关系的最初生成也可能是基于日常生活交集或自组织网络,而社区组织的积极倡导和推动更是起到了“事半功倍”作用。从L 社区的经验来看,社区组织在促进来华外国人的关系融入方面,主要是采取了“关系圈层化”的行动策略,即以社区组织管理的融合性组织及岗位中的外籍负责人、积极分子等为第一圈层,以驻义乌当地的外籍商会负责人、秘书长及外资公司负责人等为第二圈层,以社区邻居、房东与外籍租户等为第三圈层,并依据不同圈层的具体情况,探索出了相应的运作机制及工作重点。
在第一圈层中,社区组织主要依托分支化融合性组织和岗位等,去吸纳和推动来华外国人的社会关系融入。这种社会关系可视为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的结合体,具有以正式关系带动非正式关系、以非正式关系助力正式关系的特征。在正式关系中,社区组织通过组织规则、会议场域、任务布置、落实反馈等方式,实现对下延融合性组织及岗位中外籍负责人、积极分子等的指导或领导,而外籍负责人、积极分子等则通过参与制定规则、共同协商公共事务等产生社区组织归属感和认同。与此同时,L 社区还注重发展以社区组织为依托的非正式关系,如社区组织负责人通过设立微信群,与下延分支化组织网络中的14 位外籍人士建立起了较为紧密的人际关系。“以组织为依托的关系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借助它们可以把有关事项、服务等及时传递给更多的社区外籍人员,外籍人员也可通过它们把自己的需要或诉求等反映上来,这样有利于社区融入工作顺利开展。”(摘自L社区组织负责人访谈资料)
在第二圈层中,社区组织积极发展与外籍商会、外资公司等来华外国人自组织负责人的社会关系。外籍商会不是社区社会组织,不属于社区组织指导或管理范围,但因其包含众多外资企业或商户,动员力和影响力都比较强,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中一些比较棘手的涉外事项,往往需要取得对方所在外籍自组织及其负责人的支持。为此,社区组织在当地政府部门和下延融合性组织中外籍人员帮助下,积极衔接外籍商会和外资公司,主动拉近与其负责人的关系,包括邀请外籍商会及外资企业负责人到访社区、建立经常性的线上线下交流渠道、开展特定事项商谈和年节拜访等。
在第三圈层中,社区组织积极推动房东、本地“隔壁邻居”与外籍租户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其推动方式包括建立“以房留人”服务机制、双方传统节日文化体验活动、一年一度的“邻里节”活动等,目的在于增进熟悉度和文化分享度。其中“以房留人”服务机制,强调房东不仅要对出租的房屋负有相应的管理责任,还要熟悉租户的情况,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沟通机制。从实践效果看,绝大部分房东对外籍租户来源于哪个国家、居留时长、几人居住、租户从事行业等基本情况都较为了解,一部分房东与长期外籍租户还建立了较好的人际关系。正如来自叙利亚的巴沙尔所说的:“我在义乌已经5年了,都租在这个房子。房东对我家很好,还会拿些蔬菜、红糖给我,我也会拜访他们家,我们是好朋友,像家里人一样。我们住在这里很开心,小区很干净,(社区)活动很多,邻居还和我们打招呼。”(摘自L 社区外籍居民访谈资料)
社区组织的关系圈层化策略,遵循关系融入的“递次性”原则,即关系融入往往不是均衡的或均质的,而是有着某种相应的“差序”特征的。例如,在第一圈层中,社区组织负责人与分支化组织负责人及岗位积极分子形成了“强关系”,而第二圈层则介于“强关系”与“弱关系”之间,第三圈层虽然也可能形成“强关系”,但更多的是“弱关系”。当然,圈层之间并不是封闭的,关系强弱也不是固定的,关系融入的需求状况以及关系圈层的营造状况等,都会影响人们在关系圈层中的位置。L 社区的经验表明,通过营造相应的圈层化关系,积极拓展类似于“朋友圈”的情感交往网络,也是社区组织推进来华外国人“居民化”融入、培育情感认同和社区团结的重要途径。
四、结语
通过对L 社区案例的分析,发现社区组织在推进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中担负着“居民化”的整合融入角色,该角色是社区组织基于“整合”定位调适融入政策与来华外国人融入需求及我国本地居民利益的结果。这一角色在面对制度、组织、关系融入维度时,社区组织的行动策略分别是平台化、分支化和圈层化。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社区组织自身定位对其担负的新角色具有重要影响。我国社区组织自身定位是国家制度规制的结果,是作为基层社会单元而非西方的地方社会单元而存在的,因此实现社区各类主体需求、利益的整合,尤其是“科层”与“自治”的整合是其基本定位。在这一定位下,社区组织通过平衡“居民化”融入政策、来华外国人融入需求及我国本土居民利益,形塑了一种“居民化”的整合融入角色。
本研究进一步表明社区组织角色落实到行动策略上往往关注政府融入政策的落实、社区组织的开放包容及社会关系的生产等三方面,而这三方面恰恰是影响来华外国人社区融入的重要因素。在此,社区组织通过治理的平台化、组织的分支化和关系的圈层化三种行动策略,分别推进了来华外国人的社区服务、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从而为来华外国人“居民化”的整合融入提供了支撑。
注释:
①Henry,I.P.,Amara,M.,&Aquilina,D.(2007),Multiculturalism,Interculturalism,Assimilation,and Sports Policy in Europe,In I.P.Henry (Ed.),Trans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Sport: Globalisation,Governance and Sport Policy,London: Routledge,115~234.②DeSensi,J.T.(1995),Understanding Multiculturalism and Valuing Diversity: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Quest,47,34~43.
③Hilary Silver,(2010),Understanding Social Inclusion and Its Meaning for Australia.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45(2),183~211.
④John Pitts&Tim Hope (1997),The Local Politics of Inclusion: The State and Community Safety,Social Policy &Administration,31(5),37~58.
⑤Wilson,W.J.(1996),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New York:Knopf,64.
⑥Turok,I.& Bailey,N.(2004),Twin track cities?Competitiveness and Cohesion in Glasgow and Edinburgh,Progress in Planning,62(3),135~204; JochemTolsma,Tom van der Meer & MauriceGesthuizen (2009),The Impact of Neighbourhood and Municipality characteristics on social cohesion in the Netherlands.ActaPlitica,44(6),286~313.
⑦Ponic,P.,&Frisby,W.(2010),Unpacking Assumptions about Inclusion in Community-based Health Promotion:Perspectives of Women Living in Poverty.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20,1519~1531.
⑧Frank Gaffikin&Mike Morrissey (2011),Community Cohesion and Social Inclusion: Unravelling a Complex Relationship,Urban Studies,48(6),1089~1118.
⑨Ontario Council of Agencies Serving Immigrants(2006),Inclusive Model for Sports and Recreation Programming for Immigrant and Refugee Youth,Toronto: Ontario Council of Agencies Serving Immigrants.
⑩Foord,J.& Ginsburg,N.(2004),Whose Hidden Assets? Inner City Potential for Social Cohesion and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in M.Boddy& M.Parkinson (Eds),City Matters: Competitiveness,Cohesion and Urban Governance,Bristol: Policy Press.
⑪李友梅:《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 期。
⑫樊鹏:《国际化社区治理:专业化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方案》,《新视野》2018年第2 期。
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课题组:《北京市朝阳区“国际化社区”建设——“朝阳模式”的新思路与实践》,研究报告2016年8月。
⑭闵学勤:《从无限到有限:社区平台型治理的可能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6 期。
⑮Roland L.Warren (1978),The Community in American,Chicago: Rand McNally and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