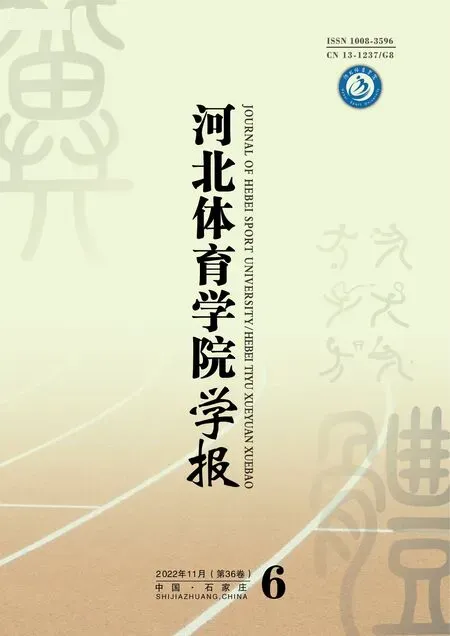武术中的威慑仪式
——时下社会习武者的戏仿想象
路云亭
(上海体育学院 传媒与艺术学院,上海 200438)
自媒体时代到来后,各种民间比武事件被频繁曝光,探究其生发缘由的文章日渐增多,其中一部分文章涉及民间武者的精神世界,其以对网民世界的研判为主体。类似的问题也受到了体育界、社会学界以及一些人类学家的关注。其实,传统游戏包括原始游戏、儿童游戏、仪式游戏和风俗游戏4种形态。除却维多利亚时代的户外体育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现代奥运会体系之外,世界上鲜有身体类游戏演进成体育项目的,中国武术也不例外。中国传统武术以威慑仪式为精神构架,这本身就说明了其非体育的特质,而探究威慑仪式的民间性问题也会涉及传统的仪式文化在现时代的存在情貌。大体而言,仪式文化在传统武术本体系统中的地位很明确,也一直富有积极的社会与文化意味。在人类学家的眼中,仪式学曾经是人类知识体系之总和,至今仍是一种为广大民众所信奉和依照的积极的生活态度,同时也是人类精神世界健康演进的核心动力。客观而言,威慑仪式带有表演性,它源于人类先民对猛兽、天灾以及外敌的防御性心理需求,其以部落文化中的刀山火海、猎头祭祀之类的表演为代表,其通俗形态则为一种诅咒技术。威慑仪式在远古时代一度是人类族群抵御外在危害的精神点,而非如当下人所想象的负面行为模式,更非一种供人游戏之物。中国语境中的儒学和威慑仪式学虽然有融合点,却也有抵牾之处,儒家文化的奉行者为了维持其纯洁性与统治地位,一直将威慑仪式设计为一种负性的存在,正因如此,威慑仪式之神秘符号意义尚难完全消解,其在现实世界中仍有变相性活力。
1 流传广泛的非尚武类武术
先说气功问题。气功其实是武术的精神学载体,它几乎一直承载着武术的核心价值观。但是气功并非体育,因此,武术的本体也极难成为体育。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机构将气功分为健身气功与非健身气功,国家体育总局倡导的是健身气功,而在民间的威慑仪式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左道”类气功则开始调整其演示方式,并重新蛰伏到隐性社会。但是,威慑仪式类的武术或武术类的威慑仪式都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在特殊的语境中一定会重新出现。近期活跃于网络世界的武术钟情者即为此类武功的代言人。与西方搏击术不同,中国的传统武术习练者大多以有文化为身份标志,喜欢在公共空间展开争论、论辩,借以展示门户、门派、功法、理念,换句话说,他们喜欢文战而不喜武斗,文战派武术一直热捧武术表演学的基本教义,他们在构建一种新型娱乐观的同时,也将一种深隐不显的价值观彰显出来。无以否认,由于史前文化本然的转型性惯性作用,威慑仪式的武术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威慑主题存在于人类各个民族的仪式展示领域,它一度是族群主义、集团主义乃至国族主义生发之基石。威慑仪式带有很强的表演性,其在汉文化领域中则集中体现在戏曲领域,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净角是威慑仪式中的角色主体。时至今日,威慑仪式及其表演性内涵在中国武林仍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其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社会性的要求细节所致。儒家文化要求每一个人做人要不伤对方的面子,与人交往也不应伤了和气,人们遵守以和为贵的交际原则,秉持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行为惯性。在这样的文化机制下,竞技性的比武必然会遭受遮掩、屏蔽乃至被完全废弃,取而代之的便是带有剧本意味的表演性比武,其承续的恰是传统文化中的威慑惯性。当下的武林赛事的确容纳了大量的表演性元素。这便凸显出两个问题,其一,因为交手双方都是儒家伦理的捍卫者,而经受过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国人大多承受不了绝对胜负的精神压力。其二,戏剧性表演更符合绝大多数观众的接受心理、思维习惯和欣赏理念,其所违反的仅仅是现代竞技体育的真实性,如果非要在竞技的真实性与表演的真实性之间做出选择的话,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更愿意接受后者。其实,大量的表演性比武所揭示出来的仍是那条中西方文化的巨大鸿沟。从本质上说,表演性比武是传统武术套路的扩大版,而威慑仪式表演则是表演性比武的扩大版,传统武术的戏剧性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参与表演性比武或威慑性仪式的知名者也极有可能成为新型的武打明星,或可认为,只有参与表演性比武或威慑性仪式的知名者才可能成为媒介明星。
传统武术一直维系着武术、舞蹈和威慑仪式三者合一的关系,且以套路为例,武术套路即蕴含有武术套路、舞蹈套路两者,但其勇于挑战强者的勇气则来自威慑仪式思维。三者的真正融合点则是表演学、戏剧学的综合体,而非竞技学,正因如此,传统武术中更容易派生出成龙、李连杰、甄子丹之类的武术艺术家、武打演员、武行艺人,而难以培育出格斗家、技击家和其他尚武类体育家。近年出现在媒介视野中的闫芳、马保国、皮香远等人皆属于武术威慑仪式的参与者,其在局部场域内甚至有可能取代成龙、李连杰、甄子丹等的地位。
不可否认,中国武术中存在非身体攻击性元素,其以威慑仪式为代表。威慑仪式是一种人类族群中的通用仪式,当然亦属于植根于中国人思维深层的精神元素,且一直助力中国人实现自己的美好意愿,中国礼乐文化中的“礼”的刚性化品质即来自威慑仪式。李泽厚认为礼乐文化就来自于仪式学与历史学合一的传统,由此可知,中国武林中的威慑仪式的实用性要大于学理性[1]。很多人认为威慑仪式在中国的下层社会广有影响力,其实,威慑仪式思维在中国的上层社会更为流行,理由很简单,上层社会一直是礼教仪式的策动者。中国的上层人士中不仅有威慑仪式思维,还经常活学活用,将其发挥到极致。抛开武术的影视化之路,仍旧可以看到其在全社会的表演性能量,只要看一眼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气功热就会发现,那里有一种将静态的武术扩展到极限状态的诉求。这里需要指出,当年的气功大师所展示的并非武术的攻击体系,而恰是武术的文战派、口号派、舌战性内涵,它属于一种黏附于传统武术身上的威慑仪式的文化学意趣,当年的气功大多辅以舞蹈学品格,而武术原本具备的攻击力几乎荡然无存。气功热兴起的原因很多,大体上有抽象的信仰学和具象的附体仪式两种动能,而两者皆有背离武术主体的倾向,并将武术的对抗性内涵磨损为零。
从动作到拳谱,从恪守的道德到从业者的禁忌设置,从师徒感情到交际方式,中国传统武术都浸润着温厚的伦理精神,又以诗情画意的想象力为构建动能,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对超自然能力的隐形精神依赖。其实,非洲、澳洲、巴西以及马来西亚部落的原始武术仍带有较为纯粹的威慑仪式色彩,与之相比,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威慑仪式学内涵显得温和而有节制。而较诸西方近代体育理念下的各种徒手格斗项目,传统武术的威慑仪式学内涵所带动出来的想象力、意志力、国族主义、温情主义等元素依然存在,且已成为其内在特质,并为武侠小说、武打影视剧广泛接纳。
笔者曾经认为足球是一种戏剧而非科学,或者说足球的第一属性是戏剧,第二属性是科学,第三属性是游戏。中国的传统武术与之类似,传统武术中有科学性,也有游戏性,但仍是一种戏剧。正如任何一种武术形态都有其优势与劣势一样,中国传统武术的最大优势便是其独有的文化性、审美性和表演性。一些研究武术的学者已经开始接受了传统武术的表演性价值。“当下我们不再要求传统武术具备多么强大的决斗功能和自我保护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形式美的武术套路、意蕴美的武术内容,以及武术为我们带来的融表演与技击于一体的视觉盛宴,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感受传统武术的魅力。……如何将武术套路与难度动作结合起来,让人们在练习中既不乏味又能够学到真正的技能,是当下传统武术面临的危机。”[2]由此可知,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很难接受武者之间的血腥格斗。与此同时,影视剧中的武术也将武术带到另一种极端。中国传统武术的定位分歧就体现在这里。
传统武术缔造了武侠小说以及与之匹配的动作影视剧,这是大多数体育项目无以具备的品格,这便涉及影视学的本质问题。影视学的核心是人类的表演学,具体到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动作片的源头之一是1928年的《火烧红莲寺》,由于中国传统武术与威慑仪式有内在的互动关系,电影将武打戏与神怪戏合流,展示出一种动作表演与超自然想象力的融合态势。《火烧红莲寺》上映后,票房很高,万人空巷,在此后的3年内,各种续集类影片一共拍了18部,到1931年,中国电影市场一共上映了227部武侠神怪片,武侠神怪片之名称就此出现。香港的武打电影受20世纪20年代上海电影的影响,1949年,香港导演胡鹏开始拍摄以黄飞鸿为主人公的电影,将香港武侠电影推进到集约化开发的新时代。中国大陆的首部武侠电影是拍摄于1980年的《神秘的大佛》,为避免与神怪武侠戏产生联系,当时此影片定位为悬疑惊险动作片。
只要略加考察就会发现,武侠影片从上海走到香港,又从香港返回大陆,其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其审美宗旨未易,都以极限性动作与极限性想象力为主体。这便涉及中国传统武术的基本规制。中国传统武术就是如此,一直将动作的极限性与想象力的极限性相结合,其动作的形态来自远古体操体系,其极限想象力则来自威慑仪式及其整套的思维惯性。
2 为非体育元素浸润的中国传统武术
新近涌现的网民生长于科学主义时代,也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科学主义的理念、思想与价值观,因此,他们往往会对现实版的威慑仪式表演有所怀疑,认为中国传统武术中的神秘主义、想象力以及意志至上主义都属于不良体育现象。“一些拳种为了宣扬自身拳派开创的历史和功法的神奇,往往将一些神仙和法术引入其中,对拳理的阐释也往往充满神秘色彩。‘传统社会习惯于把许多东西的创造归功于神灵与圣贤。’而这种做法已经阻碍了传统武术的发展……与西方体育相比中国传统武术体现了更多的人文色彩,而缺少科学实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武术的发展。”[3]强大的反想象主义思潮对传统武术进行批评的同时,也会破坏传统武术的基本建构理论,让传统武术无所适从。反对传统武术增魅化的人士依然坚守己见。“这种迎合人们满足感的‘假功夫’电影使得武术电影面目全非,加上现代媒体的宣传,造成了武术的信誉危机。”[4]与此同时,想象力丰富的观众又对传统武术中的传奇性元素极为倚重,希望再度看到好看的武功设计镜像,其欲念之源仍在于威慑仪式思维。
一切似乎进入一种矛盾状态。然而,在现代性语境下,为威慑仪式正名似乎成为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其难点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历史的惯性。包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内的各种主流文化都一直有抑制威慑仪式的传统,对威慑仪式采取过歧视、贬抑与封冻措施。其二,现代性要素。现代很少有人公然支持威慑仪式,这也加剧了威慑仪式的非积极性的强度。其三,科学与威慑仪式的对立论。很多人认为科学是正面的、积极的、体面的元素,而威慑仪式是负面的、消极的、不雅的元素,科学与威慑仪式不仅势不两立,而且科学还经常被人当做一种压制乃至消灭威慑仪式的有效武器,在此语境中的威慑仪式早已失去了其应有的天真、拙稚、朴实乃至温暖的原色。人们在表演艺术领域仍旧可以看到大量的威慑仪式元素,但是,现代人很少有人敢于承认表演艺术是远古威慑仪式的后续表现形态。正因如此,现代世界各国的威慑仪式活动多已消隐,人们已经很难感受到威慑仪式对自己生活的显性影响。但是,威慑仪式作为一种人类原始思维的产物,其所散发出来的诸多元素仍旧存留在人类的思维深层,并时而作用于现代社会。
目前的中国武术界由三类人员组成,也由此构建出三种武术范式。其一,套路表演。这是国家体育总局试图推入奥运会的项目。套路表演的重点在于武术体操化、舞蹈化、戏曲化。当今世界所有的格斗类项目皆以点数判胜负,但竞技武术中的套路表演则以打分判胜负。这便是问题的关键。其实跆拳道也有套路表演,它叫“品势”,品势与技击并无直接的关系,跆拳道选手品势做得好可以威吓对手,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果。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武术一致。其二,国家体育总局主导的散手。其实,散手的基本理路来自西方格斗,与中国武术无关,中国人基本不接受此类项目。中国人对待散手运动员大多态度冷淡,原因就在于其动作体系与传统武术相差甚远,其审美的复合性缺失,更不具备太多的中国人所理解的动作的艺术性品质,因此,散手运动在中国属于小众化体育项目,人们大多将其看作是与军体拳类似的格斗术,以其艺术性较差,也便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武艺。中国人的心理热区投射点仍在看似美轮美奂的传统武术,正因如此,目前相当多的传统武术钟情者便打起了各种武术大师名号,试图借助传统武术的名号谋生。其实,传统武术是一种发育稳健的固有文化,其所缔造的武者更接近超凡武者的类型,而中国的普通民众也的确更喜欢有一些超人式武术家的存在,他们不认为散手是中国武术的正宗,也不愿意接受散手技术,更谈不上接受其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武术也有散手,它指的是一种将固有套路拆散后临时组装的对抗技术体系,但与国家体育总局的散手毫无关系。其三,传统武术。传统武术讲究发力、呼吸、节奏,整体来说,距离技击较近,但是由于禁武时代延续下来的巨大的禁锢性阻力,几乎所有的传统拳师都很忌讳格斗。正因如此,传统武术中的格斗术几成绝学。
在失去了擂台赛式的格斗术之后,中国传统武术便只剩下了一些信徒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习武者。这便涉及擂台空间的合理性问题。其实,中国的武者从习武开始就对擂台没有兴趣,也不考虑擂台赛中的任何细节。代代相传的武者也从未有人讲述过擂台赛的经历,理由很简单,中国传统武者很忌讳擂台赛,认为它是一种背离了儒家文明的事物,是一种血腥、暴力、为人所不齿的行为,擂台也便成为一种不够圣洁的存在物。但是,当今的部分武者已经接受了传统武术是体育之理念,误以为武术的终极评判标准在于擂台,而非其他任何地方,这便形成了一种认知的巨大裂隙。
简单来说,网络世界中的传统武术钟情者很难有实战意识,他们一直生活在评书、戏剧和小说式想象情境中,并坚信隔山打牛之类可以成功,且极易步入幻觉状态。无以否认,媒体也是想象性武林故事的缔造者。很多媒体报出来的“武术家”都只能算是传统武术的精神追随者,而非身体力行的格斗者。但是,此类人士几乎是凭借着意志力、想象力甚至幻觉在打拳,他们心目中有自己的胜负标准,甚至可以自定标准,正因如此,他们大多不会接受失败的结局,即使自己失败甚至出现更为严重的伤残或死亡现象,此类人士及其团队成员也不会接受失败之结果,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功法必胜,即使败灭也有各种各样的托词,而那些托词既包含了幻想性的信息,亦有艺术性的加工元素。客观而言,此类人士的精神世界迥异于常人,其中有三方面的表征,其一,早年有过受人欺凌的经历,形成了最早的心理阴影,成年后渴望成为令人仰慕者;其二,崇拜中国武术中的传奇人物,并立志成为那样的人;其三,未见过真正的武术大师,未洞悉武术的真谛,却只想使自己成为大师。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类似人士并不鲜见,他们几乎是武术的门外汉,但一直以武术家、超人或拥有特异功能者自居,其思维和言行方式如出一辙,无一例外都带有强烈的神经质。这就是部分传统武术钟情者宁死都不承认失败的原因。然而,如果将传统武术当做一种戏剧来看待,所有的问题都不成为问题,人们不会责怪一个演员在一秒之内是否哭泣或者哀嚎,更不会对隔山打牛的电影情节感到困惑。这样的现象并不难解释,很多中国人更希望将武术置于一种视觉艺术的环境中,并借以满足自己的神话想象。在此风潮的裹挟下,社会上不仅会出现闫芳、马保国、皮香远之类的催眠者、口战者、舌战者“武术家”,如阿俊、张太海式的人士也先后参与到了武术戏剧的汇演浪潮中,大家共同营造出一种彼此对立、相互攻讦同时又连带发展、携手前行的喜剧镜像,其所缔造的是一种新喜剧形态,这里权且称之为社会喜剧,而置身其中者则是文丑、武丑以及混合性社会丑角演员。从本质上说,他们仅仅是一群社会武术的涉猎者,而非竞技体育学意义上的格斗者。
3 以想象代实战的传统武术
既然传统武术是一种文化而非一种单一性的体育项目,那么传统武术的文化属性可否压倒或取代其体育属性?简单说,搏击术习练者有可能面对的是一些真正的武术大师,抑或一群凭借幻想格斗的人士,这便给搏击练习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惑。退回到整体武术的领域便可看出,竞技武术习练者认为武术是体育,但仅仅是一种体操式体育,习练的目的是为了健身而非格斗。与之对应,传统武术的诸多习练者从一开始就认为武术是一种道德载体,习武者首先要有很强的道德律,而道德的背后是儒学文化体系,儒学文化体系的背后则是更为原始的威慑仪式思维体系。这里不妨将传统武术习练者分为三派,其一,精神灌注派。此派人士在步入传统武术领域之时就以超人自居,而从未将武术当做一种视失败为常态的竞技体育项目。其二,技击保密派。此派人士认为武术是杀人技,绝对不传,他们对武术外宣一事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并且认为那仅是一个伪命题。其三,威慑仪式思维派。他们恪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古训,认为武术的至高境界是口战,而非实战,更非一种血腥的鏖战。传统武术的钟情者则近似此派。三派人士各守其道,互不干扰,中国传统武术的洋洋大观一直呈现在这里。
近期较为活跃的并非精神灌注派和技击保密派,而是威慑仪式思维派。该派人士认为武术是一种独立的信仰或图腾体系,习练者修炼到一定程度之时,利用意念就可以致人死亡,且不需要任何动作类的技术,即使使用技术,亦皆为随心所欲之举,而非一种固化的肢体性技术。这一派人士大多对武术中的“气”十分在意,理由很简单,气不可视、不可触,甚至不可知,充满了无法量化的特点。直到当下,很多人仍然对武术中的气充满了无以名状的不可知感,解释者纷呈,却难以形成定论。笔者认为,武术中的“气”其实是一种假想性存在物,并非一种武学实体,而传统武术的钟情者们大体就生活在这种精神性空间中,此类精神一旦遇到物质性的空间就会失灵。从各种民间比武现象中可以看到,传统武术的钟情者通常都会以一种十分狼狈的方式脆败于拳场,但是他们始终不承认失败,因为传统武术的精神性空间依然可以容纳下他们,他们会一如既往地将那种精神不败的原则凌驾于一切现实比武镜像之上。
再往深里探究便会发现,类似的精神空间其实就是催眠。大而言之,很多传统武术习练者都对催眠极有兴趣,有些已经达到深度迷恋之地步。为了展示出某种幻想性动作效果,他们放弃了体育精神,转而在魔术、戏法以及一些致幻术领域寻求援助,于是,一些传统武术习练者在他人的配合下,往往能展示出所谓神功的威力,传统武术的钟情者都在生活中多次自导、自排、自演了类似情节。此类人士也经常在各种空间击败与之过招的人,但仔细辨析就会发现,此类人士所击败的人大抵只有三类。其一,自己的徒弟。中国习武者有严格的辈分限定,辈分是一种等级制,且有潜在的约束力,在任何场合,晚辈不可以胜过长辈,因此,通常情况下,晚辈会主动配合长辈的示范动作。其二,自己的信徒。信徒也会因为迷信施术者的影响力而丧失了继续抵抗、竞争、格斗的欲望,被动地配合施术者的指令。其三,迷恋超自然能力的人。此类人士中外皆有,具有一定的普泛性。
其实,世界上所有的格斗术一旦脱离了竞技体育的范畴,都有跌入威慑仪式学的可能性,这便会在客观上缔造出一种文化差异。西方的体育文化和中国的游戏文化之间的差异也一直存在,如此的镜像在霍元甲时代就已经出现过。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霍元甲从未与俄国力士、英国武者交过手。然而,人们宁愿相信霍元甲战胜过上述人员,这便是霍元甲的故事一直流传的原因,也是传统武术的钟情者引发的事件一再激起舆论风浪的缘由,同时也是一种来自远古文化场域中的威慑仪式朝现实社会的转移现象。
面对各种传统武术的钟情者的疑似武功的表演,各路人士纷纷表达出了自己的态度和观念,其中不乏鄙夷派人士的回应,这一派人士大体对中国武术感情很深,对传统武术的钟情者未能展示出王者风范感到失望,从而对其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
笔者曾经接触过一位自称可以开发人体潜能的民间武者。此人言:“以前的练家子,打人凭骨头硬,后来凭的是肌肉,随后就得凭筋,现在我开发出来的是膜,用膜打人,功力比骨头、肌肉、筋都要厉害几百倍。”可以设想,类似的事情今后还会出现,这便涉及武术的信仰问题。威慑仪式一旦演进到一种信仰高度后,其将体现出明显的固化性和强直性。那位民间武术信赖者就坚定地认为“膜”是战胜一切的终极利器,只要利用膜,相信膜,崇拜膜,保护膜,就无往而不胜。不难看出,其已经将“膜”当成了图腾。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看,这样的人不仅有偏执心理,还有强烈的孤独感。他们不知实战为何物,却沉迷于威吓之术,希求将想象性威慑仪式植入体育学的武术序列,借以获得身份认同。与实战相比,他们更偏爱符号;与格斗竞赛相比,他们更喜欢精神胜利法;与真实的体育相比,他们更喜欢某种与身体无关的图腾化的理念。尚需说明,类似的例证反倒可以更好地说明中国传统武术的非体育特性。
4 结语
威慑仪式是一种远古文化遗存。大而言之,它一度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的精神能量,使人类不再惧怕毒蛇猛兽、滔天洪水,展示过其积极有为的进取性、活跃性与拓进性品质;小而言之,其所激发出来的元素会演化为一种尚武性。然而,威慑仪式本体是一种高度文雅化的文化形态,它在人巩固意志力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当武术无法完全朝演艺方向转移之时,其所蕴含的超强的精神性、信仰性与理念性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由于威慑仪式思维已悄悄融入传统武术钟情者的深层意识,其所起的作用就很难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由此可知,当传统武术本身的非体育特质成为某些人从事武术投机活动的机会时,一定会派生出一系列新型的江湖人士,此类人士一旦在现实社会中造成影响力,中国武术的功能就会出现裂变,而以上人士则会从中获益。必须承认,中国传统武术界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存在不适性,而一些打着武术招牌从事非法活动的江湖人士的大量违规操作一定会递进为中国武术文化体系的潜在破坏者。他们制造的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其以威慑仪式为信念的做法显然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更无以融入科学主义的大潮,亦无法动摇中国传统武术的真实演进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