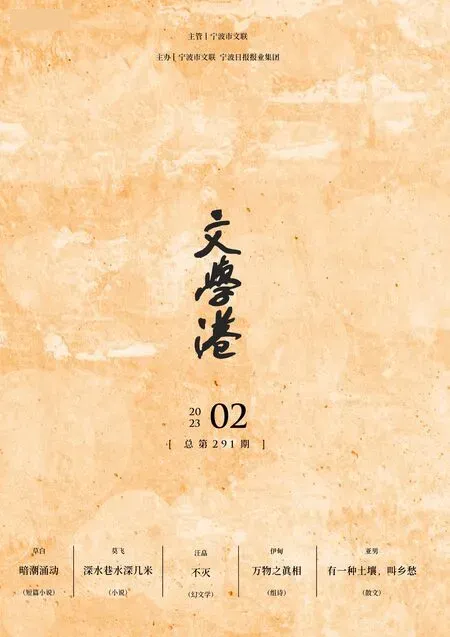想起了胡墼
武晋宁
一
小时候,我跟随父母亲生活在甘肃平凉,一直到17岁高中毕业参军离开。幼年、童年、少年时光的事情至今印象深刻。
这天中午,有学者在 《百家讲坛》讲述 “穿越千年的夯土”时说到了 “胡墼”。近50年没听过这个词,我的记忆猛然被激活了。
所谓 “胡墼”,估计许多人不知为何物,不识 “墼”这个字。尤其在江南地区,知道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说文解字》的解释曲里拐弯: “墼,令适也,一曰未烧者”。 “令适”就是 “令甓”。 “甓”就是砖,墼就是未烧的砖; 《汉语大辞典》的解释简单粗暴, “胡墼:方言,土坯。” 《新华字典》的解释不很准确: “墼,未烧的砖坯。粉末加水做成的块状物。”看来用以规范文字的字典也会出错:胡墼不是砖坯,亦非 “加水的粉末”。
胡墼 (jī)其实就是用黄土夯打而成的土坯,是一种取材广泛、制作简单、使用方便、生态环保、经济实惠的建筑材料。胡墼也称胡基、胡期、胡其、土墼。胡墼是长方形的。大小我说不准。大体是四块标准砖头合起来的尺寸,厚度约10厘米。也许更大些。作为黄土高原常用的建筑构件,胡墼的用途非常之广泛:盖房、砌墙、盘炕、垒圈、搭棚、箍窑。经济实惠,冬暖夏凉,特受老百姓尤其是穷人的欢迎。大西北那些千年古刹、古老宫墙、牌楼院墙、百姓老宅,到处能看到胡墼的身影。
作为极其普通和大众化的建筑材料,胡墼对人们的生存繁衍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它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馈赠,作为中国北方文明的开端,惠泽一方百姓,是人与自然共同创作的奇迹,黄河文明的优秀篇章,黄土文化的杰出典范。
二
我对 “胡墼”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或曰 “胡墼情结”。这种敏感的体验来自一段古城墙根下生活的经历。
从小到大,我家都住在平凉市人民银行家属院。这个很大很空旷的院子,位于城区东大街南侧的 “九天庙巷”与 “南极巷”拐弯处。大院住着20多户人家,都是银行职员和家属,当时银行的职员称作 “银行干部”。院里家家户户分有一块地,种点玉米、向日葵等。我家还种了党参、烟叶、黄花菜。没事的时候,我也经常和弟弟妹妹在地里忙活忙活,每年都小有收成。
出大院门楼右拐百米,有段不算很残破的长城,我们叫它 “城墙”。甘肃人把城墙的计量单位叫 “堵”,城墙用黄土夯制,没有包砖。估计至少是汉代修筑的。城墙的高度大约有20米,另一边是广阔的低洼地,与我们这边的高差有十多米,称为 “南河道”。站在城墙顶看南河道,视野开阔,很远的地方一览无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刚好碰上十年动乱和 “复课闹革命”,功课不紧张,没有“家庭作业”这一说。参加 “红小兵” “红卫兵”也没什么活动,放学了就成群结队去踢足球,瞒着老师和家长去柳湖游泳。回家后或去井里挑两担水灌自家水缸,或到父母单位去打两三瓶开水,或者帮忙拉拉风箱。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能不受限制地尽情玩耍。经常和院里年纪相仿的一伙人纠集起来爬城墙。顺着城墙上的脚窝,脚蹬手攀爬上去。
城墙顶部不是很宽,没有垛口。每隔百把米就有一个人工竖井。想来大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 “大炼钢铁”时挖的炼铁炉烟囱。洞壁两侧挖有从上至下的脚窝,我经常踩着脚窝沿洞顶爬至三分之二处,因为下面是二十到三十多平方米圆形的炼铁炉,下不去了。大炉子和烟囱壁呈 “火烧土”样,纯净的黄土长时间被火烧过,呈发红发黑疙疙瘩瘩的琉璃状。有时大家也成排坐在城墙边缘,看着南河道的景色,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无聊的话或者发呆。
城墙根有个比足球场大点的土坑,可能是当年修长城取土留下来的,我们称 “垃圾坑”,一直是附近老百姓倒垃圾的地方。积年的垃圾只占了大坑很小的一角,剩下很多地方成为胡墼制作场。少时有一组人、多时有三五组人在打胡墼。每组多则2人,1人供土,1人捶打;少则1人,自供自打。成品被横一排、竖一排整齐码放在场内。只要不下雨下雪,几乎天天在打。有时我也会在这挖点黄土,回家糊墙、盘火炉、泥一下兔子窝,或者与粉煤掺和起来做煤饼或蜂窝煤。
三
打一块好胡墼,对土的要求近乎苛刻。须是黄土、净土、素土、纯黏土,最好是从未被扰动过的土,不能掺杂一点点沙石或含有任何杂质,有杂质容易破。而黄土高原之土,经过大自然长距离搬运和风吹雨打,千百年层层积淀,非常纯净,成为不二原料。
土的湿度更讲究:过干粘不到一起;过湿打不成型,还粘连模具和石锤。判断水分的标准是:抓起一把土,稍加用力能攥成团。只有含水量适宜,打的时候不仅速度快,而且有棱有角,光洁好看,密实耐用,风干晾透后敲起来叮当作响,高处掉下摔不破。这全凭经验,我称之为 “酥土”。
要求如此严格的土壤,只有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河南、河北这些地方才有,所以只有在这些省份才能时不时地见到数百年前用胡墼建造的各种建筑。
我们常去的那个胡墼场用的土,全部是挖城墙根和城墙中的夯土。可见当年建造时的用土很讲究、质地好。在土中还时不时能挖到一团很黏的土团,我们叫它 “胶泥”,可以任意捏成各种形状而不变形。有人说这东西能充饥,一九六零年大饥荒时有人干过这事。我也尝过,咀嚼的口感类似上海 “大白兔奶糖”,只是没糖味奶味甜味,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观音土”。
匠人们为保证合适的水分,每天上工第一件事情就是取土,而且只取当天能用完的量,绝不多取。取土过量被风干就浪费了。
打好的胡墼要立马移至阴凉处有规律地码放整齐。每块之间要有间隙以利通风,一排胡墼一般摞五到六层高。
晾干时最忌太阳暴晒,会龟裂报废。也怕遭雨雪,遇水会像冰棒融化一样化为泥。所以但凡正在阴干的胡墼上,都苫有瓦或麦秸草来防晒、防雨、防水,直到自然阴干晾透。时间长点硬度更佳。
四
打胡墼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它有技术含量,是中国传统 “版筑技术”的一种,很有讲究。

打胡墼的工具有五大件:草木灰斗、木模、石锤、青石板、铁锹。青石板要厚实并光滑如镜,大铁锹要平头,木模具要用老榆木或槐木,耐磨经打不变形不粘土,石头锤是八到十斤平底的。为方便取土,有的还备一把铁镐头。匠人们的铁锹永远都是明光铮亮、泛着金属的银色光泽,永远不生锈。
打胡墼的动作有要领,口诀是 “三锹六脚十二锤”。我将流程归纳成六个字:
刮:将青石板和模具的浮土刮净,模具放在石板上并锁住卡口;
撒:撒半把炉灰或草木灰防粘;
填:往模具中填入黄土三锹并拍光;
踩:跃上模子,脚尖朝前踩一脚,脚跟往后踩一脚,再从中间踩两脚,将模子里的虚土踩实压紧。有些人穿布鞋踩,有的光脚踩;
夯:提起平底捶四角各一锤,四边及中心各两锤,共12锤;
摞:把打好的成品在晾晒场依次码好。
有人形容打胡墼像舞蹈:轻巧、流利、飘逸、自如。脚不走空步子,手不作空动作。一招一式,不慌不忙,有章有法,准确无误,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提得快,捶得准,摞得匀,干净利落。标准工作量是每天打一垒500块,有人拼拼命也能打800块。
打胡墼的声音很动听,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富有节奏和韵律感。捶打声以12响为一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咔!”最后一声 “咔”,是用脚后跟磕开模子卡口的声音。几组人同时打胡墼的时候,捶击声此起彼伏如同交响乐,又像是同时擂响战鼓。
其实,这种声音早已是艺术并成为能登上“大雅之堂”的经典。中国最早的诗歌集 《诗经·大雅·绵》中对此有精彩描写: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译成大白话同样富有诗意: “叫来了司空,叫来了司徒,吩咐他们造房屋。拉紧绳子吊直线,绑上木板栽木桩,造一座庄严的大庙宇。聚土的声音 ‘扔扔扔’,填土的声音 ‘轰轰轰’,捶打的声音 ‘噔噔噔’,削墙的声音‘砰砰砰’。同时起筑百堵墙,盖过了擂响大鼓声”。
最精彩的则是 “陾陾” (réng)、 “薨薨”(hōng)、 “登登” (dēng)、 “冯冯” (píng)几个叠音象声词,把打夯筑墙时的宏大场面和发出的各种声音刻画得生动传神。
这么好听的声音、潇洒的动作,时常引起我们围观。也央求匠人让自己试一试,打不好时大家轰笑一场。为讨好匠人,常帮他们整理场地、挖土填土、搬运成品,以换取一次游戏机会且乐此不疲。
五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明。北京猿人住洞穴,河姆渡人用树木稻草搭房,黄土地的人则很聪明地就地取材,用最普通不过的土制成墼,盖一座能遮风挡雨的房子,从此改变了 “穴居”式的生存方式,脱离了 “刀耕火种”式的原始生活,生存状态根本改善。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永远在路上。
然而,这个文明却是汉文化与西域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
据考证,中国最早的 “版筑技术”见于商朝。早年在山西中条山脉运城平陆一带做奴隶、后来成为商王武丁宰相的傅说,是比孔子还早800年、中国第一个被史料记载为 “圣人”的贤相。 《史记·殷本记》说: “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他发明了 “筑”这种技术,被称为中国的 “版筑之父”。传说傅说后来得道成仙变成一颗星,称“傅说星”,也称 “天策星”。至今平陆城内还有 “傅相祠” “圣人大街” “圣人窟” “圣人涧” “殷商中兴贤相傅公版筑处”等遗址。
2011年春节我和家人在平陆去看过傅说祠,宏伟的神殿前有一通 “功参伊仲,道贯商殷”石碑,赞颂傅说的功德比肩名相伊尹和管仲,思想和政绩惠及天下。
到西周中期,宫廷有了砖瓦建筑。汉代,土坯技术广泛用于民间建筑,作为形声字的“墼”字也出现在西汉。但这时的土坯被称为“土墼”,尺寸比胡墼要小,厚度要薄,重量要轻。
有学者研究过两河流域、波斯帝国、古埃及以及中国新疆的建筑史后发现,这些区域的土坯建筑比黄河流域要早,工艺更成熟。随着西域和中原交流的不断深入,西域建筑模式也渐次流入中原。汉人发现西域的土坯比自己的要好用,于是采用了这种规制和方法,并把它命名为 “胡墼”。汉代中原人把从西域输入的东西都加个 “胡”字,比如胡萝卜、胡瓜、胡椒、胡笳、胡麻、胡桃、胡琴、胡服、胡妆等,从西域传来的土坯夯打技术被称为 “胡墼”就很自然了。
可见它和佛教一样,是 “西风东渐”的产物,也是胡汉民族大交融的真实见证。
六
我离开从小生活的西北大院几年后,父母亲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带着弟弟妹妹举家东迁离开了平凉。我在结束了40多年的军旅生涯退休后,携夫人重返过一次,见到了几位老同学和老战友。从小生活在广东的夫人,对我想看的地方觉得既陌生又新鲜。我很费力地一处处寻找那些曾经熟悉的街巷、院落、门楼、城墙、庙宇、学校的踪迹和地标。孰料世事变迁,早已物是人非。不仅 “人非”,物也“非”了:城墙找不到,大院找不到,胡墼场找不到。向住在这里的人打听,也都说不知道。幸好 “南河道”的地形地貌变化不大,以此为参照,给旧日的地方各自定了一下位,结果发现原银行家属院的旧址,现在是一个叫“南湘园”的居民小区。在无数次走过、进出的地方站一站,拍张照,勉强安慰了一下自己。
平凉城,这个位于六盘山东麓的千年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地,史称 “西出长安第一城”。公元358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前秦帝国第三任皇帝苻坚灭前凉,取 “平定凉国”之意在此建 “平凉郡”至今。著名的崆峒道源文化、成纪伏羲文化、西天王母娘娘文化独具魅力。我在平凉的17年时间里,胡墼建筑随处可见,现在却不见踪影了。放眼望去,代之以钢筋水泥、砖头瓦块、钢铁结构、复合材料建造的各式高楼大厦。“胡墼制造”这个古老的传统工艺,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坚决而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现实生活中。
以前,人们都嫌用胡墼土气、住胡墼房落后。但现在看来,它比砖块厚重,比石材接地气,比钢筋水泥透气,比用空调保持恒温,比砖瓦省钱,比复合材料各类涂料绿色环保,比高楼大厦有生命感!它与自然共生死,与土地共节奏,与空气同呼吸。不需要烘烤,不需煅烧,不会成垃圾,不污染环境,不会将人类与土地阻隔。成本很低,作用很大;工艺简单,使用很广;原料很土,环保很赞。把使用了上千年的胡墼打碎,它还是黄土,还是几千年前的样子,还是优良的土壤改良剂,用于肥田叫墙土粪,还可供你反复循环使用,生生不息。
小小的胡墼,大大的历史。土土的技术,悠远的文明。 “土得掉渣”的东西是最好的东西。厚重的黄土不仅养育万物,还是一方民众曾经遮风挡雨、避暑御寒、安居乐业、成长壮大、生存繁衍不可或缺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