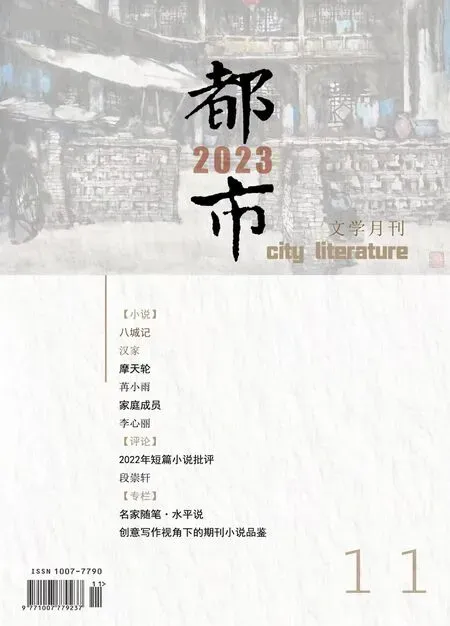少年的雪
卜进善
大年初三早上,一个瘦削的、穿着并不合雪天规制的大学副教授从电梯移出来,缩着脑袋,朝我晃晃手机上的绿码。我尴尬地说没必要吧!他涩滞的眼怔怔看向我,干裂的嘴唇蚕蛹样蠕动一下,旋即安静。我握住他树枝般的手。他,比我矮了。
看啥?快进来!我身后的朵朵招呼他。
春节时,女儿以“就近过年”为由,窝在博士生楼里。我和朵朵计划去的几个地方下雪,亦有疫情防控要求,只好宅家。家,是唯一即便丑也丑得让人舒服的地方。
副教授松开我的手,去解外套的扣子。我劝他进屋再脱,他不理,解扣后脱下外套,轻置在墙角。我去捡,他拦住我说上面有雪。我和朵朵知道,衣服上的雪早消了,但他怕雪。我关门时,注意到那是一件普拉达简约薄夹克,他老婆明颖的面容,瞬间闪向我的脑海。
他换上朵朵找来的拖鞋,径直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
都是这讨厌的雪,我找件外套给你。朵朵说着,转身疾步走向卧室。中途,她喊了我。我跟进卧室,她吐一下舌头说,我说错话了。我伸手刮了下她的鼻梁,说注意点就好。她懊恼地点头,打开我的衣柜。
屋里暖气烧得热,只要不怕冷,穿一件加厚衬衣就够了。我这样想着,走出卧室。
鬼天气,我们那里下雪了。我查了预报,昨天又问你。结果高铁坐到半路,天变了。陆一民回头看一眼窗外的雪说,小董,我真不该是扫帚星吧。走哪哪下雪不说,用六分钟才能打开健康码。他望着我,眼眸里的光,没有一丝是凝聚的。他比我大两岁,大学时叫我小董。这次他从秦岭以南的城市坐高铁,六个多小时来我这里。我安慰他,十几年气候变暖,冷一年也正常。然后问,喝什么茶?冰岛普洱,还是安吉白茶?
来几口酒。陆一民说。
好嘞。我愉快地走向酒柜。
朵朵拿着外套出来时,我已给陆一民倒满了茅台酒。陆一民端着酒杯,对朵朵说,谢谢,我不穿,你收了。他把杯子朝朵朵的方向举了举,又转向我说,来,干杯!我这才给自己倒上酒,举杯相迎。“砰”一声,两只玻璃杯磕在一起,他的眼珠映在杯中晃荡的酒面,像鲤鱼露头吸氧。很快,他鱼样的嘴巴吸吮了酒液,说,确实是好酒。他咂咂嘴,伸手去拿酒瓶。朵朵说别干喝,我弄点下酒菜。陆一民眨眨眼说没事,给我俩各添了一杯。
干喝了三杯,陆一民往后一靠,两臂展开搭在沙发背,金鱼一样充血的眼瞅瞅天花板,又闭上。我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顺着他微红的脸看过去,墙壁上是一幅国画。陆一民的手臂,像从画面上伸出的藤蔓,黄中微红的脸,给画面填补了温润的质感。他鼻孔里出的气,像瓜藤间升起的地气。我知道他不大喜欢喝酒,两年多来更是控制着喝酒。我让他靠在沙发上休息,正要起身时,朵朵走进客厅,看见陆一民这个样子,拿眼瞪我。我侧眼看陆一民。陆一民闭着眼,张嘴说没事,有吃的吗?朵朵笑笑,回应一个“有”字,折身,如燕飞去。
你没吃饭?
赶车,昨晚都没吃。
过了能挨饿的年龄,不要硬扛。
也是,比上学那会儿差远了。
你一个人,吃,也不能凑合。
有时觉得吃饭也麻烦。
你不能把自己搞垮。
我怕见人。陆一民抬眼懒懒看我一下。
吃饭了——朵朵在餐厅喊。陆一民“哦”了一声,准备起身。我说没事,就在这儿。我去餐厅端过来两个盘子,一盘是朵朵自己卤的牛肉,一盘是买来的烟熏鸡胸肉。朵朵一手端着一碟面包,一手拎着未开罐的黄油,放到茶几上后说再弄一个什锦凉盘来。她转身时叮咛先别着急吃,肉刚从冰箱里拿出来。陆一民朝我说,酒是热的。他说着,但没动盘子边的筷子,而是拿了面包,也不抹黄油,直接往嘴里送。
等什锦菜的时候,朵朵的手机响起语音通话请求。她早上打理博古架时把手机放在荷花石前了。我喊朵朵电话,接连喊了两声。她说你看谁打的。我去看时,手机没了声音,像只巴西龟趴在那里,眼里闪着绿光。
第二块面包下去了,陆一民拿起第三块,嘴里嚼着,起身走到博古架前看我的石头。他巡视一遍,拿起一方褐色文昌石看。那是一方文字石,我期望他能夸奖一番,可他轻轻放下了,移到我叫“母亲石”的荷花石前凝视起来。荷花石光滑、沉稳,昨天我刚保养过。
茶几上我的电话响了,我回身拿起,是女儿打来的。她开口说我妈怎么不接电话,是不是还想跟我吵架?我心想,吵架能放松女人的心情,你妈还想跟你吵架呢,但嘴里却说你跟我吵好了。女儿说哪有女儿跟爸吵架的,我就想跟我妈吵。我说那就把电话给你妈了啊。
我拿着电话走进厨房给朵朵说,老陆这会儿在博古架前发呆。
咱俩过年都没意思,他一个人咋过。朵朵把声音尽量放轻一点说,再说了,明颖对他那么好。
对他那么好就不该走那条路。
她愁肠难解,不像我吵吵闹闹就完了。
刚好,女儿跟你吵来了。我递过手机。
你下来劝劝他。朵朵说着,接过电话轻轻叫了一声“董小姐”。
着力即差。我说。朵朵向我挥手。
明颖是陆一民的老婆,也是我和朵朵的大学同学。两年前,他们所在的城市难得下了一次雪,明颖从十八层的楼上跳下来。后来,我赶到陆一民家里,见过她摔下来后的照片。她的脸面砸开了薄薄的积雪。那时,陆一民的天要塌了,钻进追寻明颖的窄巷里。我差不多用劫持的方法才让他到我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我回到客厅,陆一民还待在博古架的石头前。早先,陆一民知道我捡石头,说我玩物丧志。我跟他说,我是在空气清新的山水间锻炼,是在天然氧吧呼吸自由,是在石头堆里发现美,是在寻找几亿年前的情人。见我这样,他在外出讲学时买了一方当地的石头,准备送我,没承想,明颖喜欢得不得了。他在微信里给我说了情况,我给他说,你就说是专门给明颖买的。半年后,他们的儿子出事。又半年,明颖也出事了。再后来,他说只要看见那方石头,就想起明颖,想起明颖的凄惨。他便将石头寄给了我。
朵朵终于端上什锦凉菜。我们开始动筷,当然,吃过早饭的我和朵朵象征性动筷。陆一民主人一般让我和朵朵吃。
我不能再吃,再吃就胖了。朵朵说。
人胖了也不好吗?陆一民嚼着牛肉问。
胖女的中年危机程度与丈夫给她买衣服的多少成反比。朵朵瞄着我说。
是吗?陆一民又喝了一杯酒。
怎么会呢!鞋厂的钱她都管着。我争辩。
哦——小董。陆一民自己倒了一杯酒,喝完,红着脸,面朝着我说,小董若是对你不好,你找班长。
这下子朵朵挣足了面子,端起面前的酒杯仰头而饮。陆一民又给她添了一杯,她接过酒杯放下,拿起酒瓶给陆一民添上,端起酒敬向陆一民。
班长,过年我们哪儿也不能去。把人憋死了。欢迎你的光临。
陆一民接过酒杯,眨一下莹润的眼,想说什么又没说,举杯仰头喝酒后把酒杯在空中翻倒,两滴透明,露珠一样滴下来。他摇摇头,放下酒杯。
朵朵给我和陆一民的酒杯添了酒,给自己也满上,端起说,来,为我们再次相聚干杯!她一仰脖子,酒杯空了,少许酒还在滋润嘴唇时,她用手摸着说,怪不得老董不让我喝酒,原来酒这么好喝。她拿起筷子夹了一口什锦菜。我起身给她倒温开水。
班长,早上我还给老董说,我跟你送给他的石头一样,是个操劳的母亲。朵朵接过水杯,喝了一口。我操心他的吃穿,操心他的鞋厂,还陪他到河滩捡石头、散心。我这容易吗我!朵朵把手按在自己胸脯上,瞪眼望着博古架上的荷花石。
不容易。陆一民附和。
那你给老董说,我也是“母亲石”。
你是活人,小董不会把你当石头。
不,你不知道,这大不一样。我想活成石头。朵朵保持着先前的姿势,发出了卷舌音。
朵朵,你……我欲言又止,觉得她有些醉了。
博古架上的荷花石,有二十多厘米高,表面有火山沉岩爆发时留下的气孔。黑色石体中间,一些石英石和玛瑙石团在一起,形成一个留着剪发头,胸部扁平,从家里出来往外泼洗衣水的女性形象。她的左腿后蹬,右脚被垂落的衣裙遮拦。从盆中泼出的水悬停并凝固,流动的瞬间成了永恒。她的腹部岁月没落一般塌陷下去——这让我时时想起被子女和生活掏空了的母亲晚年的身子。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它是我的“母亲石”。
班长,我为这家操碎了心啊。朵朵打了一个酒嗝说,就说女儿的学习吧。她又打了一个酒嗝,我趁机踢了一下她的脚,她的话在嗓子里噎了一下,说,女儿说她在学校也没意思,不如跟我吵架。呃——不说了。她俯身端起酒杯。我劝她别喝了,她瞪我一眼,足足掂量了十秒时间,放下酒杯,唏嘘一下,说这会儿我能理解明颖了。说完,她起身要离开,脚步踉跄。我连忙扶住她。她倚着我往前走了两步,停下来,嘴巴快碰到我的鼻子时,呼出一口酒气,说,老董,我好着哩,不用休息,只想喝点水。她扭过身子。我扶她坐在单人沙发上,再去给她端水时,她说我自己来,不要在班长面前丢人。她果然起身从茶几上稳稳端起先前我给她倒的水,“咕嘟嘟”喝完,仰面靠在沙发上。微醺状态中的她,脸颊上正盛开着两瓣桃花。
陆一民低垂着头,双手抚弄着酒杯。
我透过落地窗看了一眼窗外。有一些雪花正在努力敲打着玻璃。
老陆,你什么时候开学?我打破了寂静。
三月五号。陆一民抬起头说,不过,也可能推迟。
那好,你就在这儿待到开学。我说。
你的鞋厂,今年给外贸的订单怎样?他没有直接回答,问起我的生意。
还可以。世界躺平了,我们不能躺平。再说了,我什么时候也不是躺平的人。
你就能折腾。
你别再让他蹬鼻子上脸啦。朵朵突然说。她直起身子,红着脸。
实事求是说,小董比我和明颖都强。我想,可能是他爱好广泛的缘故吧。陆一民说。
我就是担心他对女人也爱好广泛。朵朵红着脸巧笑。
班长说了要实事求是,你不能冤枉我。
这会儿讨好班长了。
朵朵,你,你要有自信。陆一民努力寻找着大学当班长的样子。
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我有信心。朵朵眼睛发亮,像被一盏灯照着。我只要他像认可“母亲石”一样认可我。她停顿一下,略带娇嗔地说。
朵朵还不知道那方“母亲石”也是明颖喜欢的,可我不想告诉她。
再好的石头,还是石头。陆一民看看我说,小董认可你,不能跟石头比。
错了,班长。老董说过,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我不敢相信,朵朵都被石头弄得神魂颠倒了。这是朵朵的过,还是石头的过?陆一民后仰过去,头望着客厅的吊灯长叹。
谁知道。哦,可能是想从石头上发财吧。会持家的女人都这样。她盼着我捡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东坡肉石。女人的心,海底的针嘛!我谑笑着,用筷子夹了一块卤肉比试。
朵朵嘴角扯了一下,说,别指望石头发财。你捡一个狗头金,还不是送人了。
陆一民坐直身子问怎么回事。我说起了狗头金的事。
那年我开车到一条河边,坐在修河堤时翻起的一堆石头上。我给你说,我捡石头总有一个习惯,就是先要在河边坐一坐,看一看。那天我坐在河边,看着河边田野里的桃花,河岸的青翠芦苇,河中的水鸭,还有天空中的白云、飞鸟。正在享受时,一位少年走过来,弱弱地问我,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但转念一想,我便理解了。我知道他看我好长时间了。我说捡石头,并举起一旁的军工铲。少年愣了愣,然后翻了一下小羊一样的眼,抬手朝另一边指了指,说,那边的石头多。我讪笑一下,顺着他的话问哪边。他转身用手指。我满足了他的善意,拿起工具。少年也没吱声,转身朝前走。我跟着他离开河边,在一处滩涂的石堆前停下。这是我以前来过的地方,捡石的人已经几乎将石堆踩平了。他站在石堆前,抬眼看我一下。我也没说话,开始用铲子在石堆里拨弄,并装模作样拿起一块并不入眼的石头用水壶淋湿,瞧了瞧,装进肩包。少年看一会儿,说,叔叔你捡石头,我走了。望着他离去的身影,我在心头叹了一番,低头时,发现了那块黑石头。对,是狗头金。可那时我还不知道它是天上掉下来的狗头金。我只觉得怪怪的,捡起来了。它有我的手掌那么大,头部浑圆,中间略细,下边隐隐还有腿足的模样。你不知道,它的手感比和田玉重多了。我把它装进肩包,把原先的那块石头取出来,朝少年离去的方向扔了过去。
黑石头放在办公室。有一天,一个老板商议代工外贸鞋,看见鞋子模型旁的黑石头,仔细瞧完,给我说像是一块天上掉下来的金子。我不置可否,后来还是找专家鉴定了一下,确实是一块陨金,也就是狗头金。我这才把它带回家。
再后来,我继续到那处河滩捡石头。有一次下雨了,回到车里取雨具时,看到了在地里打理桃树的那个少年。他不理小雨,也不理我,好像不记得我了。我产生了和他聊天的兴趣。他说,他快上初中了,上了初中再上高中后怕考不上大学,即便考上了,他爸说也不会有多大出息,有出息的人大学毕业还要读好多书才行。他爸身体不好,怕供养不了他上大学多读书。所以,他不想上高中了,他要从现在开始学些手艺。看着雨中少年清亮的眼睛,我的眼眸有些模糊。
那天,我再没有捡石头。我穿着雨衣,在细雨下的河边走来走去。细雨,好像融化了我,我成了河,浑身都淌着漩涡、翻着浪花。
冬天的时候,我连续两次带着狗头金,去了那河滩。第三次去的时候,终于看见了那位少年。他穿着月白色的单薄衣服,像从天上掉下来的要努力挺直的月牙。他从河滩的雪地往桃树下运雪。我问为什么要把雪堆在桃树下。他说是为了保墒,雪水会慢慢为桃树提供需要的水分。他说雪水干净、甘甜,桃树喝了雪水,结出的桃子也干净、甘甜。我看着桃树下堆起来的雪,伸手抓了一把,在手中攥了攥,团出一个雪球,举起来,用舌头舔出雪球木木的味道。我咂咂嘴,问他:你愿意上大学不?他毫不犹豫地点了两下头。
我扔掉手中的雪球,掏出那块石头,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就用这个换学费和生活费。他看着我手里的黑家伙说,一块石头不值钱。我说,这块石头换来的钱哪怕你在大学读八九年书,也花不完。他瞪大眼睛瞧着奇形怪状的黑石头好半天,又摇摇头。我问他是不是不相信。他说真能换好多钱,也是你的,我不要。他的眼眸里有着柔软的雪光,我再次印证了这是一个善良、诚实的少年。我给他说,这河滩的石头是大家的,谁都能拥有。再说,是你那次领我到那个石头堆里捡的,本来就是你的。我说,如果你以后上大学有钱,不需要这个,你就还给我。我经常到这里来捡石头,你会找到我的。我反复劝说,大概花了半个小时,才说服了他。
我讲完了,窗外的雪还在下。雪好像把室内映亮了一些,茶几上的什锦菜和卤牛肉空了,烟熏鸡胸肉和面包剩了一半。时间已是下午三点多了,微醺的陆一民早已缓了过来,清癯的脸庞上放出清亮来。朵朵的酒劲也消散完了,说好像有点饿,问我俩饿不饿。我俩不约而同地点头。朵朵起身,踢踏着拖鞋,穿过客厅,去厨房煮我们前一天包的韭黄水饺。
饭后,我们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偶尔也看一下各自的手机。在我和陆一民看同学群里不知道谁发的旧时聚会视频时,朵朵开了电视。电视上正播冬奥会越野滑雪比赛。那可是30 公里的赛事,一帮选手在环形赛道的下坡段追逐。我看一眼朵朵说,别看这个了吧。我知道朵朵想看滑雪比赛,她瞟一眼陆一民,用遥控器关了电机。
没事,让她看。陆一民说着,起身去了盥洗间。
我和朵朵傻傻对视一下。陆一民所在的几乎不下雪的城市春节时下了雪,他坐高铁到我告诉他没有雪的这个城市来,没承想一头闯进更大的雪里。现在,朵朵又无意间让他面对电视上的人造雪或天然雪,我心里为陆一民叫苦。
陆一民从盥洗间出来,好像洗了脸,眼睑似乎收紧了一些。他看了一眼黑屏电视,从朵朵手中顺过控制器,一摁,电视上亮起花样滑冰赛事,又正好是慢镜头回放,一位女选手三周半跳,冰刀滑过冰面,带起浪漫的冰屑。朵朵眼里闪着亮光。
陆一民突然问我:小董,你以后再见过河滩上的少年没有?
我送给他那个黑石头后,再不去那里了。
再不去了?
去干啥?
什么时候,你领我到那个河滩看看。
你去干吗!朵朵有点惊讶。
跟你一样,一边捡石头,一边出出汗。陆一民终于露出一丝笑,下巴上的麻色胡子像被清水捋过,清亮了一些。
那选一个好天气,我们去。朵朵说。
明天就去!我说。我有点兴奋。
下着雪,明天怎么行。朵朵反驳。
就明天吧。陆一民肯定,之后拍拍脑袋,说我得去把衣服取进来,要不然,明颖晚上骂我。他的眼睛里闪着温情的光。我和朵朵对了一下眼,他开了门,拿起墙角的夹克,走到盥洗室打理。打理好了,他提着衣服对我说,有一个晚上,明颖在梦里说这件衣服不能丢。看来,我要穿到老了。他苦笑了一下。
第二天,我起得比平时晚,洗漱后叫醒了陆一民。他看起来睡得不错。朵朵已经摆好了早餐。餐毕,我到车库开车,顺便看了一下后备箱里的工具。我已习惯了,一旦去河滩,必拿捡石工具。
昨夜依然有雪,现在停了。天还阴着,街道上几乎没人。大雪给交通信号灯戴了帽子,给道路旁的树木描了白边。摩肩接踵的大楼,像宣纸上刚刚画出的水墨画。我的车轮碾压在雪面,磨损了雪的光洁。
城市的雪不好看。朵朵在后排说。
城市最美的景色都在段子里。不待陆一民吱声,我打趣说。
小董像个老司机。陆一民看着他那边画了雪边的高楼说。
唉,班长,给你说一个段子行吗?朵朵问。
什么段子?陆一民问。
怎么说呢?哦,有一对夫妻把上床叫上课。有一天丈夫下班做好菜,老婆还没回来。他给老婆发微信说吃完饭上课。老婆回说,不用了,昨晚我请了家教。丈夫就蒙圈了。哈哈,班长,你当老师的界定一下,这家教也算是上课吗?
一直看着窗外雪景的陆一民叹口气说,给你俩说说我的想法吧。他扭扭身子,看看后排的朵朵,再回过来,盯着我,嘴里嗫嚅着说:前阵子,我还想着辞职哩。
你傻了吧你。朵朵的头似乎往前伸了一下。
陆一民没有再说话。我盯着前方的道路,想轰一下油门。
越野车开出郊外,越往前开,大地上的落雪越丰沛。朵朵兴奋得有点夸张,从后排一会儿到右边窗前,一会儿到左边窗前,有时还放下窗玻璃拍照、录像。车爬上一个小山头后,她让我停车,我只好照办。她下车拍了远处的雪景,并自拍视频。
陆一民在车上看看朵朵的样子,也推开了车门。一些微软的凉风从他身旁吹向我,我看到他的身子向车头前身猛然倾斜了一下,腰部扭动几下,双手在胸前晃了晃,最后人站定了。他回头看我一眼,我微笑着点了点头。他转身轻跨了一步,一步当作三步前移,抬头看看远处的雪山,又一步当作一步走出去。
我跟了过去。
这就是天地间的大雪啊!他说着,掏出了手机,像是打开了全景模式,旋转一圈拍了一张全景照,然后石头一样立在那里看着远处雪地上素描出的树木、山崖,看着宁静、辽远、洁白的大地。天上没有太阳,大地上的白雪,把天空映得莹润、清亮。他粗眉毛下的眸子像块冰,等待着自己的呼吸将它融开。
小董,《阳光与荒原的诱惑》那本书你知道吗?陆一民侧过头低声问我。
知道,是位女画家写的。
他看着远处说,儿子看了那本书后,说要去看冈仁波齐峰的雪。要是我和他妈带他去看就好了,可他刚上初中。我俩一直鼓励他,等贮备了一定的知识后自己去看。他考上硕士那年,就独自一人看他少年时的雪去了。后来的事你知道,车祸让他永远停在被诱惑的雪路上。我和明颖一直后悔没领他去。那天,我正在学校上课,明颖在那场雪里寻儿子去了。那以后,哪怕是雪的影像、雪的预报、雪的新闻,都像是飞向我的一把把弯月刀。
现在呢?我问。
冈仁波齐峰的雪跟这里的雪有什么不同吗?是黑的还是红的,是白里透红的雪,还是往人眼里塞的沙子?那雪为什么像梦一样吸引着我的儿子,为什么像砒霜一样害了明颖?陆一民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记起少年时第一次去秦岭的事。那次,火车“吭哧吭哧”爬了好长时间。坐在车尾里看,车头转过弯,喘出的粗气好像树丛生长。秦岭真高啊!我和母亲到了一个名字很大,其实站很小的小站,父亲惊喜得不知要干什么。吃过饭后,母亲让父亲领我去钻雪林。我们走到一处相对平坦的雪地上,父亲教我看雪窝、雪沟、雪崖、雪峰。父亲在前,他的脚从雪地里拔出时干净利落,几乎带不出雪绒。我跟在父亲后面,踩着他一尺多深的脚窝,膝盖上全是雪沫。母亲跟在我后面,从旁边踩出新的脚窝。我回过头问母亲怎么不跟着踩在我的脚窝里。我喘出的气,热乎乎的,有一些扑在母亲红扑扑的脸上。母亲笑着说,有自己的脚窝多好啊。母亲回看刚踩出的脚窝,有雪雾从里面冒出。我转身越过母亲,自己踩了一个脚窝,又踩了一个脚窝。母亲笑着说要瞅准了再踩。我回头答应时,碰到旁边的一棵不太粗的树,树上的雪纷纷扬扬落在我们身上。后来,天空真的又下起了大雪。没有风,新雪落在旧雪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我的眼睫毛上挂了毛毛虫那么大的雪,惊慌时,它们被眼里的好奇融化了,眼角冰凉一下。我眨眨眼,放眼看去,近处、远处、低处、高处,白茫茫的。父亲给我指着,哪儿是沟槽,哪儿是斧子样的峭壁,哪儿有终年不退的雪线……我看到了巍峨的秦岭,看到了秦岭奇伟、壮丽、莹润的雪。父亲给我指的时候,母亲在一旁笑。雪林中,母亲的红围巾像正在盛开的花。白雪红花,多美啊!我心里喊了起来。这是我自己的秘密。以后的雪,不叫雪。
我要去冈仁波齐峰,我要替儿子去!在我回忆时,陆一民长出一口气,眼眸里闪着急迫、深远的光。
我开车陪你。我说。
陆一民看着绵延起伏、白雪皑皑的雪野,沉默不语。
我再不愿打扰他,踏着雪回到车旁,轻轻开了车门坐上去。
朵朵终于拍完了雪照,或者发完了朋友圈,发完了抖音视频。她拉开车门,神秘地说,唉,给班长介绍一个女朋友怎样?我从车窗上看到陆一民走了过来,忙说以后再说。她点头。
你像“母亲石”。可这要让女儿说才行。我急切说完,朵朵惊呆了,要扑向我。这时,陆一民脚上带着雪沫上了车。
下山转弯的时候,路边沟里有一辆白色轿车。我开启雪地模式后,慢慢把车停在一旁下去看。轿车无大碍,但不见人影。站了半分钟,我又上了车。下山到了平缓的路段,我开得稍快了一些,侧耳能听到轮胎压到雪地的“咕咕”声。
到了那条曾经捡到过狗头金的河段,我们下了车。
陆一民不理从后备箱取工具的我和朵朵,像看不见雪那样,径自踏雪而去。我瞥一眼河畔的雪地,似乎有几个不同的少年的身影来回闪现,又仿佛隐入了雪尘。
我看到了青玉一样的河流。一只白鹭,好像是雪变的,带着莹亮在河面上方翱翔。“雪/当我用战栗叫你,用自己的真/写下你/你就不再是虚构/我们相互打量 凝视/听从一只猎豹的速度/把我带入荒原,那白色的床单/它要留下什么”我想起早上朋友圈里一个叫艾子的人写的诗。
陆一民在河边看河面上的白鹭。他的周围,大雪沉默,大地白茫茫一片真清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