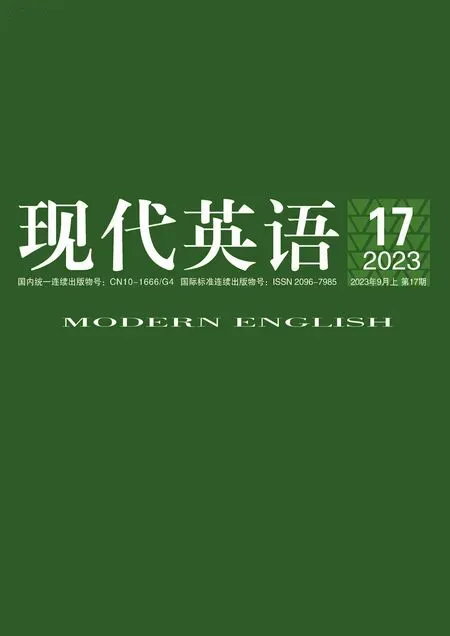“三美论”视角下«Crossing the Bar»两个中译本对比分析
——以黄杲炘、汪飞白译本为例
努尔比亚•吐尔迪
(新疆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 诗人在诗歌中,通常运用高度凝练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并运用节奏、韵律和特定的排列形式来让诗歌这一体裁得以呈现。 在翻译诗歌时,译者不仅要努力再现诗歌的主题和作者在诗歌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还要使诗歌的韵律和形式得以再现。 许渊冲先生提出的“三美论”在诗歌翻译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文章从意美、音美、形美三个层面对«Crossing the Bar»的黄高炘和汪飞白的两个汉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一、 作者和作品介绍
«Crossing the Bar»的作者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 他于1850 年因著名诗歌«悼念集»的出版被授予“桂冠诗人”称号。 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也获得了空前的突破,旧的思想和不断涌现的新知识和新观念(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动荡和价值观念的变化造成了信仰危机。 丁尼生在作品中尖锐地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与旧思想的冲突。 一方面,丁尼生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虽对旧思想产生过怀疑,但是最终调和了科学与旧思想之间的这一冲突。 另一方面,丁尼生自身的经历也影响着他的创作。 父亲的去世和好朋友哈勒姆的早逝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融入诗歌作品中。 丁尼生的诗歌充满了与离世相关的意象,离世主题成为他众多诗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Crossing the Bar»这首诗写于1889 年,是丁尼生晚期的作品。 这首诗不是丁尼生写的最后一首诗,但他要求把这首诗放在他诗集的最后。 丁尼生的对旧思想的态度经历了早年的模棱两可、中年的幻灭与思考和最后晚年的平衡与和解[1]。 这首诗是作者晚年时的创作,当时他已经在科学和信仰之间做出了折中与调和。 在这首诗歌中反映了作者视死如归的观念。 他认为离世不是人类的终结,而是与上帝的精神结合、信仰的回归。 整首诗表达了作者对离世超然豁达的态度。
在这首诗中,诗人用“日落”“晚星”“暮色”等名词,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寂静的黄昏图,一日中的黄昏景象象征着诗人也步入生命的黄昏。 诗人将抽象的情感寄托在具体的意象上,表达了晚年面对死亡的平静、安宁的态度。 “当我出海去,河口沙洲莫悲哭”“当我登船去,别离时分莫哽咽”,流露出诗人对将要来临的死亡的坦然的思绪。
文章选择了流传较广的黄杲炘和汪飞白的译文。 汪飞白的译本出版于1985 年,而黄高炘的译本出版于1995 年,两个译本出版时间相差十年,有较高的对比分析意义。 下文中将从“意美”“音美”和“形美”三个层面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
二、 “三美论”概述
20 世纪下半叶,许渊冲先生基于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说的“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提出了“三美论”[2],即“诗歌翻译不仅应忠于原文,还应做到意美、音美和形美”[3]。 “三美”的基础是三似,即意似、音似和形似。 “追求意似就是要传达原文的内容,不能错译、漏译、多译”[4]。
许渊冲先生认为,意美是诗歌翻译的第一要务,是“三美论”的核心和关键。 “意美”要求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象征、双关、深层含义等。 意境美是诗歌形式美和音韵美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也是诗歌美的最高境界[5]。 诗歌中的“意美”有时与文化和历史有较大关系,将诗歌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时,不同语言背景下的文化和历史差异导致原诗的“意似”无法实现,而原诗的“意美”也不容易传达。
音美,指的是“诗要有节调、押韵、顺口,听起来好听”[4]。 音美要求在译文中要体现原诗的节奏,韵律等。 尽管因为中西方语言差异,较难做到“音似”,但译文中也不能忽略“音美”的传达。
形美,主要是指诗歌的长短和对称两个方面最好也能够做到形似,至少也要做到大体整齐[4]。 想要体现原诗的形美,就要做到译文的行数和节数与原诗一致,在句子的长短和对仗工整方面做到形似。
许先生还认为,“三美”的地位不是并列的,而是有轻重、主次之分的。 “三美”之中,意美是最重要的,音美是次要的,形美是更次要的。 我们要在传达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三美齐备。 如果三者不可兼得,那么首先可以不要求形似,也可以不要求音似,但一定要尽可能传达原文的意美和音美[4]。
三、 原文与译文对比分析
(一)意美层面
原文题目:«Crossing the Bar»
黄杲炘译:«过沙洲,见领航»
汪飞白译:«越过海滩»
原诗题目“Crossing the bar”中的“crossing”用了双关的修辞手法。 一方面,它有十字架的意思;另一方面反映作者的死亡观,即死亡是从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 题目中的“bar”的本意是指河道或港口泥沙淤积处,涨潮时没入水中,退潮时部分裸露出来的地方;而“bar”往往会阻碍船的顺利通过,因此常常被喻为“生死关口”,象征着生与死的界限。
黄杲炘译文中的“沙洲”和汪飞白译文中的“海滩”都再现了“bar”本意。 两位诗人都通过使用注解,向读者说明了“bar”在诗歌中的含义。 两位译者的译文中都没有体现出“Crossing”的十字架这一层含义。
原文[6]:But such a tide as moving seems asleep,
Too full for sound and foam,
Turns again home.
黄杲炘译[7]:海深邃,洋空阔,
潮来海洋总须回头流;
满潮水悠悠,
流水似睡静无皱。
汪飞白译[8]:浑然流动的潮水似已睡去,
加强外部环境的防护与监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财务人员可能面临的风险,只有找到会计职业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才能从源头上处理将风险最小化。通过分析,本文建议增强风险意识教育才是最长效的防范机制。
潮太满了,反而无声无息,
从无边的海洋汲取的,
如今又复归去。
原诗前两句描写了海面平静的景象,衬托出作者面对死亡时平静的心态。 原诗第三句中的“that”指的是第一句中的“tide”,第四句中的“Turns again home”中的“again”代表来生,表达了作者视死如归,将死亡看作是生的延续的死亡观。
黄杲炘译文中,将原诗第三句中的“that”与第四句相结合翻译为“潮来海洋总须回头流”,将“that”明确的翻译为“潮”,向译文读者明确指明了原诗中的景象。 汪飞白译文中,第三句中的“that”所指代的“tide”没有明确的翻译出来,使译文前两句和后两句脱节。
原文[6]:For though from out our bourne of Time and Place,
The flood may bear me far.
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sed the bar.
黄杲炘译[7]465:尘世小,人生短,
这潮却能载我去远方;
过了沙洲后,
但愿当面见领航。
汪飞白译[8]:虽然潮水会把我带到无限遥远,
越出我们的时间、空间,
我希望见到领航人,面对着面
当我越过了海滩。
原诗第一句中的“bourne”是指“boundary”,意思为“边界、界限”;“Time”和“Place”大写为专有名词,并非指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是指诗人将要结束这一次的人生,实现生命的延续;第三句中的“Pilot”指的是上帝;第四句“When I have crossed the bar”与题目相呼应。
黄杲炘译文中,将“bourne”与“Time”和“Place”相对应,翻译为“尘世小,人生短”;将第三句中的“Pilot”译为“领航”;第四句的翻译和原诗一样与题目相呼应。 汪飞白译文中,将“Time”“Place”直接译为“时间”和“空间”,没有直观地译出原诗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境;将第三句中的“Pilot”译为“领航人”;第四句的翻译和原诗一样与题目相呼应。
(二)音美层面
«Crossing the Bar»这首诗由四节组成,每一节有四句,各节的尾韵分别是abab, cdcd, efef, baba。下面分别列出原文、黄高炘译本和汪飞白译本中的韵律,见表1:

表1 原文中的韵律

表2 黄高炘译文中的韵律:

表3 汪飞白译文中的韵律
押韵是达到音美的重要手段。 从上述表格可以看出,在原诗中,诗人通过头韵和尾韵的结合使用,使诗歌朗读起来节奏分明。 另外,诗人在第一节与第四节采用了一对重复的韵脚,形式上前后对仗,使诗歌富有节奏感。
由于中西方语言差异较大,在诗歌的翻译时较难实现译文与原文的“音似”,但可以通过中文中常用到的韵律来再现诗歌的“音美”。 黄杲炘和汪飞白的两个译本虽和原诗不“音似”,却都通过使用尾韵再现了原诗节奏上的“音美”,使译文与原文一样富有节奏感。
(三)形美层面
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最注重形式的一种文学体裁,形式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诗歌译文的形美,主要表现在行数长短整齐,句子对仗工整方面。
原文全诗共4 个诗节、16 行、102 个单词。 虽然每一节诗歌的长度都不一样,但每一节诗歌的第一行和第三行都比第二行和第四行长,长短句的交替出现使诗歌在形式上产生了抑扬顿挫的效果。 还有诗歌中的第一、三、四节最后一句都以“When I...”开头,形成了平行结构,增强了诗歌的气势。
黄杲欣译文共4 个诗节、16 行、108 个汉字。 译文中在保持原文意义再现的同时,通过交换原诗的行序,使诗歌每一节中第一句和第三句都比第二句和第四句长,长短句交替出现的特点得以再现。 四节诗歌每一节都严格做到了第一句6 个字,第二句9 个字,第三句5 个字,第四句7 个字,实现了每一节诗歌字数和形式上的统一。 原诗第一、三、四节最后一句中以“When I...”开头的三个句子,译文中在第一节第三句和第三节的第三句以“当我……”的形式再现。
汪飞白译文共4 个诗节、16 行、137 个汉字。 译文严格按照原文的行序翻译,也做到了长句和短句的交替出现。 原诗第一、三、四节最后一句中以“When I...”开头的三个句子,译文中在第一、三、四节的最后一句以“当我……”的形式再现,形式上与原诗保持一致。
四、 结论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 诗人用凝练的语言,借助具体的意象营造诗歌的意境美、音乐美和形式美,从而表达思想情感。 通过上文对«Crossing the Bar»的两个中译本在意美、音美和形美层面上的对比来看,黄杲炘和汪飞白的译文都各具特色。 在意美层面上,黄杲炘译本较大程度实现了原文意境美的再现,而汪飞白的译本中有上文指出来的个别几处之外,也再现了原文的意境美;在音美层面上,因为中西方语言上的差异,较难实现译文与原诗的“音似”。 二者的译文都没有实现与原诗“音似”,但通过对“音美”表现形式的调整,都在较大程度上再现了原文的“音美”;在形美层面上,黄杲炘的译文中,通过严格控制每一节中每一行的字数,实现了每一节字数和形式上的统一,形式较为对仗工整;而汪飞白的译文中,虽没有像黄高炘的译文中那样严格控制字数,但是长短句交替出现,译文形式较为自由。 黄杲炘和汪飞白的译本都在较大程度上再现了原诗的形式美。 总而言之,两位译者运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都以最大限度地传递了诗歌的意美、音美和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