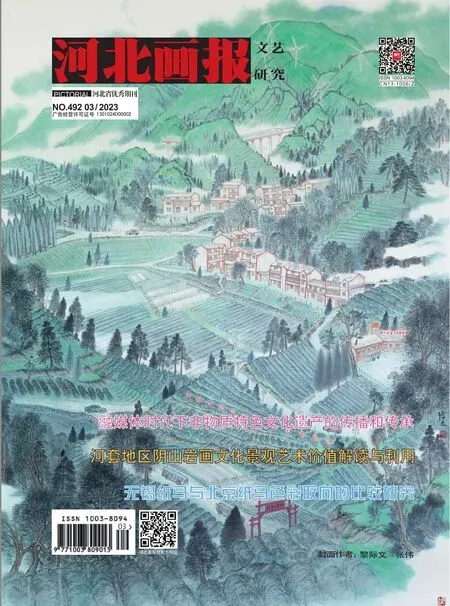昙曜五窟飞天形态考略
王楚昀 王双晖
(太原师范学院艺术学理论研究中心)
一、昙曜五窟飞天的位置及类型
(一)位置
昙曜五窟中的飞天形象不似早期敦煌飞天自由,只固定出现在两类位置,一为佛龛龛楣周边,二为大佛像头(背) 光侧。
1.佛龛龛楣周边
昙曜五窟中盝形帷幕佛龛较为常见,其帷幕上方的龛楣通常被划分为较为均等的六个格间,格间内刻有飞天形象,一般可见三组六个飞天,左右各三个为一组,两侧对称。16窟,明窗西壁下方的龛楣例外,为两组四个飞天,中央两个格间雕刻莲花纹饰。除该特例外,16窟南壁盝形佛龛,17窟西壁帷幕立佛大龛上格间,18窟明窗东壁盝形佛龛上格间中均有三组六个飞天形象。另外,16窟南壁的尖楣圆拱龛不设格间,但楣上也有飞天形象,且该组飞天形象较为特殊,为昙曜五窟中唯一一组伎乐天,龛楣左右两侧分别有六个飞天形象,各手持一类乐器,在其下方为一排手持莲花的供养式飞天。另外是位于佛龛顶部内侧,如17窟东壁和西壁佛龛内侧均有飞行式飞天。整体来说,昙曜五窟中的飞天形象大多可见于佛龛龛楣周边。
2.佛像头(背)光侧
除了佛龛龛楣上的飞天形象之外,其余飞天形象均出现在窟内佛像头(背)光外层处。包括17窟西壁帷幕大龛主佛火焰大背光外侧;19窟西耳洞佛像头光外层以及20窟主佛背光西侧的两处飞天。
(二)类型
昙曜五窟中的飞天形象主要包括飞行式飞天、供养式飞天和伎乐式飞天三类。其中飞行式飞天又可分为上升式飞天和平飞式飞天两类。
1.飞行式飞天
飞行式飞天是飞天形象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在昙曜五窟中数量最多。通常可依身体姿态分为平飞式和上升式飞天。敦煌早期石窟中出现的下降式飞天在昙曜五窟中缺失。平飞式通常出现在龛楣隔间中,身体与地面基本呈180度平行,腿部略有弯曲,呈漂浮状。手臂上举,手中持物。第16窟南壁龛楣内下侧飞天,其左手位于腰侧,右手向前上方举起,手中持有莲花。除16窟明窗西壁的龛楣格间平飞式飞天外,均为左右对称的两组,上升式飞天则通常在龛楣格间的斜砖面上 (如图1)。

图1 昙曜五窟佛龛龛楣飞天类型分布(自绘)
2.供养式飞天
供养式飞天也称供养天,通常出现在主佛背(头)光侧。20窟主佛背光西侧上升飞天下方即为一供养天。其侧身面向主佛,左腿蹲姿,右腿跪地,双手平举于身前,手中持有莲花。19窟西壁火焰大背光外侧的供养天风格与其他供养天有别,其身着汉式衣衫,脚下为莲花座但其身体姿态与其他供养天单膝下跪状,手中捧有类似莲花物。
3.伎乐式飞天
昙曜五窟中的伎乐天仅16窟南壁龛楣一例(如图2)。其形态相对单调,均为平直立姿,手中持曲颈琵琶、腰鼓、竖箜篌等中西乐器。此类飞天姿态较为统一,面部雕刻遵循一定的模本,只是手臂姿态依据所持乐器类型差异而略有变动。

图2 云冈16窟南壁佛龛龛楣伎乐天(线稿摹绘)
二、昙曜五窟飞天形态的范式
(一)昙曜五窟飞天形态样式及其溯源
学界对飞天概念的探究基本明确其与乐舞行为的关联。目前公认的是印度地区的飞天形象主要有两种姿态,一是以演奏音乐为主要场景刻画的直立落地式飞天,一种是以舞蹈瞬间姿态刻画的腾空式飞天[1]。马土腊的飞天不像犍陀罗飞天富有曲线,但二者在姿态上都与一种名为Vrscika的印度传统舞蹈相似。这种姿态以下肢呈现从跪姿到起身的动作[2]。
云冈第17窟西壁佛龛内侧的上升式飞天和18窟明窗东壁上部佛龛龛楣格间中的平飞式飞天的下肢姿态均为类似Vrscika的姿势,其一腿屈膝向前,一腿向后伸出。昙曜五窟的飞天通常肢体都以固定的样式呈现,只出现了个别尝试性汉化的案例。例如17窟主佛大背光外侧的供养飞天和上文提到的18窟龛楣上的残损飞天,此类飞天数量较少,表现为与中原汉晋时期羽人类似的形象——褒衣博带,身形纤瘦, 不似印度。
(二)昙曜五窟飞天形态范式之成因
1.政权更迭与地区统一
北魏与赫连夏的交恶是昙曜五窟开凿前或是说佛教真正在北朝流行前发生的一件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大事。太武帝时期北魏对胡夏的战争胜利一方面使得北魏领土与河西西域地区再无间隔;另一方面北魏对中国北方地区的统一使得原本分散在各个地区的民族实现了融合。
昙曜五窟中的飞天形态是跨过河西地区对印度本土艺术的直接继承。在云冈石窟一期造像中的一些艺术因素——例如发式、佛衣等细节,均体现了犍陀罗和马土腊艺术风格,包括水波纹发和曹衣出水样式佛衣等。这说明昙曜五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未加改造或修饰的印度佛教造像手法。这则需要归因于北魏对中国北方地区的统一导致的绿洲丝绸之路重新开通以及粟特人在征胡夏之后的移民迁入。
2.艺术风格个性化因素缺失
当然艺术作品的形成不能脱离艺术家个体。沃尔夫林在《艺术风格学》中认为艺术家的个人因素同样是塑造艺术作品风格的重要因子。对于昙曜五窟的飞天形象而言,创作它们的工匠便承担了艺术家的身份。首先是北朝时期的官方大规模艺术,如石窟寺造像、墓葬壁画等的创造并不是由专业艺术家完成的,工匠的表现能力良莠不齐,不追求艺术家的个性表达。再者,大多数官方性艺术创造都有“粉本”,这已是学界公认的观点。
3.早期中国佛教艺术的复合型母题
昙曜五窟的飞天形象一方面如上文所述直接继承了印度本土飞天形象的艺术风格,但另一方面也对个别飞天形象进行了汉化改造尝试,例如上文提到的17窟和18窟飞天形象。其主要蕴涵了两种地域风格。一是对汉晋时代中原本土羽人母题的继承。这可能是出于对政权汉化政策的附和。18窟残损龛楣中的飞天形象(如图3)身着交领衫,下裳长而有汉族衣饰。汉代羽人中比较典型的是人首人身,肩背生翼的形象。虽然学者称其生翼,但实际上可能只是长毛或简单的类三角几何形(如图4)。云冈18窟的这一飞天形象左右肩背部延伸出弯曲变形的三角状物,但其无汉代羽人立于头顶的大耳,腿部也无类似的长毛(或翼)。

图3 云冈18窟南壁明窗上部残损佛龛飞天形象(线稿摹绘)

图4 东汉羽人戏灵瑞画像石拓片
二是对印度本土飞天母题的学习。即便是在汉化因素较为明显的17窟和18窟飞天形象上,也无可避免地具备印度飞天造型的因素。在姿态上,这两组飞天都保留了犍陀罗和马土腊的古拙特征,肢体线条平直,不像敦煌飞天或者汉代羽人一样具有明显的曲线;在动作上,汉代羽人一般呈现出跪坐、飞翔或者奔跑姿态,一般无单膝跪姿。这基本可以解释昙曜五窟出现少量有汉化倾向的飞天形象的原因。
三、昙曜五窟飞天形态的功能分析
(一)时空叙事功能
1. 动静结合的时空叙事
2021年十二月天梯山石窟搬迁时发现了一组珍贵的北凉时期飞天壁画(如图5),其中央是一供养天,上方是一平飞天。在云冈第20窟中存在一致的构图安排——第20窟光背西侧上部为一平飞天,其下方是供养天(如图6),与天梯山石窟的壁画一致。可惜天梯山的这组飞天有残损,不能看到供养天下方的情况,但可以通过残留的半个头部推断其下方还有另外的飞天形象。而云冈20窟则保留了完整的画面,在平飞天和供养天下方还刻画了更多体积缩小后的供养天形象。

图5 天梯山石窟新见飞天壁画

图6 云冈20窟光背西侧飞天
这组构图有两种叙事意味。第一是动静组合产生的时空叙事。平飞天的姿态是动态的延续,其停留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最富孕育性的时刻”[4],从而能够引发观众的想象。相比之下,供养式飞天就不存在更多想象的空间,因为他的姿态本身就是静止的延续。无论怎样揣测飞行姿态的飞天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都不影响这一组合营造的时空叙事效果。第二是缩小的供养天群像,其作用主要在于构建一个“飞天朝拜”的空间,按照大小顺序排列的供养天暗示了在画面之外的供养空间,当然也具备空间叙事的含义。
2.卷轴画式的连续时空叙事
另外在飞天的组合构图上,佛龛龛楣格间中的飞天同样具有叙事意趣,并且是中原古典图像叙事手法的延续。在中国古典卷轴画的构图传统中,时空是被平行铺开的。例如《洛神赋图》这种长卷轴形态的古典绘画,通常将整个画面默认地分为几个区域,《洛神赋图》的第一卷首先是曹植站在洛水河畔与洛神相遇,第二卷中再次出现相同的人物,第三卷类同,如此用完整的长画完成了洛神赋的故事叙事。有了长卷轴画的叙事经验,昙曜五窟的飞天也具有类似的叙事性。首先是格间中的飞天往往极其相似,只有衣衫动作略有变化,排除模本照刻的原因分析,这种相似的人物面部和体态构成了单一飞天由外部进入佛龛层,最后在佛龛中完成一系列舞蹈动作的叙事,就像《洛神赋图》中多次出现曹植和洛神一样,佛龛中的飞天实际上只有两位——左右分别是同一飞天,不过在不同的格间中处于不同的时空。
(二)符号表意功能
正如索绪尔所言,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5]。实际上在飞天图像流传的过程中其意义已产生了跨区域的共性能指便,在所指上可能因地区不同而略有变化但整体上来说飞天与忍冬纹或者佛陀眉心的白毫一样具备符号的指代性质。
更重要的是实际上是昙曜五窟飞天符号的能指含混性。鉴于上文提出昙曜五窟飞天形象的姿态特征和风格处于“受传”和“接受”的过渡中,我们必须考量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规则观念和“羽化”观念在其符号能指中的影响。
《阿弥陀经》载,“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在东汉时期的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中出现了饰金的情况,学界大多以之为佛典“三十二相之身金色相”之具象,有学者认为这一结论有待考据,因为犍陀罗造像的饰金手法显然早于“金色相”的文本记载[6]。但无论是两者何者为先,抑或是两者何者为主要影响因素,都不能否定饰金是法相庄严的具象化表达。那么即便是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庄严”也是佛教造像必须要遵循的艺术准则。通常飞天或天人形象在佛典中都有活泼生动的特征,敦煌的飞天形象即是对这一文本描述的再现。而在昙曜五窟乃至犍陀罗和天梯山的案例中,这种特质似乎被削弱了,飞天的姿态具有单一性、规范性,甚至一些飞天的面部表情也是“复制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工艺不能做出像敦煌一样富有活力的飞天形象,而是因为“法相庄严”思想在佛教早期造像中的重要地位,犍陀罗本土和马土腊佛教艺术都遵循这一规则。如此来看,敦煌早期飞天的形体反而更加自由,其中缘由仍待讨论。但可以明确的是昙曜五窟飞天作为一种宗教符号保留了佛教原生的“庄严”能指。
另外是“羽化”观念在昙曜五窟中虽然并不明显,但是毕竟也有表达,这说明在这一时期中原世界的宗教理想进入了佛教的符号世界。从东汉时期开始,羽人就逐渐形成了引导、愉悦(游戏)和侍从的意指功能[7],其中引导、侍从功能在西传的飞天上也可寻得相似之处。这也是羽人能够与飞天融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飞天的原因。而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羽人的出现并不单纯是图像借鉴,也是中原汉族“羽化登仙”的世界观、宇宙观、宗教观在佛教信仰体系中的延续。无论是前往昆仑还是前往天界的汉族往生理想都很好地被贯彻在佛教净土观中,于是飞天便具备了指引人类精神、灵魂进入更加美好的空间的能指,这在佛教的原生教义中并不存在。
四、结语
昙曜五窟作为我国早期官造佛教艺术的代表,其中飞天形态主要包含三类,即飞行式飞天、供养式飞天和伎乐式飞天。飞行式飞天的模式与敦煌尤为不同,极大程度上保留了“犍陀罗模式”,即便融入了“羽人”的形符号能指,却仍旧保持印度的本土身体姿态。供养式飞天的形态较为统一,伎乐式飞天同样反映了飞天“云冈模式”的规范性特征。而在图像功能上,首先,昙曜五窟的飞天既承担了北凉飞天中普遍存在的时空叙事功能,同时又借鉴了汉式长卷轴图像连续叙事的经验,完成佛教净土场景的构建。其次,昙曜五窟飞天图像具有符号性,并同时承担了佛教概念、造像观念和中原宇宙观、世界观的所指和能指。这些“云冈模式”正是中国早期石窟寺艺术的特征之一。
注释
①图采自冯骥才.中国大同雕塑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116.
②本文对云冈石窟的分期方法承宿白先生1978年发表的《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一期为昙曜五窟,其可再分两组,以19窟为中心的18、19、20窟较早,以菩萨装交脚弥勒像为主尊的17窟和释迦像16窟较晚。二期界定在文成帝后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洛前。三期自太和十八年迁洛始,最晚不早于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34年)。
③图采自冯骥才.中国大同雕塑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55.
④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藝发掘报告[M].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6:12.
⑤图采自甘肃省博物馆推https://mp.weixin.qq.com/s/fuiOh2PrYt3VkDwYT44Uw。
⑥图采自图采自冯骥才.中国大同雕塑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