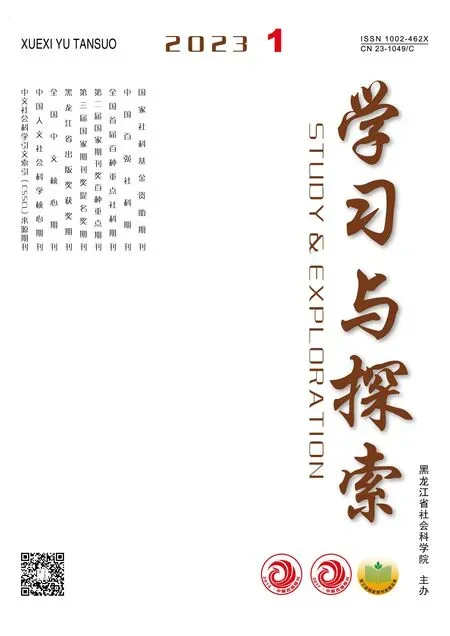新诗之“歌”建构
——重审1930年代《新诗歌》的诗学主张与创作实践
方长安,扈 琛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诗歌会敏锐地捕捉到“歌”对于新诗艺术建构的价值,在其机关刊物《新诗歌》中提出了“新诗歌”主张。长期以来,文学史著作虽对这一诗史现象多有论述,但大都将其发生归因于时代主题的要求,对中国诗歌会和《新诗歌》的诗艺探索价值缺乏充分的学理性估衡。实际上,如果将中国诗歌会对“歌”的建构置于中国新诗艺术发展历程中重审,不难发现,它触碰到了五四以来新诗重“文字”而轻“视听”、重“诗”而轻“歌”的问题,具有重要的诗学史价值。
一、“新诗歌”观念的提出
长期以来,“诗歌”作为一个约定俗成、不言自明的概念,为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着;然而,在不假思索中,作为诗歌之“歌”却往往被忽略了。1933年2月,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在上海创刊,正式提出“新诗歌”的概念,发起了“新诗歌运动”,“《新诗歌》的名字,使诗坛另开别一生面”[1]。作为一个复合名词,“新诗歌”既可以解读为“新”的“诗歌”,也可以解释为“新诗”之“歌”。前者以总称意义上的“诗歌”,向在30年代基本取得合法性地位的“新诗”发起挑战,强调其区别于既有“新诗”之“新”特征;后者同样是以“新诗”为本,突出其相对于既有“新诗”的“歌”性,强调新诗之“诗”与“歌”的融合。显然,“新诗歌”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其“新”特征体现在“歌”上,目的在于改变长期以来新诗观念中“诗”与“歌”相分离的状况,使新诗真正成为“诗”与“歌”的统一体。
首先,中国诗歌会以“诗歌”取代“诗”,以“新诗歌”取代“新诗”,特别强调了诗歌之“歌”性。他们不仅以“诗歌”命名其文学团体,以“新诗歌”命名其机关刊物,而且在纲领性的《发刊诗》《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以及“编后记”中,特意使用了“诗歌”“新诗歌”的概念。在《新诗歌的技术问题》《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新诗歌运动底目标》等重要理论文章中,“新诗歌”也取代“新诗”成为诗学讨论的对象。在诗歌作品中,更是出现了大量以“歌”“曲”为诗题的作品,如《码头工人歌》《矿工的歌》《小宝宝的歌》《一九三二年交响曲》《夜底进行曲》等。可见,突出、强调诗歌之“歌”性是中国诗歌会提出“新诗歌”的重要意图。
其次,“新诗歌”观以“新诗”为基础,在承认新诗合法性的前提下,倡导“新诗”文字性的“诗”与视听性的“歌”相融合。中国诗歌会不仅继承了五四以来“用新鲜的通俗的文字”[2]、“有什么就写什么,要怎么写就怎么写”[3]的“新诗”创作理念,而且认为“新诗歌”在“创造新格式”时,应取法歌谣、时调、歌曲等具有“歌”性质的民间形式,“接受他们普及,通俗,朗读,讽诵的长处”[4],创造新诗“歌”的艺术品格。在用韵方面,主张“新诗歌”的韵“应当如歌谣时调所用的一样,采用通俗的自然韵……讲究严格的格律自然不必,虽然,对于节奏的铺排应有相当的注意”[3],通过对韵律、节奏的把握突出新诗的“歌”性。王亚平在河北分会发行的《新诗歌》中也提出,新诗歌“要有便于唱读的韵律。虽然有许多人提倡废除韵律,但在可能范围内总以有韵律的好。尤其大众诗歌,为了容易颂读,为了容易普遍化,是必需有韵律的”[2],特别强调了韵律对于营造“新诗歌”之“歌”格的作用。显然,以承认新诗的合法性为前提,在对歌谣、时调等具有“歌”性质的民间形式借鉴中,特别关注节奏、韵律等“歌”的特征,发现、构建新诗之“诗”与“歌”的统一关系是中国诗歌会倡导“新诗歌”的基础。
再次,中国诗歌会将“歌”理解为“歌唱”“朗读”的声音化传播功能。在《发刊诗》中,中国诗歌会反复使用“唱”“歌颂”“歌唱”等语词,提出“我们要唱新的诗歌,歌颂这新的世纪”,“我们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我们唱新的诗歌罢。歌颂这伟大的世纪”[5],“歌唱”“歌颂”被认定为传播“新诗歌”的重要方式。中国诗歌会在《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中也指出:“写完一篇诗歌以后,最好能够注意到:找个机会朗读出来,看别人能否听懂。基于此点,将来可以扩大成为新诗歌的朗读运动。有价值的诗歌,应该拿到大众里头朗读起来。”[3]“朗读”不仅成为拉近“新诗歌”与大众的方法,更成为衡量“新诗歌”大众化效果的标准。森堡在《关于诗的朗读问题》一文中还专门探讨了新诗“朗读”的必要性和方法论,认为“诗是一种‘言语的艺术’”,“用文字来表现的场合,纵令贴在很大的壁上,但在同一的时间内,因为要受到一定的视觉的限制的缘故,能够看到的到底不多。可是,在朗读的场合里,纵然也要受到听觉的限制;但在同一的时间中,却可以对着几十几百几千甚至于几万的大集团朗读,获得组织上的效果”[6]。中国诗歌会同人更是反复强调新诗歌“要紧的是要使人听得懂,最好能够歌唱”[3],“我们作‘新诗歌’的运动,是要创造新的,大众化的,使大众读得懂,听得懂,反应大众生活的诗歌”[4]。显然,“读得懂,听得懂”成为“新诗歌”的关键诉求。穆木天在《关于歌谣之制作》中也认为“诗歌是应当同音乐结合一起,而成为民众所歌唱的东西”[7]。在中国诗歌会同人看来,诗歌不再是静态的、固定于纸质媒介的文本,而应成为动态的、读者歌唱出的声音。1934年,鲁迅在《对于诗歌的一点意见》中也对重视“歌”的诗学探索表示支持。他认为:“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8]指出了既有“新诗”中“歌”的缺失,肯定了“歌”对于新诗艺术、新诗传播与合法性建设的必要意义,同时也明确了新诗书面作品声音化的实现,需要以赋予新诗“节调”“韵”等“歌”要素为前提。因此,在承认新诗合法性、坚持白话书写与自由体的基础之上,通过对音响、节奏、韵律的锤炼赋予新诗以“歌”之要素,进而以朗读、朗诵、歌唱等声音化方式完成“新诗歌”的建设,是中国诗歌会提出“新诗歌”口号的重要目的和深层意义。
“新诗歌”的提出以及对新诗“歌”的关注,是中国诗歌会基于新诗发展现状,沟通古典诗歌传统的产物。它从概念层面强调了“歌”对于新诗艺术建构、传播的意义,承认了“歌”是推进新诗大众化的重要形式。同时,对新诗“歌”的声音传播策略的强调,也反向推动了新诗创作艺术本身的调整——取法与大众关系紧密的歌谣、时调等民间形式推动新诗“歌谣化”;创制适应广场化、集体化朗诵的诗剧以推动新诗“戏剧化”,成为赋予新诗“歌”属性的创作方案。
二、新诗之“歌”创作实践
五四以来,新诗倡导者对格律、对仗的质疑性批评,对节奏、押韵的弹性要求,以及对自由体式的过度推崇,都在相当程度上阻隔了“诗”“歌”之间的联系,削弱了新诗歌唱、诵读的功能。以“新诗歌”观为诗学依据,中国诗歌会在创作实践上倡导新诗向具有音乐性、舞台性的歌谣、戏剧等文体靠拢,赋予新诗作品以“歌”的属性。
首先,套用歌谣、时调等民间形式,使新诗“歌谣化”,赋予新诗“歌”的属性与品格。
《新诗歌》创刊之初,中国诗歌会就主张“新诗歌”的创作要“采用大众化的形式……有利用时调歌曲的必要,只要大众熟悉的调子,就可以利用来当作我们的暂时的形式。所以,不妨是:《泗洲调》《五更叹》《孟姜女寻夫》”,“采用歌谣的形式——歌谣在大众方面的势力,和时调歌曲一样厉害,所以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些形式”[3],就是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5]。王亚平也认为:“有时为了某种体裁,就不惜用旧调填新词——这并非受旧调的拘束。未执笔前,却觉得这内容和某种流行调儿相吻合。不但不受旧调拘束,而且能使内容和形式更相统一起来。”[2]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新诗歌》前4期发表的33首作品中,就有《新莲花》《新谱小放牛》《新编十二个月花名》等十余首改编自民歌、歌谣。1934年6月,中国诗歌会还专门推出了《新诗歌》“歌谣专号”,刊发“歌”“谣”“时调”等歌谣作品60余首——“歌谣化”俨然成为赋予新诗“歌”属性的主要方式。虽然中国诗歌会反复强调套用歌谣并非“新诗歌”的全部,但这种将时调、歌曲当作“新诗歌”暂时的形式,将“新诗歌”视为用白话语言写成的小调、民歌的观念,都令对歌谣、时调“旧瓶装新酒”式的套用成为“新诗歌”的创作主流。
所谓“旧瓶装新酒”,即是在“旧瓶”“旧酒”分离的前提下,使用“旧瓶”(旧形式)以共享歌谣、小调的曲调与唱腔,赋予“新诗”以“歌”的属性;注入“新酒”(新内容)以满足文化启蒙与革命动员的现实需要。在具体的创作方式上,即是在保证歌谣原调的前提下,将新内容灌注其中,调用歌谣已有的接受基础,唤醒读者的阅读记忆。例如在当时广受好评的《新谱小放牛》,其创作实质就是对原有小调内容的替换:具有神话、传奇意义的“赵州桥”“玉石栏杆”“张果老”“柴王爷”就被替换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大工厂”“花车机器”“纺纱女”“资本家”。这种替换主要集中在名词性的意象上,而较少涉及原有的曲调结构,即使必须要有所创造,也不会超出原有的押韵方式。故而在“什么人成天不住手?什么人享福硬揩油?”[9]的改写中,奇玉特意保留了《小放牛》“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了一道沟?”中原有的韵脚;在“大工厂什么人修修?花车机器什么人留?”的改写中,也完整保留了“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的框架结构,“什么人修”“什么人留”的话语方式也被直接套用。故而,“《新谱小放牛》中所重建的音响结构使它得以在听众中唤起耳熟能详的感官愉悦,在听觉记忆的参与下,其中的叙事与讯息变得易歌、易诵、易记”[10],即使读者不能在第一时间理解其内容,也能在口口相传的重复中不断强化对“新诗歌”的印象,“在歌着新的歌曲之际,不知不觉地,得到了新的情感的薰陶。这样,才得以完成它的教育的意义”[7]。朱自清在评价《新诗歌》时指出:“歌谣的组织,有三个重要的成分:一是重叠,二是韵脚,三是整齐。只要有一种便可成歌谣,也有些歌谣三种都有。”[11]“旧瓶装新酒”的“新诗歌”创作策略,正是在对歌谣“重叠、韵脚以及整齐”的组织复刻中,调取歌谣原有的音响节奏,赋予新诗以“歌”的属性。其他如《新编十二个月花名》《国难五更调》《新十叹——为正泰橡胶厂惨案而作》等也多依照这种方式,在保留歌谣、小调原有“歌”的框架基础上,在对“旧形式”的洗刷与重建中,将具有现实意义、符合教导大众要求的“新内容”灌注其中,以扩写、重写、改写的方式赋予了“新诗”以“歌”的品格。
其次,借鉴歌曲、戏剧等文体形式,使新诗“戏剧化”,赋予新诗“歌”的属性。
虽然在具体的创作中,对歌谣小调等“旧瓶装新酒”式的套用是“新诗歌”实践的主流,但在中国诗歌会构想的“新诗歌”蓝图中,“创造新的形式,为大众合唱诗”[3],“致力于大众合唱诗,朗读诗,诗剧以及一般大众诗歌的创作”[4],也是赋予新诗“歌”属性的重要方式。中国诗歌会在《发刊诗》中就曾发出号召,“朋友们!我们一齐舞蹈歌唱罢,这伟大的世纪的开始”[5],具有表演性的舞蹈也被作为“歌”的一种表现方式。森堡也认为诗应该具有“直接的感动性”“大众的普及性”以及“集团的鼓动性”,“当我们朗读时,若能把所读的诗背熟,则一壁朗读,一壁表情,做手势,其效果恐怕也不小。这也可以说是朗读的演剧化”[6]。在此基础上,以舞台表演为目的,反映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诗剧与大众合唱诗应运而生。所谓诗剧是“诗”与“剧”的文体结合,即“剧体的诗或则诗体的剧”[12],而大众合唱诗则是“解放过去新诗歌的叙事性和抒情性的狭隘,主要的是采用集团底力学的,私演剧的要素而歌唱,用集团的朗读、合唱、音乐、照明、肉体运动等把诗的节奏表现出来”[13]。这类“新诗歌”作品虽然不多,在《新诗歌》(上海,1933)中仅先后发表有芙的《六士兵——一首大众合唱诗》(大众合唱诗)、柳倩的《阻运》(诗剧)、甘馥的《一面坡——一段民众的说白》(合唱诗)、雪芙堡的《防俄——一段民众的说白》(诗剧)四首,(1)仅统计《新诗歌》中明确标明为“诗剧”“大众合唱诗”的作品。却表现出迥异于既有新诗的特殊质素。
与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杨骚的《心曲》《迷雏》等取材历史或彰显自我的“剧曲”“诗剧”不同。30年代的诗剧、大众合唱诗在内容上多取材于社会事件,在形式上多讲究重叠、押韵与分行。与同时期的“歌谣化新诗”等“新诗歌”相比,诗剧、大众合唱诗普遍篇幅较长,具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且表现出鲜明的戏剧特征,呈现出“新诗+戏剧”的跨文体写作趋向。例如柳倩的《阻运》,开篇即以舞台布景形式,对诗剧的发生做简要介绍;又以“团总”“壮丁甲”等角色的设定,区别不同层次的诗歌内容,形成对话;再以舞台说明,方便表演活动的展开——显然,这种新形式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适应舞台表演的需要。同时,诗剧仍保留了诗歌分行的基本特征,并特别关注韵脚的使用,充分发挥了诗行安排上的节奏优势,不仅读来上口,而且也在层层递进中渲染了诗歌的鼓动色彩,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其中,对“舟子之歌(合唱)”的劳动号子设置,也更容易与大众的情感产生共振,“变成一种有节奏的自然音乐”[14]。又如甘馥的合唱诗《一面坡——一段民众的说白》,简化了舞台背景、舞台说明等戏剧元素,以多声部合唱的方式,在各角色唱词以及“一个声”“几个声”“大家合唱”的渐进式设计中,营造渐强的氛围,引发听众、观众共鸣。这种新诗“戏剧化”的实践,在故事性情节推进以及舞台化艺术行为的结合中,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将视觉与听觉融为一体,以肢体动作与舞台布景的加入,降低了诗歌的理解难度,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读者的从众心理,为新诗书面作品的广场化传播提供了可能。
新诗“歌”的创作实践,既是对古典诗歌声音化传播方式的接纳,也是在继承与突破中,从“歌”——音响节奏以及朗读、合唱等声音技术——入手,推动“新诗歌”创作的主要方式。歌谣化新诗、诗剧以及大众合唱诗的“新诗歌”实践,都在相当程度上加速了新诗的传播,降低了新诗的接受门槛,也从新诗文本的建构层面为读者体验和参与“新诗歌”提供了必要的文本。“大都市里僻街狭巷一般蓝衣短裤的人们和不知忧乐的孩子们,有意无意地在唱《打倒日本泗洲调》《招募义勇军莲花落》《爱国山歌》《中日交战景》”[15],成为“新诗歌”声音化、广场化传播的现实写照。
三、新诗“歌”性探索之反思
中国诗歌会提出“新诗歌”观、创作新诗之“歌”的价值和限度何在?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需结合时代语境,将中国诗歌会对“歌”的重视,尤其是围绕“新诗歌”展开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置于五四以来新诗自身的发展路径上进行考察。
从起源上看,古典诗歌“歌”“诗”一体,“歌”在相当程度上是“诗”得以成立的必要因素,并在后来逐步演变出格律、押韵等形式要求。但新诗发生以后,现代诗人对旧诗格律的批评,对韵律的弹性要求,对自由体的极端倡导,导致了新诗之“诗”与“歌”相当程度的分离。严格意义上讲,很多五四新诗仅能称之为“诗”,却不能称其为“诗歌”;仅能通过眼睛阅读,而不能借助声音传播。30年代初,中国诗歌会提出“新诗歌”概念,在理论上对“歌”的言说,对“朗读”“歌唱”等声音传播形式的探讨,都一定程度地发现了“歌”的诗性价值;在创作中,对歌谣、戏剧等形式的借鉴,对重叠、排比等技巧的接纳,也有效赋予了新诗以“歌”的属性,完成了“大众歌调”的创造,改变了五四以来新诗只重视“诗”而轻视“歌”的局面,为重新思考、探索“诗”“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然而,抗战救国的时代诉求决定了中国诗歌会对“诗”“歌”问题的触碰并非诗性维度上的有意为之。它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到了“歌”对于新诗大众化的重要意义,但却未能深入探讨“诗”“歌”之间的艺术相生关系,也未能冷静思考“歌”对于“新诗”建构的深层意义,在新诗“歌”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方面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中国诗歌会对“新诗歌”的倡导与实践,是在重大社会事件背景中出现的,是在需要诗歌发挥其教育、教化功能时发生的。30年代初,“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令社会环境剧变,强化新诗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发挥诗歌“重教化”的实用功能成为新诗的时代任务。然而,“新诗运动虽然是相当地成功,可是,新诗止于为几个人之享受品,而没能获得大众性,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新诗未能广泛地被民众所接受,诗人只管作新诗,而大众仍在唱封建的五更调”[7],“旧形式的诗歌在支配着大众”[3]。中国诗歌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目光转向“歌”,进而提出“新诗歌”概念的。但是,时代主题的过度参与导致诗人对“歌”的关注和探索并非新诗艺术建构本身的逻辑使然,因而也就不具备发展的延展性和持续性。当时代主题对诗歌的传播、教育需求降低,对新诗可“歌”的呼声也随之衰退。事实证明,在“新诗歌运动”之后,虽然“朗诵诗运动”的出现曾将“新诗歌”导向“朗诵诗”与“街头诗”的高潮,发现了适应现代新诗声音化、广场化传播的新形式; 50年代末还出现了以演唱、朗诵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民歌运动”;贯穿50—7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也仍在继续探索新诗“歌”的新可能。它们都强调了“歌”对于新诗传播的重要意义,肯定了新诗大众化和声音化的发展方向。但这些诗学现象都是在外在目的要求下发生的,是在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出现的。进入80年代后,“歌”的热度快速退潮,新诗又转向对个性、技巧的“诗”探讨,再次“回到了它的老家”[16]——在内容上向诗人内心深处挖掘,在形式上愈发精致,也愈发与大众审美脱节。对于现代新诗发展而言,这种以社会现实需求为导向,随现实语境而起伏的诗学探索恐非新诗发展的良性趋势。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诗”“歌”一体的意识并未内化到新诗建构、发展的逻辑之中,仅表现为应对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办法,未能在诗人心理层面上升为诗学探索的方向和形式,功利性和工具性仍是诗人追求新诗可“歌”的主要动机。
其次,在新诗“歌”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方面。新诗书面作品声音化、广场化的前提是新诗音响节奏的建设。“新诗歌”的提出,就是创新性地试图在“新诗”与“歌”的融合中将古典诗歌对音响节奏的关注以及其“诗”“歌”融合的创作形式,延续到新诗的建构中来。然而,在紧张、急切的社会革命动员诉求中,中国诗歌会将“新诗歌”的“歌”简单理解为“歌唱”“表演”的传播方式问题,将“歌”处理为“歌谣化”和“戏剧化”的创作方案,忽视了追求白话自由的“新诗”与要求音响节奏的“歌”之间的张力关系。而在中国诗歌会“旧瓶装新酒”的“新诗歌”实验中,无论怎样冲刷“旧瓶”(旧形式),实际都难以避免对“新酒”(新内容)造成“污染”,这就导致通俗的形式在吸引读者关注的同时,也削弱了内容本身的效力。读者在阅读这些“新诗歌”时,触发的到底是已有的经验还是诗歌的内容,仍需画一个问号。同时,对歌谣、小调等讲求对仗的民间形式的套用,也限制了内容的发挥。《新十叹——为正泰橡胶厂惨案而作》中就有“苦辛是为舍人苦!为了厂主(还要)压死人”[17],为适应七言的体式而不得不使用括号来做内容上的补充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重蹈了“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18]的覆辙,成为对以诗体解放为特征的新诗的反叛。虽然中国诗歌会同人在理论探索中反复强调,“我们对于这期‘歌谣专号’所持的态度,是当为新诗歌运动中部门的工作。这点是不够足的”[4],对“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式亦常存警惕之心。但在实际创作中,对歌谣的套用仍占了大部分,即便是新创制的诗剧、大众合唱诗等新形式,也未能有效吸纳“歌谣、时调”等对音响节奏灵活运用的优势。尤为有趣的是,有关歌谣“重叠、押韵、整齐”的组织特征总结还是由中国诗歌会外的朱自清提出的。在新诗“戏剧化”探索中,也有人批评“《六士兵》是没成功。我曾经叫好几人来合唱过,但是不能合唱的地方很多,唱起来也不紧张,听不懂,有许多人物说的话就非要和做戏一般的先介绍出来不行”[14],相当一批“新诗歌”仍存在难懂、不上口的弊端。此外,对时事消息的偏重将“新诗歌”简单化为传递新闻的工具,这也导致了相当一批“新诗歌”只能敷一时之用,而缺失历久弥坚、经久不衰的“经典化”能力,导致“新诗歌”少有“经典”作品的产生。时至今日,《小放牛》仍在北方地区被广泛传唱,而在当时广受好评的《新谱小放牛》却潜沉于历史的长河风光不再,这也是值得反思的。
总之,中国诗歌会对新诗之“歌”功能价值的发现,对“新诗歌”概念的提出,以及对“新诗”与“歌”一体化的实践,都在观念层面重新联通了“诗”与“歌”的关系,在实践层面强化了对歌谣、小调等中国诗歌小传统的接纳,对推动新诗大众化,改变五四以来重视“诗”而轻视“歌”的新诗发展现状具有纠偏意义。然而,中国诗歌会对“歌”工具性的过度考量,对“诗”“歌”关系的简化理解,对歌谣、小调等形式的简单套用,都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诗之为诗”的前提性要求,又令“新诗歌”难免落入“非诗化”的怪圈,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