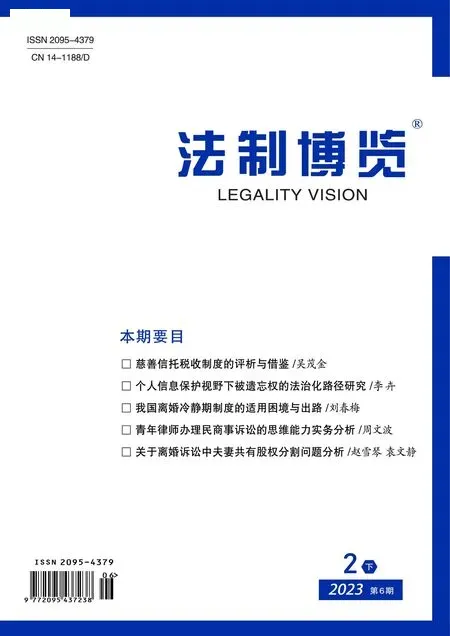公司设立阶段签订合同的责任划分问题研究
张 蕊
江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发起人往往会在公司设立阶段就进行一些交易行为,但如若公司没有成立或者成立之后却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第三人就会向代表公司签订合同的发起人追责,由此引发的发起人合同纠纷比普通的合同纠纷更为复杂。这也就是要探讨设立中公司责任制度的原因所在。
一、必要设立行为责任承担具体划分
以行为主体的名义为标准,可以分成三种情形来讨论必要设立行为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分别是设立人以自己的名义、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和以拟成立公司的名义进行的必要设立行为的责任归属。
(一)发起人以自己名义签订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非常容易引起歧义,其并未说清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还能不能请求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换言之,对该条款的隐含意义有三种推断:第一,是不是意味着发起人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第二,合同相对人是否可以任意选择由成立后的公司或发起人承担责任?第三,发起人与成立后的公司是否需要对合同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适用第一情况,有利于发起人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设立公司的活动中,但是同样也容易导致发起人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而故意从事某些风险行为。另外,这种做法对发起人是一种“赦免”,与之相对应,这对相对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无疑是给合同相对人从事商事活动带来了极高的风险。如果适用第三种情况,商事活动的各方当然都希望自己能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同时承担最小的风险,发起人希望成立后的公司对合同的法律关系进行追认并单独承担责任以使自己能够独善其身,而合同相对人则倾向于由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来确保自己的债权能得到充分实现。因此,不论是第一种推测还是第三种推测都无法实现合同相对人与发起人之间的相对平衡。综而观之,第二种推测是更加适当的,即合同相对人能在成立后的公司和发起人之间选择任一方承担责任。这样的规定可以帮助合同相对人及时了解发起人和成立后公司的财务状况,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能够增加对合同相对人损失的救济机会,此时发起人也会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避免责任的承担。
2003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三十七条规定和2006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二条规定都透露出司法实践倾向于在公司成立前,由发起人承担责任,在公司成立后,如果公司享有了权利,那么相对人享有选择权,并且不能反悔。因此,综上所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应更改为合同相对人选定由任一方承担责任后,就不得改变自己的选择。
(二)发起人以拟设立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合同
在讨论发起人以拟设立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的责任划分之前,必须要先对两条法律规定进行讨论,分别是《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这两个法条都禁止了不得以未经核准登记的公司名义从事设立必要行为,那这种绝对禁止是否恰当呢?或许可以合同效力为切入点来考量这一问题。如果发起人以拟成立公司的名义从事设立必要行为认定为违法的话,那么发起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就是无效的。但是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都是非常排斥认定合同无效的,因为认定合同无效不利于合同双方的利益保护。故发起人以拟成立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不应当归于无效,也就不应当是绝对禁止的,应该分情况进行讨论。
另外,其实早在2003年,最高法在《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一)》)中就已经有了相关规定,其中第四条明确指出,发起人以拟设立公司名义签订的先公司合同对成立后的公司具有约束力。在司法实践中,因发起人以拟成立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而引发的纠纷也不在少数。例如“S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诉G营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S公司与L村村委会、G公司签订“三方协议”时,S公司正在设立过程中,随后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最高法引用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三条和《规定(一)》第四条的规定,认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S公司既然已经成立,主体资格完全合格,可以享有该案所涉合同的权利,承担义务。
学术理论和司法实践都从反面印证了《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的不恰当性,因此,这两条规定应当予以修改。第一,针对《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应当区分发起人的主观心态,如果发起人是恶意冒用未经登记的公司名义从事法律行为,那么自然应当禁止并加以惩罚;如果发起人是善意的,把公司还未登记的事实告知相对人,那就不应当禁止发起人以拟设立公司的名义从事法律行为。第二,针对《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应当增加例外情况,即善意发起人已经事先通知合同相对人公司尚未成立时,发起人以拟设立公司名义从事的法律行为并不绝对无效。
既然善意发起人以拟成立公司的名义从事的必要设立行为并不必然无效,就需要对责任承担方式进行分类。一方面,如果发起人无恶意,也就是发起人已告知相对人公司尚未成立时的前提下,当公司成立后,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如果发起人恶意隐瞒公司没有成立的事实而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并导致合同相对人的利益遭受损失的,应由发起人单独承担相应责任。
(三)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合同
这种情况的讨论意义不大,既然是为设立公司所必需的行为,而且是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进行的,自然应当由成立后的公司来承担相应责任。
二、非必要设立行为的责任归属
(一)司法实践
司法实践中,法院多会承认非必要设立行为对成立后公司的约束力。例如“钦州市R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H大学技术合同纠纷案”,2010年8月10日,钦州R公司与H大学签订了《技术开发(委托)合同》,2010年9月28日及2010年11月21日,双方又另外签订了《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的《合同附件(1)》及《合同附件(2)》,而2011年6月24日钦州R公司才成立。在本案的判决书中,法院是如此论述的:“虽然涉案《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签订时钦州R公司仍处于设立过程中,但在该合同签订后钦州R公司依法成立,且《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有钦州R公司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同时钦州R公司并不否认《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对其产生的拘束力,故钦州R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另外,在“北京T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与山西D铁路轨枕有限公司、M控股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中,2013年3月1日,北京T公司作为甲方与山西D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而2013年3月7日,北京T公司才成立,在本案中,法院判定《合作协议》有效,成立后的公司应当承担责任。
通过这两个案子,可以窥见法院的裁判态度,不过这样的做法容易导致发起人铤而走险,按照并不完善甚至尚未成形的决策去实施高风险的商业行为,对设立中公司发起人限制过少并不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做法。重视公司的营利性和交易机会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需要对发起人的自由规定相应的限制,否则将矫枉过正。我国《民法典》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就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我国《民法典》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效果由法人承受。按本条规定,设立人不论以谁的名义所做的,只要是以设立法人为目的行为,那么所有后果和责任都由法人承担,而不管该行为是否真的属于设立法人的必要事项,该规定一旦在实践中被大幅运用,就会给成立后的公司带来极大的麻烦,不利于商事活动的开展。[1]相较于《民法典》第七十五条,《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更有利于成立后的公司的发展。
(二)理论探讨
1.发起人以自己名义所为的非必要设立行为
对于这一情况下的责任划分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两派观点:合同之债相对理论与代理理论。[2]合同之债理论是指一般情况下由发起人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但是如果成立后的公司予以追认或者实际享有了合同的权利义务,就由公司来承担责任。代理理论是指发起人与设立中的公司是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责任承担按照代理关系进行划分。因为设立中公司并不是非法人团体,而且发起人与设立中公司也并非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因此,此处我更赞同合同之债理论。[3]
2.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所为的非必要设立行为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了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成立后的公司承担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先公司合同的民事责任。这条规定其实存在一定的漏洞,因为它没有对必要设立行为和非必要设立行为加以区分。本条第二款又规定了成立后的公司能证明发起人是为自己的利益签订先公司合同的,可以不承担责任。本款规定也有一定不合理之处,如何才能证明发起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签订先公司合同呢?尤其是当发起人故意隐瞒自己的获益的情况下,成立后的公司想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如果公司难以证明的话,那岂不是发起人所做的任何行为都能对成立后的公司产生约束力。这样很明显是不合理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从事的非必要行为,如果成立后的公司予以追认,那么就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责任;如果成立后的公司不予以追认,那么就由发起人承担责任。不过发起人如果能够证明成立后的公司是实际享有合同权利的主体时,可以提起不当得利之诉。
3.发起人以拟成立公司名义所为的非必要设立行为
分析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可以发现我国其实并不提倡发起人以拟设立公司的名义去从事各种行为,涉及该问题的法律法规也寥寥无几。只有《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禁止了发起人以拟成立公司的名义从事商事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发起人以拟成立公司的名义订立的合同就是无效的,原因在于如果合同一旦宣告无效,反而可能会成为成立后的公司或者发起人逃避债务的借口。[4]为此,可以参考国外相关制度。例如美国法律是以是否善意为标准来判断发起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如果发起人是善意的,就可以免除责任。如果发起人是恶意的,就要承担连带责任。《德国公司法》中亦规定了发起人如果在公司设立之前以公司名义进行商事行为,就要承担连带责任。[5]其实绝大多数国家从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都倾向于由发起人来承担设立中公司行为的责任,而且对合同效力也持谨慎态度,一般不予认可。但是对这类合同一律否定很容易打击发起人创建公司的积极性。所以国外通过追认制,合同更新理论以及探寻真意理论等来加以救济和弥补。如德国法规定发起人可以通过公司成立后的债务转移手续获得免责,而且不需要经过合同相对人的同意。
综上所述,公司成立后,发起人以拟设立公司的名义所为的非必要设立行为的责任承担应当根据合同相对人是否知情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当合同相对人不知情时,如果是发起人恶意隐瞒的,那么即便成立后的公司进行追认,也应当由发起人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是发起人过失导致的合同相对人不知情,那么发起人是否承担责任就取决于成立后的公司是否追认了,追认即免除发起人责任,不追认就只能由发起人承担这一责任了。第二种情况,合同相对人知情的前提下,若成立后的公司进行追认的话,由公司来承担责任。若成立后的公司不予追认,那么责任自然落到了发起人的身上,尽管如此,发起人如果认为成立后的公司实际享受了合同权利的,可以提起诉讼。
三、小结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发起人为了实现效益最大化,在公司的设立过程中难免会实施各种商事行为,其中会涉及多方利益。为解决各主体的责任承担问题,我国颁布了多部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解决纠纷有一定作用,但是在责任划分问题上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之处,本文结合司法案例和相关理论对设立中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进行了分析,希冀可以帮助解决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