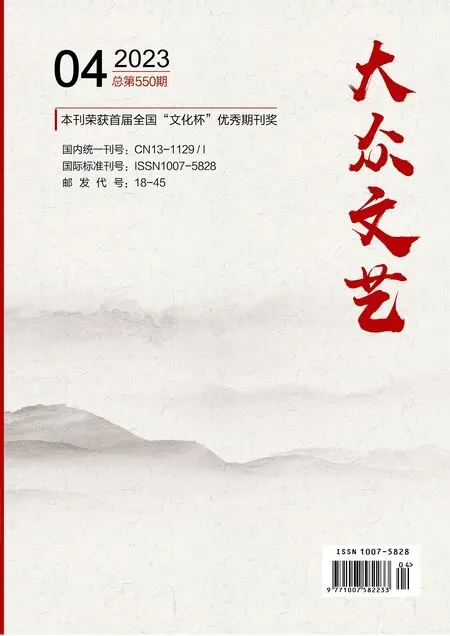论大江健三郎未收录作品《火山》中的文学表象*
田 泉
(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 300204)
一、引言
《火山》是大江健三郎学生时代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这部作品作为第一届“银杏并木奖”的入围作品于1955年9月发表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校友会的机关杂志《学园》之上。从“技巧上非常的巧妙”“作为寓言式的作品是十分成功的”①等的获奖评语中虽然能够看到评委对作品给予的肯定,但从“一种像是读优秀学生作文的感觉”②的评语中可以看出评委整体上对《火山》完成度的评价并不高。
在大江健三郎的早期作品中有一些由于政治原因或作品的完成度不高而未被收录到单行本或大江小说集中的作品,这些作品只能通过查阅最初作品发表的杂志才能够阅读到。不被收录造成了这些作品不仅不能进入读者的视野,甚至在大江文学研究领域也存在着对这些作品的忽视。本文将以大江最初的习作《火山》为对象展开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思考大江文学的起点以及该作品中的相关文学主题与之后的大江文学之间存在的联系。
二、《火山》的作品世界
首先回顾一下作品内容。小说描述的是因学生运动受挫而自杀的表妹“L子”之死使青年“我”深深陷入了一种“灰暗情绪”之中。为了从这种负面情绪中解放出来,“我”登上了奔赴火山的旅途。然而奔赴火山的旅程和经历却让青年“我”正视了在表妹走上自杀之路的过程中自己冷漠旁观的态度。整部作品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主体,在叙述我奔赴火山的途中经历的同时,以插叙的方式讲述了有关表妹“L子”的回忆。在叙事的过程中,以“我”奔赴火山的旅途经历为主线,有关表妹“L子”的回忆为辅线展开叙事。在作品的结尾处,火山爆发的光景与想象中“L子”火葬的光景交织在一起,主人公“我”发现无论是面对表妹的学生运动、还是面对抵制美军基地的S村农民运动,在对待他者关系时总是采取冷漠的“旁观者”姿态而“茫然自失”。
关注作品内容就会发现,这是不能简单否定的一部作品。无论是叙事方法,还是作品中的文学要素,与大江之后的文学创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大江的早期作品乃至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都能看到这部作品的影子。
三、历史与现实相交叉的叙事模式
正如前文作品内容介绍所言,《火山》是以大学生“我”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讲述了“我”奔赴火山的旅途经历和对表妹“L子”之死的回忆。作品中奔赴火山的旅途见闻这一现实叙事和对表妹的点点滴滴的回忆这一历史叙事看似两条不同的叙事线索,在叙事进程中二者相互交叉,共同刻画和凸显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文学主题。小说的两条叙事线索梳理如下。
作品在开头部分就宣告了表妹“L子”的自杀。为了摆脱表妹自杀所带来的“灰暗情绪”,主人公“我”开启了奔赴火山的旅途。然而在这趟火山之行的伊始“我”就预感此次旅途是一个“不祥的”旅程。果不其然,途中因为美国逃兵跳车逃跑而被射杀,引起了车内的一阵骚动。而那个美国逃兵就是坐在“我”对面,专心看着画报,出于礼貌给“我”劝让点心而面露打扰到别人的难色。尽管赞叹于外国士兵的温文尔雅,而在骚乱后发现对面坐着的美国士兵不见踪影时,“我”仅仅以旁观者的姿态想象着“那个男人即使在水中也一定很安静吧,唯恐打乱映照在河水中的月光,以优雅的自由泳穿过水面”的样子。之后,“我”在转乘的车站结识了赴S火山对新物质M的成分进行实地调查的矿山技师。到达S车站,不顾矿山技师的阻拦收下了车站列车员送给“我”的小山羊,带着小山羊和技师一起开始了登上S火山的旅程。然而二人登山的步伐被美国军团S火山支队所设立的“禁止入内”的告示牌所阻拦。原来美军将把S火山作为其军事基地正在对火山进行人工喷发的作业施工,以探明新物质M的分布状况。尽管火山喷发将对S村村民的生命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威胁,但S村内部分裂成基地合作派与基地反对派。合作派的农民受雇于美军,配备了新型武器协作美军S火山支队的施工作业,禁止人们登上火山。在与射杀闯入禁区栅栏小山羊的合作派农民进行理论的过程中,“我”和矿山技师结识了基地反对派农民假肢少女,并受到假肢少女的邀请参加农民们的反基地大会。这一过程,“我”总是半推半就地在技师的勉强下参加了基地反对派农民的大会。在村民大会上,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决定由“我”和技师上山调查火山口的情况,同时反对派农民将与合作派农民进行斡旋说服他们炸毁人工喷火的装置,必要时进行武力斗争。最终在“我”和技师登上火山口发现了火山人工喷发装置,面临喷发在即的火山,生怕卷进村民们的纷争,以一幅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而逃离S火山的“我”不同,为了检测新物质M的成分并提醒村民们及时避难,在火山喷发的火光中矿山技师再次返回了S火山。
同时,作品在旅途见闻的现实叙事过程中,穿插了“我”对表妹“L子”之回忆的历史叙事。对表妹之死,从我听说时起就努力地逃避着回忆。这种卑鄙的“努力”硬生生地让我对L子的记忆就如同那遥远的回忆一般逃离开来,虽然那“并不是十分久远的记忆”。然而作品中青年“我”的这种努力从旅途的一开始就是一种徒劳,在奔赴火山的列车刚一驶出车站我就陷入了对表妹的回忆:在表妹死后的追思会上无论是表妹曾经的恋人“Y”还是好友“N”,这些曾经与表妹参与同一学生组织活动的同志面对着死去的表妹,“僵硬地紧绷着身体”、以“一幅防卫似的姿态”和“痛惜什么人似的、满脸悲伤的表情”刻意酿造出一种“哀悼的气氛”,这些人并非为表妹之死而感到悲伤。表妹之所以自杀就是因为她在所属学生团体“人道主义党”活动中的所感受到的一种孤立。这样,小说在“我”的这趟“不祥”的旅途中并行讲述了表妹“L子”与学生组织的关系。小说中在与美国大兵短暂的客套寒暄之后“我”又陷入了陪表妹参加学生运动组织“人道主义党”主持的“P式和平大会”的光景。作品汇中这一场景的描写揭示出了表妹“L子”在学生运动组织中之所以感到孤立的原因。作品呈现出了以合唱、鼓掌、握手的方式让人狂热兴奋的“人道主义党”大会作为同一化、均质性话语空间的属性,这样均质性的话语空间强制人们与不合乎“逻辑”的“新纲领”保持步调的一致,小说中表妹的这段话语暴露出这些处于群体运动中的每个人的实际状态与所谓的连带感和一体化相距甚远的事实,把集团主义下人们理性的丧失和在这种集团活动中人的内心和行为之间存在的龃龉形象地描绘了出来③。因此,置身于运动团体中的表妹根本无法和作为同志的恋人Y、闺蜜N之间建立信任关系,这一点从表妹死后的追思会上,这些曾经的同志甚至要“努力”酿造出“诚实”“哀悼”的氛围的光景就可以一窥究竟。
由上可以看出,小说在叙事进程中将“我”奔赴火山的现实与对表妹的回忆这一历史交叉推进。这样的叙事方式可以说是大江文学的源点,在之后的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之一的《万延元年的足球》(1967年)中愈发成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模式。在《万延元年的足球》中,哥哥根所蜜三郎夫妇和弟弟根所鹰四各自因为对自我生存现状的迷失而返回故乡的峡谷村庄,试图通过归乡寻根实现自我救赎。因意外而右眼失明的哥哥蜜三郎和妻子因为无法接受智障儿的出生,又接连遭遇挚友自杀的打击而沉溺于酒精逃避现实。弟弟鹰四参与60年代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左翼学生运动受挫,后作为右翼剧团的一员辗转美国演出“转向剧”以示悔改谢罪,但“转向”却成了鹰四内心不可触碰的伤口,在美国所过的也是一种迷失自我的放浪生活。就是在这样一种陷入泥泞的生存状态下,突然归国的鹰四邀请哥哥蜜三郎夫妇回到了故乡。在该作品中将回到故乡峡谷村庄的根所兄弟寻找自我救赎的现实与曾经发生在峡谷村庄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展开叙事。回到故乡的蜜三郎兄弟试图弄清一百年前发生在峡谷村庄他们的曾祖父和弟弟参与的农民暴动的历史以及二战复员归来的S兄在朝鲜人部落被杀害的真相。在这一过程中,弟弟鹰四建立了村里的足球队,并试图通过带领足球队的训练发动青年们抢劫村里朝鲜人超市的暴动,以此恢复自己在左翼学生运动中“转向”的挫败感。在这样的故事发展进程中,“鹰四指挥着这群暴徒。他仿佛与引导万延元年暴动时曾祖父的弟弟化为一体,猖狂地向藏在仓房里的我、母亲和那些家中的亡灵挑衅”④,正如柄谷行人所言,《万延元年的足球》所呈现出的是蜜三郎兄弟所生活的历史现状与一百年前万延元年时的历史、“村庄=国家=宇宙”这样一种“超历史性”的“同心圆式的结构”⑤。显而易见,发端于《火山》中的将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叙事模式在《万延元年的足球》中呈现出了更加成熟甚至可以说是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四、火山的文学含义
《火山》的开头是以“我”对火山的憧憬开篇。作品主人公“我”对火山的憧憬完全是一种光芒四射的幸福感。大江作品中把“火山”作为一种对“幸福的憧憬”的文学书写在其文坛处女作《奇妙的工作》(1957年)中也可以看到。《奇妙的工作》是一部描写20世纪50年代末东京的大学生生存生态的短篇作品,作品讲述了三个大学生为了价格不低的兼职收入,在职业杀狗人的带领下处理大学附属医院实验用犬即杀狗的故事。作品通过大学生的知性,对人所主张的“生活伦理”以及战后不断膨胀的日本经济增长体系进行了批判⑥。作品中身患严重“脚气病”的女大学生甚至为了去火山的旅费而从事杀狗,在女大学生眼中“火山真不可思议”“想起火山我会笑得流泪的!巨大的山正中有个洞,从那里呼哧呼哧地冒出烟,有多神啊”⑦,充满了幸福的色彩。对于大江作品中“火山”的表象,有学者认为是对“混沌而沉重之现状的逃避”⑧,也有学者认为火山只是一种“瞬间获得救赎的意象”⑨。然而在《火山》和《奇妙的工作》中可以看到,火山既没有成就主人公对现实的“逃避”,也没有让主人公获得所谓的“救赎”。《火山》中的青年“我”虽然到达了火山,但在喷发的火山面前,我却没有矿山技师奔赴喷发的火山去协助村民的勇气,在火山面前我发现的却是自己一直以来冷漠的“旁观者”的姿态以及对表妹“L子”之死应负的责任。而在《奇妙的工作》中,最终因为肉贩子的欺诈行为使得女学生并没有获得应得的收入,作品中女学生奔赴火山的计划被无限地搁置。因此,大江作品中的“火山”这一意象,既没有成为逃避现实的“理想国”,也没有成为获得“救赎”的乐土。作品中的火山只是主人公憧憬“幸福”的一个“幻影”⑩。
还值得注意的是,《火山》中的主人公对火山的向往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逃离志向”在之后大江的文学作品中也是被反复书写的一个文学主题。在《我们的时代》(1959年)中的23岁的日本大学生靖男试图通过参加法国书店和日本报社共同举办的有奖征文比赛获得赴法国留学的机会而逃离日本,作品中把这样的“逃离志向”描写成为“离开日本的希望,从混杂着愉悦与屈辱的颓唐无赖的生活中摆脱出来的希望”“这是从在日本青年中飞扬跋扈猖獗流行的精神阳痿中摆脱出来的希望”(11),这样的作品设定既表明了青年大江对于日本战后时代的不满,也是大江作为同时代青年所发出的呐喊。而这一脱离日本逃向海外的主题设定在《个人的体验》(1964年)中则演化为主人公“鸟”对非洲的向往。在《个人的体验》中,即将为人父的主人公“鸟”面对自己的婚姻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却惶恐不安地担心着“我实实在在地踏上非洲大地,戴着太阳镜仰望非洲长空的日子真的会来吗”(12),“一旦妻子生产,我被关闭到家庭的牢笼里(事实上自结婚以来,我就走进牢笼里了,但笼盖还开着。不过,生下来的孩子将笼盖严丝合缝地盖上),我独自一人的非洲之旅就会彻底告吹”(13)。可见《个人的体验》中向往非洲的“逃离志向”隐喻着主人公对现实和责任的逃避,尽管这一点与《火山》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而不同于前一部作品的是在《个人的体验》中主人公最终经过炼狱般的现实逃避,最终接受了智障儿的出生这一现实,实现了与智障儿的共生。此外,大江作品中“逃离志向”的文学主题在其描写核时代下的人类生存危机和谋求救赎的作品《治疗塔》(1991)、《治疗塔惑星》(1991)中则被描绘为逃离地球奔向宇宙惑星“新地球”的大逃亡。在这些“逃离志向”的文学表象中,无论是法国、非洲还是外星球,其中都表明了对现实的不满,其原形都可以追溯到《火山》这部作品中。
结语
可以看出,《火山》的众多文学要素在该作品之后的大江文学创作中得到了灵活的应用。鉴于篇幅,不能更加详细地对文中涉及的其他要素进行一一详细的分析。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出,《火山》虽然是一部未被收录的作品,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大江文学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当我们把这部作品纳入大江文学的整体创作中对其进行梳理就会发现它与之后的大江文学所存在的紧密联系,不得不重新审视该作品作为大江文学之出发点的重要地位和文学价值。这也促使我们去进一步探讨大江早期那些未被收录的作品。
注释:
①第一回银杏并木奖入选作品揭晓[J].山下肇等.学园,1955(09):54.
②同①.
③大江健三郎のアルバイト小説-習作「火山」から「運搬」へ[J].高橋由貴.日本文芸論叢(19),2010(03):47.
④万延元年的足球.大江健三郎著.于长敏、王新新译.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124.在原文基础上略做修改。
⑤历史与反复.柄谷行人著.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109.
⑥大江健三郎《奇妙的工作》中的现实批判[J].田泉.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5(09).
⑦奇妙的工作.斯海译.收录于死者的奢华[M].大江健三郎著.王中忱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6.
⑧大江健三郎「奇妙な仕事」-−犬殺しの歌[J].橋川俊樹.稿本近代文学,1988(12).
⑨火山のイマジネ-ション―暗い山と栄光の山[J].川本三郎.文学界,1991(08).
⑩『万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ール』論―火山のイメージその他―[J].助川徳是.古典と近代文学,1971(10).
(11)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译.性的人·我们的时代[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73.
(12)大江健三郎著.王中忱等译.个人体验[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4.
(13)同(12):6.
——以大江健三郎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