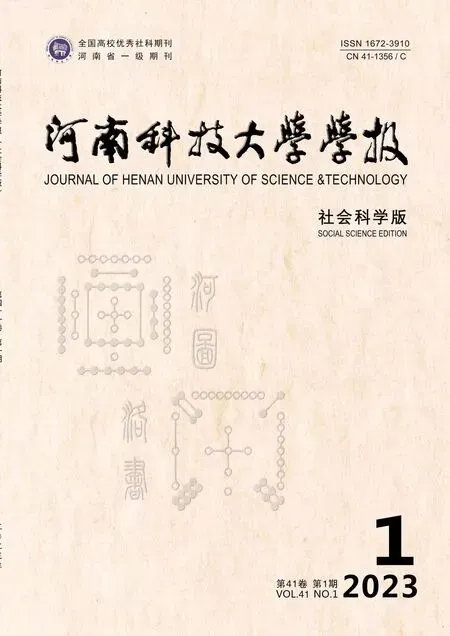中国现代黄河诗歌中的苦难抒情
吕亚斐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苦难是文学中经久不衰的抒情。所谓苦难,从狭义的个体角度,可以理解为现实苦难(艰难和不幸的遭遇)和精神苦难(如痛苦);从广义的社会学角度,则可以理解为社会苦难(贫穷、动荡、战乱等)和大地苦难(自然、生态苦难)[1]。在20世纪上半叶河患和战争频发的大背景下,黄河诗歌苦难抒情有两种表现方式:其一,泛滥成灾展现出黄河凶横和险恶的一面,代表作有葛葆桢的《咆哮的黄河》;其二,战争给底层民众带来无法挣脱的苦难,不同于可怕的黄河形象,此时的黄河感受着百姓悲惨的生活和悲剧的命运,悲哀地发出呼喊,代表作有郭沫若的《黄河与扬子江对话》《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艾青的《北方》《风陵渡》《乞丐》等。
杨匡汉在《黄河吟》序言中首次提出“黄河诗歌”,他认为“新诗取代旧诗应运而生于黄河流域,新诗人们遂以更加挥洒自如、活泼流畅的笔墨,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直接诉诸人的情感体验,俯视和评说着黄河的总体意象”[2]3。本文在河南大学刘涛教授界定的“黄河文学”的基础上定义“黄河诗歌”,即以黄河为叙事背景、叙事对象或抒情对象,讲述黄河及黄河两岸所发生的人和事,展现黄河文化,颂扬以黄河为象征的民族精神的诗歌。构成黄河诗歌的要件有两个:一是诗歌,二是黄河。“诗歌”指黄河诗歌的性质,包括歌词与诗;“黄河”指题材、内容和对象。这里的黄河指狭义的黄河本身,不包括广义的黄河流域。
一、北方大河的咆哮
黄河诗歌的灾害书写,不仅记载着现实社会黄河和民众的实际状况,而且传达着动乱多难时代下诗人的情感和愿望。黄河泛滥的原因之一是暴雨使得黄河水位急剧上涨,超过天然或人工的限制范围,这种情况下它属于自然灾害的一种。自然灾害的发生虽然有非自然因素的作用,但自然异常变化仍是诱发灾难的主因,故而将“自然灾害”解释为“由自然事件或力量为主因造成的生命伤亡和人类社会财产损失的事件”[3]。根据以上界定,本节涉及到的自然灾害指的是,由于自然因素,黄河带给人的身体和精神创伤,不包括人为因素,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失控,以及人为造成黄河决口泛滥都不在本节论述的范围内。
1933年是20世纪黄河最严重的水灾年,“当年从7月中旬开始,上中游就集中发生暴雨……据陕县站测录,最大流量为22 000立方米每秒。由于来势迅猛,河床来不及宣泄,下游决口50多处,受灾面积达11 000余平方千米”[4]。可见,这次黄河水灾受灾面积大、受灾人口多,对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1949年以前,黄河频繁决口泛滥,从自然原因来说,一是暴雨导致黄河水流量过大,二是源自黄土高原的泥沙淤积在水流变慢的下游河道里,使得河床不断加高。伴随灾害发生的是房屋被冲毁,土地被淹没,因此灾后百姓的生存更加艰难,摆在大部分灾民面前的选择是饿死或者逃亡。灾害后带来的饥荒,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
葛葆桢《咆哮的黄河》刊载于《文学》1935年11月第5卷,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诗人在揭露和批判现实的同时,也传达出对饱受灾害的人民的同情。《咆哮的黄河》共分为四小节,内容可以概括为“黄河泛滥”“人民受难”“诘问黄河”“遥寄不屈”。前两节揭示“咆哮的黄河”是国土的浩劫,人民的灾难,透露出悲苦的时代情绪。后两节诗人在追思中诘问黄河,作出回答后转向展望未来,并试图用强烈的抗争情绪摆脱现实难解的悲愤。诗人情感最终走向坚信群众力量。
诗歌开头,黄河以“愤激”“跳跃”的姿态出现,汹涌“狂奔”的态势让诗人连发三个来处与去向的疑问。而黄河“一怒的气势”果真印证了诗人的猜想,它凭借磅礴的气势“残破”北中国,摧毁了“万千的村落”。雄伟的长城和泰山皆无法阻挡这股咆哮着的奔流,以致古开封、铁桥成为灾难的承受对象。黄河泛滥使得人民赖以生存的家园遭到破坏,在自然灾害面前,灾区百姓不论选择“残存”还是死亡,都被拽入苦难的深渊。诗人以民众为中心,借助黄河水以及风这两个直接作用于人的自然因素,通过“跳跃”“动荡”等动词的使用,把整个社会动荡的状况浓缩在“摇晃晃的长堤”中,构成一个能够折射时代普遍苦难的微型世相图。当一切存在物都处于“动荡”的状态时,“孤堤上几千几万的魂灵”[2]18与“残存的只得还挣命”[2]18的社会实状,便以苦难为唯一的桥梁,贯通了现实与真实。灾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灾害导致食物匮乏,繁重的劳动又造成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灾民面临着饥饿和压迫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社会关系失调与民众的生存欲望产生强烈冲突。至此,前两节完整叙述了灾害发生的过程和灾后的社会现象,面对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人民承受着现实苦难,又在沉重的苦难中寻求生机。
其后,诗人在目睹社会苦难的情况下,向黄河发出“为什么不知疲倦”“为什么毫不抖颤”的悲愤诘问,紧接着又通过追忆历史的方式,感怀昔日黄河对“先民”和“文化”的帮助。由于诗人的出发点从受难的人民转换到黄河,因而情感色彩也随之变化——低沉变为乐观的疑问。诗人用怀疑黄河“要把这批柔弱的子孙锻炼”[2]20的语气,扭转了沉潜在诗中的悲痛情绪,从而流畅地衔接起下一节要传达的热烈情感。第四节中,直白的语言与豪壮的叙述语气,直接冲撞了前三节铺垫的凄苦气氛。连续两句“你且休要”“你休想”的心灵呐喊,表明诗人寄托“伟大的将来”后萌生出希望,这希望来自“无数的巨灵”向黄河“争命”和对黄河“管教”。而“无数”意味着数目多,“巨”有高大之意,两者联合起来指的是具有强大力量的群众,这个指称包含着诗人对“通体光明、力量无边而且始终代表着真理和正确方向的群体”[5]的坚信和颂扬。不过,这种裸露且不加雕琢的情感未免显得空旷,诗人对现实灾害治理的认知受此情感驱动,只得去未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
二、黄河与扬子江对话
战争具有复杂的两面性,它推动了人类历史进程和社会演进,促进人类的发展,但这一极端行为又给民族带来灾难,其巨大的破坏力使普通民众遭受家破人亡的苦难,百姓不仅失去故土沦为难民,还要压抑着无法规避的伤痛。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备受战火的侵扰,各地哀鸿遍野,在此背景下,产生了许多书写战争的诗歌。位于北方又承受着战火的黄河,成为诗人创作战争诗歌的题材、背景或者叙事对象之一。中国的诗人们或鲜明地表达激愤,将诗歌作为宣泄情感与鼓舞士气的武器;或融入民间,作为亲历者用诗歌记录所见的哀景,以排遣内心的悲痛。但是由于“只有随着现代的民族国家概念的诞生,黄河才会获得民族、国家的象征喻义”[6],以及当时对黄河相关问题的不重视,现代书写战争的黄河诗歌数目并不多,主要创作者有郭沫若等。
1928年相继出版的郭沫若诗集《前茅》《恢复》,分别收录了书写战争的黄河诗歌《黄河与扬子江对话》《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前一首发表于1923年《孤军》杂志第4、5期合刊“打倒军阀”专号。1922年,国内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悲惨的境遇中,黑暗的社会现实使郭沫若的理想破灭。不过,在短暂的苦闷彷徨后,郭沫若依然为诗作定下前进的基调。他反抗军阀统治,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着眼现实高呼革命,激愤地创作出《黄河与扬子江对话》。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下令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通缉郭沫若。郭沫若被迫决定前往苏联,不料出发前病倒。1928年初,在医院恢复期间,他写下了《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这一态度鲜明的无产阶级战歌。昂扬乐观的诗歌格调昭示着白色恐怖非但没有动摇作者的革命决心,反而使其更加清晰坚定。
基于以上背景,郭沫若以黄河为叙事对象的战争诗歌的创作绝不是偶然。它的必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写黄河的必然和写战争的必然。郭沫若与黄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23年,他在《创造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热烈不羁地呼号目前的文学事业要先从破坏做起,要爆发出生命中潜藏的最热的力去反抗,提起全部的精神向黄河扬子江一样的文学奋斗。这里的“黄河文学”实际上指的是像黄河一样具有冲击力和破坏力、融合西方文化后全新的中国文学,而黄河文学蕴含着丰富的黄河文化。郭沫若之所以能够发现黄河,并把黄河作为表情达意的对象,深层原因在于他无形中受到黄河文化的影响。确切地说,郭沫若继承了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黄河文化。季羡林阐述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时,曾强调文化必然依托国家,因此文化与国家成为同义词,并认为爱国主义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般的是爱我的国家,高层次的是爱我们的文化[7]。这样看来,郭沫若的爱国主义基于中国传统文化,黄河文化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祖国和文化的热爱促使他以黄河为对象进行诗歌创作。正如他1923年的宣言,“我们要把固有的创造精神恢复,我们要研究古代的精华,吸收古人的遗产,以期继往而开来。”[8]可见郭沫若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这一点在其浓重的历史研究情结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例如仰韶文化研究。
郭沫若高涨的革命情绪促使其聚焦战争中的黄河,这种情绪与他独特的个性密不可分。从两首诗歌的内容来看,他在《前茅》与《恢复》时期的革命热情,仍然带有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色彩,虽然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动,情绪时有悲抑的气味,但总体上保持了高昂的基调。尽管1926年郭沫若明确声称,对于反革命的浪漫主义文艺要采取彻底反抗的态度,并主张“凡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而且同时是反抗浪漫主义的便是革命文学”[9]41,但革命诗歌《黄河与扬子江对话》《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实际上延续了五四时期郭沫若在《女神》中展现出的浪漫主义精神,只不过他思想观念的转变使统摄全诗的方向由宣扬“自我”转向了赞扬革命。也就是说诗人追求理想、自然流露情感的个性,标示着这一时期的诗歌并未完全褪去浪漫主义色彩。这种个性结合革命后,“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10]变成“快起!起!起!/快在这二十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别演一场新剧!”[11]314洋溢着理想主义的革命激情。当然,倾泻直下的冲动和热情并非一成不变。经历大革命失败,郭沫若开始沉静理性地思考革命,尽管革命态度仍然积极,诗歌总体的基调也保持着惯有的高昂奋进,但不免“气魄不雄厚,而有时更带着浓厚的悲抑气味”[9]221。不可遏制地急呼革命,冲破一切诉说理想的情绪已然被苦闷中寻找希望,进而坚定立场和理想的情感取代。
这两首革命性质的诗歌将黄河与扬子江拟人化,以对话体的形式呼唤反抗和革命,它们表现战争时有很多相同之处。一方面,两首都立足时代,全面记录了战争场景,是流动着个人情绪的“战争史”。郭沫若敏锐把握现实的能力,以及爱国主义的情绪,使其融入战争,切实地感受战争,这样的诗歌能够基于战争史实凝聚出尖锐的美感,一并把读者拉回战争的现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流血的历史。”[11]3111923年,百姓因军阀的恶行受难,这种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有一群害怕流血、不愿行动的“畸形儿”竟然“向那‘毒菌’求怜”[11]312。黄河的哀怜和愤怒显示出郭沫若内心的积郁,他借扬子江之口大声疾呼:“把那‘菌队’们扫除得干干净净,然后才有希望!”[11]312并且迫切地要“把他们的迷梦唤醒”[11]313。郭沫若以激越的情感对军阀进行控诉,处处传达彻底革命的心愿。到了1928年,百姓不仅受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内新军阀的压迫统治,而且遭遇国外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为了“开拓殖民地方”[11]383,身为宝藏的中国“成了榨取的屠场”[11]383。郭沫若主张建立国际工农联盟,坚定地认为“联盟的主体”绝对不能是“新旧军阀”,或者阶级利益不同的“全民”。
另一方面,这两首诗既概括地展现出战争背景下百姓受难的状况,又作为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出战争引发了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中,宽广的黄河充满了血液,血色的黄河目睹了流血的战争,哀怜着人民乃至民族遭遇的苦难。而人民在饱受痛苦之后,“只剩得些清淡的眼泪在流”[11]310。这里,郭沫若运用“黄土之后”“洞庭湖”“鄱阳湖”等多个地理名称来诠释流血的深度和广度,展示战争的残暴性质以及民众的生命状况。其后通过叙述人民的血被战争吸完,连哀嚎也发不出,只能流下个人生命中最后的眼泪这一生存悲剧,揭示他们痛苦的精神状态。《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描写了更加复杂的多方混战,人民受到的压迫也更多。黄河的血液“更染红了一点”,黄河以人的语气抒发的情感不再是单一的悲悯,而是加入了看到人民“自相屠杀”的愤恨。与此同时,人民的生存苦难不仅来自随时失去生命,还有“重重的经济压迫”,是政治与经济共同导致的社会问题。
我们面对这样两首革命意味浓厚的诗歌,可以看到它们在诗歌艺术、写作手法上的局限。重叙述、重情绪使得诗歌成为大篇幅故事性的抒情诗,为了让诗歌发挥“时代传声筒”的宣传作用,不免出现“呐喊的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呼声”[12],从而落下口号化、标语化的弊病,内里的诗韵和诗意也大大折损。不过这些创作与当时郭沫若的心境是吻合的。正如他本人所言:“我要充分地写出些为高雅文士所不喜欢的粗暴的口号和标语,我高兴做‘标语人’‘口号人’。”[9]221郭沫若不能自已地悲痛着人民的苦难,从而乐意在众声低回的年代做一个“喧哗者”。他的革命诗歌不仅揭露出民众苦难的生活,而且鼓舞着人民反抗非正义的战争。
三、忧郁的黄河之歌
苦难是艾青个人生命中难以抛开的存在,它向这位歌者的吟咏贡献了凝重和博大,也促成了他忧郁的天性。艾青前期诗作中以“我”的体验、“我”的姿态生发出的苦难,指向的却是民族和国家。这使得艾青在战争环境下迅速抓住了“悲哀”的情绪,唱出生存于中国土地上的人民的苦痛,其真实地写诗的信仰,让流淌在诗歌中的凄切的声音,得以直击读者心灵深处。正如胡风所说:“他是抗战前就引起了读者注意的诗人。抗战一开始,他是最快地唱出了战歌的诗人之一。……诗人对古国的黑暗和冷酷有深刻的感受,他唱的挽歌是非常深沉的。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同情,他描述的穷人的形象,是使人禁不住感到伤痛的。”[13]
初版于1939年的诗集《北方》,是抗战全面爆发时艾青怀着投身战争的愿望,北上途中所作。初入北方,个体与民族未卜的命运,使得艾青身上时时缠绕着悲怆的情绪。当“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叹息“北方是悲哀的”时,适逢艾青行至潼关看到黄河,他猛然将难以抓取的自我与民族的苦难融为一体,不可抑制地作出诗歌《北方》。面对战火下的黄河,身为漂泊者的艾青,在黄河岸边的风陵渡,写下《手推车》和《风陵渡》。艾青深广的胸怀意味着他不仅仅着眼于时代话语下个体的普遍生存状况,黄河流域民生的艰难,也促使他将目光凝聚在悲苦的个体上,具体地关注相同的苦难下不同身份个体所用的不同谋生方式,如《乞丐》。
《北方》围绕苦难展开,战争带来的深重苦难触发了沉积在艾青生命深处的忧郁情绪。他的忧郁萌生于童年时代,始终扎根于民族土地,抗战时期从对个人命运的无力出发,又不断超越,直至跳出个人遭遇的范围,迈入对战争年代人民境遇的同情,这种忧郁最终落在对光明的执著,以及对扫除苦难的力的期盼上。艾青在“自己也不愿意竟会如此深深地浸染上了土地的忧郁”[14]的情况下,却自觉地为战斗和人民献身。因而他能够联结起自我、社会与时代,也成功完成了大众化、写实化的诗歌实践。在以上所述诗歌中,黄河构建起诗人与苦难、人民与苦难的关联,也因此被赋予了双重身份,它既是苦难的施加者,又是苦难的感受者。
于诗人而言,时代浪潮如同险恶的黄河浪,给“我们”带来苦难。宏大的民族危机面前,个体只能将自身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顺应时代作出选择,再从中寻求某种共鸣。因此,民族命运的曲折同时意味着个体命运的坎坷,也就是,诗人在时代变化的前提下,发出了心灵和生命无处归属的喟叹。在《风陵渡》中,艾青透露出叩问命运后交织着茫然、孤苦的复杂心境,借助险恶的黄河,深化为宿命下的不安:“听呵/那野性的叫喊/它没有一刻不想扯碎我们的渡船/和鲸吞我们的生命。”[15]14艾青在战争前线目睹了北方人民苦难的情状,初期积极和高昂的抗战情绪开始走向深沉和忧郁,他用“黄河的浪”象征时代的浪潮,从“险恶”“扯碎”“鲸吞”可以看出战争带给艾青的直观感受。艾青通过细致地书写黄河这一客观对象,呈现出“我们”面对黄河时无助的情景,同时传达着个体在时代面前的渺小。诗中第二、三节以叙述者“我们”的视角,叙述乘坐“古旧的渡船”过黄河的事件,“我们”意指“我”与大众,表明艾青的诗歌中逐渐汇入社会和时代要求的大众。如果看向大众诗歌之后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我们”直接指大众,因为“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新诗歌·发刊诗》)。
于人民而言,黄河虽然“倾泻着灾难与不幸”[15]11,但也感受着“北国人民的悲哀”[15]29。黄河镶嵌在土地上,滚滚的黄河水滋润着土地,“黄河”与“土地”共同刻写着中华民族生存的痕迹,当它成为历史的脚印时,就清晰地显示出黄河奔流过的北方大地升腾过辉煌,也领受过苦难。艾青赋予“黄河”“土地”“北方”“手推车”等客观存在物以丰富的情感和时代特质,并使它们成为凝聚着“苦难”的意象,同时这些意象蕴含着诗人忧患民族、执著追求光明的情感。
诗歌《北方》中,艾青用“北方是悲哀的”[15]9慨叹,引入两个发出苦难的意象——沙漠风和黄河。艾青采取隐去战争暴力书写,专注具体存在物描写的方法来表现苦难。受难对象不再局限于人,而是向外扩充为人与自然。当艾青把一切物的受难看作一个整体时,他自然而然地会跳出浮泛的政治呐喊和阶级斗争,回归受难本身,这也造就了其诗歌的博大意境。全诗第一节展现了苦难从“来”至“留”的完整过程。“沙漠风”呼啸着带给“原野”“行人”“驴子”“雁群”苦难,这一系列存在物有着相同的情绪,艾青分别用“忧郁”“困苦”“悲哀”“不安与悲苦”表达。可以看出,景、人以及物流露出的忧郁情绪与艾青的情感是一致的,那么诗人和书写对象就构建了一种互通共融的关联性。这决定了艾青的同情不是源自自上而下的俯视式观察,而是产生于自觉地切身感受。除此之外,艾青宽广的胸怀赋予了他以广阔的视野看事物的能力。第一节的苦难书写秉着“由远及近”,再“由近至远”的顺序。艾青首先站在高处远望并从广角摄入荒凉的景象,接下来迅速回缩视角,目光重新聚焦在近处的实景,其后他再次慢慢拉远视线,将重点放置在与近景连通的远景上,从而构成了一幅全面又无断裂感的苦难画面。第二节“万里的黄河”呼应上一节的“沙漠风”,总述长期灾难带来的结果是“贫穷与饥饿”。第三节以“我”之口连呼两个“我爱”,其姿态从悲痛地匍匐转换为崇敬地肃立,崇敬的原因是“我看见”祖先在“荒漠”中生活的情形,他们的繁荣在于顽强地和“自然相搏斗”,在于不屈地“保卫土地”。艾青试图通过追忆历史并进行反思的形式,打通古今之间的道路。他要传达的不单是自身向往光明和希望的情绪,更重要的是他意在坚定人民的生存信念,唤起现今民族抗争的信心。整体上看,经过艾青的笔,黄河流域的土地不再是简单存在的“物象”,而是融入丰富情感后具有生命力的“意象”。作为贯穿全诗的意象,“土地”集中凝聚着艾青的独特感受,它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每一种形态都与苦难紧密相连。艾青以“农民之子”的身份悲哀着贫瘠的“大地”,同时敬重着“埋有我们祖先的骸骨”的“土地”,由此形成了对继承“遗留”土地且深受战争侵害的人民,既爱又痛的矛盾情感,从中可以嗅出艾青基于同情生发出的抗争意识。在艾青热望的斗争之心背后,强烈的现实关怀逐渐上升至对“国土”的赤子之爱,“土地”最终融入艾青的国家和民族情怀,成为其诉说希望的灵魂归宿。我们从诗歌《北方》中可以窥见“那是怎样一种博大深厚的感情,怎样一颗火热的心在消溶着牺牲和痛苦的经验,而维系着诗人向上的力量”[16]。
《手推车》和《乞丐》中,黄河成为人民苦难的感受者。在“黄河流过的地域”以及“黄河的两岸”,艾青捕捉一件物、一个人,间接地展现出北方农民在战争年代的艰苦。他谈到《手推车》时曾说:“凡尔哈伦写农村的破落与城市的触角,启发了我写黄河流域日益增长的苦难。”[17]诚然,凡尔哈伦诗中多次出现的手推车题材给了艾青创作的灵感,但艾青将“手推车”塑造成了“更中国的”且有象征意味的意象。手推车具备的“唯一”“单独”轮子的外形,与北方农民流离失所、孤苦无依的现实状况达成了直接联系,而“发出使阴暗的天空痉挛的尖音”[15]29和“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15]30都表明土地承担着手推车过载的负重,手推车装载的生命重压一面刺向天空,一面埋入大地,其背后是人民试图狂喊的悲凄,以及不得不垂下头颅忍受苦难的无奈。这两点从整体上丰富了手推车的内涵,使其展示出一幅浓缩着“北国人民的悲哀”[15]30的生存图景,并成为象征着贫困和艰难的意象。此外,艾青摄取了战争时代的一角,速画出黄河两岸饥饿的乞丐求乞的场景,将乞丐的苦难形象细致地印入《乞丐》。来自灾区和战地的乞丐因为可怕的饥饿选择了乞讨的生存方式,苦难不会由于他们年老或年幼而变得仁慈,战争让他们呈现出相似的受难形象。艾青扣住听觉、视觉、动作这三方面,从乞丐“最使人厌烦的声音”“固执的眼”“永不缩回的手”着手,勾画出他们共有的麻木。
总之,中国是大河文明之国,黄河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孕育了民族文化,滋养了文学。自古以来黄河便与文学紧密相连,诗人将奔腾不断的黄河纳入诗歌史,赋予它多重意蕴。滥觞于先秦时期的黄河歌咏,在现代以新的姿态登上文坛。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下,源自自然与战争的苦难,将人置于艰难的生存状态中。黄河两岸的人民含着血与泪咀嚼着苦难,而诗人感受着大地之上时时回响的悲诉,吟咏出一首首苦难之歌。